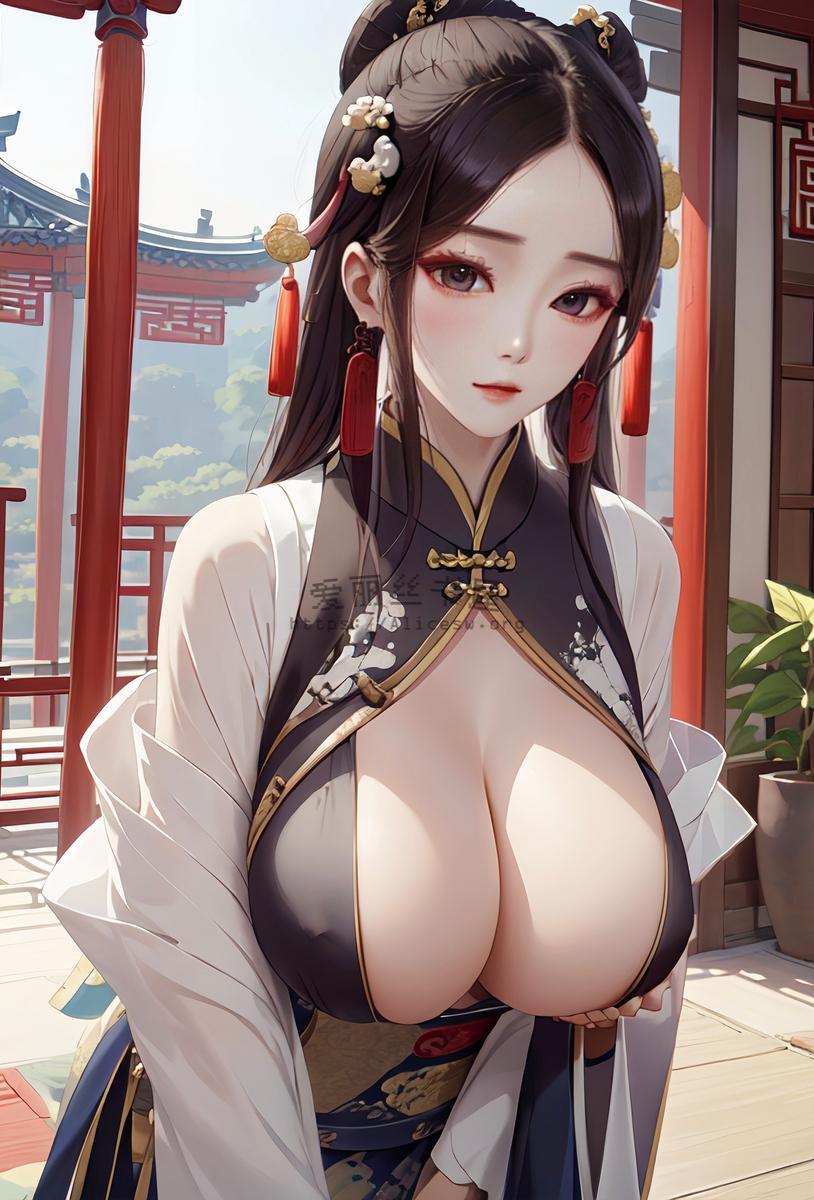鐵牛早上出去,原本是打算犁地的,可打秀芹家院門口經過時,正逢著秀芹端一盆潲水出來倒,見了夢中的人兒吆著牛兒過來,一時眉開眼笑,叫起來:“啊喲!鐵牛,昨黑里雨才歇下,你就開工了?”
“是哩!是哩!早開工早歇活……”鐵牛衝著她憨憨地笑,那牲口卻跟女人相熟,喝勒也喝勒不住,拖了鏵犁直往前走。
到了跟前,女人順手牽了牛鼻子便往院子里拉,急的鐵牛直嚷:“俺犁地哩!犁地哩!”
“就知曉犁你家那穴地!俺這穴地荒了一冬,也不見你來犁!”秀芹格格地笑著,將牛拴到院中碗大的椿樹山,拉了鐵牛便往屋里走。
“不敢哩!不敢哩!娃娃都懂事了……”鐵牛嘴上咕嚨著,腳早踏進了門檻,孩子卻不在屋里,火上的沙罐“咕嘟嘟”地直冒熱氣。
“娃娃都到河邊去了,就俺一個,前日去鎮街上買了個豬蹄,才燉上,正巧被你趕上哩!”
秀芹朝灶上的沙罐努了努嘴,鐵牛果然聞到了一陣肉香吃肉還得等上一會,兩人關了里外兩道門進到房間里,一個干柴一個烈火,滾到了一堆。
鐵牛把將女人裹在身下,一張毛乎乎的臉埋在女人的脖頸間,大口大口咬她的鎖骨,舔她的喉嚨,還要親著她的嘴。
女人閉了眼翻滾,一張嘴巴卻死也不松開。
纏斗良久,舌頭竟不得門道而入,鐵牛便棄了口,一把抓了布衫下擺便往上掀,女人又牢牢地按著不給掀。
“說是犁地!又不讓犁?!”
鐵牛低吼著,懊惱地將衣裳抓在手里,往兩邊猛一分勁,“嚓嚓嚓”一片響,破舊的布衫便從中裂開,一直裂到鎖骨上,抖出那白花花的肚皮和兩只大奶來,晃的眼皮都睜不開了。
“這個野牛啊!野牛!”
秀芹驚慌,雙手交抱著護住了奶子。
說時遲,那時快,鐵牛早瞅了下方空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褲子褲衩一堆兒拉扯下來,一甩手扔到床頭上。
秀芹顫聲叫了一聲,兩條白生生的藕腿便蜷曲起來,緊緊地夾住了那團烏黑的毛叢。
鐵牛哼哼著,三兩下將身上的衣服剝了個精光,胯間的肉棒早已直挺挺地翹了。
他大口大口地喘著氣,冷靜地將手指搭在女人火熱的嘴唇上試探。
誰知秀芹竟張了口,含了粗硬的指骨吮咂,鐵牛受到了莫大的鼓舞,手也不抖顫了,靈活地在光滑的小肚子、豐腴的腿上、肥滿的屁股上游走、摩挲……
指骨上有咸津津的滋味,秀芹“吚吚嗚嗚”地吮著,另一只粗糙的手掌點燃了欲望的火,似乎每個毛孔都在呼吸,她的身體開始焚燒,大腿根也潮熱起來、猶豫著漸漸地松弛開了。
她摸到了,軟塌塌、皺巴巴的是卵蛋,粗大的、光柔的、堅硬的是肉棒,“俺要哩!俺要你的大雞巴哩!”
她握了男人的肉棒呢呢喃喃地呻喚。
鐵牛伸手抓住女人的腳脖子,將兩條白腿直拖到床沿上來,往上一提豎成個樹丫子,把眼往胯里一瞅,黑烏烏的毛叢下綻開了一溜粉亮的溝道。
“來哩!鐵牛……”秀芹乜斜著眼波,身子軟得像根面條似的癱在床上,破碎的布條扭結在脖頸間,鼓凸凸的乳房驕傲地挺立在胸脯上,“姐姐癢呐!你要讓俺癢死了才好?”
她等不及,伸手來抓。
鐵牛深吸一口大氣,立定腳跟,將兩條腿扛在肩頭上,屁股對准那口兒猛地一撞,“噼噗”一聲響,干的女人“啊呀”一聲怪叫,長甩甩的肉棒便沒入了溫暖的泥沼里,影兒也尋不見一分。
穴里早已經汪洋一片,肥厚的皮肉立時重新聚攏來,緊緊地裹纏了肉棒,裹得渾身的血液急速地奔流,鐵牛迫不及待地抽了十幾個來回,那膣道便出奇地滑溜起來。
秀芹眉心結成了一塊,鼻孔往外呼呼地噴氣,扭扭蠻腰擺正了肉穴,兩只手各抓一個奶子拉扯著、揉搓著,肥肥白白的屁股一下一下地迎湊過來,嘴里便“嗯嗯哦哦”地呻喚開來。
一開干,鐵牛便粗魯得像頭野牛,撞得女人的屁股“啪嗒啪嗒”地響,撞得身下的床架子也“吱嘎吱嘎”地搖,“荒了一冬……還給俺犁不?給俺犁不?”
他的聲音粗啞,似悶雷似鼓點一樣轟擊著女人的耳膜。
“你犁!你犁!犁爛俺的騷逼,犁爛了才好咧!”
秀芹浪叫聲聲,半個身子在床面上垂死地扭動、翻滾,穴里的肉棒如一根石杵舂在碓窩里,越舂越快,越舂越快……
舂得她氣都快回不過來了,“緩些哩!緩些……逼就要……要被你衝壞衝穿了啊!”
她又止不住哀求道。
鐵牛正在興頭上,偏不聽,沒頭沒腦地衝撞不休。
不大一會,也不知是天突然變熱了還是怎地,豆子大的汗珠從額頭上滾落而下,手中的腳踝也滑唧唧地快把握不牢了。
就在這檔兒,秀芹口中“咯咯”作響,垂死般地嚷叫:“嗚哇哇!俺受不下了,要死哩!要死哩!”
雙腳一蹦從肩頭上蹦落,頭向後抻直頂了床面,身板兒挺地直直的,使勁兒地抓扯了高高凸凸的奶子,屁股一陣陣地抖顫起來。
命根子被緊緊地夾纏著動彈不得,鐵牛連忙咬緊牙關,抖擻起精神來狠狠地抽,狠狠地插,夠快夠深,才幾十來下工夫,女人僵死的身子突然活轉來,雙手放開了奶子,發了羊癲瘋一樣地抽搐著……
肉棒像有只手緊緊地攥住,抽不離推不進,鐵牛一著急,一股氣流突突地躥上來,腰眼里一麻,“嗷嗷”地叫喊著激射而出。
幾乎同時,秀芹猛地掙起上棒身來,死死地摟了鐵牛,底下一通急速地蠕動,隨著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聲過去,一潑濃熱的汁液兜頭澆下,燙得鐵牛一哆嗦,雙膝一軟栽倒在了女人的身上,女人栽倒了床上……
豬蹄早燉得稀爛了,秀芹湯湯水水地舀了滿滿一碗端給鐵牛。
鐵牛出了一身汗,肚里正“咕咕”地唱空城計,接過來也不怕燙,一仰脖子像喝酒那樣“嗬咯咯”地喝見了底,“真香咧!放點蔥末就更好了……”他咂咂嘴皮將空碗遞給翠芬,秀芹又舀了一碗給他,自己卻不吃,取了梳子鏡子來在窗眼下梳理亂蓬了的頭發。
鐵牛一連喝了三大海碗,又去撈起骨頭來歪了嘴啃,油水涌上來打了幾個飽嗝兒,才想起女人還餓著肚子的,“你咋不吃呢?”他問道。
秀芹忙推脫說犯胃病,鐵牛忙問疼得厲害不,秀芹笑了笑說:“常犯的小毛病,過一會就好的,只是不能喝油湯,油燙你全喝了啊,俺下老鴰頭吃。”
“那怎麼行?!俺給你留一碗!”
鐵牛端起沙罐來倒,卻倒得出半碗,便尷尬地搖了搖頭:“俺這嘴賤,一吃起來就歇不住,你還是下老鴰頭吧!”
他知道老鴰頭的做法:將麥面摻水和一和,甩在沸水里滾起來就好。
秀芹梳妝完就開始和面,鐵牛跑到茅廁去痛快了一通回來,卻發現兩個孩子從河邊回來了,正在院牆下一人端一只碗吃那老鴰頭,走進去一看,碗底漾著淺淺的肉湯,想是從那半碗均勻分出來的。
奇怪的是,兩個孩子卻不把燙先喝了,而是盯了對方碗里的老鴰頭數,一個、兩個、三個……
數完了對方碗里又來數自己碗里的,數目卻不相等,便爭執起來。
鐵牛鼻頭一酸,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進屋來訓斥著秀芹說:“秀芹啊,你這是把俺當豬哩?把好的都給俺吃完了,娃娃沒得吃,你是讓俺得噎死病哩?!”
秀芹的手哆嗦著,臉色十分難看,眼睛皮一擠,眼淚珠子“啪啪”地往下掉:“統共就一個豬蹄,你叫俺咋分嘛?咋分得過來嘛?”
“那也不能讓娃娃餓著呀!俺都成罪人哩!”
金狗氣衝衝地出來,往院子里的牆根腳一坐,候著兩個孩子吃完了,拉起髒乎乎的小手就往外走:“走!叔叔給你們弄肉吃吃!”
兩個孩子一聽有肉吃,歡天喜地跟著他來到河邊,鐵牛就甩了鞋去掀淹在水里的那一片石頭,發狠似的翻,翻起來一個又一個,除了綠色的青苔什麼也沒有。
小時候是有的呀!
鐵牛傻了眼,他嘴笨,不知道給孩子們說些什麼安慰話,只問:“愛吃螃蟹嗎?!”
“愛吃!”兩個孩子齊刷刷地回答,末了又眨巴著眼睛問:“螃蟹是啥?”
“螃蟹是肉!頂好頂好的肉!”鐵牛看著孩子純真的髒臉,眼淚就快包不住了,撅了屁股又掀石頭,弄得一身是水一頭是汗。
兩孩子跟在後頭,眼看著鐵牛翻過去一槽又一槽,卻一無所獲,倒累的“呼呼”地牛喘,便叫:“鐵牛叔叔,你歇歇呀!俺們不吃肉了!”
“只要你們愛吃!叔就弄給你們吃,俺有力氣,能捉好多的哩!”
鐵牛拍打著胸口,“咚咚”地響,兩個孩子就“嗚嗚”地哭起來,鐵牛只得生硬地笑了笑:“你們一哭,俺就抓不著螃蟹哩!得笑,得喊'加油','加油'……這樣子!”
一個孩子便抹了一手背的眼淚,怯怯地叫一句:“鐵牛叔叔,加油……”
鐵牛贊賞地點點頭,彎下腰去“嗨嗬”一聲吼喊,掀起一個兩百斤重的石頭來,下面果然有兩只成年的螃蟹在約會,一把抓去,被鋒利的鉗子夾了手指頭,大喊大叫地在水窪里跳躍起來,逗得兩個孩子哈哈地破泣為笑了。
“叔叔沒記錯,說有就有的嘛!”
鐵牛擰著兩只螃蟹朝孩子們甩過去,指頭上滲出血來順著指尖淌,滴在河水里漫開了一朵朵漂亮的小花,他心里卻無比高興,忙在衣角上撕下一溜布條來包扎了,勝利地衝著孩子們揮揮手:“只要叔叔一抬石頭,你們就齊聲喊加油!”
實時似乎在證明,這樣做能給他帶來好運氣。
兩只螃蟹還是活著的,橫著在卵石間亂撞,兩個孩子遠遠地丟石塊砸它們的頭,直到死了不動才罷手。
在孩子們的加油聲里,鐵牛的力氣更大了,沿著河岸一路翻下去,翻得太陽都落山了,總算搞到了十幾只大小不一的。
鐵牛洗淨了手腳,脫了上衣將捉來的螃蟹籠在一處,在兩個孩子的簇擁下凱旋而歸了。
到了門口,看到拴在椿樹上的牛,才連連叫苦今兒可把犁地的活給耽誤了哩!
不過再看看兩個孩子的笑,值!
秀芹雖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還是煮好了飯等鐵牛和孩子們歸來,一見到孩子們歡歡喜喜地纏著鐵牛,一時想起了丈夫還在世的日子,那時候是多麼幸福啊!
偷偷跑到房間里抹了眼淚才出來。
“娃娃些,知曉這是甚東西不?”
她指著這些在衣服上四下的亂爬的東西問孩子,孩子齊刷刷地叫:“螃蟹!”
叫的她心花齊放,多少年都沒這般開心過了,簡直比過年還要開心一萬倍哩!
鐵牛自然也很得意,可在怎樣吃的問題上卻犯了難,要炒要炸,又太費油!
秀芹終歸是女人家,麻利地刷洗了鐵鍋架起蒸籠來蒸,當滿屋都彌漫了那奇特的香味的時候,悄悄從櫃子里翻了瓶子酒出來倒給鐵牛喝。
當月光像水銀一樣流瀉到院子里的時候,螃蟹出籠了,在昏黃的燈光下、在孩子們期盼的眼神里端上了桌,滿滿的老大一盤,冒著騰騰的熱氣,筷子插穿一個一扒拉,白白嫩嫩的蟹肉還沒到口里,口水先就滴滴答答地流了。
鐵牛這回學了乖巧,陪著她娘兒三個吃了一個,就再也不動筷子了,一個勁地往嘴里灌酒,酒精發著起來,又一個勁地呵呵地笑。
趕了牛兒出來,鐵牛腳步已飄飄地踩踏不實在了。
秀芹默默地跟在後頭,一直送他到了家門口,分手的時候,鐵牛突地轉身將她摟在懷里,酒氣兒嗆得她直躲閃:“干嘛哩!干嘛哩!你婆姨出來瞧見了!”
“你就是俺婆姨!你是俺婆姨才好哩!”
鐵牛手舞足蹈地嚷,秀芹見他在說醉話,忙捂了他的嘴連推帶搡地將他推到了院門里,轉身一路小跑著回來,止不住就“嚶嚶”地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