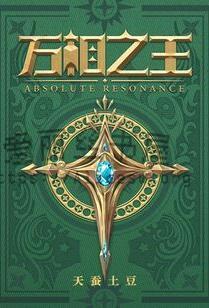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原創】前塵
【原創】前塵
序、
古時有一山,名曰清霄,山上終日為煙雲籠蓋,僻靜出塵,有世外仙境之貌。後有江湖大能游歷至此,深為此景所服,於是長居於此,以山為號,稱之清霄散人。
清霄散人者,甚惠也,以山巒溪流為鑒,修養身心,竟悟出絕頂內家心法,喚之“明霄功”。又依世道循環之理,悟出一門借力打力,後發制人的挪移之法,名之“接玉掌”。
然,散人心系天下,願以一身本事助世間太平,因而建上行宮,曰清霄宮,擇聰慧而又剛正者傾囊相授,傳下衣缽。
清霄宮傳人謹遵師祖教誨,明察善惡,為世人稱道,尊其“三上派”之首。
卻說這一載,清霄宮傳至第四代,為一年青女子受宮主之位,號之玉霄。
玉霄者,出行必以紗掩面,江湖中只知其貌美,而鮮有人見其真容。
曾有登徒子欺其一屆女流,欲要揭開面紗一探究竟,卻為其打斷雙手。
原來,其“明霄功”已練至第七層,內勁深厚,當世已鮮有對手。
由此,江湖中人提及這“玉霄宮主”時,除卻敬重,更多有懼意。所幸她性情正直,能辨善惡,多行俠義之舉,倒也不至人人自危。
玉霄宮主座下多有門徒,親傳者卻止一人,名之風青,乃河北風氏少子。
這河北風氏長居罡嵐劍莊,多有接濟江湖,亦是俠義之輩。
可這風青卻不然。
此人雖天資聰穎,飽讀風氏藏書,為玉霄宮主所擇,傾囊相授,然心術不正,喜修邪術,又性情好色,多有沾花惹草。
所幸玉霄宮主察其本性,未將明霄功授之,為時尚未晚矣。後又將其逐出山門,驅至蠻夷蟲瘴之地,生死未卜,方才罷休。
經此一事,玉霄宮主再無授業之興,乃禪掌門之位,退居宮內,潛心修行,不問江湖之事。
一、
這日,有一身著獸衣,口誦蠻夷歌謠,作夷人打扮的青年來到清霄山下。山下農夫長居於此,哪見過這般怪異模樣,皆以為是惡鬼所化,紛紛避之。
青年對此並無在意,徑自尋至村舍,與那村頭乘涼閒漢問起路來,一開口,竟是一口流利官話:“老鄉,我聽聞山中有仙子月宮,欲尋其拜之,敢問是否屬實?”
那閒漢倒是於鎮上說書先生處聽聞過夷人之事,只是卻沒想到夷人能將官話說得如此自然,一時呆愣,沒有回應。
夷人青年見他遲疑,卻是會錯了意,以為禮數未盡,又自懷中取出銀錢,交至閒漢手中,笑道:“一些銀兩,不成謝意,老鄉但說無妨。”
那閒漢平日也就經些小本生意,哪見過這麼多銀兩,當即回過神來,說道:“先生多禮了。只是這山上哪有什麼仙子月宮啊,不過是閒人言語夸大罷了。”
“哦?此話怎講。”
“先生不知,這山名叫清霄山,山上有個清霄宮,據說是多年前江湖中人所建,為江湖一大門派。現在這清霄宮傳至第四代掌門,好像叫什麼······玉霄什麼的來著。”閒漢搖起手中破扇,緩道,“聽說那掌門武功高強,有踏風御劍的本事,又飄然出世,不以真面目示人。於是便有閒人稱其仙子,夸大其談。”
“原來如此。只是我既已至此,舟車勞頓,若不上山見上一見,實難接受。敢問老鄉可否指點一條上山之道?”
那夷人言語中雖有沮喪之意,可閒人細觀神色,卻見其微露喜色,似是別有它意。
閒漢正思索著,又轉念一想,自己既收其錢財,便無須多慮。更何況,揣度人心本就非己一閒漢所善,何必徒增困擾。
打定主意,那閒漢於是點點頭,笑道:“上山之路倒也不難,你且緣那山間小道上山,至山中見一青石門戶,與那看守講明來意,自會有人領你前往。”
閒漢語畢,又憶起一件大事,補充道:“只是,聽聞前些年,這清霄宮中有一弟子心術不正,為掌門所逐,遁入蠻夷蟲瘴之地。自那日起,這清霄宮便對夷人多有防備,先生此行,怕是多有困難。”
“哈哈哈,有勞老鄉費心了,若真不得見,我自會退去。”夷人青年大笑,又取出一貫銅錢,賞與那閒漢,躬身謝過,回身離去。
——————————————————————————————————
卻說那夷人青年別了村中閒漢,緣道上山,不多時,便見一山門立於道前。恰逢山中林霧漸起,那青石門戶隱於雲霧間,倒真有幾分天境仙宮模樣。
青年既能看清山門模樣,那守山弟子自然也能看清他模樣,當即便是一聲厲喝:“站住!爾等夷人,來此所為何事?”
守山弟子言語中已露不悅之情,可青年卻是恍若未聞,足底生風,不多時便行至那守山弟子跟前。
“一介閒人,聽聞此地有仙子月宮,特來拜之。”直至此時,青年才握拳行禮,講明來意。
“爾可知我清霄宮不迎蠻夷之客?”夷人能這般言官話,本已怪異至極,更兼來者舉止囂張。守山弟子於是更露不善之意,一手握住腰間寶劍,欲要以武相逼,下逐客令。
“知曉。”然而不知那青年是遲鈍還是有它,見此威脅之舉,仍只淡笑,毫無怯意。
“那爾還不快快退去?我可不願我這寶劍染爾之血。”
怎曾想,那青年見此景象,竟是大笑:“朝弦,你不過是玉霄的貼身侍女,得那婆娘指點,方有門徒之名,怎得如此傲慢,不由分說便動起粗來?”
聽他道出自己姓名,那名為朝弦的守山弟子當即一愣,繼而拔出寶劍,以劍鋒指那夷人,厲聲問道:“爾究竟是何人!”
“算來,你還得稱我一聲師兄才是。”那夷人青年以手拂面,刮下一層薄皮來。
見那青年真實模樣,朝弦登時大驚,也不言語,舉劍便刺,便欲將青年就地斬殺。
然而這劍卻刺了個空,只見青年微側身軀,將劍鋒避過,而後以二指夾其劍身,運力一震,竟將寶劍震得脫手,跌落於地。
只此一回合,二者便是高下立判。可那朝弦卻不死心,又運內息,連攻數掌,皆為青年輕松化去。
這朝弦倒也果斷,見果真不敵,竟是側身一滾,拾起寶劍,便欲自刎!
然而這劍抵至脖頸,卻終究未能斫下。原來,那青年先其一步,以點穴手法封其穴道,令其無從動彈。
“自刎以警宮中,倒的確是個妙策。等那換班弟子前來,不見你蹤影,定會稟報宮中,令宮中人有所防備。只可惜,還是慢了一步。”青年仍是那副悠哉模樣,一語道出她心中所想。
“風青,爾這賊子,心術不正,為尊主所逐,竟還敢回來!”他並未奪其言語之能,因而她自是開口便罵,“爾若有種,便在此殺了我,到時尊主駕臨,定要讓你粉身碎骨!”
“嚯?想不到脾氣倒挺烈。”聽此威脅,風青反倒生出興致,伸手拂過朝弦俏臉,“只是,你還別有用處,若只是殺你,未免太失情趣了。”
她還想要說些什麼,卻為他先一步點下穴道,強行制止。
只見他湊上前來,依朝弦耳邊,低聲道:“你既能想出尋死之策,想必是知我本事。那這河北風氏深藏之秘,便請你試上一試。”
見他如此,朝弦面露驚恐之色,只是苦於穴道受制,無從動彈,乃至無從呼喊。
“何必這般驚慌,放寬心來,且看我目中光彩~”
他聲音陡然變得柔和,如風般輕逸,又別具迷心攝魂之意。
朝弦雖奮力與之對抗,卻並無成效,慌亂間無意與其雙目對視,登時感到天旋地轉。
在那黑目中,仿佛有無窮絢麗的光彩,又仿佛只有深沉噬人的混沌,令她無法移開視线,而那靡靡之音則好似一只大手,不住將其推入其中。她無從反抗,只得任由黑暗將己吞噬,將自我撕碎、融解。
只聽哐當一聲,寶劍自朝弦手中滑落,復墜於地。緊接著,其雙手亦垂落,嬌軀失力,竟是雙膝一軟,跪坐於地。
風青扶起朝弦額頭,只見一雙美目呆滯停駐,光彩全無,一派痴相,哪還有先前那般靈動。
“甚好,這不傳之秘既有這般效力,那便可堪一用。”
他順勢俯下身,在朝弦額頭親上一口:“你可還有求死之念?”
這問話自是無從得到回復,少女仍是那副痴傻模樣,好似木偶。
身為玉霄宮主貼身侍女,她自不可能是歪瓜裂棗之輩,盡管情感缺失使這俏臉少了幾分靈動,但仍無法掩蓋少女那上上之姿。
只是此時,風青卻未有享受之意。他輕點少女額頭,交代起需其所做之事來:
“你至此,可為這般······,若聞此言,則可這般應答······”
——————————————————————————————————
這清霄宮既能被閒人傳為月宮,自是宏偉異常,而既為卸任掌門,玉霄宮主修行之處更是金碧輝煌。
卻見那首座之上,有一麗人,盤膝而坐,調理內息,運轉周天。
麗人身著一襲紗衣,上有明珠暖玉點綴,光彩照人,華美至極。
可那麗人容顏卻更勝一籌,嬌顏玉肌,柳眉纖腰,更別有出塵之相,竟反倒壓得華服黯淡失色。
這麗人自然便是玉霄宮主。
自那風青為其所逐,她便禪掌門位與師妹,退居幕後。避開凡塵俗世,她得以潛心修習內家心法,幾年間竟真有突破,更進一層。
話說這日,她一如往日,依法門運功,卻不知為何,愈感心悸,怎也靜不下心來。
難以言表的危難感不住涌上心來,令她不由得柳眉微顰。
恰在此時,貼身侍女朝弦入殿奉茶。於是她便問起朝弦:“今日山中可有異樣?”
“回尊主,未有接到通報。”朝弦深鞠一躬,回道。
不知為何,少女聲音雖與往日無異,但玉霄宮主卻總覺其中缺了幾分靈動。
她細細看去,卻完全尋不出半分異樣。反倒是朝弦被她這般注視,有些怯然:“尊主還有它事交代麼。”
“無它事,且退去罷。”
確認無果,玉霄宮主終究還是擺了擺手,令朝弦退去。
興許真是多慮了。
江湖中人聽聞清霄宮名號,懼之尚來不及,又怎會有人尋釁滋事。何況近年宮中戒備愈發森嚴,巡山弟子輪換頻繁,若有來犯者,她不多時便可知之。與其徒增煩憂,倒不如先品好茶。
這茶以上好茶葉輔高山清泉,更以妙法烹之,茶香四溢,只聞其味,便已令人神往。
若是往日,她那師妹,如今的清霄宮溯星宮主定當聞著茶香前來,與她飲上幾杯。
想至師妹,玉霄宮主一雙清冷美目中浮出些許柔和,唇角不自覺挑起一抹弧度。
她那師妹,性情活潑,又不拘小節,嬌嗔可愛,與她尤為親近。
只可惜,其既受掌門之位,忙於瑣事,鮮有機會休憩,更別提飲茶之事。她也只得對鏡獨飲,自尋逍遙。
飲畢,她不願荒了修習,又欲再試上一試。
這次反倒更是怪異,她方坐定,還未調動真氣,便突覺頭腦昏沉,無明倦意涌上心來,眼瞼不由得下垂,乃至全不可見。
玉霄宮主何等聰慧,立時便知那茶中有異,忙調內息以御。只是為時尚晚,她雖能護住本心,卻無從抵御軟筋之效,嬌軀一軟,竟直接癱於榻上。
待得她軟倒,門外立有足音響起。來者緩行至榻前,輕笑道:“想不到,武藝高強,內息深厚世間罕有的玉霄宮主,竟如此簡單便著了道,防人之心未免太過淡薄。”
這聲音玉霄宮主日夜間常有想起,切齒恨之,只剛聽見,便知曉了來者是誰。
——風青,她那最“得意”的“親傳弟子”!
來者仍在喋喋不休,他想是怨恨至極,此時竟是惡語不斷,將她貶得豬狗不如。
——只是他卻未有察覺,她的內息已有些許恢復運轉。
想來他定是不知,自己以內息守御本心,此刻意識仍舊清明。
只消以內息導之,她即可將所中之毒強行逼出。雖無法根除,但調用內息以將這豎子擊斃,卻是綽綽有余了。
玉霄宮主於心中辨明局勢,會真氣於掌間,趁來者不備,突以一掌印出。
這一掌打了個正著,傳出的卻是女子悶哼之聲。玉霄宮主心生不妙,竭力撐起眼簾,定睛細看,只見為她這掌所傷之人倚於牆邊,哪是那入邪弟子風青,竟是她那侍女朝弦!
也不知那朝弦是著了什麼邪法,此刻竟一語不發,受此重傷卻毫無動靜,簡直如一不知傷痛的偶人。
她正思緒大亂,卻見側邊轉入一青年男子,面帶邪笑,正是那風青。
“玉霄宮主,你看我這李代桃僵之策,善耶?”他譏諷道。
“豎子,拿命來!”
玉霄宮主本就厭惡其人,此時被他這般戲耍,登時怒火大盛,一聲大喝,運起內息,一掌直朝這賊子頭頂劈去。
風青側身躲過,運功回以一掌。玉霄宮主本欲施挪移之法,令其自討苦吃,卻在那掌風迫近時嗅得其中腥臭異常,於是堪堪避過。
見她避開,風青反倒有些驚訝:“想不到玉霄宮主這般機靈,竟能察覺我特意為你而修習的暗招。你若是接下我方才那掌,雖能挪移勁力,卻無從阻止毒效入體。”
說至一半,他又挑釁道:“只是,離了挪移之法的你,便如喪牙之犬,又有幾成實力?”
“爾試上一試,便可知之!”玉霄宮主也不多言,只加劇了掌上攻勢,內息傾瀉而出,一時間掌風竟有排山倒海之勢。
她此刻出掌只求殺之而後快,下得盡是死招,風青雖依仗奇詭身法,閃避迅捷,卻也只能堪堪化去,毫無還手之力。只此局勢來看,風青已落入下風,不時便會斃於掌下。
只是風青卻仍是成竹在胸,毫無怯意。
就這般糾纏了約有一炷香時辰,風青似有倦怠之意,足底腳步漸有遲滯,露出破綻來。玉霄宮主趁機出掌,直取風青要害,而風青此時已無處可避,只能任由掌風襲來。
“著。”
隨著風青一聲低喝,玉霄宮主突覺內息一滯,身軀不自主軟倒。盡管這遲滯只在刹那,於風青而言卻已足夠,只見他側身繞過玉霄宮主攻勢,迅速出指,點中其頸後大穴。
大穴受制,內息自然無從奔流,而內息停滯,跗骨之毒立時涌現,玉霄宮主只覺如有重錘擊頭,繼而意識漸行潰散,雙膝不由得一軟,跪於地面。
昏沉間,她聽得風青大笑:“我早已料到你察覺中毒,定會以內息將毒逼出,而後出手將我就地斃之,可你卻不知,我這蠻夷之地尋得的奇藥,逼出後仍有跗骨之效,可依我所好,隨時令中毒之人內息凝滯一瞬。只是,若要跗骨之毒生效,卻得中毒之人劇烈調動內息,方可激其藥力。因而我多有挑釁,所為便是引你出手。宮主內息深厚,我遠不能及,若不行此之策,我絕無任何還手機會。而若宮主選擇退走,我也無可奈何······”
在觸覺徹底消散前,她感到有一冰冷物什輕觸眉心。而後風青聲音繼續響起:
“但我知你性情,你對我欲殺之而後快,又極高傲,絕無遁走可能。可惜啊可惜,終究是我棋高一著。如今你護體真氣已散,已非百邪不侵之身,不如·······”
“放空心神,且來嘗嘗夷地傀儡之毒的功效·······”
他運起河北風氏深藏禁止的迷心攝魂之法,柔聲道,聲音好似穿堂妖風,直刺腦髓,又柔軟溫和,短痛後化作絲絲暖意。
她此刻失了真氣護體,又值深受毒效,更兼心神渙散,這妖言便如一口鳴鍾,不住在腦中回蕩,蕩得僅存心神紛紛碎裂。
到後半,她已無從分辨這妖言所說為何,又有何含義,只覺有陣陣暖意,令已破敗不堪的心神消融其中。
愈發空無······
空無······
無······
——————————————————————————————————
見麗人躺倒在地,不再動彈,風青這才松開一口氣,額頭迸出豆大汗珠。
這計策說來輕巧,可實施起來卻並無嘴上說的那麼容易。
僅在玉霄宮主這般絕世高手的全力攻勢下躲避,便已是極其困難之事,若非她不熟悉夷人身法,只一回合便可取他性命。方才他面上閒庭信步,以求激起其急攻之心,心中卻早已慌亂不止。只因一有閃失,他便會斃命當場。
再者,這傀儡之毒是否有效,玉霄宮主是否察覺朝弦異樣,皆是未知之數。他所能賭的只有那夷人奉己為尊之心屬實,未以仿品訛之,及自己交代朝弦之時交代得足夠詳盡。
所幸,最終的實施皆在掌握之中。他趁其衰弱混亂之際,以迷心之法化去她心防,而傀儡毒則蠶食心神,將之盡數融解。二者既成,則受術者再無神智,只依施術者號令行事,有若傀儡。
這便是他風青在蠻夷蟲瘴之地所得的“報恩”之策。為這傀儡毒,他還與那夷人三大氏族周旋數年,最終許引夷人入中土,共謀中原,行禍水東引之舉,方才得之。
憶起往昔他方入門之時,見玉霄宮主,驚為天人——他自生來便從未見過有如此美艷,更兼出塵之人。
自那時起,他便想將這麗人獨占,令其作婢奴之態。因而他於家中尋迷心攝魂之法,潛心修之,欲求大成。
只可惜還未有成,便為她所察,乃逐出山門,遁入蠻夷之地。只是也因禍得福,非但習了一身蠻夷武功,迷心之法亦是大成,還得了這傀儡毒相輔。
如今,也該當享用之時了。
這傀儡毒傷損心神,待得毒發,受術者心神潰散,雖有活人體征,卻對諸事皆無回應,便如斷线傀儡,與活死人無異,故有此名。然這河北風氏迷心之法,卻可於心神潰散前留下烙痕,使受術者聽命施術者。二者結合,毒致受術者喪其心神,有如傀儡,而迷心之法則架細线,以己之思替之,其雖無自我,卻可依施術者心念而動,即為操线傀儡。
“起來。”
他呼喝道。
話音未落,麗人便有了動靜,迅速支起身來,雙臂垂於身側,面無表情,便若熟睡一般。
“睜眼。”
聽聞指示,她緩緩撐起眼簾,只見一雙如墨美眸空洞無神,幽然無光,定於原位,而對外界之事毫無反應。
她面容仍如在世仙子般精致美艷,亦殘有些許出塵之意,只可惜眸中無光,平添了幾分呆滯痴傻。
“張嘴。”“吐舌。”“跳。”“左走。”“躬身。”
他又下了幾個基本指示,面前麗人皆是默然照做,舉手投足間,哪還有一宮之主儀態。
就如她此刻躬身,紗衣緊貼翹臀,勾勒出其輪廓,便是底下褻褲亦能看得一清二楚。若是往日,僅多看這翹臀幾眼,她便會挖出觀者雙眼,絕無可能像這般自行展示。
他笑著拍了拍這團美肉,聽其發出陣陣脆響:“宮主不是欲殺我而後快麼?怎得還誘惑起我來了。還是說你骨子里是個騷貨?”
已無神智的玉霄宮主自然無從回應,任由他詆毀,將己比作青樓蕩婦。
“我 是 騷 貨·······”
然而這時,卻聽得有女子之聲微微響起。聲线清冷,語調卻是毫無起伏,更兼遲滯,仿佛滯澀的機關木拓。
仔細聽起,竟是從玉霄宮主那微張的小嘴中流出。
原來,這迷心之法別有玄妙,可以己思緒控失心之人,無需言語便可傳達指示,更有控其言語之能,可令那失心之人依己之好復述言語,若是操弄熟練,更是能對答如流。
雖為自欺欺人之舉,但於風青,其卻可從中獲得征服之悅,體會將這出塵仙子踐踏足底的快活。
“呵,果真蕩婦。”他在玉霄宮主那裸露於外的玉腿上上下其手,不時還舔上幾口,享受這玉肌滑嫩。同時一只手沿玉腿往上,一直至她股溝深處,觸碰到那藏於褻褲之下的窄縫,撓動幾下。
如此幾番,風青只覺欲火上涌,急於發泄,於是將她放開,一把推倒在地,命令道:“脫掉衣物,跪好。”
玉霄宮主緩步站直,依他指示脫去衣物。只是其身為傀儡,毫無吝惜之情,竟是直接大力拉扯起身上華服。
風青恐其將這華服扯爛,連連叫停,而後親自上前,為她寬衣解帶。
待得把包括束胸、褻褲在內的所有衣物除去後,風青這才再次下令,讓她跪下。
而後,他掏出早已腫脹不堪的胯下龍根,扳開玉霄宮主的小嘴,塞了進去。
在龍根塞入後,盡管她面上仍是一副茫然模樣,但身體卻動了起來,素白纖長的雙手環住他的龍根,令其在口中得以自由進出。
她口中溫熱,本就已令風青舒適不已,更兼有香舌舔弄挑逗頂部,不多時,他便感到有陽精上涌,也不壓制,徑自在她口中射了出來。
待得他將龍根抽出,只見上面涎水與濁液混作一團,淫糜異常。再看玉霄宮主口中,已滿滿當當接了大半白濁之物。
他隨意地將龍根於她胸前擦了擦,命令她將濁液盡數吞咽,而後也不停歇,直接一把將她踢翻,扛起玉腿,將龍根又塞入了下方肉穴之中。
玉霄宮主深居清霄宮內,鮮少與異性接觸,自然仍是處子之身。
而她這肉穴之中緊致非凡,饒是風青素來風流,常出入青樓,閱女無數,也不禁長吁一聲,為之稱道。
他便如這般抽插著,一般感受肉穴之中的緊致美好,一邊將龍根緩緩推前,最終抵到了一層薄膜之前。
“那我便收下你的處子之身咯?”他略帶嘲笑地問道。而後又操弄著玉霄宮主答道:“請 便 。”
得到了她的“許可”,他更是情欲大發,於是一狠勁,直接捅穿了這象征處子之身的薄膜。
可憐玉霄宮主守身如玉多年,將這處子之身尤為看重,此時處子之身被奪卻是一語不發,漠然接受他行此無道之舉。
然而他更是興致高昂,龍根長驅直入,一直頂至肉穴深處,在其中又是亂射一番,這才心滿意足地將其抽出,退至一邊。
玉霄宮主仍擺著方才被他扛起玉腿時的姿勢,高抬著的肉穴中,白濁的液體混雜著些許緋紅滿溢而出,全然不見平日冷漠出塵的仙子儀態。
看著她這副模樣,風青滿意地點了點頭。
這具絕色的傀儡,他還有的是時間享用。
他深呼一口氣,坐到屬於玉霄宮主的位置上,打算歇息一會兒,品上些許好茶。
方一坐定,他便發覺,玉霄宮主的茶盞之下正墊著一封家書,署名乃是清霄宮現任掌門溯星宮主。
展開看之,只見家書上筆跡娟秀,乃是溯星宮主談其游歷江湖所遇之事。看至末尾,卻見溯星宮主提及,不日便會歸宮。
溯星宮主之美貌,風青自是有所耳聞,當即心念一動,想出一策來。
二、
“姊姊!”
經數日,有一女子歸至清霄宮中。方一進門,便嬌笑喚道。
只見女子體態輕盈,著一襲素袍,面容柔美,正是清霄宮那溯星宮主。
玉霄宮主性情冷冽,不好與人來往,而好閉門清修,行事者多憑己見而為;而這溯星宮主則與之相反,活潑善言,不拘小節,好游歷江湖,於那江湖之事皆是略知一二。二者雖無血緣,卻極親近,便是親姊妹也不逞多讓。
若在以往,聽得她呼喚之聲,她那姊姊定會出門相迎。只是這日甚是怪異,仍她如何呼喚,卻始終無人前來接引。
溯星宮主心感疑慮,恐宮中有異,忙運起輕身功夫,疾步奔至玉霄宮主平日修行所在。
這山門至深宮不過數里,溯星宮主僅幾息功夫便已通過。若是往日,這點路程於她便如閒庭信步,可眼下心緒憂慮,內息受擾,竟是一時喘不上氣來。
所幸,深宮之中並無異樣,她遠在正門,便已望見玉霄宮主整端坐主殿之上,手中握一茶盞,正孤身飲著茶。
見姊姊安然無恙,她懸著的心也總算得以放下。
於是她調理內息,斂起憂慮神色,大步踏入正殿,故作嗔態:“姊姊,怎得如此健忘,竟連妹妹歸宮時辰都忘了。”
聽得她言語,玉霄宮主方才抬起頭來,冰冷淡漠的俏臉上浮出一絲淺笑:“只因這茶水太過香醇,忘了時辰,師妹見諒。”
“那於姊姊心中,究竟是我重要,還是這茶水重要?”溯星宮主卻是不依不饒,湊至玉霄宮主身前,撒嬌道。
“那自是師妹重要。”玉霄宮主仍是輕笑,攬溯星宮主在茶案另一側入座。
溯星宮主輕哼一聲,仍似有些慍怒。
只是一與玉霄宮主對視,便立時破了功,轉而嬌笑,笑顏如暖花盛放:“如此便好,我就知姊姊最是愛我。”
“自是如此。”玉霄宮主輕點臻首,取茶盞,為溯星宮主砌上好茶,“師妹,我這茶有寧神之效,你舟車勞頓,不如試上一試?”
“那便多謝姊姊了。若是姊姊有興致,也可聽妹妹將那江湖雜事說上一說。”
“既是師妹有意,那我自然樂意至極。”
······
約莫半個時辰之後,已無人聲的清霄宮正殿之中忽有足音響起,來者正是風青。
他徑自走入大殿,猶如在自家宅院閒庭信步。
望那榻上,只見溯星宮主伏於茶案,美目微閉,毫無聲息,似已沉沉睡去。
而玉霄宮主雖托腮微笑,似仍有清明之相,但眸中卻早已空無一片,有若土偶雕塑,以致這溫和笑意中也平添了幾分虛假。
這殿中景象,便像是溯星宮主睡去之後,玉霄宮主立時停滯了所有舉動,以致笑意都未來得及收回。
事實也確是如此,畢竟此刻玉霄宮主已為風青操线人偶,一言一行皆隨風青心意,在未得指示時自然不會有任何舉動。
方才宮中姊妹二人的問候、洽談,不過是他設下的一台戲,只為騙溯星宮主飲下這摻有軟筋之藥的茶水。
為行此策,他於這數日間多以玉霄宮主為傀練習操弄之法。如今他已可隨心操弄言語神色,令其談吐自如,若無細查,便與醒時無異。
若非如此,以溯星宮主之心細,絕無瞞過可能。
不過,木已成舟,現下軟筋之藥深入骨髓,饒溯星宮主再聰慧,也已無力回天了。
風青嗤笑一聲,安然打量起面前這沉眠麗人。
溯星宮主與其姊姊一般,亦是絕色佳人。與玉霄宮主那清冷出塵的美不同,溯星宮主的嬌艷更為溫潤柔和,有若盛放牡丹,雖尊貴華美,卻非遙不可及。
他看得有些痴了,下意識伸出手去,意圖觸碰這朵嬌艷欲滴的“牡丹”。
就在他即將觸碰到這嬌顏時,異變橫生。
只見一只素手以迅雷之勢將他虎口擒住,隨之有青芒掠起,直奔他要害而去。
事發突然,饒是風青反應迅捷,立時運起蘊毒真氣以逼素手松脫,卻也已失了躲閃時機,只得奮力甩出暗器兩枚,令那青芒偏轉些許。
只覺一陣劇痛,他低頭望去,兩根手指已為青芒所斷。
再看溯星宮主,此刻手持碧青長劍,柳眉倒豎,美眸怒視,哪還有方才安睡模樣。
原來她竟是佯睡以詐之,欲引蛇出洞!
只是風青百思不得其解,他令玉霄宮主以留存記憶為基,佯清明之相,言語神色都與往日無異,本應天衣無縫才是,卻不知是何處露出破綻,為她所識破。
“奸賊,爾竟敢對姊姊行這般事,且拿命來。”溯星宮主厲喝道,手中長劍又是一劍刺出。
清霄宮有一神兵,名曰碧血,通身碧青,極盡鋒利,可削金斷玉,為清霄宮掌門所持,想來便是此劍。
他不敢接此一劍,於是側身堪堪避過。可溯星宮主卻未與他喘息時機,劍法施展開來,有若漫天散花,直壓得他喘不上氣來。
幾劍下來,他內息失衡,腳步虛浮,露出破綻來。溯星宮主抓此之機,側揮手中長劍,便要將他頭顱斬下。
眼看長劍襲來,他避無可避,只得喊道:“且慢!”
他本以為己命休矣,卻未想到長劍果真停下,止於脖頸旁。
“爾還有何話說?”
溯星宮主挑了挑眉,沉聲道。
劍鋒的寒氣深入骨髓,引得他寒毛直豎,幾乎不敢信自己仍在人世。
他伸手探了探,確認頭仍在頸上,這才整頓心思,徐道:“無他,只是想知曉你如何看穿玉霄宮主有異,做明白鬼。”
不曾想,聽得他此言,溯星宮主嬌俏的臉上閃過一絲緋紅,遲疑片刻,這才回道:“姊姊於人後只喚我星兒,此番忽以師妹呼之,自然有異。”
原來如此,竟是這般原因。
風青心中恍然。
他令玉霄宮主依記憶佯其言行,行為舉止天衣無縫。只是傀儡無思考之能,自然也無情感,因而,其無從分辨人前人後之別,不知何時親近何時疏遠,而以一情蔽之,以致露了破綻。
答完他所問之事,溯星宮主目光一凜,便欲將手中長劍斬下。
然而,他詢問心中困惑只為目的其一,主要目的卻是拖得片刻喘息時機,片刻即可。
溯星宮主正欲斬下,卻忽覺身後有勁風襲來,忙回身以劍格之。只聽一聲清響,一雙手掌正拍於碧血劍上,激起回聲陣陣。
細看,出手者卻是玉霄宮主。
“姊·····姊?”溯星宮主失聲道。
她本以為那賊人以言語控制姊姊,因而以迅捷攻勢壓制,令其無從言語。只是卻未想到,他尚未開口,姊姊竟還是攻了過來。
她何等聰慧,立時便明白了,方才風青喝止,所為正是拖延時間,令其能操弄玉霄宮主出手。
望見玉霄宮主毫無神采的美眸,溯星宮主只覺心頭滴血,回身再欲斬殺風青,卻發現他已躍至大殿房梁之上,為斷指塗抹金瘡藥,而玉霄宮主則是直接挪移至她與風青之間,阻擋她前行。
她知曉自己這姊姊已毫無心神,形同傀儡,聽不見她所說之事,但仍是深鞠一躬,這才仗劍上前:“姊姊,得罪了。”
玉霄宮主未有回應,只是拉開架勢,與她纏斗起來。
二人自幼便長居宮中,情同姊妹,平日里亦是多有切磋,對對方的招式皆是知根知底。只是這回“切磋”,玉霄宮主為風青所制,所下皆為死手,而不顧自身生死,可溯星宮主卻恐傷及玉霄宮主,處處束手縛腳,連像樣的劍法都施展不開,更要面臨“接玉掌”的回敬之威,一時間完全落入下風。
這般姊妹反目的景象,風青看在眼里,不禁撫掌而笑,連連稱好,言笑間更令溯星宮主心中如被利刃穿過。
不多時,溯星宮主已是精疲力竭,守勢漸緩,而玉霄宮主仍舊不知疲倦,攻勢似有愈加迅猛之勢。
溯星宮主明白,如這般拖延下去,自己絕無勝機,於是決意放手一搏。
她後退幾步,趁玉霄宮主追前的喘息之機,倒轉劍柄,運起內息,一掌拍在劍柄上。
只見碧青長劍夾雜破空之聲,如利箭般飛射出去,直取風青面門。而溯星宮主則由於分神,招架不及,被玉霄宮主一掌擊中後心,登時一口鮮血噴出,雙膝失力,軟軟跪倒。
風青未有想到她竟會行此共損之策,眼見長劍飛來,慌忙閃躲,然而他忘了自己所處之處乃是懸梁,竟是一腳踩空,從那房梁上跌落下來。
自這高度跌落,這賊子無法運起輕身功夫,必死無疑。
雖無從取勝,尋得解救姊姊之法,但能為江湖除去禍患,也非惡事。
溯星宮主唇角勾起一抹弧度,美目輕闔,力竭睡去。
······
不知過了多少時辰,溯星宮主意識漸回清明,悠悠醒轉。
只是方一睜眼,她心下便是大驚。
原來,玉霄宮主此時正跪坐於她腰腹之上,不著寸縷,冰冷出塵的嬌顏上透露出呆滯漠然。一雙如墨美眸仍然空洞無神。
她試圖支起身,將玉霄宮主推開,卻發覺渾身酥軟,完全提不起勁力。
而這時她才察覺,自己竟也是不著寸縷的模樣,而玉霄宮主此刻正是在以雙手揉捏她的一雙美乳。
只是,為何會是現在的景象?那賊人摔死,姊姊理應失去控制,有若斷线木偶才是,莫非·······
“醒了?”
果然不出她所料,那個光是聽見便能讓她牙癢的聲音響了起來。而後,風青邪笑著自側方走出。
“你定是以為我會摔死吧。只是你卻忘了,我有這位言聽計從的傀儡。”他親了玉霄宮主的俏臉一口,而後當面拍了拍她的翹臀,“她充當我的肉墊,替我減緩了傷害,讓你的想法落空了。好險呢,多虧有你的這位好姊姊。”
“你!”聽他在“好姊姊”三字上加重了語氣,溯星宮主頓時美目圓睜,滿面憤怒之色。
若非身體受制,她此刻便要將這侮辱姊姊的賊人就地誅殺。
風青自然也看清了她的表情,卻只嘿然一笑,淡淡說道:“為報你姊姊的恩情,我決定獎勵你。賤偶玉霄,陪你師妹好好玩玩。”
他話音剛落,就見玉霄宮主緩緩低下身來,整個身子壓在溯星宮主身上,俏臉與她越挨越近。
“你······唔·······”
她還想要說些什麼,卻直接被玉霄宮主用嘴封住了嘴,一條丁香探入口中,與她纏綿起來。
由於身體虛弱,她甚至提不起力來抗拒,只能任由玉霄宮主主動挑逗纏綿。
“你喜歡你的姊姊吧,那便讓你姊姊好好為你服侍一番,如何。”
她想要探出手,將玉霄宮主的頭推開,卻被對方一把按住,十指相扣,讓她無從反抗。
待得二人唇分,從未經歷過情欲之事的她早已是雙腮緋紅,身體微微顫抖,被勾起的欲望近乎噴發。
但她仍留有意識清明,朝向風青罵道:“賊人,你行此不道之舉,人若不除天必誅之。”
本應是厲喝的叫罵聲,此刻由於她身體虛弱而顯得有些輕柔,不像叫罵,倒似撒嬌。
風青自然不與她計較,揮手間,玉霄宮主又吻了上來。
只是這回,又加了些許猛料。
她纖長的玉指,輕輕探進了溯星宮主的肉穴之中,慢慢挑逗起來。
情欲的快感自那肉穴之中上傳,陣陣衝擊起溯星宮主的頭腦。
霎時間,她只覺頭腦空白,恍惚間竟分不清自己是為何人。
盡管還有反抗的念頭,可她身體卻已經失了控制。不知何時,她竟主動與玉霄宮主探入口中的丁香纏綿起來。
她能感覺到,在情欲快感的影響下,理智正在飛速流失,但她卻無從阻止。
甚至她都已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討厭這種感覺,還是喜歡這種感覺。
二者再次唇分時,溯星宮主的眸中已是渾濁一片,嬌顏緋紅,一小截丁香耷拉在嘴角,哪還有原先的溫潤柔和。
“姊姊······”
她最後的理智讓她說出微不可聞的話語。
而玉霄宮主只是往下移動,舔了舔她的乳頭。
伴隨著大量淫水噴濺而出,情欲終究占了上風,她僅存的理智崩塌潰散,口中只余下了破碎的音節,以及陣陣的淫亂呼聲。
“嘖嘖,果然這以性欲抹去心神的毒劑,比起傀儡毒更有效用,也更安全。那麼接下來,就該我出手了。”
她聽見風青嘖嘖笑道。
只是這字詞只見的含義,她早已無從理解。
她只知道,自己想要索求性欲——
·······
金碧輝煌的清霄宮大殿中,風青安坐在主位之上,身前是兩具不著寸縷的素白嬌軀。
堪稱當世絕色的玉霄、溯星二宮主,此時正將自己盡情展現給這叛出師門的逆徒。只見二人嬌俏的面龐皆是漠無表情,呆滯茫然,美眸中亦是毫無光彩,乃至微微放大。
她們的自我已經消融,如今身受邪法與藥毒作用,為風青傀儡,除風青的指示外再無思考能力。
為宮主者尚且如此,就更不提門下小輩了。
如今這清霄宮已不是什麼“三上派”,而不過是他風青的行宮!
而今,他的仇怨已報,所需考慮的便只有一事了。
他許那夷人,待得事成便會引夷人入關,共議中原。
只是若貿然引夷人,必為中原門派所阻。中原門派傳承多年,以夷人之能,能否勝過尚為未知數。
不過,如今他手中有這二枚棋子,略施小策便可解決此事。
他摸了摸溯星宮主溫潤柔和的俏臉,輕笑道:“我的小傀儡,你們會為我擺平此事的,對吧。”
“願為主人效勞。”二人異口同聲說道,聲音木然平淡,全無感情色彩。
“那好,那便請你們修書與江湖門派,便說那清霄散人誕辰將至,請江湖人上山拜壽。”
“願為主人效勞。”
“尤其是那河北風氏,定要將其列入。”
“願為主人效勞。”
三、
近日,清霄宮以師祖誕辰為名,廣發請帖,請江湖中有名有姓之人上山,這是江湖中人盡皆知的事。那清霄師祖德高望重,在世時為一代名俠,當世江湖中人多有受其恩惠,此番拜壽之約,自是欣然接受。
河北風氏既非無名之徒,當然也收到了這一邀約。
卻說這日,罡嵐劍莊那風閒莊主於莊中宴請門客,欲點幾人共上清霄山,向那清霄師祖拜上一拜。席間門客觥籌交錯,談笑歡愉,一派祥和。
然風閒莊主素來心細,細點之下,卻發現有一人始終未至,於是朝眾門客賠罪一聲,離席前去廂房查看。
行至廂房,果見那未至之人在屋內,只見那人面床而立,床上攤一包袱,似是急於離去。
這門客風閒倒也熟悉,名之司塵,乃是於一大雪之日為他所留。那日這人昏於門階前,風閒見其可憐,遂與湯食,收入門下。
此人甚少言語,然其所說之事多有應驗,更能出良策以應對。乃有大智慧之人,況其深諳禮數,凡事皆以禮待之,此刻不辭而別,斷然有異。
於是風閒問之,曰:“先生何以如此匆忙,收拾行裝,竟無暇赴某之宴,與某別之?”
那司塵轉身,徐道:“在下豈是不識禮節之人?只因廈之將傾,欲自保也。”
風閒聽得他話中別有它意,連忙追問:“何以將傾,還請先生說之。”
“我聞明公有一侄兒,名曰青者,可有?”
“有,此子天資聰慧,飽讀某莊中藏書,又拜入清霄門下,為嫡傳弟子。只是此子心術不正,入了邪道,後為玉霄宮主所逐,遁入蠻夷之地,再無音信。”風閒不知他為何問起風青之事,於是如實相告,“此子雖為某侄兒,然其好施邪術,為族中不齒,已廢其族名,無人與之來往,先生何以問之?”
“明公既知那風青之事,又怎覺此番之邀無怪耶?要知那玉霄宮主最好顏面,風氏出此高徒,令其清霄顏面掃地,她未率眾討罪都已是顧及情面,又怎會如此往來,奉帖邀公往之?”
經司塵點出,風閒方才如夢初醒:“確是如此,先生所言極是。”
“那請帖據江湖中人稱,乃玉霄宮主親筆所書。鄙人非江湖人士,無從分辯,只假以此事為真,為明公說上一二。”司塵莞爾,“若請帖真為玉霄宮主所書,則其定受賊人所制也,然公知其脾性,剛正烈直,斷然不會聽命賊人,況其內勁深厚,若逼得緊了,更會拼個魚死網破。想來,興是為人迷了心智,已無本我,方才如此,行其不悅之事。又,我聞公族中有一異法,能攝人心神,使喚人心,喝之如傀儡。公將之封於藏書閣,不為人所閱,可有其事?”
“先生之意,可是說那玉霄宮主已為風青迷去心智?”風閒心下更是大驚,言語中流露出震顫。
“止推測耳,鄙人並無術算之能,不知其詳。只是若真為那豎子所為,此番之邀定然凶險異常,況其既能制玉霄宮主,定已成氣候,待得清算時,公等宗族,又何能逃脫干系。因而鄙人言之,曰廈之將傾。”
“先生可為粱道乎!”聽得司塵言論,風閒早已信服不已,當即面其跪下,便要拜首。
“明公多禮了,我既受公茶飯之恩,自當為公接煩。”司塵忙將風閒扶起,待他站定,方才悠悠說道,“此事牽涉深遠,為當世江湖之凶咎也。公可聞古人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乎?此番之事,公只一家之言,無從左右江湖,以驅其避之,而賊人卻有中天之勢。如此,則公當避世歸隱,明哲自保。待得風波安定,公可再以討賊之命,聚良善之士伐之,還天下太平。”
話畢,司塵又是一笑,也不理會床上行囊,徑直朝門外走去。
“我本欲與公共渡此番凶咎,奈何另有要事需行,故在此別過。公乃良善之士,當有福報,此次一別,還望珍重。”行至門前,司塵又背過身,再行一大禮,“公若有難,某定當竭力相救。”
見得他這般行徑,風閒方知其整頓行囊為虛,告誡謀劃為實,心下感其俠義,回之以禮,又問道:“敢問先生有何要事,如若某能行綿薄之力,但說無妨。”
“哈哈哈,俗事罷了,何勞明公心神。只是我近日聽聞那文胤病勢漸重,不日便要殯天。我與之有緣,思來想去,還是應當見上一面。”司塵大笑,轉身離去。
風閒呆愣片刻,方才想起,這“文胤”乃是當今文氏承天皇帝名諱,當下心中驚異,便欲追問。然司塵卻已漸行漸遠,只余高歌聲:“獻此三方策,報君一飯恩,快哉,快哉!”
風閒追出門去,卻只見一朱鳥戾天飛去,而不見門客身影。自此方驚覺,知其非常人也。
其後三日,風閒依司塵之策,遣散門客,攜家眷遁走深山,閉戶不出,潛心鑽研武學之道。
後數日,眾英傑齊聚清霄宮,為清霄師祖拜壽,怎想那玉霄、溯星二宮主竟設下埋伏,一時間江湖豪傑死傷大半,英才隕落,江湖大亂。
而後清霄宮改頭換面,引夷人入中原,自稱神教,奉名風青者為尊,為禍一方,殘殺正道,江湖人士皆是流離失所。只河北風氏提前知之,人去屋空,未遭此劫。
有江湖人稱,常見那風青教主騎一麗人出行。麗人不著寸縷,目中空無,似是那玉霄宮主模樣。
此即那魔教之由來。至於那風青如何著《枯蟲經》;河北風氏出不世出之天才風玲兒,如何整頓正道殘部反攻魔教,取風青項上人頭;風玲兒如何為江湖之人推崇,以一屆女流之身居“風雨雷電”四大高手之首,皆為後話,暫不表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