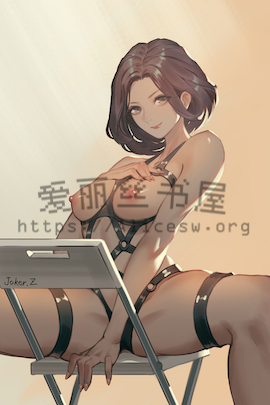午宴在盧府中進行,李宓完全沒玩好,幾個“頗有音律造詣”的樂工表演節目,關鍵是風韻不存的半老徐娘,李宓掃興之至。
席間一眾文人清談,李宓自喻讀書人還刻印過書冊,卻是插不上嘴,也不知道他們扯那些玄虛有啥用。
他喝了一會兒酒忍不住說漏了嘴:“淡出鳥來。”
一句話就暴露了這李宓原來是個俗人,倒沒想到他能俗成這樣,盧公也不禁露出鄙夷之色,那眼神不僅是在鄙夷李宓,好像還鄙視整個薛崇訓政權。
本來見這御史年紀輕輕就得重用,以為很有點文化修養,結果當眾說出“淡出鳥來”這等話,是武將也就罷了這廝明明是個文官。
不過長史王賢之心下已有了主意,下午就以協助御史辦公為名帶著李宓離開了盧府,到了州衙。
晚上就在州衙下設的官妓中開晚宴,大魚大肉加烈酒美女,李宓盡興回下榻之所。
晚上服侍他起居的兩個婢女體態豐腴穿作暴露,李宓覺得還常常對自己拋媚眼,也就沒有客氣,將她們奸至黎明方休。
不過他仍然惦記著白天有正事,一早就起床了,兩個女人赤身來纏他,不料李宓態度驟變哪里還有昨夜的柔情蜜意,一腳將其中一個踢翻,頭部撞在床腳流血不止。
到州衙見了長史等人,不料又以酒色相待,每提及巡視各地他們便左顧而言他。
一連三天都是這樣,李宓怕一同過來的隨從小吏回去說壞話,又想起皇恩破格提拔,三天之後就有點坐不住了。
一日午宴上他又提及要先巡查軍隊,再察漢民少民雜居之地的治理,王賢之等人照樣岔開話題只說李宓感興趣的玩樂之物。
這回李宓大怒,忽然掀了食案,喝道:“爾等遮遮掩掩,竟是在遮掩何物?”
滿地狼藉,幽州官將面面相覷,長史王賢之沉住氣道:“李御史說笑了,咱們哪里是在遮掩?御史領皇上聖旨自京里來,咱們以禮待之,為表仰慕之心,御史何故而發怒?”
掀了食案後李宓的氣消了大半,這會兒也想幽州官員確是沒有什麼地方怠慢,還每晚找女人來玩,再說自己要把差事干好也得多少要依靠地方官的配合,否則他李宓就帶了幾個人來,偌大偌繁雜的幽州軍政何年何月才理得清楚?
李宓便道:“王長史等的好意心領了,但不能成日沒完沒了地設宴歌舞,從今日起每天卯時至酉時為辦公之時,你們應盡力協助我巡查軍政之務,以好早日歸去稟報皇上。午宴也省了,我自命隨從帶食盒應付。”
幽州官吏應允。
李宓在晉王府走動幾年,也受了其中辦事風風火火作風的影響,二話不說,當天下午就讓幽州都督派人協助他巡視駐扎在幽州城附近的官健兵:直屬中央的常備軍,除了名存實亡的府兵,這是現今一等的帝國正規軍;然後才是長期駐守各邊鎮的邊軍。
官健是完全領皇糧的職業兵,邊軍實際上家室都在駐地附近,雖然也領補給但家人會從事其他經濟。
李宓只見營中軍紀嚴明,盔甲軍械完整。
披堅執銳的健兵看起來還不錯,都督趙瞿倒不完全是個酒肉之徒。
但李宓隨即就問隨行的督府官僚:“這里有多少人?幽州都督全部健兵都在營中?”
隨行官員緊張,也不敢胡扯,要是說派到別處去了接下來那李宓可能會追問去了哪里,說不定還要去看,都督的兵權有限在沒有嚴重軍情的時候不能把軍隊調得太遠,要實地去看也不是多難的事。
官員便道:“全都在這里,大約三千多人。”
李宓聲色俱厲道:“大約?三千多是多少?”
官員急忙叫人去督府拿名冊,冷汗直流。敢情這些日子對李宓好酒好肉好色招待都是白費?
名冊拿來後李宓翻了一遍,說道:“我臨走前核對兵部卷宗,明明幽州官軍是八千三百四十二人,以‘軍’為制的都督,竟只有這麼些?半數以上的名額哪里去了,你們吃空餉?一面上奏契丹欲反軍情緊急,一面又裁撤兵員實額,意欲為何?”
不一會趙瞿也趕著過來了,對李宓解釋道:“這中間有實情李御史沒弄清楚。幽州健兵原來確為八千多人,但皇上親征突厥時從幽州調兵,我等不敢以老弱者充數,便先裁撤了一部分,幽州兵又在漠南戰場上死傷半數,傷者已無法編入都督府。之後實數便只剩三千多人了,官健屬於兵部直轄,我們無權擅自招充兵員,結果就是現在李御史看到的這份名冊,督府已復抄一份上呈兵部,可能因途中蹉跎,兵部尚未改新卷宗,故而造成御史之前得到的情況與實情不符。若是我等欺瞞長安吃空餉,李御史現在手里的名冊又從何而來?我等更不敢妄言,新冊遞送長安之事是有據可查的,絕不敢信口雌黃。”
趙瞿又解釋道:“都督府健兵不足,在兵部授權之前我們又不能擅自在名冊上增加名字(朝廷發工資),為了穩固幽州防務,都督府用增加鎮兵和地方團練的辦法來解決,邊地以城中健兵、鎮兵、團練鄉兵組成城堡哨防衛布置,這幾天御史大可以巡察各鎮各堡,看看都督府是否瀆職!”
趙瞿一番辯白,李宓便不再責難,只說稍後兩天就實地巡查。
李宓晚上回去後,隨從勸說道:“明公只是奉旨看看情況,不動聲色看清楚報上去就是,何必在當地就和他們過意不去?畢竟這地盤是王、趙二人管的。”
“怕甚,難道他們還敢對我不利?”李宓冷冷道,“就算我死了也算完成了使命,朝廷自有定奪。”
隨從遂不再勸他。
……
長史王賢之和都督趙瞿也私下碰頭關切李宓的事兒。
按理在晉朝的地方格局下,王趙二人根本是兩路人,此時有軍事活動的地方實行的是軍政分離。
都督掌一地兵馬包括朝廷健兵和地方各種雜牌軍;行政及刑獄由州刺史(長史)掌握,少數地區有監督協調幾州政務的經略使,薛崇訓為了防止軍閥割據在沒登基之前就撤銷了節度使的實權成了一個名譽虛銜,和以前的都督一樣的地位,比如兵部尚書程千里就掛著隴右節度使的官銜,實際上他人在京師根本管不了隴右的任何事。
經略使不得干涉軍務,只能管民政財政刑獄等事,和唐朝相比名字沒多大變化實質變化挺大。
御史王、趙二人一個管兵一個管政,就是沒有多少職權相交的人,但他們往來很密切,常常一起參加各種宴會和活動,平日關系很好。
身寬體胖的王賢之看起來一副寬厚反應遲鈍的模樣,但此時他已感覺到不對勁,對趙瞿說:“看李宓的事兒,咱們恐怕情況不妙。朝廷不是派他來查契丹軍情,反而是查咱們來的,長安肯定是先懷疑咱們了才會派這麼一個人下來。”
趙瞿的神色也不怎麼樂觀,他的眉間形成了三道豎紋,沉吟良久才說道:“就算懷疑也無妨,咱們眼下也沒多大的把柄讓人抓。”
“趙將軍的意思是坐以待斃?”
王賢之不高興道,“朝廷本來就開始懷疑咱們了,如果李宓再回去說兩句不利的話,趙將軍覺得咱們會怎麼樣?”
趙瞿正色道:“我們又沒有真憑實據弄到長安,能怎樣?大不了調個地兒繼續當官,長安還能莫名其妙就逮地方大吏下獄不成?”
王賢之道:“你倒是想得輕巧,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說不定咱們在幽州經營的事兒早就被密報到長安了,調個地方?正好,離開幽州地盤想怎麼弄你就怎麼弄你。”
“都督和長史不都是流官?你還真把幽州當自家地盤。當初咱們聯手的想法是什麼?眼看薛氏倉促登基,防著天下大亂手里沒有實力,現在天下不是沒亂麼?咱們能干甚,你想干甚!趙某是京官,一家老小都在長安;你倒好,在幽州扎根了。出事兒了趙某全家怎麼辦,王明公啊,你這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王賢之道:“成天就想著自家妻兒,是干大事的做法嗎?”
趙瞿道:“要是你王長史全家也在長安,再和我說這話,我就服你。”
“我這也是為你好。”
王賢之嘆了口氣,“你以為人家就查有沒有空餉,幾千兵的餉銀有多少油水,犯得著麼?趙將軍最大的問題是那些鎮兵和團練兵。”
“有什麼問題?”趙瞿不解道。
“你養了太多的契丹、奚等非族的人。”
王賢之道,“趙將軍只道行軍布陣,可知大晉朝廟堂上從皇帝到大臣的態度都是極度不信任蠻夷族人?他們口里說的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還有近幾年議論不休的華夷之辨你以為是怎麼回事?蘇晉在漠南擁立皇上,找的由頭就是薛家是根正苗紅的漢人。就這麼回事兒,您真看不懂?”
趙瞿強辯道:“我招的那些人能打仗,再說幽州的胡人還少嗎,要在幽州擴兵源有什麼辦法?青壯不夠,難道就要舍棄弓馬嫻熟的胡兒拿老的漢人充數?”
王賢之只顧嘆氣,一副很有玄虛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