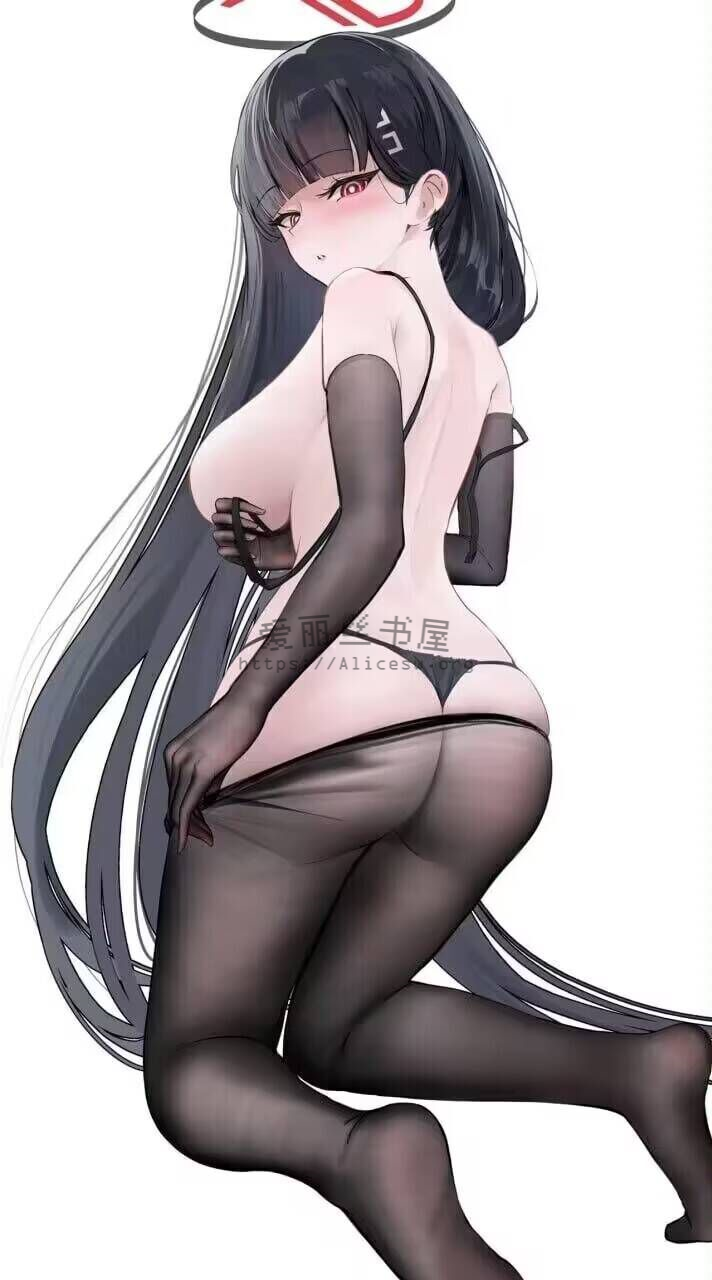MeUmy的幸福結局
MeUmy的幸福結局
“真是的...咩栗老師怎麼還不來?明明是她把咱約出來,結果電話也不接,消息也不回...”
一處明顯不是什麼正經地方的,上面頂著個粉色大愛心的旅館正前,正有一位少女百無聊賴地佇立在門邊。由於少女精致可愛的面龐,姣好的身材,在搭配她所在的地方,很難不讓路人頻頻側目,想入非非。
但是,她卻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可愛的女孩子。她身穿紅黑配色的長袖,截短的上半身衣服還裸露著肚皮;下身則穿著黑色的短褲,搭配的是過膝黑絲與白色的運動鞋。這一身裝束跟可愛完全不搭邊,倒不如說是中性風或者假小子——也很性感就對了。不過,這都不是她回頭率甚高的原因——一頭及腰的銀發如狼般不羈,頭頂一對比起尋常狼來講要大得多的北極貝般的狼耳,少女赫然就是一名狼耳娘。
“嘖...看咩栗老師發的消息那麼著急,所以沒做偽裝就趕緊出門了...早知道她會鴿那麼久就多賴會床了......”
狼少女嘆了口氣,看著手機屏幕之中幾十條全是自己發送的消息,默默地鎖了屏。而通過聊天軟件上的名稱,便可以得知少女的名諱:嗚米。雖說嗚米不怎麼在乎別人的目光,可一直在這里像個傻瓜一樣拄著,總讓她覺得不是個事兒。於是,在大街上無數人驚嘆、惋惜、好奇的目光之中,少女直接推開了情侶酒店的大門,走了進去。
“真是的,再不回我消息,我可要回去點外賣准備晚上的直播了。”
被放了許久鴿子的嗚米氣哼哼地想著,前腳才剛踏入情侶酒店的門口,後腳自己的兜里就響起了振動聲。她趕快掏出來一看,那位一直不回她消息的咩栗,終於回話了。
“抱歉,剛才有點事沒看到...你到了嗎?到了的話就來四樓,出電梯右手邊第二個房間。”
哦豁?
看著對面發來的消息,嗚米隱約覺得這次看似平常的約會,恐怕實際上卻不一般。嗚米和咩栗是一對女同——這在認得她們的人之中幾乎是人盡皆知的事情。
“不對啊,如果真要干那活兒在家里不好嗎,非要約出來干什麼?是有什麼特殊play嗎?”
一想到咩栗那小綿羊般柔軟的身軀,與她發間帶有些許香草氣息的芬芳,嗚米頓時覺得小腹上燃起了一團火焰,而與此同時,幾乎要從嘴角滴落的還有嗚米的口水。
拭去嘴角的掠食者衝動,嗚米搓搓小手,在酒店前台欲言又止的目光中迫不及待地衝進了電梯。
......
MeUmy,又稱狼羊,指的是咩栗和嗚米,是現在風頭正盛的一對主播。其中,狼是嗚米,羊則是咩栗。而當銀發的狼娘拉開房門,站在雙人床前的,是一位留有白發的少女,正是咩栗。她幾乎就是嗚米的翻轉版:瞳色是和嗚米的赤紅相對的天藍,身上穿的是藍白配色的可愛洋服,裙下的大腿上套著素朴的白絲,腳上穿著的是天藍色小皮鞋;身高比嗚米矮了不少,臉蛋比嗚米圓潤可愛了不少,腦袋上還長有一對羊角......一個獵手,一個獵物,一個帥氣,一個可愛——簡直就是天生一對。
“嗚米,你、你來啦......”
“怎麼了,叫我出來要干什麼?今天晚上還有直播預定呢。”
“呃...其實......”
“怎麼?難不成是要干那個?”
嗚米豎起兩根手指,在自己的掌心不斷地摩擦。
“呃......那個,我......”
咩栗的狀況顯然有些不對勁,腦門上一個勁地冒著冷汗,同時兩手捏住了裙角。可不要把她這種反應當做是未經房事的小女孩,她和嗚米老夫老妻的都做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睡一張床早起犯起床氣的時候都能邊罵邊磨豆腐。
可惜,粗神經的嗚米並沒有發現咩栗的不對勁,鞋都來不及脫,直接一個彈射起步,飛撲到了情侶酒店柔軟的大床中間。
“來吧,不要扭捏了!確實我們沒在情侶酒店里做過啦,今天就圓夢了,怎麼樣?”
出乎意料地,並沒有發生什麼嗚米一把將咩栗撲倒在床上的情景。這只從長相到聲音到氣質都寫滿了攻的狼耳少女,竟躺在了床上,雙手雙足都抬起,擺出了像狗狗一樣的服從姿勢。
“來呀,來呀!像往常那樣就好!”
嗚米滿臉的興奮之色,白皙的臉蛋已經被潮紅所覆蓋。然而,咩栗卻保持著沉默,一言不發。
就在這時,一邊的衣櫃門突然被踹開,從中竄出兩個彪形大漢。嗚米的注意力全放在咩栗的身上,一時躲閃不及,一下被其中一名戴著墨鏡的黑衣人撲倒在床上。不過雖說嗚米在咩栗面前會擺出這麼丟人的樣子,面對別人時可絕不手軟——她蹬起一腳正中黑衣人的腹部,直接將他踹飛了出去,“哐啷”一聲跌回了衣櫃。
“咩、咩栗,這是怎麼回事?!”
嗚米直接轉過頭來,可對方卻躲避著她的目光,身體朝著房間的角落里縮了縮。而另一個瘦弱一點的男人則擺好架勢,一副隨時都可以打過來的樣子。於是,嗚米也不多浪費時間,一個鯉魚打挺從床上站起了身,准備一拳也把這個男的打飛。可正當她舉起拳頭時,卻突然感覺腳步虛浮,渾身的肌肉都隨之松弛了下來,還有一股疲憊感襲遍了全身。
“嚇?!”
嗚米兩腿一陣顫抖,“噗通”一聲跪坐在了床上,再也不能動彈分毫。直至此刻,她才發現插在自己脖頸上的針管。
“媽的,這一腳差點沒把我踹背過氣去...”
從衣櫃里狼狽地爬出一個男人,剛剛被踹飛的男人身上還留著一個鞋印。他在嗚米難以置信的目光之中,一邊解開著褲腰帶,一邊指使著另一個男人干活。
“你也別愣著了!這小婊子已經沒有反抗能力了,你去准備一下工具......”
見他們完全無視了自己,咩栗急忙小跑到那瘦弱男身旁,小皮鞋踩在地板上發出篤篤篤的響聲。
“那、那個,先生?就如您之前所說的,只要人家把嗚米交出來,就保我前途無憂,也不會傷害人家......對吧?!”
“對對對,答應你的事兒怎麼可能反悔呢。”
瘦男不耐煩地擺了擺手,像是驅趕蒼蠅一樣地把咩栗推到了一邊。
“那、那沒什麼事的話,我就先離開了?”
咩栗回頭看了一眼此時在她視野里完全被男人擋住的嗚米,咽了口口水。
“那可不行...你得留在這里,一直到我們處理完你的女朋友為止。”
聞言,咩栗的臉色更差了。可是一想到此時最近幾個房間里蹲守著的持槍黑幫,她只好乖乖地回到沙發上坐好,臉色蒼白。
至於嗚米,由於藥物的作用導致她注意力渙散,咩栗剛剛說的話她完全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嗚...動起來啊,動起來啊!”
她努力想抬起手臂,可即使抬起來了也只是提起了一根軟肉而已。也多虧她沒聽到咩栗說的,否則現在沒准都要精神崩潰了。
“奶奶的,就你剛才踹我啊,嗯?還囂張不?”
墨鏡男已經把褲子脫了下來,將那根丑陋而粗長的男性器亮了出來。
“是、是那玩意...”
嗚米頓時感到一股生理上的不適感,讓她感到一陣惡心。而從空氣之中緩緩飄來的,那在男人褲襠里悶了許久的荷爾蒙氣息,更是令她幾乎要嘔吐出來。而她什麼都做不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掏出肉棒的男人慢慢地靠近她。
“噫...不要...男、男人,好惡心...咩栗?咩栗在哪里,她沒事吧?!”
根本沒時間讓她想太多,墨鏡男人已經將肉棒抵在了她的耳邊。
“...啊、啊嘞?”
嗚米眨巴眨巴眼睛,漸漸意識到事情的不對。
“等、等下?!你是不是捅錯地方了?”
“老子插的就是耳朵,歐啦!!!”
不等嗚米反應,男人的肉棒直接抵住了嗚米的大狼耳,狠狠地向里面頂去。用來保暖以及保護耳道的絨毛一下被龜頭突破,直奔耳穴內部——嗚米只在顱內聽到一陣什麼東西破碎的黏膩聲響,整個左耳就瞬間喪失了聽覺,只能聽到隆隆的悶聲與嗡嗡的轟鳴。
“啊啊啊啊啊?!住、住手!!!”
強烈的刺痛讓嗚米忍不住慘叫出聲,肌肉松弛的身體奮力掙扎,卻連讓自己變換姿勢都做不到。獸耳娘的耳穴幾乎全靠著茂密的絨毛保護,很快便被肉棒整個兒捅穿,直接通到了
“咩栗!咩栗你能聽到嗎?!咩栗你在哪里??救救、救救我......”
而此時的咩栗,正被瘦男人強行按在沙發上,觀摩嗚米的腦姦。她不忍再看,本想扭過頭去,卻被黑洞洞的槍口抵住了後腦勺。
“給我好好地看...看被你親手賣掉的小情人是怎麼死的......”
“啊啊嗷嗷??嗚啊喔嘔、嘔嘔......”
嗚米的慘叫逐漸變形、變聲,男人粗長的肉棒已經捅破了通往她顱腔的最後一層防线,跳動著的炙熱物體破開大腦皮層,直接闖入了嗚米的腦中。顱內組織遭受破壞,嗚米的眼前頓時一片黑暗——可能是負責視覺的腦片區被攪碎的原因,她即便奮力睜開眼睛,也再也看不到任何東西了。
“啪嗒、啪嗒......”
嗚米失去力量的雙手徒勞地倚在男人的大腿上,試圖把他推開,但完全起不到半點作用,反倒像是被插得起了快感、開始撫摸施暴者。嗚米的舌頭已經不受控制地吐了出來,涎水和淚水滴滴答答順著舌尖和下巴滴落在床單上;赤紅色的雙瞳因顱內控制快感的部位遭受刺激而翻白著,又因痛苦而急劇縮小,最後變得模糊、失神。呈鴨子坐跪在床上的嗚米,襠下隨著男人的肉棒在自己腦子里的抽插而變得越來越濕潤,纖細的腰肢和豐潤的臀部不斷抖動抽搐,仿佛在她的小穴里塞了顆大功率跳蛋一樣。
“女孩子的腦子好爽,好爽!”
“呃啊...嗚嘔...嘔嘔嘔...”
嗚米的反應越來越弱,聲音越來越模糊不清,男人的動作就愈發粗暴強健。他喘著粗氣,每一次衝擊都能在嗚米的顱腔內爆發出一陣黏膩的氣泡破碎聲與啪滋啪滋的水聲,不知是腦脊液還是前列腺液的東西不斷從她那只被插入的大耳朵里飛濺而出。而此時的嗚米雖說還保有一絲意識,但腦內的思維已經徹底錯亂,控制排泄的神經被毀滅,膀胱開閘,下體竟嘩啦啦地淌出了尿液。頓時,她身下的床單便濕了一大片。
然而,就是在這無限接近死亡的腦交之中,嗚米居然體會到了曾經和咩栗磨豆腐時從未體驗過的...快感?之所以帶著問號,是因為現在的嗚米已經無法分清何為痛苦、何為快感了。爆著青筋的肉棒已經將她腦內負責此部分思考的組織摧毀,她在一片漆黑之中只覺得自己的下半身隨著顱內重錘的一次次擊打,而自發地放出了高潮的愛液。
“這、這是為什麼......咩栗...你在哪里......”
混沌之中,嗚米所僅剩的極為可憐的少的能夠用來思考的念頭之中,已然僅剩下了那只長著羊角的白發少女。
“我還沒......嘗過你的大腿肉啊......”
......
“蕪!!!射了!射了!”
墨鏡男突然一聲低吼,按住嗚米的腦袋,將子種盡數播撒在了女孩的腦子里。
“噗嗞...噗嗞...”
滾燙的濃精乘著輸精管的軌道高速射出,仿佛一枚小型炸彈一樣轟然於嗚米的腦中炸開,讓她剛剛所積攢的一切思念與想法都與腦組織一同爆成了碎渣。她兩邊的大腦一下被打了個對穿,就連對側的耳膜都被打爛,讓男人一大股一大股的精液摻雜著無數粉紅的破碎腦組織,從嗚米的另一只耳朵里潑灑而出。狼娘那軟趴趴萎靡在床單上的大尾巴,成了吸收這些腦子和精液的軟墊,被染得髒兮兮的。
“嘔嗚!”
咩栗面色鐵青,急忙捂住嘴巴,才沒有被滿屋子的血腥味與精液臭味刺激得當場嘔吐。看著嗚米那抽搐著倚在男人大腿上的臂膀,她突然覺得心里缺了一大塊兒,變得空虛。
“......”
大腦被肉棒和精液徹底攪碎,嗚米的身體終於徹底停止了掙扎,扶住男人的雙手也從對方的身上滑落,意識也緩緩地溶解在了黑暗之中,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噗通!”
隨著男人把老二從她的耳穴之中拉著精絲和血絲抽了出來,嗚米的屍體便直接側躺著倒在了床上。從她那被插出一個血洞的耳道之中,汩汩地往外淌著被攪成泥的腦子和血液,以及先前射進去的精液。
望著和自己同居的摯友兼情人如此悲慘地死在了眼前,咩栗強忍著淚水與心中的恐懼之情,用顫抖的聲音征詢著這兩個人的意見。
“那、那個......我,我可以走了嗎?”
墨鏡男沒有回復咩栗,瘦高男也沒有把抵在咩栗腦袋上的槍口移開,她只能緊張地抿著嘴,看著對方把染血的肉棒蹭在嗚米的黑絲大腿上,直到把上面的髒汙擦淨後提上褲子。
“呼...真可惜,你沒有像是嗚米那樣可以插入的大耳朵。”
依舊沒有正面回復咩栗的問題,墨鏡男一邊解開嗚米的鞋帶,一邊緩緩地把她的運動鞋往下脫。
“不過我倒是有個問題:她是狼,你是羊,你們兩個卻成了一對兒...嗚米,她是怎麼忍住食欲,不去直接把你這個細皮嫩肉的小羊吃得只剩骨架的?”
“可能是因為,她...她喜歡我?”
咩栗說著,頓時覺得一陣悲哀。她居然在向殺死了摯愛的凶手解釋她們之間的關系?
“她喜歡你嗎...那確實。不過,我們可不喜歡你。”
“?!”
“別會錯意...我們是不喜歡你為了苟活直接出賣另一半,對你身上鮮嫩的羊肉可是喜歡得不得了哇。”
猛然,在咩栗身後的男人一下將她從沙發上架了起來,制住雙臂。
“噫、噫?!?等、等等?”
咩栗一下就慌了,忙蹬著兩條小腿,掙扎著想要掙脫男人的束縛。
“來幾個幫廚,我們今天就吃羊肉湯!”
墨鏡男一聲吆喝,頓時在門外駐守著的十幾個大漢便一下涌入房間,甚至還一塊扛著一套移動廚房——灶台、案板、插頭、鍋碗瓢盆以及各種廚具調料,除了抽油煙機應有盡有。
“等、等一下?你們不是說,保我前途無憂,更不會傷害我嗎?!你、你們不是黑幫嗎,要講誠信啊!”
咩栗把先前墨鏡男劫持自己時的說辭當做救命稻草,一邊奮力掙扎著,一邊觀察著周圍那些大漢們的反應。
可惜,這些人看向她的表情,卻滿滿都是嘲弄。
“咩栗小姐,我關注您很久了...甚至還給你上過艦長哦。我相信你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其中一個男人緊著把移動廚房放在房間里,扭頭便朝著咩栗搭上了話。
“那、那就把人家放了...”
“不過,我家老大可是說的保你前途無憂,不再傷害你......那肯定是會履行承諾的。”
男人繼續說著,從一旁的架子上抽出了一把尖刀。
“從我剛開始看您直播的時候,就饞您和嗚米的身子很久了......包您前途無憂,變成燉羊肉進到兄弟們的肚子里,自然是咩栗小姐最好的歸宿;老大也確實不會再傷害您,負責宰殺您的是我們呀。”
“什麼——”
咩栗的聲音一下驚恐地拔高了一個八度,呼吸也變得急促了起來。剛剛嗚米被肉棒插進大腦慘死的場景還歷歷在目,恐懼一下扼住了她的喉嚨,教她腦內的思維和邏輯全都混亂,兩腿一蹬,整個人都僵硬了——這是羊的應激反應。
待得咩栗驟然回過神來時,她已經被死死地按倒在了案板上,動彈不得,更是有一人搬著木桶將其放在了她的腦袋下方。咩栗也不知道自己這一應激究竟過去了多長時間,她也沒時間想這些雜七雜八的。她只知道,當她扭過頭來看向一邊時,看到了第二個木桶。在那桶中,卻是宛若菜市場的肉鋪,農村大院的後廚一樣,滿是血腥。各個說不上來名字,又或者是因為被破壞了完整性所以認不出來的內髒像垃圾一樣堆積在桶中,其中七彎八繞的腸子更是盤旋著壘得老高,甚至還能夠從桶邊垂下來一截。顯然,咩栗現在四肢健全,這桶東西也不可能是這幫男人現去菜市場弄得,那麼這堆內髒的主人,就已經顯而易見了。
“不、不要......嗚米、嗚米!!!”
“叫個屁,嗚米早都死了,你乖乖躺好別動挨宰就是了!”
企圖掙扎的四肢再度被死死按住,男人們各司其職,情趣酒店里臨時搭建起的廚房變得異常忙碌。
“挨、挨宰......啊啊...啊啊啊啊!!”
咩栗尖叫出聲,驚恐、悔恨、茫然,她只能憑借這種原始的方式發泄心中淤積的情緒。而似乎是嫌棄她太過吵鬧,男人竟抓住咩栗的腿彎,一把將她的雙腿岔開來,露出已經完全真空的白虎穴。
“別吵別吵,讓你死前爽爽。”
“不、不要,不要男人,不要!!”
不加理會綿羊少女眼角的淚滴,肌肉壯實的男人直接掏出了胯下的巨棒,對著她的小穴就要插入。咩栗只覺得自己冰涼的下體上突然被什麼灼熱的東西抵住,而那東西正試圖繼續前進——
“咿呀啊啊啊啊啊啊——!!!”
咩栗猛地仰起頭,挺起身子,發出了有史以來最淒厲的慘嚎,聲音都因為嗓子不堪重負而有些沙啞。
“喝,你和嗚米小兩口平時玩這麼大,結果你的處女還沒破?”
根本沒空去理會男人戲謔地嘲諷,咩栗只覺得自己的意識又快要消失了。因為恐懼的原因,她失禁了——不過是在她應激反應的時候,為了清理干淨,男人們才脫下她的內褲的。而現在,咩栗的穴口沒有任何潤滑,僅僅只有幾滴先前沒擦干淨的黃金聖水作為阻攔,讓男人的肉棒毫無阻攔地撕裂著陰穴之中粘合著的肉,輕而易舉便捅破了形同虛設的處女膜。
“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咩栗不斷搖著頭,雙眼緊閉叫喊著,仿佛這樣就能消除下半身被生撕一樣的痛苦,但無濟於事。異常粗大的肉棍緊緊堵著咩栗的小穴,甚至她的處女血都沒辦法正常流出,就這樣留在了陰道之中成為了潤滑劑助紂為虐。而更令咩栗無法接受,乃至於幾欲想死的是,在這堪稱殺妻/殺夫仇人賜予的痛苦之中,她竟能感受到一絲快感...那是和嗚米做愛之時從未有過的體驗。
“別急,別急啊,馬上就輪到你了。”
另一邊的男人從工具箱中拿出各種各樣的道具,一件件地擺在桌上,擺在咩栗的身邊:負責劈開骨頭的斬骨刀,用來從骨頭上剔下肉塊的剔肉刀,傳統的厚背菜刀,刀刃內彎的柴刀,還有看起來就可怕的鋸子等等,沒掏出來一件就要對照著咩栗身體上的某個部位好好打量幾番,讓她渾身寒毛倒豎。而下體不斷傳來的疼痛,更是讓她懷疑這幫人是不是已經趁著自己失去意識的時候給她剌了一刀。
“火都生好了,鍋都熱了,你們那兒啥時候把肉准備好啊?”
“好嘞,馬上就好!”
從遠處,似乎是隔著一堵牆傳來了一聲吆喝。而在這里挑選著屠刀的男人,則抄起了那把一開始便亮出,間接導致了咩栗出現應激反應的尖刀。
“喂,等等?我還沒射呢...”
“沒事,趁著放血的時候她身體還是熱乎的。”
說著,男人高高舉起尖刀,正對准了咩栗的脖頸。
在這生死一线的關鍵時刻,咩栗竟然連一句求饒的話都說不出,腦袋里一片空白。而她那緊縮的碧藍瞳孔之中倒映而出的,是那把正飛速靠近自己的,閃著寒光的尖刀。
“啊...嗚米......人家這麼快就要來找你了嗎?”
咩栗的大腦變得迷迷糊糊,朦朧之中,似乎感受到了一股震動——
一條斷腿“碰”的一聲被放在了她的身邊,其上穿著的黑絲和運動鞋讓她第一時間就認出了嗚米的身份。
咩栗在這一瞬間失神了。
“嗚米...是、是你?”
“噗!”
刀鋒猛地插入咩栗的脖頸,直接破開了她的氣管和大動脈。鮮血潑灑著,先是噴濺出一大股,隨後便減弱了下來,汩汩地從血管里流淌而出,落到位於咩栗腦袋正下方的空桶里來。
“這羊血可是好東西,不能浪費。”
男人一邊說著,一邊抱著咩栗的頭扭動著刀子,一刺一拉,又開出一個大豁口。少女脖頸之中的筋、肉、脂肪,簡直就像是芹菜梗一樣被輕易斬斷。
而咩栗,在反應過來自己被割喉時,已經為時已晚。她還想說什麼,可氣管早就被割開,她連呼吸都只能任憑空氣從傷口處漏出,更別提說出什麼有意義的字句了。她的身體和腦袋,仿佛是一人一個想法,腦袋那邊因為空氣不斷吸入而發出空虛而尖銳的哨聲,身體這邊卻因為血管里的血液倒灌進了氣管而一直有著咕嚕咕嚕的泡沫響。窒息、失血,讓咩栗眼前的世界仿佛都變成了黑白二色,男人為了方便割開喉嚨而將她的腦袋往下掰,更是讓她的視野都上下顛倒。但出乎意料的,反倒是她並沒有感覺到多麼痛苦。咩栗勉強還能看到架著已經不再受自己控制的兩條大腿,正氣喘吁吁地抽插著自己陰穴的男人,竟然感到了一絲絲的解脫。
“嗚米......對不起......我、我來找你了......”
嘎巴!
隨著尖刀刺向了咩栗頸椎之中的縫隙,隨著男人扶住她的腦門狠狠往下一按,少女脆弱的頸椎便應聲而斷。她緊縮的雙眼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渙散了開來,瞳孔之中失去了神采而變得渾濁,模糊,氣管不斷通風而產生的嗚嗚聲也戛然而止了。
咩栗終於是死了,緊隨嗚米其後。
不過雖然說咩栗死掉了,但她的屠宰工作才僅僅做了個開頭而已。現如今,她的腦袋和身體已經僅剩了一層皮肉連接著,整個腦袋也不再需要男人掰著,無力地從桌邊耷拉下來,放出的血液便自己淌進下方的桶中。而男人則換了一把刀,粗暴地連著咩栗身上穿的衣服一同,從她的胸脯中央一直向下劃開了一道大口子,隨後一股腦兒地把里面的腸子、肝、胰、胃等等下水內髒掏了出來,用小刀切斷與身體的連接後便囫圇丟進塑料桶里。那剛剛被男人使用過,里面淨是精液的子宮,也被小刀割下,連同膀胱一塊兒丟進了桶中。至於那塑料桶的底部,早就被嗚米的內髒裝得滿滿,咩栗的子宮被新丟進來的一塊腎髒一擠壓,頓時噗嚕噗嚕地噴出來不少精漿,從腸子的褶皺之中穿行,慢慢滲到了最底部那嗚米的子宮上。咩栗嗚米二人生前也僅僅是用手指、假陽具或者用下體廝磨,卻想不到她們死後還能內髒見內髒,真正意義上的負距離交合了。
放完了血,男人們抬著並沒有什麼價值的一大桶下水,把它們合力灌裝到了一台大號的粉碎機里備用。將來,把他們吃剩的骨頭、不需要的部分,還有桔梗、麥稈之類的東西混合再統統倒進來打碎,粉碎機便會吐出一大坨一大坨營養豐富的豬飼料,又或者是肥力超群的土法肥料。而放血完畢,已經呈現出蒼白之色的咩栗的屍體,則由男人們共同為她扒去一切沒必要的衣服,脫下白絲和小皮鞋,露出下面白白嫩嫩的肉體。連同嗚米的黑絲、運動鞋、衣物、大尾巴上的絨毛等等,也都丟進了粉碎機里。反正這東西功率大,把這些東西也都打碎成沫應該問題不大。
解決了一切先期工作,男人們便分別扛著咩栗的無頭死體——她的頭顱在放完血以後就被割了下來,用於餐桌上的點綴——以及一大桶嗚米被肢解分屍後的加起來十幾塊的碎屍,一同前去了隔壁的豪華大床房。
異常寬敞的酒店房間里,已經擺上了足以坐下十幾個人的大圓桌。圓桌中央則是一大盆煮沸的鍋子,里面事先鋪好了青菜、蘑菇、棗子、枸杞等物什,圍繞著大火鍋則擺著一盤盤的豆皮、金針菇、紅薯、豆腐等配菜。等候多時的食客們各個搓著手,盯著眼前的麻醬或者油碟,有的饞極了便用筷子挑上點蘸料來,放進口中細細品嘗,唇齒之間仿佛有肉味。
“久等咯!”
一盤盤新鮮片好的鮮肉擺在了圓桌之上,盤子上還貼心地標明了這盤肉取自嗚米身上的哪些部位。口干舌燥的人們迫不及待地把桌上的食材都下進了鍋,一時間房間里蒸汽繚繞,碗筷相擊之聲、咀嚼聲、飲酒聲,把酒店房間變成了餐廳包廂。食材組的幾個男人也把圍裙解下坐上了位,筷子挑著指甲蓋厚的肉片便將其沉進了清湯鍋里。等待幾秒鍾後,再把筷子一抬,鮮紅的肉片就變成了灰褐色。隨後,再將肉片沉在蘸料里,讓蜷曲起來的肉絲和脂肪都抹遍與之顏色相同的麻醬,直接塞進嘴里!
“新鮮羊腦來咯!”
雲霧繚繞之間,眾人正吃得滿頭大汗,突然聽到一聲爆喝,竟是又有一盤東西被端上了桌。男人們揮揮手驅散蒸汽,赫然發現那盤中所裝的,正是咩栗的頭顱。此時的她依然維持著生前略帶驚恐的表情,脖頸處的斷口與盤子的連接處還有著一抹鮮血,足以證明其新鮮程度——剛砍下來十幾分鍾,咩栗的臉蛋上還帶著生前的余溫呢。
“這羊腦都上了,狗腦呢?”
“哪兒還有狗腦?你要吃混著老大孩子的狗腦嗎?”
頓時,餐桌上一片歡聲笑語,咩栗的上半邊腦殼也在笑聲中被掀開。泡在血水之中的完整大腦上面撒著調料,顯然是提前取出進行過醃制,又放回顱骨之中的。餐桌之上十幾二十個人,這一份腦子一人挖走一勺,便變得空蕩蕩了。
“烤全羊好咯!”
大伙正吃得高興,又是傳來了一聲吆喝,一眾人馬便直接關上電磁爐,迅速轉移陣地。咩栗的無頭屍體扒去了衣服,開膛破肚去了內髒以後,又沿著脊椎處細細劈開,將咩栗平攤在了一張烤網上。至於她的雙手雙腳,則像是烤雞一樣擺成了M形,也被兩大片鐵網夾在了一起。男人們提前把煙霧報警器封好,在室內生起了炭爐,就是為了這烤全羊。咩栗如今的形象,已經與她還活著的時候大相徑庭。大塊的油脂都被烤化,本來就身材嬌小的小羊更顯得瘦小;咩栗的背上還灑滿了孜然辣椒面,滴滴油脂從她的足尖、肋排上滴落。火候剛好的皮膚,拿刀子劃上去發出咔咔的脆響,令人食指大動。用餐刀去切,尚未切破上方的皮,在底下的肉便已經散開脫骨,油脂四溢的大塊烤肉帶著淡淡的羊膻味,好的地方入口用嘴唇一抿就抿化,不怎麼樣的如羊腿的地方也纖維分明,唇齒留香。一群如狼似虎的男人們爭搶著肋排,搶完了以後又用刀子劈著臂肉腿肉,最後手不夠快的人只能分到咩栗烤得都有些發黑的兩只小腳......竟是十幾分鍾就把鐵網上流油的珍饈瓜分得只剩下了骨架。
嗚米身上片下來的狗肉片吃得差不多了,便將整塊整塊的帶骨肉下進湯鍋,再填上香料,一大盆清湯火鍋便搖身一變成了滋補養身的肉湯。嗚米的整腿在黑絲和運動鞋里悶了許久,剛剛解放,就再次帶皮丟進了滾煮的湯鍋中繼續熬制。豆腐、青菜吸飽了肉湯,一咬便湯汁四濺,燙得人直吐舌頭。鮮美的狗肉湯混搭著蔬菜,一口湯一口配菜,再搭配上先前被涮肉稀釋的蘸料,給這頓飯劃上了完美的句號。
望著滿桌的殘羹剩飯,酒足飯飽的男人們收拾好碗筷盤子,拎著大包小包,野炊用的燒烤架、電磁爐也統統拆卸下來裝回包裹里。剩菜、咩阿栗已經涼掉的骨架、嗚米吃剩大半的腿子、已經涼透了個蘸料、剩飯、鍋底的渣滓......統統投入粉碎機。機器一啟動,亂七八糟的東西就被打成了糊糊一樣的粘稠泔水。再那之後,小弟們會把這一大兜子肉骨渣賣到偏遠農村當做肥料,而那些尚未通網的人們自然也不會把肉渣之中混著的銀白色毛發當回事。再加上早已提前買通的當地“保護傘”和情趣酒店的老板,自此再也沒發過任何一條動態的咩栗、嗚米二人,就這樣永遠失蹤了。至於她們倆的頭顱,原本計劃應該也是要丟進粉碎機里打爛的,但考慮到機器成本問題以及二人的身價,男人們的首領最終還是決定把它們帶回家里。
墨鏡男家中那面插滿了少女首級的裝飾牆,又新添了一狼一羊。嗚米的首級在經過了防腐處理後已經沒有了被腦姦至死時的狼狽表情,反倒是用渙散的瞳孔瞪視著前方,宛若凶猛的掠食者。而咩栗的臉蛋,則固定在了那副驚恐的表情之上,一如被捕食的羔羊。至少在她們死後,狼攻占了上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