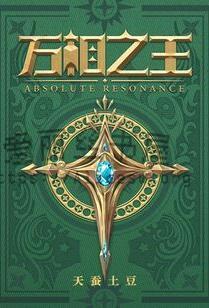我大概是瘋了。
如果你看到正在全速前進的大貨車的駕駛員突然雙手離開方向盤,掏出針管扎在自己胳膊上,而這輛車又沒有自動駕駛系統的話,你大概也會產生和我同樣的想法。但我卻不敢把車子停下哪怕一秒,即使我包著厚厚繃帶的右手正在隨著貨車的顛簸而不停顫抖,左臂原本完好的皮膚也被針頭劃出了一道道血痕。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將針扎進合適的位置,剛剛從靜脈里抽出了半管血,這輛和我相性不和的貨車就咔的一下拋錨了。
畢竟我在搶到這輛車之前也在停車場進行了一番激烈的槍戰,當時打壞了什麼部件也說不定。於是我掏出望遠鏡朝著軍事基地的方向看了看,確定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跟著了之後才跳下了車。
希望只是什麼晃上幾下就能處理好的故障,畢竟我逃出基地的時候沒有想到再去順幾包零件出來,況且我也從未學習過如何修理貨車。想到這里,我掀開了車廂上蒙著的綠色苫布,然後用力地在車身上踹了幾腳。
發動機並沒有重新開始運作,但堆在車廂角落的那堆物資卻發出了奇怪的響動。它們原本也被一塊布遮蓋著,但是那塊布地下似乎有什麼活物在小幅度地動作著,布料的輪廓也從這里變成了曲线。我走上前掀開了那塊布,藏匿其中的女孩露出了受到驚嚇的眼神。
車廂里光线昏暗,我第一眼並沒有看清那女孩的臉,只看到一副眼鏡在黑暗中分外明顯。她手里捧著半袋壓縮餅干,在我闖進來的時候她失手弄掉了正在吃的那塊,牙印的形狀還殘留在上面。吃完那塊餅干,她迅速對我露出一個微笑:“被您發現了還真是沒辦法啊!”
我仔細打量著那女孩。她和我年齡差不多大,身上穿著同樣由粗糙布料制成的軍裝,紫紅色的長發也被盤起來收到沾滿塵土的帽子里。和我不同,她並沒有配槍,甚至連把匕首也沒帶,甚至露出的手臂线條也不像是經受過太多鍛煉的樣子。盡管如此,我還是從腰間掏出了手槍頂上她的額頭,問:“你叫什麼名字?哪個連隊的?是人還是鬼?”
她笑著揮揮手,然後識相地將雙手舉過頭頂:“七種茨,工程兵。至於第三個問題……您要把我脫光看看身上有沒有可疑的傷痕嗎?”
說這句話的時候她打量著我右臂的繃帶。我清楚地知道那底下只不過是一大片擦傷,以防萬一我還倒了半瓶過氧化氫用於消毒——盡管下一秒我就後悔了。我放下槍,之後從角落里撿起一條麻繩,毫不留情地緊緊捆住了她潔白的手腕。“我可不吃那一套。”
她對著我吐了吐舌頭,像是在抗議我不懂憐香惜玉,只可惜我和她同為女性。哪個男人都不會舍得把這樣可愛的少女捆在貨車車廂里的,我這樣想,然後轉身進駕駛室拿出了醫藥箱。還好用於檢測是否感染病毒的試紙還充足,我在滴了血液的兩份試樣上分別標注伏見弓弦和七種茨,然後將它們放入培養皿中。
她對我抗議說繩子要把手腕的皮膚磨破了,要求我松綁,但我堅持要把她綁到檢測結果出來為止。於是她問我:“如果連你也感染了病毒怎麼辦?”
“那就自殺好了。咬住槍口扣動扳機就行了,我可不想像軍事基地里面那些家伙一樣到處追著人咬。”
“既然如此,在自殺之前和我來一發怎麼樣?”
七種茨眨眨眼睛看著我,原本好好挽著的頭發從歪掉的帽子里滑了下來落在肩頭。正當我有些出神的時候,她又笑出了聲:“我剛才看過了,車上的東西大概夠我們兩個人吃上五天,或者一個人吃上十天吧,反正那些見鬼的外星玉米又不能吃。所以接下來您打算怎麼辦,如果我沒有感染病毒的話就收留我,還是直接殺掉我以免浪費糧食嗎……啊,我怎麼忘記了,屍體應該也能吃個幾天吧?”
“如果發信器沒被破壞,大概三天之後就會有人來救我們了。到那個時候還沒有人來的話就只能衝進基地搶東西了。感染了僵屍病毒之後只會對人類的血感興趣,不會動儲藏的食物。但是現在車子壞掉了。”
“我說了我是工程兵吧。”
她催促我立刻檢查試紙的情況。我身上並未攜帶可以用於精確計時的東西,不知道現在是否已經到了檢測所需時間,但試紙的顏色已經發生了特定的變化,說明兩份試紙上的都是正常人的血液。於是我准備去解開捆住七種茨的麻繩,同時在她耳邊問:“你該不會在我解開繩子的那一刻就用這條繩子勒死我吧?”
“我?不行,我不會開車。我有一點精神疾病,法律禁止我學習駕駛。不過簡單的維修還是可以的,不然我就沒有被雇來維護機器的必要了。”
她靈巧地從車廂里跳下,跑進駕駛室轉動鑰匙試著打了幾下火,然後熟練地鑽進了車底。幾分鍾後她探出了頭:“弓弦,扳手有沒有帶呀?”
說這話的時候她臉上已經蹭上了一塊灰綠的油跡。我從車廂里找出扳手遞給她,順道用紗布擦了擦她的臉蛋。貨車的底盤足夠高,就算找不到架起車子的千斤頂,車底的空間也足夠她嬌小的身軀自由活動。
“是氣溫太低的問題。車子的燃料是從外星玉米里面提煉的,比普通汽油更容易凝固,所以太陽下山之後車子可能就沒辦法正常行駛了。我建議明天上午再繼續前進,不過如果好好保暖的話現在應該也能開。”
現在她的頭發徹底亂掉了。她摘了沾滿油汙的手套,把頭繩咬在口中,坐在地上用手指梳理著。將那頭豐美的長發全部塞進帽子里花了不少工夫,但這種和機械打交道的人大概都被科普過長發容易被卷入高速運動的轉軸這一常識,所以她還是認真地整理好了頭發。我也走到她旁邊坐下:“我也差不多到極限了,所以還是先休息一下明天出發好了。你不會一個人跑掉的吧,所以乖乖給我放哨。”
“所以你是想要一個哨兵嗎?”
“差不多吧,我需要哨兵和機械師,你需要司機,否則我們都沒辦法從這篇玉米海里走出去。除此之外我對你可沒什麼想法。”
我終於肯邀請七種茨進入駕駛室,我坐在駕駛員的位置,而她在副駕上握著望遠鏡盯著公路另一端。這星球似乎已經進入了冬季,雖然氣溫還沒有達到會讓地球人覺得寒冷刺骨的程度,但夜里持續的低溫還是和焦慮一起讓我難以入眠。終於我睜開了自欺欺人地閉上的雙眼,這時那紫紅色長發的女孩就在我眼前,她對我說:“這里睡不舒服的,去車廂那邊躺一會吧。”
前半夜似乎沒什麼動靜,我猜僵屍大概已經失去了我們的方位,於是我才同意了她的提議。
車廂里可能會比全封閉的駕駛室要冷些,於是我們將原本蓋在物資上的那塊布拿了下來,權當被子蓋在身上——雖說這又厚又硬還冰冷潮濕的布和溫暖棉被的觸感相差甚遠。她跪坐在車廂的中央,而我枕著她的膝蓋,從這個角度向外望去可以看到天幕中明亮的群星。
我情不自禁問她:“茨,你是從哪里來的?”
“我?我啊,之前是星際海盜的性奴。”
她沉默了一會,然後在以為我要對她投來可憐眼神的時候笑了起來,蓋在我們身上的布也隨之震動著,冷風灌了些進來。我掖了掖被角,她繼續說:“至少我對警察是這麼說的。我的演技還算不錯吧,他們完全沒懷疑過這個說法,就算我實際上並不是海盜的性奴而是海盜本人。”
“你才多大啊……看起來還未成年吧?那種人會拉這種小女孩入伙?”
“確實不大,不像你,我看了都想揉一揉呢。不過那個時候我比現在還小得多,大概是五……不對,應該沒有五年,五年前我還是個農民家的小姑娘呢。我的村子被洗劫了,那些海盜見人就砍,還放火燒了所有的房子。那時我對他們說,求你們別殺我,把我帶走當貨物賣給誰也行,我不僅不會反抗還會幫著數錢。”
“所以他們就這麼容易讓你入伙了?”
“才沒那麼容易呢——住我隔壁的小男孩也這麼說了,那群海盜讓他強奸自己三歲大的妹妹,否則就一槍崩了他。那槍還是我開的。我也忘了自己到底都干了什麼了,只記得老大說我真是個當殺手的好苗子啊,從那以後髒活累活就都交給我干了。”
她用不屑一顧的語調講述著這些事,身體卻不自然地顫抖著。我翻了個身,臉貼到了她的小腹。她咽了口口水,繼續說:“我跟著他們殺人放火,見到獵物就咬,像荒原上的野獸一樣度過了自己童年的後半部分。我只知道自己不想死,別的什麼也管不了。當時我也想過執行任務的時候偷偷溜出去投案自首,但是像我這樣的人,就算還沒成年,也會被憤怒的民眾聯名請願要求處死吧。”
“是啊,前段時間那個最臭名昭著的海盜團不是落網了嗎?那群呼喊著要慎用死刑的政客都沒能留下誰一條命來。”
“我當時就在那里。特種部隊攻進來的那一天,我脫了衣服跑進了老大的房間。老大不在,所以我把他的女人從船上推了出去,然後戴上她的項圈,鑽進角落里那個籠子。政府派來的人早已接到通知,他們要盡可能營救被海盜綁架的無辜民眾,於是我對他們說,警察叔叔好,人家是七種茨,在被他們綁架的幾年里每天都在遭受慘無人道的虐待——那群人看到我身上的舊傷疊新傷,自然而然地相信了我的話。於是他們把我送到政府出資建造的福利院,還給我配了專業的心理醫生。”
“對我說這麼多,不怕我揭你老底嗎?”
“盡管報警啊?警察也不能把小貓變回來。反正心理醫生早就告訴過警察,我受到了太嚴重的精神創傷所以經常會胡言亂語,甚至有的時候還會到處亂說自己是殺人狂——這下鄙人想投案自首也不可能了呢。不過也好,就算我的口供和事實有什麼偏差,警察也只會當我精神錯亂所以放我一馬。”
我又換了個姿勢,將頭埋進滿是外星玉米提取物味道的被子里。她又說:“我在醫院里躺了好久,身體的病治好了,但是醫生覺得我的心理問題沒這麼好康復。她說我不能太頻繁地和人接觸,否則又會自以為是殺人狂,不過和機械相處就沒問題。所以我才找了這份工作。在這里保養機械是很清閒的工作,沒人願意來只是因為交通不便而已。我又不像別人那樣要一年回個幾次家,就算死在荒郊野外也沒問題,所以老板對我可是非常滿意啊。”
見我對她的心理問題並沒有多關注,她又推了推我,說:“別這麼輕易睡著啊?雖然我沒有被那樣虐待過,但心理陰影說不定還是留下了一些的。這些年里我得到的都是錯誤的疏導,所以這些陰影不僅沒有消失,說不定還擴大化了。可能我真的會半夜變成殺人狂然後割開你的喉嚨哦?”
“那就更好了,畢竟我更擅長對付殺人狂一些。”
說完這句話,我便再也忍耐不住睡意,從童年起每晚都會在夢中出現的那場大洪水又向我襲來。她對我說了句晚安,眼鏡鏡片上反射著星星的光輝。那一夜我睡得並不比同樣被噩夢籠罩的每一夜差,我想,那是因為我還不知道即將和我一同在僵屍堆和外星玉米田里旅行的七種茨小姐到底是如何可怕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