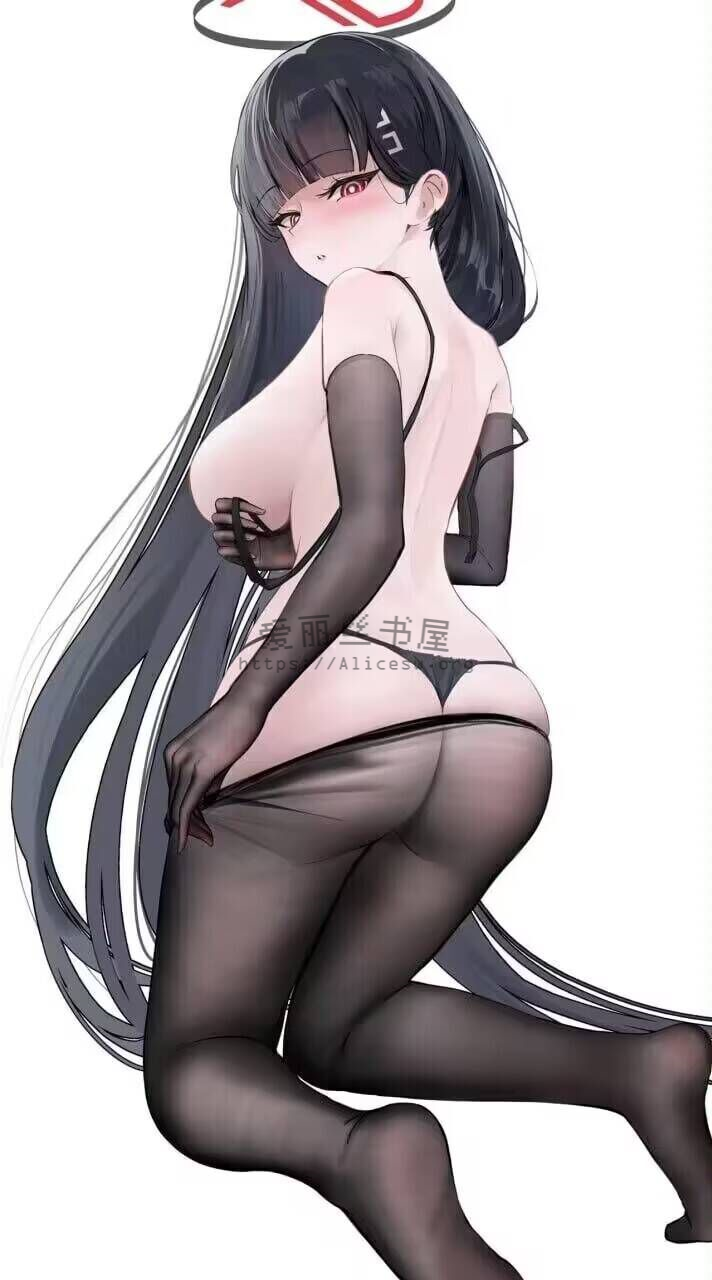15.我想我大概是病了。
我開始沒來由地嘔吐,毫無食欲,隨後是體溫升高,一直沒有降下來。直到我在鼻塞和頭暈的地獄里過了不知多少個世紀,我的大腦都停止了思考。
畫家像是變成了個正常人,他隔一段時間就打開房門,把我懷在手臂里,喂我吃不知道什麼藥丸,把水泱泱的食物往我嘴里塞。他居然很久沒暴躁過了,我從來不知道生病原來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
只在那很早的記憶中,我能恍惚地看見母親的身影,不斷為我調整睡姿,想要緩解我的痛苦。但那太過久遠了。等到我能稍微記起一些事情,生病就伴隨著沒日沒夜的痛苦,直到自己痊愈。
夢,無數的夢在交織。穿插在夢中的,是男人那可怖的臉。
“你會好些的……”
他好像在跟我說話,我卻也懶得張嘴回應了。經常就這麼睡過去,伴隨著男人身上的腥氣和老而不死的腐朽氣息,他的臉都憔悴了蠻多。
那夜,靠外的窗戶閃起亮光,我好像恢復了點力氣,趴住窗口,順著木板的縫隙去看:是一輛黑色的轎車,從村子中穿過,停在山坡下。
我無力去想,只是重新躺回床上挺屍。過了挺長時間,我聽到了醫院的側門被打開的聲音,還有兩個男人的交談聲。
“你就不考慮住到更方便的地方嗎?大畫家?”
“別多話了,蘭,做你該做的。”
在我的大腦低速思考另一個聲音是誰的時候,門被打開了,一股福爾馬林的味道衝了進來,隨後是刺眼的燈被打開。
“這真是,破敗。”
我認識他,准確的來說是認識他的聲音,他是之前救了我的那個醫生。
醫生進來就感嘆了一句,似乎有點驚訝這里的條件之差。
他坐在床邊,用手撩起我的劉海,隨後拿起了旁邊櫃子上的空藥板,來回翻看。
“我給她喂了藥,她也不願意吃什麼東西,病也一直都沒有好轉。”
“當然,當然,你喂的是胃藥。”
我這幾天胃部沒來由翻江倒海的原因似乎找到了一點。
他把住了我的左胳膊,似乎是想讓我側過身子來。他的手很穩當,有股厚重的力量,和他的年齡不是很相配。
我順勢側了過去,他的手從我的領口伸進去,在我腋下夾住一根水銀溫度計,隨後用手扶住了我的下巴:
“說,啊——”
“呃咳,哈——”
我的嗓子發不出聲音來,有什麼黏糊糊的東西堵住了它。
醫生扭過頭去,是對著畫家說的:
“垃圾桶。”
那個男人居然很聽話的出去了,回來時,手里提著一個桶。
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似乎和我只有一只眼睛有關,在昏暗的光下面,那個男人顯得十分頹唐,這七個月來有些好轉的體態又融化了下去。
“咳痰,全咳出來。”
盡管我已經沒有力氣了,我也明白該聽醫生的話。我想深吸一口氣,等到要咳出來的時候,卻又卸了大半:
“呵呼,咳,咳———”
先是斑駁的黑痰,一塊一塊地墜到桶里,然後是粘稠的、大片的黃痰從嗓子的縫隙鑽出,連綿不絕。我感覺到有些窒息,於是本能地用上了更大的力氣,整個身子都顫抖起來。
最後一絲阻塞突然滑走了,我頓時感覺到好了不少,盡管剛才的動作業已消耗了我不少的體力。
醫生埋下頭去,看了看我咳出來的痰,接著抽出了我腋下的溫度計。
“三十九度二,按你說的她在這躺了七天,現在還活著真是一個奇跡。”
他將隨身帶的公文包打開,拿出了一個瓶子和一張小紙袋,從瓶子中倒出了幾枚白色小藥片,裝進了紙袋中,又余出了兩顆。
“熱水。”
畫家又佝僂著身子出去了,回來時端著一杯水。
醫生扶住我的身子,讓我稍微坐起來了一些。接著將藥和水給我服下。水意外的不燙,帶著適口的溫度。
他又扶著我躺下了,我頓時有了困意,和從未如此強烈的安心感。像是浸泡在水里一樣,我閉上了雙眼,在熱到要蒸發的意識里半夢半醒。
在這迷迷糊糊夢與現實的邊緣,我好像聽到了兩個人在交談。
“……她怎麼樣?”
“拜某人所賜,不怎麼樣。有一個好消息和半個好消息。”
“……”
“好消息是她就是得了很正常……抱歉,或許有些嚴重的感冒,不過只要按時吃我給的藥,她會好起來的。”
“那……”
“另外半好不好的消息是,她不是你想的懷孕,因為她的生育能力已經被破壞地差不多了——拜某人所賜。”
“我……”
“行了,有什麼話等她好點了你對她說吧。大家一開始都以為她在你手上活不過三天,現在看來,她倒還挺幸運的。”
“我不夠格。”
“你當然不夠格,然而我們誰又有資格去說你什麼。事情已經發生了,就往好處想,沒准你還幫這孩子脫離了苦海也說不定——我隨便說說,你不要當真,千萬不要,那很惡心。”
“咳,咳咳。”
我感覺到喉嚨不適,咳嗽了兩聲。隨後便是一陣匆匆的關門聲,兩個人似乎想給我一些安靜,卻忘了把這個房間亮得能刺穿眼皮的白熾燈給關上。
16.
我堅信那個醫生一定會什麼魔法。
倒不如說,迄今為止,我所見到的這幫瘋子、怪胎、混蛋,都擁有超出我理解的能力。
我至今不明白,明明被我一刀捅進心髒,出血量極大的那個男人,為什麼還可以活著。
我更不明白,從懸崖邊墜落的我,明明都成了那個樣子,是如何又能活著的,甚至沒有一道疤痕——左眼的缺口除外。
但隨著這一場發燒,我突然就對這些事情沒了興趣。
那個男人,在我休養的這幾天唐突地變了樣子。他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出過遠門,卻正著衣裝,像是有誰會看一樣。
“你想干什麼。”
隨著他又一次打開房門,我將問題拋了過去,並沒有帶什麼多余的感情。
他一下子囧促起來,只是拉了拉帽檐:
“沒什麼。”
說實在的,如果是我剛被抓來的那會,如果我這麼冷淡,他一定是會生氣的。不同於以往的他,變得好像正常起來。
而對他正常的那面報以冷淡,沒來由地讓我心頭產生一股快感。
我總之是不怕他了,他大抵是不會害我性命的,現在就連施暴都少得多。就算他真發怒了,對我動手動腳,我也不很害怕了——一是習慣,二是他真的有些虛弱了,而我在那一方面還挺有活力,最後是誰先累著還說不定呢。
於是,在危險的邊緣來回試探,成了我躺在床上的一大樂事。
至於下床的事情,醫生沒有說太多。他只說高燒影響到了神經,如果不想下肢癱瘓,那就好好躺上一段時間,至少不要劇烈運動。
我一般很聽醫生的話,幸運的是,畫家也很聽從。所以他的變化或許也能歸功於醫生。
當他又一次打開房門的時候,我忍不住了:
“好吧,如果你想畫我的話,沒有比我不能動的時候更適合的時機了。”
“什麼?”
他顯得有些愕然,似乎根本沒想到這邊去。我對他的愕然也有些驚訝。
“……你是個畫家不是嗎?你有多久沒產出作品了?”
“……”
他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藍色的單瞳像是要把現在的我重新解構一遍一樣。
“如果你樂意的話。”
他將門大推開,然後離開房間,不一會,他提著顏料和畫架進來了,接著又折身,帶回來一把水果刀和一枚苹果。
“你吃吧,不妨礙的。”
他把苹果遞給我,也沒問我會不會用刀。還好我會。
他拿起畫筆和調色盤,開始認真地端詳著我。
說起來,這是我第一次主動讓他畫我,也是我第一次觀察他畫畫的樣子。盡管我只有一只眼睛了,他的面容依舊不被模糊,十分可怖。
我拿水果刀切開了苹果的表皮,刀子並不利快,我割地很費力。汁水從手指肚留到手背,接著在臂膀上泛出光的痕跡,房間里緩緩飄滿了苹果的香氣。
我伸手,理所應當一般向著他:
“……紙巾”
他放下調色盤,從一旁的卷紙中撕下兩張,小心地擦拭著我的手。
“……你從來沒有這樣過,你最近怎麼了。”
男人依舊用他那沙啞的聲音問道,像是不很在乎的樣子。
“我該問你的,你變化可比我大多了。”
他沉默裝死,仿佛剛才那段對話不曾發生,直到我把削好皮的苹果放入口中,陡然地聽見他說:
“或許是你有什麼魔法吧。”
我噗嗤一笑,讓他揚了揚眉毛。
“……我的天使啊 ”
他喃喃了兩聲,以為我沒聽到。但我居然沒生出什麼不適感,似乎我也變了。
但變化了什麼,我卻無所謂深究了。我突然想著一個世界,時間靜止在這一刻,哪怕下一刻破碎了,那也該有多麼完美。
我依在床上,陽光順著木板之間的縫隙,將我的意識分割,我便安適地睡了過去。
17、
當我心中逃離的種子都快被這段時間的安穩渴死的時候,她來拜訪了。
那個一身紅衣的金發女性,優雅得好像在發光。一頂紅色的大洋帽蓋住了她的半張臉,從另外半張里,我看見了她那神秘莫測的微笑。
她衝我微笑,我卻毫無頭緒。但我能確認那絕非來自於善意,我感受到了一種久違的情緒——惡心。
我似乎天生帶著人渣感應器。據我母親說的,我出生的時候便不親近父親,甚至有時候會帶著敵意。當然,這也變成了我母親口中父親離去的歸因。
畫家算一個,只是隨著時間與習慣慢慢淡去了罷了。而面前的女人又重新喚醒了這種感覺。
“……毋須那末大的敵意,實在沒什麼理由。”
我站在男人的身後,說實在的,我是第一次看到那個男人這麼緊張。他的汗毛都站了起來,肌肉不安地顫抖。他把左手背在身後,握住了纏在腰上的刀。
我不想他現在失控,於是將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他頓時泄了脾氣,將發汗的手在褲子上擦了擦。然而女人下一句話差點讓他掏刀子:
“我來是為了你身後的那個小丫頭。”
“等等!”
我也沒壓抑住疑惑,從男人的身後走了出來。他想擋在我身前,卻被我攔了一下。
“你說清楚,不要說那麼讓人誤解的話好嗎?”
女人抬起了右手,無名指上帶著一枚銀色的戒指。
“是我太過唐突了,容我解釋一下罷。”
她看著男人,淡灰色的眸子里閃著光:
“我需要她的血,你知道理由,每隔十年的慣例。”
“你不缺她這樣的收藏,你不可能會缺少這些……‘副產品’。”
“這次的情況不一樣,我需要血的本源也活著,而且血液要足夠新鮮,所以必須請她跟我走一趟了。”
“你可以把蘭叫過來,在這里完成儀式。”
“不可能,這里的怨氣太重,完成儀式的一瞬間我就會變成骸骨。”
“找不到其他替代?”
“我忙著維護收藏,等反應過來已經是這個時候了。”
女子的微笑帶上了一絲苦澀:
“我給你一個承諾,這次的儀式完成後,直到這個女孩死去,我都不會再向你要求什麼了。”
男人只是用獨瞳盯著她,良久才開口:
“……這該讓她決定。”
“我可沒想到你會顧及到她的想法,只望這不是你的推辭。不過你說的對,我確實沒有強迫一個小丫頭的興趣,讓我和她單獨談談罷,就這一會。”
我扭過頭,看見畫家真的在示意我決定,突然感到有些不適。
我很想拒絕,我不確定能不能在另一個瘋子的手中全身而退,我想讓男人主動拒絕她,但他突然又開口:
“……你可以放心,她不會傷害你。”
我頓時有了火氣,他的潛台詞有夠明顯了。
“好啊,那談談唄。”
我對他翻了個白眼,他的眼神立馬躲閃起來。
裝模作樣。
18、
“你想不想回去?”
當她拋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嗆了一大口水,然後緊張地盯著房門,深怕男人會突然闖進來。
“什麼?”
“你想不想離開這里,回到家里,回到學校,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
我張了張嘴,但實際上並沒有立刻回答的勇氣。
“……你小聲點吧,別被他聽到了。”
“我很了解他,只要我說不讓他偷聽,他定是會遠離這里的。”
“他憑什麼聽你的?你又了解他什麼?”
我皺緊了眉頭,她卻只是抿了口水。
“看起來你的確被安逸蒙蔽了眼睛,我想你記得是誰把你從正軌的人生中拖拽出來,又是誰把你殘害成這麼一副模樣。”
可能是因為窗外的陽光,我的眼神一陣恍惚,我似乎真的在權衡了。不過,我能確定的是,就算以前的人生不能算做正軌,也比和這幫變態在一起要強。
“我可不覺……就算是如此,也已經這樣了,我又何必引他發怒呢?”
“你沒有看清他的本質,玉子,野獸再怎麼溫馴,也會有失去理智而傷人的那天。”
“我問你了!你憑什麼說得這麼了解他一樣?”
我站在椅子上,挺直了身子,越過矮桌,幾乎要壓到她的臉上。
“上一個,像你這樣對他有善意的人,已經死了。被他殺死的。”
“去你的善意……”
“婭瀾•斯洛冗思,十七歲的時候,死於銳器切割傷。她和你一樣有著栗色的好看的頭發,她現在在我那里。”
我突然沉默了,不知道該如何回應。
“……我從未對他有過善意,我只恨他,只是現在我更恨生下我的母親罷了。”
“你的嘴里沒有一句真話,小丫頭。你騙不了我。”
又是良久的沉默,眼前的女人似乎特地來給我找不快。
“所以,還是那個問題。你想不想,回去。”
“……你怎麼幫我。”
“很簡單,順路將你帶回家,然後和這個男人隔絕往來。我的匿藏處不被你和蘭以外的任何人知曉,只要斷絕音信,這個男人就永遠找不到我。他只是一個假畫家、流浪漢,等到你搬家,他便永遠找不到你,或是報警將他繩之以法,你就永遠擺脫了這個噩夢。”
“聽上去太簡單了。”
“做起來也很簡單,小丫頭,只要我一心幫你,做成這件事就如同喝水一般簡單。”
“你沒理由幫我,我也付不起你的代價。”
她聽到我說完,臉上浮現出更加詭異的笑容。
“你當然付得起,只是一份血液,和一個不值錢的口頭契約罷了。”
她站起身走到我的身旁,抬起了我的下巴。
“我要你……變成我的收藏。”
19、
紅夫人提出的契約是三方的。她渴望身心的永生,惡魔期待殘破的靈魂,我可以回家。
惡魔只是我心里這麼叫,但祂們似乎並不喜歡這個稱呼。紅夫人讓我不要隨意說出口,稱呼祂們以“殘靈”就好。
祂們的契約真的只來源於話語。在承諾說出口後,我的舌頭突然刺痛,照了照鏡子,在舌尖處很清晰的出現了一道十字黑紋。
“殘靈會寄宿於你的部分器官,吸食你的氣運與命數,孕育名為‘黑胎’的種子。祂們只喜歡年輕的食物,黑胎會將你的身體維持在現在這副模樣,但你的靈魂會隨著黑胎成長而質變,你在現世活的越久,你的靈魂就會愈發可口。”
我突然有些後悔。
“死後的世界……是什麼樣的。”
“是做不完的一場夢,是永不變的黑暗,殘留的意識不斷質疑自己存在的理由,直到徹底陷入永夢,消散為撥動鳥羽的清風。”
她的眼神變得有些遙遠,像是在回憶。
“聽起來和活著並沒有什麼不同。”
我只是聳了聳肩,卻看到她閉上了眼睛。
“並不是……罷了,我與你說甚。”
她站起來,領著我出門,卻看到畫家佝僂著身子,對著大廳里唯一一扇沒有封起來的窗戶發呆。
“我要帶這孩子去我那里了,大畫家。”
紅夫人走到他的身側,看著窗外的山林,平淡地說道。
他突然把頭埋下去,聲音幾乎哽咽。
“所以她同意了……我沒有資格拒絕。”
“在你殺死婭瀾的時候,你就已經失去資格了。只是帶她出去消遣一天而已,你有什麼好傷心的。”
“我明白,我明白。”
畫家自始至終沒有看我一眼,我看不到他的正臉。但一直縈繞在我心中的恐慌和困惑,驅使著我開口:
“你……”
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
“你為什麼要殺死那個女孩,那個婭瀾?”
真是個蠢問題,我難道不知道眼前的男人是一個怎樣的變態嗎,他殺人還需要理由嗎?
可他真的在猶豫,他的嘴唇抿住、顫抖。早衰的皺紋無助地幾乎要崩潰,他剩下的那顆眼球里,泛白的眼瞳孔卻深邃如海。
那不是一個“沒什麼理由”的答案,他真的在思考怎麼告訴我。
“……不是現在。”
“什麼?”
“等你回來吧,等你回來。我會告訴你一切,所以求你了,不要走。”
“我……”
我幾乎要反胃了,男人的話語扭曲異常,他明明沒有說這些的資格,卻說的那麼理所當然。
但,比反胃更多的,是不甘的憤怒。
“好啊,那就等我回來。”
紅夫人低了低頭,往門外走去。我跟上了她的步伐。
“你殺了人,你毀了我,你就是永遠的人渣!你等我回來,然後因為惱羞成怒殺了我吧!”
我跺了跺腳,一副生氣的樣子,扭頭跟上了紅夫人的步伐。
他什麼多的感情也沒有。只有悲哀,看著我們離開醫院。
我想我大概是胃病了,我的反胃無法停止,糾結的氣體從食道涌上鼻腔,在喉處翻滾。
20、
“紅夫人,你去那個畫家那里做什麼?”
“紅夫人,你要走了,下次得什麼時候回來?”
“紅夫人,你看我可以做你的收藏嗎?”
我們是被一個嘰嘰喳喳的小女孩領下山的。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這山後還有一條更為緩和的坡道。
那個女孩領在前頭,時不時回頭過來,黑色的馬尾辮晃來晃去,腳步在亂石堆和泥巴上自由地穿梭。
“要你做我的收藏尚且太早,待你再長成一些吧。”
“那你身後那個女孩又比我大多少呢?等等——”
她立在一片石灘上,身後就是公路,停著一輛黑色的轎車。
“她不會就是大畫家撿來的那個孩子吧。”
我看見紅夫人微微點頭,隨後女孩的臉立馬就垮了下來
“啊~我不喜歡她。”
女孩在大石頭上來回跳躍,在言語間還參雜著難以辨認的喃喃:
“先是勾引番薯哥,害他被畫家砍成十二塊,接著又毫不自覺地來到我們的村子,還到處亂跑。要不是事後焦臉叔躲得及時,指不定會變成什麼樣呢。”
她說著,對我扮了個鬼臉。
我簡直無法理解她的話語。但我多少猜到了,這是另一群人渣飼養出來的惡犬。
“我不可能站在那里等死,那叫正當防衛。”
“正當防衛?”
女孩突然單腳站住,雙手張開保持著平衡,做出像鳥兒滑翔一樣的姿勢,隨後一跳便到了我跟前。
“哈哈,我喜歡那個詞,你叫什麼?”
“稻妻玉子。”
“tama……嗯,我叫潔莉可,是‘外國人’哦。”
她好像把這當成什麼了不得的身份。她分明長著亞洲人的面孔。她只有眼睛泛著灰光,充滿著幼稚又可恨的好奇。
“閒話就聊到這里吧,潔莉可,你的爸爸在哪里?”
“爸爸?哪個?啊,是有徽章的爸爸吧,雖然不是很懂,但他讓我給你帶話哦。”
“他說了什麼?”
“他說他不會再來了,他讓黑爸爸好好照顧我。”
“這樣就夠了。”
紅夫人點了點頭。
“他是什麼意思呢,紅夫人?”
“就是結束了,所有的這一切。”
“唔……”
她還在思考,紅夫人便示意我跟上。
直到走出了石灘,來到了公路上,我拉開車門,卻不由自主地回了頭。
她還站在那里,似乎一直在思考,但和我對上眼神後,便興奮地揮了揮手,長大了嘴巴和我道別。
我看的清她的口型,微弱的聲音也能穿過石灘,證實了我所讀出來的話並不是誤解。
“下次一定,一定要嘗嘗你的味道!”
我上了車,關上後座的車門,不禁笑了出來。
“你笑起來,終於好歹有一些這個年齡段的女孩的影子了。”
身旁的紅夫人揚揚眉毛。
“是麼,我正常了一點嗎?”
“一點。”
坐在駕駛位的是一個穿著嚴肅的老頭,在我上車後,他踩下油門,離開了這片空無一物的荒山。
原始地址:https://www.pixiv.net/novel/show.php?id=8627646
或者:https://www.pixiv.net/novel/series/8627646
總之就是這倆中的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