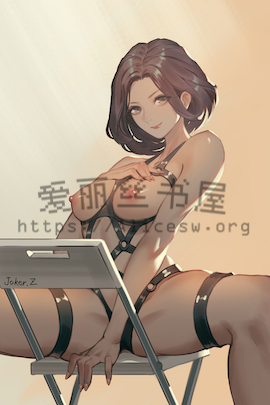第26章 【寫在建黨百年】上海娼妓改造史話摘抄
《上海娼妓改造史話》序——曹漫之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具有國際意義的大事,今年美國哈佛大學有個研究娼妓問題的社會學教授來訪問我,她調查比較了世界上幾十個城市,又在上海住了一段時間,考查了解了五十年代上海改造娼妓的全部過程,最後她對我說:像上海這樣解決娼妓問題,全世界沒有先例。這位女教授認為,上海娼妓改造的最大成功之處有兩點:一是改造徹底,上海曾是世界各大都市中娼妓人數最多的一個城市,解放後只經過七年時間,從公娼、暗娼到各種變相賣淫全面徹底地消滅了。二是工作扎實,世界上也有一些城市踢出喝實施過取締娼妓的法令,但取締後妓女出路何在,如何使她們成家立業,變成社會的生產力,從而最終根絕娼妓,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中國解決了,而上海做得最好。上海婦女勞動教養所收容的7500多名妓女和各種變相賣淫者,除極少數屢教不改分子以外,全部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
上海娼妓改造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歷史事件。當年我是在陳毅同志領導下,和市公安局李士英局長,楊帆副局長直接主持下參加這項工作的,從妓女浸入教養所後治愈性病到從事改造教養,主要由我負責。早在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初,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領導機構已在江蘇丹陽組成。我是上海軍管會政務接管委員會副主任,並出任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兼民政局長。我們政務接管委員會的牌子就掛在民政局。我們在接管中碰到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主要遇到了三個問題:其一是對以杜月笙、黃金榮為頭子的青洪幫兩大流氓集團;其二是對在他們羽翼下的各種社會腐敗組織;其三是構成冒險家樂園的各種集團性的社會黑勢力,包括娼妓、職業乞丐、舞女、偷盜扒手等等、這些都是有領導、有訓練,有固定活動場所的集團性的社會勢力。對每個組織每種勢力的首腦人物(包括去了香港等地和留在上海的)都要采取不同的方針和對策,對他們中的全體分子都要指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分期分批地、全面徹底地進行社會改造。而三大問題種最復雜最困難的則是對娼妓的改造。
娼妓的存在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盡管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法律條文規定過娼妓之存在為社會之必須,盡管從封建的開明君主到資產階級的不少政治家都相繼提出過禁娼,可是沒有一個國家取得成功。娼妓改造之所以特別困難、特別復雜,那是因為:一方面,娼妓是壓在社會最底層苦難最深的階層,在舊中國,她們不進要像所有婦女那樣受神權、政權、族權、夫權四大繩索的捆綁,而且要忍受作為一個人最不堪承受的凌辱和摧殘。另一方面,妓女身上又集中了人世間最腐敗、最無恥、最惡劣的種種習性,妓院是惡勢力泛濫的場所。在妓女身上,她們既是災難深重的弱女,又是墮落成性的游民。是的,妓女是游民,我們中國共產黨根據階級分析的科學方法,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開始,酒吧妓女的階級成分定為游民,她們不是工人農民那樣的勞動者,而是依附舊社會黑勢力生存的寄生蟲,但這不是她們自身的罪過,是萬惡的舊社會強加給她們的。
正是妓女的這種雙重身份,使我們確定了改造娼妓的政策基點,在指導思想上明確妓女是需要極大同情的對象,在改造方法上卻要借助強制執行的某些特殊手段。我們不是用慈善家的善心來解決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肮髒問題,而是用強制改造的手段,達到既徹底清除一切汙泥濁水,又能最終解放一切改造對象(包括妓女在內)的目的。我認為這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人道主義。
既然如此,為什麼在上海這樣娼妓為害甚烈的大都市,不是一解放就里脊取締,相反害准許妓院開業,政府收稅,直至1951年11月25日,在上海解放兩年半以後,才明文下令禁娼呢?還在丹陽訓練接管上海的干部時,就多次討論這個問題。有一部分同志認為,對如此丑惡的社會現象,一天也不能容忍,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我當時找了黨內黨外的許多同志(包括上海地下黨的同志、情報系統的工作同志,以及對妓院情況及其背景較熟悉的同志),開了多次的座談會。絕大部分同志主張不能馬上取締,因為上海這樣的十里洋場,萬惡淵藪,百廢待興,如果我們一解放就取締娼妓,既沒有足夠的醫療條件為她們醫治性病,更沒有專項的經費為她們安置就業,其結果只能把她們從妓院推到社會上去,使她們流離失所,暗中賣淫,這就會造成比公開掛牌更慘的悲劇。我們既然收容了妓女,就要對她們的出路和新生負全部的責任,而決不允許出現這樣的悲劇。陳毅同志綜合大家的意見最後決定說:“剛進去(指進上海)恐怕還不能馬上解決妓女問題,只好讓她們再吃幾天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將來在中國的語詞中,‘妓女’這個詞必將成為一個歷史名稱!”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在丹陽秘密通知地下黨上海市委,告訴他們,熟悉妓院情況同妓院打過交道的同志不要分散,全部集中在公安系統,准備不久的將來作為收容改造的骨干力量使用。
經過兩年半的准備工作,這一天。共產黨的認真負責體現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個環節。治療妓女的性病急需盤尼西林,當時我們既不會生產,由於美帝國主義的封鎖,也無法進口。我們手中只剩下了從國民黨反動派手中繳獲的,從美國進口的數量不多的盤尼西林,那是留給負重傷的志願軍戰士用的。為了給妓女治病,陳毅同志親筆手令各個解放軍縱隊後勤衛生部,把這些盤尼西林藥物集中起來,先供婦女教養所使用。當時少數妓女聽信謠言,堅決拒絕打針,醫務人員硬是給她們注射。後來,妓女要安置就業了,一個方案是,少花點錢,就地安置在上海工商企業中,但考慮到不脫離上海這個環境,不少人還難以徹底改造。於是,下決心用了聯合國救濟總署留下來的一批救濟物資,相繼開辟了蘇北、皖南、新疆、甘肅、寧夏等安置基地,辦工廠,建農場,幫助她們成家立業。對改造妓女,我們自始至終堅持三條:一是治愈性病,二是安置就業,三是解決婚姻。正是靠了這三條,世界娼妓最為嚴重的上海娼妓終於絕跡,全世界都為之嘆服。
這段歷史今天已經成為過去了。本書作者搜集了很多材料,訪問了許多當事人(包括改造者和被改造者),以翔實的史料和生動通俗的筆調,再現了當年的歷史。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這不僅對認識我們的社會和社會變革很有價值,而且對研究全世界都未能解決的這個社會問題提供了有意的啟示。讀了這段歷史,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婦女,理應感到自豪。當然,這本書還沒有來得及對解決娼妓問題作理論上的探討,這個問題確實大可研究,我期待著更有深度,更有見解的學術專著問世。
1987年6月5日
全書節選段落:
“在世界八大都市中,公娼人數與城市總人口的比例,以中國的兩大城市為高,其中尤以上海為最高。甘博爾調查時,北平的公娼人數是3135人,城市總人口為811556人,對上海他沒有提供絕對數字,根據他調查的比率推算,當時上海人口約為250萬-260萬人,那麼公開掛牌營業的公娼就有近2萬人。這個調查雖然未必精確,但畢竟反映了上海娼妓之多,加上私娼,數字就更驚人。鮑租寶在1935年出版的《娼妓問題》一書中提到,據他當時的調查,上海的公娼和私娼相加約在6萬至10萬人之間(因私娼流動性大,且很難確切統計,故上下幅度較大),當時上海全市人口約在360萬人,其中女性約150萬人左右。也就是說,20名左右的上海女子中,就有一個是娼妓。而如果剔除十幾歲以下的幼女喝五十多歲以上的老年婦女,娼妓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上海的娼妓之所以在世界都市中比例這麼高,根本原因在於帝國主義侵略下上海半殖民地都市經濟的畸形發展。鴉片戰爭後,上海首批開埠,各國帝國主義競相來到上海搶占租界,數年之間,高樓林立,人口驟增,隨著都市的日益繁華,為‘冒險家’‘淘金者’服務的淫樂視野,也就急性膨脹。周圍農村的迅速破產,促使貧苦女孩紛紛逃來上海謀生,很多人不得不陷入火坑。這個數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後,社會經濟的凋零和道德的淪喪,反映了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婦女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壓迫下所蒙受的巨大恥辱。”
“上海公開的娼妓,始於清朝道光年間,盛於同治光緒兩朝。國民黨反動派‘保護’並發展了娼妓制度,而日寇侵占上海後,娼妓更是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1948年元月出版的《上海市大觀》上有這樣一段記述:‘……滬濱風月,天下艷稱,青樓妙姬,韶顏稚齒,煙視而媚行者,不可計數……海上自遜清同光而後,女閭之勝,殆甲江南,大道青樓,珠簾瑣院,清歌一曲,粉頭十千,養成一時佚蕩之風,釀為今日奢靡之習。’”
“舊上海的反動統治者之所以保護並支持娼妓制度,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他們荒淫無恥的生活,腐蝕人民的反抗意志;另一方面,他們可以從妓院獲得大筆收益,所為‘花捐’‘花稅’是歷代統治者的主要稅源之一……妓院就這樣成為反動統治階級榨取婦女血淚的‘一本萬利’的‘合法’事業。日寇侵入‘租界’後,據侵略者當局1942年《年報》所載,該年上海妓院(公娼)數目增至3900余家。1945年日寇投降後,國民黨反動派為了無恥地滿足美國主子和戰爭暴發戶的獸欲,一本正經地提出要對娼妓加強管理,當時的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冠冕堂皇地提出了一個‘化私為公,化繁為簡,化整為零’的娼妓管理計劃,要把私娼變為公娼,對公娼進行‘身體檢查’,把變相的賣淫場所變為公開合法的妓院,把四散的賣淫活動集中為大規模的‘人肉市場’。警察局長宣鐵吾在1946年3月‘臨時參政會’的報告中宣布‘擬以虹口提籃橋分局轄境化為娼妓集中的所謂風華區’,還計劃將其擴大。正因為如此,直到1949年1月上海臨近解放時,盡管國民黨達官貴人,紛紛逃離上海,和反動勢力關系密切的許多上等妓院大批解散,當時登記的妓院還有八百多家,妓女四千多人。實際上,據租界巡捕房的不完全統計,上海靠賣淫為生的婦女約有三萬人左右。”
“婦女被賣為娼妓有種種方式,一種是買絕了的,叫做‘討人身體’,妓女也叫做‘討人’,是為‘斷賬’。賣了‘斷賬’的妓女,生死完全操縱在妓院主手里。另一種是‘包賬’,得了一筆身價錢,包定要替妓院主當幾年妓女,這幾年的生死自由一切由妓院主處置。還有一種是‘拆賬’,名義上有人身自由,妓女可以從自己的血淚收入中分得一小部分,大部分(通常是六七成)歸妓院主……做‘斷賬’和‘包賬’的,不但賣身收入全部歸妓院主,就是嫖客有時私贈給妓女一些小玩意,也要統統被妓院主搜身而去。總的說來,上海的妓女分‘捆’著和‘站’著兩種。前者沒有自由,一‘捆’就是五年,十年。後者名義上有選擇客人和隨時離院的權利,但必須付出相當的代價。嫖客要是看中了某個妓女,必須付出妓院老板的開價,這個妓女才可能脫離妓院。‘捆’著的妓女,若有嫖客看中,也可‘贖身’,但這時妓院老板更會漫天要價了。”
“妓院對妓女的剝削,除了固定方式以外,還會耍出各種各樣凶狠毒辣手段,使受害者永無出頭之日。例如向妓女放高利貸,罰款,引誘妓女吸毒及賭博等,牽制和迫使妓女繼續為娼。”
“上海中下等妓院的一般妓女,老板規定每晚要接八個左右的客人,一個月就要接二百多個,所以,妓女落進火坑不滿半個月,就會傳染到花柳病。日久皮破日爛,出賣一次肉體,就是遭受一次慘重的刑罰。如果接不到客人,等待著妓女的就是挨餓、罰跪、鞭打、火烙……六合路裕德里一家妓院主,逼著一個滿身梅毒的妓女繼續接客,那妓女實在受不了慘痛,死活哀求,妓院主就讓她跪在兩個敲碎了的玻璃瓶底上,兩腿鮮血淋淋,不幾天便被虐待身死。還有一個叫徐淑敏的妓女,她三歲即被人拐賣,賣了‘斷賬’,到臨解放那年正好二十歲。十多年來,她因不堪忍受賣淫的慘苦,多次拒絕接客,先後被妓院主用尖刀戳破肚子,用竹筷子扎破臉頰,還把她捆起來吊在天井里。和她同院還有個叫翠琴的妓女企圖偷偷從良,竟被妓院主活埋。”
“緊張的戰斗進行了14個小時。上午10時,上海封存妓院這一莊嚴的歷史使命宣告完成。全市共封閉了妓院72家,收容公娼181名,暗娼320名,總計501名。並對違背政府法令、依靠剝削妓女為生的324名妓院老板、老鴇、鬼頭等集中到第一勞動教養所,一邊強制勞動,一邊進行審查,然後按其罪惡輕重分別作出處理。”
“上海各界人民熱情贊揚、積極配合人民政府封閉妓院。福州路老會樂里的居民興奮得不得了……‘夜都會’妓院所在地的福裕里居民還專門寫了大標語,貼在大門上:歡迎夜讀會姐妹們站起來!走向光榮的勞動生產崗位!……老閘區‘就是我’妓院的妓女們回去取衣服時,沿途居民都為她們得到新生而感到高興。汽車送著姐妹們到教養所去的時候,一路上行人都用喜悅的目光望著他們,好像在為她們祝福。一些經歷了清朝、民國、敵偽等好幾個朝代的爺爺奶奶們老淚縱橫,無限感慨地說:‘世世代代,見過多少良家婦女被逼為娼,見過多少浪蕩子弟在書寓青樓撩到一生。但是哪朝哪代能為這些能為這些被害的女子撐腰伸冤?哪朝哪代能挽回如此傷風敗俗的世道人心?只有共產黨,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說到做到啊!’”
“1951年12月27日,天寒地凍,北風呼嘯。通州路婦女教養所的廣場上豎起了兩條巨幅標語:‘往日有冤無處訴,今朝翻身吐苦水!’全所姐妹集中在一起,要向昔日的仇人作最後的清算。市民政局、公安局、人民法院、婦聯的五百多名代表來了,接著由武裝民警押著五花大綁、罪大惡極的妓院老板和拐賣婦女的私娼老板等人進了會場。許多姐妹呼地站了起來,‘打倒惡霸’的口號聲震天動地。任人摧殘的弱者,筋條要做主人,清算惡霸的滔天罪行。”
“這是怎樣的非人生活啊!她們從肉體到靈魂都已全然不屬於自己,她們存在的唯一價值就是供人蹂躪。她們的賣身所得全部落入老板的腰包,連‘相好’私自贈送的財物也被搜刮一空。她們一天接待八個、十個嫖客都是常事,最多的竟達二十多個。十天半月就染上了花柳病,做一次‘生意’就是受一次慘苦的刑罰。接客少了,皮鞭、藤條、燒紅的炭、明晃晃的鋼針……種種酷刑把她們折磨的死去活來……在張菊卿妓院,妓女一天接不到客,就要罰‘跪香’。大冷天,脫光衣服跪在洗衣板上,不到一炷香點完不給起來。有一次馬路上漲大水,漲到膝蓋深,老板硬逼著妓女穿著木屐去拉客。有一個叫黃培芳的妓女突然流產了,肚痛如絞,苦苦哀求放她一天假,老板一腳把她踢進了水塘,一陣大出血後被人抬回房中,二十一歲的黃培芳就此絕了月經。妓院中還有一個姐妹叫王莉莉,她得了梅毒,下身的肉爛成一個一個小洞,遍體長滿了楊梅子,張菊卿和張金芳兩人說要給她治病,竟用燒紅的鐵條把楊梅瘡燙焦,再用剪刀減掉,擦上食鹽和明礬,一道烙痕,一聲慘叫,一汪鮮血,這個姐妹就這樣活活地痛死了。”
“還有一個叫小梅的,生了肺結核,重病纏身,老板戴雲卿說:‘不能賺錢,沒有用了。’決定把她處置掉。她還沒有氣絕,就被裝進了薄皮棺材,蓋上棺材還能聽得到她微弱的呻吟聲。滅絕人性的戴雲卿,竟叫人把長長的棺材釘,對著她胸口所在的位置,狠狠地敲下去……字字血,聲聲淚。姐妹們一個接著一個上台控訴。有的披頭散發,有的一言未出就泣不成聲。還沒開口,喉頭就哽住了,眼淚不斷地留下來……最後,人民政府依法判決五名罪犯死刑,立即執行。為非作歹,血債累累的惡霸得到了應有的下場,壓在姐妹們頭上的石頭被搬掉了!”
“檢驗結果表明,第一批檢查的515名姐妹種,患各種性病的有459人,占88.3%……經過全面檢查,發現姐妹們身上的性病主要有四種……”
(對於娼妓性病病情的具體描述因為極易引起不適,故而暫時隱去——摘抄者注)
“性病一定要根治,這不僅為了解除姐妹們的痛苦,更是為了鏟除舊社會遺下的毒瘤,但是,治療性病要用當時價格相當昂貴的盤尼西林(青霉素)。一個早期梅毒病人,每天注射60萬單位,十天一療程,最少要三個療程,按當時價格,就要一百多元(采用55年後新幣值,下同——編者注)。一個二期、三期的病人,得用100萬單位的盤尼西林,反復十幾個療程,時間在半年甚至一年以上、所用藥物價格昂貴且不說,解放不久的上海,盤尼西林還全部要從海外進口,國家要花大量的外匯,而且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封鎖下還很不容易買到。當時上海醫藥倉庫里的盤尼西林,原來是專供朝鮮戰場志願軍傷病員使用的,可是,姐妹們沒有盤尼西林就治不好性病,為此,報告從教養所打到民政局,一直送到陳毅市長的辦公桌。”
“‘先給教養所,志願軍戰士另想辦法。’陳毅市長果斷地作出了決定。”
“如果說,血淚斑斑的控訴,是把姐妹們救出火坑的第一課的話,治好性病,恢復健康,就是第二課,而且是最使姐妹們感激的一課。過去妓女得性病,妓院主總是逼迫她們接客,待到性病入骨,下身腐爛,實在不能接客時,便把她們關起來,讓她們活活爛死、餓死……姐妹們懇求老板給口薄皮棺材,妓院老板冷笑一聲:‘譬如死條狗!’這一切,都牢牢地記在姐妹們的腦子里。如今,共產黨竟要省下志願軍英雄用的針藥,先給她們治病,這件事一傳開,整個教養所內簡直發狂了,好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們有的奔走相告,有的痛哭流涕後又放聲大笑,有的竟‘撲通’一聲給醫生跪下,連連磕頭。有個叫馮蘭英的姐妹,十八歲時給賣絕身子,已經做了十年妓女,染上一身惡瘡。當她得知人民政府要替她治病的時候從這個房間跑到另一個房間,大聲說:‘十年來,我一直在假笑、苦笑、含著淚笑,今天可是開開心心地真笑了!’……楊紅梅剛進所時,性情暴躁,對政府的收容教養政策不滿,專講怪話。後來住進醫院,別人告訴她,她所用的藥是當時奇缺的貴重藥物,要用外匯進口,還很難買到,她吃驚得睜大了眼睛。一年以後,她的病徹底痊愈了,她跑到所辦公室說:‘人家志願軍急需用進口盤尼西林,他們是流血拼命,保家衛國的英雄,這是理所當然的;現在我這樣的人也用上了這樣貴重的藥,能不感動嗎!我只有拼命干活,加緊改造,來報答人民政府的大恩大德。’當她得知棉花工廠彈出來的棉花制成藥棉是送到朝鮮前线時,便一再要求到最繁重的棉花工廠里彈棉花,不久被評為勞動積極分子。”
[newpage]
摘抄者後記:本文全部摘自《上海娼妓改造史話》,來自那一段波瀾壯闊的,真實的歷史,一個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中國把鬼變成人的傳奇。翻身的姐妹們後來陸續投入到了勞動生產當中去,投入到了為人民為國家的奉獻當中去,在這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為造福人民貢獻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是一個自認為並沒有多少能耐的普通寫手,也曾幻想過青樓的奢靡,幻想過名娼佳話。而當我真正了解到那一段歷史時,我便有了一個新的想法:我要將當年這些被苦難壓迫的姐妹,和她們在人民政府的幫助下得到救贖,走向新生的故事,用我自己的方式寫出來。
我知道,我們所處的同樣是一個物欲橫流,觀念繁雜的時代,而我也只是閃爍的霓虹燈光陰影遮蔽下的小生物,為躲避愈發雜亂的競爭而偏安一隅。但即便是這樣,我也明白,什麼是穩固我們生活的同時,在前方為我們照亮道路的明光。而我也理應向往著那束光,貢獻出我自己的一份薄弱的熱量。
這篇摘抄,算是一紙並不算合格的建黨百年賀禮文。謹作為我個人表達態度的,一個頗有些快捷而簡易的方式。所謂誠意,也不過是又將整本書粗淺地吞讀一番後挑選了幾個有代表性的文段放置於此,實在難說虔誠。而在之後的日子里,我也會將書中所記載的十名姐妹翻身重生的故事,盡可能地用我自己的語言轉述,作為我之後為此付出的努力,而去盡力完成。
最後,願紅旗遍插寰宇,願理想照耀人間。願壓迫不再,願共產終成!
寫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