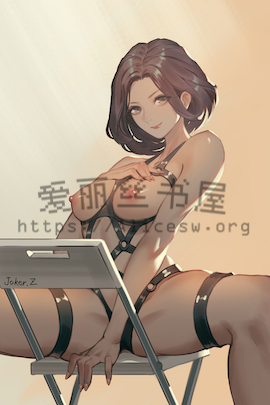他只說他們行事醃臢,道姚修身為讀書人做這事當以為恥,卻不知道要沒這些個字畫,姚修早待不下去。
姚修當初進京時的銀錢還是族里湊的,他在京中住了六年,當初連個筆墨都買不起,不偷不搶,就連給個稚兒當啟蒙先生也甘願。
陳元卿哪里懂,他生來便是貴胄,姚修便是天下文曲星下凡又如何,還不是敵不過卑劣的小人。
就像她在他身邊曲意逢迎,他要如何便當如何,也不知哪里未當心就觸怒了他。
陶幼金不該是這樣的,十里街上誰不知道陶家婦人不好惹,她以前和她那嫂子掐起架來,手都動過。
“娘子?”王婆吃驚地喚了聲,娘子怎就哭了,看著比姚相公還要傷心的,“姚相公都說了,這科不中下科再考就是。”
王婆心覺不對,娘子莫非對姚相公有別的想法。
幼金拿袖口拭了拭眼,對王婆道:“我這也不知道想的什麼,你快些去灶上做飯吧,我剛去鋪子買了些肉回來。”
她心想,哪還有什麼下科,有那人在,姚修這輩子怕是都別想考中。
這一朝榜上題名的差別,幼金不是不清楚。
晚間那人又來,幼金聽到敲門聲制止了王婆:“我開門,你回房歇著去,一會兒將門鎖緊了,無論聽到什麼可別出來。”
“娘子?”這話聽著怎這麼叫人心慌,而且娘子把自己關在屋里一下午,臉色看著不大好。
“你之前亂敲門他惱著呢,難不成你還想讓他再踹一腳。”幼金笑看著她,“你不是說他喜愛我,他舍不得這般待我,對你可半點都不留情。”
王婆一想不正是這個道理,大人的心思連她都瞧出來了。
“娘子你軟些便是,這戲文里常說,再硬的漢子都過不去那繞指柔。上回老婆子在旁看著,大人瞧您那眼神,怕是您要什麼都給的。”
王婆往屋子里走。
還要幼金再如何軟,她都已經給陳元卿跪下。
陶幼金完全忘記,陳元卿怎就這麼巧,今日剛放榜他人便來了。
屋子里只聽得她撲通跪在地上的聲。
“胡鬧!”陳元卿見她這樣,眸里那點光亮盡消逝了去,他盯著揪住自己直裰的婦人,勉強將心中怒火壓制下去,“有話再說,你先起身。”
幼金卻仍跪在那兒,她甚至重重給他磕了一個頭。磕得陳元卿頭暈目眩,幾乎站不穩身,他譏諷笑了聲,似是已清楚她的心思。
看來她完全未聽進去過自己的話。
他給過她機會的,她叫自己信她,他信了。可她如何回報自己,為了姚修那書生不分青紅皂白來指責他!就這樣還說未對姚修存有私心!
陳元卿閉了閉眼,他其實一直有幾分欽佩姚修,庶民出身卻得兩朝帝王賞識,追捧者更是無數,這婦人喜歡上他也不足為奇。
男人撣了撣直裰,抬腿往前走了兩步徑自坐上榻沿,不動聲色問陶幼金道:“又有甚事你說罷。”
他一副若無其事的模樣,幼金仰頭望了眼高高在上的這人,她的眼眶忽被糊住了,連他的樣子的都看不清。
她咬著下唇開口道:“大人,您饒過姚修吧。”
陳元卿點頭,反問她:“幼娘,你以什麼身份來求我?”
兩人視线對上,幼金僵硬地別開臉,她答不出。
他說喜愛自己,自己在他那兒也不過是個玩意兒,所以他對自己的承諾從來都是反反復復。
陳元卿也不逼她,甚至起身給自己倒了杯茶,那茶盞是幼金慣用的,就擱在幾案上。
屋子里的氣氛越來越冷。
她跪在那處久了身子搖搖欲墜,腿都沒知覺,陳元卿皺眉喝了口茶。
小娘子發髻微散,終於伏下身去:“您覺得是什麼便是什麼。”
她先前與這人將线畫得明明白白,這會兒倒顯得異常可笑,可誰見過蚍蜉撼大樹。
幼金心中堵得厲害,眼淚欲墜落又讓她生生阻了回去,陳元卿盯著她,面上瞧不出喜怒,男人聲冷冷地開口:“也好,你過來。”
他招幼金前去,像往常一般要去親她。幼金這會兒哪有心情,她躲閃著卻掙脫不開,干脆放棄了掙扎,任由男人的吻落在自己臉上。
陳元卿驟然推開她,她身子直直撞向後頭的幾案,背磕碰在案角上。
“陶幼金!”陳元卿真的是怒了,她這心如死灰的表情,難不成真要給那姚修守節,“你不怕我讓人去殺了他。”
他能做得出,她知道他殺過人的,幼金背後鑽心的疼,男人這話重重地砸在她腦袋,她什麼都來不及想。
啪的聲,陳元卿臉上落了個紅印子,幼金手直顫抖,指甲陷入掌心:“你騙我……你又誆我,我哪里對不住你,你要覺得前世是我害了你,你殺了我便是。”
她終於說出來,每日這般難道她就不覺得累麼,她不如他身份尊貴沒錯,可她原本也是清清白白的良民,不是他府中任他呼來喝去的奴仆。
小婦人瞪著他,她做慣了活計,手勁不小,將陳元卿臉都給打偏。
這祖宗何曾受到這樣侮辱,讓人直接掌摑。
陳元卿死前叁十有六,若成婚得嗣,連孫兒都該有了。當下卻生生叫個婦人直戳了心肺管子,他沉下臉,死死拽住她的胳膊。
陶幼金卻似個潑婦,扭頭狠狠咬住他的手腕,陳元卿一陣吃痛,松開桎梏。
小婦人鬢發亂了,倔強地跪坐在榻上跟看著仇敵般看他,看得陳元卿那顆老心髒一陣慌張。他早知她性子不馴,未想到乖張到這地步。
幼金緩下神來才有些後悔,不過打也已經打過,任由他發落處置就是,她腰背疼得厲害,只想趴下或找個東西靠一靠。
她不再管陳元卿,慢慢下了榻。
床簾擋著果真清淨不少,幼金怔怔地趴在枕間,也不知道在想什麼。
踏板前的簾子忽讓人掀開,她驚恐地扭頭看去,陳元卿已經順勢坐在她身側,她欲往里躺,他卻勾住她衣角。
“不是膽子大得很。”陳元卿皺眉嘲道,“既由著我決定,你便呆在這院子里,哪里都不要去,等我來接你進府。”
幼金手微微顫抖,繞來繞去原來還是躲不過。
陳元卿卻不打算就這樣放過她,自上元節後他就沒有再碰這婦人,他將她下面衣物都扒光了。
他從幼金身後將她腿分開,趴在她身上,手蹭在穴口摸了摸,已曠了月余的陽物撐開肉縫捅了進去。
小娘子身體里還很干澀,何況她背疼,乍被他這麼猛戳,幼金畏縮地挪了挪屁股。
陳元卿那處太大了,他嫌這姿勢不過癮不能都插進去,直接抱著幼金的腹部讓她撅起屁股跪趴在床上。
嫩穴咬著他的陰莖,原本留在外面的小半截也讓陳元卿徹底埋了進去。
不過他好歹還存著理智,念她幾分,沒這樣不管不顧抽插。
男人溫熱的掌在幼金身上緩緩游走,他的指停在她胸前,輕捏著她那兩顆果子。這小婦人長大了些,這對乳兒越發沉甸。
陳元卿忍不住扣著她的腰肢接連抽插了數十下,棍身下睾丸重重撞擊著她的陰戶,肉棒直往甬道深處擠。
“疼……疼……”幼金伏著去掐他的手,呼吸不穩地喊道。
男人聞言還是冷著臉止住了動作,陽具埋在她身體里,陳元卿硬聲問她:“哪處疼?”
幼金不開口,手仍去掰他,陳元卿干脆將她襦衫給往上卷了。難怪這婦人會喊疼,腰部右側露著觸目驚心的青紫,也不知是何時弄的。
陳元卿再禽獸也沒法見著她這樣再逞凶,男人喉頭滾動瞄了眼,額間汗珠滾落,胯下深紫色的硬物擠在嫩白的穴肉間,看著很是違和。
幼金只覺身上負重驟失,陳元卿已經從她穴內抽出去。
男人披了衣服下床去尋王婆子。
王婆子看幼金之前那樣子哪里敢睡,一直留神聽著屋內的動靜,這會兒見陳元卿臉色不虞出來問她要跌打藥,也嚇得撲通給他跪下:“大人,讓奴婢去看看娘子罷。”
陳元卿險些讓這主仆給氣糊塗,一腔怒氣無處可發,腳伸出去又收回來:“還不滾去拿。”
他何時伺候過人,更別說幫人上藥,手下力道略重了些,惹得幼金渾身哆嗦著哼,音很低,卻似貓般抓撓著男人的胯下。
“閉嘴!”陳元卿面露尷尬,衣袍攏了攏方才繼續幫她推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