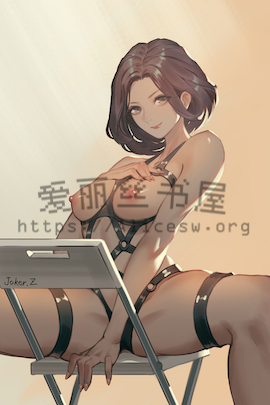褚婪的嗓音緊巴巴的,若無其事到有點刻意的程度:“寶貝,你坐那兒干什麼呢?風這麼大,快進來。”
但他甚至沒能抬步往那邊走一步。
安笙卻不看他了,重新回過頭去,不知在看窗外的什麼。
半晌,她問:“你看見了嗎?”
“看見……什麼?”
“我的刺。你看見我的刺了嗎?”少女的聲音有些飄。
褚婪聽見自己心髒“咚”的一聲重響,差點停擺。
他當然知道“刺”這個梗,出自一部現在看來相當狗血的言情劇,里面女主角站在跨江大橋的圍欄上,聲稱她要找她的刺。
她說她是一只刺蝟。
一只為了一個人拔掉身上所有刺,終於活不成了的刺蝟。
這段名場面甚至後來成了網友惡搞段子的寵兒,已經到了所有人聽了都會會心一笑的程度。
但褚婪現在聽到這句突兀的問話,卻半點感受不到其中幽默,只覺得心快要從嗓子眼里跳出來。
但他終於還是只好裝作get到笑點的樣子,挑眉嬉笑道:“怎麼?你的刺也丟了嗎?”
說完又立刻收起笑,滿臉不贊同:“再大的戲癮也等身體好了再說,個小破陽台cos什麼跨海大橋呢?來,趕緊回床上去。”
少女終於對他的話有了反應,卻不是答後一句,而是前面那句。
“沒有哦,”少女白皙透亮的小腿在欄杆外歡快地擺動著,回眸淺笑,俏皮又純真,“我的刺沒有丟。只是有個人看出了我是一只刺蝟,所以我用我的刺扎傷了他。”
接著,她又重新問了一遍:“你呢?你看到我的刺了嗎?”
褚婪干巴巴地咽了一口唾沫,“……沒有。”他哈哈一笑,聽不懂的樣子,“你這打什麼啞謎呢?”
安笙歪著頭盯著他的眼睛,忽然跳下陽台,還沒等褚婪心髒驟停便向他飛身撲過來,歡快地一頭撞進他的懷里。
小腦瓜依戀地在他結實的胸膛上蹭了蹭,揉得毛茸茸的,然後少女抬起頭,一雙水靈靈的月兒眼亮晶晶地望著他:“要做嗎?”
褚婪:?
“我說,要做愛嗎?”
安笙見他居然遲疑,便毫不留戀地轉身就要走:“哦,那我去找……”
“做!”褚婪從身後一把將人撈住,一個公主抱將女孩直接扔到松軟的大床上,咬牙切齒的壓上去,“包君滿意!”
——
遙遠的一家地下俱樂部,飛鏢室內。
一個身穿暗紫色哥特風洋裝的嬌小金發少女,雙腿懸空坐在寬大的台球桌上,口中含著棒棒糖,手中握著一枚紅色飛鏢,正向門邊的鏢盤上瞄准。
就在這時,門忽然被一只手從外面拉開。
女孩手中的飛鏢也在這一刻極速射出,看方向卻不是衝著鏢盤去的,而是進來那人的面門。
明明尖銳的飛鏢朝著自己急射而來,門口那人卻連眼睛都沒眨一下,甚至連閃躲的動作都沒有。
他面無表情地看著台球桌上已經咯嘣一聲將棒棒糖咬得粉碎的女孩,等飛鏢以離他頭頂半厘米的偏差飛掠而過後,才抬步向女孩走來。
“切,沒勁。”
少女嫌棄地看著走到她面前的身穿黑色燕尾服的男人,一頭半長波波頭,本來是更適合女生的發型,卻因為發量太少,每一片頭發都幾乎垂直地順流而下,尾端被剪切地過於齊整,如同薄而鋒利的刀刃。
“怎麼是你親自來了啊?”少女的小皮鞋蹬了一下桌面,又遠離男人一點,好像生怕棺材臉會傳染一樣。
“先生親自吩咐的,”他將一張照片遞到女孩面前,“貼身監視,注意出現在她身邊的任何可疑人員,等待下一步指示。”
“就這樣?”女孩撇撇嘴,將照片接過來,一看之下,忽然露出一個奇怪的微笑來,“是她啊?”
燕尾服男人卻似乎對她表現出的,認識照片上的人這一件事毫無興趣,只是再次叮囑:“記住,監視和一切動作的前提,是保護這個人的人身安全。她很重要。”
“okok~知道了知道了,我保證她在我手上,一根頭發絲都少不了。趕緊回去復命吧。”女孩招財貓一樣揮了揮手里的照片,“拜了個拜。”
男人看她一眼,轉身離開。
女孩在門合上之後,饒有興味地再次端詳起那張照片。
照片上的女孩穿一身青色紗質古裝,正巧笑倩兮地接過劇組人員分發的慰問品,額間好像有一點薄汗,卻半點不影響那令人過目難忘的絕世容姿。
要不要通知那個照顧弟媳照顧到床上去的家伙呢?
還是暫時保密吧,父親的命令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