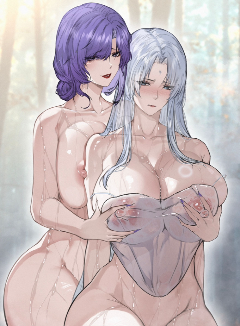“是,閣主。”
“玄雲晏!”
許致安拽住了我的手,狼狽道:“你冷靜點一些。洛兒他並不是那個意思。”
飛鴻森然看了他一眼,我知道,只要我一聲令下,許致安人頭落地,不過是呼吸之間的事。
我頓住腳步,看著裙擺掃過地面,蕩起一陣塵土,身上地上都是髒兮兮的:“你以為我要和皇兄說什麼?”
胸口處噎著一團東西,說不出那是要燃盡一切的火焰,還是一團濕透的棉絮,只是沉甸甸的墜著,憋脹的厲害。
我偏頭去看許致安,他頭發凌亂,上身只穿著件灰撲撲的單衣,狼狽至極。
“你以為我要殺了他,是不是?”
我居高臨下的看著他,聲音輕軟,嘴角帶笑:“因為他不順我的心,討不了我的喜歡,所以該死,對吧?”
這場景像極了十七年前我和他的初遇,我在上,他在下,我說的每一句話都是金口玉言。
只要是我想要,只要是我喜歡,他什麼都反抗不了。
許致安臉色猛然一片蒼白,我輕笑一聲,把手抽了出來,看他僵在原地,胸腔處那沉甸甸的一團竟然無聲無息的松散開去,不那麼難受了。
“怎麼不說話?駙馬,我等著呢。”
我揮了揮手,飛鴻便退在一邊,只有我和許致安兩個人相對著,兩個人都是滿面風塵,一點年少時的風采都看不出了。
這十七年,我只管作端莊的許府女主人,雖然身份高貴,卻足夠謙恭。
許致安則是一路高升,從罪人之子一躍成了皇帝面前的寵臣,滔天權勢,無邊美色,他都有了。
我倆之間卻一直是相對如賓,他含恨不發,我也只用張錦繡壓下一地血腥,這麼多年沒有紅過臉,到了這個時候,我反而不想再忍了。
我細細端詳許致安的臉色,想要看清他臉上的每一分痛苦:“許洛是我兒子,為了你的體面,總是……”
“求你。”
我雙手顫了下,幾乎要疑心是自己聽錯了:“你說什麼?”
許致安定定的看著我,緩緩的跪下去:“但求公主寬宏。”
他當年昂揚肆意,我用公主的名號要強壓他低頭,他也只是近乎於輕蔑的看了我一眼,轉身就走,絲毫沒有留戀顧忌。
十七年後,這人竟然也學會低頭了。
“許洛年幼,被人迷惑,子不教,父之過。請公主降責於我,饒他這一次吧。”
他磕了個頭面,直起身來,平靜的看著我:“致安絕無怨言。”
我猛地往後退了一步,嗓子眼一片干澀,心里突然怕的利害,就像是看到許家那些冤死的女眷一樣,失聲道:“你做什麼!”
許致安淡淡的:“臣什麼都做不了,砍頭還是凌遲,只由公主喜歡就是了。”
“罪臣玄雲晏!”
正在我直勾勾的看著許致安,魂飛魄散之際,遠處突然遙遙傳來一聲大喝:“太後懿旨已下,你觸犯禁令,罪無可恕!”
呼吸之間,說話的那人已經快馬加鞭,到了我倆身前,飛鴻立刻擋在我前面:“大膽!你是何人?”
來人身著玄色,腰間懸掛著墨金令牌,是皇族的行刑人。昂然道:“墨衛!無關人等立刻散開,否則一並拿去!”
墨衛這種壓制皇族的東西在先帝時期就已經被滅的差不多了,玄端即位之後,在太後手里又死灰復燃了。
“就憑你?”
飛鴻眼神冷冽,哂道:“也敢在閣主面前亂吠!”他武功甚高,旁邊幾個下屬也絲毫不差,怎會把這等貨色放在眼里。
“你說什麼!”
那墨衛勃然大怒:“我是秉著太後懿旨來的,你們是想抗旨麼?”
場面一時緊繃到了極致,飛鴻冷哼一聲,抽刀就要上前,那墨衛慌忙後退,眼見立刻就要見血,一只蒼白的手伸了出來,擋住了兩個人的劍拔弩張。
“敢問這位墨衛兄弟。”
許致安不知什麼時候從地上站了起來,離我不遠不近,皺著眉頭道:“梓安公主是冒犯了太後的哪條禁令,值得如此大動干戈?”
我低垂眉睫,突然覺得有些好笑。
現世報來的竟然這樣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