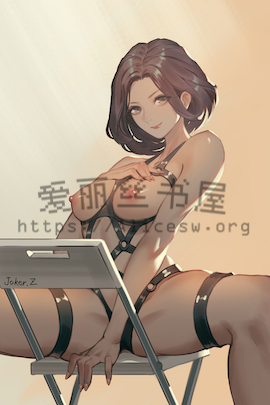有了法號的那就算是廟里的正式員工了,可以一本正經的被人稱呼一聲大師。
比如寶光大師,寶印大師,了緣大師或者了殘大師……
雖然對自己的法號不滿,可了殘對自己目前這個行當還是滿意的。
少了江湖上風來雨去的奔波,也不用再被官府攆的雞飛狗跳,自己一個窮困潦倒的醉鬼,為了混口飯吃才想著來當兩天和尚,至少能暫時混個肚圓。
本著有棗沒棗一竿子的想法,沒想到還真被這寺廟收下了,這一進來就不想走了。
這和尚當的滋潤呀,有酒喝,有肉吃,甚至你要是在寺里的地位夠高,連女人都可以玩弄,那可是真真的良家婦女,自己的師傅寶光大師前兩天弄回來的那個細皮嫩肉的船娘,想想都叫人眼饞。
雲山寺坐落在離洛陽不遠的山腳下,寺院的後門便緊挨著渭水河,寺里專修了一個私用的碼頭。
前有山後有水,寺廟占地不小,寺里有僧侶幾百人。
由於地里位置的原因,香火還算旺盛,今天是了殘值知客,這出來進去的人多了便也乏了,眼看著日頭已經過午,這人也少了,便想著找個沒人的地方先喝兩口。
便在這時,一定軟轎停在了寺門前。
這種軟轎了殘見的多了,一般都是女眷才會乘用。
來雲山寺來拜佛的女眷還是不少,別看他們背地里做著齷齪的勾當,那也是分人。
一看便是大戶人家的家眷他們也是不動的,沒來由的給自己找麻煩,這里可是洛陽旁邊,你知道哪個是侍郎的夫人,哪個尚書家的小姐?
雖然後台很硬,可也不能肆無忌憚。
了殘正要迎過去,跟在轎邊的一位胖胖的青年就攔在了他身前,他的身後,簾子挑起,一位端莊秀美的少婦邁步走了出來。
……
兩個時辰前,呂冠在為人選犯愁。
七天的日子到了,總要有人給二禿子送解藥去,雖然那天喂他吃的是六味地黃丸,可撒了慌就要圓,不然以後怎麼拿捏他。
送藥的人卻不好選,自己還不方便露面,雲竹又打死都不去,玉娘忙著家里的生意,若瑤,敏瑤要在家里照看孩子,沙丘那一腦袋紅頭發看著就不靠譜,就在這時有人影從門前閃過,“那個,你,對,就是你,那個大波妹,你過來一下……”把婉兒派出去了,呂冠又後悔了,就婉兒那性子,那一寺廟的色和尚,姑奶奶你可別拆了人家的廟呀,我這人還沒救出來呢!
與此同時,在雲山寺中,婉兒在說明了來意後被引到了偏殿,據說廟里的大師要親自見她。
了殘心里那個罵呀,他媽的好不容易來個極品就全冒出來了,換個那些尋常的婦人就全不見蹤影,心里罵著臉上卻不敢有所表示,一雙賊眼再次裝著不經意間掃過婉兒的胸脯。
小婦人的臉更紅了,好端端的非要自己來送什麼解藥,送也罷了還要穿這礙手礙腳的衣服。
婉兒的衣櫥里有練功夫、夜行衣,然後還有另一款式的練功夫和夜行衣……
好吧,只能借雲竹姐的一身先穿上。
家里的幾個女子中,婉兒的身材最是高挑修長,胸又最大,所以這衣服雖能穿上卻顯小了一些,束胸無論如何也裹不住那對兒碩大的乳房,被緊緊的撐在胸前,仿佛隨時都會裂開,即使這般還是有一小半的乳肉頑強的擠了出來,被壓迫的泛起了淡淡的青絲,白皙,豐滿,滑膩,如若不是肩上還披著一層透明的薄紗,束胸下那兩粒明顯的凸起也會毫無保留的展現於人前。
“南無阿彌陀佛”隨著一聲佛偈,廟里的所謂大師終於出現了。
婉兒和站在她身後的胖墩兒當然不認識,如果呂冠在當能一眼認出正是那個搶走船娘寶光。
只是他此時一身大紅的袈裟,手持佛珠,倒也顯得幾分寶相莊嚴,眼中看向婉兒時貪婪的精光一閃而沒。
眾人假意寒暄了幾句,寶光出言試探道“聽我這徒兒說女施主有意為菩薩再塑金身,只是這出家人講究因果為先,不知女施主所求的又是什麼?”
按照事先編排好的,婉兒假意看了眼寶光身邊的了殘,又看了看自己身後的胖墩兒,臉色羞紅,似有難言之隱。
寶光馬上會意“徒兒呀,帶著這位施主先去廟里轉轉,我與女施主有話要講。”
了殘心中暗罵,嘴上卻連忙稱是,最後狠狠的衝婉兒的胸口盯了一眼,便招呼著胖墩兒出了殿去。
至此一切順利,婉兒只要能拖上片刻,胖墩兒就有機會見到二禿子,送出解藥同時拿回寺廟的地圖和知道武僧的確切人數。
因為雙方早已約好,七日後,會派人來給他送解藥,可再多保七日的性命,雙方在彌勒殿門口相見。
在來之前,呂冠已經交代了婉兒空頭支票隨便開。
雖然不知道確切的意思,但婉兒也大概明白了就是自己怎麼胡說八道都行。
這就容易多了,先說自己生於官宦人家,父親官至刑部尚書,這一部分是真話,聽的寶光心頭冰涼,眼看著這麼誘人的小婦人居然後台這麼硬;又說自己不得父親寵愛,被嫁給了一介商賈,寶光大師心又活了,商人的地位可不高;再說自己和丈夫情投意合,琴瑟和諧,寶光又死心了,這夫妻感情太好的要插手可難;最後說自己一直無所出,丈夫又納了幾房小妾,眼見著要失寵了……
這簡直比雲霄飛車還刺激,寶光充分體驗著冰與火的快感。
不過面對這麼個秀色可餐的美人,胸前的那抹春光已經刺激的他呼吸隱隱有些粗重,要不是顧忌著對方身後刑部尚書的背景,這只鮮桃是無論如何都要咬一口的。
“大師,大師?”
“哦,”寶光回過神來,“女施主無需著急,佛渡有緣,我聽女施主以前並不是信徒,這臨時抱佛腳麼……”頓一下又接著說道“給菩薩塑金身倒是不急,倒不如女施主今後常來拜佛,持我這串手珠可由知客直接領來見我,待我為女施主講經,只要心誠塑不塑金身的到是表象了。”
這便是以退為進,說著寶光自僧袍中摸出了一串手珠,遞了過去。
婉兒伸手去接,待二人雙手相交時,婉兒只覺得一股內力突然自那串佛珠上傳來,自己被懷疑了?
電光火石間,婉兒果斷的放棄了與之相抗的想法,完全放松了身體,“啊”的一聲嬌呼,身子向前倒去。
寶光確實是試探,見她反映完全是不會武功的模樣,只是人都倒過來了哪有不接住的道理,雙臂一伸,溫香軟玉的抱了個滿懷。
其中的一只大手完全的是無意識的就那麼抓住了婉兒兒一側的乳房。
手感是如此之好,豐滿柔軟,一只手根本就抓不過來,束胸是如此之薄,寶光已經清晰的感覺到了掌心處那粒凸起的乳頭。
婉兒的身子是真軟了,乳房一旦被人抓住便全無反抗之力,“大師,大師……”她羞羞的叫著,身子卻完全沒有起來的意思。
眼看著懷里的小美人輕聲的低吟,卻毫無反抗的動作,寶光甚至就把她在此就地正法的衝動,只是沒等他有所動作,門外傳來了胖墩兒的聲音,“夫人,時候不早,該回府了。”
到手的機會就這麼飛了,好在這小婦人答應以後常來寺里聽經禮佛,對於剛才的事看來她只覺得是個意外,那不就是今後還有機會?
想到這寶光不由得期待起下次的相會,“了殘,你出寺一趟,幫我查查……”派走了了殘,此時還是白天,寶光卻覺得自己欲火難耐,匆忙了回了後山自己的禪房,禪房並未上鎖,屋內的小婦人現在已經不跑了。
自從跑了三次都被抓回來後,寶光也不折磨她,只是和她歡好時都開著窗戶,每次都感覺窗口影影綽綽的有人偷看,把船娘羞臊的恨不得找個地縫去鑽。
偏偏自己這身子又不爭氣,雖然心里恨他可是又被他肏的高潮迭起,羞人的叫聲忍都忍不住,要不是心里還掛念著孩子,掛念著當家的,船娘自己早就自盡了。
可是今天,現在是白天呀,“你,你干什麼,天還沒黑呢,大師不要……”嗤啦,哐當,……
不多的衣裙再次被從豐滿的身體上撕扯了下來,寶光還順勢一把推開了窗戶。
讓船娘更恐懼的事發生了,胖大的和尚競推著她來到了窗邊,被迫雙手扶住了窗沿,整個赤裸的上半身都探了出去,“大師,不要,求求你不要在這,會讓人看到的……啊……”隨著船娘的一聲痛呼,豐滿的兩瓣肥臀被人從後面扒開,一根如槍似棒的巨物毫不留情的衝著桃源鑽了進去。
船娘成熟的身體展示著自己驚人的適應性,最初的十幾下後陰道內便逐漸濕潤,“可他媽憋死我了”寶光這時已放下了自己的偽裝,面目猙獰,一雙大手不斷拍打著船娘豐膩的肥臀,“還好有你,這身子怎麼用都不膩,我都不想放你回去了。秀雲,要不你以後就跟了佛爺我,別回那個窮家了。”
秀雲是船娘的閨名,按說除了墨大別人是不可能知道的,可是自從有一次寶光肏爽了之後,答應玩三個月就放她回去,代價是這三個月兩人歡好的時候要像真正的夫妻那般。
於是秀雲才將自己的閨名說與他知道。
其實回去也只是希望能再見他們一面,自己是沒有臉重新走進那個家門,現在聽著寶光連自己這最後的希望也要剝奪,秀雲終於激烈的反抗起來,費了好大勁才將秀雲按住,雞巴也重重的頂在女人的花心上,寶光才開口“好好,讓你們回去團聚,那你答應我的是不是也得算話,來,叫聲聽聽。”
啪的一聲拍在肉臀上,蕩起了一層漣漪,“啊”的一聲輕叫,“相,相公……”
“大點聲”
“相公,相公……”
“看來的肏的你不夠爽呀,要不要相公抱著你去院子里?”
秀雲一聽嚇壞了,好在這會院子里沒人,自己半裸著身子在窗子里還算有個遮擋,這要是出去了光天化日下在院子里……
“不要,不要去院子,相公肏的人家好爽,啊……這下頂的好深,妾身的花心都酥了……”雪白的乳房在胸前晃動著,啪啪的聲響自女人的臀後傳來,在男人粗重的喘息,女人的陣陣嬌啼中,沒有人注意到,偏僻的角門處的陰影里,一個男人默默的站在那里,不知已有多久。
距離有些遠,他並不能完全聽清他們的對話,只是和尚叫出了他女人的閨名,他聽到了,滿臉驚怒,然後在女人一聲聲相公,一聲聲嬌吟中,驚怒漸漸的變成了失落甚至是絕望,他忽然覺得自己現在所做的一切完全沒有意義。
那和尚的聲音大了起來,女人的叫聲也大了起來,他清楚的聽見自己從記事起就認識的那個女人,那個從十五歲就嫁給自己的女人,那個為自己生了一個兒子並且相約終老的女人,在祈求著另一個男人把精液射進她的屄里。
墨大覺得自己渾身發熱,他想要離開這個地方,去帶上兒子,再也不回來,再也不見她。
也許……
再見她一眼就離開,就最後一眼。
墨大向前走了數步,半邊身子走出了陰影,自己的女人無力的趴在窗邊,身後一個胖和尚正趴在她身上,一只手還在玩弄著她的乳房。
二人站的很緊,也許雞巴還沒抽出來呢!
墨大自嘲的想著,夠了,自己要離開這里,再也不回來。
就在這時,那女人無力向後半轉著頭,“大師,無論你怎麼玩弄我,肏我都行,只是你答應讓我走的,我只想再見我的孩子,再見他一面。”
墨大的腦子里轟的一聲,僵立了不知多久,直到耳邊再次傳來和尚的喘氣聲,和秀雲那熟悉的呻吟聲,他才默默的退回到陰影中,只是這一次,他的目光堅定。
……
了殘的結果讓寶光完全放下心來,刑部尚書確實有個女兒,也確實是嫁了個商家,是賣藥的,那商賈也確實娶了好幾個女人。
這就沒什麼可疑的了,雖說這樣的女人不能硬來,可看昨天撲進自己懷里那嬌羞的樣子,勾搭勾搭也不是沒有可能。
船娘自然也不能放了,昨日那小婦人雖然誘人,看年紀也更輕些,可頂多也就是露水的姻緣,船娘就不一樣,難得的小門小戶的出這麼個極品,自己玩的毫無負擔,還那麼好騙,放回去?
佛爺還指著她生小佛爺呢!
她家是哪里的?墨家村?男人好像是叫墨大?“了殘,上次墨家村的租子是誰去收的?”“師傅,是二禿子那個廢物。”
“好,你去跟他說,再跑一趟,找個叫墨大的。”寶光說到這突然住了嘴,剩下的就全需要下屬領會了,不得不說他頗得某黨干部真傳。
好在了殘機靈,對那女人的來歷也有耳聞,師傅這是想把那女人留下了,“師傅放心,那二禿子也是個手黑的主兒,再說還有我盯著,包您滿意。”
二禿子手黑麼?
當然黑,這他媽都成黑疙瘩了。
呂冠那個氣呀,這畫的什麼狗屁玩意兒,老子上小學那會都比他畫的強……
中學。
幾個方塊,這是房子,一個三角,這是山,兩條线,這是河,還有一排排的圓圈,這是人腦袋?
感情那二禿子根本就不識數,一個人就是一個圈,數了半天213個圈,呂冠覺得自己都有點213了。
正恨的牙癢癢呢,胖墩兒帶進個人來,呂冠一看就忍不住了,先揍了再說。
鼻青臉腫的二禿子態度很端正,頗有狗腿子的潛質,呂冠還沒問就交代了。
“他們讓你來殺墨大?”呂冠皺著眉沉思下來。
事實證明二禿子這頓打挨的不冤,在他眼里能打的就有213個,這對現在的墨家村來說有點多了。
對於他執意不肯找青麒幫忙,大家都有些不解,但有時候這就是男人的堅持。
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自己太弱小了即使開口別人看情分幫了,一次兩次,次數多了呢?
一直依靠別人?
如果自己連一個有200多武僧的寺廟都解決不了,那也不用去想那片青色的高原了。
於是二禿子帶著任務回去了,當然六味地黃丸還是要吃的。
“廢物!你就這麼被人打出來了?”了殘怒道。
“師兄,了殘師兄,那些個暴民要造反呀,種咱們的地,我都沒說要干什麼直接就打了我一頓。師兄,咱可不能咽了這口氣呀!”
“當然不能!”
寶光不知什麼時候站在了門口,邁步走了進來,“正仇沒借口呢,這樣也好,了殘你安排三十人去一趟,這一旦衝突起來麼……”話講一半,當領導的都這壞習慣。
三十人的武僧隊伍出發了,最不放心的是二禿子。
也不知道村里那邊頂不頂的住,這要是被滅了……
我這解藥可找誰去。
忐忑完了屁用沒有,還是去外邊找個小妞壓壓驚,這毒藥吃的二禿子最近總是想女人。
正在這時,突然背後傳來一股大力,二禿子被人猛的踹翻在地,還沒等他呼喊,一把冰涼的匕首已經橫在了項間,“我問,你答,別耍花樣。”
聽聲音是個中年男子,那鋒刃刮的二禿子勃子生疼,哪敢不聽。
“剛才那隊僧人是做什麼去了?”就這問題?還以為是寺里發現自己是奸細了呢!反正是早晚捂不住的事,“去,去殺人。”“去哪?”
“墨,墨家村,聽說那里的暴民抗租。”
感覺到身後的男人一震,匕首卻是離自己的脖子更近了,這是要動手?
這些人都太不講誠信,那個公子說好了給解藥的,結果是毒藥解藥一起給,自己還毫無辦法。
這個劫道的隨便問個問題就要殺人,大家還能不能好好聊天了?
生死存亡的一刻,二禿子突然福靈心至,“你,你就是墨大!”
這是呂冠告訴他的,墨大可能就在雲山寺中,只是不知道具體在哪,還告訴他要小心,墨大是殺人去的,死在自己人手里那是活該,絕對沒人給他報仇。
充分認識到自己是後媽生的這個身份後,二禿子已經格外小心,結果還是差點……
幸好差點。
“你是誰?你認識我?”
匕首微微拿開了一些,但是身後的男人還是十分警惕。
二禿子盡量把自己的叛變投敵,說成是棄暗投明,時刻不忘記美化自己的形象,自己臥薪嘗膽,打入敵人內部雲雲。
“所以那公子現在接手了墨家村?”
墨大現在已經猜到那公子是誰了,自己可不認識什麼富貴人家,唯一有交集的就是救了那個落水的年輕人。
“不成的,”墨大已經收回了匕首,“你也知道雲山寺有多少武僧,村子里的人我知道,都是些莊稼人或者漁夫,不會是他們的對手。”
這時候再想回去報信已經來不急了,人的腳力無論如何和不會快過三十匹駿馬。
與此同時,呂冠在暗處看著寨門外那有些散亂的三十騎,知道自己算對了。
他們果然不會重視幾個暴民,這些一輩子只會在土里刨食的莊稼漢子還引不來大隊的人馬。
帶隊的僧侶是個三十幾歲的漢子,看著眼前低矮的寨牆,顯然是新修不久,嘴角牽出一抹冷酷的笑容。
好久沒出來吃點野食了,當和尚的日子雖然不用再害怕官府的圍剿,可也少了幾分笑傲山林的爽快。
這座村子也許不會很富裕,但至少女人總會有幾個吧!
隨著他的揮手,身後的武僧們吆喝著開始加速,都是手下的老兄弟了,洗劫這樣一座村寨簡直是手到擒來。
門口站崗的村民已經嚇傻了,顫抖著雙腿向兩邊躲閃,甚至連寨門都不知道關。
隊伍一衝而過,只是領頭的僧侶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已經嚇的躲在門邊渾身顫抖的村民要衝自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