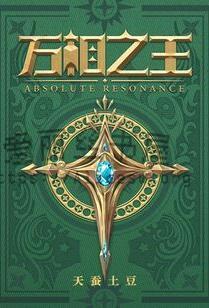有幾點要確認……裱裱脆生生的追問:“是什麼?”
懷慶抿了抿嘴唇,一邊關注著許七安,一邊思考著他會有什麼發現。
同樣在屋子里仔細搜查的自己,此刻心里卻一團漿糊,沒有得到太有用的线索和重大發現。
“首先,如果福妃真的遭到了太子的凌辱,她必然會呼救,為什麼清風殿的當差和宮女們沒有聽到?咱們先下樓……你去召集院內所有宮女和當差。”
最後一句是對小頭目說的。
眾人當即下樓,在院子里召集了清風殿所有的當差和宮女,共計十二人,四名宮女,八名當差。
“爾等聽好,這位是奉旨查案的許大人,福妃遇害案由他全權處理。許大人現在有話要問你們。爾等須有問必答,不可隱瞞。”小頭目沉聲道。
“是!”
眾人低頭應答。
小頭目滿意點頭,看向許七安。
許七安鎖定一位清秀的宮女,招手道:“你過來。”
小宮女低著頭,小碎步上前。
“再過來一點。”
小宮女來到許七安身前,他附耳低語了幾句,然後道:“去吧。”
小宮女小跑著進了閣樓。
他要干嘛?
裱裱和監督的小宦官茫然不解,懷慶則若有所思。
許七安環顧其余宮女和當差,道:“本官問你們,當日福妃出事,為什麼閣樓里沒有宮女侍奉在側?”
宮女和當差的面面相覷,有些畏畏縮縮的不敢說話。
許七安瞳光一厲,呵斥道:“凡隱瞞不報、知情不報者,視為殺害福妃的疑犯,押入打更人大牢。”
一位小宦官立刻說:“回大人,我們不敢靠近閣樓。”
不敢靠近閣樓?
許七安感覺自己發現了華點,有男人進入福妃的寢宮,院內的下人們卻不敢靠近,這說明什麼?
說明元景帝頭頂有草原啊。
許七安心里暗暗期待。
小宦官解釋道:“福妃娘娘愛飲酒,喝多了,對清風殿的下人動輒打罵。我們害怕遭受無妄之災,逢著娘娘喝酒,我們便離的遠遠的。”
“每次都這樣嗎?”許七安問道。
“是的,沒有例外。”小宦官回答。
“什麼時候開始的。”
對於這個問題,小宦官囁嚅片刻,搖頭道:“奴才進了清風殿,福妃娘娘便如此了。”
白斬雞,你的資歷不行啊……許七安掃過眾人,發問道:“哪個是福妃娘娘的貼身宮女。”
“是奴婢……”一位年歲稍大的宮女出列。
“你來回答本官剛才的問題。”許七安盯著她。
“這,這……”年歲大的宮女猶猶豫豫地說道:“前些年還好的,這些年娘娘的性格越來越奇怪,常常一個人站在閣樓上,也不知道在看什麼。
“飲酒時,喜歡吟誦一些悲春傷秋的詩詞……”
她說的很隱晦,大概是不敢置喙福妃,不敢置喙皇帝的家事。但許七安和懷慶都是聰明人,聽懂了言外之意。
這是一個寂寞婦女的悲傷啊……唉,元景帝不當人子,後宮佳麗這麼多,還辣麼漂亮,竟然跑去修道,竟然還禁欲……許七安嘆口氣,又問道:
“出事當天,有人聽見福妃的呼救聲嗎?”
眾人紛紛搖頭。
許七安沒有表態,望向閣樓方向,微微頷首。
眾人隨他目光看去,眺望台上站著剛才進閣樓的小宮女,得到許七安授意,小宮女當即關閉瞭望台處的格子門,俄頃,里面傳來微弱的呼救聲。
到這一步,腦瓜子不算太聰明的裱裱,也明白了許七安的意思。
“混賬,你們敢說謊,呼救聲明明這般清晰。”裱裱怒道。
院子里的下人們嚇了一跳,連忙辯解。
許七安壓了壓手,示意他們稍安勿躁,然後轉頭吩咐小頭目:“把斷裂的那截護欄抬出來……
接著,他看向年歲大的宮女,道:“你留下,其他人退下。”
那位年歲大的宮女有些慌張,雙手不安的攪動。
“小公公,你先到外院去,稍後喊你,你再回來。”許七安原以為這個不怎麼識趣的小太監會反駁,他都打算抬出懷慶和臨安來壓人了。
結果,小宦官什麼都沒說,心甘情願的轉身離去。
“你有什麼發現?”
待人走後,懷慶率先開口。
清冷高傲的公主殿下,心中有自己的推理,剛才宮女在閣樓內呼救,外頭是能聽見的,盡管很微弱。
那麼就有兩種可能:一,福妃根本沒呼救。二,福妃被人控制住了。
“太子修為如何?”許七安問道。
“練過幾年武藝,弓馬騎射都很嫻熟。”懷慶回答。
哦,是一只弱雞……許七安點點頭。
太子修為在煉精境,甚至都不到,這其實可以理解。
對於一位皇子來說,傳宗接代,延綿子嗣是頭等大事。
個人武藝算什麼?
皇帝又不需要衝鋒陷陣。
其次,自身能不能面對美色坐懷不亂,也是一個重大考驗。
尤其是太子身為皇子,身邊美婢如雲,恐怕很難在年少衝動的時期守身如玉。
許七安覺得,也就自己這樣擁有大毅力的人,才能保持母胎單身十九年。
“太子雖然修為淺薄,但要對一個弱女子用強,想來還是很容易的,所以福妃也許根本沒機會發出求救聲。”許七安道。
“我太子哥哥不會做這種事的。”裱裱立刻反駁,這是她作為胞妹,最後的倔強。
許七安沒有回應把圓潤臉蛋鼓成包子的裱裱,冷笑的看著年長的宮女,道:“剛才沒有說真話吧?”
宮女眼里閃過一絲驚慌,擺手道:“奴婢所言句句屬實,絕對沒有說謊,請大人明鑒。”
“沒說謊,但也沒說全,對吧。”許七安用刀鞘拍了她大腿一下:
“本官沒什麼耐心,你要不說,就去打更人衙門的大牢里交代,我不保證里面的獄卒會怎麼對你。”
這些小宮女小太監,心思多,膽子小,恐嚇是最好的方法。
宮女咬了咬唇,心一橫,道:“兩位殿下,許大人,請隨我來。”
她轉身進閣樓,許七安和懷慶、臨安跟在身後。
返回閣樓上,宮女徑直去了床底,吃力的拉開一只大木箱,從一件件舊衣衫底下,取出一只小木盒。
宮女低著頭,畏畏縮縮的把木盒奉上。
許七安接過,打開木盒,看清里面的東西後,腦海里就兩個字:蕪湖!
要不是身邊還有臨安和懷慶,他還會吹一聲浮夸的口哨。
木盒里躺著一根用玉雕琢而成的物件。
許七安頓時理解為什麼宮女吞吞吐吐,不敢說。
這東西在宮廷屬於禁品,道德層面是一方面,再就是這里是宮廷,妃子是皇帝的女人,肯定是不行的。
皇帝不要面子的嗎?
一旦被人發現,重則打入冷宮,輕則降位份。
這就可以解釋福妃為什麼要把下人驅散出閣樓,酒後心情不佳是方面,眼前這東西是另一方面……幸好我把小宦官趕出去了,不然元景帝得殺我滅口……許七安神色復雜。
“這是什麼東西?”臨安公主蹙眉道。
許七安看了她一眼,再看一眼懷慶,高冷公主面無表情,專注了審視著玉雕物件,眼里有著困惑。
不是吧不是吧,臨安目不識丁就算了,飽讀詩書的懷慶公主,寧也不認識嗎?
許七安咳嗽一聲,用很輕的聲音解釋給公主們聽。
臨安“呀”一聲,驚恐的後退幾步,圓潤的臉蛋漲的通紅,脖子和耳根都紅透了。
懷慶公主觸電似的縮回目光,扭過頭去,白皙的臉蛋浮出兩抹淺淺的暈紅。
“福,福妃她……她竟然私藏這種東西,不,不知羞恥,快,快收起來……”臨安結結巴巴地罵道。
你別激動,說不定你娘床底下也有……許七安蓋上盒子,交還給宮女,道:“收回去,不要髒了兩位殿下的眼。”
宮女順從的照做。
許七安問道:“當日福妃墜樓時,這東西是在床上,還是在箱子里?”
“應當是在箱子里。”宮女說道。
如果床上有這玩意,卷宗里不會不寫……許七安點點頭,又問:“那位失蹤的宮女,與你一樣,都是貼身伺候福妃的?”
宮女點點頭。
“好了,下去吧。”
等她出去後,許七安坐在桌邊,一邊惋惜不能拿“玉如意”做化驗,一邊給兩位目不識丁的公主分析:
“福妃墜樓當日,院內的下人沒有聽到呼救聲,有兩種可能:要麼太子控制了她;要麼福妃心甘情願與太子私通。”
懷慶搖搖頭:“倘若是心甘情願的私通,房間里為何會有抵抗、掙扎的痕跡?”
一看你就沒有經驗……許七安笑道:“還是兩種情況:一,福妃開始是不願意的,所以抵抗,但太子用某種辦法脅迫了她。
二,有時候……也不一定要在塌上。”
兩個公主同時臉紅,啐了一口。
“那福妃為什麼會墜樓呢?你說過,她是被人推下去的。”懷慶質疑道。
“這個問題我暫時無法解答,”許七安分析道:“事發當日,福妃飲了酒。
“我要是太子,可以以此脅迫,達成長期的苟且關系。福妃久曠之身,說不定就半推半就,完全沒必要推她下樓。即使太子酒醒,要殺人滅口,也不該是完事之後,因為賢者時間里,男人是最冷靜的,斷然不會衝動。
“還有一個疑點,福妃既要做那事,驅趕了閣樓里的宮女和當差,那更沒道理再遣貼身宮女去邀太子,除非兩人早就有了私情。
“但是根據三法司的調查,以及院內當差和宮女們的口供,福妃與太子素無往來。”
“就是說,我太子哥哥真的是被冤枉的。”裱裱眸子晶晶發亮。
“這個可能性不小,但還沒到下定論的時候。”許七安點點頭。
懷慶問道:“你是怎麼看出宮女有所隱瞞?”
她一雙澄澈剔透的美眸,緊緊盯著許七安。似是在求教,但又抹不開面子。
微表情心理學了解一下……許七安道:“人的表情和肢體動作,會一定程度暴露內心,它們比嘴更誠實。”
懷慶秀眉緊蹙:“本宮從未見過記載這類知識的書。”
“這是我自己鑽研的。”
懷慶緩緩點頭,有些佩服:“你果然是破案天才。”
……其實破案最重要的不是天分,是經驗和知識,沒有這些東西,你即使是推理天才,也邁不進門檻。許七安笑道:“殿下謬贊。”
這時,侍衛小頭目在樓下喊道:“許大人,東西帶過來了。”
許七安當即起身,道:“下面要驗證我的一個猜想,福妃怎麼死的,也許馬上見分曉了。”
三人來到樓下,許七安接過侍衛手里斷裂的護欄,仔細檢查斷口,反復查驗。
他陷入了沉思。
紅裙和白裙默契的沒有打攪。
盡管裱裱裙底下的一雙小腳丫不停的踩踏,顯示出焦慮的心情。
因為許七安剛才說過,福妃的死馬上見分曉。事關太子哥哥清白,她焦急的很。
可還是不敢打攪他思考。
“走,去冰窖。勞煩長公主去請一位嬤嬤。”許七安帶著眾人離開了清風殿,懷慶吩咐殿外的侍衛去請老嬤嬤。
來到冰窖,留下侍衛,許七安、懷慶、臨安以及監督的小宦官和老嬤嬤,五個人進了冰窖內,再次見到了福妃的遺體。
“勞煩嬤嬤除去福妃身上的衣物,再將她翻轉過來。”許七安道。
老嬤嬤有些猶豫,但看許七安直覺的背過身,她這才用詢問的目光看向懷慶公主,沒有看臨安。
懷慶點頭道:“按許大人說的辦。”
幾分鍾後,嬤嬤道:“老奴做完了。”
許七安回過身來,福妃赤著身,趴在木板上,慘白的背部布滿屍斑,但沒有許七安想要看見的東西。
“可以了。”他點點頭。
離開冰窖,來到偏廳,臨安迫不及待地問道:“怎麼樣?福妃是怎麼死的,我太子哥哥是清白的吧。”
許七安看了眼監督的小宦官,再掃過兩位公主,沉聲道:“福妃應該是自己跌落閣樓的。”
“何以見得?”懷慶眉梢一挑。
這個結果,讓所有人都感覺意外。
“清風殿閣樓的護欄,沒有朽爛,堅固的很。如果福妃是被人推下去的,身體撞斷護欄的同時,後背必定留下淤青。
“但是剛才檢驗過了,福妃後背沒有長條狀的淤青。只有屍斑和墜樓產生塊狀淤痕。”許七安道。
懷慶沉吟道:“但她確實是撞斷護欄死的……你是說,有人在護欄上做了手腳?”
許七安頷首:“除此之外,福妃墜樓前喝了酒,清風殿的宮女說,她常常在瞭望台看風景……我猜她是在看陛下會不會來,當然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喝了酒,會本能的趴或靠在護欄。福妃是仰面墜樓,因此她當時應該是靠在護欄上,但護欄被人做了手腳,因此墜樓而亡。
“剛才我問過了,也就是說,福妃當日……嗯,你們懂。所以,她會站在瞭望台的可能性很高很高。
“仵作驗屍時,沒有被侵犯的說詞也可以充當佐證。清風殿的宮女們沒有聽見呼救聲,因為福妃根本沒有遭遇強暴,自然不用呼救。”
懷慶和臨安恍然大悟,後者由衷的欣喜,因為太子的嫌疑頓時輕了許多。
前者則陷入沉思,咀嚼、回味著許七安的分析,就像在消化老師講課內容的學霸。
負責監督的小宦官低頭,拼盡全力,默默記下許七安的每一句話,晚些時候要匯報給干爹。
聽到這里,老嬤嬤插嘴道:“這位大人,給福妃驗身子的也是老奴,不是仵作。”
“哦,原來是嬤嬤啊。那正好,本官還有些細節要問。”
他拉著老嬤嬤走到一邊,低聲道:“嬤嬤,你們判斷身子是否清白的標准……”
他小聲的把疑惑問出。
老嬤嬤道:“嚴絲合縫。”
“哦哦,那本官就明白了。”許七安心說,這老嬤嬤車技比我還溜。
這樣一來,就更加確定,福妃沒有被玷汙,而是真的死於意外,有人精心布置的意外。
既然不是見色起意,那麼太子的嫌疑就很輕很輕。
得到確認答案後,許七安說道:“能做到這些的,應該只有那位貼身宮女。”
宮女當然不會無緣無故殺害福妃,陷害太子,這是裱裱都能想明白的問題。
“那指使宮女的人會是誰呢?”裱裱看了一眼懷慶,眼里充滿了不信任。
懷慶冷笑一聲,裱裱就立刻縮到許七安身後。
她懶得和臨安一般見識,蹙眉道:“那麼房間里凌亂的痕跡如何解釋?
“福妃未墜樓前,宮女肯定無法當著她的面故意弄亂房間。而福妃墜樓後,立刻引來了清風殿下人的注意。”
“可能是福妃脾氣非常糟糕,所以弄亂了房間。也可能是酒水有問題,比如致幻。”許七安解釋。
可惜不能解剖福妃,因此這個猜測無從證實。
“今天先到此為止吧,我想回去再斟酌斟酌,梳理案情。”許七安道。
他不能說自己是消極怠工。
把臨安公主送回韶音苑,許七安見懷慶公主在外頭等候,心照不宣的走了過去。
兩人沉默的往前走,侍衛沒有跟上,遙遙墜在後邊。
“沒想到你一出手,福妃的案子就立刻有了突破性的進展。”懷慶公主稱贊道。
“這案子其實不難,至少證明太子是無辜的,這一點不算難。”許七安說完,隔了幾秒,道:
“三法司似乎不急著證明太子的清白。”
許七安一直覺得這個時代的推理知識,刑偵手段落後,但不能否認,三法司里人才還是很多的。
福妃案不像稅銀案那麼細節,也不像桑泊案那麼詭譎,更不像雲州案那樣燒腦,其中沒有摻雜太多的修行手段。
想證明太子清白,有點難度,但不是不能做到。
懷慶公主目視前方,沉默了十幾秒,淡淡道:“這件事無外乎兩種可能:一,真凶就是太子。二,太子是被嫁禍的。”
許七安“嗯”了一聲。
“太子如果是真凶,那麼他就會被廢。京察剛結束,便要迎來國本之爭,不管是父皇還是滿朝文武,都不願發生這樣的事。而且,也會被太子一黨嫉恨,平白樹敵。
“如果太子是被嫁禍,那麼,後宮之中,誰有這個能力,誰連太子都敢嫁禍?三法司更加不願得罪。歸根結底,這還是父皇的家事。”
許七安直截了當的回答:“所有能繼承東宮之位的皇子,皆有可能。”
懷慶道:“但嫌疑最大的,是我胞兄,以及我母後。”
因為四皇子是嫡長子,第一順位繼承人。
“嫌疑歸嫌疑,只要沒有證據,即使是陛下也不能如何。”許七安道。
有嫌疑是在所難免的,宮中有皇子夭折,那些個得寵的妃子都有嫌疑。但只要毀掉證據,即使嫌疑再大,又能如何。
宮斗其實很簡單粗暴,不可能後宮里每一位妃嬪都是布局深遠,老謀深算的諸葛亮。
懷慶緩緩點頭。
“有件事不明白,四皇子是嫡長子,為何陛下卻立了臨安的胞兄為太子?”
許七安問出這個問題時,目光緊盯著懷慶,如果她有厭煩和抗拒的表情,那麼說明自己腳踏兩只船的行為讓她心生芥蒂了,不把自己當心腹了。
懷慶沉思片刻,搖頭道:“父皇的心思誰都猜不准,不過我有次偶爾的機會,聽到了些許傳聞……”
許七安連忙打斷,“殿下,卑職想活到兒孫滿堂,壽終正寢。”
難得的,懷慶莞爾一笑,“並非什麼秘辛,聽了也無妨。”
頓了頓,她繼續說道:“宮中都說,太子之所以是太子,是因為陳貴妃年輕時寵冠後宮,父皇才破例立庶出的長子為太子。
“但是皇兄曾經私底下與我抱怨過,幼時父皇待他極好,還常常向他灌輸為君者當如何如何……試問,若無意立皇兄為太子,父皇又豈會說出這番話?”
許七安轉過身,朝著遠處的侍衛揮了揮手,然後與懷慶走出一段距離,才難掩八卦之心,搓著手問道:
“那為什麼最後立了庶出的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