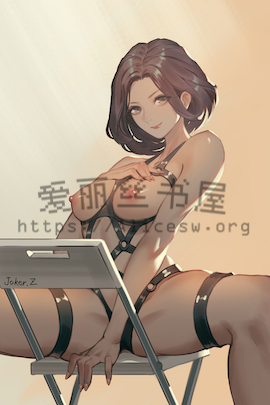我一直對自己充沛的體力充滿信心,多虧小時候奶奶放養,我每天都在院子、土堆、田溝里撒歡玩耍,到處跑跑跳跳,吃得好、睡得香,自然而然體質就上來了。
饒是如此,扛著背包一步步爬山,也是個氣喘吁吁、腿腳酸麻的體力活。
今天是安葬奶奶的日子,我起了個大早上山,打算完成奶奶的遺願。
松林山就在村子旁邊,不是很高,但也有峻崖峭壁。
滿山郁郁蔥蔥的松柏,樹繁葉茂擋住了天,抬頭只能看見深深淺淺的綠色重疊在一起。
沿山路蜿蜒而上,進入密林深處,樹葉和草地被踩得咯吱咯吱響,時不時還能看見緩緩流淌的小溪從高向低流到某個石縫中,再從石頭的另一邊流出來。
大概兩三個小時,我終於爬到山頂。
眼前景色豁然開朗,重重疊疊連綿不斷的山峰之間,是一片霧蒙蒙的湖水,藍得像透明的水晶,沐浴在金色的陽光中。
眼前的景色幾乎完美得令人窒息,我朝懸崖邊走了幾步。
不遠處有幾根倒下的樹木,看起來就像是故意放在那里,專門讓上山的人有一個安靜的地方眺望遠山湖水。
我感激地坐下來,肘部放在膝蓋,手掌托著下巴。
寂靜像柔軟的毯子包圍著我,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甜甜的空氣,然後又吐出來,沉浸在一片純粹的安詳寧靜中。
這就是我回來的目的。
上山之前,我和區域經理通了電話,告訴他我必須延長假期。
自從知道奶奶去世,他並非不通情理,給了我三天假期處理後事。
可我知道他的耐心也到此為止,如果我錯過即將開盤的房地產項目,十之八九會失去這次升店長的機會。
可我不能拋開奶奶留給我的一切扭頭離開,最後,經理和我的電話在不歡而散中結束。
我會失去這個工作,有那麼片刻我很懷疑自己的決定。
努力打拼那麼多年,就這麼輕易放棄麼?
實際上,爬山這一路上我都在問這個問題。
都說親人在時,人生尚有來處;親人去時,人生沒有歸途。
奶奶像是海邊矗立在高塔上的明燈,忽然熄滅了,我的航行頓時沒了方向。
我告訴自己打道回府還不算太晚,奶奶已經仙去,我可以委托村書記幫忙善後,只要給錢,有的是村民出手幫忙,效果不會比我差。
然後我會生氣,生氣自己怎麼能夠有這樣的念頭。
又很難過,難過奶奶走了,再也回不來了。
此時此刻,心中那點兒郁悶就像我頭頂上的一層薄霧漸漸蒸發,我能想象它消失在頭頂蔚藍的天空中。
不論是誰,身處如此美麗祥和的景色,都會豁然開朗、通暢喜悅。
奶奶希望我留在這個地方,我能感覺到她就在我的身邊,告訴我我屬於這里。
我喝了些水,吃了一條巧克力棒,休息足夠後從口袋里小心拿出一張照片,奶奶最後一次上山看爺爺時照下的照片。
從照片看,爺爺被埋在一處非常特別的地方。
我小時候和奶奶來過好多次,原本以為憑借記憶和這張照片,掩埋的地方將會非常好認。
沒想到這里如此特別,竟然到處都像照片里的模樣。
“你不用找了,我知道在哪兒!”一個聲音忽然從背後傳來。
“啊啊!”我嚇得跳到空中,轉身尋找聲音的來源。
我驚恐地睜大眼睛,瞪著站在我面前的男人。
他是我這輩子見過的塊頭最大的男人,穿著一件黑色短袖和藍色帆布褲,不是很搭配,但我估計照他的身材,能有合適的尺寸穿都不錯了。
這個男人太魁梧,像座山峰一樣聳立在我的面前。
不僅如此,他的肩膀寬闊,胸膛厚實,周圍陽光都吸附在他身上,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壓迫感,無法直視。
“你不用找了,我知道在哪兒!”他又重復了一遍。
“我……我……我……”我嗚咽著。
“你……?”他揚起又黑又粗的眉毛,和半張臉上的濃密的胡須倒是很相配。
“我……”我想說話,但一時間竟然找不到自己的聲音。
他依然默默地看著我。雖然很不舒服,但我還是鎖定他的目光。
“任莎,”我脫口而出:“我叫任莎!”
“我知道,”他歪著頭,繼續看著我。
漆黑的眼眸深處,有什麼東西在閃爍。
我注意到他的睫毛烏黑濃密,這應該不是壞事,畢竟沒有壞人有這麼漂亮的眼睛。
“那麼,你是誰?”
“鐵蛋,”他回答道。
我發出輕微的窒息聲,張大嘴叫起來:“你是鐵蛋?”
我的天啊!
鐵蛋怎麼長成這副模樣,我不記得上次見他什麼時候,但一定是平淡無奇、毫無特點的,不然我不可能這麼吃驚。
他再次歪著頭看著我,我感覺自己像只蟲子被釘住,更糟糕的是我的腦袋在旋轉。
親愛的奶奶給我留下一個二百平米的院子,她期待我與這個男人共享?
“我知道你爺爺埋在哪里,順著流水,繞過西邊的石坡,再走三四百米就到了。”鐵蛋抗起手里的鐵鍬和鐵鏟,示意我跟著他。
“你怎麼會知道?”我追上他的腳步,問道。
“我幫三奶奶鏟的地方,埋下任三爺。”
“哦,難怪。謝謝你!”旬村村民大部分姓任或者姓黃,追溯起來每家都沾親帶故。
爺爺在他那輩兒排行老三,小輩兒都叫爺爺任三爺,叫奶奶三奶奶。
鐵蛋確實知道在哪里,我跟著他沒走一會兒就停下來。當我拿著照片進行比對時,高興地說:“哇,你果然找到了!”
我卸下背包,從里面拿出一個小巧的樹洞挖掘器。
上山之前我在網上一陣好找,那麼高的山根本不可能開個挖掘機上去,那麼只能手動。
我必須學會如何挖土刨坑後才能做好埋葬奶奶骨灰的事兒。
搜索之後,我發現比自己以為的要簡單很多。
買個樹洞挖掘器,操作簡單,而且價格便宜,一百塊錢不到就能輕輕松松搞定。
我先拿出像把槍的家用電鑽,這個負責挖土的動力,我已經確保上山之前充足電。
再將一片帶有圓形鋸齒片的鑽頭接到不鏽鋼鐵杆上,這個負責開洞。
看視頻解說,這種螺旋形狀的鑽頭可以不斷挖向深處,而且泥土會被旋轉動力帶出坑外。
免去了鏟土的步驟,省時省力。
按照廣告上的介紹,我應該十分鍾不到就能做完。
組裝好後,我拿起電鑽,發動機發出巨大的轟鳴聲。
當鑽頭垂直對准土地一瞬間,泥土松動,像沸騰的水泡翻滾涌起,沒有一分鍾一個圓圓的土坑就成型了。
我正暗暗高興之際,忽然鑽片的聲音變得尖銳,像是碰到一塊非常堅硬的東西。
我還沒來及提起來,尖銳的刺耳噪音又變成啪啦啪啦聲。
我趕緊關掉開關,拿起來一看,圓形的鋸齒片被磕掉了半扇,坑底不僅顯露出石頭的一角,而且還有一部分巨大的老樹根。
“你這東西種個樹苗,花草或者埋個木樁可能好使,松林山是到處是樹林,碗一樣的樹根盤根錯節,稍微往深挖一些,就不是一個鑽片能做的了。”鐵蛋忽然發聲。
原本以為鐵蛋給我引路之後就自己離開了,沒想到鐵蛋竟然沒有走,而且全程觀察。
我沮喪地問道:“你干嘛不早說?”
他沒有再說話,拿起鐵鏟走近我。架勢有些嚇人,我不由朝旁邊退了退。鐵蛋又仔細看了我挖好的坑,然後揮起鐵鏟將坑中的土清理出去。
我再遲鈍,這會兒也看出鐵蛋打算幫我一起掩埋奶奶的骨灰。
村里人說鐵蛋是個怪物,人們都很怕他,覺得他充滿危險。
不過沒人敢當著他的面這麼說,惹惱這麼大塊頭的人,打起架肯定會吃虧。
我回旬村後,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面見到鐵蛋。
我並不擔心安全,雖然這個男人動動手腕,我就能飛到空中再重重摔下來。
然而,奶奶這輩子最痛恨的就是暴力,遠離這樣的人是我一路成長的座右銘。
現如今,把院子分出來一塊兒給他居住,說明奶奶信任他,而我信任奶奶,所以我也信任鐵蛋。
日頭已經升高,山里還很涼快,但依然能感覺到溫度升高了好幾度。
我把馬尾辮上散落的發絲往腦後固定,著迷地看著他一鏟一鏟將坑里的土挖出來。
這個令人不安的大塊頭男人認真做著眼前的活兒,泥土、樹根、石塊兒,像是有了生命一樣,在他的操作下乖乖聽話,真是一種享受。
很顯然鐵蛋不是碰巧出現在這里,而是一直跟著我,打算和我一起埋葬奶奶。
我原本還納悶,甚至有些生氣,奶奶在世時一直在照顧鐵蛋,而且立遺囑時還專門提到他,但他卻從未露過面。
白事那天,他甚至沒有來燒根香,敬杯酒。
現在看來,他並非我以為的那麼冷漠無情。
鐵蛋和村里其他人確實不一樣,短短幾分鍾的相處,我已經看出鐵蛋不愛說話、不善交流,不喜歡人多喧鬧的地方,也許他也知道自己不受歡迎,所以只是悶頭做事。
我的注意力被他的前臂吸引,結實的肌肉和鋼絲一樣的靜脈上,布滿一層黑色的毛發。
他一次又一次將泥土甩出坑外,幾乎和我小腿一樣粗的二頭肌在動作時聚在一起,滾動伸展。
我這輩子從來沒見過像他這樣的人,渾身上下散發純粹的力量,陽剛之氣達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如果鐵蛋真像村里人說的那麼離群索居,孤僻安靜,是否表示還沒人觸摸過這一身的肌肉,沒人見過褲子里面藏著的家伙。
在我還沒來及壓抑之前,胸口積累的呻吟就從嗓子里滑出來。
我尷尬地趕緊低頭,迅速彎腰拿起腳邊的背包,從里面取出一瓶水。
鐵蛋也停下手里的動作,朝我看過來。
我不知道鐵蛋有沒有聽到,即使聽到了他也什麼都沒說。
還沒等我將水瓶遞給他,他又換了個鐵鎬,朝坑里砸下去。
鐵蛋小時候非常悲慘,父親脾氣暴躁,動不動就對母子倆飽以老拳。
鐵蛋總是盡他所能保護媽媽,但還是阻止不了悲劇發生。
媽媽沒了性命,鐵蛋憤怒中殺死了他的父親。
奶奶總說鐵蛋的爸爸是罪有應得,那個老頭是個殘暴的混蛋,早該有人在他兒子動手之前將這個男人大卸八塊。
奶奶對鐵蛋充滿同情,經常收留他在家里吃飯過夜。
後來鐵蛋從教管所放出來,又把他接回來住在一起。
村里人對他卻一直抱有戒心,無論社會發展有多快,村民的生活水平有多大改善,農村就是農村,閉塞而保守。
任何與他們不同的人,都會嚇到他們。
他們不喜歡鐵蛋沉默無語,不喜歡鐵蛋獨來獨往。
我估計圍繞在鐵蛋身上的黑暗過去和流言蜚語著實嚇人,再加上他的體型和力量令人生畏,盡管也會有人出於好奇多看他幾眼,但仍然保持著距離,不會想到接近他。
鐵蛋沒在莊稼地里忙農活時,又在干什麼呢?
當然,我知道他現在在干什麼,他在幫一個沒有土地常識的女人挖土埋葬親愛的奶奶,可是其他時候呢?
鐵蛋是個謎,自從奶奶去世,我搬回村子這幾天,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知道他住在院子的另一邊,但沒有多少機會接近他,也沒有更多了解他。
盡管鐵蛋這會兒會時不時看向我,而且眼神熱烈,但也明顯散發出一種'請勿靠近'的氣息,這種氣息在五十米以外就可以感覺。
“莎莎?”
我驚訝地眨眨眼,低沉的聲音聽起來謹慎、堅韌,惹得我心跳加快,皮膚泛起一層雞皮疙瘩,就像一陣冷風吹過全身。
我臉上掛著微笑,強迫自己的目光停留在他的肩膀上方。
“哦,鐵蛋,你要不要休息一下?”我客氣地問道。
“已經夠深了,任三爺就在旁邊,都好好的,你看可以麼?”鐵蛋低下下巴,頭發因汗水而變得更黑,向前垂落在額頭上。
我眯起眼睛迎著陽光,靠近幾步,墓坑平平整整、端端正正,鐵蛋知道他在做什麼。我感激地說道:“非常謝謝你,喝點兒水吧!”
我有點兒局促不安。
該死,怪不得鐵蛋不招人待見,這個男人太凜冽,好像在無聲地告訴你,他不在乎你是否相信所有關於他的故事,更不在乎你的看法。
我無從判斷真假,也懷疑這是否是他為了保護自己,多年養成的習慣。
但他的眼神,確實令人非常不舒服。
我後退一步,“好吧,我聽你的,你比我更有經驗。”
我小心從背包里拿出木盒,當我捧在懷里時,我的情緒才開始融入沉甸甸的環境中,這一刻有點兒詼諧有點兒難過。
奶奶生前挺胖,但身體一直很好,走路飛快。
小時候走在她身邊時,總是要牽住她的手才能跟得上腳步。
後來漸漸大,我還是沒有習慣奶奶的走路速度,不止一次扯著她的胳膊讓她慢點兒走。
每次奶奶都很高興,我也發現這樣可以帶給她滿足感,如此輕而易舉。
如今,抱著骨灰盒的我好像還在做類似的事兒。
一步一步緩慢向前,可還是覺得走得太快。
這是最後一次我跟奶奶說慢點兒再慢點兒了吧!
奶奶希望在這里安葬,可是我卻那麼舍不得。
鐵蛋默默等著我,直到我來到跟前,才舉起手接過盒子,小心放到坑底,再用厚厚的油氈一層層結結實實包好。
他雙臂撐著坑壁,借著凹凸起伏兩三下從坑中跳出來。
鐵蛋還是沒說話,退到一邊給我時間和奶奶說再見。
我捧起一把土撒下去後,他才跟著我用鐵鍬將土一點點填埋回去,很快地面就平整了。
鐵蛋還將原本被破壞的花草重新修復,蓋在上面,遠看近看都和周圍沒有絲毫區別。
我拿出香爐,點了三根香插進去,跪在原地想再陪一會兒奶奶。
沒想到鐵蛋隨著我,也點香跪拜。
直到香燃盡,我們才站起身。
趁著鐵蛋收拾工具,我清清嗓子,客氣地說道:“鐵蛋,謝謝你今天幫我完成奶奶的遺願。沒有你,我真不知道會有多狼狽。占用你這麼長時間,這麼大力氣,你看我該給你多少錢呢?”
鐵蛋的眼睛微微一閃,眼角的皮膚皺起來。
不是因為微笑,不,我沒見過他笑的樣子,他看上去很緊張,布滿頸背的下巴繃得緊緊的,喉結在粗壯的脖頸前上下滑動。
很快,他的表情平靜下來,又變成毫無情緒的冷淡模樣。
我垂下目光,注意到鐵蛋有力的拳頭在身體兩側握緊又松開。
我明白付錢給他的主意讓他很不舒服,我有些愧疚,雖然沒有說出來,但知道鐵蛋真心希望能幫奶奶做些事情。
我一定沒給他留下好印象,即使他會用火熱的眼光看我,但他從未表現出任何想要更多的跡象。
我猜他這輩子已經受夠了,像個怪物一樣走哪兒都被人盯著,在他背後竊竊私語、猜測、評判。
“呃,時間不早了……”我跌跌撞撞後退一步,就像我有兩只左腳似得。
鐵蛋指著壞掉的挖坑神器,說道:“挺沉的,我幫你拿吧!”
我沒有推辭,上山容易下山難,這點兒常識我還是有的,輕裝上陣比負重前行要容易很多。
我再次謝謝他,請他晚上來家里吃飯。
這是最稀疏平常的事兒,但鐵蛋只是扛著所有工具,轉身朝回走。
他走得非常快,沒一會兒就不見身影。
我看著腳下的路一步步向前,不知何故,我能感覺到鐵蛋強烈的目光一路追隨著我。
自然而然,我腦子里冒出一個念頭,有可能性麼?
從目前的情形看,鐵蛋更像是奶奶收養的一個孩子,就像她當年收養我一樣。
換句話說,鐵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我的兄長,而不是戰利品。
所謂戰利品,是說解決生理需要的那類獎賞。
另外,我現在需要的是長期穩定的關系,三十多歲啦,這個年齡和男人上床,都是衝著結婚生孩子。
天啊,鐵蛋這樣的男人會生出什麼樣的孩子?
我心念一動,也許……住在我家院子這件事兒可以影響他……我吸了一口氣,為自己的大膽念頭驚嚇不已。
我真的在考慮利用房東身份讓這個男人與我發生性關系嗎?
我怎麼了,竟然墮落邪惡到這個地步!
我一定是因為剛失去奶奶思緒混亂,所以大腦不能正常運作。
有趣的是,混亂的大腦還能做其他事情。
譬如回家後洗澡的時候,尤其關注體毛。
這在洗浴間可不是容易的事兒,我不得不把一只腳抬到淋浴牆上踩實,然後屁股頂在洗臉盆上,才能仔細干淨地剃毛。
其中涉及的靈活性令人驚訝,更不用說體現出的決心了。
為什麼?
因為我想!我是一個獨立的現代女性,如果我願意的話,可以和任何健康且單身的男人發生性行為,不必有絲毫負疚感。
我套上一條干淨的運動褲和一件柔軟的襯衣,開始在廚房里忙碌。
這一切都可能是浪費時間,我甚至不知道鐵蛋會不會來。
我仔細回想在山上的情形,非常確定鐵蛋沒有給我一個肯定的答復,但是他也沒說不來。
我一邊做飯一邊琢磨,沒想到抬眼就從窗戶看到鐵蛋從遠處走過來。
他沒有到門口敲門,而是站在窗戶外面,等著我發現他。
“正是時候,”我微笑著跟他招招手,讓他進屋。
鐵蛋非常拘謹,我必須說點兒什麼才能讓他放松。
“鐵蛋,奶奶經常和我提起你,說你給她幫了很多忙。現在奶奶不在了,我十有八九還是得靠你。你放心,奶奶已經囑咐我,你在這里想住多久都沒問題,我不會趕你走的。”
桌子太小,鐵蛋坐在我對面時,我們的膝蓋碰在一起。
我沒有挪開,他也沒有。
鐵蛋把一筷子食物舉到嘴邊,咀嚼、吞咽、舔嘴,喉結上下滑動,我們的目光交匯在一起。
我看著他的嘴唇分開,如果沒有那些胡子,他的嘴唇會更清楚些。
我的天,我什麼時候這麼開放?
單身太久麼?
還是辦公室里呆得太久?
真是……太不要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