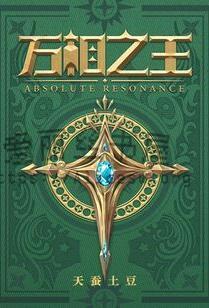雲州,雲中府。
城外西去一十五里,一片草木金黃,竹籬之外,鴨鳴陣陣,碧水之東,水聲瀟瀟。
一隊人馬迤邐行來,一個青衣小廝牽著一匹青灰色高頭大馬走在最前,馬上端坐一位中年男子,他一身素黑金线襴衫,頭戴黑色鑲金幞頭,發髻上插著一支黑檀描金木釧,面上髭須綿延,天庭飽滿,雙目炯炯,顴骨豐圓,面容清癯,望之便有一番沛然華貴之氣。
一輛雙轅馬車隨後行來,環佩叮當作響,門窗精雕細琢,車夫輕抖韁繩,三匹健壯兒馬輕嘶聲聲,輕松拉著馬車穩步向前。
隊伍後面跟著十幾號人,肩扛手提,拿著各式箱籠等物,塵煙四起,聲勢不小。
駿馬筆直行到農園竹籬之外,早有仆役打開院門候在門口,中年男子輕身下馬,看著馬車停穩,車里丫鬟先自下來,隨後設下腳踏,才有兩名貴婦先後下來。
頭一人滿頭金銀翡翠,面上濃妝淡抹,花容精致,雲鬢烏黑油亮,眉毛彎如柳月,櫻桃小口微笑,瓊瑤鼻兒高挺,香腮紅艷欲滴,臉若皎月當空,腰如楊柳迎風,伸出素白軟嫩一雙玉手,就著車前丫鬟婢女扶著,這才伸出香蓮,踩在錦榻之上。
只見那小腳細致如弓,一雙白綾金絲粉面繡花高底鞋上,各自嵌著一顆璀璨雪白珍珠,邁步之間,便是滿目富貴風流。
婦人落步青石路面之上,男子早已過來接了,輕輕牽住女子玉手,等著車上另一人下來。
卻見馬車之上,又一女子探出頭來,她秀發簡單盤攏,一身素布衣裳,不施粉黛,清淨自然,卻仍是眉如天河倒掛,目若日月繁星,熒熒白白一支素手扶住車門,舉步邁出,未見其人全部,已覺春風撲面,待其下得車來卓立車前,不由讓人自慚形穢。
女子純淨淡雅之美別有韻味,與此田野鄉間鴨鳴水光渾然一體、相得益彰,無形中更添無盡風華,直將先前女子比了下去。
先前女子已是風華絕代,後面女子卻占盡天時地利,其中細微差別,凡俗之人自難體悟,那中年男子看見身邊女子櫻唇嘟起,卻是看得明白,連忙小聲說道:“夫人今日端的好看,嫵媚動人之處卻是無人能及!”
聽她說得好聽,婦人終於眉眼含笑,抿嘴小聲回道:“倒是不如你家溪菱妹子淡雅可人!”
女子正是岳家長婦柳氏,身邊男子則是岳家當代家主,姓岳名元祐,乃是雲州推官,素來剛正不阿、嫉惡如仇,只是家中柳氏妖嬈且又性格潑辣,不知怎的便有了個懼內的毛病,岳家內外事體,皆自運籌帷幄閨房之中,闔府上下,倒是無人不知,便連外人也已知曉一二。
柳氏系出名門,娘家乃是省中豪門,原來與岳家聯姻本是門當戶對、官商相得,不成想岳家長輩去後,這代岳元祐官路不順,年逾四十仍只是個七品推官。
好在柳氏借著娘家幫襯,細心經營家中田產生意諸事,日子過得如日中天,竟比老太爺在世時還要家紫殷實了些。
“這處田產乃是新近購得,依山傍水,風水上佳,便將祖墳遷移於此;待我百年之後,也讓樹廷將我埋於此地……”岳元祐看著妹妹過來,面色一肅說道:“溪菱既要獨居,太過寒酸也是不好,你嫂嫂心思細膩,將你安排在此,田園景象倒也舒適,距離父母墳前不遠,自此向北兩百余步便是。”
岳溪菱輕輕點頭,面上隱現悲戚神情,她還家至今,已然明白父母故去因由。
當日父親與友人飲酒,至深夜方歸,隨後夜間病發,次日便駕鶴西游。
父親去後,母親整日以淚洗面,積郁成疾,兩年後也溘然長逝。
三人當前而行,後面幾個丫鬟仆役扛著祭掃之物,沿著一條新修甬路向北而行。
“母親在時,常常念叨與你,不知你是生是死,這麼多年來不曾捎個口信回家,若是活著,如何這般狠心……”岳元祐牽著發妻緩步而行,說起父母,面容哀戚沉重。
“當日不是老太爺逼迫太甚,菱兒也不至於離家出走!”柳氏秀眉一挑,櫻唇輕啟,出言便是毫不留情,“總歸是自家女兒,喊打喊殺逼著墮胎,最後倒好,溪菱心一橫走了,倒是成全了海棠!早知如此,當時直接將海棠許將出去多好!”
岳溪菱默然無語,岳元祐卻無奈嘆息說道:“莫要胡言亂語!當日若不是溪菱出走,父親權當……權當她不在了,豈會以妹代姐完成婚約?”
“那卻不是這般道理……”柳氏不甘示弱,自然便要反擊。
眼見兄嫂又要拌嘴,岳溪菱連忙說道:“好了好了!千般不是萬般過失,皆在小妹年少無知、錯付他人,當日若非我做下錯事,父親也未必……”
她說的悲戚,柳氏聽在耳里,知道自己勸解不了,便推了推丈夫。
岳元祐無奈勸道:“卻也不能全然怪你,父親宦海沉浮、不得其志,郁郁難平之下,每日飲酒作樂,以至傷了根本,才有此急病……”
柳氏白了丈夫一眼,“什麼『不能全然』,根本不怪三妹!溪菱去後,公公只是罵了幾日便再無言語,若非遭人讒害、貶黜回鄉,豈能如此終日飲酒?你可莫要學他,當個推官倒也夠了,不必整日鑽營向上,免得到時郁郁寡歡,步了老太爺後塵!”
“你……”岳元祐惱她胡言亂語,卻又不敢發作,長嘆一聲,干脆不再說話。
岳溪菱一旁掩嘴輕笑,兄嫂如此相處,她早已見慣不怪,不成想二十年過去依然如此,不由心生感觸,只是笑著說道:“官路坎坷,起伏由人,看淡看開便是,兄長倒也不必強求。不過我聽嫂嫂說起,樹廷卻已考中舉人,卻不曾進京赴試,早早補了官身,這卻是為何?”
聽三妹說起兒子,岳元祐眉頭輕皺,便要細說一二,卻被妻子推了下手臂,趕忙閉緊嘴巴不再言語。
柳氏隨即笑道:“樹廷書讀的倒是極好,只是這科舉一途,我倒也不盼他如何精進,如今僥幸中了舉人,便也足夠了,我可不盼他學你父兄,進京趕考,蹉跎三年,不中再考,如此反復,最後也未必得償所願……”
岳溪菱明白柳氏所指,岳家詩禮傳家,祖父當年高中進士,官至戶部侍郎告老還鄉,父親當年十六歲中舉,而後六次入京趕考卻一無所獲,兄長則考了兩次仍舊一無所成,被柳氏逼著補了官差,熬了這十幾年才升至七品。
柳氏不想兒子走父輩老路,岳溪菱卻深知,岳家自詡詩禮傳家,卻連著三代不出一個進士,實乃奇恥大辱,只是兄長懼內,明明有心讓侄兒樹廷繼續進學,卻又不敢直言,畢竟父母去後,岳家上下柳氏一人獨大,早就無人可制,若非柳氏人品還好,並不如何囂張跋扈仗勢壓人,只怕比眼下還要難挨。
三人邊走邊聊,不多時來到一處墳塋之前,只見青磚壘砌,石碑光潔,占了好大一塊田地。
“祖父曾有遺命,自他以降,岳家開枝散葉,便不再歸入祖墳,老家那邊人物凋零,平時也無甚往來,今後只怕再無瓜葛了……”
岳溪菱輕輕點頭,眼中浮現淚光,只是強忍著說道:“當年一番齟齬,祖父庶出離家成就功名,自然心有怨恚之意,而後風生水起,老家卻人才凋敝,兩邊形勢不同,不肯認祖歸宗倒也情理之中……”
岳元祐點頭,接過仆役遞來黃紙燒酒等物,按著規矩祭掃起來。
岳溪菱端跪墳前分別給父母叩了響頭,當日還家她已在祠堂拜祭過父母靈位,後來便與兄長嫂嫂商量,要來父母墳前守孝三年略盡孝心,才有今日之行。
岳元祐自無不允之理,只是公事繁忙,直到今日得空方才成行。
岳溪菱放聲大哭,嚎啕之聲綿延不絕,岳元祐眼眶潮濕,念及父母恩情,不由得也悲戚慘淡。
柳氏也流了幾滴眼淚,看小姑溪菱哭得傷懷,趕忙衝丫鬟使了個眼色,自己也過去將她扶起勸解不已。
良久兄妹倆整肅儀容,重新跪下磕頭,柳氏也跟著磕了頭,這才一起回到農莊之中。
農莊里住了七戶人家,皆是岳家佃農下人在此,柳氏早已命人騰了三間房屋出來,土坯膠泥牆面,茅草松木屋頂,平常日子有人專門打柴拎水,岳溪菱推辭了柳氏安排的幾位仆役傭人,只留下一個丫鬟作伴。
莊里已備下午飯,一應菜肴皆是田間所產,河中鯉魚、田里絲瓜,醬煮鴨肉、山里香蘑,菜肴不似平日精致,味道卻是極佳,只是兄妹倆哀思濃重胃口不佳吃得並不香甜,只吃了半碗米飯便即飽了。
柳氏見兄妹倆都不再吃,只得放下筷子漱了口,叮囑農莊管事的一些尋常話語,這才與丈夫一道回了城里。
岳溪菱帶著回府後新配的丫鬟小玉送到農莊門口,看兄嫂上車走遠這才回返進院。
“以後卻要勞煩你在此陪我,若是呆的膩了便與我說,自當不會耽誤你三年光景……”岳溪菱當前而行,側回頭與丫鬟小玉說話。
小玉年紀不大,買來府里三年,一直在柳氏房里伺候,如今十三歲上下,容貌出落得更加秀麗,身段苗條細致,此番過來伺候岳溪菱,便是柳氏防著丈夫之舉,想及方才兄長看小玉眼神,岳溪菱心知肚明,卻也並不說破。
岳家三代單傳,父親便有些懼怕母親,兄長怕嫂嫂更是畏如猛虎,卻不知侄子樹廷夫妻相處如何,若也如此,只怕岳家香火難旺。
聽她這般客氣,小玉連忙說道:“奴婢不敢當姑奶奶如此客氣!若是姑奶奶呆的煩悶,奴婢陪著走走散散心倒是有的!何況這里便再憋悶,卻也比府里寬敞的多,奴婢自幼長於田間,能夠陪著姑奶奶在此長住,不知道心里多快活呢!”
岳溪菱看她玲瓏剔透,不由心中滿意,連日相處,彼此早已熟悉,她心中感慨,天地生人,卻是同人不同命,小玉家中三兒兩女,父輩本是附近農戶,只是當年遭了水災,這才賣兒賣女,如今她兄妹幾人各在不同人家為奴為婢,衣食不愁,卻總要仰人鼻息。
回到房中收拾床鋪細軟,主仆二人便就此住下,此後每日里,岳溪菱雞鳴便起,灑掃庭院,整治粥飯,而後為父母墳塋填土除草,閒來無事讀書寫字,晚來便登榻而眠,日子倒也過得平靜淡然。
此間日月,便如當年山中十數年一樣,只是眼前並無亭台樓閣,身邊也無玄真那般知情識趣伴侶,膝下更無彭憐那般骨肉相連愛子,個中孤獨苦澀,卻是不足與外人道也。
夜里偶然醒轉,岳溪菱便即想起山中歲月,與玄真溫柔繾綣,與愛子耳鬢廝磨,隨即春思難耐,總要自瀆一番才能睡著。
想著與兒子三年之約,心中更是情動,既盼著兒子信守諾言,三年後再來尋他,心中卻又隱隱怨恚,他竟然舍得讓自己苦等三年,心中矛盾彷徨,輾轉反側,夜不能寐。
十月將近,這一日,一騎快馬翩然而至,送來岳府家書,原來家中大姐池萍歸鄉省親,柳氏命人送來書信,邀她還家團聚。
岳家四女,大姐池蓮遠嫁他鄉,二姐湖萍嫁與鄰省富商,當年岳溪菱留書出走時,家中便只有她與四妹海棠,待她去後,海棠代她出嫁邊關守將為妻,平日里只有二姐偶有來往,大姐四妹俱是至今音信皆無。
如今大姐歸鄉省親,岳溪菱自然要去一見,連忙命人備了車馬,次日一早出門,回到城中來見大姐。
一路行來,路邊秋意遼闊,天高雲淡,天氣甚好,岳溪菱觸景生情,不由念起玄真彭憐,心中自是好生難過。
路過城門時,車窗外人影一閃,岳溪菱心中一動,撩起窗紗去看,卻再無旁人,她深知自己思念情切,不由又是一陣感傷。
馬車進了岳府側門,在內院門前停下,丫鬟小玉當先下車,扶著岳溪菱下地站穩,主仆二人這才進了小門,來到內院。
岳府原址兩間四進,這幾年柳氏持家有道,又將鄰家幾處院落買來修葺一番,如今已是五間七進大宅,自己住著正房院子,兒子兒媳住著東院,女兒住著後院繡樓,其余房舍倒都空著,岳溪菱回來暫住在後院繡樓,如今她搬了出去,卻不知大姐住在何處。
進了內院,早有丫鬟迎了上來,說夫人與大姑奶奶正在正房等候。
岳溪菱心情急切,腳步竟有些不穩,三步並做兩步上了內宅正房台階,卻見廳中兩位美婦端坐正中,一位自是柳氏,另一位渾身珠光寶氣,衣飾華貴,氣度雍容,不是自家大姐更是誰人?
“大姐!”岳溪菱快步上前,撲到起身迎來的大姐懷中,悲鳴一聲,隨即痛哭起來。
連日來悲傷愁苦,終於遇到體己之人,尤其大姐池萍遠嫁,父母病故也未侍奉床前,彼此差相仿佛,自然感同身受。
“好了好了!昨日大姐歸來,便哭得我肝腸寸斷,今日你們姐妹再哭,我怕不是要被哭死!”柳氏一旁喝了口茶水,見姐妹倆哭個不住,不由出言勸止。
長嫂有命,姐妹倆果然止住哭聲,岳溪菱擦去眼角淚水,細細去看自家大姐。
她已二十余年未見自家大姐,只見岳池蓮依稀還是當日出嫁模樣,頭上梳著高椎發髻,上面插著金珠鳳簪玉蘭花釵,耳上嵌著銀絲珍珠吊墜,除卻面容哀戚氣色不是甚好,裝扮華麗之處竟是不遜柳氏多少。
“姐姐一去多年,如何今日才想起回鄉省親?”岳溪菱在大姐身邊坐下,溫言說起家常。
“說來話長,昨日午間到此,嫂嫂問起,我卻有口難言,如今卻不得不說了……”岳池蓮聲音淳厚溫和,她面容瘦削,雖有粉黛遮掩,卻難掩衰敗氣色,面容與岳溪菱相仿,只是略顯疏闊,不似自家三妹那般精致。
她娓娓道來,說明此間因由。原來岳池蓮當年遠嫁他鄉,許了嶺北許家次子,而後生育一兒一女,多年來相夫教子,日子倒也過得順遂。
後來家中老太爺病故,幾個兒子分了家產自立門戶,大姐家中分得不少田地房產,金銀財寶更是不計其數,以此開端,先是夫婿手中有了錢財好酒如命,後是兒子仗著金銀無數隨意揮霍整日花天酒地、留戀青樓,更交了一些狐朋狗友,每日里招災惹禍,弄得家宅不寧。
終於三月前許家二爺醉酒失足墜馬而死,岳池蓮自覺脾氣秉性管束不得兒子,便以省親為名帶著兒子女兒回鄉,盼著兄長能幫著教導一二,不求兒子幡然悔悟洗心革面,只為遠離那般狐朋狗友,免得到頭來也落得個橫死下場。
聽她說完,柳氏與岳溪菱對視一眼,都覺得此事難為,她輕聲問道:“若我推算不差,鵬兒年紀當與樹廷相仿,約在二十上下吧?已是這般年紀,卻如何管教得來?”
“實不相瞞嫂嫂,”岳池蓮泫然欲泣,“鵬兒在原籍已是惡名遠播,每日里欺男霸女,民怨早已沸騰,若任由他長此下去,只怕殺身之禍近在眼前……”
“我已將家中田地房產盡數變賣,用了迷藥將鵬兒綁上馬車,全家搬遷至此……”岳池蓮起身跪地不起,口中哀求不住,“還望嫂嫂為妹妹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