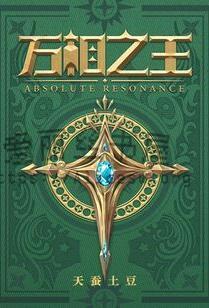如今的青衫渡只是有了個仙家渡口的雛形,除了渡船停靠處,就只建造出一間負責登記乘客關牒、發放登船玉牌的屋子,在這里臨時當差的是裘瀆和胡楚菱。
這個昵稱醋醋的小姑娘如今已經是一宗之主崔東山的嫡傳弟子,在山上確實也算得上是一步登天的造化了。
按照從落魄山傳下的老傳統,屋門前擺了一張桌子,其實就是崔東山專門為周米粒准備的,作為每日巡山一趟的休歇處。
青萍劍宗暫時還名聲不顯,也沒有與桐葉洲各大山頭、渡船簽訂契約。
既然沒有渡船,就自然沒有修士落腳了,這張桌子就是個擺設。
不過周米粒每天都會在這兒坐上個把時辰,與裘老嬤嬤和醋醋姐姐聊聊閒天。
裘瀆的大道根腳使然,對這個俱蘆洲啞巴湖出身的洞府境小水怪天然親近。
但是今天周米粒離開洞天道場後,一路巡山到屋外,將金扁擔和綠竹杖都擱在桌上,不勞煩裘嬤嬤,自個兒燒了一壺開水,煮了三碗茶水,先端給老嬤嬤和醋醋姐姐各一碗,再拿著自己那份離開屋子,獨自坐在桌邊長凳上,兩腿懸空輕輕搖晃:好茶好茶,老廚子親手炒制的茶葉好,自己煮茶的手藝更是爐火純青哩,相得益彰!
周米粒嚼著一片茶葉,揉了揉眼睛:真有客人來訪?
只見遠處來了兩人,一個年輕人,背著個竹箱;一個胖乎乎的,隨從模樣,斜挎包裹,風塵仆仆的,就像兩個風餐露宿的行腳商。
當年在故鄉啞巴湖,周米粒見過很多這樣的人,一下子就生出了親近之心,小臉蛋上兩條疏淡微黃的眉毛掛滿了喜悅。
她趕緊放下茶碗,再將桌上的金扁擔和綠竹杖取下,斜靠長凳,快步向前,只是沒有跑出屋子太遠,站定後,一只手輕輕拽住棉布挎包的繩子,稚聲稚氣道:“兩位貴客從哪里來,到哪里去?我們這兒叫青衫渡,屬於青萍劍宗地界,與客人們道個歉,如今渡口建立沒多久,尚無供人遠游的渡船。”
背著竹箱的年輕男子看著那個斜挎棉布包的小水怪,神色柔和,輕聲道:“我叫張直,是個走南闖北的包袱齋,來這邊逛逛,不乘坐渡船遠游。你們宗門有無需要外人注意的山水忌諱?”
周米粒搖搖頭,笑道:“來者是客,無甚忌諱。”
其實話一說出口,小米粒就後悔了。
怪自己業務不精啊,只是來巡山,渡口忌諱規矩啥的,得問過裘老嬤嬤和醋醋姐姐才行。
完蛋了,完蛋了,如何補救,如何是好?
黑衣小姑娘皺著疏淡的兩條小眉毛:愁啊,等會兒與兩位外鄉人寒暄過後,得趕緊找裘老嬤嬤搬救兵去。
張直笑道:“這位小仙師能否容我們歇腳片刻?”
周米粒使勁點頭,學暖樹姐姐的樣子與他們施了個萬福:“請。”
一起走向桌邊,張直身邊的胖隨從笑著自我介紹道:“小仙師,我叫吳瘦,胖瘦的瘦,道號靈角,空靈之靈,不是吃的那種菱角。”
周米粒趕忙回話:“大仙師,我叫周米粒,碗里米粒的米粒,能吃的那個米粒。”
吳瘦笑著點頭,用眼角余光瞥了眼密雪峰,以心聲說道:“主人,龐超就在山上瞧著這邊,不過看樣子,不會主動下山來見主人。”
張直以心聲答道:“見了也沒什麼可聊的,不見好,省得尷尬。吳瘦,如果能夠見著那位年輕隱官,你就莫要舊事重提了,不討喜,別搞得我們像是登門討債似的。”
吳瘦是昔年寶瓶一洲包袱齋的話事人,其實與落魄山還有點淵源,因為牛角渡最早的那個包袱齋就是吳瘦當初親自與大驪宋氏打下的基礎,只是吳瘦膽子太小,氣魄不夠,或者說是光盯著可見的財路,結果沒做幾年生意便早早撤掉了人手,關門大吉,只留下了個空殼子,算是便宜了後邊與北岳魏檗一同接手牛角山的落魄山,山頭都歸人家了,自然就順便將那些仙家建築一並收入囊中。
但是這麼多年,落魄山一直沒把那邊的渡口生意真正做起來,一開始還是門派的底子薄,手里邊沒貨,後來開辟出了一條俱蘆洲東南航线,生意剛剛有點起色就開始打仗了,整座牛角渡被大驪軍方征用,商貿運轉一事就徹底擱淺了,這些年形勢有所好轉,但是還缺個會打算盤的主心骨。
幽居修道,與跟人做生意,隔行如隔山。
因為吳瘦當年自作主張撤出寶瓶洲絕大部分的包袱齋,與大驪宋氏鬧得不太愉快,在那之後,包袱齋等於是徹底失去了寶瓶洲這塊地盤,只要大驪宋氏一天不改口,包袱齋就不敢擅自在寶瓶洲開張,哪怕是齊渡以南都已陸續復國,包袱齋還是不敢去觸這個霉頭。
走了個繡虎,來了個隱官,何況這兩位還是同門師兄弟。
周米粒等到兩位商賈落座後,問道:“張先生、吳仙師,要喝茶嗎?”
吳瘦瞥了眼桌上的茶碗,茶葉與煮茶之水都不講究,便搖頭笑道:“不用了。”
張直卻說道:“勞煩周仙師給我來一碗熱茶。”
周米粒立即站起身笑道:“好嘞,張先生稍等片刻。”
吳瘦疑惑道:“這只小水怪瞧著腦子不太靈光啊,就只是個洞府境,當真是落魄山的右護法?就不怕外人看笑話?”
張直微微皺眉。
一道白虹貼地長掠而至,飄然落座,招手大聲喊道:“右護法,別忘了算上先生和我的兩碗。”
除此之外,又有一位青衫客站在吳瘦身後,一只手搭在胖子肩膀上:“我家周米粒擔任落魄山右護法,你一個外人,有意見?”
正是一路慢悠悠返回仙都山的陳平安和崔東山。
吳瘦愣在當場:自己不是以心聲言語的嗎,怎就被聽了去?
吳瘦剛要有所動作,就發現肩膀上的那只手往下一按,他整個人身小天地的靈氣運轉就隨之凝滯,如河水結冰一般。
那人繼續笑道:“我問你話呢。”
張直抱拳道:“陳山主,吳瘦口無遮攔,多有冒犯,我先幫他道個歉……”
陳平安斜眼望向那位包袱齋老祖師,直接打斷:“這里是青萍劍宗,你幫不了他。”
崔東山繃著臉憋住笑:好好好,這張直真是自家好兄弟,吳瘦更是條鐵骨錚錚的硬漢子,敢在青衫渡這麼說小米粒,腦殼都給你敲爛。
看看,自家先生平時脾氣多好,更是一貫禮敬前輩的,這都給你們整生氣了。
活該活該,千不該萬不該,不該說我們小米粒的壞話。
陳平安單手負後,一手搭在吳瘦肩膀上,身體前傾,低頭彎腰,微笑道:“再這麼裝聾作啞,我可就要下逐客令了。”
吳瘦顫聲道:“恕罪,隱官恕罪,無心之語,多有冒犯,是我鬼迷心竅了,腦子犯渾。”
周米粒和胡楚菱一起端來三碗茶水,胡楚菱將兩碗茶水輕輕放下,周米粒負責端給張直。
她朝好人山主咧嘴一笑:這個張先生是外人哈,禮數要足,雙手奉上。
陳平安笑眯起眼,輕輕點頭:明白。
崔東山笑道:“右護法,你先跟醋醋回屋,外邊天寒地凍,不比屋里暖和。”
周米粒皺著眉頭:我一只大水怪,怕冷?天大笑話!只是她又靈光乍現:曉得了,好人山主要跟人聊正事,大買賣!
陳平安拍了拍吳瘦的肩膀,坐在余下的一條長凳上。
方才大白鵝見先生起身,就開始拿袖子擦拭身邊長凳,白忙活了。
陳平安開門見山說了兩句話:
“張先生喝完茶就可以走了,包袱齋在寶瓶洲重新開張一事,免談。”
“就算大驪朝廷點頭,哪怕是皇帝宋和答應,一樣作不得准,我說不行,就是不行。”
張直笑容如常,喝了一口茶水。
吳瘦苦笑道:“陳山主,難道就因為我這句冒失言語,就要與整個包袱齋交惡?”
張直微笑道:“這種個人恩怨,別扯上我的包袱齋。”
吳瘦心一緊,使勁點頭:“是我又說錯話了。”劍修的惡劣脾氣,這回算是真正領教了!
崔東山哀嘆一聲:“張直啊張直,你真是帶了個活祖宗在身邊。原本好端端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機會,結果給這麼一鬧,雪上加霜了不是?一下子就少掉兩洲生意,擱我是你,這會兒已經先甩自己兩個大嘴巴,再甩吳老祖幾個耳光了。”
周米粒守在屋門口盯著所有人的茶碗,等會兒一看到誰喝完碗里的茶水,她就可以准備隨時添水。
至於幾人具體聊了啥,她聽不清楚,也不會偷聽,多半是大白鵝又抖摟了一手術法神通。
瞧瞧,大白鵝正朝自己擠眉弄眼呢。
唉,如今都是當宗主的人了,也沒個正行。
再看看好人山主,正跟人談笑風生呢,估摸著這樁送上門來的生意是十拿九穩了!
又有一位劍修化虹而至,落在桌旁,崔東山看熱鬧不嫌事大,抽了抽鼻子,眼神幽怨道:“米首席,這位吳老祖方才罵我們小米粒腦袋不靈光呢。”
米裕原本還面帶微笑,聞言瞬間臉色陰沉,盯著那個滿臉呆滯的……吳老祖:“哦?那就是元嬰的境界、飛升的膽子。聊完事就給自個兒找塊地去,挖個坑。”
周米粒瞧見了米裕,悄悄抬起手勾了勾:余米余米,來這兒來這兒,好人山主在跟人談買賣呢,咱倆不是這塊料,都不摻和。
於是米裕的臉色又變了,眼神溫柔地走向屋門口,其間轉頭看了眼張直和吳瘦,張直還好,依舊神色自若,吳瘦只覺得如墜冰窖。
張直喝完碗中茶水,轉過身,笑著提起手中白碗,周米粒趕忙拎著火盆上邊的爐子飛奔到桌旁,接過茶碗,倒了七八分滿,再遞還給那位張先生,張直就又與小姑娘道了一聲謝,笑道:“下次煮茶待客,取水需有講究,我是無所謂,風餐露宿慣了,只要能解渴就是好茶,但是好些山上仙師嘴刁,一喝就能嘗出滋味高低,哪怕表面不說,心里卻要犯嘀咕,只是將就而已。以後煮茶之水不如從山中清泉汲取,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三座舊山岳中都有不錯的水源。”
喝茶有這講究?真是這樣嗎?周米粒看了眼好人山主,見陳平安點點頭,她立即綻放笑容,與張先生道謝:“受教!”
張直喝了一口茶,笑道:“落魄山果然不一樣。”他雙手捧住茶碗,“正式介紹一下,我叫張直,洛陽木客出身,壞了祠堂祖訓,就被譜牒除名了,在山下做點小本買賣,積少成多的路數,比不得范先生的深謀遠慮和劉財神的家大業大。”
“旁邊這位,吳瘦,道號靈角,曾是寶瓶洲包袱齋分部的負責人。吳瘦只盯著算盤和賬本,從不抬頭看長遠大勢,唯一的功勞就是誤打誤撞,為牛角渡留下了那些建築,如今歸屬落魄山,實屬萬幸。這麼些年,與各洲包袱齋同行碰頭,唯獨此事可以讓吳瘦挺直腰杆說話,吹幾句不打草稿的牛皮。”
吳瘦滿臉苦澀。主人極少這麼與人言語的,何況先前還專門告誡自己不許提及牛角渡一事。
不過張直最後幾句倒也不算什麼虛情假意的場面話,吳瘦確實經常與同行炫耀此事,只是稍微更改了事實,說自己與那位年輕隱官當年是怎麼相識的,如何相逢投緣,稱兄道弟。
那會兒的陳平安還只是個窯工,但他吳瘦何等眼光,一瞧就看出對方不簡單,酒桌上撂下一句“我覺君非池中物”,陳平安那會兒都不信呢,只是與自己敬酒,干了一大碗……說得多了,說到最後,吳瘦自己都快信了。
不要覺得這種低劣手段如何滑稽可笑,生意場上,還真就有可能換來真金白銀。
陳平安說道:“桐葉洲這邊,我管不著。”
張直明顯松了口氣。
吳瘦低下頭,擦了擦額頭汗水。至於是不是做樣子給人看,啞巴吃黃連,有苦自知。
張直也是直爽人,直接問道:“敢問陳先生,除了你們青萍劍宗,在這桐葉洲地界,能說上話的勢力有幾個?”
崔東山晃著白碗:“消息這麼靈通,是玉圭宗還是大泉王朝戶部走漏了風聲?”
陳平安喝完茶水,笑道:“如今管事的是崔東山,你們聊你們的。”
他起身告辭,走向屋門口,摸了摸周米粒的腦袋,笑道:“不用繼續幫忙添水了。”
米裕雙臂環胸,背靠牆壁,始終盯著吳瘦。
陳平安沒好氣道:“干嗎呢,眼神能殺人,我怎麼不曉得劍仙這麼牛氣?”
米裕笑容尷尬。
進了屋子,陳平安與裘瀆、胡楚菱笑著打過招呼,坐在屋內一個火盆邊,伸手烤火取暖,猶豫了一下,說道:“小米粒,剛才有人覺得……嗯,反正說了些不是什麼好話的混賬話,湊巧被我聽著了。”
周米粒挪了挪小板凳,靠近好人山主,伸手擋在嘴邊,壓低嗓音說道:“不是那個張先生,對吧?”
陳平安笑著點頭:“是那個叫吳瘦的胖子。張先生還是很喜歡你的。”
周米粒一下子眉眼飛揚起來:“哈哈,猜中了,我就知道不會是張先生!”
黑衣小姑娘搖頭晃腦,肩膀一起一落的,還蠻開心,好像不管吳瘦說了啥,已經被她忽略不計了。
她光顧著開心了,就像她經常一個人在落魄山崖畔看風景,不開心的事兒就隨雲飄走吧,開心的,如鳥雀停枝頭,留下做客吧。
陳平安就要忍不住站起身,這下子反而輪到米裕慌了,咳嗽一聲:“隱官大人,實在不行,還是我出手吧。”
周米粒伸手輕輕拽住好人山主的袖子,搖搖頭,咧嘴一笑,好像在說,在自己家里呢,怎麼可能不開心呢?
小姑娘撓撓臉,又開始與好人山主竊竊私語,說自己與裴錢也會在背地里說岑姐姐是憨憨嘞。
陳平安笑著揉了揉小米粒的腦袋:“右護法說了啥,我怎麼沒聽清楚?不知道,記不住。”
周米粒:“哈!”
陳平安:“哈哈。”
周米粒:“哈哈哈!”
陳平安:“你贏了。”
米裕看著隱官大人,唏噓不已。也就是隱官大人不拈花惹草,不然自己加上周首席都不是對手吧?
陳平安轉頭怒罵道:“滾你的蛋。”
米裕愣了愣。奇了怪哉,隱官大人怎麼聽到自己的心聲了?
落魄山一張飯桌旁坐著朱斂、陳暖樹、謝狗。
謝狗感嘆道:“朱老先生,我還以為以隱官大人的能耐,你們落魄山得有大幾千號人馬呢。”
劍修幾十上百個,練氣士來個數百號,純粹武夫幾千人,再加上些外門弟子、雜役、奴婢啥的,年輕隱官一聲令下,指哪打哪,有事沒事就去大驪京城耀武揚威,逛蕩一圈。
實在沒想到,落魄山上就這麼點人。
小陌也真是的,半點氣力都不肯出,估計還是懶。
他們這撥老不死的,她跟小陌,加上那個名字都沒想好的無名氏都是不差的,不過都是獨來獨往。
至於那個滿身寶貝的離垢,還有那個大胸婆姨,也都是不喜歡熱鬧的。
但是其余比如王尤物幾個,都是肯定會重新開宗立派的。
呵,小樣兒,殺力不夠法寶湊,本事不高嘍囉多。
朱斂笑道:“其實還有一座蓮藕福地,加上那邊,人就多了。”
謝狗毫不掩飾自己的嗤之以鼻,夾了一大筷子菜放入嘴中,含糊不清道:“那也能算人?加在一塊兒能頂個玉璞境使喚嗎?”
陳暖樹聞言,只是默默低頭嚼著米飯。
朱斂笑容如常:“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雖說各有各命,不管怎麼說都是命。”
謝狗哦了一聲,只是下筷如飛,心不在焉敷衍一句:“有理有理。”
之後陳暖樹便收拾碗筷,去了灶房。
朱斂笑著提醒道:“謝姑娘,以後就不要隨便試探人心了。我們落魄山雖說規矩不多,但是為數不多的幾條,不管是誰,都得稍稍在意幾分。謝姑娘初來乍到,所以我得把這個理兒說清楚。”
謝狗打了個飽嗝,咧嘴笑道:“曉得了,入鄉隨俗,客隨主便,道理我懂!”她站起身走出屋子,“散步散步,飯後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呸,是活到九萬九!”
朱斂搖搖頭,不再說什麼。不懂裝懂不可怕,就怕懂了卻假裝自己是在不懂裝懂。
歸根結底,這個只是來找小陌的白景還是不覺得這座落魄山當真嚇人,所以除了小陌,沒有什麼是值得她真正上心的,哪怕是仙尉,在白景眼中,可能只能算半個人?
謝狗走出宅子後,扯了扯嘴角。可惜了,朱老先生學問再大,到底是讀書人,規矩多了點。
之後謝狗就開始閒逛落魄山諸峰,比如會去竹樓,趁著陳暖樹打掃一樓屋子的工夫,若無其事地跨過門檻,走進去看幾眼。
陳暖樹見狀只是停下了手上的活計,等到謝狗離開屋子也沒說什麼。
謝狗又去了後山,坐在屋頂上看著倆年輕男女練拳。
兩人察覺到屋頂上的不速之客,立即停下走樁,滿臉疑惑地望來。
謝狗只是伸出手,示意他們繼續練,當自己不存在就是了。
謝狗就這麼晃悠了幾天,這天暮色里來到了山下,正巧碰上看門的仙尉。
仙尉一般看門到戌時就准時拎著竹椅回大風兄弟的宅子去,不怠工,但也絕不多待,反正如今落魄山也沒啥外來客人。
一寸光陰一寸金,多讀一本書,哪怕是多翻幾頁,都是增長一分學問哪。
仙尉見那頭戴貂帽的少女不太開心的樣子,便雙手插袖站在原地,打算跟這個小姑娘隨便聊幾句,再回宅子繼續看書。
等她臨近山門口了,就笑著打了一聲招呼:“這是學岑姑娘練拳呢?”
謝狗揉了揉貂帽,搖搖頭:“學啥拳,不曉得咋回事,可能是哪句話不小心說錯了,這不就惹惱了朱老先生,算是把我趕下山了,發配到騎龍巷的一個店鋪當差。”
仙尉大為驚訝:朱老管家那麼好的脾氣,謝姑娘你是造了多大的孽、作了多大的妖,才能讓朱先生都覺得不順氣?
他猶豫了一下,還是忍不住說道:“謝姑娘,我們山上一向是言語無忌諱的,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幫你復盤復盤,找到了紕漏所在,大不了我陪你一起上山去與老廚子道個歉認個錯,就可以繼續留在山上了。”
謝狗直愣愣看著這個身穿棉布道袍的假道士:這廝除了頭頂那根木簪,真是怎麼看都不是那個道士啊。
這要是被那個神出鬼沒的王尤物找著了,小陌又不在山上的話,還不得落個嘎嘣脆的下場?
仙尉笑道:“謝姑娘,認個錯有多難,千萬別覺得丟面兒,不至於。”
謝狗眨了眨眼睛:莫不是個傻子吧?
自己跟小陌在內,他們這一小撮差不多道齡、輩分的,撇開殺力和防御各前三,其余那幾個老廢物……其實按照一般修士的計算法子,也沒有那麼廢,算是各有擅長吧。
比如道號山君的王尤物,術法最雜,保命逃命、潛藏偷襲都是一把好手,之所以背了把劍,是因為王尤物還是個半吊子的劍修,雖說極不純粹,兩把被大煉的飛劍都是半路強搶來的,但劍術勉強還算是劍術。
此外,王尤物的道號不是白取的。
所謂山君,可不是說那個老東西在山中就可以學那三教一家的聖人坐鎮天地,而是與山下的人和有關。
再說得簡單點,就是只要世道不好,山下活不下去的人越多,王尤物的道行就越高。
書上說了,苛政猛於虎嘛。
所以王尤物比起其余醒來的幾個是有先天優勢的,先前去見白澤,老東西故意繃著臉,一路上偷著樂呢。
王尤物如果早點清醒過來,又能早早潛藏在浩然天下,精心挑選一處隱蔽道場,比如那個曾經戰亂不斷的扶搖洲,一個不小心,真有希望被那廝躋身十四境,只因為那廝的合道契機就在道號寓意中。
但是謝狗一直覺得這個啥都肯學又啥都不是的老東西根本配不上“山君”這個本身極好的道號。
官乙也差不多,如果早點跟隨蠻荒甲子帳趕赴浩然天下,每一個廝殺慘烈的戰場都由她來收拾殘局,再一路吃過去,可能要比那個白瑩更有用處。
歸根結底,都怨白澤老爺遇到大事就喜歡犯糊塗唄,太遲返回蠻荒,太晚喊醒他們幾個。
那個如今化名胡塗的家伙估摸著就是在故意惡心白澤吧。也難怪,當時白澤瞧見他們幾個後,視线好像在胡塗身上逗留最久。
傻了吧唧跟白澤老爺抖機靈,找死不是?虧得如今蠻荒天下缺少頂尖戰力,不然就要嗝屁嘍。
當年那位小夫子是出了名的講道理和好脾氣,白澤也差不多,好說話。
可問題在於,這兩位不講理和不好說話的時候有多可怕,她都是親眼見識過的。
謝狗哈哈笑道:“知錯能改,善莫大焉。粗淺道理,怎麼不懂?”
仙尉賠著笑,心中忍不住腹誹一句:怎麼瞅著這個小姑娘不像是個實誠人哪,懂個錘子。
謝狗沿著山路往小鎮走去,仙尉拎著竹椅去往宅子,打算將大風兄弟的旁白批注單獨匯集成冊,以後自己的職務高升了,再不當這風吹日曬勞苦功高的看門人,總得給下任留點寶貝。
從鄭大風起,到自己,再往後,代代相傳,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也是一樁美談。
開春時節,雨過群山,青翠如滴。
清晨時分,仙尉縮著身子,正坐在竹椅上打瞌睡,迷迷糊糊的,好像聽到有人在喊仙尉道長。
好不容易撐開眼皮子,仙尉瞧見了一張熟悉面孔,黃帽青鞋,原來是小陌先生回了。
仙尉趕緊坐直身體,伸手輕輕拍了拍臉頰,難為情道:“熬夜看書,容易犯困。”
小陌微笑道:“眼下正是春困的時候,辛苦仙尉道長了,趕明兒起,我來看門幾天,仙尉道長只管養好精神……”
仙尉連忙擺手:“不成不成,怎敢讓小陌先生看大門,成何體統,小陌先生的好意我心領了,保證看門看書兩不誤。”
小陌坐在一旁的竹椅上,長呼出一口氣。
仙尉問道:“小陌先生,陳山主沒有一起回來?”
小陌擠出一個笑臉,道:“公子在桐葉洲還有點事,稍晚些返回。”
仙尉有些奇怪,試探性問道:“是有心事?”
小陌想了想,說道:“得去見個人,不太想見,又躲不開,就有些犯愁。”
這個對他糾纏不休的白景,大概能算是小陌的唯一苦手了。
仙尉點點頭。人人各有煩心事,很正常,他不覺得自己能夠開解什麼,雙手搭在膝蓋上輕輕拍打,沉默許久,哼起一支老家的鄉謠:
“山一程,水一程,風一更,雪一更。近路愁,遠道愁,南一聲,北一聲。”
“思悠悠,恨悠悠,江水流,河水流。夢難成,意難平,東山青,西山青。”
壓歲鋪子多出個店伙計,代掌櫃石柔當然不會有意見,就是添一副碗筷的小事。
周俊臣就不太樂意了,不用想,又來個混子。
結果才一天相處下來,那個名字古怪的少女就讓周俊臣刮目相看,滿是好感。
謝狗對待掙錢一事,竟是比周俊臣更上心,先與石柔借閱了歷年積攢下來的賬簿,算出每日入賬的銀兩數目,然後開門見山說以後鋪子得跟她明算賬,超出這筆錢的五成收入歸她。
石柔無所謂,周俊臣覺得這筆買賣怎麼都不虧,就算通過了這項決議。
然後謝狗就堵門去了,但凡是去隔壁草頭鋪子的客人都要被她軟磨硬泡拉到壓歲鋪子來瞧瞧,周俊臣看她的架勢,恨不得要去槐黃縣城滿大街牆壁上張貼告示。
謝狗還與兩人合計,說牛角渡那邊可以立一塊招牌,就當是給壓歲鋪子的糕點招徠點客人,反正牛角渡也屬於自家山頭。
木牌上邊除了寫明壓歲鋪子的具體地址,還要寫哪幾種糕點被某某劍仙、某某宗主、某國皇帝陛下嘗過了,贊不絕口之類,比如阮邛、劉羨陽、祁真、宋睦、楊花……總之寶瓶洲誰名氣大誰就登榜。
管他們有沒有吃過呢,大不了被誰罵上門來,就與他道個歉,再換一塊牌子唄——其實都不用換,抹掉個名字就行……
這般生意經,聽得石柔目瞪口呆,周俊臣倒是眼前一亮,要不是石柔攔著,小啞巴已經去後院找木板和准備筆墨了。
周俊臣見過掙錢凶的,但沒見過為了掙錢這麼不要臉的。
謝狗自有理由:人總不能為了面子,連錢都不掙了。
周俊臣一下子就覺得踏實了,在外人面前難得有個笑臉。
謝狗問他:“周俊臣,你既然是陳山主如今唯一一個徒孫輩的,結果一年到頭只能苦哈哈在這兒掙點碎銀子,混得也太慘了點,不覺得委屈啊?”
在蠻荒天下,開山老祖的親傳、嫡系徒孫,在自家或是外邊,不弄出點麼蛾子,都沒臉在山上混。
周俊臣咧咧嘴:“我跟陳平安又不熟,這麼些年就沒見過幾次面,攏共沒聊幾句天,什麼祖師徒孫的,反正我跟他,誰都不當真。”
謝狗點點頭:“有志氣。”
她突然抹了把嘴,嘿嘿笑起來,讓周俊臣覺得怪瘮人的。
謝狗走出櫃台,扶了扶貂帽,從門口探出頭,望向那個走進騎龍巷的家伙,黃帽青鞋綠竹杖,嘿,俊俏!
小陌沒有停步,眯眼以心聲道:“你來浩然天下做什麼?”
謝狗皺著臉。慘啊,造孽啊,小陌這種說辭,跟書上那種背棄花前月下山盟海誓的負心漢有啥兩樣嘛。
小陌緩緩前行:“別裝了,有意思嗎?”
謝狗哦了一聲,伸了個懶腰,蹦出門檻,站在騎龍巷街道中間,徑直說道:“給陳平安當死士,是那個存在的意思?”
小陌點點頭。
謝狗怒道:“那你知不知道,如果陳平安在城頭刻的不是‘萍’字,而是‘平’或者‘清’字,你的下場是什麼?”
小陌還是點頭。那位持劍者找到自己的時候,就明白無誤說過此事。
與其問劍?小陌既不敢也不願意,畢竟自己一身劍術,絕大部分都傳自這位遠古至高存在之一。
逃?逃不掉的。
謝狗搖搖頭:“都不是我認識的你了。”
小陌冷笑道:“我們本就不熟。”
之前的白景,真正的她,並非如今這般少女姿容,而是極美艷的,充滿野性。
謝狗笑呵呵問道:“找個地方,喝點小酒?”
沉睡萬年,一覺醒來,她發現如今天下頂尖修士的戰力好像變化不大,唯獨釀酒技藝高了不少。
小陌搖頭道:“喝酒誤事。走走這條騎龍巷台階,走到頂部,談攏了是最好,談不攏,你我去海外。”
練氣士飲酒可以與常人無異,想要喝個痛快自有手段,至於大醉過後想要睡多久,沒個准,就看練氣士的個人喜好了,反正能夠早早敲定醒來的時辰,大修士還能夠憑此養神,醉個幾年幾十年不算什麼稀罕事。
謝狗撇撇嘴,說道:“陳平安又不在,能誤啥事。”
小陌面無表情。
謝狗一跺腳,撒潑一般,雙手亂晃:“不就是沒喊一聲陳公子嗎,你為了個外人就跟我起殺心?”
喊公子?喊個大爺的公子。自己來了落魄山這麼久也沒能瞧見對方一面,架子忒大,當自己是白澤還是小夫子啊?
謝狗直截了當說道:“陳平安故意撇下你單獨見我,這種人,這種脾氣,我不喜歡。你跟著他混,我不放心。按照這邊的書上說法,這就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嘛。果然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在劍氣長城還敢拋頭露面賺點戰功,掙點名聲,說到底,還是放心背後城頭上有陳清都坐鎮唄,篤定會護他性命。你瞧瞧,到了這兒就露餡了,還不是怕我殺他,擔心你護不住他。”
小陌說道:“公子是臨時要去見一個人,很重要,一個白景,根本不能比。”
謝狗疑惑道:“誰?桐葉洲有這麼一號人物?”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桐葉洲的頂尖戰力是要遠遠遜色於俱蘆洲和婆娑洲的。
兩人一起拾級而上,小陌說道:“與你無關。”
謝狗說道:“真不喝酒?”
小陌猶豫了一下:“就在草頭鋪子喝便是了,賈老神仙那兒有酒,回頭我再與他打聲招呼借幾壺來,賈老神仙不會計較的,都不用我事後補上。”
謝狗翻了個白眼。
氣死老娘了,喝個酒還有這麼多道道,看把你得意的,這就算混出名堂了?
當年那個獨自仗劍橫行天下的小陌呢?
那個與落寶灘碧霄洞主一起釀酒的小陌呢?
那個曾經差點做掉仰止的劍修呢?!
謝狗皺了皺鼻子,好像在說:小陌小陌,你變成這樣,我可傷心了。
小陌對此視而不見,徑直轉身走向草頭鋪子。
謝狗冷不丁一個餓虎撲羊,結果被小陌按住腦袋:“白景!”
刹那之間,小陌和謝狗道心震顫,幾乎同時轉頭望向騎龍巷最高處。
有人坐在那兒,身邊站著一個身材高大的白衣女子,雙手拄劍,似笑非笑,俯瞰著他們。
而那個眼神溫柔的男子微笑道:“你們先忙,當我們不存在就是了。”
騎龍巷霎時間變成了一座飛升台,頂部依舊是女子拄劍,旁邊男子坐在台階上,雙方皆有一雙精粹至極的金色眼眸。
謝狗的整副身軀皮囊瞬間如灰塵飄散,繼而凝聚為一個姿容嶄新的修長女子。
這才是白景的真身真容,白景雙手持劍,高高揚起頭顱,與頂部那兩位對視。
小陌說道:“勸你最好收劍。”
白景眯眼笑道:“機會難得,剛好舒展舒展手腳筋骨。我還真就不信了,他們真能把我一口氣拖拽到萬年之前的光陰長河中去。如果本事這麼大,就不會有今天了!”
將一位萬年之後的飛升境圓滿劍修從變成由三教祖師坐鎮的天地拽回萬年之前的舊山河,十五境都做不到!
台階頂部,單手托腮的男子滿臉笑意,輕聲道:“我們小陌還是向著白景的,看來有戲。”
白衣女子點頭道:“患難見真情嘛。”
小陌雖然聽不見頂部那兩位存在的言語,不過看著那個既面容熟悉又氣息陌生的自家公子,總覺得不像是說了什麼好話。
陳平安笑眯起眼,朝小陌輕輕揮手作別,微笑道:“小陌,悠著點啊,可別被生米煮成熟飯了。”
異象隨之消散,小陌和謝狗重新置身於騎龍巷中。
謝狗扶了扶頭上貂帽,嗤笑道:“假的假的,裝神弄鬼,嚇我一跳。”
小陌神色尷尬。清清白白的,怎麼有種被捉奸在床的錯覺?
謝狗埋怨道:“小陌,都怪你,那個存在是循著你的劍道脈絡找來的,就像在光陰長河的下游守株待兔,把咱們倆給抓了個正著。”
言語之間,謝狗抬手擦了擦額頭汗水,小陌看了一眼,謝狗立即解釋:“就算是假的,也很嚇唬人啊。天下就這麼點大,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沒必要把路走窄了。走,喝酒去,壓壓驚。”
到了草頭鋪子,小陌讓酒兒幫忙拿來兩壺糯米酒,笑著說不用去廚房炒菜了,他們有個地兒光喝酒就行。
謝狗盤腿坐在長凳上,喝了一大碗糯米酒釀,感嘆道:“掙點辛苦錢真不容易,小陌你是不知道,我來到浩然天下後,為了攢點錢,這一路走得有多辛苦,山上挖草藥山下擺攤子,差點被人調戲呢,混得可慘啦。”
小陌喝了口酒:“真正掙不著錢的人才有資格說辛苦。”
謝狗氣呼呼道:“這話說得真像個人。”
小陌放下酒碗,以心聲問道:“你敢不敢殺飛升境?”
謝狗眨了眨眼睛:“你睡傻了?”
有什麼不敢的?明明是能不能的事,這兒又不是蠻荒天下。
你就這麼想我被小夫子抓起來,在功德林陪劉叉一起吃牢飯啊?
也對,如此一來,見不著我,你就可以眼不見心不煩了。
負心漢說起混賬話來,真是比飛劍戳心窩還厲害。
謝狗抽了抽鼻子,擦了擦眼角,見桌對面的小陌無動於衷,也覺得沒啥意思,便換了一種臉色,懶洋洋道:“說吧,殺誰?”
小陌說道:“曳落河舊主,仰止。”
謝狗恍然道:“原來是她啊,逃命本事不差,打架本事不頂,很不頂,白瞎了那份道傳,看著就煩她。這婆姨要是沒有被文廟留在這兒,如今在蠻荒天下的話,呵。”
仰止的一門本命神通謝狗眼饞很多年了,天生就不適合仰止,可若是被謝狗學到手,掰碎了嚼爛了,剛好能夠補全謝狗的某份大道缺漏,一個不小心,真就躋身十四境了。
事實上,當初小陌追殺仰止,白景就一直遠遠跟著,悄無聲息,等到搬山老祖袁首出現後,她就跟著現身了。
敢打我男人,問過我白景沒有?
二打二才公平,他們這對神仙眷侶對付一雙姘頭還不是手到擒來,咋個會輸嘛。
可惜小陌不願與自己聯手,直接就走了。
“我跟白老爺和文廟可是有約定的。不過嘛……既然是你開口,我可以考慮考慮,前提是你得保證我能活著離開浩然天下。”謝狗伸出一只手掌朝小陌挑了挑眉頭,“好處呢?親兄弟明算賬,咱倆要是道侶也就不談這個了,問題是咱們還不是嘛。”她抹了把嘴,“我如今翻書茫茫多,書上不就都是這麼個路數?英雄救美,大恩大德無以為報,只好以身相許了。擱咱倆身上,一樣的道理!”
小陌正要說話,酒桌一邊,陳平安悄然落座,笑道:“小陌,千萬別答應以身相許啊。”
至於謝狗身後,則又有人伸手按住她的貂帽:“剛才不跟你計較,結果還是這麼皮?”
謝狗縮了縮脖子,眼神幽怨:“小陌小陌,趕緊幫我說句公道話,我膽子小,怕慘了。”
修道之人,神游萬里算個錘子,這倆莫不是神游萬年而至?
仙都山,青衫渡。
崔東山掰手指開始計數,將幾個盟友名號一一報出:“大泉姚氏、蒲山雲草堂、太平山、玉圭宗、皚皚洲劉氏、中土玄密王朝郁氏,六個。暫時就這麼點,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各司其職,分工明確,相親相愛,同舟共濟。”
張直點點頭:“是個很好的搭配。”
一般的飛升境修士都攏不起這麼個大好局勢,這就是劍氣長城末代隱官的潛在底蘊了。
吳瘦眼皮微顫,尤其是聽到有皚皚洲劉氏就想要打退堂鼓了。
如今他算是包袱齋桐葉洲分部的三把手,連二把手都沒能撈著,屬於降職任用,以觀後效,要是再做不出點成績,可是要被祖師堂秋後算賬的。
倒不是說皚皚洲劉氏賺錢心狠心黑,而是劉氏一向喜歡完全主導一樁買賣,外人只能從旁輔助,無法插手關鍵財脈的運轉。
包袱齋內,很多買賣光動嘴皮子吹得天花亂墜是沒用的,按照祖師堂規矩,誰要是看中了某樁生意,半數錢得自掏腰包。
虧了,砸鍋賣鐵也好,與人借錢也罷,都得乖乖把錢補上;錢不夠,立下字據,寫張欠條,反正都得優先補上包袱齋的窟窿,絕不是拿了錢就可以大手大腳開銷或是中飽私囊的。
而且祖師堂會專門派出賬房先生,身份有點類似戰場監軍,想要繞過此人在賬目上動手腳,比登天還難。
吳瘦就有個師叔,足足七百年都在為包袱齋還債。
遙想當年師叔最風光時,流霞洲天隅洞天都曾與師叔借過一大筆錢,光是每年吃利息就能躺著享福了,富可敵國算什麼,可以說是富可敵洲。
結果就是心太肥,攪和進了一樁上下宗的內部事務中去,大傷元氣,偷雞不成蝕把米。
崔東山瞥了眼吳瘦微妙的神色變化。
精於賺錢,也只知道賺錢,看來是好了傷疤忘了疼。
莫非張直這是趕來青衫渡釣魚,以吳瘦作餌?
就像大魚難釣易脫鈎,但是對張直這種老狐狸來說,一次提竿大魚出水就可以大致推斷出自家先生的心性,畢竟張直肯定沒那膽子覺得自己可以真的一鼓作氣釣起隱官陳平安,和落魄山、青萍劍宗兩座新興宗門。
簡而言之,張直就是奔著故意讓大魚脫鈎來的,只為整個包袱齋作長遠計。
崔東山比較煩這個,就懶得七彎八拐,以心聲直接問道:“張直,你這麼精明的人,為何要故意帶著個吳瘦來這邊自討沒趣?”
張直笑道:“還是不如崔宗主和你家先生精明。”
“此話怎講?小心點說話,你可別步吳老祖的後塵。”
“崔宗主何必明知故問。”
“張直啊張直,我裝傻自有裝傻的本事和底氣,可你跟我裝傻就是真傻了。奉勸一句,我如今是青萍劍宗的宗主,也可以跟著先生依葫蘆畫瓢下出第二道逐客令,你們包袱齋在桐葉洲南邊的買賣我管不著,那邊是玉圭宗的地盤,我跟現任宗主韋瀅半點不熟,跟上任姜老宗主也不算太熟,但是北邊的買賣,即日起,就別想順遂了。”
當初寶瓶洲的包袱齋是被繡虎崔瀺驅逐出境的,下場跟劉桃枝的西山劍隱類似,都屬於不歡而散,就此結下了梁子。
崔瀺絕對不允許有任何外來勢力在那場即將到來的戰事中出現半點分歧,扯後腿,各行其是。
這是因為戰事未起,包袱齋就嗅到了危機。
不過浩然九洲的包袱齋分部,只有吳瘦的寶瓶洲表現得過於市儈了。
陳平安根本不用去理會其中的彎彎繞繞,所以先前陳平安在桌上所謂的逐客令,就已經把話說得很明白。
如今浩然天下和蠻荒天下的這場大戰才打了一半,別想著把便宜占盡,既然有本事避害,就別再想著趨利了,至少寶瓶洲就別想了。
而張直故意帶著吳瘦登門拜訪,何嘗不是一種試探?
對於這個年輕隱官,張直有三件事需要驗證:第一,他會不會擔任大驪國師,繼承文脈師兄繡虎崔瀺的衣缽;第二,青萍劍宗在這桐葉洲有無擔任一洲仙府執牛耳者的野心;第三,陳平安的心性與繡虎有多相似,又有多少差異,他張直和包袱齋才好看菜下碟。
包袱齋在這邊到底投入多少本錢,得先看過三個答案才能有個粗略的定論,因為包袱齋真正在意的兩座渡口已經不在那個南方諸國恢復極快的寶瓶洲,而在桐葉洲和扶搖洲。
天下九洲有仙家渡口處,或明或暗,幾乎都有包袱齋的買賣。
崔東山突然笑道:“吳瘦的包袱齋當年在寶瓶洲沒有做什麼見不得光的事情吧?”
張直淡然道:“要是有,哪里需要米劍仙提醒吳瘦自己找個地方,我早就幫他挑好了。包袱齋是我一手創建起來的,我是勞碌命,事無巨細都喜歡親自盯著,所以包袱齋始終就是個一言堂。舉個例子,我要是中土大龍湫的宗主,處置小龍湫那幾個吃里爬外的孽障,根本無須通過祖師堂議事,一言決之,只需派出龍髯仙君到小龍湫就地處決。做買賣的人有自己的生財之道,自古而然,只是生意人歸根結底還是做人,還是要講一講底线的。買賣想長久,跟著大勢走,可要是虧心事做多了,人不收天收。”
聽到這里,崔東山點點頭:“這才算明白人說了些敞亮話嘛。”
張直說道:“當年趕走了包袱齋,崔國師立即為寶瓶洲引入了范先生和商家,就像為後者清場。吃了這個悶虧,我們包袱齋認栽,咎由自取,沒什麼怨言。”
“那就照陳先生說的,關於寶瓶洲重新開張一事,何時天下太平了,包袱齋和落魄山再來好好商議。至於桐葉洲這邊,包袱齋誠意如何,底色又如何,我覺得可以用開鑿大瀆的合作一事作為開端。崔宗主意下如何?”
吳瘦知道自家祖師與白衣少年在以心聲交流,他是悔青了腸子。早知道就跟那個小姑娘討要一碗熱茶了,也好過現在干坐著。
不知為何,那位年輕隱官又走出了屋子,身邊還跟著那個拎著爐子的黑衣小姑娘。
現在吳瘦再瞧見這個洞府境的小水怪,堂堂元嬰境,但凡在座諸位不覺得砢磣,他都恨不得跪地磕頭高呼姑奶奶了。
周米粒又給所有人添了茶水,輪到吳瘦時,吳瘦趕忙低頭與小姑娘連連道謝,差點熱淚盈眶。
崔東山笑道:“上個胖子同樣走了遭仙都山,還不如你幸運呢。”
陳平安坐在長凳上,周米粒就坐在一旁。
陳平安從袖中摸出一把合攏起來的玉竹折扇,輕輕放在桌上,笑道:“方才在屋內才記起之前在鴛鴦渚仔細逛過張先生親自開設的包袱齋,齋名和氣。開門做買賣,果然是和氣生財,我跟幾個朋友大開眼界,好像還欠了張先生一個人情,兩張字據。天下事,一碼歸一碼,買賣不成仁義在。”
原來之前在和氣齋內,陳平安一眼相中了這把珍貴折扇,只是當時身上沒帶多少神仙錢,囊中羞澀,不承想齋內很快就有一位符籙美人姍姍而至,主動提出可以讓陳平安先行帶走扇子,以後在任意一處渡口包袱齋補上錢就是了,事後包袱齋肯定會自行銷毀欠條字據。
之後李槐瞧上了那塊好似盆景的仙山,一位老柳樹精就棲息其中,包袱齋開價十枚谷雨錢,陳平安就又代替李槐訂立了一張字據。
崔東山伸手拿過折扇,啪一聲打開,扇面節錄蘇子《祈雨帖》,另外一面是謫仙山柳洲草書《龍蟄詩》。
扇子本身完全可以視為一件水法重寶了,法寶品秩跑不掉的,資質好一點的劍修,運道好,揀選一個雷電交加大雨滂沱的時日,沐浴更衣之後,打開扇子,一邊看草書一邊看天候,機緣巧合之下,說不定還能學點昔年劍仙柳洲的些許劍意仙氣。
崔東山疑惑道:“先生,當時包袱齋開在鸚鵡洲,好像不在鴛鴦渚。”
陳平安恍然道:“這樣嗎?那就是我記岔了。”
吳瘦都快崩潰了:隱官大人你說話這麼有誠意的嗎?
張直從袖中摸出兩張字據,落款人都是落魄山陳平安,其中一張欠條是折扇的五十枚谷雨錢,另外一張是仙山盆景的十枚谷雨錢。
崔東山掃了一眼,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快拿出六十枚谷雨錢,打算為先生分憂,把債務還清了,取回欠條。
別銷毀啊,得保留下來,以後可以給嫩道人瞅瞅。
十枚谷雨錢?
傻了吧,那位老柳樹精可是與純陽真人呂喦論過道的,拳頭大小的山石上邊,“仙山”二字可是呂喦以劍氣書寫,這等崖刻,可是真跡!
但是張直卻以手指按住兩張欠條,笑道:“陳先生今天給出六十枚谷雨錢就算結清債務了,按照規矩,這兩張欠條需要立即銷毀。但是我想要跟陳先生打個商量,我們包袱齋能不能花七十枚谷雨錢,相當於與陳先生買下這兩張借據?”
周米粒呆住了:好人山主的字,不過兩句“落魄山陳平安”就賺了十枚谷雨錢,這麼值錢的嗎?!
陳平安笑著搖頭:“太不合規矩了,還是錢貨兩訖比較清爽。”
張直笑道:“並不是專門為陳先生破例,這種事,包袱齋歷史上不乏前例。”
崔東山冷笑道:“七十枚谷雨錢,打發叫花子呢?七百枚!”
周米粒又震驚了:大白鵝,不對,可愛可敬的大師兄跟人做買賣,一向喜歡這麼獅子大開口嗎?不怕被人打啊?
不承想那個張先生立即從袖中摸出只大袋子放在桌上,迅速將兩張欠條收回袖中:“那就一言為定,就此錢貨兩訖!”
“落魄山陳平安”的真跡以後只會越來越值錢,當然很難值錢到十二個字就需要用七百枚谷雨錢去買的份上,那也太夸張了,幾十枚谷雨錢是比較恰當、穩妥的價格,以後和氣齋碰到千金難買心頭好的山上土財主,不愁賣。
但這可是兩張欠條,意義非凡,尤其還是陳平安參加中土文廟議事之前訂立的字據,這就等於多出個意義深遠、極有嚼頭的歷史掌故了,如此一來,七百枚,真心不貴。
吳瘦看到這一幕後,心中佩服不已:不愧是自家包袱齋的老祖師,做買賣足夠果決,出手夠快夠狠。
崔東山小心翼翼地去拽那一大袋子谷雨錢。
虧得不是官場,不然這算不算是某種雅賄?
唉,運氣來了擋都擋不住,天上又掉了七百枚谷雨錢下來,自家賬房先生種秋得多高興啊。
陳平安面帶微笑地看著做賊似的崔東山,崔東山只得中途更換路线,將錢袋子推到周米粒跟前,語重心長道:“右護法,此錢歸公,記得好好保管啊,回頭交給風鳶渡船上的韋賬房,不許貪墨啊。”
周米粒雙手抱住錢袋子。嘿,真沉!小姑娘挺直腰杆:“得令!”
她突然皺了皺眉頭,偷偷看了眼出手闊綽的張先生,撓撓臉,還是沒說什麼。
她如今可窮了,私房錢零零碎碎攢一起也湊不出一枚谷雨錢,這要是出了紕漏,錢袋里少了一枚谷雨錢,豈不是把自己賣了也還不上債務啊?
張直微笑道:“剛好七百枚,不多不少,小仙師只管放心。”
被看穿心思的周米粒笑容靦腆:張大仙師真是善解人意的好人呢。
陳平安摸了摸周米粒的腦袋,朝張直笑了笑。
張直笑問:“陳先生、崔宗主,能不能冒昧問一句,桐葉洲開鑿這條大瀆,第一筆神仙錢,大致數目是多少?”
崔東山嘖嘖道:“還真不是一般的冒昧。”
都是老狐狸。
要是被張直知道了這筆谷雨錢的數量,未來那條大瀆的規模其實就可以大致估算出來了,一個不小心,以包袱齋的精打細算,甚至可以完全繞開青萍劍宗這些勢力早早布局,仔細研究桐葉洲中部堪輿畫卷和各國山水形勢圖,再以兩個方向各自入海的大泉埋河和沛江作為推演起始,就有一定把握演算出一條大瀆水道走勢,再暗中與那些早就窮瘋了的王朝皇帝、藩屬君主低價購買那些暫時看來完全不值錢的山頭、地盤,迅速交割地契,就可以等著大瀆找上門去了,財源滾滾,旱澇保收。
所以陳平安直截了當搖頭道:“恕不奉告。”
張直說道:“包袱齋確實希望通過大瀆開鑿一事既求利也求名,並且求名更多,可以少掙錢,甚至是完全不掙錢。我們不會也不宜繞開青萍劍宗另起爐灶,同樣的錯誤再犯一次,得不償失。”
崔東山雙臂環胸:“你們包袱齋在浩然天下的名聲確實真就一般,很一般了,比起皚皚洲劉氏差了何止十萬八千里,比起范先生的商家同樣差了幾十條街。試想一下,千百年後,包袱齋子弟每逢路過桐葉洲,別管是奔波勞碌掙錢還是閒逛山河的,只需看著奔流到海不復回的那條大瀆流水,無論是乘船渡水還是站在岸邊,或是在仙家渡船上俯瞰那條橫貫桐葉洲東西的蜿蜒水龍,都可以問心無愧地與朋友笑言幾句,學吳老祖這般吹吹牛皮,說這條大瀆有咱們包袱齋一份功勞!”
陳平安微笑道:“人過留名,雁過留聲。”
撇開一門心思只求證道長生不朽的,那麼劍術高的、拳頭硬的、有權勢的、兜里有錢的,總得給世道留下點什麼。
吳瘦嘆了口氣:你們倆擱這兒唱雙簧呢?
結果吳瘦就又看到那個眉心有痣的白衣少年直愣愣看著自己,瞬間身體緊繃,心中叫苦不疊,所幸有張直幫忙解圍,繼續先前的話題:“這種澤被蒼生功在千秋的事業,確實不可以單純追求賬面上的盈利。”
張直繼而笑道:“實不相瞞,之所以這次只帶吳瘦來碰壁,是因為掌管桐葉洲包袱齋的那對道侶話事人,再加上那個出身包袱齋祖師堂的賬房,三人都對隱官大人太過敬仰。他們跟只認錢的吳瘦不一樣,以致我都要擔心他們過來根本不會討價還價,見著了隱官大人,一個意氣用事,就太不把買賣當買賣了。”
陳平安一笑置之。這種生意場上的客氣話,聽過就算,不用當回事。
張直舊事重提:“那就算上我們一份?六千枚谷雨錢,桐葉洲包袱齋占一半,我再自掏腰包補上另外一半。”
崔東山問道:“誰求誰呢?”
張直笑道:“當然是我求你們。”
崔東山轉頭望向先生。大方向,當然還得先生拿主意。
陳平安點頭說道:“張先生可以提要求了。東山,在這之前,你給張先生說說大致情況。”
崔東山這才開始拿出些許誠意,與包袱齋說明了第一筆神仙錢的出資情況:“青萍劍宗給出三千枚谷雨錢,玉圭宗拿出五千枚,大泉姚氏會與青萍劍宗和玉圭宗分別借一千枚谷雨錢,皚皚洲劉氏和玄密王朝郁氏各自拿出一萬枚和兩千枚谷雨錢。這些錢很快就會陸續到賬,而這還只是第一階段的投入。”
“想要開鑿出一條嶄新大瀆,工程浩大,牽扯到方方面面,只說大瀆沿途各個恢復國祚或是另立正統的新舊朝廷借此機會以工代賑,救濟背井離鄉的災民,動輒需要動用數以百萬計的勞力,各國既能借機收拾舊山河,也能將各地難民聚攏在一起,有朝廷和各地官府集中管理,最少也能保證國境內不至於一遇到荒年就餓殍千里、白骨盈野。”
“此外,皚皚洲劉氏承諾會主動提供三百條不同規模的符舟幫忙運送百姓去往嶄新大瀆河床處,只是這些劉氏私人渡船的靈氣消耗、掌控符舟的仙師等一系列人手調度、渡船輾轉各地的神仙錢開銷,都由沿途各國自行負責。”
張直聽過之後,心里大致有數了,剛想開口說話,崔東山就已經加重語氣提醒道:“張直,你要知道,劉氏和郁氏出了這麼多錢,運作不當,虧了就虧了,就當是打了水漂,絕無怨言,可沒有任何欠條字據的。即便將來可以掙錢,大瀆一起,不管未來如何盈利,劉聚寶和郁泮水都早已承諾,白紙黑字,都是簽訂好契約的,兩家最多只掙本金的一成。賺到了這筆神仙錢,桐葉洲大瀆就等於跟他們沒有半枚神仙錢的關系了。”
至於具體的大瀆收益從何而來,想必是張直和包袱齋最感興趣的,只是對不住,得先見著了真金白銀才有資格知曉,不然就猜去。
張直說道:“在錢財上算賬,我們一樣可以學劉財神和郁泮水,虧了認栽,賺了最多收取本金的一成數額。此外,包袱齋額外的,也是唯一的要求,就是大瀆沿途所有仙家渡口,不論新舊,都建造包袱齋,各國朝廷不收地租,都算包袱齋花錢買下的,更清爽些,不用扯皮,空耗精力。除非當地王朝更疊,換了國姓,到時候再來另算歸屬,否則買賣就是一口價。至於渡口各個新建包袱齋的具體價格,我會讓吳瘦他們去談,也算給了各國朝廷一筆額外收益,不至於讓諸國君主和戶部衙門一談到錢就覺得捉襟見肘,容易拖延了大瀆開鑿工程的進展。”
崔東山氣笑不已:好家伙,這是明擺著搶地皮來了。
張直笑著解釋道:“仙家渡口有無包袱齋,人氣還是很不一樣的。”
吳瘦終於覺得有機會將功補過了,剛想要賣個人情,說可以率先在青衫渡掏錢,人力物力財力都由桐葉洲包袱齋出,包圓一座仙家渡口該有的各色建築……只是還沒張口,就見張直轉過頭來,雙指並攏,輕輕敲擊桌面:“吳瘦,老老實實喝你的茶。”
難得動怒的包袱齋老祖師真給氣到了。
要是有私心,青萍劍宗何必消耗那麼多的山上香火情作為大瀆開鑿的發起人,填補這個好像無底洞一般的窟窿?
你吳瘦要是開口給出心中那個建議,就等於昭告一洲山河:不,你們青萍劍宗其實是有私心的。
崔東山笑嘻嘻道:“張先生就不要苛求所有屬下都與你一般視野開闊,有個天大格局了,不然如今包袱齋早就將商家取而代之了,自立為祖,或是被范先生青眼有加,請去當個商家三祖。”
張直無奈笑道:“這種話可不能外傳。”
確實就如崔東山所說,一個門派里邊,行事風格,掙錢方法,不可能全如自己一人。
陳平安站起身,笑著抱拳告辭:“既然方向談妥,接下來就只是磨細節了,就讓東山跟張先生細說,該吵吵該罵罵,不用客氣,就都當好事多磨了。”
張直站起身,抱拳相送。
陳平安對吳瘦笑道:“今天咱倆才算真正認識了,以後就別與外人吹噓一起喝過酒了,反正一起喝過茶是真的。”
吳瘦小雞啄米,信誓旦旦保證道:“曉得曉得,隱官教誨,銘記在心。”
隨後,陳平安就帶著周米粒,還有米大劍仙一起離開青衫渡,徒步返回密雪峰。
周米粒問道:“好人山主,一起回家嗎?”
陳平安笑著點頭:“算是半路吧,等風鳶渡船到了老龍城,我再陪著宋前輩下船走上一段,然後就會獨自趕回落魄山,肯定比你早到家。”
周米粒點點頭:“這敢情好。”難得好人山主等自己返鄉,不是自己等好人山主回家哩。開心開心賊開心,比過年收紅包還開心。
米裕回頭瞥了眼吳瘦,問道:“隱官大人,真就這麼算了?”
陳平安揉了揉周米粒的腦袋:“要不要打他一頓出出氣?”
周米粒咧嘴笑道:“又不生氣,出啥氣?行走江湖要大氣!”
陳平安收起手,笑著點頭:“米大劍仙,聽見沒有?學著點。”
米裕就想要學隱官大人揉揉周米粒的腦袋,結果被小姑娘伸出手掌拖住手腕,著急道:“余米余米,干嗎呢干嗎呢,再摸腦袋可真就不長個兒啊!”
米裕猶豫了一下,以心聲問道:“隱官大人,你不是一直對那位包袱齋老祖師十分仰慕嗎?就不借此良機多聊幾句?”
陳平安笑道:“仰慕是真,不過就像張先生自己說的,跟仰慕的人合伙做買賣,很容易腦子一熱就失了分寸。再者,我看著那個心寬體胖的吳老祖就煩啊。”
桌子那邊,崔東山開始與張直訴苦。
原來,為了開鑿大瀆一事,臨時組建成一個類似祖師堂的存在,自家青萍劍宗這邊會派出種秋和米裕,不可謂不重視。
玉圭宗由王霽出面,大泉王朝派的是禮部尚書李錫齡,再加上一位專門為此事離開京城的戶部侍郎,也算一種機遇難得的官場鍍金了。
蒲山雲草堂的薛懷,還有太平山那邊,來的是護山供奉於負山。
皚皚洲劉氏和中土郁氏也都會各自派遣一人趕來桐葉洲,極有可能是那個居心不良被套麻袋的劉幽州,以及與隱官大人和裴錢都是老朋友的郁狷夫。
此外,未來那條大瀆沿途諸國也可以各自安排人手參與議事,能夠在這座“祖師堂”擁有一席之地。
只說青萍劍宗這邊,除了會動用崔東山的那撥符籙力士,還有金師、摸魚兒和挑山工在內的傀儡。
種秋擔任賬房先生,首席供奉米裕親自帶隊,陶然陶大劍仙負責護道,何辜、於斜回,再加上老虬裘瀆,甚至還會從落魄山挖來元嬰境水蛟泓下,以及雲子。
當然,還有三位搬山倒海易如反掌的大人物,崔東山暫時沒有為包袱齋泄露天機:東海水君王朱、舊王座大妖仰止,和擁有半部《煉山訣》的蠻荒桃亭,如今的嫩道人。
萬事俱備。
添加茶水的人換成了胡楚菱。
崔東山喝完最後一碗茶水,嘆了口氣:“張直,真不是我說你啊,我家先生原本對你可是極為敬重仰慕的,你說你瞎試探個啥,這下好了,差點翻臉,虧得我辛苦補救,今日見面才算有個善始善終,又開了個好頭。”
張直自嘲道:“見面不如聞名。”
崔東山感嘆道:“千秋萬古天下事嘛,總是意外又不意外,生於慮,成於務,失於傲,得於真,歸於淡,留於憶,死於忘,活於……張直,我沒詞了,你來補上。”
張直搖頭,以心聲道:“張某人才疏學淺,不如繡虎真知灼見,當然不敢狗尾續貂。”
崔東山疑惑道:“你曾見過我?”
張直更是疑惑,這是個什麼問題?只得道:“當年在寶瓶洲,不是你自報名號,再親口讓我滾蛋的嗎?”
崔東山點點頭:“那就是我學到了先生的學問精髓之一,不小心記岔了。”
直到張直這天離開青衫渡,密雪峰上的洛陽木客龐超也沒有露面與這個山中晚輩敘舊。
風鳶渡船開始起航南下,陳平安和周米粒都登了船,米裕隨行。這趟走完,米大劍仙就需要全身心投入到大瀆開鑿一事當中去了。
密雪峰宅邸書房內,與先生和小米粒道別之後,崔東山返回此地,當下坐在椅子上,一旁站著掌律崔嵬。
牆壁上掛著一張宣紙,以古篆額書“青萍劍宗”,下邊寫著一些人名木牌和旁注,以不同境界劃分。
最高處書寫“十四境”三字,空白。
其下飛升境,依舊暫時空缺。
仙人境這一欄,有崔東山,半劍修;米裕,劍修。
下邊的玉璞境,有柴蕪,半劍修,宣紙上猶有一行蠅頭小楷:最多十年,爭取五年。
元嬰境,有崔嵬,劍修;隋右邊,劍修;裘瀆,老虬。
金丹境,有曹晴朗,半劍修;陶然,劍修,旁注一句:需要補劍;吳鈎,鬼修;蕭幔影,鬼修。
崔東山問道:“崔嵬,知道浩然宗門的行情吧?”
崔嵬點頭道:“清楚。”
崔東山說道:“所以你身為我們青萍劍宗的掌律祖師,必須要比隋右邊更早躋身玉璞境。隋右邊不爭這個是她的事,她也有資格不著急去打破元嬰境瓶頸,但這不是你不抓緊的理由。”
崔嵬說道:“先前小陌先生在落寶灘道場傳道授業,我曾多次請教劍道,豁然開朗,受益匪淺,三年之內,必定玉璞。”
崔東山嗯了一聲:“這可是你自己說的,過了三年不成事,那就別怪我翻臉。”
在浩然天下,一座宗門是否有資格被稱為頂尖,有一道門檻,就是當下有無飛升境大修士坐鎮。
一流宗門則是有無仙人境當金字招牌,其中,祖上出過飛升境的天然高人一等,宗門內擁有兩位甚至更多仙人境的又瞧不起只有一位的。
二流宗門可能暫時沒有仙人境,但是擁有數位玉璞境,或者說其中有閉關多年、有望仙人的玉璞祖師。
三流宗門只有一位玉璞境,有些青黃不接的宗門甚至已經沒有玉璞境祖師或宗主了。
當然,“宗”字頭就是“宗”字頭,不是誰都可以不當回事的,在一般譜牒修士和山澤野修眼中,還是高不可攀的龐然大物。
崔東山笑問:“崔大掌律,你知道我為何要選擇此地作為青萍劍宗的根基所在嗎?”
崔嵬搖頭道:“不知。”
崔東山靠著椅子,擰轉手腕:“其中一點,是想要找個隱世高人。他生平最不喜歡打架,卻偏偏很能打,當年就是他找到了緋妃的撤退路线。不過這位行蹤不定的散仙最大的能耐還是鑄劍,卻不是浩然人氏,來自青冥天下。既然是敵人的敵人,那就是朋友了嘛。”
崔嵬問道:“姓名道號?境界如何?”
崔東山道:“你不用知道這些,只需知道有這麼一號人物就行了,遲早能碰面的。”
青冥天下首屈一指的鑄劍師徐夫人。他並非女子,只是姓徐名夫人。
“雲水悠悠,與君共愁,花下真人道姓徐,唯夢閒人不夢君,一路沽酒到余杭。自言嗜酒見天真,豁得平生俊氣無。”
“這位稱得上是世外高人的修道之人,其實暫時出不出現都無所謂了,反正都需與我仙都山借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