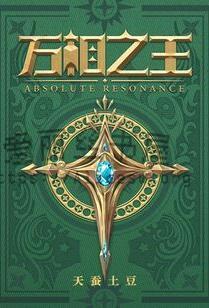聽著青衣小童的肺腑之言,中年僧人率先說道:“那就再看看。”
老夫子笑道:“我看這就很善嘛,等了萬余年光陰,何必急於一時。”
道祖點點頭,對那頭青牛笑道:“既然暫時無事,你隨便逛去,記得別越界。還有就是肚量大些,今天的事情不要記仇了,太過小心眼,於修行是好事,為人則不然。”
青牛沒了那份大道壓制,頓時現出人形,是一位身材高大的老道人,相貌清癯,氣度凜然,極有威嚴。
正是東海觀道觀的老觀主,藕花福地當之無愧的老天爺,由於藕花福地與蓮花洞天相銜接,時不時就與道祖掰掰手腕,比拼道法高低。
老觀主也是塑造出朱斂、隋右邊在內畫卷四人的幕後主人,更是世間公認最強大的十四境大修士之一。
天地間資歷最老、年紀最大的存在,與托月山大祖、白澤、初升都是一個輩分的。
撇開年齡,只說修行歲月的“道齡”,文聖一脈的劉十六,在劍氣長城隱蔽身份的張祿,都算是晚輩。
老觀主每次出門遠游,本身就像是一首游仙詩。
何況在那遠古時代,落寶灘旁碧霄洞,自出洞來無敵手,能饒人處不饒人。
直到它遇到了一位少年模樣的人族修士,才淪為坐騎,再後來,人間就有了那個“臭牛鼻子老道”的說法。
陳靈均微微抬頭,用眼角余光瞥了一下,比起騎龍巷的賈老哥,確實是要仙風道骨些。
如果老道人一開始就是以這般容貌示人,估計那個騎牛道祖只會被陳靈均誤認為是這位老神仙身邊的燒火童子,平日里做些看顧丹爐、搖蒲扇之類的雜事。
老觀主看了眼還坐在地上的青衣小童,一只膽大包天的小爬蟲。
陳靈均立即低頭,挪了挪屁股,轉過頭望向別處。我看不見你,你就看不見我。
老觀主笑眯眯道:“景清道友,你家老爺在藕花福地丟掉的面子,都給你撿起來了。”
陳靈均頭也不抬,耷拉著腦袋,悶悶道:“不知者不罪,如果老神仙與我計較這點小事,就不那麼仙風道骨了。”
話是這麼說,可如果不是有三教祖師在場,這會兒陳靈均肯定已經忙著給老神仙擦鞋捶腿了,至於揉肩敲背,還是算了,心有余力不足,雙方身高懸殊,委實是夠不著,要說跳起來拍人肩膀,像什麼話,自個兒從來不做這種事情。
老觀主呵呵一笑,隨後身形消散,果真如道祖所說,去往別處晃蕩了,連那披雲山魏檗都無法察覺到絲毫漣漪。
小鎮的伏线和脈絡實在太多,斷斷續續,有些已經徹底斷絕,有些尚且藕斷絲連,錯綜復雜,老觀主其實對此頗為欣喜,提綱挈領一事,本就是他大道所在。
若能以此觀道,定會受益匪淺。
道祖自東方而來,騎牛過門如過關,無形中給了舊驪珠洞天一份紫氣東來的大道氣象,只是暫時不顯,以後才會緩緩水落石出。
無須刻意行事,道祖隨便走在哪里,哪里就是大道所在。
這還是在浩然天下,若是在青冥天下,種種祥瑞異象,會更加夸張。
道法自然,道祖原本是不太刻意遮掩這類氣象的,只是做客浩然,礙於禮聖制定的規矩,才收著點。
道祖走向楊家鋪子,打算去後院檐下那條長凳坐一坐。
中年僧人去了趟龍窯,正是姚老頭擔任老師傅的那處。
只留下至聖先師站在陳靈均身邊,老夫子打趣道:“是坐著說話不腰疼,所以不願起身了?”
陳靈均剛要起身,便手腳俱軟,一屁股坐回地上,尷尬道:“回至聖先師的話,我站不起來。”
老夫子笑道:“膽子變得這麼小了?我出現之前,不是挺橫的。”
陳靈均尷尬道:“瞎胡鬧,作不得數的。有眼無珠,別怪罪啊。”
老夫子笑道:“修道之士,一身精神全在雙眸。登山證道,是人非人,只在心竅。”
陳靈均感慨不已,至聖先師的學問就是大啊,說得玄乎。
老夫子問道:“景清,你能不能帶我去趟泥瓶巷?”
陳靈均一聽說是那泥瓶巷,立即一個蹦跳起身,道:“沒問題!”
老夫子疑惑道:“喲,這會兒又是哪里來的氣力?”
陳靈均撓撓頭,赧顏道:“也不知道咋回事,一說起我家老爺,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老夫子嗯了一聲,說道:“約莫是行走在復雜的世道上,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主心骨,幫助我們對抗整個世界。輸了,就是苦難;贏了,就是安穩。”
趁著其余兩位都走遠了,陳靈均試探性問道:“不然我給至聖先師多磕幾個頭?”
老夫子擺手笑道:“用不著,聽多了磕頭聲,也煩。”
陳靈均小心翼翼問道:“至聖先師,為啥魏山君不曉得你們到了小鎮?”
青衣小童趕緊補了一句:“魏山君很懂禮數的,如果不是真有事,他肯定會主動來覲見。”
個人恩怨與江湖規矩,是兩回事。
魏檗對他如何,與魏檗對落魄山如何,得分開算。再說了,魏檗對他,其實也還好。
老夫子笑道:“因為游歷小鎮這件事,不在道祖想要讓人知道的那條脈絡里,既然道祖有意如此,魏檗當然就見不著我們三個了。”
陳靈均贊嘆不已:“道祖的道法就是高啊。”
老夫子笑道:“何止是道法高,先前真要打起架來,我也怵。”
陳靈均一個真情流露,也就沒了顧忌,哈哈大笑道:“輸人不輸陣,道理我懂的……”
只是越說嗓音越小,一貫嘴巴沒把門的臭毛病又犯了,陳靈均最後悻悻然改口道:“我懂個錘子,至聖先師大人有大量,就當我啥都沒說啊。”
老夫子倒是不以為意。
其間兩人路過騎龍巷鋪子,陳靈均目不斜視,哪敢隨隨便便將至聖先師引薦給賈老哥。
老夫子轉頭看了眼壓歲鋪子和草頭鋪子,道:“瞧著生意還不錯。”
陳靈均點點頭:“小本買賣,價格公道,細水長流,其實掙不著什麼大錢,但是我家老爺經手那麼多的神仙錢,偏偏十分在意這點銀子銅錢的盈虧,經常親自下山來這里翻賬查賬的,倒不是老爺信不過石掌櫃和賈老哥的為人,只是好像看著賬簿上邊的盈余,他就會很開心。”
老夫子點頭道:“這是個好習慣,掙得了小錢,守得住大錢,年年有余,越攢越多,一個門戶的家底就愈發厚實了,一年光景比一年好。”
陳靈均唏噓不已,仰頭望向那位老夫子,誠心說道:“至聖先師說話可真實在,連我都聽得懂。”
老夫子似有所想,笑道:“禪宗自五祖六祖起,法門大啟不擇根機,其實佛法就開始說得很平實了,而且講究一個即心即佛,莫向外求,可惜之後又漸漸說得高遠隱晦了,佛偈無數,機鋒四起,老百姓就重新聽不太懂了。其間佛門有個比不立文字更進一步的‘破言說’,不少高僧直接說自己不樂意談佛論法,若是不談學問,只說法脈繁衍,就有點類似我們儒家的‘滅人欲’了。”
陳靈均聽得迷糊,也不敢多說半句,所幸老夫子好像也沒想著多聊此事。
兩人一起在騎龍巷拾級而上,老夫子問道:“這條巷子,可有名字?”
陳靈均使勁點頭:“有啊,叫騎龍巷。再高一些,巷子頂部,我們當地人都習慣稱呼為火爐尖。”
老夫子點點頭:“果然處處藏有玄機。”
陸沉在離鄉之前,曾經逍遙游於浩然天地間,也曾呼龍耕煙種瑤草,風雨跟隨雲中君。
老夫子走到了台階頂部,轉頭望向一級級台階,問道:“景清,你的成道之地是在哪里啊?”
陳靈均一臉震驚,疑惑不解道:“至聖先師那麼大的學問,也有不知道的事情啊?”
老夫子笑了笑:“不是不能知道,也不是不想知道。只是我們幾個需要克制,不然各自一座天下的人、事、萬物,就會被我們道化得很快。”
“所以道祖才會經常待在蓮花小洞天里,哪怕是那座白玉京,都不太願意走動。就是擔心一旦那個一過半,就開始萬物歸一,不由自主,不可逆轉,先是山下的凡夫俗子,繼而是山上修士,最後輪到上五境,可能到頭來,整個青冥天下就只剩下一撥十四境大修士了。人間千萬里山河,皆是道場,再無俗子的立錐之地。”
“這是當年河畔議事,一場早就有過約定的萬年之約。需要道祖負責找尋出破解之法,一開始就是他最擔心此事。”
“道祖的道法當然很高嘛,能者多勞,天經地義。”
陳靈均聽得苦兮兮,慌得不行,喃喃道:“至聖先師,與我說這些做啥啊。”
老夫子笑呵呵道:“只是聽人說了,你自己不說就行,何況你如今想說這些都難。景清,不如我們打個賭,看看現在能不能說出‘道祖’二字?今天遇到我們三個的事情,你要是能夠說給旁人聽,就算你贏。對了,給你個提醒,唯一的破解之法,就是不立文字,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陳靈均心中起念,只是剛要說點什麼,比如一想到要如何跟賈老哥吹牛皮,就開始頭暈目眩,試了幾次都是如此,陳靈均晃了晃腦袋,干脆不去想了,一五一十說道:“我那修道之地,是黃庭國御江。”
老夫子哦了一聲:“《黃庭經》啊,那可是一部道教的大經。聽說誦讀此經,能夠煉心性,得道之士,久而久之,萬神隨身。術法萬千,細究起來,其實都是相似道路,比如修道之人的存思之法,就是往心田里種稻谷,練氣士煉氣,就是耕耘,每一次破境,就是一年里的一場春種秋收。純粹武夫的十境第一層,氣盛之妙,也是差不多的路數,氣吞山河,化為己用,眼見為實,繼而返虛,歸攏一身,變成自己的地盤。”
“所以道門推崇虛己,儒家說君子不器,佛家說空,諸相非相。”
聽著這些令人腦瓜子疼的言語,青衣小童額頭的發絲,因為滿頭汗水變得一綹綹,十分滑稽,實在是越想越後怕啊。
陳靈均攤開手,滿是汗水,皺著臉可憐巴巴道:“至聖先師,我這會兒緊張得很,你老人家說啥記不住啊,能不能等老爺回家了,與他說去,我家老爺記性好,喜歡學東西,學啥都快,與他說,他肯定都懂,還能舉一反三。”
老夫子不置可否,笑了笑,換了個話題:“你家老爺的那位先生,也就是文聖老秀才,關於‘御’這個字,是不是曾經說過些學問?”
陳靈均一臉呆滯茫然。
文聖老爺是我家老爺的先生,又不是我景清大爺的先生,至聖先師你這樣神出鬼沒地考校,就有點不講究了啊,真心不合江湖規矩。
算了,至聖先師也不是混江湖的。
唉,要是先生在這兒,不管至聖先師說啥都接得住話吧。難不成以後自己真得多讀幾本書?山上書倒是不少,老廚子那里,嘿嘿……
嘿個屁的嘿,至聖先師就在旁邊站著呢,找死啊,陳靈均直接甩了自己一耳光,他娘的出手重了,一個氣沉丹田,繃著臉。
老夫子笑道:“不用這麼拘謹,食色性也。一個人的諸多欲望,本性使然,這當然會讓人犯很多的錯,但是我們的每次知錯、認錯和改錯,就是為這個世道腳下添磚,為逆旅屋舍高處加瓦,其實是好事啊。如道祖所言,連他都是人間一過客,是句大實話嘛,但是人人都可以為後世人走得更順當些,做點力所能及的事情,既能利人又可利己,何樂不為?當然了,如果偏有人只追求自己心中的純粹自由,亦是一種無可厚非的自由。”
老夫子笑著給出答案:“是那《大略篇》里說‘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更早的說法呢,御,祀也。再早一些,也有個老皇歷的說頭,聖人流徙四凶,散落天地,以御螭魅。”
至聖先師拍了拍青衣小童的腦袋,笑道:“青蛇在匣。”
到了泥瓶巷,依舊是陳靈均帶路,先幫著介紹那個修繕過的曹氏祖宅,然後走向陳平安和宋集薪相毗鄰的宅子,老夫子緩緩而行,稍稍繞路,停下腳步,看了眼腳下一處,是昔年窯工埋藏胭脂盒的地方。
水神燒火。
青童天君也確實是難為人了。
這尊雨師,在遠古天庭是水部第二高位神靈,僅次於水神李柳。
被藥鋪楊老頭抹去了散道的所有痕跡,而且這場散道極有分寸,不是那種一股腦兒丟給陳平安,而更像是在泥瓶巷少年的心田,種下了一粒種子,漸漸花開。
舊天庭的遠古神靈,並無後世眼中的男女之分。如果一定要給出個相對確切的定義,就是道祖提出的大道所化、陰陽之別。
大雨中,消瘦少年在這條巷子里堵住了一個衣衫華麗的同齡人,掐住對方的脖子。
草鞋少年曾經釣起一條小泥鰍,隨便轉贈給小鼻涕蟲,被後者養在水缸里。
當然還有窯工漢子埋藏的胭脂盒在此。
宋集薪蹲在牆頭上看熱鬧,陳平安出聲救下了劉羨陽。
一起遠游大隋書院的途中,朝夕相處之後,李槐內心深處,獨獨對陳平安最親近、最認可。
無數類似的“小事”,隱藏著極其隱晦、深遠的人心流轉,神性轉化。
不單單是陳平安的悄然獲得,也有陳平安自身神性的流失,這才是楊老頭那個手筆的厲害之處。
每一次肯定他人,陳平安就會失去一份神性,但是每一次自我否定後的某種肯定,就又能悄悄吃掉一部分積攢在身的神性。
況且李寶瓶的赤子之心,所有天馬行空的想法和念頭,某些程度上亦是一種“歸一”,馬苦玄的那種肆意妄為,何嘗不是一種純粹。
李槐的洪福齊天,林守一近乎天生熟稔的“守一”之法,劉羨陽的天賦異稟,學什麼都極快,擁有遠超常人的得心應手之境地,宋集薪以龍氣作為修道之起始,稚圭有望脫胎換骨,在恢復真龍姿態之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桃葉巷謝靈以“接納、吞食、消化”道法一脈作為登天之路,火神阮秀和水神李柳以至高神性俯瞰人間、不斷聚攏稀碎人性……
小鎮所有年輕一輩,各自互為障眼法。
這一場無聲無息的天道爭渡,原本人人都有希望成為那個一。
老夫子抬起胳膊,在自己頭上虛手一握。
頭頂三尺有神明。
遠古神靈造就人族,掬水為本,所掬之水,來自光陰長河,此後才是撮土為形,人類隨之有了最粗糙的形神。
先前道祖與陳靈均閒聊,隨便提及了山水相依一事。說來說去,其實說的就是人之大道根本。浩然山河是如此,人更是。
所以崔東山曾經說過,三教祖師,唯獨在大道親水一事上,和和氣氣,從無爭吵。
火煉為術,煉化之物正是神靈饋贈給人族的一部分粹然神性,此為火煉金之道。
所以大地之上,既先天擁有神性又同時欠缺完整神性的人類,才會有七情六欲,有種種復雜心性。
修道之士所謂的塑造“金枝玉葉”,即是以天地靈氣為枝葉,此為木。
這就是最早的天地五行。
而適宜有靈眾人修行證道的天地靈氣,到底從何而來?就是眾多神靈屍骸消散後未曾徹底融入光陰長河的天道余韻。
這就決定了為何人族才是世間得天獨厚的萬靈之首,為何妖族想要修行登高,就一定要拋棄先天體魄堅韌的優勢,必須煉出個人形。
當初三教祖師與楊老頭是有過一場約定的,只要後者遵守誓約,三教祖師的眼光就不會打量此地。
只是儒釋道三教一家,歷代聖人,會負責盯著這邊的飛升台和鎮劍樓,看了那麼多年,臨了臨了,還是著了道。
而且事實上楊老頭到最後也不曾違約。
老夫子笑了笑,也對,只有千日做賊,哪有千日防賊的道理。
不過最根本的緣由,還是青童天君的最終選擇,太過巧妙了,障眼法實在太多。
最關鍵的,還是楊老頭並非一開始就選擇了陳平安,而是不斷押注,一點一點增添籌碼,這類行徑在楊老頭萬年畫地為牢的生涯當中,太不起眼了,小鎮年輕一輩,宋集薪、趙繇、顧璨這些孩子身上,當年哪個沒有得到一份甚至是數份拐彎抹角的饋贈?
在陳平安身上,楊老頭的押注反而十分“吝嗇”,好像只在數次不易察覺的關鍵節點,才稍稍添油,一盞燈火,始終風雨飄搖,不滅而已。
比如讓一個五歲大的孩子,必須上山采藥才能從藥鋪換錢,再買藥回家,才能煮藥。
“雷打不動的等價交換”,這個道理,多少成年人,多少山上修道之人,可能活了一輩子都不曾懂。
又比如陳平安年幼時的那場“過河”,直到需要有人拉扯一把,孩子才不至於跳入洪水中,楊老頭才現身。
老夫子看了眼小巷盡頭,眯眼望去,好嘛,果不其然,當年孩子在巷中徘徊不去,從黃昏走到夜幕,終於被孩子等到了開門,是那個婦人自身的善心使然,更是楊老頭的有意牽引……不對,不是青童天君!
老夫子一步跨出,側身靠牆而立,一手負後,一手雙指並攏,輕輕拈住那根虛线。
是藥師佛轉世的姚老頭?
“人性是神靈給予人類的一座牢籠。”
“自由是一種懲罰。”
佛家說自性,講究即心即佛,就是希望人能夠以大毅力、大開悟和大悲憫,在那條原本通往完整粹然神性的山巔處,稍稍改變軌跡,走出一條嶄新道路。
老夫子轉過頭,巷子里仿佛站著一個飢腸轆轆的孩子,身材瘦小,面黃肌瘦,先聽見了開門聲,孩子好像猶然不敢相信,小跑幾步,又停下腳步,再看到那片昏黃的光亮,驀然從大門往巷子里涌出,眨了眨眼睛,最終怔怔看著那個開了門的婦人。
絕望里的希望,往往如此,最早到來的時候,不是欣喜,而是不敢相信。
孩子當時的眼睛里,逐漸煥發出來光彩,明亮得就像一雙眼眸擁有日月。
一個孤苦無依的陋巷孩子,在那一刻,綻放出一種無比璀璨的人性。
正是希望。
而這種人性和希望,會支撐著孩子一直成長。
老夫子轉頭望去,隔著一堵牆壁,遙遙望向了那座未來的書簡湖,看到了那個面目憔悴、心神枯槁的賬房先生。
老夫子收回視线,嘆了口氣,這個劍走偏鋒的崔瀺,當年就真心不怕陳平安一拳打殺顧璨,或是直接一走了之?
一旦陳平安的人性脈絡在此斷去,後遺症之大,無法想象。
以後來陳平安的種種遠游歷練,尤其是擔任隱官的人心鍛煉,會使得陳平安遮掩錯誤的本事無限趨近於崔瀺的那種自欺欺人,變得神不知鬼不覺。
他媽的你個繡虎,一個不小心,說不定如今陳平安就已經是“修舊如舊,而非嶄新”的那個一了。
老夫子小聲嘀咕,罵罵咧咧了一句。
陳靈均始終站在自家老爺門口那邊,在這兒,心安些。
老夫子轉頭笑道:“景清,你在這里稍等片刻,我去個地方,很快回來。”
陳靈均立即挺直腰杆,朗聲答道:“得令!我就杵這兒不挪窩了!”
青鸞國一處水神祠廟,占地十余畝的河伯祠廟,僥幸未被戰火殃及,得以保存,如今香火越來越興盛。
在第四進的游廊當中,老夫子站在那堵牆壁下,牆上題字,既有裴錢的“天地合氣”“裴錢與師父到此一游”,也有朱斂的那篇草書,多枯筆淡墨,百余字,一氣呵成。
不過老夫子更多注意力,還是放在了那楷字兩句上邊。
老夫子仰頭看字,撚須而笑。
天上月,人間月,負笈求學肩上月,登高憑欄眼中月,竹籃打水碎又圓。
山間風,水邊風,御劍遠游腳下風,聖賢書齋翻書風,風吹浮萍有相逢。
好個風月無邊,碎圓又有相逢。
陸沉在劍氣長城那邊,說天上月是攏起雪,人間雪是碎去月,歸根結底,說的還是一個一的去返。
而朱斂的草書題字在牆壁,百余字,都屬於無心之語,事實上文字之外,撇開內容,真正所表達的,還是那“聚如山岳,散如風雨”的“聚散”之意。
曾經之朱斂,與當下之陸沉,算是一種玄之又玄的遙相呼應。
道祖攤上這麼個只喜歡看戲、清靜不作為的嫡傳弟子,說話怎麼能夠硬氣?
驪珠洞天最終折騰出這麼大的動靜,陸沉曾經在此擺攤多年,推波助瀾得算他一份,逃不掉的。
這次暫借一身十四境道法給陳平安,與幾位劍修同游蠻荒腹地,算是將功補過了。
道祖先前之所以願意再看看,是因為陳平安作為年輕隱官做出的那個選擇,至關重要。
返回泥瓶巷,老夫子走到陳靈均身邊,看著院子里邊的黃泥牆壁,可以想象,那個宅子主人年少時,背著一籮筐的野菜,從河邊回家,肯定經常手持狗尾巴草,串著小魚,曬成魚干,一點都不願意浪費,嘎嘣脆,整條魚干,孩子只會囫圇吃下肚子,可能依舊吃不飽,但是就能活下去。
民以食為天。
嘉谷布帛二者,生民社稷之本。
家家戶戶,豐衣足食。
路上行人,衣履溫暖。
老夫子雙手負後,站在門外望向門內,沉默許久。
陳靈均趴在黃泥牆頭上邊,雙腳懸空,喃喃道:“至聖先師,我先生雖然是劍仙,是武學宗師,是落魄山的山主,是劍氣長城的隱官大人,可是我曉得,我家老爺最心心念念的,還是當個問心無愧的讀書人,一路走來,可不容易了,道理說破天去,天底下最不想吃的飯,可不就是個百家飯嗎?因為自個兒沒有家了,才會不得不吃百家飯嘛。而且我家老爺又念舊,又最感恩,長輩緣怎麼來的,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因為我家老爺打小兒就常與老人們聊天嘛,所以這些年其實很辛苦的,每次回了家鄉,都會來這邊坐一坐,是老爺在提醒自己做人不能忘本呢,你老人家是讀書人的祖師爺,可不許別人欺負他啊。”
老夫子笑道:“那如果做人忘本,你家老爺就能過得更輕松些?”
陳靈均毫不猶豫道:“好人一生平安,平安一生好人!”
老夫子笑道:“這確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值得我們去給予希望。”
陳靈均咧嘴一笑,趴在牆頭上,總算能夠為自家老爺做點什麼了。
老夫子好像這會兒心情很好,拍了拍青衣小童的肩膀,滿臉笑意,道:“走。”
陳靈均松開手,落地後納悶道:“至聖先師,接下來要去哪兒?去文武廟逛逛?”
老夫子笑眯眯道:“都拍過了道祖的肩膀,也不差那位了,以後酒桌上論英雄,你哪兒來的敵手?”
陳靈均滿頭汗水,使勁擺手,一言不發。
至聖先師,你坑我呢?!
老夫子伸手拽住青衣小童的胳膊:“怕什麼,不大氣了不是?”
陳靈均雙腳立定,身體後仰,差點當場落淚,號道:“不去了,真的不去!我家老爺信佛,我也跟著信了啊,很心誠的那種,我們落魄山的山風,第一大宗旨,就是以誠待人啊……”
以後要是給老爺知道了,揍不死他陳靈均。
落魄山,山門口一邊擺放了一張桌子,另外一邊,有個黑衣小姑娘,肩挑金扁擔,橫膝綠竹杖,斜挎著一只棉布小挎包,坐在小竹椅上。
她瞧見了桌旁那站著的老道人,揉了揉眼睛,不是自己眼花,小姑娘將行山杖和金扁擔都斜靠竹椅,立即站起身,小跑到高大老道人身邊,一個站定,仰頭問道:“老道長,口渴不?咱這兒有茶水待客嘞。”
小姑娘補了一句:“不收錢!”
見那老道人不說話,小米粒又說道:“就是茶水沒啥名氣,茶葉來自咱們自家山頭的老茶樹,老廚子親手炒制的,是今年的新茶哩。”
老觀主點點頭,坐在長凳上。
比起在小鎮那邊,消了點氣。
不然這筆賬,得跟陳平安算,對那只小爬蟲出手,有失身份。
地薄者大物不產,水淺者大魚不游。
小米粒去煮水煎茶之前,先打開棉布挎包,掏出一大把瓜子放在桌上,其實兩只袖子里就有瓜子,小姑娘是跟外人顯擺呢。
小米粒問道:“老道長,夠不夠?不夠我還有啊。”
老觀主又想到了那個“景清道友”,差不多意思的言語,卻天壤之別,老觀主難得有個笑臉,道:“夠了。”
黑衣小姑娘讓老道長稍等片刻,她就自個兒忙碌去了。
很快就拎著一只錫罐茶葉和一壺沸水,給老道人倒上了一碗茶水,小米粒就告辭離開。
老觀主笑問道:“小姑娘不坐會兒?”
小姑娘使勁搖頭:“不嘞,暖樹姐姐不許,說是免得客人喝茶不自在。”
小米粒最後提醒道:“對了,剛煮沸的茶水,老道長小心燙啊。”
老觀主笑了笑,心誠的言語,讓他記起了當年那個背著把長氣闖入藕花福地的泥腿子。
人間萬物多如毛,我有小事大如斗。
老觀主舉起茶碗,笑問道:“你就是落魄山的右護法吧?”
周米粒剛要轉身,立即使勁點頭。
小姑娘抿嘴而笑,一張小臉龐,一雙大眼眸,兩條疏淡的小小的黃色眉毛,隨便哪兒都是喜悅。
老道長早這麼敞亮,她早就不客氣落座了嘛。
小米粒坐在長凳上,自顧自嗑瓜子,不去打攪老道長喝茶。
沒來由發現老廚子不知何時來到山門口這邊了,小米粒拍拍手,好奇問道:“老廚子,今兒怎麼下山啦?書看完啦?”
朱斂笑道:“還沒呢,得慢慢看。”
小米粒轉頭望向老道長,伸手擋在嘴邊:“老道長,老廚子是我們落魄山的大管家,炒菜一絕!你們倆要是聊得投緣了,那就有口福嘞。”
老觀主點點頭:“再是惡客登門,給小姑娘這麼一款待,也要和氣生財了。江湖故人,會投緣的。”
朱斂笑道:“小米粒,能不能讓我跟這位老道長單獨聊幾句。”
小米粒乖巧點頭,又打開棉布挎包,給老廚子和老道長都倒了些瓜子在桌上,坐在長凳上,屁股一轉,落地站穩,再轉身抱拳,告辭離去。
朱斂與老觀主抱拳再落座,相對而坐,給自己倒了一碗茶水。
老觀主笑眯眯道:“藏掖做什麼,白瞎了一副能讓天地養眼的好皮囊。”
朱斂一笑置之。
各自修行山巔見,猶見當初守觀人。
老觀主問道:“何時夢醒?”
最有希望繼三教祖師之後,躋身十五境的大修士,眼前人得算一個。
朱斂答非所問:“人生就像一本書,我們所有遇到的人和事,都是書里的一個個伏筆。”
老觀主點頭道:“所以說無巧不成書。有些巧合,妙不可言,比如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陳十一。陳是一,一是陳。”
陳靈均哪敢去拍那位的肩膀,當然是打死都不去的,只差沒有在泥瓶巷里邊撒潑打滾了,老夫子只得作罷,讓青衣小童帶自己走出小鎮,只是既不去神仙墳,也不去文武廟,只是繞路走去那條龍須河,要去那座石拱橋看看,最後再順便看一眼那座類似行亭的小廟遺址處。
陳靈均試探性問道:“至聖先師,先前那位個兒高高的道門老神仙,境界也很高很高?”
老夫子點點頭:“很高,若是境界不高,道祖也不會傳授道法給他了。而且這位道友在早年歲月里於我們人族有大恩澤,故而在禮聖制定與地支契合的十二屬相里邊,排名很高,就是道友的那個牛脾氣……算了,背後說是非,不厚道。”
陳靈均憂心忡忡:“可是聽口氣,好像跟我家老爺有點過節?”
咋辦,自己肯定打不過那位老道人,至聖先師又說自己跟道祖打架會犯怵,所以怎麼看,自己這邊都不占便宜啊。
廢話,自己與至聖先師當然是一個陣營的,做人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什麼叫混江湖,就是兩幫人斗毆、打群架,哪怕人數懸殊,己方人少注定打不過,都要陪著朋友站著挨打不跑。
先前老道人提及了藕花福地,聽口氣,自家老爺在那邊還吃過虧,丟過面子。
關於更名為蓮藕福地的那處福地,陳靈均只知道裴錢和曹晴朗,還有老廚子、種夫子幾個,都來自這塊人傑地靈的風水寶地,只是一個個都不喜歡多說半句家鄉事,陳靈均也懶得多問,所以始終誤以為一個昔年下等品秩的藕花福地,連修道之人都沒幾個,更無地仙,能折騰出啥風浪。
哪里想到會跑出一位被道祖稱呼為道友的家伙,真是不可貌相啊,虧得自己處處好心,與人為善,多嘴提了一茬自家山中多青草的事情,不然這筆糊塗賬,自己這小胳膊小腿的,可扛不下來。
老夫子搖搖頭:“其實不然,當年在藕花福地,這位道友對你家老爺的為人處世,還是頗為認可的,尤其是一句發自肺腑的道長,寬慰人心,恰到好處。”
陳靈均如釋重負,挺起胸膛哈哈笑道:“我家老爺,長輩緣一向很好。至於我,有樣學樣,還湊合。”
老夫子微笑道:“長輩緣這種東西,我就不太行。當年帶著弟子們游學人間,遇到了一位漁夫,就沒能乘船過河,回頭來看,那會兒還是氣盛,不為大道所喜。”
陳靈均壯著膽子說道:“我家老爺那會兒帶著寶瓶他們去大隋游學,一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都是我家老爺與樵夫敲門借宿,還是比較順遂的。”
老夫子問道:“景清,你跟著陳平安修道多年,山上藏書不少,就沒讀過陸掌教的《漁夫》篇,不曉得‘分庭抗禮’一說的來源,曾經罵我一句‘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陳靈均神色尷尬道:“書都給我家老爺讀完了,我在落魄山只曉得每天勤勉修行,就暫時沒顧上。”
老夫子笑呵呵道:“還是要多讀書,好歹跟人聊天的時候能接上話。”
陳靈均小雞啄米,使勁點頭道:“以後我肯定看書修行兩不誤。”
回頭每次下山逛蕩,還要經常去槐黃縣文廟那邊給至聖先師敬香,磕頭!
陳靈均猶豫了一下,好奇問道:“能不能問問佛祖的佛法咋樣?”
言下之意,是想問你老人家打不打得過佛祖。
老夫子撫須笑道:“能夠撮大千世界為一粒微塵,又能拈一朵花演化山河世界,你說佛法如何?”
陳靈均嘆了口氣,一個沒管住手,就下意識拍了拍老夫子的袖子,沒事,反正打架這種事情,傷和氣,少打為妙。
老夫子對此不以為意,隨口問道:“在這邊待久了,有不喜歡的人嗎?”
陳靈均悻悻然收回手,干脆學自家老爺雙手籠袖,免得再有類似失禮的舉動,想了想,也沒啥真心討厭的人,只是至聖先師問了,自己總得給個答案,就挑出一個相對不順眼的家伙:“杏花巷的馬苦玄,做事情不講究,比我家老爺差了十萬八千里。”
老夫子自然是知道真武山馬苦玄的,卻沒有說這個年輕人的好與壞,只是笑著與陳靈均泄露天機,給出一樁陳年往事的內幕:“蠻荒天下驅使傀儡搬動十萬大山的那個老瞎子,曾經對我們幾個很失望,就掏出一雙眼珠子,分別丟在了浩然天下和青冥天下,說要親眼看著我們一個個變成與曾經神靈無異的那種存在。這兩顆眼珠子,一顆被老觀主帶去了藕花福地,給了那個燒火道童,另一顆就在馬苦玄身邊,楊老頭早年在馬苦玄身上押注不算小。”
老夫子感慨道:“老瞎子那會兒,只說相貌,確實是頂好的,陳清都比他差遠了,不過兩個都是實心眼,一根筋,臭脾氣。”
話趕話的,陳靈均就想起一事:“其實討厭的人,還是有的,就是沒啥可說的,一個蠻不講理的婦道人家,我一個大老爺們又不能拿她如何,就是那個冤枉裴錢打死白鵝的婦人,非要裴錢賠錢給她,裴錢最後還是掏錢了,那會兒裴錢其實挺傷心的,只是當時老爺在外游歷,她就只能憋著了。其實當年裴錢剛去學塾讀書,上課放學路上鬧歸鬧,確實喜歡攆白鵝,可是每次都會讓小米粒兜里揣著些米糠玉米,鬧完之後,裴錢就會大手一揮,小米粒立即丟出一把在巷弄里,算是賞給那些裴錢所謂的手下敗將。”
老夫子點點頭:“是要傷心。”
在最早那個百家爭鳴的輝煌時代,墨家曾是浩然天下的顯學,此外還有在後世寂寂無名的楊朱學派,兩家之言曾經充盈天下,以至於有了“不歸於楊即歸墨”的說法。
然後出現了一個後世不太留心的重要轉折點,就是亞聖請禮聖從天外返回中土文廟,商議一事,最終文廟的做法就是打壓楊朱學派,沒有讓整個世道循著這一派學問向前走,再之後,才是亞聖的崛起,陪祀文廟,再之後,是文聖提出了人性本惡。
諸子百家的老祖師里邊,其實有不少都對此非議極大,認為是禮聖擔心自己的大道“禮儀規矩”,與楊朱學派推崇的“個體自由”有不可磨合的衝突,出於私心,才答應了亞聖的提議。
他們覺得世道的秩序與個體的自由之間,確實存在著一場無形的大道之爭。
一向不太喜歡喝酒的禮聖,那次難得主動找至聖先師喝酒,只是喝酒之時,禮聖卻也沒說什麼,喝悶酒而已。
老夫子當然知道其中緣由,不是推崇“人人為己,天經地義”的楊朱學派不好,若是不好,也不會成為天下顯學。
這一派學問論生死,極敞亮透徹,談貴己,更是獨樹一幟,極其新穎,“勿為物累,勿傷外物”的宗旨,也是極好的,也不是因為與道家離得近,只是這一脈學問成為世道,會讓行走在這條道路上的所有人都變得越來越極端,這里邊就又涉及了更為隱蔽的人心和神性之爭。
老夫子問道:“景清,你家老爺怎麼看待楊朱學派?”
陳靈均想了想,老老實實答道:“我家老爺沒提及過,但是聽大白鵝說過,那是一種混沌的精致,不咋的,一撮人治學此道,無傷大雅,還能裨益世道,如果人人如此,皆是曇花。”
如果不是崔東山胡說八道,陳靈均都沒聽過什麼楊朱學派。
陳靈均一直覺得大白鵝就是個醉鬼,不喝酒都會說酒話的那種人。
兩人沿著龍須河行走,這一路,至聖先師對自個兒可謂知無不言,陳靈均走路就有點飄,忍不住問道:“至聖先師,你老人家今兒跟我聊了這麼多,一定是覺得我是可造之才,對吧?”
老夫子笑呵呵道:“這是什麼道理?”
陳靈均滿臉誠摯神色,道:“你老人家那麼忙,都願意跟我聊一路。”
老夫子答非所問:“每一個昨天的自己,才是我們今天最大的靠山。”
“景清,為什麼喜歡喝酒?”
“啊?喜歡喝酒還需要理由?”
“也對。”
“至聖先師,我能不能問你老人家一個問題?”
“當然可以。”
“酒桌上最怕哪種人?”
“是那種喝酒上臉的家伙。”
哦豁,果然難不住至聖先師!這句話一下子就說到自己心坎上了。
陳靈均繼續試探性問道:“最煩哪句話?”
“是說著勸酒傷人品,我干了你隨意。”
哦豁哦豁,至聖先師的學問確實了不起啊,陳靈均由衷佩服,咧嘴笑道:“沒想到您老人家還是個過來人。”
“景清,那麼我問你,你覺得怎麼才算窮?”
“光有錢,沒學問?”
老夫子看了眼身邊開始晃蕩袖子的青衣小童。
陳靈均立即重新雙手籠袖,改口道:“為富不仁、窮凶極惡之輩?”
老夫子笑道:“就說點你的心里話。”
陳靈均松了口氣,瞎琢磨累死個人:“那就是兜里沒錢,窮得娶不起媳婦,打光棍,找人賒賬買酒,都沒人樂意肯借錢,窮得死要面子,而且這點面子還得躲躲藏藏,好像見不得光,然後啪嘰一下,最後僅剩的這點面子,在某天也給人隨便一腳踩了個稀巴爛,只能等到人散了,旁人看完了熱鬧,才敢自己找機會從地上撿起來。”
“就這些?”
“只敢懷疑世道,不敢懷疑自己?”
老夫子點點頭,先後兩個答案,尤其是後者,還真有點出乎意料,於是笑問道:“你是在酒桌上邊琢磨出來的說法?”
陳靈均有些難為情,抬起袖子蹭了蹭臉:“那哪兒能啊,酒桌上真喝高了,可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是跟著老爺到了山上,太懶,還喜歡給自己找借口,變著法子成天瞎逛蕩,就喜歡下山來小鎮這邊散心,至聖先師你別怪罪啊,先前我說自己修行勤勉,屁嘞,我就是山上混吃,下山混喝,好在老爺都看在眼里,卻也從來不管我這些,老爺不管,其他人哪好意思管我,至聖先師,真不是我吹牛皮啊,咱們落魄山,不管是誰,都打心底敬重老爺的。”
老夫子抬頭看了眼落魄山。
除了一個不太常見的名字,論物,其實並無半點古怪。
但這就是最大的古怪。
老夫子問道:“陳平安當年買山頭,為何會選中落魄山?”
陳靈均嘿嘿笑道:“這里邊還真有個說法,我聽裴錢偷偷說過,當年老爺相中了兩座山頭,一個真珠山,花錢少嘛,就一枚金精銅錢,再一個就是如今咱們祖師堂所在的落魄山了,老爺那會兒攤開一幅大山形勢圖,不曉得咋個選擇,結果剛好有飛鳥掠過,拉了一坨屎在圖上,剛好落在了‘落魄山’上邊,哈哈,笑死個人……”
老夫子笑問道:“小鎮老話有說頭?”
陳靈均使勁揉了揉臉,好不容易才忍住笑,道:“老爺在裴錢這個開山大弟子那邊,真是啥都願意說,老爺說窯工師傅姚老頭帶他入山找土的時候,說過山水之間有神異,頭頂三尺有神明嘛,反正我家老爺最信這個了。不過老爺當年也說了,他後來猜測可能是國師的有意為之。”
老夫子點點頭,陳平安的這個猜測,就是真相,確實是崔瀺所為。
落魄當然不是什麼好說法,但是若能得個定字,意思可就截然不同了。
崔瀺之所以剝離出來一個心性跳脫的崔東山,除了那些已經水落石出的天大謀劃之外,其實還藏著個比較有意思的手段,就是用一個另外的自己,可能是通過一兩個關鍵詞,打開某種禁制,就像一封封“家書”,遙遙寄給未來歲月的自己,幫著提醒自己在什麼階段、時刻、節點,應當說什麼話做什麼事情。
就像道祖這次走出蓮花洞天,離開青冥天下,就早早‘自說自話’,與一些他早已看到未來卻暫時沒有走到自己跟前的有緣之輩,有著不同的問答,都是在洞天內大道演化,縝密推衍,早就算好了的。
浩然繡虎,這次有請三教祖師落座,一人問道,三人散道。
當然不是說崔瀺的心智、道法、學問,就高過三教祖師了。
這就像是三教祖師有萬千種選擇,崔瀺說他幫忙選出的這一條道路,他可以證明是最有益世界的那一條,這就是那個毋庸置疑的萬一,那麼你們三位,走還是不走?
走到了那座再無懸劍的石拱橋上,老夫子駐足,停步低頭看著河水,再稍稍抬頭,遠處河畔青崖那邊,就是草鞋少年和馬尾辮少女初次相逢的地方,一個入水抓魚,一個看人抓魚。
多少小魚優哉游哉碧水中,一場爭渡為求魚龍變,人間復見萬古龍門,紫金白鱗爭相躍。
陳靈均一屁股坐在橋邊,雙腳懸空,雙臂環胸,仰頭問道:“至聖先師,你老人家先前在泥瓶巷那邊,往宅子里邊看啥呢?”
老夫子雙手負後,笑道:“一個窮怕了餓慌了的孩子,為了活下去,曬了魚干,全部吃掉,一點不剩,吃干抹淨,悄無聲息。”
一個泥瓶巷無依無靠的孩子,最早是跟藥鋪伙計學煮藥,再跟劉羨陽學那些上山下水,然後是跟龍窯的姚老頭學燒瓷手藝,從拳譜上練拳學認字,再憑借陸沉的藥方學寫字,走出家鄉後,依舊是小心翼翼看待這個世界,不斷與他人學習為人處世之道,盡可能學到更多的一技之長,每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可,每一次小心翼翼的自證和修心,都是一種默默的成長。
與此同時,竭盡所能,不斷回饋世道。
陳平安年輕時曾經與人說過,一切好的,他都會學,到了最後,連吳霜降和鄭居中的拆解萬物、人心之術,如今不惑之年的年輕隱官都還是在學,想必以後陳平安還是如此。
老夫子看著那條河水,問道:“世界這個說法,最早是佛家語。界,若是依照咱們那位許夫子的說文解字?”
陳靈均哭喪著臉:“至聖先師,別再瞥我了啊,我肯定不知道的。”
老夫子抬手指了指河邊的田壟,笑道:“田畔也,一處種禾之地,阡陌縱橫之范式。老秀才說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你聽聽,是不是一條很清晰的脈絡?所以最終得出的結論,恰恰是人性本惡,正是禮之所起。老秀才的學問,還是很實在的,而且換成你是禮聖,聽了開不開心?”
陳靈均慚愧不已:“至聖先師,我讀書少了,問啥啥不懂,對不住啊。”
“沒事,書又不長腳,以後有的是機會去翻,書別白看。”
老夫子拍了拍青衣小童的腦袋,安慰之後,亦有一語勸誡:“道不遠人,苦別白吃。”
陳靈均懵懵懂懂,不管了,聽了記住再說。
老夫子和顏悅色道:“景清,你自個兒忙去吧,不用幫忙帶路了。”
陳靈均壯起膽子問道:“要不要去騎龍巷喝個酒?我家老爺不在家,我可以幫他多喝幾碗。”
老夫子搖搖頭,笑道:“這會兒喝酒就不像話嘍,得了便宜就別賣乖,這可是個好習慣。放心,不是說你,是說我們儒家。”
陳靈均後退幾步,與至聖先師畢恭畢敬作揖拜別,這才轉身跑下石拱橋,沒敢直接御風返回落魄山,打算去騎龍巷找賈老哥喝頓酒,壓壓驚。
青衣小童已經跑遠了,突然停步,轉身大聲喊道:“至聖先師,我覺得還是你最厲害,怎麼個厲害,我是不懂的,反正就是……這個!”
陳靈均高高舉起手臂,豎起大拇指。
老夫子笑著點頭,也很寬慰人心嘛。
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我輩亦是路上行人。悲哉苦哉?奇哉幸哉。
渡水看花,不知不覺到君家,就此別過,在此謝過。
老夫子與整個天地作揖致謝,亦是道別。
修道之士,御風而行,高奔日月,泠然善也。
人間世人,因為不自由,所以追求自由,希望下一次滄海桑田,苦海可變福田,人人豐衣足食,處處書聲琅琅。
最後至聖先師看了眼小鎮那條陋巷。
小小的巷弄,名叫泥瓶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從淤泥里開出一朵花,自心作瓶,花開瓶外,不是很美好嗎?
相信游歷小鎮的其余兩位,也是這般看待那個一的。
老觀主斜瞥一眼山道,好似一朵白雲從青山中飄落。
除此之外,還有個走樁下山的女武夫,那位白衣少年就在女子身邊轉圈圈,呼呼喝喝,蹦蹦跳跳,耍著拙劣拳腳把式。
女子約莫是習慣了,對他的鬧騰搗亂視而不見,自顧自下山,走樁遞拳。
老觀主懶得再看那個崔東山,伸手一抓,手中多出兩物,一把龍泉劍宗鑄造的信物符劍,還有一塊大驪刑部頒發的平安無事牌,雕工質朴。
至於兩物到底從何而來,天曉得。
老觀主雙指拈住符劍,眯眼端詳一番,果不其然,蘊藏著一門不易察覺的遠古劍訣,境界不夠的練氣士,注定看不穿此事。
至於何謂境界不夠,當然是十四境練氣士和飛升境劍修之下皆不夠。
只是劍訣不全,想要補齊,約莫還需要五六把符劍。
不過不管符劍售價如何,只要有人有心做成此事,就是一筆大賺特賺的買賣。
怎麼個賺?
光憑這道劍訣,就足可讓一座劍道宗門在浩然天下站穩腳跟了,關鍵是此訣門檻低,只要是個劍修,不用資質太好,都可以按部就班煉劍修行,若說殺力,劍訣品秩不高,可就是修行起來安穩。
所以越是大宗門,越看重這類道訣。
崔東山在台階那邊,一個高高躍起,側身翻轉,在桌旁落定,抖了抖兩只雪白大袖,仰頭遠望,自顧自說道:“即將入秋啦,秋風清秋月明,秋雲滿太虛,秋水落芙蕖。”
然後才收起視线,先看了眼老廚子,再望向那個並不陌生的老觀主,崔東山嬉皮笑臉道:“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浩浩泱泱,難辨牛馬。”
朱斂一笑置之,這話說得是有點欠揍。
崔東山背對著桌子,一屁股坐在長凳上,抬腳轉身,問道:“山水迢迢,雲深路僻,老道長高駕何來?”
朱斂嗑著瓜子,擱自己是老觀主,估計就要動手打人了。
老觀主冷笑道:“世間萬物皆有裂縫,眼中所見一切,哪怕是那神靈的金身,不可見的,即便是修道之人的道心,都不是什麼完整的一,這條道路,走不通的。任你崔瀺究其一生,還是找不到的,注定徒勞無功,不然三教祖師何必來此。道與一,若是某個實物,豈不是要再天翻地覆一場。”
崔東山埋怨道:“什麼王八蛋,我是東山啊。”
老觀主呵呵一笑。
崔東山搖晃肩頭,念念有詞,如學塾夫子之乎者也:“再說了,道近乎哉?眼不見睫。道遠乎哉?觸事即真。聖近乎哉?參商出沒。聖遠乎哉?了悟即神。”
老觀主微笑道:“當年崔瀺,好歹還有個讀書人的樣子,要是當年你就是這副德行,貧道可以保證,你小子走不出藕花福地。”
崔東山拍了拍胸膛,好似後怕不已。
老觀主喝了一口茶水:“會當媳婦的兩邊瞞,不會當媳婦的兩邊傳,其實兩頭瞞往往兩頭難。”
拿袖子擦了擦桌面,崔東山白眼道:“前輩這話,可就說得不妥帖了。”
老觀主見這家伙繼續裝傻,轉頭看了眼那個沿著台階走樁的女子,問道:“這就是你挑中的拳法弟子?”
朱斂笑道:“不是記名弟子。何況我那點三腳貓功夫,女子學了,不美。”
老觀主不以為然,對那個女子問道:“你叫岑鴛機?”
岑,山小而高也,形容山石崖岸峻極之貌。鴛機,即是世俗的織錦機,詩家則有移花影之喻。
陸沉行事一貫隨心所欲,最喜歡放長线釣大魚,釣不著也無所謂。
騎龍巷的石柔也好,那件來歷七彎八拐的法袍金醴也罷,就像只求一個願者上鈎,根本不在乎那些斷去的魚线、吃餌而走的游魚。
岑鴛機剛剛在山門口停步,她知道輕重,一個能讓朱老先生和崔東山都主動下山見面的老道士,一定不簡單。
不知為何,老道人神色如常,但是岑鴛機就覺得壓力極大,抱拳道:“回道長的話,晚輩名字確是岑鴛機。”
朱斂笑道:“嚇唬一個小姑娘做什麼。”
崔東山招招手:“小米粒,來點瓜子嗑嗑。”
黑衣小姑娘立即從竹椅上邊起身,小跑到桌子這邊,從棉布挎包里掏出所有剩下的瓜子,倒是不多,道:“給,小師兄。”
崔東山一拍腦袋,問道:“右護法,就這麼點啊?”
小米粒聽到大白鵝換了個稱呼,板著臉,又從袖兜里邊掏出了一大把。
崔東山點點頭:“右護法出手闊綽!”
老觀主又對朱斂問道:“劍法一途呢?打算從劍氣長城的劍仙坯子里邊挑選?”
同樣是老觀主,大玄都觀的那位孫道長慫恿陸沉散道,轉去投胎當個劍修,不全是玩笑,而是有的放矢。
當然,就孫懷中那脾氣,陸沉要真跑去當劍修了,估計不管如何,都要讓陸沉變成玄都觀輩分最低的小道童,每天喊自己幾聲老祖宗,不然就吊在桃樹上打。
朱斂笑道:“我哪有臉教別人劍術,不是誤人子弟是什麼。”
浩然劍修,隨便丟一個到藕花福地,都是當之無愧的劍仙。
藕花福地歷史上,也有些地仙事跡,只是無據可查,朱斂在術算賬簿、營造之外,還曾經著手編撰過官家史書,見過不少不入流的稗官野史,什麼地仙之流,口吐劍丸,白光一閃,千里取人首級。
不過在家鄉那邊,哪怕是這些志怪傳聞,提及劍仙一脈,也沒什麼好話,什麼非是長生久視之大道,只是旁門法術,飛劍之術難以成就大道。
可是朱斂的武學之路,歸根結底,還真就是從書中而來,這一點,跟浩然天下的讀書人賈生如出一轍,都是無師自通,單憑讀書,自學成才,只不過一個是修行,一個是習武。
朱斂最早走江湖的時候,也曾佩劍遠游,走遍名山大川,訪仙問道。
朱斂想要知道天下的邊界所在。若真是天圓地方,天地再廣袤,終究有個盡頭吧?
小米粒沒走遠,滿臉震驚,轉頭問道:“老廚子還會耍劍哩?”
朱斂擺手道:“會什麼劍術,別聽這類客人說的客套話,比起裴錢的瘋魔劍法,差遠了。”
崔東山低頭嗑瓜子,道:“小米粒,你不知道了吧,咱們這位老廚子,在灶房摘掉圍裙後,出門在外,耍起劍來蠻好看的,在藕花福地的江湖上,大名鼎鼎,都說貴公子朱斂的長劍之上,纏繞的都是女子的旖旎情思,余米都比不了。不知多少江湖女俠,一輩子轉去痴心練劍,就是為了能與老廚子比試一場。”
崔瀺曾經跟隨老秀才游歷過藕花福地,對那邊的風土人情了解頗多。
小米粒趕緊一手捂住肚子,使勁抿嘴,含糊不清道:“老廚子還當過貴公子嘞。”
朱斂笑道:“好漢不提當年勇,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江湖事嘛,都是以訛傳訛,越傳越玄乎。”
小米粒重重點頭,嗯了一聲,轉身跑回竹椅,咧嘴而笑,就是照顧老廚子的面兒,沒笑出聲。
騎龍巷的那條左護法,剛剛溜達到山門口這邊,抬頭遠遠瞧了眼老道長,它立即掉頭就跑了。
老觀主看了眼,可惜了,不知為何,那個阮秀改變了主意,否則差點就應了那句老話:蟾蜍吞月,天狗食月。
隋右邊從別處山頭御劍而來,她沒有落座,只是想要與這位藕花福地的老天爺,問一問自己先生的事情。
老觀主對她說道:“告訴陳平安一聲,桐葉洲金頂觀的存亡,貧道無所謂,但是必須留著那個邵淵然。至於那個倪元簪,你只需與他說一聲,送出那枚金丹,他就是自由身了。”
金頂觀的法統,出自道家“結草為樓,觀星望氣”一脈的樓觀派。至於雲窟福地撐篙的倪元簪,正是被老觀主丟出福地的一顆棋子。
隋右邊欲言又止,可到最後,還是一言不發。
朱斂幫忙解圍,主動點頭攬事道:“這有何難,捎話而已。”
老觀主問道:“那個玉圭宗的姜尚真,怎麼沒在山上?”
朱斂笑道:“本來應該留在山上,一起去往桐葉洲,只是我們那位周首席越想越氣,就偷跑去蠻荒天下了。”
隋右邊得了朱斂的眼色,默默離開,去了小米粒那邊。
老觀主環顧四周,嘆了口氣:“有了散道一事,不承想到最後,還是你們儒家最占便宜。余斗估計會氣得不輕。”
一旦三教祖師同時散道,書院、寺廟、道觀處處皆得,那麼相對最為容納別教學問的浩然天下,當然得到的饋贈最多。
散道的同時,三教祖師會聯袂走一趟舊天庭遺址,這個天大的問題,當然不會留給他人。
崔東山笑道:“氣死道老二最好。”
老觀主輕聲道:“只說一事,當人間再無十五境,已經是十四境的,會如何看待有機會成為十四境的修士?”
崔東山點點頭:“是要變天了,有壞有好吧,反正我如今更傾向於後者。”
老觀主問道:“如今?為何?”
崔東山一本正經道:“有我先生在啊。”
老觀主轉去望向那個陸沉五夢七相之一,甚至可能是之二的朱斂。
朱斂笑道:“前輩看我做什麼,我又沒有我家公子英俊。”
老觀主呵呵笑道:“真是個好地方,貧道不虛此行,門風極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