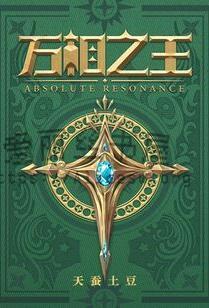婆娑洲,大海之濱的一座尋常山頭,名副其實的結茅而已,勉強算是有了個修行之地,哪怕是下五境的山澤野修,其實都不會如此簡陋。
相鄰的三間茅屋,卻住著三位上五境:陸芝、邵雲岩、酡顏夫人。
前兩位還是劍仙。
桐葉洲太平山有人祭劍之後,陸芝起身走出茅屋,眯眼遠眺東南。
在邵雲岩和酡顏夫人紛紛走出屋子後,陸芝說道:“隱官回了。”
酡顏夫人臉色僵硬,邵雲岩大笑不已。
容貌俊美的老劍仙齊廷濟選擇開宗立派的地點出人意料,既不是山河最為遼闊的中土神洲,也不是財神爺劉氏所在的皚皚洲,而是再無醇儒的婆娑洲。
齊廷濟經常會來與陸芝閒聊幾句,也不藏掖,明擺著是希望陸芝擔任首席供奉,哪怕退一步,當個客卿都無妨。
陸芝自然不願意當那供奉,至於沒什麼約束的客卿,其實在兩可之間。
終究雙方都是劍氣長城的劍修,齊廷濟在浩然天下的一次次出劍也確實不曾讓人失望,尤其是陳淳安離開婆娑洲去往大海的最後一程,還是齊廷濟獨自一人為那位醇儒仗劍護道。
最終陳淳安成功將大髯劍客劉叉留在了浩然天下,使得那只王座大妖未能返回蠻荒天下。
但是浩然天下,尤其是中土神洲,依舊對這位莫名其妙苟活、莫名其妙赴死的醇儒非議極多,覺得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連一只飛升境大妖都不曾打殺、肩挑日月如同擺設的陳淳安在該死的時候不死,在能活的時候不活,不會雪中送炭,偏要錦上添花,簡直就是惜命怕死到了一定境界,愛惜羽毛更是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一場大戰,除了勉強算是護住了婆娑洲那一洲山河外,再無建樹……如今的蠻荒天下,哪怕多出個劉叉,又能如何?
如果不是齊廷濟在中土神洲為此出劍一次,只會更加怨聲載道。
被齊廷濟問劍之人在挨了一劍之後依舊骨頭極硬,說就算劉叉在蠻荒天下收攏氣運躋身了十四境又如何,那蕭𢙏不一樣是十四境劍修,不一樣被左右趕去了天外戰場,至今未歸,始終去不得蠻荒天下。
就算多出個劉叉,齊廷濟真有本事,就重返劍氣長城,再在城頭上刻個大字……所以懶得多說的齊廷濟就又賞了那修士一劍。
一個玉璞境,齊廷濟卻要遞兩劍,只能重傷,還不能殺,這讓齊廷濟返回婆娑洲找到陸芝後,破天荒沒有勸她加入自己宗門,而只是默默喝酒。
如果換成陸芝,大概會一劍砍死那個玉璞境,然後就干脆返回劍氣長城遺址了。
能讓陸芝在浩然天下願意多聊幾句的人其實就倆,也就是當下她身邊這兩位。
其中酡顏夫人說話一貫拐彎抹角,大抵意思還是勸陸芝答應下來,當個客卿而已,又是同鄉,於情於理都不該拒絕。
邵雲岩卻堅決反對,有酡顏夫人在,邵雲岩也不敢把話說得太過直接,擔心自己獨自出門的時候,一個不小心就莫名其妙挨一劍。
所以邵雲岩只說齊老劍仙劍術卓絕,自然不需要陸芝錦上添花,當什麼客卿,若是當那首席供奉,倒是可以考慮。
“齊廷濟說得對,他所在宗門得有個不太講規矩的劍仙,我會答應他擔任客卿。”陸芝說道,“邵雲岩,你帶著酡顏一起游歷中土神洲,再繞去俱蘆洲,最後才去見隱官。”
邵雲岩點點頭:“如此最好,不然意圖就太明顯了。”
至於陸芝當不當那客卿,邵雲岩其實並沒有太多想法,先前只不過是看不慣酡顏夫人的做派。
酡顏夫人試探性說道:“陸先生,我還是留在這里陪你好了?”
陸芝淡然道:“你們立即動身。”
酡顏夫人哀怨不已。她是真不願意見那隱官大人啊,上次是少了一座梅花園子,這次呢?
邵雲岩深吸一口氣。
既然他們知道隱官終於重返浩然天下,那麼皚皚洲謝松花、金甲洲宋聘、俱蘆洲酈采……所有走過劍氣長城的浩然劍仙,憑借太平山那場祭劍,就都該知道此事了。
皚皚洲。
早年突然就答應當了劉氏供奉的女劍仙謝松花從劉氏祖師堂議完事後返回雷公廟。
反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就能白拿一大筆錢,不拿白不拿。
謝松花甚至專門提醒劉氏,但凡有議事,甭管大小,千萬記得飛劍傳信,只要她在皚皚洲,就一定趕到。
她好歹是個正兒八經的供奉,得出力,哪怕沒機會出力,也該建言獻策。
按照一般的山上宗門,早腹誹不已了,但是皚皚洲劉氏,議事無論大小,還真就都會飛劍傳信謝松花,次次變著法子給錢,多次過後,別說兩位嫡傳弟子練劍所需要的神仙錢,就連謝松花自己那份都不缺了。
謝松花難免有些過意不去,這次離開劉氏祖師堂前,就問劉聚寶,劉氏到底有沒有那種想砍又不方便砍的仇家,她可以代勞,悄悄往返一趟就是了,劉聚寶卻說沒有。
如今師徒三人差不多是把雷公廟當半個家了,沛阿香也根本無所謂,不冷清,又不至於太喧嘩,其實還不錯。
就是那個女劍仙的有些話讓人扛不住,什麼阿香你長得這麼俊俏,不找個男人真是可惜了。
今天謝松花御劍落在了雷公廟大門外,兩個弟子正坐在台階上翹首以盼呢。
沛阿香一見到謝松花,就立即起身返回廟內,謝松花玩笑道:“想不想師父幫你們找個師娘啊?”
朝暮恍然道:“原來師父不是女子啊?”
舉形一臉無奈:“原來你是個傻子啊?”
謝松花不再開玩笑,以心聲言語道:“師父帶你們走趟寶瓶洲。”
竹海洞天,青神山。
純青趴在欄杆上,雙手托腮。
一名女子鬢發絕青,赤足行走,看著那個神游萬里的唯一弟子,會心一笑。
曾經她也這般百無聊賴地趴在青竹欄杆上發呆,然後就蹦出一個更無聊的無賴,把腦袋擱在欄杆上,轉頭側臉,眯起眼,一臉嚴肅,目不轉睛,一開口就不是個正經人:“這位姐姐,小心壓塌了欄杆啊。不過沒事,青神山如果找你賠錢,只管報上我的名字。記住了啊,我叫阿良,善良的良!”
等到她站起身,他也站起身,斜靠欄杆,笑臉燦爛:“你該不會就是那位青神山夫人吧,不然姐姐長得這麼好看,我要是那位山神娘娘,肯定嫉妒得抓心撓肝,容不得你當鄰居啊,每天大半夜都要蹲你床頭,拿竹簽戳你的臉。倒也不會真戳,畢竟,哪怕是女子,瞧見了你,一樣都會喜歡的……我覺得你多半不是那位山神娘娘了,知道原因嗎?哈哈,很簡單,我與她其實關系……嘿嘿,你懂的。”那漢子抬起雙手,擠眉弄眼,拇指對戳,“這個,老相好。”
她當時問他:“你找死?”
那漢子竟然滿臉靦腆羞赧地瞥了眼廊道一側的屋子,好像不敢正眼看她,微微低頭,似笑非笑,欲語還休。
最後,那人御風逃竄時,抱著屁股。
純青回過神,抬頭問道:“師父,那個阿良怎麼莫名其妙就去了西方佛國?”
她微笑道:“當了和尚才好。”
俱蘆洲,彩雀府,山腳的茶鋪。
掌律女祖師武峮對面有一個姿容俊美的白袍男子,姿態慵懶,坐沒坐相,幾乎是趴在桌上。
武峮無奈道:“余米,你能不能收斂點?”
余米打了個呵欠,委屈道:“武峮妹妹,咋個了嘛,我一句話沒說,一個斜眼都沒有,就在山上散個步,也不行啊?”
武峮遞給他一杯茶,自己舉起茶杯又放下,伸出手指揉了揉眉心:“你就是個禍害,再這麼下去,我們彩雀府的名聲就算毀了。就算你不招惹她們,可那些涉世未深的小姑娘,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你又是個金丹劍修……”
說到這里,大概武峮也覺得怨不得這個來自落魄山的余米。
這家伙確實太過好看了些,就算不招惹誰,可只要一個稀松平常的臨崖遠眺,或是大雪賞景,一襲白衣手持綠竹杖,又或是大雨滂沱,撐傘緩行,手拈桃枝……他娘的,余米沒說話也等於說話了啊,關鍵還是那種無聲勝有聲……
余米更委屈,趴在桌上,用手指撚動茶杯:“都說你們俱蘆洲劍修如雲,劍仙遍地都是,一抓一大把,我才斗膽用了個金丹劍修的名頭,早知道就不打腫臉充胖子了,老老實實當我的觀海境練氣士。”
余米到了彩雀府之後,沒有出手,所以武峮到現在為止,還是無法確定余米的真實境界。
不過她可以確定對方不是什麼觀海境,極有可能是一個深藏不露的元嬰劍修。
余米好像對那個趙鸞很在意,卻不是那種男女之情,反而就像一位長輩在為晚輩護道。
如此一來,府主的得意弟子柳瑰寶好像就有些不得勁兒了。
柳瑰寶與趙鸞原本關系極好,如今就有些小小的別扭了。
柳瑰寶冷著臉,從山下走來茶鋪,將一封密信放在桌上。
余米眼睛一亮,雙手合十,念念有詞,然後才拆開密信,差點當場熱淚盈眶,一個沒忍住,轉頭對柳瑰寶感激涕零道:“柳姑娘,大恩大德無以為報,以後誰敢欺負你——孫府主除外,武峮姐姐除外,俱蘆洲所有地仙除外——你大大方方與我說一聲,我保管打得對方……”
柳瑰寶就只是直愣愣看著他。最欠揍的,不就是你自己嗎?
余米知道這姑娘眼中的答案,卻依舊裝傻扮痴,只是不再言語,小心翼翼收起那封來自披雲山的密信,站起身,深吸一口氣:總算可以回了。
這余米不是旁人,正是用化名在彩雀府擔任掛名客卿多年的米裕。
突然有三名劍修御劍而來,武峮和柳瑰寶趕緊起身。
來人竟是女宗主酈采,身邊跟著她的兩個嫡傳——極其年輕的金丹境劍修陳李以及只好相對年輕的龍門境劍修高幼清。
陳李以心聲笑道:“這不是米大劍仙嗎,風采更勝往昔啊,都快閃瞎我的一雙狗眼了。”
聽聽,多熟悉,不愧是劍氣長城的小隱官,你都沒辦法回罵。
米裕還真就喜歡這些,太久違的感覺了。
酈采與那兩個彩雀府女修打完招呼,聊完客套話,與米裕以心聲說道:“我不去寶瓶洲,就有勞米劍仙護送他們倆去落魄山了。”
米裕說道:“我得先去趟雲上城,帶上趙樹下。”
酈采擺擺手:“你就算帶上彩雀府所有女修,我也不管你。但是事先說好,敢勾搭幼清,我砍死你。哪怕你不勾搭,只要幼清對你有想法,我一樣砍死你。”
米裕笑道:“酈劍仙有所不知,有些姑娘,我一看她們看我的眼神,就知道她們是不是對我有意思了。”
酈采嘖嘖道:“你這死不要臉說假正經話的樣子,是你那把飛劍的本命神通嗎?”
米裕微笑點頭,然後問道:“真不見見那位周供奉?”
酈采大罵道:“死沒良心的王八蛋,他滾來見我才對。”
米裕使勁點頭:“在理!”
寶瓶洲。
大驪王朝的新科榜眼,一個姓曹的翰林編修突然告病,悄然離開京城,在一座仙家渡口乘坐渡船去往牛角山渡口。
除此之外,一個個落魄山譜牒嫡傳、供奉、客卿,以及與落魄山交好的觀禮之人都開始紛紛啟程。
雲舟渡船上,姜尚真坐在欄杆上笑道:“還以為你會連打兩場架。”
陳平安搖搖頭。
當時在齊瀆祠廟內,他與王朱只是隔著窗戶,屋里屋外遠遠閒聊了兩句。
王朱問了個問題:“為何解契?”
陳平安反問一個問題:“你想好了,真要當這齊瀆公?”
結果雙方都沒有給出答案。王朱重回大瀆之水,繼續閉關去。
雲舟渡船緩緩停靠在牛角山渡口,但是陳平安已提早離船,落在了一條山間小路上,最終走到了那兩座小墳頭前,跪地磕頭,然後取出一只只小袋子,開始為墳頭添土。
已經不惑之年的青衫男人在墳前倒了一壺酒後,單膝跪地,彎著腰,低著頭,在心中默默言語。
最後男人微微顫聲,皺著臉,輕聲笑道:“爹,娘,不要擔心啊,除了離家有些久,在外邊這些年,其實都很好。”
陳平安在原地沉默許久,等到他起身緩緩下山,已經是暮色四合。
他稍稍繞路,去了趟曾經的神仙墳,遠遠看了一眼,等再走路回到泥瓶巷一端時,已經是深夜時分。
掏出一串鑰匙,打開院門,再打開屋門,抬頭看了眼門上貼著的“春”字,進入屋內,陳平安點燃桌上一盞燈火,趴在桌上,原本想要守夜,卻一個不小心,就那麼熟睡過去。
都不知道睡了幾天幾夜,等到這天的拂曉時分,陳平安坐起身,雖然有些睡眼惺忪,不過還是緩緩起身,發現門外只有一個裴錢在。
裴錢笑道:“我攔著暖樹姐姐和小米粒,讓她們在霽色峰山腳等著師父呢。”
陳平安笑著點點頭:“是今天?”
裴錢使勁點頭:“都到了,連小師兄都趕來了,這會兒估計還趴在地上打盹呢。”
如果不是魏檗施展了山水禁制,估計這會兒,整個北岳地界都察覺到自家霽色峰的異樣氣象了。
陳平安關好屋門和院門,站在泥瓶巷內,說道:“跟上。”
一襲青衫扶搖而起,一襲黑衣尾隨其後,飄然落在霽色峰的山門口。
從蓮藕福地返回的暖樹施了個萬福,喊了聲“老爺”。周米粒一個咧嘴,笑得簸箕大了,怎麼都合不攏。
陳平安眯眼而笑,一手一個小腦袋,輕輕揉了揉,微笑道:“走,上山去。”
當頭別玉簪的一襲青衫現身台階頂部,才發現霽色峰祖師堂外竟然站著數十人,有自己的學生、弟子,落魄山供奉、客卿,以及各自的再傳弟子,當然,還有朋友們。
比起第一次,今天的霽色峰祖師堂多了太多人。
陳平安緩緩向前,最終停下腳步,一時間有些神色恍惚。
裴錢帶著暖樹和周米粒快步向前,走向人群,再一起轉身面朝陳平安。
山風陣陣拂過,一襲青衫背劍,大袖飄搖。
面對著眼前眾人,山主陳平安猛然抱拳致禮,對面眾人肅然回禮。
陳平安率先跨過祖師堂大門。
霽色峰祖師堂內懸三幅掛像:文聖、齊靜春、崔誠。
一襲青衫站在最前方,雙手持香。
陳平安身後,是他的學生崔東山,弟子裴錢,學生曹晴朗。
落魄山掌律長命,賬房韋文龍。
山巔境武夫朱斂,遠游境盧白象,金丹境瓶頸劍修隋右邊,遠游境魏羨。
陳靈均,陳如初,石柔。
落魄山護山供奉、右護法周米粒。
蔣去,張嘉貞。趙樹下,趙鸞。
岑鴛機,元寶,元來。真名周俊臣的阿瞞。
仙人境劍修姜尚真。遠游境巔峰種秋。玉璞境瓶頸劍修米裕。元嬰劍修崔嵬。
記名供奉:
目盲道人賈晟,趙登高,田酒兒。披麻宗元嬰修士杜文思,金丹劍修龐蘭溪。
狐國之主沛湘,元嬰水蛟泓下,棋墩山雲子。
九個劍仙坯子:何辜,於斜回,程朝露,納蘭玉牒,姚小妍,虞青章,賀鄉亭,白玄,孫春王。
觀禮之人:
劉羨陽。李二,李柳,韓澄江。林守一,於祿,謝謝,董水井。
北岳山君魏檗。
太徽劍宗劉景龍,弟子白首。
龍泉劍宗開山大弟子董谷。
鰲魚背劉重潤。
老龍城范二,桂夫人、弟子金粟,孫嘉樹。
浮萍劍湖嫡傳陳李、高幼清。
春幡齋劍仙邵雲岩,倒懸山梅花園子酡顏夫人。
書簡湖真境宗李芙蕖、周采真。
披麻宗財神爺韋雨松。
彩雀府府主孫清,弟子柳瑰寶。
雲上城徐杏酒,記名供奉桓雲。
皚皚洲劍仙謝松花,弟子舉形、朝暮。
風雪廟大劍仙魏晉。
指玄峰袁靈殿。
金烏宮元嬰劍修柳質清。
中土神洲郁狷夫,邵元王朝林君璧。
今天的霽色峰祖師堂內,劍修極多,武夫極多,而那個站在最前方的山主,遠游歸來的陳平安,既是劍仙,也是止境武夫。
既是寶瓶洲落魄山的山主,也是曾經劍氣長城的隱官,更是浩然天下文聖一脈的關門弟子。
很快,整個浩然天下就會知道,那個隱官陳十一,叫陳平安。
眾人跟隨山主陳平安敬香拜掛像,作揖三拜,然後各自按照禮敬順序,插入香爐。
陳平安作為東道主,還需要與每一位觀禮之人還禮致謝,光是此事,就耗去了足足三刻鍾。
三幅掛像下,一桌兩椅,一張空懸,一張屬於陳平安。
陳平安始終沒有落座,一襲青衫的男子背朝掛像,面朝祖師堂大門,與上香的眾人一一還禮。
三十六位觀禮客人,要麼與陳平安微笑點頭致意,哪怕言語也極為言簡意賅,最多輕輕道賀一聲,沒有誰會在這種關頭與他過多寒暄客套。
在譜牒上姓名為陳如初的暖樹因為擔任山水唱誦的香使女官,所以得以站在山主陳平安身邊。
她需要喊出觀禮上香客人的名字及宗門山頭,最後跟隨山主一起與那位客人還禮。
陳平安率先落座,主客雙方隨之紛紛落座,井然有序。
今天霽色峰祖師堂的座椅分為三種,第一種當然是有資格參與霽色峰祖師堂議事的,屬於在落魄山祖師堂已經擁有了一張“雷打不動”的座椅,除了陳平安,還有崔東山、裴錢、曹晴朗。
此外,朱斂、周米粒,隋右邊、盧白象、魏羨,周肥、種秋、鄭大風,陳靈均、陳如初也在此列。
當然,這類椅子會在今天增添幾把,例如長命、韋文龍,米裕、崔嵬、沛湘、泓下。
第二種是雖然列入祖師堂山水譜牒,但是按照輩分屬於再傳的嫡傳弟子,例如岑鴛機、元寶、元來等人。
再就是一般的供奉、客卿,例如騎龍巷賈晟師徒三人以及披麻宗杜文思、龐蘭溪等人。
而記名客卿,按照山上舊例,可以算是半個自家人。
只是在落魄山這邊,舊例之外又有新規矩,半個就是一個了。
最後便是那三十六位來自浩然各洲的觀禮客人。
後兩種椅子,只會在今天這樣的日子搬出,供人落座。
陳平安獨自一人坐在掛像下的椅子上,望向剛剛從中土神洲趕回寶瓶洲的學生崔東山,點點頭。
崔東山破天荒將一襲雪白法袍換成了儒士青衫,站起身,輕聲道:“裴錢,曹晴朗。”
裴錢和曹晴朗同時起身。
陳平安一樣站起身,崔東山將從文廟取來的玉牒、金書,分別遞給裴錢和曹晴朗,剛要挪步前行,將一件從文廟請出的禮器交與先生,陳平安卻輕輕搖頭,只是從袖中取出了一摞書。
崔東山會心一笑,也就無所謂這點規矩禮儀了,霽色峰祖師堂內都是自家人,沒人會去文廟碎嘴。
金書玉牒,投書於天,化作一股清氣,埋牒在地,與山水氣運相融,分別用以昭告天地、一洲山河。
中土文廟贈送一件禮器,供奉在宗門祖師堂。陳平安也沒有壞了這個規矩,只是卻添了自家先生的著作,一並供奉起來。
曹晴朗從崔東山手中接過金書,朗聲誦讀內容。不過百余字,都是照搬一套古老禮制的文字。
裴錢接過玉牒後,有樣學樣,讀了遍玉牒上邊的文字內容。
無論是落魄山譜牒還是觀禮之人,都早已再次起身,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繁文縟節。
宣讀完畢,曹晴朗和裴錢並肩走出祖師堂,一個御風往高處去,一個去往山腳。
片刻後,兩人在大門外碰頭,一起返回祖師堂,先後說了一句“禮畢”,而後陳平安和崔東山分別將一摞書和文廟禮器擱放在桌子上,陳如初便嗓音清脆道:“禮成!”
寶瓶洲落魄山自即刻起,就已經躋身浩然宗門之列。
今天的祖師堂聚會,所有觀禮之人所觀之禮,當然就是落魄山的提升宗門之浩然頭等大禮。
浩然天下的仙府山頭想要躋身宗門,如果沒有上宗的運作,一般流程,就是由祖師堂所在王朝的皇帝陛下先向中土文廟舉薦,提升為宗門候補,在坐鎮一洲天幕的某位陪祀聖賢認可之後,再交由中土文廟審查、勘驗。
文廟正副三教主、三大學宮祭酒負責一同批復此事,最終交由禮聖決斷。
七位儒家聖賢,只要其中有一人不點頭,就休想躋身宗門。
當然,歷史上也曾有六人都已點頭,唯獨禮聖不點頭的情況,只不過這種情況在萬年歷史上只出現過兩次。
書簡湖真境宗因為上宗是桐葉洲玉圭宗,又有荀淵的巧妙籌劃,就其實與大驪宋氏皇帝關系不大。
這是有些壞規矩的,所以姜尚真和韋瀅先後兩任下宗宗主,無論個人的性情、境界、手腕如何,在書簡湖當家做主時都顯得極為隱忍,重視與大驪鐵騎的關系修繕,力求入鄉隨俗,將功補過。
而阮邛的龍泉劍宗以及昔年的宗門候補正陽山和清風城,三者就都需要大驪王朝皇帝宋和的舉薦,最終也都順利成了寶瓶洲的宗門。
據說正陽山甚至已經著手籌備下宗多年,只是中岳山君晉青對此事始終態度模糊,大驪宋氏廟堂那邊,宋和與宋睦之間也好像有些異議。
宋和的意思,是正陽山的戰功雖然不太夠,但既然正陽山已經借來包括神誥宗、雲林姜氏和老龍城在內的眾多勢力,就不妨順水推舟,再扶持正陽山一把。
但是本該與正陽山關系更為親近的宋睦卻說正陽山哪怕縫縫補補,在大驪山水功勞簿上湊齊了足夠的戰功,依舊缺了一大筆功德,哪怕宋氏舉薦給了中土文廟,一樣極有可能被打回,批復以“再議”二字。
今時不同往日,已經是太平盛世了,不應該將正陽山喂得太飽,容易讓其余宗門候補山頭心懷怨懟,認為大驪王朝太過偏心。
宋睦在寄往京城御書房的那封密信的末尾寫了一句話:除非正陽山的劍修敢去蠻荒天下開疆拓土,憑此戰功積攢功德。
不管如何,落魄山終究是成了“宗”字頭山門。
就當下這一刻而言,落魄山還會是浩然天下最“年輕”的宗門。
陳平安輕輕松了口氣,抬手虛按兩下,笑道:“都坐都坐,今天都是自家人,接下來我們都隨意些,只要別袒胸露腹,或是脫鞋子盤腿坐,就沒什麼講究了。”
在所有人都落座後,陳平安才坐下,笑望向落魄山右護法,輕聲道:“米粒,端茶。”
“得令!”周米粒左右肩頭一晃,趕緊滑下有些顯大的椅子,挺直胸膛。
小姑娘滿臉漲紅:總算輪到自己露面了!
她今天可是又多出了一個官職,茶水官!
負責給祖師堂所有人端茶送水,多有面兒!
暖樹姐姐和景清都只是幫忙打下手的茶水副使嘞。
周米粒這樣想著,他們開始給所有人分發茶水,陳靈均負責從方寸物當中取出茶水,一手托一個茶碗,周米粒和陳如初負責遞茶給人。
劉羨陽從周米粒手中接過茶水的時候,笑呵呵道:“啞巴湖的大水怪,名氣真要比天大了。”
周米粒瞪了眼劉羨陽:我又不是那種計較虛名的。
只是小姑娘一個沒忍住,滿臉笑容。
劉羨陽伸手去揉她的腦袋,周米粒趕緊拿腦袋撞開,快步去給下一位客人恭謹端茶。
陳平安只是象征性喝了一口茶水,就放下茶杯。
落魄山的山水譜牒抬升一個大台階,從原本的大驪禮部歸檔,變成了被中土文廟記錄在冊,顯然有意無意繞過了大驪。
沒有向大驪宋氏討要那份舉薦,落魄山只是飛劍傳信京城禮部,算是與大驪朝廷說了有這麼件事,打過招呼而已。
觀禮一事,陳平安其實只能算不陌生,因為只有一次,就是他早年游歷青鸞國,路過青要山的金桂觀時,那會兒身為金丹地仙的老觀主張果要收取九名譜牒弟子。
而登山之人,除了山澤野修,山上的譜牒修士觀禮次數本都不該如此少。
相較於金桂觀,霽色峰祖師堂哪怕是躋身“宗”字頭這樣的大典,都辦得簡單得不能再簡單。
同樣是躋身宗門的儀式,清風城和正陽山幾乎都是從早辦到晚,其間只是“請出”金書玉牒和文廟禮器這一件事聽說就耗費了兩個時辰。
那個祖師堂唱誦官每每還會用上類似道門青詞寶誥的拖腔,極緩極慢,而那不過百余字的金書玉牒在禮官捧出誦讀之前,都會有各類興師動眾的慶賀儀式作為鋪墊。
例如正陽山劍修的聯袂祭劍,用以祭奠祖師堂歷代祖師,還要營造出六到九種不等的祥瑞氣象,再通過山水陣法以及開啟的鏡花水月傳遍一洲山上仙家。
此外,光是提供給觀禮貴客的仙家茶水、山上瓜果,以及沿途栽種奇花異草,仙鶴靈禽齊鳴在天,祖師堂禮制處都精心籌備了月余光陰,為此消耗的神仙錢更是以谷雨錢計算。
而落魄山這邊,就是清茶一碗待客而已。
劉羨陽莫名其妙跌了一境,但是無論本命飛劍、體魄神魂、氣府經脈,都沒有任何損傷,就只是一粒元嬰,有等於無,極其古怪,阮邛才會答應讓他留在鐵匠鋪子養傷。
他笑眯眯地望著陳平安,每次視线交會,陳平安都擺出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表情。
北岳山君魏檗是寶瓶洲歷史上第一位上五境山君,如今又是首位等同於仙人境的大山君,所以前些年披雲山又辦了一場名正言順的夜游宴。
大戰落幕後,各有戰功撈到手,大驪多有封賞,所以各路譜牒仙師、山水神祇原本干癟的錢袋子又鼓了起來,北岳地界不至於砸鍋賣鐵,哀鴻一片。
太徽劍宗上任宗主韓槐子戰死於劍氣長城,掌律老祖黃童戰死在寶瓶洲中部戰場,以至於如今整座宗門就只有宗主劉景龍這一位上五境劍仙,他的弟子白首結丹後得以開峰,成為翩然峰新任山主。
白首今天覺得有些奇怪,因為劍氣長城的九個小屁孩里邊有個叫白玄的小家伙總瞅自己,好像跟自己很熟的樣子。
金烏宮柳質清、雲上城徐杏酒都坐在劉景龍附近,兩人都找劉景龍喝過酒,如今劉景龍享譽兩洲的酒量,他倆功勞不小。
再加上之後女劍仙酈采、老武夫王赴愬等人的推波助瀾,算是有了定論——劉劍仙要麼不喝,只要開喝,酒量就無敵。
所以這次登門做客,劉景龍既是為落魄山道賀,也要與陳平安道謝。
龍泉劍宗的開山大弟子董谷,也就是劉羨陽的大師兄,如今是元嬰境,卻非劍修,他的師妹徐小橋則是金丹境劍修。
另一個師弟謝靈是元嬰境劍修,同時精通符籙、陣法,躋身寶瓶洲年輕十人之列,而且這些年中,名次不斷提升,如今已經超過了風雷園元嬰劍修劉灞橋。
寶瓶洲年輕十人之首是真武山馬苦玄,其他榜上之人除了謝靈、劉灞橋,還有隋右邊,以及雲林姜氏的元嬰修士姜韞和觀湖書院那個當過三次君子、在“君子”“賢人”兩個頭銜上來來回回樂此不疲的周矩。
剩下的四人,則是在大戰當中崛起的新面孔,例如馬苦玄的師伯、兵家修士余時務。
寶瓶洲還有候補十人,其中有正陽山的一個少年劍修,是個劍仙坯子,名為吳提京,在正陽山躋身宗門之時被正陽山山主收為關門弟子。
董谷坐在魏晉一旁,畢竟風雪廟算是龍泉劍宗的“娘家”,而魏晉如今又是當之無愧的寶瓶洲劍修第一人,董谷在魏晉面前自然十分恭敬。
而在山上一向清高到孤僻的魏大劍仙對這個山澤精怪出身的龍泉劍宗大弟子也算破例了,言語雖然不多,但是帶著幾分笑意。
要知道,魏晉是出了名的不會與人客氣,哪怕是回到風雪廟,他也一樣只去神仙台。
先後兩場問劍天君謝實,在劍氣長城和寶瓶洲兩處戰場問劍大妖都是一言不發,唯有遞劍而已。
孫氏家主孫嘉樹和桂夫人的唯一嫡傳金粟已經結為夫妻,也是一對山上道侶了。
趴地峰火龍真人的愛徒張山峰正在閉關,所以未能出席觀禮。
按照指玄峰袁靈殿的說法,小師弟張山峰此次是洞府境躋身觀海境——當年青鸞國一別,張山峰都還不是中五境修士。
除袁靈殿外,張山峰的幾個師兄,連同師父一起為他“護道”。
也就是說,一位飛升境的火龍真人,以及白雲一脈祖師,還有桃山一脈、太霞一脈,都在洞窟外為一個洞府境修士護道……這種事情,估計也就趴地峰做得出來。
不過所謂的護道,其實也就是幾個師兄弟陪著師父他老人家一起嘮嗑,擺好桌子,備好酒水,佐酒菜來幾碟,瓜果一大盆,賞賞月色,看看風雨,靜待師父的詩興大發,打油詩來那麼幾首,然後一個個眼神真摯,拍案叫絕……袁靈殿看不慣那兩個溜須拍馬的師兄很多年了,尤其是這次,原本他都備好了筆墨紙硯,總覺得肯定可以扳回一局,不承想師父要他來落魄山觀禮,沒能派上用場。
李希聖帶著書童崔賜正在游歷流霞洲的天隅洞天;鍾魁與骸骨灘鬼蜮谷的京觀城城主高承在從蠻荒天下托月山重返浩然的亞聖護送下,跟隨那個雞湯老和尚一起去了西方佛國;白帝城城主的關門弟子顧璨如今身在扶搖洲,據說因緣際會之下,被他找到了一處小洞天秘境,正在閉關煉化;披麻宗宗主竺泉去了中土上宗;邵雲岩與酡顏夫人聯袂雲游,來到了寶瓶洲。
邵劍仙當年讓劉景龍和水經山盧穗一起幫忙帶走春幡齋那串葫蘆藤,結出的十四枚小葫蘆最終瓜熟蒂落,春幡齋運道極好,其中竟然有十枚養劍葫。
預期的七枚早已預定出去,如今邵雲岩手上還有額外三枚品秩極高的養劍葫,此次來觀禮的賀禮就是其中一對,寓意好事成雙,同時算是幫了囊中羞澀的窮光蛋酡顏夫人一個大忙。
不然酡顏夫人這一路走得惴惴不安,登山之前差點就要轉頭就走,打死都不敢見那位隱官大人了。
邵雲岩臨時送她一枚養劍葫,她這才有膽子登山恭賀。
林君璧和郁狷夫是被崔東山“順路”帶來落魄山的,落魄山這次沒有邀請春露圃修士。
趁著所有人都喝茶的間隙,陳平安與崔東山快速以心聲言語,才知道這位學生這趟中土文廟之行確實很忙。
崔東山從桐葉洲大泉王朝動身,跨洲遠游,先是去了趟功德林,見到了先生的先生,祖師老秀才,好得很,在那邊與一個被譽為“天下儒者宗”的董老夫子,還有俱蘆洲舊魚鳧書院的山長周密,仨臭棋簍子經常下棋。
然後崔東山得了祖師爺的授意,先留下了那方藏書印,再得了祖師爺的口信,以及董老兒的一封書信,去禮記學宮找大祭酒。
而茅小冬辭去大隋山崖書院的副山長一職,進入三大學宮之一的禮記學宮擔任司業一職,僅次於大祭酒。
按照山上好事者以山水官場的算法,學宮司業一職低於大祭酒,卻要略高於七十二書院的山長。
賢人君子,再“正人”君子、書院山長、學宮司業、學宮大祭酒、陪祀聖賢、文廟副教主、文廟教主,這就是儒家文廟相對比較按部就班的“官場進階”了。
茅小冬帶著李寶瓶、李槐,還有一撥學宮儒生一路南下,先後游歷婆娑洲、雨龍宗、劍氣長城,如今一行人應該身在劍氣長城了,山水迢迢,所以錯過了這場觀禮。
崔東山與那學宮大祭酒一合計,就以禮記學宮茅司業的名義舉薦落魄山提升宗門。
崔東山還七彎八拐地找到了一位文廟老聖賢,輩分極高、功德極大的伏勝,於是手中就又多了一封舉薦信。
最後加上即將趕赴桐葉洲擔任一座書院山長的周密,山長、司業、陪祀聖賢三封舉薦信在手,再跑去中土文廟找到了副教主韓老夫子。
最終,三位正副教主和三位學宮大祭酒在文廟聚頭議事,其中有兩人希望“再議”,理由是既然落魄山的山主按照你崔東山的說法就“只是元嬰劍修和九境武夫”,提升宗門,於禮不合,氣得崔東山差點撒潑打滾,結果禮聖現身,只說了句“不用再議了”,那麼自然就是不用再議了。
等到周米粒三個端茶,所有人又都喝過了茶水。
裴錢和曹晴朗已經搬了一套桌椅擺放在陳平安和長命的位置中間,是為提筆記錄譜牒一事而准備,因為包括長命、米裕和韋文龍在內的一大撥譜牒修士,由於陳平安太多年不曾返回家鄉,其實尚未真正記錄在霽色峰祖師堂的山水譜牒上,是以今天就要補上。
陳平安起身走向那張書案,笑道:“山水譜牒記錄名字一事,按照山上規矩,本該是掌律執筆。我們落魄山小門小戶,先前都沒來得及設置掌律一職,所以今天我先代勞,等到我親自為長命在譜牒上記名,再讓長命坐在這兒。”
雖然包括裴錢在內的陳平安三名嫡傳在敬香之時的所站位置僅次於山主陳平安,但是落魄山的座椅安置,最為靠近陳平安那張“頭把交椅”的卻是長命和韋文龍,然後才是裴錢他們三個。
這就是山上規矩。
長命站起身,先與山主作揖拜禮,再與眾人作揖致禮。
其實所有離著落魄山比較遠的觀禮之人都很好奇這位身穿一件雪白長袍、笑容和煦的女子到底是何方神聖,竟然能夠脫穎而出,一舉成為落魄山的掌律。
落魄山的掌律祖師分量到底有多重,在座觀禮之人,哪怕是像老龍城女修金粟這樣找了個好師父又找了個好丈夫、始終不太需要理會山上事的人物,一樣心里有數,很有數。
陳平安本來就是一個出了名喜歡講道理的人,而落魄山的掌律祖師就意味著是落魄山上唯一一個在名義上“道理”與山主陳平安一樣大,甚至某些關頭還要更大的超然存在。
陳平安在落魄山譜牒第一頁寫下“掌律,長命”,然後笑著擱筆起身,換成長命接替落座掌筆,寫下“泉府府主,韋文龍”。
韋文龍起身先與陳平安抱拳致禮,然後與眾人行禮,最後抱拳不放,望向那位傳道恩師——春幡齋劍仙邵雲岩。
邵雲岩大笑著站起身,執平輩禮,與昔日弟子韋文龍抱拳還禮。
按照山上規矩,霽色峰祖師堂內,與雙方今天出了大門,禮數可以分開算。
邵劍仙是真沒有想到自己這個修行資質一般的嫡傳能夠成為落魄山的賬房先生,隱官大人的左膀右臂。
酡顏夫人瞥了眼滿面紅光的邵雲岩,有些不是滋味。同樣是倒懸山四大私宅,春幡齋大概是取名取得好,如今倒是最為春風得意了。
她立即收斂視线,正襟危坐,原來是那位年輕隱官笑眯眯望向了自己。
浩然天下四位夫人,如今落魄山祖師堂內竟然就有兩位,梅花園子的酡顏夫人和桂花島的桂夫人。
長命、韋文龍之後,是前不久剛剛從披雲山辭去客卿職務的劍仙米裕。
之後是元嬰劍修崔嵬,賬房一脈的張嘉貞,符籙修士蔣去以及趙樹下、趙鸞,還有裴錢的開山大弟子、綽號阿瞞的周俊臣。
再之後是這些年都身在蓮藕福地修行的元嬰狐魅沛湘、元嬰水蛟泓下、剛剛結金丹的雲子,以及九個來自劍氣長城的劍仙坯子。
在這之後,又有三樁禮儀。
第一樁,是將劍修郭竹酒的名字記錄在祖師堂譜牒第二頁,使她正式成為山主陳平安的嫡傳弟子。
第二樁,一樣是拜師,年輕武夫趙樹下正式成為山主陳平安的又一位嫡傳弟子。
即刻起,陳平安的嫡傳弟子總計五人。
第三樁,周俊臣拜師裴錢,其實就等於同時成了陳平安的再傳弟子。
拜師禮,需要弟子磕頭,師父喝茶。
與裴錢各自收徒後,陳平安先後喝過了趙樹下的拜師茶和周俊臣的拜祖師茶,放下茶杯笑道:“諸位,我們落魄山聘請客卿一事,不如趁熱打鐵,今天都敲定下來吧?”
如果不是礙於山水規矩,陳平安這會兒已經讓崔東山去關上大門了。
有些是身在文聖同一文脈之內的讀書人,無須錦上添花,比如林守一、於祿、謝謝、董水井。
魏檗是北岳山君,劉景龍是一宗之主,劉重潤是一島之主,孫清是彩雀府府主,徐杏酒是雲上城城主,於禮不合,只能作罷。
有些是生意往來的盟友,不用畫蛇添足,免得混淆不清,難以明算賬,例如范二、孫嘉樹、韋雨松。
所以最終成為落魄山記名客卿的人選分別是邵雲岩、酡顏夫人、桓雲、謝松花、柳質清、李芙蕖。
魏晉和袁靈殿本來對擔任客卿一事並無想法,結果都被陳平安給說服了。
說服魏晉不難,你魏大劍仙好歹接受過我師兄左右的劍術指點,這點面子都不給的話,說不過去。
至於袁靈殿,是看在小師弟張山峰的面子上,加上本身就與陳平安相熟,就答應下來。
最後一個,是以心聲與隱官大人言語,主動請求擔任客卿的浮萍劍湖“小隱官”陳李。
陳李與白首是差不多的感覺,不明白為何那個名叫白玄的劍仙坯子的眼神里邊透著一股十分沒道理的親近。
而白首又要比陳李更加識趣些,更有危機意識,覺得那個裴錢金字招牌一般的臉色和笑意越發讓人毛骨悚然了。
白首打定主意要離白玄遠一些,免得被殃及池魚。
要知道,裴錢第二次游歷中土神洲去與曹慈問拳之前,再次路過俱蘆洲太徽劍宗的時候,白首剛剛躋身金丹劍修,在翩然峰走不開,就剛好遇到了登山做客、久別重逢的裴錢。
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不知怎的,裴錢與姓劉的聊著聊著就扯上了他。
當時白首掂量了一下自己,又見她裴錢個兒挺高,可惜瘦竹竿似的,不像是個拳重的,就覺得自己不敢說穩贏,一戰之力終究該有了,就大搖大擺與裴錢切磋了一場,結果就是裴錢負責一拳,他負責倒地不起、口吐白沫。
等他暈乎乎躺床上醒過來,裴錢跟姓劉的隨便找了個由頭,已經跑路了。
他當時悲從中來,卷起被子,繼續蒙頭裝睡。
在陳平安已經心滿意足的時候,李柳突然笑著以心聲言語,說她也要擔任落魄山的客卿,陳平安當然沒法拒絕。
李柳雖然臉色慘白,一副大病未愈的模樣,越發顯得柔柔弱弱,可她哪怕跌境,依舊是一位仙人。
崔東山曾經說過,同境修士,李柳、姜尚真都是那種最為難纏的仙人。
當然,還要加上一個當年的稚圭。
比起一般意義上的大劍仙,比如許弱、魏晉,只會更加難纏。
沛湘的惴惴不安大概絲毫不輸酡顏夫人,她擔心今天這麼大的一場觀禮過後,人多眼雜,明天清風城就知道了她和整個狐國的蹤跡。
她不是害怕許渾來興師問罪,一個玉璞境的兵家修士,就算來了,又能如何?
落魄山要留客,估計許渾就不用走了。
她只是擔憂那許氏婦人的幕後之人的手段。
走江化蛟的泓下是第一次正式見到那位年輕山主,面對對她極為和善的陳平安,她的內心深處卻泛起一種天然的敬畏。
都是堂堂元嬰境大修士,座位相鄰的沛湘和泓下發現對方好像都比自己更緊張,心境反而逐漸平靜起來。
談妥了客卿一事,落魄山觀禮就告一段落。
接下來,祖師堂還需要關起門來議事,涉及宗門機密,陳平安就送客到祖師堂大門,所有觀禮客人都下榻在霽色峰半山腰的一大片仙家府邸當中,等到議事完畢,陳平安肯定還需要一處處宅子拜訪過去。
落魄山擁有三座山峰,主峰集靈峰,也就是竹樓、山巔祠廟所在之處,這座建造有祖師堂的霽色峰其實是次峰。
因為是祖師堂議事,許多落魄山再傳弟子、一般供奉一樣需要離開,跟隨觀禮客人們一起下山。
哪怕是陳平安嫡傳的趙樹下,因為資歷不夠,今天依舊無法留下。
但是對於一個如今才四境的年輕武夫來說,依舊如夢游一般,直到現在還沒有回神還魂,因為事先根本沒有人告訴他,今天自己會成為陳先生的嫡傳弟子。
趙樹下轉頭對一旁的趙鸞輕聲道:“鸞鸞,我不是在做夢吧?”
趙鸞身穿一襲彩雀府仙家法袍,笑道:“你打自己一拳,吃疼就不是做夢。”
趙樹下嘆了口氣:“早知道這樣,就該與陳先生說一聲的,把我換成你多好。你如今都是龍門境了,我練了兩百萬拳,才跌跌撞撞躋身四境武夫。”
不承想趙鸞的一雙漂亮眼眸卻眯成了月牙兒,好像自己沒有成為陳先生的嫡傳弟子,她更開心些。
劉羨陽自然要與大師兄董谷同行,帶上個風雪廟大劍仙魏晉。
桂夫人和酡顏夫人聯袂而行,說著些女子之間的悄悄話。
邵雲岩找到了劉景龍,自然而然就認識了柳質清、徐杏酒和老真人桓雲,一行人其實都算俱蘆洲同鄉,談笑風生。
陳李帶著高幼清,還有舉形和朝暮,這四個更早離開劍氣長城的劍仙坯子,以及其余九個跟隨隱官大人一起來到落魄山的孩子走在一起,還是一大撥同鄉。
林守一在內的四名同窗並肩而行,走在他們前邊的是李二、李柳和韓澄江。
劉羨陽與魏晉聊完,快步跑到林守一和董水井身邊,一手搭住一人肩膀,然後笑嘻嘻地喊了聲韓澄江。
韓澄江臉色僵硬,身體緊繃,轉過頭,與劉羨陽擠出一個笑臉,目不斜視。
林守一眯起眼,董水井扯了扯嘴角,韓澄江的額頭立即滲出汗水。
其實花翎王朝是俱蘆洲屈指可數的大王朝,而韓氏又是花翎王朝的“太上皇”,地位有點類似中土郁氏。
韓澄江作為韓氏嫡出,其實也算出身浩然天下的頭等鍾鳴鼎食之家,只是人在異鄉,人生地不熟的,心里難免沒個著落。
他倒是半點不介意吃醃菜喝劣酒,每天做些挑水砍柴的活計,反而樂在其中,只不過委實是被小鎮唯一結識的好朋友劉羨陽給嚇跑了。
按照劉羨陽的說法,那林守一和董水井打小就是家鄉的混世魔王,喜歡半路給人套麻袋,拽農田里拳打腳踢一頓。
韓澄江不怕吵架,但是怕打架啊,要是鼻青臉腫地回了宅子,就算自己不覺得丟臉,可是丈母娘最好面子,街坊鄰居更是一個比一個長舌,他能咋辦?
說是路上摔的?
等到李柳微微轉頭向後望去,林守一與董水井立即雲淡風輕,移開視线。
孫清帶著嫡傳柳瑰寶,李芙蕖帶著嫡傳周采真,四人一起走在劉景龍那一行人的身後。
白首知道這里邊的玄機。
身後孫府主與那水經山的盧穗都是俱蘆洲十大仙子之一,又都鬼迷心竅愛慕姓劉的。
春幡齋邵劍仙又與盧穗的師父是有緣無分的半個道侶,所以這會兒先後兩撥人,咫尺之隔,卻殺機四伏。
范二、孫嘉樹、金粟正與披麻宗的財神爺韋雨松談事情。
魏檗、謝松花、袁靈殿、郁狷夫、林君璧分別來自四洲,倒是相談甚歡。
石柔、阿瞞、賈晟、趙登高、田酒兒、張嘉貞和蔣去一起下山,這幾人也算“同出騎龍巷一脈”。
賈晟撫須而笑,神清氣爽。沒法子,如今又升官了,攔都攔不住。落魄山供奉分出了三等,他是躺著躺著就享著了二等供奉的福。
到了半山腰的住處,霽色峰這片仙家府邸與落魄山後山那片鱗次櫛比的建築都是姜尚真掏的腰包,花了十多枚谷雨錢打造。
每一處宅子都由朱斂親自構圖,親自督造,不愧是在藕花福地編撰過一部《營造法式》的老廚子。
相較於集靈峰竹樓附近的那片府邸,可謂後來者居上。
但是誰都清楚,算不算落魄山真正的“老人”,還是得看在竹樓附近有沒有一處確實不值錢的“小破宅子”。
這就跟與落魄山熟不熟,就看嗑不嗑得上瓜子是一個道理。
所有觀禮客人都發現原先走在路上閒聊的隊伍幾乎都不用如何分散,因為下榻處都相鄰,所以大多繼續揀選某處宅子,繼續閒聊。
修道之士,山上各自修行,又來自浩然天下的四面八方,像今天這樣相聚碰頭的機會其實不多的。
而這些,都是暖樹與朱斂、韋文龍仔細商議過後的細致安排,光是用掉的草稿紙就填滿了一個紙簍。
因為要參加祖師堂議事,暖樹先前就將好幾串鑰匙交給了田酒兒和阿瞞。酒兒姐姐從來細心,別看阿瞞像個小啞巴,其實腦子很靈光的。
而阿瞞在山下只與掌櫃石柔關系好些,在山上只會與暖樹說幾句話。哪怕到了師父裴錢跟前,他也依舊喜歡當啞巴。
在一座大院子里邊,陳李斜坐石桌,看著雙手負後的白玄。
陳李問道:“白玄,你躋身觀海境了沒有?”
白玄如遭雷擊,腹誹不已:你他娘的怎麼跟小爺說話呢?你是劍氣長城公認的小隱官咋了,跟在曹師傅身邊混過幾天啊?
高幼清有些替他打抱不平,埋怨道:“陳李,沒你這樣欺負人的,白玄如今還沒滿十歲呢。”
舉形坐在台階上,膝上橫著一根綠竹杖,笑著看熱鬧。
他如今是龍門境劍修,瓶頸,比陳李低了一個境界。
同樣是謝松花嫡傳的朝暮卻還只是剛剛躋身觀海境。
陳李一個斜眼,高幼清立即不說話了。
陳李又問道:“先前在祖師堂里邊,還有下山路上,你瞅個啥?”
白玄眼珠子一轉,嬉皮笑臉道:“仰慕小隱官的風采唄。”
陳李說道:“以後好好修行。”
白玄忍住翻白眼的衝動,笑呵呵抱拳道:“小事一樁。”
納蘭玉牒、姚小妍都與高幼清相熟,這會兒正一左一右蹲在高姐姐身邊,眼饞那只據說是裴錢姐姐贈送的小竹箱呢。
而虞青章和賀鄉亭坐在了舉形身邊,用家鄉話問著皚皚洲的風土人情。
劍氣長城說大很大,劍修、劍仙實在太多;說小又很小,其實就那麼點人。
而且以前哪怕只是在家鄉街巷打過照面的孩子,到了浩然天下,都會變得關系很好。
只有一個例外,就是已經率先挑選一間屋子,開始獨自溫養飛劍的小姑娘——孫春王。
霽色峰祖師堂內開始重新關門議事,多余的椅子都已經撤去,只留了兩把空椅子給鄭大風和郭竹酒,其余人等都已紛紛落座。
此刻在祖師堂內的十九人中,上五境練氣士有五個:陳平安,長命,崔東山,姜尚真,米裕。
遠游境及以上武夫有六個:陳平安,裴錢,朱斂,盧白象,魏羨,種秋。
元嬰境修士有四個:陳靈均,崔嵬,沛湘,泓下。
這還是沒算上鄭大風和郭竹酒的規模,這樣的一個宗門,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龐然大物,如一條蛟龍盤踞幽深古井中,正在緩緩抬起頭顱。
除了缺少一位飛升境坐鎮山頭,落魄山其實沒有任何缺漏可言。
最重要的,是落魄山的譜牒修士都很年輕,境界卻高得匪夷所思。
陳平安一手雙指抵住茶杯輕輕旋轉,開始閉目養神。分心無數,念頭四起,並不去拘束。
沛湘和泓下這兩個新面孔大氣都不敢喘。
崔嵬其實也並不輕松,這位年輕山主到底是一人駐守劍氣長城多年的那個隱官大人,還是數個天下的年輕十人之一,如今更是浩然天下的一宗之主了。
陳平安緩緩睜開眼睛,笑道:“我很幸運,能夠認識各位,並且成為同道中人。很榮幸,在座各位能夠出現在這霽色峰祖師堂。”
祖師堂內寂靜無聲,落針可聞,只有周米粒拍掌卻無聲。
陳平安眼神溫柔,等到周米粒停下動作,才繼續說道:“近期我們落魄山還是不會太過大張旗鼓,對外的說法就是米大劍仙脫離披雲山山水譜牒,鼎力支持我們落魄山,所以才得以一舉晉升了宗門,至於外界信與不信,我們管不著。”
米裕一臉呆滯。
姜尚真贊嘆道:“多虧了米劍仙,才能瞞天過海得如此水到渠成,不露痕跡。”
崔東山使勁點頭:“是啊是啊,米大劍仙不當這個首席供奉,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
姜尚真一個發愣,打了個哆嗦:啥玩意兒?先前那封密信上說好的板上釘釘首席供奉呢?說好的在你先生跟前一哭二鬧三上吊呢?
陳平安笑眯眯道:“所以今天要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落魄山的首席供奉人選。”
裴錢說道:“師父,首席供奉誰來當我都沒有意見,只聽師父和掌律的意思。反正我建議周肥擔任次席供奉,免得泄露了周肥的玉圭宗姜老宗主身份。”
玉圭宗的姜老宗主?
就是那個身為桐葉洲人氏,卻在俱蘆洲揚名立萬的姜尚真?
那個最終幾乎可以算是憑借一己之力守住神篆峰的大劍仙?
陳靈均眼皮子直打戰,立即開始小心翼翼盤算以往周肥兄弟幾次來落魄山做客,自己有無半點冒犯的言辭、舉動。
泓下和沛湘更是臉色微白。姜尚真,玉圭宗上任宗主!桐葉洲力挽狂瀾第一人!
周米粒張大嘴巴,趕緊轉過頭,對姜尚真投以最為誠摯的贊賞眼神。
這個化名周肥的供奉很可以啊,只是瞧著也不顯老啊,好大出息,不愧是姓周的人!
朱斂微笑道:“周老哥當這個次席供奉很能服眾的,誰不服,就是與我問拳。問拳我認輸,但還是會堅持己見,除了周老哥,誰當次席我都不服氣。”
盧白象附和道:“姜老宗主終究事務繁忙,擔任我們落魄山的次席供奉,雖說大為屈才了,但實在是沒辦法的事情。”
姜尚真哀怨不已,無奈道:“我半點不忙的啊。不管是玉圭宗還是真境宗,我都不是宗主了啊。”
一直雙臂環胸打盹的魏羨終於補了句:“我是粗人,說話直接。周肥你一看就是一塊飛升境的料,以後閉關少不了。首席供奉是一山門面所在,更需要時不時偷溜下山去打打殺殺的,落魄山不好意思耽誤周老哥的修行。”
米裕聽得那叫一個膽戰心驚。祖師堂之內,肯定是他最希望姜尚真來當那首席供奉的。給他個譜牒供奉就行,別說首席,次席都不用。
曹晴朗微微訝異,不過仍是給出了自己的意見:“我覺得姜老宗主擔任首席供奉比較合理,再讓米劍仙擔任次席供奉。不過我們可以暫時對外隱瞞首席、次席兩供奉的人選。”
姜尚真差點熱淚盈眶:總算有人仗義執言了,果然還是要靠落魄山的這股清流,門風擔當曹晴朗!
陳平安忍住笑,轉頭望向長命:“分歧很大啊,掌律怎麼說?”
長命起身說道:“山主一言決之,長命只負責填補譜牒首席、次席一欄的空白。”
她走向那張並未撤去的書案,重新取出那本霽色峰祖師堂譜牒,攤放開來,剛好翻到供奉篇首席、次席兩頁空白。
崔東山兩只雪白大袖耷拉在椅子把手上,煽風點火之後,就打定主意隔岸觀火了。
一個臭不要臉鐵了心要當首席,一個嚇得劍心不穩打死不當首席。
這種情形,果然只有自家祖師堂才會有了。
至於姜尚真會不會埋怨他不厚道,他娘的,這是祖師堂議事,跟我崔東山有半枚雪花錢的關系嗎?
陳平安突然笑著站起身,朝姜尚真一抱拳:“恭喜周首席,以後有勞了。”
祖師堂內所有人,除了姜尚真,幾乎都同時站起身,朝姜尚真抱拳致禮,道賀連連。其中,被人一口一個“劍仙”“大劍仙”的米裕尤為真誠。
姜尚真抖了抖袖子,正了正衣襟,抱拳還禮,朗聲笑道:“承蒙厚愛,受之有愧,德不配位,受之有愧啊……”見陳平安微微一笑,他立即改口,“既然眾望所歸,無一異議,我就挪座椅了啊。”
姜尚真起身拿起椅子,屁顛屁顛就將椅子搬到了長命、韋文龍之後的位置上,與此同時,崔東山、裴錢、曹晴朗在內所有人都笑著跟著一起挪了位置。
姜尚真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轉身笑道:“崔老弟,咱哥倆這就當鄰居了啊。”
崔東山伸出手掌,姜尚真笑著輕輕擊掌。
崔東山一把抓住姜尚真的手掌,輕聲問道:“紅包?不人手一個,過意不去吧?”
姜尚真說道:“一人兩份,早就備好了的。”
裴錢揉了揉額頭。
陳平安起身道:“東山,打開整個小鎮西邊的山水畫卷。”
崔東山打了個響指,祖師堂內浮現出一幅山脈起伏的堪輿圖,雲霧升騰,靈氣流轉,脈絡清晰。
崔東山站起身,走到畫卷邊緣,伸出一根手指,畫了一個小圈,將一塊山河圈起來,緩緩道:“包括披雲山在內,總計六十二座山頭。龍泉劍宗占據神秀山、挑燈山和橫槊峰。此外,周邊的寶籙山、彩雲峰和仙草山其實都是落魄山的藩屬山頭,只是租借給了龍泉劍宗三百年。龍泉劍宗此後又買下了四座山頭,大體上是圍繞祖山。阮邛將祖師堂搬遷到京畿以北的舊山岳地界後,如果不出意料,以阮邛的脾氣,會將這四座山頭租借,甚至有一定可能,選擇直接賣給我們落魄山,作為當年落魄山租借三山的回禮。”
崔東山開始在畫卷上指指點點:“先生買入了落魄山北邊的灰蒙山,與魏山君將牛角山對半分。清風城許氏搬出的朱砂山,暫時租借給書簡湖珠釵島的鰲魚背。這是蔚霞峰,這是位於最西邊的拜劍台,以及位於最東邊的真珠山,再加上陳靈均牽线搭橋買來的黃湖山。在先生遠游期間,在朱斂的運作之下,我們落魄山又陸陸續續低價購入了香火山、遠幕峰、照讀崗。”
崔東山每次“指點”,大大小小的山根水運就會一一顯化。
他沉聲道:“除了龍泉劍宗,龍脊山有那斬龍崖,風雪廟和真武山肯定都不會放棄,我們也不去多想。至於在衣帶峰上修行的那撥仙師,祖師堂譜牒其實位於夢粱國,與雲霞山是鄰居。前者在寶瓶洲屬於二流仙家勢力,而且比較墊底,只是與我們落魄山關系不錯,所以一樣不用多想。但是其余十余個仙家勢力沒什麼香火情,我們也不欺負他們……”
說到這里,崔東山望向姜尚真,姜尚真就微笑道:“買買買,賣賣賣,雙方你情我願,不就有了香火情?”
韋文龍說道:“泉府賬簿上,其實略有盈余。”
陳平安終於插嘴,笑問道:“怎麼個略有盈余法?”
韋文龍立即站起身,報了一筆賬。
與骸骨灘披麻宗—春露圃—彩雀府—雲上城一线的商貿,再加上新開辟出來的披麻宗—浮萍劍湖—龍宮洞天的第二條商貿路线,還要加上與紅燭鎮三江—董水井、老龍城范二、孫嘉樹這第三條路线。
此外,還有牛角山渡口、包袱齋的收入,以及上等品秩瓶頸的蓮藕福地一大筆收入。
所以韋賬房所謂的“略有盈余”,是落魄山還清了一大筆債務不談,賬面上還躺著三千六百枚谷雨錢的現錢。
關鍵在這之外,泉府賬房里邊還有六百枚金精銅錢。
而一塊蓮藕福地與三條商貿路线的收益,還是源源不斷的。
陳平安想了想,起身走到畫卷邊緣,道:“總計六十二座山頭,我們爭取在百年之內,包含至少半數。簡單來說,就是除了披雲山、龍脊山、衣帶峰以及龍泉劍宗占據的山頭之外,其余所有被那十數個仙家占據的山頭都可以談,都可以商量。但是切記,既然是商量,就好好商量,強買強賣就算了,畢竟遠親不如近鄰。能夠連綿成片是最好,不成,就在寶瓶洲尋找幾塊藩屬飛地。”
陳平安盯著畫卷,自顧自緩緩道:“寶籙山、彩雲峰和仙草山不去說,落魄山是祖山所在,鰲魚背已經租給了劉島主,真珠山實在太小,牛角山是仙家渡口,泓下已經在黃湖山水底開辟水府,景清和暖樹的龍王簍也在黃湖山煉化為山水大陣。那麼現在空置的山頭就有灰蒙山、朱砂山、蔚霞峰、拜劍台、香火山、遠幕峰和照讀崗。十年之內,開峰儀式就不去辦了,七座山頭,你們現在就可以挑選起來了。”
泓下起身顫聲說道:“山主,我已經搬去了蓮藕福地,在那里占據了一條江河,理該讓出黃湖山,水府送給……雲子好了。”
陳平安抬起頭,笑望向泓下,搖頭道:“不用,你的仙家機緣在黃湖山,於公於私你都不能讓出。”
泓下還要說話,陳平安擺擺手:“只管寬心,留下水府。”
泓下再不敢言語,趕緊施了個萬福:“謝過山主。”
姜尚真感慨萬分。還說不是一言堂?要是在神篆峰祖師堂,得有多少人朝自己吐唾沫、砸椅子了?
陳平安輕聲笑道:“泓下,不用如此拘謹,祖師堂議事,你是一分子,是有椅子的。在這里,道理最大,誰敢出了祖師堂給你穿小鞋,你只管找我,我親自幫你評理。”
崔東山點頭道:“是啊是啊。”
陳平安氣笑道:“我說的就是你,以後別有事沒事就嚇唬泓下。”
崔東山眼角余光瞥向泓下,泓下下意識望向陳平安,剛收回視线望向山水畫卷的陳平安就只好又望向崔東山,崔東山也只好舉起兩只袖子。
一直沉默的隋右邊說道:“我想要拜劍台當作修行之地。”
陳平安搖頭道:“不行。”
隋右邊皺眉問道:“為何?”
陳平安隨便找了個理由:“別處宗門,金丹開峰,我們落魄山得是元嬰。”
拜劍台,陳平安心中是有人選的:崔嵬領銜,九個劍仙坯子都留在那兒。隋右邊不是劍氣長城的劍修,不合適。
隋右邊笑了笑,陳平安知道她為何如此,因為她破開金丹瓶頸其實不難,如果真想要躋身元嬰,當年飛升台她就可以做到,只是不知為何,她故意停滯境界。
陳平安補了一句:“你先別著急下決定。”
陳平安一拂袖子,收起畫卷,後退幾步,站在椅子旁,一只手放在椅背上,說道:“落魄山之所以繼續藏拙,原因有三。第一,我當了十幾年的劍氣長城隱官,躲躲藏藏的仇家有不少,不一定全是妖族。第二,我早年有兩樁私人恩怨。第三,我作為文聖一脈的關門弟子,身份很快就會水落石出,到時候很多的麻煩光靠飛劍和拳頭是不管用的。在這里,我先跟你們打好招呼,諸位都做好准備。當然,有我在,對方也不是那麼輕松就可以得逞的。只是有需要各位出力的時候,我不會跟你們客氣就是了。所以在這之前,我必須快刀斬亂麻,處理好手邊的家務事,大驪宋氏、正陽山、清風城,主要就這三個。嗯,還要加上一個相對比較好處理的春露圃。所以我近期會親自走一趟俱蘆洲。”
陳平安望向沛湘,狐國之主立即主動站起身。
陳平安笑了笑:“沛湘,你安心留在蓮藕福地,妥善處理狐國事務,天塌不下來。你既然成了我們落魄山的祖師堂供奉,一家人不說兩家話,與清風城許氏的那點因果,我自會幫你斬斷,不留半點隱患。但是事先說好,不用刻意為了討好祖師堂,就去做些有損狐國利益的舉措,完全沒必要。我們落魄山與一般山頭的風氣還是不太一樣,比較講道理,這麼多年相處下來,相信你應該心里有數。”
沛湘立即施了個萬福。
陳平安點頭致意,繼續道:“接下來,就是商議落魄山下宗選址桐葉洲一事。”
陳靈均瞪大眼睛:啥?
下宗都有啦?
那下宗的首任宗主,自己有點當仁不讓的意思啊。
他咳嗽幾聲,剛要站起身,陳平安已經笑道:“怎麼,景清大爺打算親自走一遭桐葉洲?會不會大材小用了?”
陳靈均立即把屁股放回椅子,笑哈哈道:“不去不去,老爺說笑了,我細胳膊細腿的,在落魄山上的擔子就很重了。”
陳平安猶豫了一下,還是直截了當說道:“我原本是打算讓曹晴朗擔任下宗首任宗主的,但是現在不單單是寶瓶、桐葉和俱蘆三洲形勢復雜,一旦我的兩個身份顯露,會有許多額外的意外針對下宗。”
崔東山笑道:“我來當下宗的副山主好了,過渡,過渡一下。”
說完又故作驚訝地“咦”了一聲,身體前傾,伸長脖子望向米裕:“這下好了,又空出個下宗首席供奉來,米大劍仙,你說巧不巧?”
米裕剛通體舒泰沒多久,這會兒就又如臨大敵了,可憐巴巴地望向陳平安,苦著臉說道:“隱官大人,當官什麼的,我真不成啊。哪怕讓我不當什麼首席供奉,卻必須要做那首席供奉的事,我都認了!”
彩雀府那邊,一個柳瑰寶不說,還有好些個眼神炙熱的譜牒仙子就夠讓米裕憂愁不已的了。
陳平安笑道:“下宗的首席供奉可以暫定,回頭再議,反正只要你躋身了仙人境,都好說。”
米裕松了口氣。能拖一天是一天。
陳平安轉頭望向隋右邊,以心聲言語道:“在雲窟福地,我見到你的先生,他如今化名倪瓚,在黃鶴磯當那撐船擺渡的老篙師,很早就離開了藕花福地,如今是玉璞境劍修,還有那江上斬蚊的事跡流傳,你在玉圭宗修行之時,其實應該聽說過。我們曾經逛過的騎鶴城,就是你先生‘飛升’離開家鄉時留下的一處‘仙跡’。”
隋右邊神色復雜,輕輕點頭,雙手攥緊椅子把手。
陳平安一拂袖,出現了一幅福地老君山的山河萬里圖。
他先為眾人大致說明了如今的桐葉洲山上山下形勢,太平山、大泉姚氏、桃葉之盟、驅山渡、天闕峰……
種秋感慨道:“下宗選址桐葉洲,其實要比選址寶瓶洲更加難做人,因為一個不小心,我們就會與寶瓶洲和俱蘆洲修士結仇。如今兩洲修士南下滲透桐葉洲,勢如破竹,很容易與他們起利益衝突。如果只是各自求財,井水不犯河水倒還好說,說不定還能順勢結盟,可若是落魄山還要求個‘理’字,難了。”
魏羨眯起眼,望向那幅山河畫卷:“難?我看未必。選擇下宗後,按山主的意思,快刀斬亂麻。比如俱蘆洲,拿那瓊林宗開刀;寶瓶洲,拿那老龍城范、孫之外的大姓開刀。只要刀子夠快,旁人哪怕不挨刀,可只要不眼瞎,瞧見了,一樣會覺得疼的。”
崔東山微笑點頭,不過視线有意無意的,卻是望向陷入沉思的曹晴朗。
曹晴朗沉默片刻,方道:“與其在各執一端各有各理的一團亂麻里攪和,不如聽魏羨的,在兩洲勢力當中找兩個全然不占理的,那麼我們再來講理,就很清爽了。旁人瞧見了刀子的鋒芒,確實會跟著講理許多,至少遇到我們,會主動選擇繞道而行。但是我們如此……霸道行事,仍是不夠,還需要合縱連橫。桃葉之盟?我們也會。先生已經挑出了蒲山雲草堂、天闕峰、大泉姚氏,其實再加上俱蘆洲和寶瓶洲,從中各挑一個盟友,最好再與那皚皚洲劉氏打好關系,足夠了!比如謝劍仙,既是皚皚洲劉氏的供奉,又是我們的客卿,是不是可以勞煩她幫我們捎話?不過千萬千萬不能讓謝劍仙覺得為難,不然就得不償失了,白白浪費先生一份極為可貴的香火情。”
崔東山拊掌而笑,周米粒聽是沒太聽懂,反正跟著拍掌就沒差了。
隋右邊突然說道:“我可以擔任下宗的首席供奉,等我元嬰境。”
種秋笑道:“我可以陪著曹晴朗走一趟桐葉洲,曹晴朗先歷練個幾年,不著急當什麼宗主。”
米裕見大局已定,就立即變了主意,笑道:“我可以給種夫子搭把手。”
曹晴朗、崔東山、種秋、米裕、隋右邊,再加上一個暗中策應的姜尚真,幾乎可以算是萬無一失了。
陳平安問道:“蓮藕福地?”
種秋笑著反問道:“山主?”
陳平安啞然失笑。
長命突然問道:“灰蒙山那邊?”
在灰蒙山,其實還有三人隱居修行:化名邵坡仙的朱熒王朝余孽和婢女蒙瓏,以及化名石湫的昔年俱蘆洲打醮山渡船女修春水。
陳平安沉默片刻,點頭道:“先送走觀禮客人,我再去趟灰蒙山。如果他們自己願意,就加入落魄山譜牒。”
長命不再言語。
陳平安坐在椅子上,雙手籠袖,怔怔望向大門。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商議,例如蓮藕福地、三條商貿路线、與大驪王朝的關系處理、賬房那麼多神仙錢的處置、山水邸報的扶植、主峰集靈峰山巔那座山神祠遺址能否打造為一座護山劍陣中樞……等到陳平安回過神來的時候,發現祖師堂除了自己,其他人竟然全走完了。
陳平安站起身,轉身倒退而走,停下腳步,抬頭望向那三幅掛像,沒來由想起自己還是一個泥腿子的時候,在仗劍劈斬穗山之前,曾經無意間說過一句“打就打”。
是與阿良閒聊過後,才知道在萬年之前,早就有一個年輕劍修在水畔撂下過一句“打就打啊”。
陳平安笑了起來,轉身大步走向祖師堂大門。
至於第二夢問心局的勝負手,陳平安在齊瀆時其實就已經明白了,想要贏過大師兄崔瀺,就要先有我下棋能贏過繡虎的心氣。
有此心,依舊未必能贏,可若無此心,肯定萬事皆休。
一襲青衫背劍離去,微笑道:“我是清都山水郎。”
當青衫劍客跨過門檻後,陽光照耀下,所有等在外邊的人都不約而同地齊齊望去。
無論是他們的先生,還是師父,或是山主,所有人都覺得那個走出大門的男人,恍若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