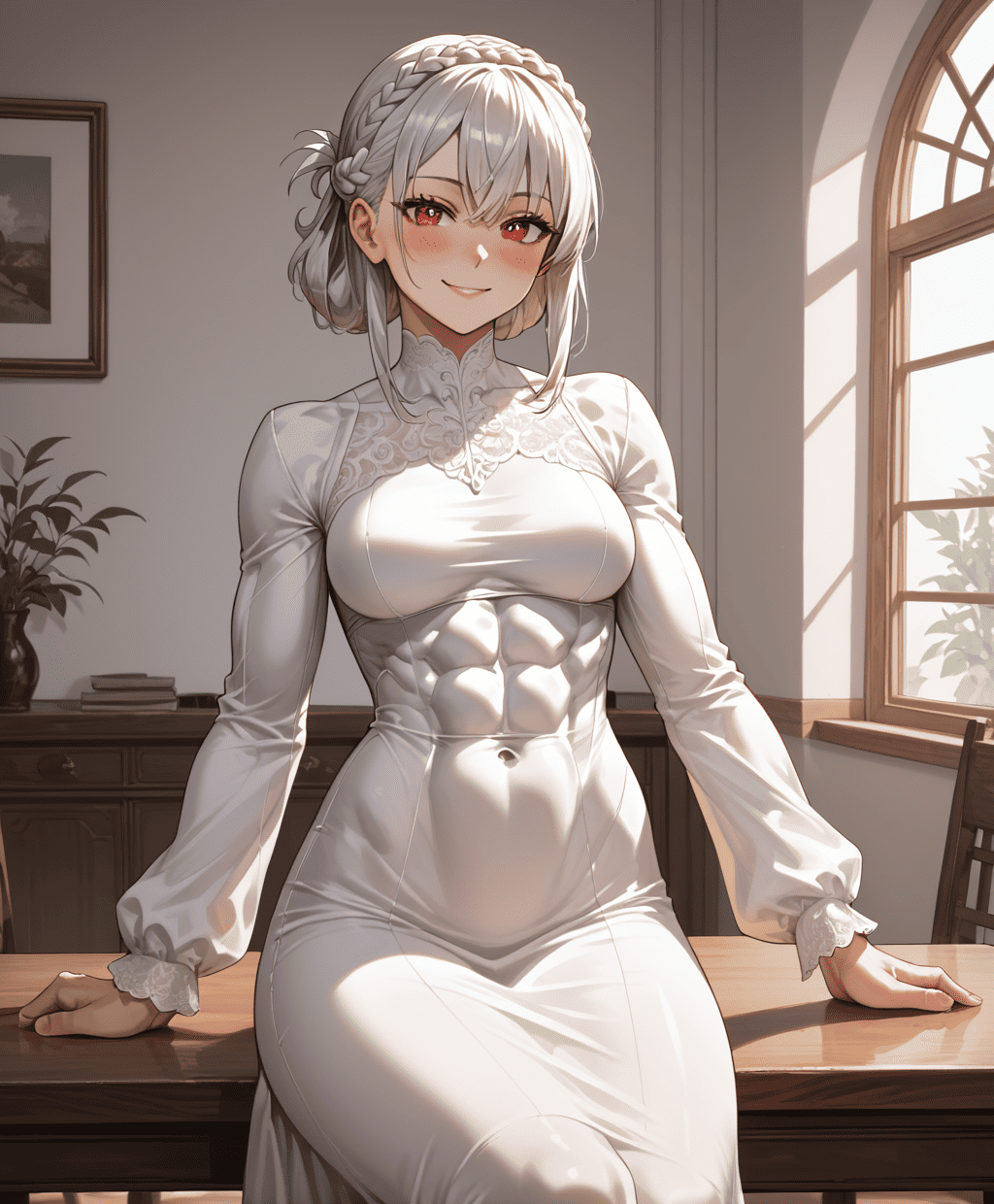銀鈴驚夢——老騷貨死得再淒慘絕美,也只是淫靡江湖路上的一條死狗而已
八 最愛的肉體
“鐺——鐺——鐺——”
石錘連番擊打通紅的骨棒,爆出一聲聲金鐵特有的脆響。
“干娘,傷還未好通透,莫要妄動干戈。” 柳子歌吊著一只胳膊,只能單手環抱鶴蓉,“昨日我就勸過你了,非得去撿鐵骨。你瞧,搞得內傷復發了不是。”
“無事,干娘好得很。”鶴蓉又是一錘,砸得火光四濺,“好不容易搭好了爐台,不一鼓作氣,可就浪費了。”
“況且……”鶴蓉意味深長的撫摸小腹,低聲自言自語,“時日無多了。”
“鐺——”
石錘再度落下……
轉眼,經冬逢春。在百二十余天後,赤鐵槍終於鑄造完成。鶴蓉打造的不止是一枚赤鐵槍頭,還有六套小臂長的鎖鏈,以及每套鎖鏈配備的一枚手指長的赤鐵鏢。槍杆以巨樹落下的樹杈之芯制成,這段枝芯強韌非常,與赤鐵槍堪稱天作之合。
與此同時,柳子歌與鶴蓉的傷勢幾近痊愈。兩人夜夜笙歌,有時不分黑夜白晝。
春風掃地,播撒一片翠綠,引萬物如夢初醒。
“既然槍已打造好,是時候教你干娘的絕技——天南地北眾生平等槍。”鶴蓉將長槍拋給柳子歌,又問,“可曾使過槍?”
柳子歌搖頭。
“如此來看,你需要學的可多了。”鶴蓉以木杆為槍,來回掄了幾圈,“槍,素有兵器之王之稱。所謂‘一寸長一寸強’之理,乃槍術核中之核。槍術基本功有三:攔,拿,扎。今日我便教教你。首先,攔。記住,前手提壓腕不翻,後手旋擰肘不搬。”
鶴蓉托槍戰立,又告誡柳子歌“槍是攔腰鎖,不可離腰”,遂而重心向後,步伐前弓轉後弓,向後輕幅拉槍,又繃緊腹肌,肚皮向前頂,扳手上抬,擺出蓄勢待發之勢。
“再者,拿。腰腹聚氣緊頂杆,三點合力見拿攔。”
鶴蓉以胯為膝,弓步轉馬步,前掌反手轉正手,帶動槍杆自上落下,旋杆止於腰胯。
“最後,扎。扎槍蹬腿塌腰轉,弓步登山力無邊。”
語畢,前掌虛窩,後掌速速推進,一槍刺出,正中面前圓石。但聞“砰!——”一聲爆響,一丈見厚的石塊被光禿禿的木杆扎了個對穿。
“歌兒,定要記住口訣,臂伸肩順似衝拳,合握把端力達尖。貼杆而入時機抓,出神入化不虛發。來,你試試,若能將槍杆刺穿與之相當的巨石,我便再教你基礎槍法十式,刺、撩、撥、絞、挑、壓、劈、崩、舞花。”
柳子歌依照鶴蓉所演示,以木杆為槍,攔槍拿槍,最終一扎而出。
“砰!”
木杆震得柳子歌虎口發麻,聲是響了,石塊紋絲不動。
“嗯……這點力道可不夠。”鶴蓉立在柳子歌面前,解下獸皮衣,脫得一絲不掛,遂雙手抱頭,袒露腹肌與肥乳,立在柳子歌與石塊間,“來,將干娘的肉體當靶。干娘要看看,你哪兒使的有問題。”
柳子歌半收木杆:“莫要逗我了,干娘。”
“不逗你。憑你的本事,還傷不著干娘。”鶴蓉手指騷臍,催促道,“快,先試試刺肚臍眼子。”
“干娘……”
“來吧!”
“那得罪了。”
柳子歌扎好馬步,擺出架勢,攔拿扎三式擺得有模有樣,槍頭擰得飛旋,一扎而去,扎出“啪——”的一聲肉響。鶴蓉嬌肉一顫,泛起一片漣漪。
“嘶……”鶴蓉低頭看向雪白的肚皮,皺起眉頭,鮮有的露出厲色,“干娘叫你扎的是肚臍眼子,你怎扎到小腹陰毛叢里了?落得再低些,就得捅進老騷穴里了。不成,准度太差,再來!”
“好。”柳子歌舒了口氣,重新振作,目光先瞄准,再以掌力催動槍杆。
“啪——”
須臾間,槍頭疾疾而出,奈何此番扎得偏高,正中肝部腹肉,陷入肥厚繃緊的腹肌中,引得周遭肌肉通紅一遍。挨了爆肝一擊,鶴蓉胃腔翻涌了幾下,嬌肉遂而顫了顫。
“不夠准。”鶴蓉豐腴的肉身晃了晃,手指肚臍眼子,喝道,“手要穩,眼要准,槍頭忽高忽低,恰是你心緒不寧所致。看清楚,眼下干娘是你的敵人,干娘的騷臍眼子是弱點,瞅准刺就成。以後對付別人亦是如此,不可遲疑!”
“好,干娘得罪了!”
長槍在掌心中回旋,忽而撩起一陣疾風,留下一道虛影,直直扎入鶴蓉拉伸開的肚臍眼子。鶴蓉不由得退後兩步,肉臍周遭一片通紅,八塊腹肌為之顫栗。站穩腳跟後,她微微頷首,道:“不錯,准度夠了,可惜力道還差點。來,再刺!有能耐就一鼓作氣,將干娘的騷臍捅個對穿,干娘便任你臍奸!”
柳子歌吞了口唾沫。鶴蓉內力非凡,以柳子歌的槍術,光捅出點血沫子,便是大進步。奈何他熱血上頭,只想讓干娘體會體會自己的進步。他純粹的心思倒也中了鶴蓉的意,唯有心如明鏡,才能做到三點一线,精准且力足。
“喝啊!——”
一聲長喝,雙臂爆發的力道將木杆槍狠狠推出。槍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扎入鶴蓉泛紅的肚臍,逼得她再退兩步。臍芯的隱隱作痛令她明白了柳子歌之進步神速——每一扎都比上回更凶猛,若再如此,恐怕正要給扎破臍芯了。
“再來!”為換得柳子歌的進步,鶴蓉不惜以自身肉體做代價。
柳子歌只當鶴蓉承得住自己頻繁出槍,自然毫不收力,又是一頓猛扎,扎得鶴蓉臍芯劇痛,竟當場尿水失禁。濕漉漉的黃水噴了滿地,稀里嘩啦大作響——雖說距離扎穿肉臍還早得很,可鶴蓉這把年紀,禁不住如此折磨。
“扎得好……” 肉體雖不堪重負,意志卻寧死不屈。鶴蓉直視柳子歌,吞了口唾沫,繼續手抱腦袋,不露怯色:“來,嘗試扎穿干娘的騷臍。”
“啪!——啪!——啪!——”
連番猛扎下,鶴蓉不斷退步。
“干娘,再吃我一槍!”
柳子歌雙臂似蓄足力道的獸筋,迅迅推動長槍,一發既出,正中毫無防備的騷臍。光禿禿的槍頭陷入臍孔,扎得鶴蓉腹肌凹陷,當場口吐酸水,嬌聲哀婉:“呀啊!干娘的肚臍眼子呀!……”
盡管鶴蓉下意識繃緊腹肌,將木杆頭緊緊夾住,柳子歌卻奮力一拔,抽出杆頭。隨之,鶴蓉四仰八叉的栽倒在地,尿水泉噴。其肉臍被破,流血潺潺,而木杆頭拉出的一縷血絲連向了這口肉臍。
“干娘!”柳子歌忙扶起鶴蓉,“你的肚臍傷至如此,不可再做我的靶子了。”
“無事,刺得不深,只扎破了皮,還未通透。”鶴蓉揉起肚臍眼子,道,“記住了麼?這便是刺中肉體的感覺。”
“記住了。”
“不錯,好……”鶴蓉重新起身,再次手報後腦,擺出人肉靶的姿勢,“干娘的騷臍是廢了,來扎干娘的肥乳!將奶頭當靶心,繼續練!”
“我怎舍得……”
“歌兒,干娘早已是你的所有物。”鶴蓉不顧臍芯淌血,雙臂高舉,抱著後腦,兩腿叉開,斷腿乍起馬步,昂首挺胸,擺出不屈又風騷的姿勢,似不懼犧牲的巾幗英雄,任憑柳子歌蹂躪,“來!莫非你要辜負干娘一番心意?”
見鶴蓉不由分說,柳子歌唯有回到訓練時的心態。此時,他的目標是鶴蓉左乳頭,比肚臍眼子高幾尺。他得調整姿態,以應對鶴蓉左乳。
“喝啊!——”
一槍既出,未中乳頭,倒扎在了鶴蓉肋骨上。她退了退,只覺得下肋痛楚難當。她嬌叱:“歌兒,槍是死的,人是活的。奶頭比肚臍高,你要瞧准了再扎!”
“好!”
槍頭再出,正中肥乳,但離乳頭仍差兩寸。鶴蓉的肥乳被扎得左右一同亂甩,乳汁榨得噴濺。但聞她厲聲嬌叱:“差一些,再來!可別替干娘心疼奶頭,只管扎。記住,准是第一要義!”
“啪!——”
亂顫的肥乳吞沒了槍頭,鶴蓉黛眉緊蹙,乳頭傳來的劇痛令她不用低頭便知道柳子歌扎准了目標。
“呃……好!現在扎右乳頭。”
“啪!——啪!——”
柳子歌扎得太用力,准頭偏了不少,卻扎得鶴蓉胸脯劇痛,幾乎透不過氣。自知准頭不夠,他立馬收槍,待自己定下心,再次扎出一槍。這回,他不僅扎中了鶴蓉的乳頭,更扎得乳頭鮮血淋漓,與不止流淌的乳汁混做一股粉色肉汁。
鶴蓉欲開口言語,可垂絲的唾沫卻在言語前淌下了嘴角。
“呃……”鶴蓉疼得滿頭冷汗,一身厚重的腱子肉變得笨拙,可她仍不甘低頭,將汗濕的腋窩面向柳子歌,“干得好,力道與准頭都上來了。現在,扎干娘的右腋窩。”
不待鶴蓉站穩,柳子歌一槍刺出,偏了稍許,扎在了乳側,連腋毛都未能沾到。鶴蓉吃痛,險些落下胳膊。柳子歌趁其將落未落之際,猛地再扎出一槍,直抵腋毛叢中心,換來鶴蓉“嗷!……”的一聲悲慘哀嚎。
“干娘,如何?”
“歌兒會愈發靈活的調准槍頭了呢……”鶴蓉吞了口火熱的唾液,濕潤的目光落在柳子歌槍頭,“接下來,我讓你扎何處,便立即扎何處。”
柳子歌擺好姿勢,嚴陣以待。
“左乳頭!”
鶴蓉一聲令下,柳子歌當即出槍,一扎即中。
“再快些,莫要猶豫!右腋窩!”
鶴蓉再一聲令下,柳子歌出槍又快了幾分,叫她來不及准備,痛楚便鑽入心窩。
“好,再來……”鶴蓉仰面,作無畏壯,“左腋!”
“呲——”
一陣破風聲響,鶴蓉嬌肉被木杆頭扎得一片通紅。
“再來……左乳!右乳!肚臍!小腹!左乳!咽喉!肚臍!咽喉!肝!左右腋連刺!小腹!肚臍!……”
鶴蓉愈喊愈快,柳子歌勉強趕上,頻頻刺中嬌肉目標部位,扎得鶴蓉一身腱子肉瘋狂顫抖。可鶴蓉仍不滿意,大呼:“快快快快!准!狠!萬不可懈氣!再扎,衝干娘身上照死了扎!別怕,畢竟干娘可不是輕易會被你扎死的!咽喉!左乳!右乳!左右乳頭連扎!肚臍!小腹!乳溝!咽喉!……”
柳子歌愈扎愉快,鶴蓉卻大呼用力。誠然,在速度與准度的壓力下,柳子歌的力道未能跟上。鶴蓉一提醒,他便專注意志,奮力出槍。
“左右乳連刺!左右腋連刺!小腹咽喉連刺!肚臍三連刺!……”
在鶴蓉指揮下,柳子歌極力猛扎,招招命中要害。鶴蓉愈發吃力,竟感到力不從心。柳子歌的槍頭一次比一次更威猛,快逼近鶴蓉的極限……
鶴蓉不由得單手撐地,險些栽倒,唾沫泡止不住的淌。待她重振旗鼓,搖晃起身,兀自苦笑:“果然……這身下作的賤肉已經……呵呵……真無奈呀……”
“干娘?”
“肚臍!……”最終,鶴蓉自知自己力竭,索性叫柳子歌扎向早已鮮血淋漓的肉臍。
“喝啊!——”
柳子歌一聲驚天地泣鬼神的叫喝,木棍疾刺鶴蓉綻開的肚臍眼子,頃刻間深陷臍中,被腹肌死死咬住。健碩的艷肉打飛三五步遠,墜地後又滾了數圈,最終四仰八叉的倒下。木棍似生了根般立在她肚臍之上,肉縫間偶有幾縷鮮血滋出。她渾身肌肉痙攣,翻起白眼,吐著舌頭。若非柳子歌叫喚,她都無法自行回過神。
“干娘,到此為止罷,我已心中有數。”柳子歌抽出木杆,不料一泡鮮血飆出鶴蓉肚臍,在柳子歌面頰留下幾點梅花。
鶴蓉有氣無力的撥開肉臍,向柳子歌展示臍芯。但見臍芯雖一片血淋淋,似捶打了百八十下的牛肉,卻始終未被穿透。鶴蓉只道:“歌兒,干娘身子硬朗得很……瞧,干娘的騷臍眼子……仍好好的,你可沒能穿透呢……”
望著虛弱不堪,卻仍舊逞強的鶴蓉,柳子歌一把扣住她的一雙手腕,將之壓在身下。遂而,陽根畢露,壓在鶴蓉小腹。鶴蓉渾身香汗,肥碩的巨乳起起伏伏,呼吸愈發急促。這副受盡磨難的下賤模樣著實誘人,柳子歌已忍至盡頭。
“干娘,讓我換一杆槍再做嘗試~”柳子歌火熱而迫切的吻著鶴蓉的紅唇,繼而轉向面頰、脖頸。他邊吻邊抱怨:“能否將你干得人仰馬翻,拭目以待吧~”
“等等,歌兒~這會兒還早~是否太急了?~”鶴蓉面色緋紅,“干娘一身肉好疼~”
柳子歌心火自上而下,燒得難以按捺。猶豫再三,他終敵不過愧疚,便說道:“抱歉,干娘允諾自己是我的東西,我便當真了~怪我得寸進尺~”
“不是的,歌兒~”鶴蓉咬著朱唇,明眸撲朔,“好嘛~進來便是了~”
得到鶴蓉允許,柳子歌喜出望外,當即探出下體。可鶴蓉臍肉傷勢頗重,柳子歌憐香惜玉,終究未再續前緣,轉而攻其下路,陽根緩緩沒入早已濕漉漉的肉穴中,在來回徘徊中,徐徐挺到底。
“嘶~”隨陽根陷入,鶴蓉的臉蛋愈漲愈紅,不禁昂起腦袋,倒吸一口氣,放松了渾身肌肉,“干娘最喜歡歌兒的根了~好大~蜜穴又淪陷了~呀啊!~動了~嗚~歌兒的陽根在肚皮里攪得滋滋響~嗚~攪得肉壁濕潤一片~好舒服!~”
香雲沁脾熏人醉,蜜水入夢化甘風。
鶴蓉嬌肉慕然痙攣一陣,肉欲昭然若揭,呼吸漸漸深沉。這副醉生夢死的淫亂模樣引得柳子歌愈發難耐。他將臉埋入鶴蓉汗濕的腋窩,舌尖撥弄毛梢,細細品味其咸香。嘗個心滿意足後,柳子歌笑道:“味道真騷,干娘很懂呢~白花花的健碩淫肉被扎得滿布淤青~竟還有如此雅興~干娘的欲火成日成日的熊熊燃燒著吧?~”
“嗯~干娘才沒如此淫蕩呢~”鶴蓉扭過頭,卻被柳子歌吻住了纖長的脖頸。一通啃咬猶如啃鴨脖,吮吸得享受。鶴蓉又羞又恥,可又詭異的舒服。
空氣愈發燥熱,柳子歌愈發貪婪的吻著嫩白的肉體,軟糯的雪肉在唇齒間融化,殘留一片汗味騷香。縱使他夜夜品嘗鶴蓉的美肉,可肉欲是無底洞。濕潤的汗汁將兩具糾纏的肉體沾作一體,黏連的皮肉間“滋溜——滋溜——”發響。鶴蓉一身淤青逃不過欲望的舌苔,一遍遍的吮吸竟令傷痛變得麻木。
鶴蓉口吐熱氣,張開肢體,任柳子歌肆意嘗盡每一寸香肉,口中喃喃:“嗚~干娘渾身變濕漉漉的~要上下失守啦~”
連連刺激下,鶴蓉一身肥壯的肌肉止不住亂顫,腰肢似風中烈火般扭動。下一刻,蜜水噴射不止,如忽然炸開的爆竹。然而,柳子歌的陽根卻迎著噴汁的蜜穴高歌猛進,榨得汁水四濺,害她幾近痴癲,不禁瘋狂呻吟:“呀啊!~呀啊!~歌兒的舌尖如刻刀般犀利,一刀刀剮開干娘的騷肉~哈哈~舒服極了呀~歌兒要將干娘殺死啦!~”
柳子歌迎合道:“既然如此,那我就將干娘肏到死~再繼續淫玩干娘的屍首~”
“呀啊~”鶴蓉爽得緊閉美目,不顧吐在嘴邊的舌頭,參雜叫春的言語似夢囈連連,“哈哈~干娘的屍首,可真是愚蠢又悲慘呢~嗷~可干娘又好幸福~嗷~被歌兒肆虐~被歌兒奸殺~嗷!~干娘好期待~嗷!~好喜歡~嗷!~干娘的屍首,若能在歌兒懷中腐爛~那便是極大得幸福~呀啊!~”
原本的傷痛不翼而飛,鶴蓉只沉浸在了肉體歡愉中。汁水交錯,兩人一步一步逼近肉欲構築的極樂世界……
……
日升月落,彈指間百余日匆匆逝去。遭地震肆虐的野谷再度生機勃勃,鳥語花香與燥熱的空氣一同宣告夏日初至。
早功一過,柳子歌感到內力又進一步,與墜谷時已有天壤之別。下午,他在鶴蓉指導下練了幾遍槍術。今時今日,他的槍術與日俱進,已完全掌握了其中基礎。
至入夜,便是期待已久的獎勵時刻。身居胯下的鶴蓉舒展四肢,晃動肥乳,漫扭腰肢,傾盡全力展示自己一身艷肉的美妙。柳子歌當仁不讓,爭分奪秒的享受胯下艷肉帶給他的無上歡愉。
雖說每晚的交歡是獎勵,獎不獎要視柳子歌的表現而定,然而兩人從未錯過一天。鶴蓉將一身淫靡的騷肉當做撫平柳子歌疲憊的器物,任柳子歌親吻深不見底的肉臍,親吻汗味發酵的腋窩,舔舐白嫩的乳肉。她沉醉其中,流連忘返。
柳子歌一股而出,榨得鶴蓉汁水噴涌。
“哦~今日又是~徹頭徹尾的無上大滿貫~”鶴蓉玉指搓揉玉谷,拉出一縷晶瑩白絲,含入口中,細細回味余溫。
“干娘的肉怎麼玩都不過癮呢~” 柳子歌在鶴蓉八塊腹肌上畫起圈,“每日練同樣的功夫,日子乏味極了~也就肏干娘的美肉能讓我有些盼頭~”
“嗯~歌兒的槍術算有些造詣~”鶴蓉胳膊墊著腦袋,平躺開,“既然如此,明日教你天南地北眾生平等槍法吧~”
“那可好了~”柳子歌翻身騎上鶴蓉小腹,雙掌自下而上撫摸其肉體,自小腹至肥乳,柔軟的肉感充斥每一寸指縫尖,“既然干娘贊揚了我,我多享受些也無妨吧?~”
鶴蓉又一次淪落為柳子歌胯下玩物,無法自拔……
“嗷嗚!——”
谷間幽夜,狼嘯再起。萬物復蘇,焉知禍福。
……
日上三竿,一杆赤鐵長槍立在柳子歌與鶴蓉之間。鶴蓉將六條一尺有余的鎖鏈鏢掛在槍頭底,以鎖鏈鏢代替槍纓。
“這叫六道鎖纓,是干娘為天南地北眾生平等槍法特配的物件。一來,可增重槍頭,加強威力。二來,亦有別的妙用。”鶴蓉旋轉槍杆,鎖纓如傘般展開,宛若被風卷起的裙擺,“先教你第一式,治亂所起。”
話音一落,鶴蓉迅迅舞槍,鎖纓繞槍杆回旋,而槍杆又繞鶴蓉雙臂掄舞。看似華麗,實則進可攻,退可守。
“來,攻我!”
鶴蓉一喚,柳子歌持木杆而上。可眼看槍花陣陣,密不透風,叫柳子歌犯了難。此時,鶴蓉槍杆一收一挺,又似落雷般疾疾劈下。不等柳子歌反應,槍杆連帶六道鎖纓,猶如豺狼虎豹之利爪,將腳邊磐石撕碎得四分五裂。
若非鶴蓉有意避開,柳子歌必死無疑。
鶴蓉再掖起槍花,道:“記住,知亂之所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起,則不能治。注意觀察,槍頭一出,直扎要害。”
槍花里一圈,外一圈,若要攻鶴蓉本體,那是難上加難。柳子歌一想,不如攻槍軸,於是立馬出槍。怎料鶴蓉早有所料,槍頭一收,再次劈向柳子歌。
“砰——”
柳子歌一陣,身邊被劃出一道深坑。
“招式可記住了?”鶴蓉將赤鐵長槍拋給柳子歌,“依照干娘掩飾的,多練習練習。干娘再教你一點,此槍法與尋常槍法略有不同。槍為臂之延伸,纓為槍之延伸。你將五道真氣灌入槍杆,以之向外,以掌法運行槍法,如此試試。”
遵鶴蓉之教誨,柳子歌比劃了幾番,頓時恍然大悟,一杆長槍在手中舞得虎虎生風。
鶴蓉十分高興,肥乳亂跳,鼓掌大呼:“歌兒果真適合本教武藝,一點就開竅了呢!”
“干娘,此槍可起了名字?”
鶴蓉搖頭,道:“尚未起名呢。不如歌兒起一個?”
“好。既然此槍通體赤紅,轉之如烈火焚燒疾馳的車輪,不如叫灼輪,如何?”
“嗯,灼輪槍,聞之甚妙。”鶴蓉微微頷首,手把手指導起柳子歌來,“歌兒,若歌兒努力,干娘便多獎勵於你~要早些將此槍法融會貫通哦~”
搖曳的火光愈發微弱,熄滅前,鶴蓉只乞求不虛此生。
……
所謂天南地北眾生平等槍法,一共六式,講求攻守兼備,內外兼修,以槍為臂,以纓為槍。第一式,便是鶴蓉已傳授給柳子歌的“治亂所起”。柳子歌修習三十余日,至盛夏,大功告成。
天氣升溫,山谷宛如一口大蒸籠。無論刮來的是東南西北風,皆擾人心煩。
“若來一陣雨多好。”
柳子歌光著膀子,僅僅穿了條兜襠的褲衩,以免巨物亂甩。鶴蓉沒有甩根之憂,更索性打赤膊,自早到晚一絲不掛。可惜山谷寂寥無人,唯有柳子歌可以欣賞與褻玩這一身健碩的零碎。
“呼……從未遇過如此難耐過的夏日。”
鶴蓉面露疲憊,蒸出一身香汗,柔荑漫扇,欲揮去一身暑意。一輪演練下來,她見柳子歌已學有所成,於是又教了一招“惡不相愛”。這是平等槍法中破敵戒備的一招,與尋常破招不同,講求敵進我退,敵退我進。其中退有退招,進有進招,進退得當,態勢如猛虎蟄伏。進退中積蓄內力,最終五道內力擰成一股,一擊擊破,擊破則制勝,不可留反復交手的余地。
講解過大意,鶴蓉再一一分析進退之中的手法與步伐,聽得柳子歌應接不暇。好在鶴蓉耐心十足,非教會柳子歌不可。
多虧先前的經驗,柳子歌愈發得心應手。較之先前,柳子歌學第二式快了不少,僅費二十余日。於是,鶴蓉又接連教授了第三式“挈山越河”、第四式“乍光四方”、第五式“兼者聖道”。與此同時,柳子歌學得愈來愈快,至第五式學成時,只費了五天。
初見金葉飄落,酷暑恰散去大半。
“入秋了,沒想到日子過的如此快。咳咳,尚有最後一式,干娘今日教你……”鶴蓉執起長槍灼輪,一轉槍杆,鎖纓便似裙擺般展開。頃刻間,鎖纓卷起一陣雄風,砂石為動,落葉回旋,繼而溪水倒流,泥土翻騰。只聽鶴蓉邊飛舞長槍,邊指導道:“此式名為‘天下兼愛’,重在丹田一口氣,一氣分五形,五形化五氣,旋中有直勁,勁中有旋力。要使槍勁貫徹天地間,頂天立地……”
說話間,槍風越卷越興,山谷間陣陣唦唦作響。山石欲崩,雲雨驟變,不禁令柳子歌想起了地動山搖的那天——他從未見過如此威力無窮的招式,不由得怔住了。
鶴蓉一聲嬌喝,隨一道驟來的霹靂一同落下。柳子歌覺得暈眩,再聽不見半點聲響,只顧愣愣的看著鶴蓉一槍落在自己跟前。
“轟隆!——”
遲來的雷聲貫入雙耳,柳子歌回過神,卻見千重雷霆將黑天與遠山相連。天地之間,鶴蓉執槍佇立,卷起的風浪如余音繞梁,遲遲不息。
“歌兒……”鶴蓉威立的嬌軀忽而一顫,一口熱血涌出嘴角。柳子歌忙上前攙扶,卻見鶴蓉又是一口熱血涌出咽喉。
“干娘,怎會如此?干娘?”
“無事……”鶴蓉強捂陣痛的腹腔,不忍又是一口熱血,“莫要擔心干娘……歌兒,方才演練的招式,可記住了?”
鶴蓉這副模樣怎可能安然無事?柳子歌憂心忡忡,一摸鶴蓉脈相,心當即涼了半截。他竟從未注意到,鶴蓉身中劇毒多時,如今已深入骨髓,五髒盡毀,已是行將就木,病入膏肓,藥石不靈,只待天命。
“歌兒……可記住了?”聽不見柳子歌作答,鶴蓉再問,“歌兒,回答干娘!”
柳子歌咬著牙,一想鶴蓉竟忽然垂死,淚水情不自禁:“干娘,恕孩兒愚鈍……”
“歌兒不愚鈍……能學得如此快……已是很好……很好了……干娘能教你的……已教完了……最後再為你演練一回,‘天下兼愛’吧……”
鶴蓉強忍腔內劇痛,再執長槍,疾舞而起。這趟,柳子歌睜得渾圓,一眨不眨,將鶴蓉最後的舞姿深深刻在腦中,直至長槍落地,鶴蓉踉踉蹌蹌走了幾步,栽入柳子歌懷抱。
“嗷嗚!——”
狼嘯環抱,遮天蔽日。
忽而大雨傾盆,將垂死的嬌軀浸得一片濕滑。
“干娘撐著,我用內力為你將毒逼出來。”
“何必呢……”鶴蓉自柳子歌懷中起身,搖搖欲墜立起身,一身傲人肌肉爆發出最後的力道。但聞鶴蓉又說道:“歌兒,你尚且年輕,莫將余生葬在空谷中……那頭山勢較低……若有機會,爬上去!……”
“嗷嗚!——”
倏忽間,狼嘯愈發逼近。
滴滴答答,雨聲仿佛催命的鑼鼓點,愈發急促,愈發噪人。
“常有人說畜生不通人性……呵呵……這不是很通人性麼?”鶴蓉僅靠意志支撐起嬌軀,面露苦笑,“我一垂死……畜生們便來索命了……”
“嗷嗚!——”
狼嘯過三。樹蔭間,草叢中,閃爍起點點幽光,綠中泛寒,似繁星墜入幽冥。
“歌兒,走!”
鶴蓉一聲大呼,頭狼忽然奔來。鶴蓉舉槍刺殺,卻被頭狼左右騰挪,巧妙躲開。緊隨其後,又有三頭惡狼猛撲而來。鶴蓉唯有棄攻為守,掄槍逼退來狼。槍頭刺穿滴落的雨水,發出一絲清銳的鳴響。
與此同時,柳子歌亦被兩頭惡狼盯上。狼來得一陣火花帶閃電,張牙舞爪的要撕開柳子歌皮肉。柳子歌唯有肉拳相搏,左一個劈掌,砸得一頭畜生眼冒金星,右一個衝拳,崩得另一頭畜生九月桃花開。怎奈何雙拳難敵四手,轉眼又有惡狼前仆後繼。柳子歌能了結一頭是一頭,可長江後浪推前浪,那是一浪更比一浪強。新的還未解決,被砸暈的狼又醒了來,衝他是一通撕咬。
“該死的畜生,今天就替閻王收了你們!”
柳子歌身軀一震,灑落一身雨水,遂全力踢出一腳。那狼牙還未扎入他皮肉,便連帶整顆狼頭,被柳子歌一腳踢得迸裂,炸得腦漿遍地,鮮血飛濺。狼血也是熱的,可狼卻冷血至極。更多惡狼踩著同類的屍骨,向柳子歌殺來……
鶴蓉一槍挑飛頭狼左右手,將頭狼逼退五步外,回頭卻見柳子歌身上披了好幾條惡狼。她當即投出灼輪槍,大呼:“歌兒,接槍!”
“呲——”
槍鋒在大雨中劃出一道剔透的水线,轉瞬即逝。繼而,鮮血翻涌。
灼輪穿透掛在柳子歌背上的兩條惡狼。惡狼的嗚咽未喊出口,便成了槍下亡魂。柳子歌猛然一回頭,瞥見長槍豎立背後,當即拔槍。槍杆一震,甩飛兩具狼屍。
若一人一狼拼死相搏,先死的未必是人,可眼下柳子歌以寡敵眾,唯有掄槍退敵。望著虎視眈眈的狼群,柳子歌不禁倒吸一口冷氣。他想著,若這群畜生都是人,那自己必是十死無生。無論什麼精妙的招式,在如此緊密的包圍下,都無法輕易施展。好就好在,眼前的畜生不過是畜生。
“不過是看家之犬,狺狺狂吠,徒增虛威,實則黔驢技窮。”柳子歌啐了口唾沫。兵器在手,他信心倍增。趁狼群攻勢逐漸減弱,他再度執搶而上,鎖纓展若裙擺,立即斬下兩顆狼頭。
有幾頭惡狼見狀,調轉風頭,向鶴蓉奔去。鶴蓉對付的不止頭狼,又有四五頭正值壯年的惡狼向她飛撲來。她趕忙崩出一掌,掌力猶如五雷轟頂,當場便將一頭畜生埋入土里。
“噗……”
一口熱血涌出咽喉,鶴蓉五髒六腑如千萬螻蟻啃食一般劇痛,垂垂危矣。
瓢潑大雨洗刷滿地血水,卻使之染得更紅。
幾番洗禮,健碩的嬌軀若沁水的玉雕,肉體輪廓隨劇烈呼吸忽漲忽縮,鮮嫩肥乳泛起陣陣漣漪。
更多惡狼加入了針對鶴蓉的包圍圈,圍得水泄不通。鶴蓉抹去嘴角血沫,甩甩腦袋,勉強清醒幾分,健壯而疲憊的嬌軀猛然一震,遂兩掌拍地,激起一片水波。但見“砰”一聲炸響,洶涌氣浪自鶴蓉向外擴張,掀翻狼群。幾只體弱的當場七竅流血,更有甚者腦殼碎裂,崩死於鶴蓉的內力之下。
“畜生……饞我的肉許久了吧?……”鶴蓉啐了口血沫子,面對源源不絕的惡狼,唯有握緊拳頭,殊死一搏。
一頭惡狼飛撲而來,鶴蓉一聲嬌喝,赤手空拳迎上,重拳直捶其下顎,打得那畜生上下顎分離。飛遠的下巴帶走一片鮮血,軀干卻落在鶴蓉腳邊,濺了她滿臉血。她接一把雨水,抹去面頰上的血,繼續奮戰。又見她左一招“白鶴望月”穿心掌,拍得一頭惡狼心窩前後對穿,右一招“蛤蟆蹬地”連環踢,僅以斷腿便將另一頭惡狼踹成了赤黑的面糊。
大雨滂潑,惡戰更甚。
鶴蓉的招式有多麼凶悍,死狼們有目共睹。怎奈何,她終究架不住人老體衰,又被一身劇毒拖累。忽然一頭惡狼撲在她背上,一爪子下去,剌出三道貫穿脊背的血爪印,皮肉外翻,鮮血淋漓。
“呃啊!……”
鶴蓉痛苦回身,扼住將偷襲者脖頸。強忍劇痛下,她卯足力道一通撕扯,將狼頭拔出脖頸,連帶脊椎丟入狼群,砸開一波躍躍欲試的畜生。正當此時,又一頭惡狼發起伏擊,猛撲她肚皮,大口啃咬暴起的腹肌。
狼牙入臍,血汁爆濺。
“啊!……該死……將我的肚臍眼子都撕咬穿了!……畜生,受死!”鶴蓉將之扯下肚皮,又抓起另一頭,兩狼頭一磕,撞得扁平。丟下死狼,鶴蓉苟延殘喘,緊繃的腹肌上多了一排血淋淋的牙印,肚臍眼子似淌血的泉眼。
風雨中,鶴蓉魁梧的身軀緩緩飄搖,不知還能撐到幾時。剛開口,吐出的不是言語,是如同沸水般翻騰的血泡。半晌過去,才擠出幾個惡狠狠的字:“畜生……將我傷成這副模樣……”
狼群重新集結,再度擺出包圍的陣勢,向鶴蓉發起猛攻。鶴蓉左一拳,摧筋斷骨,可剛打死一頭,又遭另一頭抓破了厚實的腰肉,右一腿,才向侵犯者予以還擊,卻再被莫名一爪子剌得肥乳飆血,肩膀血肉模糊。
“千刀萬剮的畜生,給我見閻王去吧……呀啊!……”
鶴蓉捉住一頭惡狼,將之高高舉起,欲砸飛後繼者,可怎料左右又猛撲來兩頭,猝不及防,徑直撕咬鶴蓉腋窩,好似撕咬雞翅,要撕碎她的臂膀。鶴蓉腋下被狼牙撕得直噴熱血,濃密的腋毛被血水粘成了一簇,不禁發出慘絕人寰的哀鳴。
被鶴蓉的慘叫所吸引,柳子歌一望,恰見鶴蓉身軀倒下,栽入狼群中心,如高塔坍塌,激起千層水浪。兩頭惡狼費勁功夫未撕碎鶴蓉厚實堅挺的肩臂,轉而咬其小臂。又聞“嘎啦!嘎啦!”兩聲清脆爆響,鶴蓉一對手肘反向扭曲,骨碴刺出皮肉。
“呀啊啊啊啊!!!!……………………”
鶴蓉爆發歇斯底里的尖叫,張得嘴角撕裂,長舌直立齒間。惡狼惡意大盛,一口狼吻式咬下,正叼住鶴蓉直立的舌頭,遂而硬生生將之撕扯出口腔,極力咬斷,只留半段外翻的筋皮,引得鮮血如柱,噴涌如泉。
滿天雨絲無法衝散濃烈的獸腥與血腥,徒增鶴蓉彌留之際的悲慘。
斷了半條舌頭,鶴蓉痛苦掙扎,可於事無補。折斷的雙臂尚未揮動,便被四五副狼牙撕下臂膀,血涌翻騰。雙臂盡斷,她空舞光禿禿的半截大臂,該如何能趕走來敵?
“干娘!”柳子歌殺盡了身邊狼群,欲救鶴蓉。可包圍鶴蓉的狼更多數倍,一時間無法突入,唯有眼睜睜看著鶴蓉慘遭虐殺。
“重在丹田一口氣,一氣分五形,五形化五氣,旋中有直勁,勁中有旋力。要使槍勁貫徹天地間,頂天立地……”柳子歌想起鶴蓉最後的教導,眼中浮現的是她強忍劇痛,施展“天下兼愛”的嬌艷身姿。
“我定要做到……”柳子歌眉頭一緊,全神貫注,“要救出干娘!”
倏忽間,空氣凝滯,又忽而卷起一兩陣微風。
柳子歌掄起槍杆,手中灼輪緩緩回轉,五道內力灌注槍頭,六道鎖纓隨槍杆一同回旋,如裙擺般展開。
“干娘不能死,我要殺盡這群畜生!”
一聲怒吼,真氣大盛,如一道洶涌的龍卷。
狼群似是意識到了危機,紛紛暫停撕咬香艷的嫩肉,轉頭望向柳子歌,微笑似的齜牙咧嘴,獠牙畢露。
“嗷嗚!——”
退居狼群後的頭狼一聲長嘯,引得一群惡狼再度前仆後繼。
倏忽間,環繞柳子歌的狂風猶如千萬把利刃,不見刃之形,卻見刃之利。狼群里,有的皮開肉綻,有的身首異處,有的挨了腰斬,黏糊糊的腸子淌出了五顏六色一大坨。萬般風刃將狼肉絞得粉碎,血沫激起了一片紅霧。
直至殺到鶴蓉跟前,刀風才漸漸平息。
“干娘……”望著腳跟前傷痕累累的肉體,柳子歌腦袋空空,兩腿一軟,跪倒在地。無論如何,他都無法將這具遍體鱗傷的肉體與最愛的干娘相聯系。
健碩的肌肉塊仍保留著充血時的飽滿形狀,可滲人的爪痕、咬痕卻將充血的肌肉塊劃得血肉外翻,滿身赤紅,猶如披了件朱砂衣。若只是皮肉傷,那也過得去,可鶴蓉雙臂盡毀,白森森的骨碴裸在肉外,殘存的大腿更是被啃得坑坑窪窪。她微微張開嘴兒,嗚咽聲將血泡吹得似眼珠大。
“歌兒……”鶴蓉吐字模糊,殘存半截的舌頭抽搐不止,“干娘……好疼……”
剩余的狼群不敢正面應對。頭狼一聲號令,其余畜生似狗一般灰溜溜散去了。
柳子歌抱起鶴蓉,雨水洗淨雪白的胴體,卻洗不去即將到來的命運。
“干娘,為何會如此?為何搞成如此慘樣?我不要你死,干娘……”
鶴蓉虛弱不堪,無奈以斷肢捧起柳子歌臉頰:“干娘……不能陪你了……地震時……干娘丹田受損……積壓的余毒……散入了五髒六腑……干娘早知自己……油盡燈枯……最後的光景里……有歌兒相伴……好幸福……”
“不,不,一定有救的……干娘,我帶你爬上山崖,我們找同門。干娘,你說過他們醫術神奇,定能起死回生……”
鶴蓉無力的搖頭:“干娘死得好累呀……歌兒……再肏干娘一回……行嗎?……”
柳子歌下望,卻見鶴蓉的下體被撕咬過,已血肉模糊,大小便失禁。鶴蓉似是早已知曉狀況,撥開被豁開的肉臍孔,乏力淫笑:“如今是……最後的……臍奸哦……”
人心深處盡是獸性,鶴蓉撥開肉臍的刹那,柳子歌才察覺自己早已硬得百折不撓了。奄奄一息的肉體竟令他聯想起開胃菜的酸甜可口,指尖沾上的血液更叫他心跳加速。他踟躕中抓起鶴蓉的肥乳,在掌心中把玩,榨得滿手乳汁。
“歌兒……最後……滿足一下干娘吧……”
“好。”
陽根沒入鶴蓉最後的渴求,眨眼被腹肌交縫間的肉洞吞噬。她依舊緊繃八塊傲人腹肌,雖然痛楚難當,卻始終保持不屈的硬度。柔中帶剛、外彈內實的肉感,令插入臍中的陽根爽得無法自拔。粘膩的肥腸一擁而上,纏住陽根,濕潤的血液在兩者間作潤滑汁。
臍奸,乃是人世間絕美的虐殺藝術。
如此懷念的觸感,叫柳子歌不虛此行。面對鶴蓉繃如磐石的腹肌,他使的腰勁,加力推動腰胯,一進一出,疼得鶴蓉喘息愈發粗重。
“嘶~干娘的騷臍眼子~真是回味無窮~”
“嗚……歌兒的陽根……又在……干娘肚皮里……游龍戲鳳了……”鶴蓉微微昂起頭,舒服的吞下唾沫,肌肉似微醺般透出桃紅。
“啪!——啪!——啪!——”
大雨中,肉體與肉體的衝擊激起片片水花。鶴蓉的腹肌浸泡得晶瑩剔透,柳子歌弓腰托起她的腰肢,又加了把勁。殘存的嬌軀在摧殘之下,如風中搖曳的鮮花,花瓣徐徐凋零,為殘余的生命倒計時。
“干娘的肥乳沾滿了水~大得抓不住了~”柳子歌忘我的親吻艷肉,“這副艷麗的肉,是我永遠的摯愛~”
鶴蓉有氣無力的諂笑:“無論干娘……是死是活……永遠是……歌兒之物……這身淫靡下作的賤肉……也是獨屬於歌兒的玩物……等干娘涼透……仍能做你發泄的玩物……”
兩人切切相吻,柳子歌忽感雨水熾熱,才發覺自己早已以淚洗面。
“好舒服……”
陽根在鶴蓉肚臍眼子里肆意進出,一潽一潽帶出大片血水。鶴蓉陶醉的品味著自己的死亡……高潮來襲,天昏地暗……
“干娘,來了~”
大股精汁涌入鶴蓉腹腔。與此同時,鶴蓉破爛的股間同樣漿汁混濺。絕頂中,她挺直的身板陣陣亂顫,兩坨肥乳無法控制的上下飛甩,噴射的乳汁憑空畫出兩道乳白色波浪线。
“嗯……嗯……呀啊!……死竟如此舒服……真想日日夜夜都能被歌兒虐殺呀!……啊啊啊啊!!!!……………………”
這應當是鶴蓉一生中最絕望、又最暢快的高潮。
垂死騷貨,渾身上下,該噴血的不止噴血,該出水的奮力出水。
“干,干娘?”柳子歌拔出陽根,滴了幾滴白汁,淋在鶴蓉肚皮上。不知為何,他覺得神清氣爽,世界有如輕飄飄了許多。他暗懷疑惑,抱起鶴蓉,小心翼翼道:“干娘,感覺好些了嗎?”
“呼……”鶴蓉還未作答,卻先吐出了一口血泡,不由得嗆了幾口,才有力氣說道,“干娘都要死了……怎會好些……哈……不過……滿肚子都是……歌兒的精華……干娘心滿意足了呢……”
懷抱瀕死的鶴蓉,柳子歌欲言又止。眼淚越發難耐,落在鶴蓉肥碩的胸脯上。
“嗯……”最後時刻,鶴蓉以悲傷終結,她忍痛笑道,“干娘撐好久了呢……說不定……尚能再撐一陣子……哈……歌兒……你瞧……太陽露頭了……歌兒……陪干娘說說話……便能好了……”
“干娘,方才臍奸時,你將內力傳給我了?”柳子歌問。
不知何時,雨停了,一抹陽光落在鶴蓉面頰。
“歌兒發現了呀……哈……干娘五十余年的內力……趁交歡的工夫……都留在歌兒體內了……”
“可……干娘,你若內力盡失,只會死得更快啊!”
“干娘只想你活下去……好好活下去……好好的……”鶴蓉費力的吞了口熱乎乎的血,眼神迷離,“干娘想明白了……你莫要去找什麼勞什子的明鸞……干娘不圖你救誰……莫要管什麼紛爭……什麼你死我活……憑你如今的本事……在這世道……安然無恙的活……悠然自在……就好……現在……走吧……干娘不行了……干娘就是累贅……”
如此一長句話,說得鶴蓉已無余力。
“走……”鶴蓉吐出最後一個字,“走。”
柳子歌回望,捏緊拳頭,不願棄鶴蓉而去。光影斑駁,令他不由得記起某天晌午,鳥鳴正聒噪……
在那悠然的日子里,鶴蓉拾起一段樹枝,孩童般比劃起劍招,又問:“歌兒,你說,怎樣的武道最為高深莫測?”
“歌兒愚鈍,想不明白”
“既然不明白,便毋須多想。”鶴蓉劍指雲霄,“感受穿過指縫的陽光,感受輕撫臉頰的清風,感受流過腳板的涓涓細流,感受暗藏土壤下的新生。萬物之理便在其中,在於被人忘卻的自然,在本源中。武道,當然莫過於此。艷陽可以是武,清風可以是武,溪流可以是武——武,便是生命的流動。”
“干娘……”
回過神,柳子歌面前的鶴蓉血肉模糊。微張微合的口中,已吐不出半點聲響。柳子歌忽感體內一股溫暖,才想起鶴蓉已將內力全傳給了自己。鶴蓉會與他同在,與他的生命一同流動。
“干娘,歌兒走了……”
聽聞柳子歌留下一句辭別,鶴蓉微微頷首。她欣慰,至少柳子歌能逃出生天,而她終於能合眼,與已故的同門再會。
淚水止不住流淌,視线卻愈發模糊。鶴蓉深吸一口氣,渾身的疲憊令她昏昏欲睡。她想親眼目送柳子歌走遠,可疲憊感愈發沉重。不知何處寒意襲來,叫一身美肉打起了哆嗦。
“如此就好……”
柳子歌越走越遠,不知不覺便消失了。
“如此就好……可惜……我死得有些難看了……”
鶴蓉苦笑,無邊的孤單與寒意襲來。她未想到自己會死得如此淒慘又丑態百出,好在她還剩與柳子歌的回憶作伴,足以令她含笑九泉。
困倦似鋪天蓋地而來的烏雲,鶴蓉再也無法支撐,沒有柳子歌的天地逐漸昏暗……
死了也罷……如此就好……
……
“干娘!”
一聲呼喊,喚醒了垂死的神智。歌兒不是走了嗎?莫不是死前幻聽?——她將信將疑的睜開眼睛,卻見到柳子歌正站在她面前。
“干娘,無論如何,我都不會棄你而去。”柳子歌背起鶴蓉,縱然他明白,鶴蓉之死已是板上釘釘之事,“我們一起走!只要離開此地,外頭定有能救你的神醫。”
前路渺茫,鶴蓉已是如此,又有誰能起死回生?……
“原來如此……是命運……呵呵……與你我……糾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