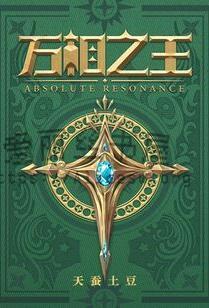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一切呢?”塞薩爾問她。
伯納黛特輕輕嘆了口氣,些許微笑消失不見,如同溫暖的陽光離開了蒼翠的林地,不再從她繚繞的發絲間灑下。
“除了你,我已經很久沒和其他人說過話了,塞薩爾。”她輕聲說,“而且,我一直在聽人們說你的事情,聽戴安娜說她有多愛你,聽人們說你成就了怎樣的功業。你和她的愛情和我過去的愛情不一樣,至少,我覺得不一樣。待到血脈的詛咒消失以後,我仍想看到你常伴在她身側。”
“我一直在做這種嘗試,但我很難保證。這世上的法術都太詭異了。”
“那就為她做我未能完成的事情,”伯納黛特用兩手握緊他的手,“一定,一定要把我未能講完的故事講給她聽。告訴她,這是你從我手中取得的東西,並且你可以代我講述當年未能完成的一切。你可以一直對她講下去。”
“我會的。”塞薩爾承諾說,“不過,我還是想知道,冬夜究竟是怎樣的存在?”
她眨眨眼,“那也是個很漫長的故事,不過,倘若你知道靈魂只是空虛的覺知者,要借著人格和記憶的綜合才能感知自己和世界,你也許可以明白,冬夜就是學派放在我靈魂中的一段綜合。她陪伴我越久,就把我浸染得越深,畢竟,靈魂中的我也只是一段記錄.......”
“也許你也浸染了那位冬夜。”塞薩爾最後說,“說到底,你的學派並不打算讓你繼續存在,她身為一段記錄,卻私自違背了他們的意願。要我來說,兩個人格和記憶的綜合身處一個靈魂當中,總是會相互浸染、相互改變的。”
就像他和那位遠在它處的阿婕赫。
.......
過了幾天,塞薩爾拿著他從米拉修士那邊找到的書前往索多里斯,當然,也捎上了菲爾絲要求的法術文獻。他們和伯納黛特共處了大約一個多鍾頭,其中有大半時間,都是塞薩爾代菲爾絲詢問她提出的各種法術問題。
在法術一途,冬夜要比伯納黛特更加高明,為了緩和他們的關系,伯納黛特把教導法術的職責交給了冬夜。不管怎麼說,她都是匯聚了葉斯特倫學派智慧結晶的一段超凡思維,不過,菲爾絲看不到她的存在,因此提問和轉述都只能由塞薩爾代勞。等到法術教導完成,伯納黛特又找他問起了神學書籍的各種疑難和困惑,看起來她很想追上自己女兒的步伐。
然而等伯納黛特放下神學書籍的時候,她已經看卡薩爾帝國的哲人們對各大神殿的批評和分析看得頭暈目眩了,整個人都不大對勁。塞薩爾提起了最近的情勢變化,想讓她緩口氣。不管怎樣,這事總是最容易理解的。
“王國騎士團分出了一部分兵力,大約有三千多人,正越過埃弗雷德四世治下的土地往北方過來。”塞薩爾說,“最近的會議一直都沒什麼成效,不過我想,等他們到了索多里斯或者古拉爾要塞,這事就會見分曉了。”
“雖然我不擅長這個,”伯納黛特說,“不過我跟在冬夜身後觀察了很久,多少也了解一些。你是要在這片土地上確保自己的地位不可動搖嗎?無論是國王,是各個貴族家族,甚至是神殿都不行。你最後是想要什麼呢?”
“我想做只有身處高處才能做的事情。”塞薩爾應道,“因為我想行使自己的秩序,所以我會不可避免地冒犯到奧利丹的貴族和王室。不過,等到血戰開始,他們總會有一方選擇站在我這邊,也有另一方選擇站在我對面。”
“聽起來你想教導世人?”她問道。
“稱不上教導,”他否認說,“只是利用我更遠的視野去做其他人來不及去做、也不知道自己該做的事情。如果我能在戰爭中取勝,人們就能看到我帶來的改變。”
“這意味著你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僅僅是為了領土和權力發起戰爭?”她繼續問道。
“我未必不是,只是我會利用自己得到的領土和權力多做一些事情罷了。”
伯納黛特點點頭,一只手托起下巴,現出優雅白皙的脖頸曲线。“那麼是誰給了你更有遠見的視野呢,你會怎麼說?”她堅持問道。
“也許是一個古老的野獸,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也可以是一個寒冰妖精,無論什麼理由都可以。”塞薩爾回答說。
“你是說編纂故事。”她說。
“不編故事的話,很多事情就太復雜了。”
“不,並不復雜。”伯納黛特輕輕搖頭,“我認為,那一定是個只有戴安娜這樣和你關系親密的人才能知道的秘密。現在離我知道它還有一些距離,不過我猜,我不會等太久。你對這個秘密很在意嗎?”
“稱不上在意,但我想,我把它說出來也毫無意義。像現在這樣任由人們猜測我的身份,我的處境反而更好。畢竟,我也不在意自己究竟是法蘭人還是薩蘇萊人。”
“你確實是個不可思議的人,難怪戴安娜眼光這麼古怪,卻還是在你身邊留了下來。所以你今天也奔波了很久嗎?“伯納黛特問他。
“我把她丟過來的事務都做完了才來的這邊。”塞薩爾承認說。
“那你一定是在那次會議上惹惱了她。”伯納黛特說,“戴安娜小時候說,如果她有丈夫,那他一定要一直跟在自己身後,說實話,有點由她做主的意思,但你不是那種人,對嗎?你一定會和她針鋒相對,然後就是各自做各自的事情。我覺得愛人之間若總是身在它處,僅靠夜晚的撫慰維持關系,難免會有間隙和隔閡發生。你應該更加,嗯......來這里,坐到我身邊來。”
塞薩爾想聽聽伯納黛特有什麼見地,剛靠近過去,她卻握住了他的肩膀,把他往下拉。他多少有點想反抗,卻發現自己很難抗拒。
她在地毯的墊子上並攏雙腿,把他的腦袋輕輕放在她膝上。“對,就像這樣,不要害羞,塞薩爾。”她輕聲說,“多年以前,我也是這樣給戴安娜講述那些遙遠的故事,就像我的母親和我一樣。你要自己體會過、經歷過,才會知道怎麼對戴安娜,還有對自己的孩子做這件事.......你覺得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我很難認為自己還是個孩子,也很難體會這種感受。”他說。
“但是,按照我們的習俗,我現在就是你的母親。”伯納黛特異常固執地說,不僅如此,她還把手指抵在他額頭上,“如果你不在乎自己是法蘭人還是薩蘇萊人,那你就不該在乎自己還是個沿襲先民習俗的人,甚至就是庫納人先民。現在你不接受,沒關系,等我把那些故事都講給你聽了,你一定會這麼叫我。不管你看著有多高大,你都要這麼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