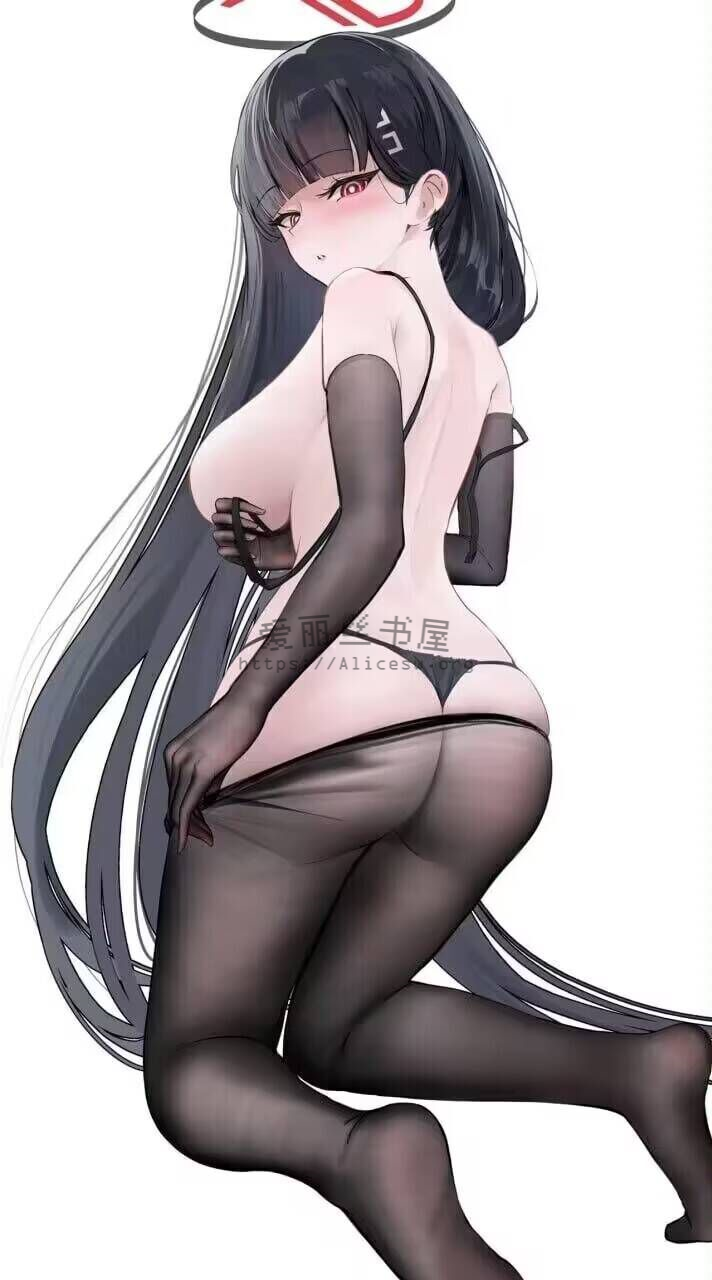平凡的詩人與聽她吟唱的少女
平凡的詩人與聽她吟唱的少女
——『如果不是起訖的時間,故事和音樂都可以永遠停留在倒數第二句該多好?』
(1)
「嘿,桐小姐!」
門前的酒保注意到走進酒館的吟游詩人,友好地打了個招呼。
「貴安,米里閣下。」
女詩人對誰都是一樣禮貌,盡管對方只是一個破酒館的小酒保。
有人曾經猜測過她是否是出逃的公主,因為她的禮貌與氣質實在是迥乎尋常,可以肯定地說,一般人絕對不會擁有如此氣質。
不過那些猜測也只是臆想,女詩人從未講述過自己的故事。
「哦,我知道的,桐小姐。按照慣例,一杯“古老之息”,對吧?」
桐優雅地點點頭,手指間夾著一枚塔林金幣。
在金幣精准地落入米里的手中後,女詩人找了一個合適的地方落座。放下她背著的尤克里里,似乎陷入了沉思,手指無意識地撥動著琴弦。
『親愛的,讓我們坐在一起,
互相注視著對方的靈魂。
我想在短暫的一瞥中,
聽到情感掀起的風暴……』
女吟游詩人彈著她心愛的尤克里里。
每當她輕動靈活的手指,就會有幾個和弦被勾勒出來。女人的聲音略帶沙啞,整個酒館里卻一片寂靜,只剩下彈唱聲。
她是個詩人,用她那豐碩的紅唇訴說著洋溢的情感。
這就是女吟游詩人日常的生活,每天她都會一如既往地來到這個小酒館,然後彈唱起獨特的旋律。
在整個諾亞塔林王國,她是最好的吟游詩人,就算是「豎琴手同盟」的那群家伙在她面前也要恭敬地自稱學生。
有人曾問過她的名字。她卻總是像是戴著一層藍灰色的神秘面紗微微一笑。詩人自稱——桐。
無疑是個很奇怪的名字,就算有人問起她,她也會略帶著歉意說自己也忘記了。
也有人曾問過她從哪來,又要去哪。
她卻總是搖搖頭,拿上已經被歲月褪色的尤克里里,唱著她最喜歡的小調。
從她婉轉的歌聲里,她唱著說她從北境的凜冬之森來。那里自從耐修斯王國滅亡以後,也變得不再平靜。
別人問起她,她還會耐心地附贈一場“額外演出”——一首叫『色欲』的詩歌。
至於詩人又要去哪里?沒人知道。只知道女詩人每天黃昏都要准時來這個小酒館駐唱,然後在黑夜悄然離去。只有冬天到來的時候,女詩人才會偶爾消失幾天,不過一段時間之後,她就又彈著尤克里里坐在那里了。
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沒人知道她在這里唱了多少歌,講了多少個故事。
其實真正的吟游詩人並不常見,而“吟游詩人”也並非坐在小酒館里吹拉彈唱的歌手,更不是在貴族宮廷里歡唱耍跳的弄臣就能被成為吟游詩人。
因為每個吟游詩人都是才華橫溢的天才,只有發現隱藏在音樂中的魔力,擁有這份最重要的天賦才能成為一名吟游詩人。
不過桐是名副其實的吟游詩人,有人曾看到女詩人坐在古樹的軀干上,吹著樹葉聯結成的樂器,自然與生命的旋律讓所有的植物為她而起舞,輕風為之合唱。後來聽說,那一年收成的麥子也金黃飽滿。
大多數詩人在經驗中學習,有時在久遠的廢墟之中,他們的手指在一座座古舊的紀念碑上徐徐劃過,尋求刻骨銘心的英知。
只有很少吟游詩人會在一個地方長期駐足,詩人的天性就是旅行——尋找新的可以講述的詩篇,學習未曾習得的技藝,他們是一群堅信“在地平线的另一端,你總能找到新的東西”的人。
但很明顯,女詩人是後者,不知為何,她沒有冒險中寫出自己的故事,也沒有去見證那些歷史更迭的痕跡,而僅僅是坐在那個平平無奇的小酒館,彈著她的尤克里里。
她的相貌看起來似乎也平平無奇,不過當你仔細打量她的時候,你又會情不自禁地被她身上某種道不清的氣質深深吸引。而在彈奏音樂時,她就是最美的——這是所有人的共感。
……
(2)
「這次妳要走多久?樹葉沒有多少時間了,妳差不多也要啟程了。」
說話的是一個身材嬌小的女孩,而實際上,從她臉上的點點雀斑能看出來她是一名侏儒。
侏儒甩著亞麻色的頭發,鮮亮的綠松石眼睛看著桐的尤克里里,琴身上面有個銀白色豎琴的標志。
「如果妳需要的話,我會給妳一些“小禮物”,相信我,妳會喜歡它們的,有了它妳就能……」
「跑得像移位獸一樣快?」
「哦,那可真不錯,妳說的也沒錯。」
侏儒毫不在意被中斷的話頭,而是繼續嘗試進行“推銷”。
「妳知道嗎,那“小玩意兒”的精巧就如同紅寶石熠熠發光。」
女詩人聞言平和地笑了笑。
「可是,如妳所見,我沒有錢,我只是個身無分文的詩人。」
「我敢說妳一定比我還幽默。我可不相信一位真正的吟游詩人會因錢財窘迫。」
「是啊,我很幽默。」
女詩人不置可否地點頭。
「但是我想一位傳奇人物出現在我面前賣“小玩意兒”可能更幽默。」
「哈!生活總是這樣的,才有樂趣不是嗎?另外妳知道大法師西摩的那句話嗎?」
侏儒摩挲著手上的紅寶石戒指,眼中流露出狡黠。
「“要想活得好,就得多加價”,多麼富有生命意義的一句話啊。西摩……聽說那個腐朽的老頭是從一個精靈那學來的。」
「這個有趣的故事啊,當初我還在『舊夜之都』傳唱過——那是西摩大法師年輕時曾經遇到一個精靈狩魔人的故事。」
「真的嗎?有機會可要給我好好講講。」
精靈狩魔人……說起來那顆銀色的墜星早已經有了歸宿呢。
「那我就不多打擾妳了,聽說剛壘王國那邊的烈酒最近風靡一時,我打算去那里“進貨”。」
「妳還真是個精明的商人。」
「那當然!也不看看我是誰——」
侏儒自豪的接受了這一稱謂,而女詩人無奈地扭過頭,因為她已經想到了接下來的畫面。
「我相信遲早有一天,“伯里特瑞特•尼德•厄•瑞奧•奧萊瑞森•伊茨•尼姆•伊斯•康米妮斯姆•拜•卡爾•馬克思”這個名字會揚名於整個大陸!」
「伯利特瑞特,我應該提醒妳,用詞要精確,或許是“臭名昭著”更合適。」
「嘿,真掃興。」
女詩人噗嗤地笑了笑。
「先不說這個,妳該怎麼說服妳那些親愛的矮人朋友向妳展示他們的美酒?所有人都知道矮人的固執,其中美酒和鍛造更是他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哈!別小瞧我,我最不缺的就是矮人的敬意。」
「哦?那些古板守舊的矮人可不會對外來者獻上敬意。」
「我和一般的外來者可不一樣,我有這個。」
說著,侏儒自豪地從她那臃腫的背包中拿出一枚徽章晃了晃,上面有魔法紋印的精致花紋。
「這可是氏族工匠的證明,能讓那些死板的矮人扭轉觀念的實力證明。」
「這倒是讓我刮目相看。」
女詩人挑了挑眉。
「不過還是不說這些了,我很好奇妳來找我有什麼事?」
「別那麼說,我們怎麼也算得上是熟稔了,妳這麼說我會很傷心的。」
「可事實上,我想說,如果妳的話語能有妳那些呆板矮人朋友們的一分真誠,我說不定能被妳感動。」
「好吧,我就是單純來告個別。」
「以往這個時候妳可沒來過。」
「……不是這個意思。」
侏儒一轉俏皮的語氣。
「我也要離開這個地方了。」
桐聞言有些詫異。
「……不回來了?」
「不回來了。」
侏儒抬起頭,她的目光從來沒有停留在小酒館的任何一杯美酒上,而時刻屬於那個漫無目的的遠方。
「我還有我的理念有待實踐,也有我的羈絆,至少我不能停下來了。這和妳一樣,親愛的詩人小姐,我們都有行走的理由,而非佇立在原地,無論那里是常人不可攀及的高峰還是一間平凡的小酒館。」
「聽起來真是浪漫,我喜歡妳的這個說法。」
詩人知道侏儒的一些事情——很少有人能明白,為什麼這個表面上是個奸商的貪心侏儒,卻是一位足以被冠以“變革者”這種名號的人。
「伯利特瑞特,妳還記得妳為什麼“出發”嗎?」
「一個契機,一種好奇。我總是想搞清楚事物如何運作,人們為何奔波。」
「所以妳的選擇就是,為了在乎的人們奮斗,對嗎?」
侏儒罕見地沒有開口,而僅僅是回應了一個堅定的目光。
「我知道了。」
女詩人微微頷首。
「有時間的話,我是說如果,我會把妳的故事寫下來的。相信我,妳的名字會揚名整個大陸的。」
……
桐在這個平凡的小酒館,見到過很多人,他們大多都碌碌無為,而只有少數人是閃耀的。
經常會有老朋友離開,新朋友到來。
而女詩人總會把他們的故事寫下來——以一個吟游詩人的身份。這是她的職責,一個吟游詩人應做之事。
也有些吟游詩人覺得歌謠從來不是讓人相信的,而是讓人感動的,因為相信歌謠的人本來就少之又少。
對此,桐並不持有相同觀點,因為歌謠不是謊言;但也不用去否定,因為給予故事一個浪漫的修飾,本來就是吟游詩人的本職工作。
桐覺得,大概是無論怎樣,過去的故事、史詩以及歌謠塑造了人們,因而它們不該被遺忘。
於是回過頭,你聽,她又在唱歌了……
女詩人要回到北方的凜冬之森了,她也開始想念那披著茸毛似的積雪了。
同時,也在想念一個少女的身影——夜雪卷起星星般的風鈴草,輕輕地撒到她的耳尖。凜冬唱著她獨有的歌,卷起雪粉的北風奪去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浮游向天涯海角。從此在灰色嚴寒的日子,她夢見了柔情脈脈的夢幻,告別了放誕不羈的生活。
所以女詩人覺得,她也差不多要和這個地方告別了,因為同樣有著不能駐足的理由——她有著一個永恒的約定。
而數年後,這里便可能有著一個新故事。
「從前有個『詩文與音樂之神』,祂是最了解世間的神之一。祂有著無數化身,以及祂那些忠實的信徒——追尋自由的詩人們,用詩文記錄下歷史。祂曾經總是化身成一個拿著銀白色豎琴的無名詩人,祂總是說音樂是時間藝術,教導人們應用詩文記載下見證的歷史,以音樂表達並傳承起訖的時間。」
「生命就像一首歌,自出生開始演奏,直至最後一個 音符結束後才重歸寂靜。人生就應該努力讓這整首歌曲更加的華美動聽,不能只偏重歌詞或曲調的部分。」
「最初的音樂與魔法並無絲毫關聯,音樂中並未隱藏著什麼奇妙的魔力,而吟游詩人也僅僅是一種賣藝人職業。祂曾想仔細諦聽整個世界,並在這篇大樂章中價進自己的曲調。」
「而卻發現這才是對自然的破壞,讓原本的音符面目全非。」
「於是祂暫時放棄了盲目追尋,決定化身一個普通凡人,也不再教導人們,僅僅是作為旁觀者去觀察、守望。」
「於是,一個叫桐的吟游詩人出現了。而故事的轉折,是一個宛如童話故事般的邂逅……」
(3)
『
我們曾在一起,我記得……
新夜充滿激動,里拉柔曼地歌唱……
妳在這些日子是——我的,
妳每小時比每小時更嬌美……
穿過琴弦的輕聲低吟,
穿過女性神秘的微笑,
熱吻滋潤著嘴唇,
琴音祈求著心的安寧。
』
……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桐在北境已行走數日。北境的風景似乎總是單調白色的,雪花飛舞是這里的主旋律。
但北境並非人跡稀少的絕境,早在很久之前,這里曾是矮人們的地盤,那時的北境之王是霜巨人。
自從『大地回音』誕生之後——矮人戰斗之父克蘭賈汀·銀須看到信徒在與霜巨人的戰斗中節節敗退,從群星中摘下一顆投入凡世。星辰從天而降落在矮人的熔爐中,矮人鍛造了一百個日夜,用一座山峰的融雪來淬火,最後得到一把渾然一體的戰錘。矮人用它擊潰了霜巨人的軍隊,進而滅絕了北地僅存的霜巨人文明。
後來隨著一場失敗的戰爭中丟失,流落入作為勝利者的人類皇室手中,雖然那時它的神力就已經寥寥無幾,但那仍然是北境的象征。從此北境的平衡維持在一個微妙的位置上。
而人類北境之國,曾經的耐修斯王國已經成為了歷史。
紀前30年,默爾瑪鐵騎就席卷了整個耐修斯地域。不過這一切也是咎由自取,古老耐修斯王國在北境立足數百年之後,終究被它的榮耀所蒙蔽而開始腐朽。
她曾化身成『最後的詩人』加里•布蘭頓德吟誦那段令人哀嘆的歷史。
而如今,北境諸國分裂,再加之環境惡劣,與南方的輝煌不能相比。不過這里的人們,身體里流有先驅者的血脈,不屈意志是他們與生俱來的品質,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能夠在北境生存。
這是她——作為“桐”第一次來到北境。上一次化身踏上這片凍土,還是在耐修斯王國滅亡過後的更迭之中。
熟悉或陌生,無論如何,這將是一個全新的旅程。
桐拍了拍她腰間綁著的皮革手袋,摩挲著手指攆出一張泛黃的羊皮紙。羊皮紙上滿是顏料的痕跡,偶爾還有一兩筆潦草的矮人語文字。
按照地圖的指示,再向西北走大概半天的路程,就能到達寒鴉小徑,沿著寒鴉小徑一直走下去,她就能到達剛壘——矮人們的國度。
說到那些矮人,雖然粗獷的他們不擅長烹飪,但是他們也會用鹿肉、豌豆及其他豆類做成凝凍,再配上鹿血及氂牛奶浸泡過的炸酥面包和烤土豆。
順便路上,她還能看看星鐵丘陵、銀光之森的風景,聽說銀光之森的元素十分濃郁,一些喜好研究的法師與學者總會帶好火絨袋和旅行背包前去一探究竟,但這個問題還是始終沒有得到答案。
而在那魔法森林中,植物狂野而又茂盛,不過似乎並無任何凶險之處。桐覺得那里或許是一處精靈的聚集地,至於這個答案是否正確,她會親自去拜訪看一看的。
一天後,她來到了寒鴉小徑的中段路程,前面遠處的“小雪山”就是銀光之森。由於北境終年飄雪,所以導致無論是最上面的枝葉,還是下面的枯枝敗葉和腐朽的樹干,都被漂染成潔白的大衣,非要說的話,就像光明教會的僧侶穿著純白的牧師袍。
整座森林散發著魔法光輝般的銀光,然而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光芒既不會傷害人們的視力,而且它還具有治愈的作用。
尤其是來到北境的旅人,時間久了會患上雪盲症,而那種神秘的銀光不僅沒有加劇傷害,甚至還治愈了過往的行人。
有人說這是無上的神力所致,他們相信在森林深處有一位擁有憐憫的神祇,祂用銀光治愈世人,銀光之森的命名就是由此而來。
不管其他人相不相信,桐知道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里不存在神。在她的感知里,這里並沒有什麼神力的力量,那種銀光也僅僅是一種高深的魔法元素效應。
不過這也勾起了詩人心中的好奇,她想知道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如此景象。
女詩人踏進了白色的迷宮森林,環顧四周,這里只有白雪與銀樹做伴,如果不加以辨認的話,旅人很快就會迷失在森林里。
桐本以為這里會有一個精靈氏族,但這種環境下,她實在想不起來有哪一種精靈會喜歡這樣的魔法森林。
女詩人選擇了最蜿蜒曲折的小路,想藏身於亘古不變的潔白中。她的身影是嵌在雪花石中,那顆璀璨的綠寶石。
吟游詩人的旅途上少不了音樂,桐也不例外,她吟唱著無名的小調,輕聲憑吊呼喚著古老英雄的名諱。
在齊特拉琴的頸部發出琴音,伴著踩踏冰雪的“沙沙”節奏聲,冬風送入也如在風笛的小孔中詮釋它的呼吸。女詩人便一路高歌。
夜幕將至,天空開始被逐漸割裂分割,然後黑暗的一幕緩緩拉下。女詩人卻發現了些許不同尋常的動靜。
該如何用語言去形容?
那是一道穿梭在密林野徑之中令人欣喜的曙光,她像是一位從幻夢境而來的女神,在月光下赤裸著起舞。
她的每一個動作都伴隨著元素潮汐的呼吸聲,晚風為之伴奏,而森林的靜謐則是她最好的舞台。
像是黑夜里一位婀娜的美人,把油燈吹滅了。
舞蹈淋漓盡致地表達著自然的美感,魔法元素伴隨在那舞動之下仿佛擁有了自己的呼吸。女詩人被之深深吸引,不敢再發出一絲聲響,生怕打擾了如此美好景象。
這美妙的一幕於這北方常年的寒冬格格不入,但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世間有這樣的存在才能溫暖寒冬。
她從黃昏,黑夜終結白日的時間開始起舞;直到黎明,白日戰勝黑夜的那一刻方在無聲的樂章中畫上一個休止符。
女詩人心中充滿了敬佩,她本以為精靈這種被冠以“超凡脫俗的優雅”生靈就是「優雅」的代名詞,然而那是在見到面前的生靈之前的事了。
在桐的感知中,對方是某種魔法生命,但以她這個掌握神職權柄者都無法分辨她是何種存在,這一點也讓她很驚訝。是突變的魔法生命嗎,還是……
自然開始伴隨著她的動作吟唱,從她的腳下冰雪也開始消融,成為滋潤這片土地的甘露,並不斷向外延伸。
踏著古樹的新生藤條構築的拱橋,那位清麗俊俏的少女走近女詩人的身邊,似乎毫不在乎赤身裸體的羞恥,不過那層隱約的魔力光輝就是紡織成的最好紗衣。
在消除距離的阻礙之後,女詩人才看清這位麗人的具體容貌,在那張奇艷絕世的面容下,是頸項以下露出的白皙皮膚。
「很驚艷的舞蹈。」
作為目睹了全程的觀眾,即使是吟游詩人也很難找到一個恰當的修飾來形容描述。
「冒昧地請問這位小姐,妳的名諱是……?」
女詩人心中莫名的有一種情緒在萌生,自從登上至高的階梯,戴上名為神柄的冠冕之後,她一度以為祂便失去了作為普通生靈的一切感性波動。而重新找回它,這也是化作化身融入這個世界平凡一面以來,她一直在做的事情。
「名字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朋友們叫我“源”。妳身上也有我熟悉的感覺,是……?」
自稱「源」的少女,女詩人思考著,似乎有些印象,但又說不清楚,畢竟身為古老中的一員,即使是神也會有遺忘的事。
至於對方所言的熟悉,桐覺得那是神職的影響。
「吟游詩人——桐。」
「很高興認識妳,妳是初到這里的旅人嗎?」
「是的,我從遠方的『音樂聖堂』而來,那里四季流淌著美妙的樂聲,是吟游詩人的聖地。最近要前往剛壘王國,所以路過這里。」
「『音樂聖堂』嗎……聽起來又是個遙遠的地方。剛壘王國又是哪里?」
聞言,女詩人的臉上顯露出一絲錯愕。
「……?妳不知道嗎,那是矮人的國度,距離這里大概沒有多遠了。」
「原來是這樣啊,我從來沒有外出遠行過,大概像一些旅人說的女巫一樣,整天“足不出戶”。事實上,我以前也從未像這樣和旅人交流。」
「恕我不能理解小姐妳的意思。」
「就是說,我是誕生於自然的生命,在用這副面貌現世,在妳之前,還沒有見到任何一個陌生人。」
「所以這就是……」
桐看著完全沒有羞恥心的源,就這樣赤裸著站在她對面,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她大概已經了解到對方是個什麼樣的存在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原始魔法生命,幾乎沒有任何常識認知的“空白圖冊”。
「好吧,源小姐,在我們繼續談話之前,我想我們還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女詩人掃視著面前的裸體麗人,嘆了口氣。
「——那就是讓妳明白要穿衣服。」
(4)
「為音樂而入魔的我不能不唱~」
「不能不想跳舞——」
「森林和冰雪在妳的舞蹈中~」
「也無法不燃起火熱的情懷……」
過往的旅者們偶爾會聆聽到森林深處的隱約歌聲。
有人說那是女妖的歌聲,也有人說是女巫在進行詭異的儀式。不過沒有一個人去親眼見證過森林深處的事物。
曾經有人雇傭一些傭兵或游俠去打探,但真相也是杳無消息。久而久之,這里也沒發生什麼事情,也就沒人去在意和關注到底發生什麼了,畢竟在緹厄倫薩大陸上像這種離奇的事情時常發生,而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有時間去當揮灑熱血的冒險者。
不過從此以後,銀光之森里也多了一個小木屋,不過外面沒人知道。
更沒人知道這里的主人——她們一個是『音樂與詩文之神』,一個是掌管元素潮汐的元素領主。
在她們結識後,最初是由於桐完全放心不下身為「空白」的源,所以停留了下來。反正本來女詩人也是一時興起地打算去矮人國度流浪。
雖然從另一方面來說,她也可以置之不顧,但是不僅是從源的身上找到了“感性”,自己也想遵從本心。
風暴開始停息了,走進簡朴的木屋,桌上鋪著花紋台布。
霞光透過樹葉遮成小窗的罅隙中照射到屋內,而女詩人一邊縫制著衣裳,一邊唱著不知名的歌謠。
另一個姑娘坐在旁邊看著她,跟著那個動聽的旋律,心中宛若跳著圓舞曲,臉上落出溫柔的緋紅。
和女詩人在一起,源學會了很多新事物。
而最為讓她深刻的,無疑是吟游詩人本身。
而她最喜歡的事,也變成了靜靜地坐在一邊,看著詩人唱著她的歌謠,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無論是在靜謐的小雪還是凜冽的風暴中。
在互相了解後,尤其是知曉對方的身份後——雙方都有一點小驚訝,不過也就沒什麼了。
「源?妳看,這樣新衣服就做好了。」
源覺得詩人小姐的手不僅能美如鮮花開放在琴弦上,還能在一張粗糙的布匹之上,發動名為“創造”神奇的魔法。
所以在桐認真的時候,她也時常看得有些出神,比如現在……
「……源?」
直到被重復呼喚,她才緩過神來,而對方已勾出了她溫柔的面容,臉頰湊得很近。
「嗯……!我、我看到了,桐……」
對方總是會捉弄她,最開始是一些她不懂的事,後來是一些調皮的小舉動,但是源心中萌芽的更多是一些前所未有的感覺。
看著一如既往有些懵懂慌張的反應,桐淡淡地一笑。
「以後不能不穿衣服哦~」
「唔!不、不是說好了不再提這個了嗎!」
源被“賦予”了名為羞恥心的事物,至於這個過程,讓她很難以啟齒。女詩人“教會”了她正常人的認知。
不過源仍然是那個舞蹈於光暗交錯之時的舞者,每到黃昏扣響房門,她便一直舞到黎明,這一慣例亘古不變。
不過,變化的卻是……
「在一個寧靜的夜晚,我看著她踏過暮色的山。」
女詩人抱著她的尤克里里,坐在輝月照耀的樹梢上。
「忽然在我面前,她深情地舞蹈著永冬。」
隨著女詩人的婉轉唱和,月下的舞者也在縱情舞蹈著絢麗。
「她邁著輕盈的腳步,柔和的薄霧隨著她晃動。」
星辰也開始為她們的歌舞而閃爍來自遠方的光芒,天穹的群星是她們最為忠實的觀眾。
「人們望著那雪花似銀白的星星,平靜地祈禱:“看啊,星辰又降臨了。”」
女詩人縱身跳下樹梢,音樂卻從未中止,反而響起更為抒情的間奏。
女詩人的每一個音符都具有非凡的魔力,當音符被連綴起來,它們總能構成一首動人心弦的回旋曲或敘事詩。
「舞蹈的少女,妳來自何方?是妳帶走了苦難人群的飢寒與無助嗎?」
「——無論日子消逝,是否快活或嚴峻,妳願意在白花中踱步,依然一遍遍地吻我嗎?」
少女舞蹈的動作微微一愣,但沒有就此停止,在動作的間隙中她自然地回首,向詩人遞出一個幽怨的眼神,隨後很快的扭過頭去,側顏上帶著些許紅暈。
「如果早知妳會像燒紅的花圈一樣害羞,我便會在清晨悄悄走進,吟唱著小詩。」
女詩人正欲繼續唱下去,而不知道什麼時候,少女已經走近面前,伸出手嘗試捂住她那靈巧的嘴。
但是女詩人豈會讓她如願?
女詩人自如地隨歡快的旋律轉了個圈,甚至腳步還踏著節奏細數著拍子。
「但實際上她的熱情像沉沒的太陽,妳看啊:她的臉貼向我,向我發出了舞會的邀請函。」
於是兩人就這樣打鬧下去,因為有音樂做伴,看上去倒像是一場自由的舞台劇。
女詩人總是能很輕易地躲開少女的“攻擊”,而看著對方的胸脯不停地喘息,女詩人得意地繼續唱著。
「少女將要停下腳步駐足,她……!」
詩人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她沒有想到少女會突然不顧其他向她撲來,最終兩人一起傾倒向潔白的雪毯。
「妳……唔!嗯嗯……?」
而少女緊抱著詩人,避免她再次逃跑,同時用一種意外而有效的措施來封堵住對方的歌謠。
少女可沒有什麼關於某方面的認知,不過在她自己作出這個動作之後,隱約感覺……內心變得有些熱烈,躁動不安。
——太近了……
一開始她確實達到目的了,但當她注意到女詩人的眼神時,那是一種她之前從未見過的眼神。
然後……她便感覺有什麼濕潤的東西在頂著她的唇,好奇怪……
而一種不妙預感萌生,但是內心中又隱隱期望著,這是什麼?
不過她知道詩人一定又在想辦法捉弄她,所以她在抗拒對方的舌尖。
源不懂得的東西還有很多,她對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認知最多到“朋友”的地步,但是總感覺哪里不對……
不過看著女詩人親近而溫暖的眼神,又覺得這是不是朋友之間一種增進感情的行為呢?
於是她放松了下來,等待著對方給她帶來新事物的認知,只不過——
「……唔嗯!?」
好奇怪,原以為只是輕輕觸碰一下,沒想到對方趁她不注意,舌尖直接鑽進了她的口腔中。
她瞪著那對明亮的眼眸,眼神里滿是不解,似乎在思考女詩人的這個動作又有何意義。
這種新奇的感覺,有一種莫名的魅力,就像是迷路的旅人遇到了魔法花園的妖精。
雖然心懷疑惑,但出於信任與某種未知的情感,少女開始生疏地迎合。
……
「不遵守規則就要受到懲罰,妳明白了嗎,源小姐?當初“緹厄倫薩交閃之戰”的結果,就是那些不守規矩的家伙被放逐到地底世界。」
桐看著大口喘息、胸口起伏不定的源,輕撫著對方的後背,在一邊耳語著。
「所以這個“懲罰”是什麼意思?」
深深地呼了一口氣後,少女的氣息逐漸平穩。
「……」
(5)
每次女詩人想起過去的事情,都會陷入往日時光的追憶中。那些記憶已經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卻歷久彌新。
她覺得,這或許正如那些智者所言——「美麗的事物總是指引我們想著其所在的方向繼續向前即是真實。」
女詩人這次從霍亞之港乘著侏儒們自豪的作品——飛翔的侏儒號前往北境的港口。
嶄新的旅途與路线,女詩人卻不再關注路上的所見所遇,似乎只有在這個時候,她心中始終指引往那個方向。
「嘿!聽我說,女士們、先生們,我以前是個流浪兒,但現在北境已經開始流傳起我的名號,娜瓦拉•角鴉這個名字終將成為傳奇!」
女詩人遙望倚著桅杆,講話大大咧咧的女矮人,她向眾人展示著她那暗紅色的釘頭錘,那上面鍍印著一只黑色的鷹隼。
「飢餓感。
如果說,這世間有什麼可怕的事——
那就是飢餓感。
父母雙亡,一貧如洗。
自幼我便獨自混跡街頭。
當生存對於一個人來說,已經成為一種奢望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考慮太多了。
這個時代,這個社會,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
沒有人會撫養照顧你,所以你必須學會如何自己謀生。
也許你會為食物不惜打得頭破血流,而為防止與自身一樣的可憐家伙的偷盜,你還必須時刻環顧四周。
我就是這樣,這是現實教會我的。」
女矮人侃侃而談,眯著眼睛看向遠方,似乎這樣能讓她跨越時間之河直視過去。
「睡在屋頂和小巷中,風餐露宿的生活里就算是生病,你也只能獨自忍耐,無法去指望藥物和醫療。
那段日子,我卻時常在思考,因為,飢餓感使你不得不清醒得不能再清醒。
自己照顧不好自己的家伙,只能算是活該。
這就是我的生活,是的,這種被稱為“生存游戲”的生活。
我最終九死一生地幸存了下來,有時候我甚至在想死亡或許是更好的解脫。」
矮人的雙眼炯炯有神,就像平常的矮人是如此固執一樣,她娜瓦拉不是個例外,於是她的演講話語充斥著感染力。
「——但是我不甘心。就那麼簡單。
認清現實,變得狡詐。
即使這樣,我也永遠不會向生活認輸!
我開始對他人冷漠,就如之前麻木的人們對我一樣,這是理所當然的。
即使這樣,我也始終想要證明自己的價值,或許這是我存活的意義吧。
即使我變得孤獨,不,我從始至終,都是一個人。
我也依舊有些自己的牽絆。
是自我救贖?還是自欺欺人?
我明白,我已經被現實轉變成那種人了。
即使如此,總有一個“傻子”,她總是拿出自己僅有的金錢去資助城內的孤兒院。
或許,這能給她帶來些許寬慰。
而這個愚蠢的“她”,這個傻子,就是我——娜瓦拉•角鴉。
呵呵,這一定很可笑吧。
明明自己都不能很好的生活下去,卻還要虛偽的這樣做。
也許我的見識和眼光皆與常人不同,因此有時候也能發一筆小財,但這樣的生活終究也只是渾渾噩噩。
不過我開始自己尋找求生之路。
流浪者們流傳著許多傳說,比如“偉大的獵馬者”尼古拉斯•波普的傳奇一生。
我開始尋求鍛煉自己的方法。
由於我出色的獵馬技巧,在年輕時我就已經得到了“祖安獵馬人”的稱號,現在北境的大部分人都聽過這個稱號,不過很少有人能想象,我這個正主是一個年僅25歲的姑娘。
我仍然在追求著,我有著自己的抱負,我會證明我自己值得擁有更好的生活!」
總有人像女矮人一樣,有著一段曲折離奇的人生經歷,在那之後也有著一些別樣的人生感悟。
而往往當他們向人們講述自己的故事時,總能贏來震耳欲聾的掌聲。
等到人群散去,她看著娜瓦拉走到她身邊,用她的飽經風霜的眼瞳打量著女詩人。
「我敢說妳是我見過的最特殊之人,比那些隱者還要脫俗。」
「哦?多謝謬譽。」
女詩人倒是沒有想到對方會過來和她聊幾句。
「我只是個平平無奇的吟游詩人而已,但很明顯,我的一些“同行”都覺得自己是真正的詩人。但事實上,『音樂聖堂』以他們為恥。」
「那還真是遺憾……」
像這樣,路上總能自然遇到新的旅人,桐也和他們交流,偶爾聽著他們講述一些大陸上的軼事。
隨著波濤滾滾地流去,海鷗也飛去了,船舶到達了北境的烈酒港。
這是剛壘王國最大的港口,向來有“矮人國度的血脈”之稱。
詩人就此與海鷗分別,從法蘭森橫跨出去,一直來到星鐵丘陵。
她要到讓她朝思夜想的地方了。
……
(6)
那是最美妙的時間,少女與女詩人的初次邂逅。可惜故事和音樂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個高潮部分,終究會迎來結尾。
「我一直在旅途中尋找啟迪,然而至今仍然一無所獲。」
女詩人訴說著自己的迷茫。
「我不知道該如何引領人們。我也曾嘗試,但結果是失望的。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將音樂編織成自然的樂章。」
少女不知道女詩人歌唱的理由,但是知道女詩人的歌唱是她所認知的——最美好的事物。
「為什麼不再嘗試呢?我相信妳的歌聲沒有人會不喜愛的。」
女詩人聞言搖了搖頭,溫柔地撫摸著少女的頭。
「這個世界上不乏有趣的故事,而我們能夠看到的就太少了。」
「那就把見到的事物記下來如何?如果能讓更多人去傳唱的話……」
少女似乎決定了什麼。
「如果如妳所言,還缺少一個方法的話,那麼——」
「魔力也將能成為一個個音符。」
身為元素源泉的少女把魔力的力量給予了女詩人。
從此那個名為桐的『音樂與詩文之神』找到了承載音樂與詩文的載體——魔法。
「約定了,當妳再回來的時候,要給我講講那些軼事。」
「我會的。」
女詩人含情脈脈地望著少女的笑靨。
作為元素領主的源無法離開起源之地,她從未離開過森林。她曾一度向往外面的世界,卻不能去親眼目睹,不過她現在有了更好的選擇。
女詩人答應她,成為她的眼睛,去幫她看這個世界。
只不過,少女對女詩人說了一個美麗的謊言。
……
女詩人想起第二次回到那個溫馨的小木屋時,雖然壁爐的爐火依舊溫暖,但仍然少不了一些冷清。
暴風雪攜裹著凜冽的呼聲,送來了少女的信。
「桐小姐,請原諒我的不告而別。」
「我是暗夜與晨曦交替的使者,像這點一樣,總要沉睡和蘇醒,不過每次蘇醒僅僅只有寥寥幾天,而下一次蘇醒?或許是短暫的一兩天,也可能是數月數年,也許是沉睡一個古老的紀元不再蘇醒。」
「就像是最近與妳初識的這次蘇醒,已經過了漫長的時間。身為掌管權柄的神,在漫漫時間中的更迭,我也已經見證太多了。但是,桐小姐,妳是獨一無二的。」
「我想我能給妳紀念的,只有魔力這個“新樂器”。我也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蘇醒……」
「為什麼這次會這麼不甘心呢?好奇怪,明明以前和“老朋友”分別都沒有這種情感的……」
某種意義上來說,桐和源是一樣的。她們都有很多“老朋友”,但是古老的記憶已經接近“模糊不清”了。
桐身為掌管權柄的神位,不會遺忘,但是在成神之前的事已經被“洗清”了。源身為元素領主,在一次一次的蘇醒中也忘卻了古老的記憶,或許自始至終,她都是宛如純白的雪地。
女詩人攥著書信,她的心情莫名其妙的復雜,但絕對說不上是什麼好心情。
她會就這麼離去嗎?
當然不會。
【——如果妳不肯蘇醒,我就用音樂將妳喚醒。】
桐來到了她們初次相遇的野徑,在魔力的影響下,飄雪、古樹以及冬風化作了各式各樣的樂器,有低沉的大魯特琴,輕揚的索加和里拉,還有少女最喜歡聽的尤克里里。
「銀光之森的黃昏白雪紛紛,我知道冬雪的旋風忠實於雪地里的少女。」
「思念——屬於少女的思念總是溫柔的,」
「可思念什麼——穿梭於林間的輕風也說不清。」
女詩人的旋律一轉,轉而從輕柔變得歡快。
「我記得妳雙肩的溫柔——顯露出敏感和嬌羞。」
暴風雪開始變得狂烈,而在那風暴的中央閃爍著一道銀光。
「忽然,在一陣快活的打趣後,妳又開始撫愛,不再啟口。」
隨著話音落下,詩人的音樂也戛然而止。
雪地里的少女,夜雪卷起星星般的風鈴草,輕輕地撒到她的耳尖。她有些睡眼惺忪,但臉頰上滿是緋紅與害羞。
女詩人輕輕在她耳邊低語。
「這次又該怎麼懲罰妳呢?」
「——我的……愛人?」
……
每年的嚴冬之時,銀光之森都會響起悠遠的歌謠,沒人知道這是什麼原因。
而每年也總有一個吟游詩人會來到北境,喚醒心愛的少女,為她唱著歌。
總是被叫醒,少女似乎也變得不是那麼貪睡了。
「我和妳相會在冰雪中,妳用舞步化冰為甘。」
「當我厭倦了理想的美妙,我愛上了妳白色的連衣裙。」
「那些無言的相會是多麼激烈,前方,在那森林雪層上倒映。」
「夕陽點燃了燭光與壁爐里的溫暖,有人在思忖蒼白的美麗。」
「我一步步走近妳,四周充斥著雪白的寧靜……」
「我們相會在冰枝雪花里,屋邊只見雪毯與冰鏡。」
「妳願意和我在冰天雪地中歡聲笑語嗎?」
女詩人唱著她的歌謠,一步一步走近了木屋。
歌聲由遠及近,而佇立在窗邊的少女早已等候多時。
歌聲突兀地停止,而雪地上的足跡也不在延伸。
女詩人對視著少女墨綠色的眼瞳,那其中充滿欣喜與愉悅。
「——我回來了。」
「——歡迎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