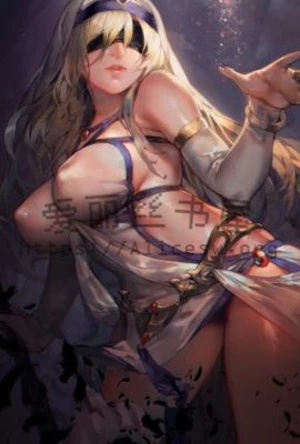第47章 計算與計劃【普博】
一、心血結晶
時間:2007年3月
地點:中國,羅布泊,“地球之耳”試驗場,海拔-142米
今天是普瑞賽斯來到這座比見過的任何人防設施埋得都深的地下實驗基地滿十八個月的日子,圖哈特連科、加繆夫和王慣例被其他科室“借用”了,只留她在這座方圓百米、布滿了神經血管般的計算機光纜和處理器的銀色大廳內,空曠和擁擠是同時存在著的東西。她試著在光腦上重啟她的原子鍾運算程序,但運行到一半就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密密麻麻的俄語彈窗看得她腦袋生痛。
她用袖口擦了擦干澀的眼睛,來到牆角的自動售貨機前,習慣性地想找到一瓶Breizh可樂*,但沒有。在格瓦斯和烏龍茶中她最後選了後者,因為包裝上的方塊字起碼比終日盯著的俄語更能緩解她的頭痛。她離開了盤踞在銀色大廳中如巨大墨斗魚般的計算機軀體,來到外面的廊道透氣。
與機房一牆之隔的礦石樣本倉庫今天仍敞開著,一隊士兵正護送一個碩大的保險箱運抵這里,透過上面的單面玻璃能看見里面礦石黃到發黑的質地。她握著飲料瓶,靠在欄杆上為運送礦石的隊伍讓道。從這里向上看去,新疆明亮的天光像是洞道巨大反斜面頂端一個炫目的輪子,它光芒的觸手順著蜿蜒向下的一條條走廊、一道道艙室向下蔓延。而在下方,羅布泊“地球望遠鏡”極深洞的人造燈光驕傲地炫耀著它的光輝,腳下研究基地的燈火幾乎比頭頂還要亮。普瑞賽斯向前伸出手,烏龍茶清澈的液面被上下交織的光芒充盈,像是滿滿一瓶太陽。
她順著廊道漫無目的地行走著,從“敵人很狡猾,要小心”中揪著一只從衣袖里伸出的觸手的紅軍戰士犀利的眼神下過。那眼神讓她有些不自在。她又想到自己剛剛參加這個項目的時候了。
那時候歐洲戰場的戰事剛剛結束,在蘇聯紅軍解放梵蒂岡之後,英吉利海峽號稱可以固守三十年的堅固防线很快便自我崩解了,連藏在北海的北極星核潛艇都放棄了最後的反擊。但即便半個歐洲最終免於兵火的燹烤,和平建立起了新的政權,但大多數科學家還是拒絕與新的當局合作。這種情況下,她作為剛從劍橋大學畢業的物理學博士,自然放下手中的課題“義無反顧”地趕赴了華沙。她還記得在費利克斯托港啟航的那天,與她同船艙的是顯然超過安保必要了的整整一個班的蘇聯士兵。他們像是一尊尊雕塑,眼中除了前方外空無一物。冷漠而尷尬的航程持續了數個小時之久。
她側身讓開一隊工作人員,繼續沿著廊道漫無目的地前行。那之後她來到華沙,被告知她將面對的是她根本不曾涉獵的人工智能領域——物理學博士便一定能應付光量子計算機的制作,就像飛行員一定會扎最好的風箏!但當時也確實是恢弘的時光。普瑞賽斯是第一次親身體會到那樣熱切的科研范疇。他們用“同志”稱呼彼此,他們之間幾乎沒有部門的劃分,也沒有行政人員與科研人員的明晰分異,更不會有同事之間藏私的事發生。而這些人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那唯一的願景和共同的目標,為了那個目標,他們可以連續無數個晝夜廢寢忘食。
她從他們那里學會了這個項目所需要的盡可能多的東西,而如今這個項目的人丁凋零了,場地不夠了,它有幸成為撤退到羅布泊聯合基地的數個項目之一,但如今或許只有她自己來支撐它了。她抬頭望著天空,此時太陽已經失去了直射洞道的方位,頭頂本應碧藍如洗的天空從地下看來昏蒙蒙的,反而腳下的人造燈光更加璀璨,幾乎令她有一種不真實感。在這個蟻穴一般的地下基地里,在川流不息忙碌著的“同志”們中,她真的幾乎是獨一人了。
那時的她,對於羅布泊望遠鏡這種地下極深洞工程的意義,尚處懵懂。
她已經下了三層,來到一處廣場。在剛來到這處基地的時候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事。說是廣場,也不過是稍微寬闊一點的集散處而已。在水泥澆築的光滑地面上,一支裝備精良的小隊正站在那里。這在這里更是不常見的。這里很少有能站定的人。普瑞賽斯裝作路過的樣子偷眼看去,這支小隊里有白色皮膚、身材高大的斯拉夫人,也有黑頭發、黃皮膚,身材小一點的東亞人。他們的隊長,一個上尉軍銜的精瘦中國漢子在用漢語說著什麼普瑞賽斯聽不懂的話,像是在訓話,交代一切必要事宜。
“達瓦里希賓說,這次任務除了檢查五千米處的洞道承重以外,還要勘測新發掘到的地下煤層。為了不發生之前那樣的事故,全隊務必做好生物防護措施,堅決服從命令,聽指揮……”嫻熟而清甜的俄語讓普瑞賽斯的腳步頓了一下,她稍稍回過頭,隱隱瞥見一個穿著解放軍軍裝的側影,那頭栗色的長發在腦後挽了個簡約的花苞。那個人正為隊伍中的蘇聯士兵做著同聲傳譯。普瑞賽斯發誓,那是她聽過的最悅耳的俄語了。同一種語言也可以有寒與暖的區別,阿爾薩斯和洛林人的口音與波爾多的同胞們比起來總歸有所不同。
回到實驗室,加繆夫在計算機的中樞旁忙碌著。這個烏克蘭出身的計算機與工程學博士正忙著把屏幕上的一組數據抄錄在那馬上就要翻到散架了的筆記本上。
“勘探六處的同志需要這組數據!”他一邊熱火朝天地抄著,一邊向她解釋,根本沒想起來問她是從哪回來的。普瑞賽斯禮貌性地笑了笑——這台機器尚未激活時的一些微弱的神經系統已經能擔負起一些工作了。但這不夠,肯定不夠。她缺乏那種跑遍各個科室,收集他們要處理的問題再跑回來啟動這台未完成計算機的熱忱,她只是守著它,推進那對於單人來說實在可以用浩渺形容的進度。
“對了,今天你的原子鍾測算系統出的錯誤我已經解決了,別列入十億億次以上的計算,目前的進度來說它承受不了這個!”
不等她道謝,加繆夫便很快跑出去了,不久後王也回來了一次——普瑞賽斯記不住這個中國科學家的名字——沒多留便又離開了。普瑞賽斯重新開始了她那測試性的原子鍾程序,浩渺的0和1的海洋在她所構想的那個虛擬中跳躍著,浮動著,如果將它們縮小一千萬倍,會看到無數跳動著的光點。如果再縮小一千萬倍,便勉強能看到質子了。它漂浮在原子碩大無朋的軀體內,如同一群歡快的精靈,組成了數據海洋涌動時愉悅的潮汐。
“咚”
錯誤的大紅叉再度出現在她的面前,她感覺自己像挨了一拳一樣,被向後狠狠拋出,跌坐在實驗室被電路和儀器環繞著的沙發上。
她再度疲倦地閉上了眼睛,花了不知道多久的時間說服自己撐著沙發立起身。理智告訴她該去生活艙休息了。她憑著記憶朝門的方向走去,似乎走了很遠——她不知道自己跨越了多少條電路,又穿過了多少儀器。等到她回過神來的時候,她紫色的瞳孔猛地顫動了一下。
她被圍困在儀器高聳的森林里,電路如瘋長的藤葛般鋪滿銀色的地面。她抬起頭,一望無際的銀色穹頂向著無法言明的方向延伸開去。直至目力所及的地方,她找不到任何參照物,更別提艙門。回頭望去,自己曾休息的沙發也不見了。
她竟然在這室內迷失了。
注:Breizh可樂,法國特產可樂
門縫與匕首
地下煤層並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樣是死寂著的,這里是煤礦的森林。枝杈齊備的古木向看不見的頭頂伸出磅礴的身軀,盤虬樹根錯落在腳下。用射燈打過去,連樹木上的紋路條理甚至蟲蛀風蝕的痕跡都纖毫畢現。
“在遠古的造山運動前,這里曾是森林。後來經歷天翻地覆的演化,整個森林在某次地震後沉入地底。又經過千萬年,才變成我們眼前的植物化石,也就是煤炭……”小隊里的工程師姓杜,高個兒白臉,是個“大師”。進入地下煤層後,他講解的嘴就沒有停。
“好了好了,要說也不急這一時。前面的岩壁被封住了,司機,去看一下。”曾在戰略導彈部隊服役,被大家稱作“導彈”的領隊李賓適時止住了杜工的絮叨。走在後面的女中校用俄語向那些蘇聯人說了兩句,被稱作“司機”,身高一米九的斯拉夫壯漢帶著幾個士兵向前,但那岩壁之內嵌著的巨石重逮千鈞,上方水蝕的痕跡油光水滑,也不知在此沉寂了多少歲月。僅憑人力,看起來極難與之相撼。
“杜工,能不能定向爆破,把它炸了?”中校問杜工,後者使勁搖了搖頭:“不可能的,這里的承力我們不清楚,光照也太暗了,要是引發二次塌陷的話,就得徹底堵住啦!”
“沒錯,在羅布泊,多一分謹慎,就多一條命,這是很多同志的生命換來的教訓。”李賓點點頭。“這上面也堵死了麼?能不能爬過去?”
兩人聞言抬頭,只見巨岩上方的岩壁杳杳冥冥,不知有幾仞高度,用小隊攜帶的礦燈完全照不到盡頭。正待再商議個計策,卻見那被叫做“司機”的蘇聯人用手托住了巨石底側。本是不抱什麼希望的行為,但也許是這斯拉夫壯漢巨力驚人,一撼之下居然隆隆作響,整塊巨岩向外傾斜。
“小心!”李賓第一時間奔上前用肩頭抵住巨石,幾個力氣大的士兵和測繪人員也紛紛趕上幫忙。卻見巨岩的下方白煙裊裊,居然有液體從中滲出。“司機”背後頂著岩壁用力,大腳結結實實踏在地上。卻不料腳下的岩質突然軟化,嗤的一聲,居然整個下陷,登時一股燒焦的氣味就散了出來。這蘇聯軍人頭頂滿是黃豆大的汗珠,饒是這樣,手中力氣居然一點沒有松懈。眾人一齊用力,便覺這巨岩下盤竟若懸空,在訇然巨響間被向後掀翻,洞道內帶著濃烈腐酸味的風一下子灌了進來。
“快急救!”杜工第一時間拉過司機,隊內的衛生員將那大腳上的軍靴拽下來一看,鞋底已經被腐蝕出一個對穿的大洞,腳掌也焦黑了一半,酸腐的味道撲鼻而來。杜工定睛一看,驚呼:“硫酸!”
“石頭上的水流痕跡也是這東西帶來的。可能是某種酸性礦物因為地壓變動而融化……在石頭下方形成了酸液池。”腦中走馬燈一般過著,杜工手中的動作一刻不停,迅速給這位可敬的戰士做著處理。李賓低頭看了一眼胳膊,面色大變,一把扯掉一截袖子,喊道:“快看看自己身上,快!”
原來,這塊石頭封堵在硫酸池上足有千年,下方的岩質早已酸化軟蝕,成了上方流下的酸液匯集之處。方才眾人推翻巨石,正是將其推進了地勢更下的酸液池里,不少酸液向上飛濺,打在厚厚的衣服上最初不覺得,一旦被其蝕穿衣料,皮膚上轉瞬就會多出一個焦黑大洞。一時間痛叫聲在坑道內此起彼伏,很多上前推石的士兵捂著肢體痛呼不已。
“趕緊把覆蓋在皮膚上的衣服去掉,用水壺衝傷口,到我這里領碳酸氫鈉溶液,塗抹在傷處,快!”杜工喊著,竭力平復那些負傷者的情緒。好在來到這里的即便是文職人員,也都屬軍隊編制,紀律性很強,甫一得令立刻執行,倒是沒有傷害加重的情況發生。
“負傷的,還有衛生員,留在這里相互照應。其余人跟我繼續向前。”李賓的面色很差,硫酸池只是羅布泊地下無數危險中不足道的一個,但僅僅這一個,就讓隊伍損傷了一半的人員。但任務必須完成,環顧當今沒負傷的,僅有自己、杜工、中校、測繪員小向、扎拉洛娃,地勘局的於干事和寥寥幾名士兵。方才的險情中士兵多衝在一线被硫酸燒傷,文職人員倒是保存尚且完好。巨岩沉在硫酸池中,正如一個天然的石梁。但岩質表層十分光滑,通過須得十分小心。
“都戴上防毒面具!我先走,拉住這條繩子,一個個過來,務必小心!”李賓牽著纜繩第一個攀上石梁,雖然只是幾個躥越的距離,猶戰戰兢兢一步步挪過,每一寸表面都踩過去,確認其光滑與否,到了對面立刻將繩索系在一處突出的岩峭。後面的人個個都不敢大意,唯恐一個失足下落骨頭都尋不見。手握纜繩,有驚無險地穿過了硫酸池。舉目之下,洞道內光线更暗,岩壁之上又分出無數復雜洞窟,不知通向何處。隊伍在盡頭通往更深處的岩洞前停了下來。
“同志,給我一支槍。”隊伍里的於干事對李賓說:“我在羅布泊公社參加過民兵稽查隊,這里我黨齡最高,我來開路!”
“務必小心,把這條纜繩系在腰上,有不對的話立刻在對講機里叫我們。”李賓點點頭,把自己的五四式手槍給了於干事。但於干事進入洞穴深處足有一個刻鍾,始終沒有回應。李賓發覺不對,忙令所有人向外拉繩索。最後卻只拉出一截斷掉的纜繩,再問對講機那邊,沒有任何回音。
“全隊注意照明,跟我來!”情急之下,李賓也不顧許多,揮手讓全隊快速前進,照明燈的電池不顧損耗開到最大,把洞道映得光明透亮。通道口窄內寬,居然容得下眾人通行。一路搜索到纜繩斷掉的地方,見四周地勢向下不止,有暗泉流水淙淙。前方的岩壁上有一片陰影,李賓心生疑竇,揮手令眾人警戒,自己上前用手一摸,都是黏糊糊的血跡。不期腳下踢到個事物,撿起來一看,竟是一截人的手指。
隊伍里的測繪員扎哈洛娃,是個烏茲別克斯坦出身的姑娘,大學畢業沒過多久,有一雙寶石般的大眼睛。她為人膽子最小,緊張之下,不由自主地貼著洞壁行走。猛聽身邊喀垃一聲,人已經被碎石埋在下面。
“他媽的!怎麼會突然塌下來?救人!”李賓雙目通紅,坍塌的那一側洞壁下站著三個人,除了測繪員小向及時躲開,扎哈洛娃和另一個中國籍戰士被碎岩活活壓在了下方。李賓正要上前刨挖,身體卻一沉,被中校伸手拽住。便見一道黑影從他的鼻尖劃過,在臉上留下一道血痕後轉入了岩隙上方。如果不是及時拉住,這一下不死也受重傷。
黑影在半空中急遽轉身,快得讓人幾乎懷疑那不是一個實體。幾名戰士開槍射擊,子彈打在岩壁上爆出一連串的火花,就看那事物如風飆電掣,轉瞬沒入上方的岩隙之間。
“可惡,難道羅布泊……”心里轉過一個念頭,李賓不由脊背陣陣發涼。下令眾人持槍警戒,同時還要把扎哈洛娃和另一位同志挖出來。中校搖了搖頭。順著她的眼神,李賓看到岩石下腦漿和鮮血的混合物緩緩流淌。再摸另一個被壓住的同志伸出岩石的手,也沒有丁點脈搏了。眾人一時默然,誰也沒說一句話。
中校摸了摸塌陷旁的岩層,感覺有些燒焦的痕跡。對杜工使了個眼色,兩人攀著岩石向內看視,卻見一道莫名的黃色光暈,在漆黑的岩層彼端輪轉不定,煞是好看。
“走吧。”身後傳來聲音,中校回過頭,看到李賓烏黑的眼睛正盯著那道光,這位軍人的聲音發著顫。“我們走。”
“任務目標就在眼前了,李賓同志!”中校急道。
“你們不懂,這里是羅布泊!”李賓低吼。“這里是羅布泊,四十年前,十年前都上演過無數命案的羅布泊!你們不能去!”
“如果不去,來到這里一路上的同志們可就都白死了!”杜工也站在了中校一邊。“放心吧,這種半生物礦石大致和兩千米處發現的是一樣的,我知道怎麼處理……”
“你們聽說過‘雙魚玉佩’事件嗎?”李賓仿佛換了一個人。他持槍站在那里,眼神里沒有驚懼,滿是擔憂。“四十年前發生在這里的一系列事——”
“雙魚玉佩?”中校皺著眉頭,大多數人也都皺起了眉。羅布泊雙魚玉佩事件蜚聲中外,但說及它的具體因由,就算這些親歷過羅布泊的人也並未知曉。
“能把任何東西復制的玉佩?那不是傳說嗎?”杜工似乎有所耳聞。李賓搖搖頭:“不,它是切實存在的,但不是一對,而是一個。十年前,它還出現過一次,那次我們將它徹底摧毀了。但我有種預感,雙魚玉佩上次出現時,便是如此發生了一系列的命案,以及時空錯亂的現象。這次發現的生物礦石,就目前看來……”
中校沉吟半晌,對杜工使了個眼色。兩人拉過李賓附耳了一會兒,李賓雙眼瞪得如同銅鈴,但依然搖頭“不行,堅決不行!”
“沒其他辦法了。”中校低聲道。杜工拿出一包雷管,交給眾人拿了,留下兩個人持槍警戒那道黑影,其余人從岩坍攀到礦石近處,在杜工的統一指揮下安裝炸藥。
中校走在最前面,仔細分辨著岩石走向。看到岩中有縫隙,用手一碰便冒出灰色的氣泡,心下里已經明白了幾分。正要說話,便見有人鬼鬼祟祟,手不老實地往岩壁的縫隙間探去。
“誰!”中校心中一片恍然,伸手便拔腰間佩槍。只聽轟的一聲,岩層又向中央塌陷開來。身後幾人連忙向後躲避,她回頭舉起手槍,看到測繪員小向慌忙逃竄的身影,槍火擊發間,身體被塌陷的碎岩裹挾,不自主地朝那塊黃色的礦石滑去。一瞬間,周圍的世界天旋地轉。
三、下一秒鍾前往地獄
不知道前方有多深,也不知道後方有多遠。站在這機房電路組成的迷宮里,普瑞賽斯犯了愁,怎麼才能出去呢?未知和已知是個同心圓,劍橋大學教給她的東西越多,她越察覺到這所高等學府漏教了很多必要的事。比如如何與互稱“同志”的人相處,如何對待顯然不可完成的項目,以及——如何在這種科學所不能解釋的地方脫身。
她依靠著一座機箱,面前是一眼望不到邊際的機房遠景。在現實與迷亂交匯的地方,銀色的地面似乎融化了,帶著一種絳紫色的詭異輝光。普瑞賽斯閉上眼睛,她告誡自己別相信極可能是錯覺的東西。拒絕視力令她的耳朵清晰,她聽見了規律的腳步聲,仿佛另一個迷途的自己正從時間的彼端走來。好奇心挑逗著她緊閉的眼簾,她小心地睜開眼。
一雙作戰靴從機箱的另一側探出,從普瑞賽斯的角度看,黑暗中走出一個側影。她身著解放軍軍裝,臉上戴著蘇制鯊魚鰓防化呼吸器,美麗的栗色頭發在腦後挽著簡約的花苞。左手擱在持槍的右臂臂彎里,似乎也在仔細看著周圍的情況。半晌,她似乎終於察覺到他人的注視,猛地轉身,五四式手槍黑洞洞的槍口直接指定了普瑞賽斯的腦袋,她的俄語如連珠炮一般:“什麼人,不許動,舉起手來!”
普瑞賽斯依言舉起雙手,饒有興致地打量著面前的中校。是了,一定是她,那一口純正的俄語只是聽便令人心神愉悅,像是家鄉舞蹈學校每天傍晚響起的鋼琴曲,在最困難的時候也能令人心神放松。但現在可不是放松的時候。她定了定心神,搜索自己的俄語詞庫,說出了自己所學到的第一個俄語單詞。
“達瓦里希。”
“你是哪個單位的?叫什麼名字?”對方的口氣緩和了些,但卻沒有放下槍的意思。
“我叫普瑞賽斯,是OGAS的工程師。”
“OGAS?蘇聯互聯網?超級物聯網和全球計劃經濟項目?”防毒面具下傳出的聲音帶了幾分訝異和敬畏,中校小姐把槍回套。“沒錯,沒錯……你們也在羅布泊。我曾在地勘六處看過加繆夫同志從你們那里帶來的數據。”
“沒你說的那樣復雜,大致只是一個光量子超級計算機項目。”普瑞賽斯稍稍有些不知所措了。她並不知道在華沙為了這個項目竭盡全力的那些人心中所想,她只是以為這些互稱“同志”的人本來便是這樣。
“不!它不僅僅是!”中校小姐的聲音有些激動。“你不知道——你這種人不清楚它究竟意味著什麼!三戰後的科技爆炸為按需分配帶來了可能,全球性的計劃經濟是人類社會新階段的第一步……”
普瑞賽斯笑了笑,沒有發言。中校小姐努力平復了一下情緒。“好吧,讓我們從實際出發——你是怎麼來到這個‘匣子’的,普瑞賽斯同志?”
“‘匣子’?”這一次輪到普瑞賽斯驚訝了。中校戴著防毒面具,語氣中透漏出幾分不滿:“怎麼,你不知道?”
“我只是驚訝你知道。你看起來不像是會讀物理書籍,尤其是‘匣子’定理的人?”普瑞賽斯頓了一下,生澀地加上最後一個詞:“同志?”
“我有中國南開大學物理系碩士學位。”雖然看不見,但普瑞賽斯確信中校小姐在面具下皺起了眉。“還有,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匣子定理’,只有‘匣子猜想’。”
“這個我倒是不清楚。”普瑞賽斯微笑了一下,坦誠地搖了搖頭。科學是嚴謹的,對於尼古拉·特斯拉的“匣子”理論她也只是偶爾讀到,用不了多久便拋到了腦後。但如今細細回想起來,似乎也只有“匣子”能解釋當今發生的一切。
所謂的“時間匣子”是塞爾維亞科學家尼古拉·特斯拉的諸多推論之一。在某種物理情況下,因為重力或者強磁場,時間將產生所謂的匣子效應。如果說時間坐標是一條线,匣子則是完全脫離了這條线的一個閉環,好似一個被時光潮汐推到岸邊的漂流瓶。
“就比如說,匣子里發生的事件換算成時間僅有30分鍾,不管有多少生命或物質,從時間的某一點進入匣子,都會共同經歷這30分鍾。匣子里的時間就如一個只出不入的半截沙漏,只能流逝一次。當30分鍾的事件結束後,匣子將徹底分解在時間的黑洞中。如果在30分鍾內還找不到逃脫的方法,就會和匣子一起永遠消失;若是在匣子中死亡或者損毀,也無法回歸真實。還有一個基於悖論的次推測:人永遠無法在匣子中遇到另一個自己。”
“那麼這個匣子的持續時間會有多長?”普瑞賽斯皺起了眉。
中校搖了搖頭,隔著防化呼吸器的目鏡,普瑞賽斯能隱隱察覺到她絕望的眼神。“在結束之前誰也不清楚,或許還有很長時間,可能就在下一秒鍾。”她見地板上的電路錯綜復雜,不知通往何處,於是問普瑞賽斯,這是否是OGAS的主機機房?
普瑞賽斯點點頭,中校小姐見這里都是電路,根本沒有參照物。如果找到機房的中央光腦,或許能辨認方向。普瑞賽斯知道這里的各個機箱是並聯設計,無論彼此如何連接,終究都與中央的主機相連。於是兩人循著電路的走向一路找去。
普瑞賽斯想起最初來到羅布泊時曾聽過的一些傳言,不過都是捕風捉影,就算有所謂的親歷者,對於十年前曾經發生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她艱難地從腦海里翻出那些零碎的信息向中校小姐詢問,時間匣子為什麼突然形成?它在此時此地出現,會不會同羅布泊曾發生的一系列詭異事件有關?
中校小姐沉吟了一下,其實她並不是沒聽說過此類傳言,只是行事向來風風火火,不把這些無法證明的東西放在心上。若不是在地下聽到李賓親口言說,她或許壓根就不會想起。所謂的羅布泊雙魚玉佩,據說當時曾做過實驗。將一條魚置於它的近處,轉眼變回變出一模一樣的兩條魚。在第一條魚身上注射毒素致死,過了八小時後第二條魚也會死亡。也就是說,羅布泊雙魚玉佩變出的“復制品”,其實都是同一個個體,它們位於不同的時間坐標,卻被玉佩拉入同一時間節點。這一點來看,那個玉佩本身可能就是個“匣子”。
“在那!”普瑞賽斯輕呼一聲,中校小姐轉過頭,看見銀色的天地間隱隱出現一個金黃色的光源,隔得較遠,看不真切。兩人飛奔過幾台機箱,終於看到這台上抵天花板的OGAS原型主機。這是一台頗具蘇聯制品風格的機器,采用了大量的本色無鏽鋼外殼,整個看來就如一棵鋼鐵澆築的參天古木。顯示屏上方的鋼板凹陷下一個巨大的錘子鐮刀徽記,靜靜俯視著踏著樹根般錯綜的電路來到它腳下的二人。
“這麼大的機器,理論上在極遠方都能看到,為什麼……”中校小姐心存疑慮,但匣子內的事如果事事用常理揣度,怕是想破腦袋也思慮不盡。看到普瑞賽斯在操作台上輸入識別碼,她靈機一動,問道:“聽說光量子計算機的計算速度極高,僅憑一台就能模擬出全世界的物聯網需求,進而達成按需分配所需的信息條件和即時速率,那麼能不能用它構建出‘匣子’的數學模型?”
普瑞賽斯從計算機中調出羅布泊望遠鏡的結構圖,聽到中校小姐的詢問,她遲疑地搖搖頭,又點點頭。中校小姐一時氣結:“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普瑞賽斯無奈地說:“光量子超級計算機還處於原型階段,而時間匣子的基礎數據我們也不清楚,我更不知道它需要怎樣的計算量……”
中校小姐仔細看著屏幕上的結構圖,機房區被普瑞賽斯特地放大,隔壁幾個房間的名稱也清晰地顯示出來。鏈接地下核子反應爐的供電中繼器,走廊,信息基站,礦石樣本倉庫……
礦石樣本倉庫?
由不得多解釋,中校小姐把手伸到普瑞賽斯身前,操縱著礦石樣本倉庫的縮略圖進一步擴大。直到屏幕上轉為倉庫內具體設施的抽象圖形,不同的顏色代表了不同的保密等級。她指著標志橙色的一處說:“就是這里!以這里為核心計算‘匣子’的時空曲率和時間流速,能辦到嗎?”
“這……恐怕不行。”普瑞賽斯看著中校小姐指出的點,紫色的眸子里滿是犯難。“這台計算機從未運行過如此復雜的程序,實際上,就算我們大致算出了匣子的曲率,進而進行無數次的推演,但我們沒有任何實際上的勘測手段,僅憑肉眼,在這個時空中找到出口的可能性也是……”
低於千分之三。她沒有把話說完。但緊接著她就被一雙手狠狠拽住白大褂的衣領,她的臉幾乎要磕在那防化呼吸器的面罩上。“那你是什麼意思?就在這里放棄麼?”
“不,不……聽我說。”心髒砰砰撞擊著肋骨,普瑞賽斯想要推開中校小姐的手,但對方的力氣比她占上風。“根據愛因斯坦相對論,單位的體積越大,時間流逝得將越慢。在匣子里這條定律也依然適用,如果我們繼續待在主機旁邊,我們的時間可能也會變慢,最後就算脫離了匣子,也不知道會被它送往哪一個時空……”
中校見周圍銀色的地面正逐漸轉為絳紫,知道此時刻不容緩。想一把推開普瑞賽斯,但自己又找不到這個復雜程序的啟動項。她隔著防毒面具對她怒吼:“美帝國主義的軍校在每年進行上千次上甘嶺戰役推演,這些推演中,美軍早已贏了上千次,而我所服役的軍隊沒有任何一次取得勝利!概率,永遠都是一個概率;如果不去做,一切都永遠是百分之零!”
普瑞賽斯停止了掙扎,隔著呼吸器的目鏡,中校看到她眼中的迷茫正在化開。此時光量子計算機的主機已經完成自檢,進入待命狀態。金色的光暈照在亮銀色的光滑地面上,順著鏡子般的金屬流淌開去。普瑞賽斯突然感應到了人,那並非人類的一個或一群個體。那是活在這地球上的七十億人,他們的行止作息就是一個巨大的計算機系統。在這里,每個人就像光量子處理器中一個小小的光點,他們的星光織起日月同輝,他們的飲食、交換與交流就是一根根光絲,無數光絲織起人類社會的巨大光網,傲然挺立於宇宙無盡的寒淵,令天邊怒燃的恒星在這光明面前黯然收斂。她看到華沙的OGAS基地,在距離它不過一公里處便是華約簽訂的拉齊維烏宮……
她看到那些曾互稱,也稱她為“同志”的人,他們在OGAS面前止住腳步,在璀璨的星海中找到自己那顆量子的位置。最終,人類社會的一切交換將由光量子計算機來模擬,沒有起伏的物價、過剩的生產,沒有被驅趕入大海的家豬和傾倒路旁的牛奶。她到此時才明白,為什麼那些出身社會主義國家的科學家擁有不屬於她所處學界的無比世俗的現實的狂熱,因為科學的盡頭不是神學,而是人類社會。
她按下了啟動按鈕。光量子計算機全力轉動的響動如同飛機馬達,巨大的轟鳴幾乎將時間震懾發顫。無數信息波濤洶涌般在計算機的光腦中碰撞,中校小姐緊盯著屏幕,普瑞賽斯卻隱隱擔憂著周遭的空間。剛才她就有預感,周圍的時間流速正在隨著兩人的行為而改變,誰也不知道這驚天動地的能量運作會在匣子中引發什麼。如果說對人類來說最大的秘密是命運,這個世界最大的秘密便是時間。時間是一條平靜的线性河流,但這條河流之外是怎樣的驚濤駭浪,根本無人能夠視測。
“咚!”一個猩紅的錯誤窗口彈了出來,那提示音令普瑞賽斯渾身一顫。
“再試一次!”中校小姐斷然以命令的口吻說道。普瑞賽斯小心地走上前,輸入了重啟和循環的指令。時間太過復雜,宇宙太過復雜,未成形的光量子計算機極難測算出哪怕千分之一的漏洞。
計算機持續運算著,旁側的液氮冷卻裝置嗤嗤作響。突然像是閃電劃過夜空,絳紫色和金色的光暈迅速交換。一瞬間,普瑞賽斯看到一個形似繭蛹的三米巨物從虛空中閃過。
“加快速度運算!”
“不行!液氮要不足了!”普瑞賽斯緊張地看向溫度指示器,冷卻倉里的液氮在來到羅布泊後本來就沒有填滿,如今在高速的運算下,液氮幾乎要無法緩解指數爆炸般上升的溫度了。普瑞賽斯想要上前暫緩程序,卻見OGAS主機旁一片片漣漪憑空飄蕩開來。所至之處,一切像是電影里的慢鏡頭,迅速凝固變形。
中校小姐和普瑞賽斯唯恐隨著OGAS引發的流速塌陷墜入另一條時間,在時間急劇變慢的過程中退到了機房邊緣。中校小姐回頭看了一眼,由於匣子內的時間出現了大規模的波動,此時這個匣子的能量也在急遽消耗,以至於保持不了穩定的封閉結構,逐漸與外界的時間連接起來。一旦時間流盡,兩人只有兩個選擇,一是隨著殆盡的時間甄滅在虛空中,二是被變慢的流速帶回過去的某個節點,成為羅布泊一系列詭異事件中的又一腳注。
普瑞賽斯突然想起了什麼,她撲向最近的一台機箱,在顯示屏上急速操作著。遠處的OGAS屏幕跳了一下,顯現出一個新的任務欄,正是她的原子鍾程序。她利用這個程序進入後台,試圖強行刹住即將過載的OGAS。
中校小姐大急,計算過程怎能輕易放松。但此時她與普瑞賽斯不知不覺間已拉開數米距離,根本來不及阻止對方的行動。情急之下唯有抬起五四式手槍,試圖將普瑞賽斯操作的終端擊毀。
此時四周被絳紫色侵染的空間一顫,發出陣陣雷鳴般巨響。原來隨著OGAS的計算倏然減緩,即將成型的時間遲滯再度反轉,二力撕扯之下匣子訇然劇震,露出了它的本來面目。那是隔離機房與礦石倉庫的一面牆,已經被匣子的能量抹去。隔過同樣被齊齊抹去了一大截的礦物架子,透過早已只剩一面艙板的封閉艙,她看到在地下五千米的煤層中曾看到的那具枯若蟬蛻的土黃色生物礦石,連上面的紋路都一清二楚。
中校小姐持槍思忖,在羅布泊望遠鏡洞道開鑿到2000-3000米之間,曾經發現這種具有詭異性狀的生物礦石。它周圍的時空呈現詭怖的特性,但好在這種特性並不持久,很快便被收容。只是在地下五千米的煤層中遇到了第二塊礦石,本已被妥善保存的第一塊才發生異動,進而形成了這個時間匣子。這樣看來,就像雙魚玉佩一樣,這生物礦石可能本來便只有一塊,在地下更深處埋著的是來自更加久遠過去的同一個體。這個礦石也正是匣子本身!
此時周圍杳杳冥冥,空間開始重新模糊融化,眼見匣子短暫的不穩定期行將終結,用不了多久就會恢復到之前的模樣,而後化作時間黑洞中小於夸克的碎屑。中校小姐當下也不顧再去論證結果,抬手三點一线,五四式手槍對准那塊礦石,直接將扳機一扣到底。
五四式手槍是仿蘇聯托卡列夫式手槍的設計,其子彈侵徹力非同小可。礦石那肉繭般的軀殼頓時翻出數個對穿大洞,渾濁的黃水一瀉而出。與此同時,整個匣子內的時空翻卷沸騰,不確定的量子潮水瞬間便將兩人吞沒殆盡。在“匣子”這一時間沙漏中,確定的“是”是在物理意義上不存在的東西。而當匣子最終損毀,不確定的時間沙礫會從確定的兩人身上滌蕩而過,為她們展現的是人腦幾乎不能承受的時間湍流。
——人類最高價值的社會會實現嗎?
——會的。正如導師列寧所教導我們的,我們現已經踏入發達社會主義社會,距離那個理想中的天國僅有一步之遙。我正是因此而生,因此而活。
——那麼,如果剝奪人類所擁有的一切,摧毀一切文明,搗碎一切卓著,讓生命回到三十五億年前這顆行星剛剛誕生有機體時的樣子,從頭再來一次,它還會實現嗎?
中校小姐睜大了眼睛,驚詫得無以復加。焚炎的大地和干涸的大海從她的身側縱去,她看到隕石砸落地面露出橙紅色凶光的礦藏。寒冷和陰暗中的活物站起起來,它們的身軀恣意生長,萬物靈長所擁有的一切被所有種族共享。文明的火在經歷過無數浩劫的母星上再一次綻放,已經消失的奴役和苦難睜開了它的眼睛。人食人,地食人,錢食人。文明演化過程中的苦難壓迫著她,令她幾近窒息。她奮力掙扎,但那壓迫太深,太重,絕望的眼睛越過苦難的大地看向天空,猩紅色的雲朵為天邊的雙月添上一層霧朧……
——它還會實現。它還會實現,因為歷史是唯物的,它不是主觀隨機的成就。生命和文明發展有其客觀規律,靈長的尊嚴也因此而生。它一定還會實現!
——那麼,如果讓你承受這一切,你能做到嗎?你能經受所有壓迫,直面所有挫折,經歷你所無法想象的貫穿文明演化過程的苦難,經歷無數冷眼、惡言與非議,最後還會愛著與你毫無血緣的生命,引導它們順利進入歷史必然導向的那個天國嗎?
——我……
中校小姐睜開眼,普瑞賽斯在她身邊,她順著她的目光向OGAS的屏幕望去。上方閃過一系列復雜宏偉的數據,最後顯露一個紅色的鐮刀錘子印記——在這個程序中,這個印記是“完成”的標志。OGAS被時間的沙漏推動,進行了一次兩人都不知道的推演。這個推演程序或許是在華沙被某個大膽的科學家埋下的,或許是它建造之初就存在的。而它的目標深埋在層層程序的底層,就如人類文明漫長演化史中蘊藏的最深奧秘。
程序閃了一下熄滅殆盡,中校小姐看向普瑞賽斯,普瑞賽斯也在看著她。機房銀色的大廳寬敞而明亮,空間的絳紫色隨著匣子的破滅而消去的同時,中校小姐的身影也越來越淡。她即將返回在本來所在的時空坐標。
“對了,同志。”普瑞賽斯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對她粲然一笑。“我能看一下你的臉麼?”
中校小姐遲疑了一瞬,伸手去摘臉上的防化呼吸器。然而,在它完全從她臉上離開的瞬間,她的眼前一花,再也見不到普瑞賽斯的身影。面前是漆黑的地下煤層,爆破後的碎岩還在向下滾落,就仿佛自己剛從岩坡上滑下來。
四、破曉
李賓和杜工從亂石中拖出測繪員小向的屍體,心有余悸地朝上面補了兩槍。看到屍骸的缺口里向外翻的黑色組織,杜工瞪大了眼睛,半晌才說:“這……是人嗎?”
李賓神色更為復雜,看向周圍漆黑的煤層,感覺後背依然一陣陣發涼。方才洞道爆炸坍塌,退回來的小向捂臉慘叫著不肯松開,一口咬定中校是敵特。剩下的所有人驚疑不定,再加上中校不見蹤影,李賓幾乎要相信他說的話了。因為這個小向是十年前羅布泊事件中除他之外唯一的幸存者,是過了命的交情。還是杜工敏銳,看著小向捂住臉慘叫不止,臉頰上卻一點血跡都無,悄悄從地上紅軍屍體旁撿起了托卡列夫手槍,繞到身後一把就扯開了他的手。就看下面那張臉,生生被中校的子彈打得陷進去一個洞,里面沒有血肉,全是黑乎乎的,就像泥塑上開了個口一樣!
小向一看事情敗露,二話不說,藏在袖子里的火焰噴燈直接朝杜工臉上招呼,卻被早有准備的杜工反扣住臂彎舉起手臂,一團火全朝空中噴去。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一路上正是此人用噴燈悄悄點燃了岩隙里的沼氣,這才有岩壁塌陷爆炸的事。李賓目眥欲裂,倒持著95式步槍,以彈夾為托,當即把小向放倒在地。他心里存了惻隱,本來還想好好說話,但杜工和隊伍里其他幾個士兵不慣他毛病,照著膝蓋就是兩槍,當場血流遍地。
“隊長,這不怪我!”眼見雙腿被廢,小向的精神似乎也不太正常了。他通紅的眼睛瞪著李賓,嘴里不住地喊著不囫圇的句子:“你不知道,很多年後,這里——”
“你他媽嘴上清楚點!”李賓狠下心來踹了著敵特一腳,卻見小向喉嚨里呼呼作響,眼見著說不出話了。他心里疑雲重重,亟待得個解釋,於是揮手阻止眾人補槍,俯身要聽個究竟。杜工快眼看到頭頂有異動,忙喊道:“塊躲!”
便見頭頂一道黑影飆掣,瞬間錯過幾人頭頂俯臥在一塊岩突上,這次看清了,是一只渾身漆黑如墨的五足怪物,兩米長,如蠑螈,尾巴也是一只腳,鮮紅的眼睛死死盯著眾人,突然它身下的岩突被扒得碎裂開來,刺鼻的沼氣一下噴涌而出。
眾人本來想立刻開槍,但沼氣來得凶猛,不得不向後躲避。就看小向手中的火焰噴燈一閃,炸響聲中碎岩落石雨點般砸下。
“這家伙……這家伙……”李賓扒開落石看了看四散的黑色碎片,這根本就不是個人了。他深吸一口氣:“這家伙不是原來那個人,他是雙魚玉佩復制出來的‘東西’。”事到如今,他也不得不和盤托出一些底細。倒不是刻意隱瞞,實在是如果不是親眼看到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他寧願相信從前的一切都是噩夢。按照他的說法,他並不是什麼戰略導彈兵部隊的成員,這個身份掩蓋的是他指揮了上一次羅布泊事件的事實。除了親手砸碎玉佩的他免於失蹤的厄運,當時受雙魚玉佩影響而離奇失蹤的人里面,小向是唯一回來的。而其中發生了什麼事已經是永遠的謎。現在那鬼影一樣的五足蠑螈仍在窺伺著還活著的這些人,受損極大的小隊除了立刻撤退,沒有其他的選擇。
“那於干事和中校——”杜工的一張白臉有些漲紅。他看向剩下的人,雖是一個個早已嚇破了膽子,但言及“撤”還是“找”的問題,卻一時莫衷一是。
“砰!”
一聲槍響從煤層深處傳來,立時令眾人止住了爭論。李賓聽得出是五四式手槍開火的聲音,正是自己給於干事的那支。因為他自己的五四式槍機久用磨損,聲音有些相迥,他最是聽得出來。於是招手帶了兩個士兵前去,杜工也堅持跟來。
“於干事?”走進暗泉下方的一個洞窟,正發現里面坐著一人。李賓用應急射燈照去,是於干事沒錯,只是已經死了多時。除右手手指掉了外,胸前還有大傷口,已凝固的血染紅了一大片地面。地面上扔著那柄五四式手槍。可是死人怎會開槍?
“趴下!”杜工斷喝一聲,一把按住要撿起手槍的李賓。便見一道黑影從兩人頭頂縱過,與身後洞穴入口走進來的一個人影撞在一起。眾人忙舉槍相對,卻見進來的不是別人,而是一道躲在岩壁下的模糊黑影,看身形正是死去的小向。
五足蠑螈爬到“小向”身上,無聲無息地吸附進去。便見小向從黑影里走出來,半張臉都已經塌陷了,黑乎乎的牙關裸露在外。皮膚如同屍皮一般呈現鉛灰色。他僅剩的眼睛看看杜工,又看看李賓,艱難開口道:“你們為什麼打我?”
“你到底是什麼怪物!”一名戰士似乎受不住這詭異的一幕,怒吼出聲,手中的槍倏地開了火。就看那“小向”身上翻開數個黑洞洞的口子,沒任何血液流出,令人頭皮發麻。
小向對臨體的子彈置若罔聞,自顧看著李賓。“隊長,您是知道我的,我沒有——我不是敵特!不是!”他的聲音難聽得如指甲劃過黑板。“我只是看見了,看見了羅布泊乃至世界在若干年後要變成的——”
“砰!”李賓果斷地扣動扳機,這一槍精准地掀飛了這家伙的下顎。小向僅剩的眼睛怨毒地瞪了一眼李賓,身體迅速漲大。
“躲開!”李賓吼道,只見五足蠑螈飛快地撲殺過來,撕開了一名戰士的喉嚨。杜工和李賓各自尋找掩體連連射擊,但這怪物在地下環境如鬼影如深潭,只需轉瞬便消失得無影無蹤,冷不防的,地上於干事的屍體一把扯住了李賓的腳。
“噠噠噠——砰!”
李賓倒也身經百戰,第一時間連連開槍將扯住自己的那只死人手打斷。然而就在這個當口,從於干事屍體後面飛射而出的蠑螈已經殺到他的面前。隨著五四式手槍砰的一聲顫鳴,這道魔影在空中轉體,似乎終於被擊中了一次,嘶嘶叫著向上方逃竄。杜工驚呼一聲指向入口,卻見中校站在那里,五四式手槍的槍口還在冒著青煙。
“它的身體可以在沼氣中移動!”中校喊道,她看見那道魔影消失在半空,順勢就地一個前滾翻,避過飛來的利爪,同時迅速回手開槍。子彈錯過怪物的身體,鑽入上方的岩層,頓時一股石灰悠悠下落,一道清水從彈著處淌流下來。
李賓見狀,抬起九五式步槍向上方掃射,打破頭頂的岩層,令暗泉水灌入洞窟,果然不再出現任何異常。五足蠑螈見勢不妙,居然攀附洞壁順著水流上行逃遁,被眾人亂槍打成篩子一般,屍體啪的一聲墜落在地。
“羅布泊望遠鏡,是一次成功達成了戰略目標的實驗性工程。雖然它最終暴露而沒能成為我們最後的避難所,但它已經證明了這種工程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坐在直升機上,普瑞賽斯回頭望向千頃黃沙內的洞道,它已經被一個巨大的鋼鐵艙蓋密封了起來。機艙的空間很小,她坐得很不安穩。但它必須被攜帶,這座未完工的超級計算機將作為烏拉爾望遠鏡的主機繼續為人類發揮余熱。
未知時間,烏拉爾山脈。
“普瑞賽斯同志,這是同期撤退到這里的科研軍官名冊,綜合實際上的需要和你本人的申請,你可以指定一名科研軍官作為你的助理。”厚厚的一疊圖紙堆中,普瑞賽斯抬起頭,本來困倦了的紫色眼瞳在接過名冊的一瞬顯得精神起來。她仔細瀏覽著名冊,反復端詳著那些軍官的樣貌。
“你的提議非常大膽,組織上已經在考慮,以‘列寧’作為這個計劃的代號。”加繆夫看了看桌上的圖紙。“你還是沒放棄完成它?”
“不太准確,我想,大概是沒放棄改動吧。”普瑞賽斯疲倦地笑了笑。“不過,現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可以讓它運作了。”
“在地下試驗場,實驗這幾種機型組合……確實是突破所有現有系統的大膽嘗試,我會在我的新崗位上為你提供便利。”加繆夫點點頭。“以及,這很不像你的一貫風格,普瑞賽斯同志。”
“有時候嘗試著跳躍一下,也是科學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普瑞賽斯淡淡一笑,在一名栗色頭發的女性中校頭像上打了個勾。“不過現在它已經不適合再被叫做OGAS了,叫它什麼呢?”
“我想,就叫它PRT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