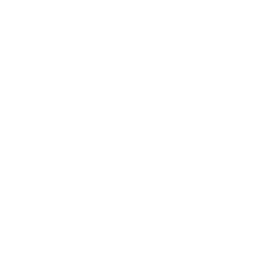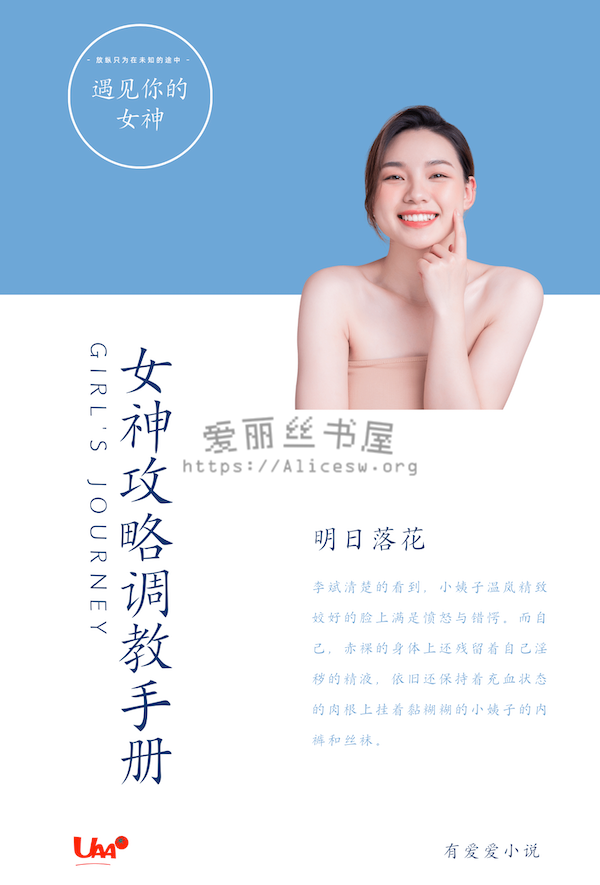第39章 說“羊”
說“羊”
(R18G警告、血腥暴力警告)
我打算將和道家、道教頗有淵源的若干動物都講講。前段時間已經講過了鹿,並且多次提到兔,按理說下一個該講兔了。不過,前兩天和群友聊到“蘿莉/少女孕婦”,他說他知道二次元有夜羊社,三次元有羊城百合。這二者正好都有一個“羊”字,其機緣巧合妙不可言,似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玄機,所以先來講講羊。
吃羊祭羊
羊,祭祀用的“三牲”豬牛羊之一,“鮮”字的一半。中醫說,羊全身都是寶,只除了羊腦不能多吃、每天吃。古代長期以來,北方人喜歡養羊吃羊,南方人喜歡養豬吃豬,然後互相地域黑,南方人抱怨羊肉有腥膻羊騷味,北方人抱怨豬肉有土腥臊臭味(當然,並不是絕對的南方人不吃羊,北方人不吃豬,底層人民時常不見葷腥,什麼肉來了不都是吃)。由於國家統一時,首都一般在北方;國家分裂時,南方政權也有很多南遷北人身居高位,所以這場口水仗中,“羊派”占上風的時候比較多,該他們“得意洋洋”。不過到了明清時期,尤其明朝末年,番薯(紅苕)等高產作物傳入中國後,中國人口開始爆炸。為了滿足人民需求,官方民間都開始選育不挑食又高產的肉畜品種,而豬在這一進程中大大領先於羊,並且豬糞肥化耕田的效果優於羊糞。時至今日,除去伊斯蘭教徒和其他少數民族、少數北方地區,中國基本是“豬派”的天下了,“羊派”式微了。中國每年豬肉消耗量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附:
六畜:馬、牛、羊、雞、犬、豕。(有時去掉馬或犬,稱五畜)
六獸:(這里只列舉食用六野獸,不列舉發簪六飾獸、傳說六神獸)麋(像鹿而大)、鹿、麕(像鹿而小,又名麇、麞、獐,生角的獐即“麒麟”。麝亦像鹿而小,曾被誤作獐的一種)、熊(有的版本為狼)、野豕、兔。
六禽:雁、鶉、鷃、雉、鳩、鴿。另一說:羔(幼羊)、豚(幼豬)、犢(幼牛)、麛(幼鹿)、雉、雁(類比前四者,後兩者也應該是指幼年體,但沒有造單獨的字),凡鳥獸未孕曰禽。(即“禽”就是還有“童子身”的鳥獸。)
祭祀的時候,中國古人倒是沒有“豬派”、“羊派”的爭議,都要殺。雖然西方人祭祀好像不殺豬,(可能是猶太人、阿拉伯人曾長期游牧,所以不養豬。與猶太教、伊斯蘭教同源的基督教可以殺豬吃豬肉,表面上,原因是傳說耶穌將魔鬼趕進了豬體內,所以比起羊更應該殺豬吃豬,但實際上,或許反映了基督教徒已由游牧轉為定居農耕,並且與時俱進地移風易俗。[並且物產不太豐富,不能和周邊游牧民族交易獲得大量羊肉。])但對於羊,東西方都是類似的習俗,有點“嫌棄”成年羊,講究祭祀時盡量用小羊羔,所以東方“羔”字下面“灬”原本是“火”字,象征柴火,西方則有“替罪(羔)羊”、“沉默的羔羊”、“待宰的羔羊”、“迷途的羔羊”等說法,出自耶經。
中國人後來殺羊羔殺出了感情,稱贊它有美德:“凡贄(初次拜訪尊長的見面禮),天子用鬯(祭祀用酒,用郁金草釀黑黍而成),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雉,取其耿介;雁,取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通嗅,氣味)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漢·何休《春秋公羊傳注疏》[又名《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八。孔子增刪魯國國史,編定《春秋》。戰國時,卜商[即《論語》中的“子夏”,世稱卜子]弟子,齊人公羊高解釋《春秋》,成一家之言,即春秋公羊家。漢景帝時,其玄孫公羊壽和弟子胡毋生[又作胡母生]一起將本門學說記於竹帛,即《春秋公羊傳》。東漢何休又注之。今通行版即漢儒注解版,已難分辨漢及以前的注文出於誰的筆下了。)也有古書說:“卿執羔,取其群而不失之類。”群而不失之類,一般是說和群而不黨同義,但是不是“不失”嗎?那應該是“群而類”啊。所以我給出另兩個說法:一,類字古為犬字旁,所以也可能是說“成群,但不脫離牧羊犬的控制”。二,“類”又是上古一種祭天的祭祀名,所以也可能是說“成群,但不貪戀群體,抗拒祭祀犧牲自己”。其實這又和“群而不黨”相通了——為何黨?結黨營私也,既得利益集團損公益私,且抗拒自我犧牲也。同時,這麼解釋亦與上文“類死義(義)知禮者也”相通了。
《詩·豳風·七月》有“四之日其蚤(通早),獻羔祭韭”一句,即後世農歷月歷(陰歷)二月初用韭菜和羊羔祭祀祖先。據其他古書,祭祀時韭菜往往還要和卵,也就是雞蛋相配。羊羔、雞蛋都是“後代”,韭菜則生長得快、繁茂,所以大概是告訴祖先,你的後代繁盛吧。又或,還取其“生氣”,讓祖先感受一下人間春天的生氣。而清明節,即農歷干支歷(陽歷)“二十四節氣”的清明(對應每年公歷4月4日或5日),其實原本是踏青、賞桐花麥花柳花、插柳、吃柳芽的。後來,晉文公在清明前一天(一說前兩天)不慎燒死了介子推,於是以這一天為寒食節祭祀他。後世把二月初祭祖、寒食、清明三個節日,外加踏青沐浴祈福的上巳節,四者混在了一起(難道是因為當時國家只給官員放一天假嗎?),於是變成了今天的清明。
然而,晉文公不慎燒死介子推之事,可能另有一番真相。現根據我查到的資料,提出我的猜想:
話說商代時,春天有兩個和祈雨有關的節日,一個是暮春三月,農歷陰歷三月第一個巳日的上巳節,沐浴後舞蹈祈雨,即《論語》中的“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看過我以前文字的話,就知道“雩”是祈雨的儀式、舞蹈名。還有一個則是早春,農歷陽歷冬至後105日,清明前一到兩天的寒食節(上古可能更早一些),又稱冷節。寒食時,先禁火,禁火三、五、七日後(不同資料說法不同),用鑽木等方式取火,稱為改火,然後將谷神稷的象征物焚燒祭天,稱為“人犧”——商代很可能真的燒的是人,或奴隸或戰俘,被周代改成稻草人和牲畜了,但“人犧”的名字流傳下來了(犧字右西,可能是從西羌抓來的?還真有可能,見下文)。俄羅斯也有個傳說,傳說原始部落時期,每年春天要挑選一個少女,一直跳舞直到倒下死去,以此祭祀大地和春天之神,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後來斯特拉文斯基根據這個傳說,創作了著名芭蕾舞劇《春之祭》。)話說那年晉國春旱,介子推就說要恢復商代冷節結束時燒人的傳統,如果沒有人去的話他就去。介子推一直說一直說,晉文公被說煩了,竟同意了。介子推死後,晉文公又非常後悔,於是下令以後寒食只有禁火改火,不再在改火時祭祀了。個人猜想,僅供參考。
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指出,一些古書中羔除了小羊羔的意思,還有侍女(女使)、奴婢的意思。侍女寄人籬下,所以“羔”字上面的“羊”就是借,下面的“火”就是灶火。但我覺得沒說對,大概率還是和商代習俗有關,“羔”就是祭祀時用作犧牲的奴婢,引申為一般奴婢。段說如下:
“(羔)羊子也。虞氏注說卦傳爲羊作爲羔,雲女使也,妾與羔皆取位賤。鄭本作陽,雲讀爲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二說字異義同。武進臧鏞堂曰:羔者,養之誤也,從羊,照省聲,古牢切,二部。”
青羊與老子
接上文,商代的“羔”,其實很難說哪些場合是人,哪些場合是羊的。事實上,商代與“羊”相關的字都是如此。很多學者指出,“羌”字的甲骨文便是象形一只羊被放在“幾”形的祭台上。直到“姜”子牙輔佐周武王滅商,才結束商代人祭的歷史。如果感興趣,之前有篇講祭祀殺人的拙作,可作為參考。
傳說,鬼谷子是尹喜弟子,寫了《關令尹喜內傳》一文。現在一般認為是西漢末或東漢時文人偽托的,但仍有參考價值。其中記載:“老子與喜別曰:尋吾於成都青羊之肆。”後來唐玄宗為了附會這個傳說,在成都修道觀青羊肆,又稱青羊宮,便是今天的成都青羊宮。但其實在此之前,成都並沒有這個地名。
那麼,什麼叫“青羊之肆”呢?有學者說,《說文解字》寫了,羊羌相通,肆祀相通。古蜀國因為信仰青衣神,被稱為“青羌”,“青羊之肆”便是“青羌之祀”,即古蜀國的某個(可能是最大的那個,又或祭祀“青陽”蠶叢氏的)祭祀場所。“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青衣神,即蠶神、蠶叢(縱)氏、冉(冄)駹,繼承了嫘祖(雷祖、累祖)的養蠶技術,教民養蠶,成為了古蜀國的第一個王(一說,是古蜀國“蠶叢王朝”的第一代王)。戰國《世本·卷一帝系篇》:“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產青陽及昌意。”有人說,青陽就是蠶叢,因為他領導青羌(青羊),又是帝子,故取諧音號為青陽。蠶叢之名則是取他的兩個特征:會養蠶,眼睛向前突起(縱目)。
另外,“青陽”不僅是人名,又指春天,正是養蠶的季節。先秦《屍子·仁意》:“春為青陽,夏為朱明。”後來發展出樂曲《青陽》。漢·司馬遷《史記·禮書第一》:“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注:《漢書》將“僮男僮女”改為“童男童女”,並刪去了具體歌名。我以前的文字曾引用過《漢書》。)陽春三月,即春天那三個月,或第三個月的暮春。(另外,也有樂曲《陽春》。)俗語三羊開泰者,既是取羊通陽(《易》以正月為泰卦,三陽生於下),又是取羊通祥。清·徐灝《說文段注箋》:“古無祥字,假羊為之。鍾鼎款識多有‘大吉羊’之文。”所以善、義(義)、羑、美等字都是羊字頭,言其祥福善良。
秦滅古蜀國後,有的羌人不願屬秦,遂在西北山區建國,以蠶叢氏的另一個名字“冉(冄)駹”自稱。現代《中國文化史詞典》:“冉駹,古族名。主要分布在今四川茂汶(今天茂縣、汶川、青川等縣)地區。游牧為生。產氂牛,出名馬。有羚羊,能解毒。又有食藥鹿。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以其地置汶山郡。”以各種動物為藥材,隱隱對應了“駹”字;而“冄”字變形一下,豈不就是一個“丹”字?所以最早的“丹”,可能就是動物煉的。結果不知道是誰想到:這里的動物都這麼補,人是不是更補?於是衍生出種種不人道。而老子要去“青羊之肆”,可能正是不滿於商代的不人道,而周代民間仍然流傳著種種相關的偏方,所以他去丹的起源地學習一下。老子本名李耳,後人尊稱他老聃(聃左耳右冉(冄),音為丹,正好符合我“丹由冄變形而來”的猜想)、李伯陽,是不是說他晚年久居冉地、青陽地,混成了老、伯呢?個人猜想,僅供參考。(此外,今天羌族仍然自稱“冉駹”人,這兩個字在羌語中音為Rrmea,可音譯為“羅馬”。所以,羌即羅馬。())
羚羊掛角
羚羊的羚字本作麢,上鹿下靈(靈),即它本來被劃入鹿一類,後世改成羚,又把它劃入羊一類。現在,羊、羚羊各自是偶蹄目反芻亞目牛科下面的羊亞科、羚羊亞科(牛科一共就三個大的亞科,其他都是小的亞科),而鹿則是反芻亞目鹿科,不屬於牛科。不過,雌羚羊和雌鹿確實長得有些像,不能怪古人分不清,不信你搜一搜網上的圖片。非洲、阿拉伯的蒼羚的一個亞種,也曾被西方學者稱作“小鹿瞪羚”。
傳說羚羊睡覺的時候,為了避免被天敵捕食,會將角掛到樹上,身體懸在半空,這便是“羚羊掛角”。但顯然這是不合理的:首先,上去容易下來難;其此,就算雄羚羊靠這招能躲過天敵,那雌羚羊(大部分品種的羚羊雌性無角或微角,尤其是中國常見的幾種)和小羚羊晚上睡覺就自生自滅了?所以我覺得是某頭不幸的羚羊,跳得太開心,角掛樹上掙扎不下來了,於是閉上眼睛等死,正好被古人觀察到了。古人感覺這和某些性交上的姿勢有些像,於是便流傳開來了。後來宋代人用“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形容詩的意境超脫,禪宗又用來比喻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妙語。
[uploadedimage:14070196]
(難道這就是“羚羊掛角”?僅供參考。)
(若有侵權,煩請聯系我刪除。)
羊與懷孕
文章開頭,提到夜羊社和羊城百合喜歡創作(蘿莉/少女)孕婦。那麼羊與懷孕有關嗎?還真有,而且很大——胎兒所生活的液體,不就叫“羊水”?而“羊水”外面,就是分泌羊水的“羊膜”。(隨著胚胎發育,羊膜和再外面一層的絨毛膜密切緊貼,形成胎膜,即中藥胞衣。)緣,妙不可言。
至於語源,或許是取羊水像羊毛一樣溫柔包裹胎兒之意?又或,羊是古人最早馴化的大型哺乳動物,所以接生知識、術語產生最早,後來為了避免“人水”、“人膜”的歧義,於是就借用了羊的?
附:
羊的美好寓意
祥:示字旁表祭祀或占卜等巫術活動。祭祀用羊,占卜得羊,則祥。
羕:水流綿長悠長。後世作漾,又與瀁混淆。
養(養):養育,供養,奉養,撫養,飼養。
美:羊羔肥美(大)而味甘,美矣。
善:上羊下言,似說善言如羊咩咩的叫聲。又或,談到吃羊,便是善。
膳:吃羊肉即用膳?
群:君子如羊群聚集。
孝:羔羊跪乳。
法:法字古作灋。傳說廌能辨是非曲直,會用角去頂觸不直之人。神獸廌又名獬豸、解豸、獬廌、獨角獸、神羊、任法獸、直辨獸、觸邪,大者如牛,小者如羊,類麒麟而黑青毛獨角,額上長著類似羊角的獨角。
義(義):舍生取義,即如羊羔犧牲之我。(《易》中便有“我”字作第一人稱,但公卿、諸子多用“吾”,唯《孟子》、《莊子》用“我”較多。可能是“我”作動詞時可以通“殺”,所以只有豪俠仗義之人才喜歡用。)
樂:羯鼓,八音(八種樂器,現在有所謂“八音盒”)之首,騸閹過的公羊羊皮為鼓面。(所以“羯”作動詞就是閹割。南北朝時期或更早一些時候,佛經的翻譯中出現了一種羊頭魚身的水生異獸,後來譯名逐漸固定為“魔/摩羯”。)又傳說,古人以馬(或曰犬)、牛、羊、雞、豕的叫聲定下五音,羊叫對應商音。
和:溫和合群,善良隨和。
羑:一通優秀之優,二通誘導之誘。言之秀者即誘。但今天“誘”卻多用作貶義,而不知古人以“循循善誘”為美,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乎?乃至“保佑”、“以右為尊”[周代普遍右尊,只有楚國和周邊一部分少數民族左尊]等詞和習俗,可能都和“羑”有關,是取的諧音。
冬天快來了,記得喝一碗熱乎的羊肉湯祛寒。(然後再羑拐幾只迷途的羔羊[bushi]。)
2022年10月12日、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