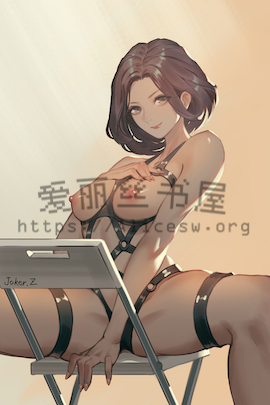從我離開醫院後就一直發生怪事。先是一些鄰居丟失的東西在我的陽台上出現,再是鄰居們看到我深夜在走道里“形跡可疑”,更奇怪的是等我不得不搬離那座公寓,“我”的小說版稅支票離奇的自己改寄去了新的公寓。我這才開始重視我病歷上那些難懂的心理學單詞,我開始服用處方藥,但這些藥物只是讓我變得遲鈍,終日昏昏沉沉,古怪的事情仍在發生。我自暴自棄停了藥,停藥地第一個晚上我就失去了睡眠。我平躺在床上,聽著時鍾嘀嗒嘀嗒的響聲,沒有一點困意。窗外偶爾路過一個打著手電的人,光线透過窗簾投射在我右手邊的牆上,我注意到上面有一塊人形的陰影,和我在鏡子里看見的形狀差不多。一個“我”正坐在我床邊,看著躺在床上的我。
隨著光线遠去人形也不見了,我起身打開台燈,什麼也沒有。房間里只有我的床、床頭櫃、一把椅子和寫字台。我的影子打在左邊的牆上,一動不動。
那之後我變得有些疑神疑鬼,我時常能看到多余的影子跟在我身後,在充滿水霧的鏡子里瞥見人形的色塊。當我回頭或擦去水霧,又什麼也沒有。我又開始服藥,沒什麼用,我變得有時失眠,有時睡一整天,並且看到更多人形的東西。我把那破藥投進了馬桶,買了便宜的威士忌喝,每天都醉得像個俄國狗熊才能入睡。終於有一天我的病情又惡化了,我把空酒瓶放在床底後躺上床,剛閉上眼睛就聽見腦袋邊上傳來一聲嘆氣。
那是和我錄音機里充滿雜音的錄音非常像的,我的聲音。
“他”終於不滿足於逼瘋我要和我干一架了。
我翻出酒瓶朝著聲音的方向扔了過去,酒瓶干脆的在牆上炸裂,我什麼也沒砸到。那當然了,“我”正躺在這里,那里什麼也沒有。我懶得和“他”糾纏,關上燈想要睡覺。燈滅後“他”卻變得更活躍了。我聽見他走向寫字台,掏出筆窸窸窣窣寫了起來。又是那些該死的小說!我摸著黑過去把筆記本扔到客廳,“他”頗為遺憾的把筆放回架子,坐在椅子上看我發飆。我要求“他”不要再寫那些奇怪的小說,但他輕描淡寫的用“寫作是我的生命”拒絕了。
“那就寫上你自己的名字,隨便什麼地方都行,把它寄到別處去。我是個偵探,不是作家。”
“可我就是你啊。”他的聲音帶著一點上揚,好像在說什麼好笑的事。
這場談判無果而終,我和他都絕不讓步,爭論到了半夜,後一個月的支票依舊寄到了我手里。比起我蹩腳的偵探工作的酬勞,他的支票值錢得多。我本想把那該死的支票撕掉,一會沒看到它就變成了房租的收據,他哼著歌用那收據在我耳邊扇風,像個打了勝仗的將軍一樣得意。我想再換座公寓,打包好行李後我的病歷卻被人惡意泄露,沒人想把房子租給一個精神病人做辦公室。我只好回去,一邊和房東交涉一邊看著他囂張地在新買的沙發上吃葡萄。
看在錢的份上房東沒有把我趕出去,但我確確實實的失去了我清淨的住所。我再也沒有籌碼和我的心魔對抗了,只能任他在我的屋子里自由活動。
他買了唱片機,買了鋼琴,甚至還養了只鳥。我的辦公室瞬間被他的私人物品擠滿。來了客人,還會恭維幾句裝修的品味不錯,鳥兒養得真好。有時我也會發現一些給我的禮物,像是風格不搭的提燈,新款的剃須刀(我沒見他長過胡子),內行人士做的黃頁,只要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什麼是“給我的”什麼是“他的”。我有些搞不懂他的想法,他像個占便宜的室友,像個強勢的監護人,又像個包養情婦的財主。無論他的本意是什麼我確確實實受到了照顧,這讓我很不自在。我決定再和他談一次。
他像是讀透了我的想法,第二天下午我注意到桌子上多出一份茶具,今天他要和我共享下午茶。作為前段時間的回禮我多叫了份糕點,用了待客的茶葉。如我猜測的一樣他對茶和糕點並沒有興趣,一手撐著頭一手用小餐叉把柔軟的蛋糕剁成碎片,仿佛在模擬他並不真正存在的咀嚼功能。他還不算是怪力亂神,他只是我的一部分。我正坐在桌子這頭,所以他不能在桌子那頭咀嚼,那些蛋糕應該是被我的幻覺加工過,我現在可能一邊喝著茶一邊瘋狂剁著桌子那頭的蛋糕……他似乎聽到了我的想法,錘著桌子大笑起來。
我有點窘迫,但只能忍到他笑完。
那之後的一下午我都在試圖向他提問,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我就基本忘記了我們問答的內容。我只記得某一刻他盯著我的眼睛對我說話,那張光滑無胡須帶著傲慢的臉像是二十歲的我在質問現在的我。
他說:“奧爾菲斯,你是叫奧爾菲斯對吧?請你記住,我不是你的敵人,從來不是。”
他還說:“我說過我是一名小說家。小說家不會阻止一些可供寫作的素材發生……無論那是好事還是壞事。”
“但你……到底是什麼?”
我洗盤子時那盤碎蛋糕屑已經被倒進了垃圾桶里。
那之後他消停了許多。白天基本不見他的蹤影,夜里總是趴在寫字台上寫小說,對我的搭話有些愛理不理。古怪的事情仍有發生,鄰居們都已經習慣了我偶爾的怪異行為。我想我可能不會康復了,我的身體糟透了。但假如有天我收到一筆偵探小說的版稅,那應該不算是壞事。一位朋友,住在我的身體里,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