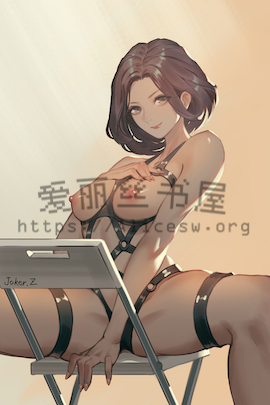那個“幸運兒”被推出了人群。不具名的小子,穿著簡朴,面容干淨,玻璃鏡片下的臉蛋帶著淡淡的痘痕,姜黃色的頭發反著火光看起來格外艷麗。
他可能和同伴失散,東張西望在圍著他的人群里找著什麼,一無所獲。他終於察覺他站在人群中的一處孤島,密密麻麻的人像潮水一樣圍著他,他試圖向旁邊的人借道出去,沒有人讓開。他開始害怕這詭異的氣氛,說話變得結巴,身子微微發抖。所有人都帶著詭異的笑容望著他,像咧著嘴看羊的狼,呆在這里一定會發生什麼不好的事情,他想要逃走,蹲下想從人縫里爬出去,但立馬有人把他拖了出來。一個男人把他從地上抓起來,人群讓出道,好讓男人扛著他走去哪里。他拼命掙扎,沒有用,那男人的手指像是鐵鈎,身軀像是石壁,任他拍打任他踢,男人一聲哼哼都沒有。最後他被帶到了終點,一個舞台,這個小村落的中心,上面打著光,燈火通明。誰是這舞台的主角?毫無疑問是那幸運的小子。
他被扔上台,幾個姑娘熱情地圍上去,按住他,對他笑,扯開他衣服。他被那些美麗的姑娘迷惑,沒有激烈反抗,但當他看到姑娘們拿出的另一身衣服,他又掙扎了起來。一件可愛的裙裝,或者說,可笑的裙裝。他掙脫姑娘們准備逃走,但那個強壯的男人立刻爬上台,把他困在上面,一拳打在他肚子上。他被這一拳打得吐酸水,接著又受了第二拳、第三拳。男人打到他不再掙扎才下去,他留在台上哆哆嗦嗦地任姑娘們給他套上裙裝。姑娘們給他拴好蝴蝶結,用手指梳理他短短的頭發,還貼心地擦去他嘴邊的汙跡。然後她們也跳下舞台,像仙子飛入花叢。
現在所有人都注視著他。他不敢跑了,站在舞台中間,緊張地往下拉裙子。台下有人向他吹口哨,大喊他像個欠操的婊子,另一個人反駁,說他明明是個欠操的處女婊子。人們哄笑起來,他在台上漲紅了臉,在人群中四處掃視,希望同伴能出來幫幫他。但他的同伴沒有出現,也許正在人群中注視著他的丑態,也許早在他們走失時就離開這鬧劇現場。等人們笑夠了,奇異的音樂響了起來,一個穿著怪異的女人走上舞台,抬手撫摸他被汗潤濕的臉頰,神色如母親般慈祥,卻讓他不安。她不知從哪里拿出一個瓶子,顏色詭異的液體在里面晃動。打開瓶蓋,一股異香飄了出來,那味道像是遠方來的香料,至少不是這個地區的土產。女人將液體從他頭頂淋下來,好像一場簡易的洗禮。以此為信號,許多男人從台下爬了上來,那女人在他額頭留下一吻,就退到了男人們的身後。他猜到了,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一場可疑的祭祀,他是塗著香料的羔羊。他知道自己無法反抗這些人,認命似的站著等待這些男人宰割。
那些男人像是吸大麻一樣湊近幸運兒的頭,聞他身上的香氣,他們開始變得亢奮,喘起粗氣。最好來痛快點的,他想。但事情可不受他控制,一個男人掏出匕首,切開了他的胸前的布,而不是他的氣管。他的身體裸露在寒冷的空氣中,帶著青紅淤痕的肌膚展現出來,一只大手拽住他一只乳頭,痛的他踉蹌向前一步,踢到一只腳,倒向那個拽他乳頭的男人。那男人哈哈大笑,吻上他因吃驚而張開的嘴,卷住他的舌頭吮吸。那感覺非常差,沒有愛,沒有溫柔,他只覺得對方想吸出他的魂。另一個人摸到他屁股,他嚇了一跳牙齒刮到和他接吻的舌頭,那男人立刻抽出嘴怒罵他,拿膝蓋頂他的腹部。他又吃了痛,變得更加驚恐與順從。後面的男人看得幸災樂禍,用膝蓋壓住他的腿,掀開他的裙子,將被脫得精光的下體露出來。肉塊軟綿綿地垂在下面,男人扇了那小東西一耳光,他立刻又開始掙扎。前面的男人動手制住了他,將他的手臂與身體捆在一起,他只能猛烈晃動他還能動的軀干,但在男人們眼中這卻只是邀請似的扭屁股。後面的男人掰開他的臀瓣,露出里面濕潤的小孔,毫不留情的把手指捅了進去。他痛到脫力,叫喊開始帶著哭腔,男人毫不憐惜,繼續摳那處密穴,並試圖塞進另外一根手指,但太緊了,完全塞不進。於是另一個男人向他提議,遞給他一個小瓶,他們拔出手指,然後直接把小瓶的口塞了進去,粘稠的液體流進他的腸道。他惡心地厲害,那東西好像有什麼放松肌肉的藥物在里面,很快他就連蹬腿都做不到了。他的下身軟如爛泥,好像已經從他身上剝去了,男人拔出瓶子換成手指,非常順暢地插到底並塞進了第二根第三根。手指用力撐開洞口,深色的丑陋的腸肉暴露在空氣中,這藥的效果遠比他們想的好,准備工作高效的完成了。手指抽了出去,短暫的休息使那小子不安,他很清楚接下來又是什麼,這才剛剛開始。
一柄肉刃,像刺刀一樣刺進了那個幸運兒的身體。他麻木的下體基本上沒有痛覺,但意識到異物在里面的瞬間他哭了起來,聲音很小,卻流下大滴的淚。第一個發現的人毫不體貼地指了出來,他們又開始笑他,前面那個男人掰起他的臉,拿舌頭舔他眼淚,戳開眼皮碰到他的眼球。他沒法掙開這男人,甚至沒有足夠的力氣趕走這惡心的肉塊,只能由著它在他粘膜上游走。謝天謝地,後面的人沒在這時候操他,要不是周圍的人都在看那舌頭要玩什麼新花樣,他的眼睛可能在運動中被戳破。但這也說不上好,肉棒一直卡在他肉里,微微脈動,時間長得要讓他以為那東西原本就長在那里了。終於,前面的男人抽出了舌頭滿意的舔舔嘴,他正要松口氣,後面的肉棒突然抽開然後猛地又挺了進去。那力道像是要擊碎他的內髒,像要把卵蛋都塞進他屁股里,但最恐怖的是,他對此幾乎沒有感覺。他們現在就算把真正的刀插進去恐怕也沒什麼變化,他能流著血拔出刀,然後流血到昏厥都感受不到痛。他的身體由里到外都不由他掌控,他甚至喪失了評估痛苦的能力。肉體麻木讓心靈也開始麻木,他像個布娃娃一樣任他們操,只求這事能快點結束。
男人們注意到了他的怠倦,他像個死物一樣趴著,偶爾發出一點聲音,像是死去的蟲仍在晃動它的腳。他們後悔讓他這樣輕松了,作為補救他們開始亂扯他尚有知覺的部分,但這也沒太大用,他的眼神像個殉教的修士。他們開始怪那個拿藥出來的同伴,於是那人只好又開始出主意,如果刺激不夠,就給他雙倍的刺激。他沒聽明白他們要干嘛,但他的身子松了刑,前面的男人松開手去拉自己的褲襠——那里面老早就准備好了另一柄硬邦邦的槍。男人們配合著讓那柄槍也頂到穴口,往那軟肉里塞。不痛,他仍然不覺得痛,只是這讓他心里發麻,兩支粗長的棒子捅進了他的體內,搞不好他就會被他們撕成兩半。當然他想得太夸張了,這最多扯傷他的會陰,他的身體不至於被肉撕開。不過他又開始掙扎就已經達到了目的,男人們得意的在他身體里競賽,像是在拼刺刀。他們還嘲笑他因為麻木與精神折磨依舊萎靡的性器,荷爾蒙讓他們瘋狂,他們就像戰勝的野獸一樣耀武揚威。軟肉和同伴的肉棒互相擠壓、磨蹭,帶出帶著血絲的粘液,他們肯定扯傷了哪里,但他感覺不出來。最終他們射了出來,在里面。子種往著幸運兒肚子里鑽,在碰到那不存在的歸宿之前被重力拽下,從肉棒的空隙間流了出來。
那兩個人躺倒在地上喘的像要死的牛,另一個人把那小子從疲軟的肉棒上拉起來。他腿腳發軟站不穩,靠到那男人身上。他這才注意到人群沒有散開,他們一直看著他受刑,好像這是一場表演。男人掀起他的裙子露出他流著濁液的下體,人群躁動起來,他們大喊繼續,大喊下一個。他再次意識到這荒唐的狂歡永無止境,直至他死亡,直至他們死亡。毫無意義,這事情毫無意義,但他們會繼續執行,痴愚而盲目,一如他們的主。他望向天空,向著滿月祈求,但滿月冷酷無情,看著他墜向深淵。於是他不再祈禱,不再思考,讓他的靈魂死去,留下空虛的皮囊為他們演劣質的木偶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