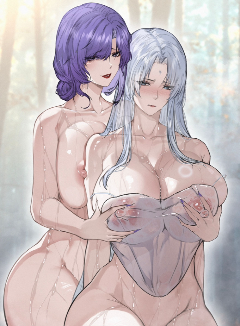岳航哪兒能讓他占了便宜,急忙抗議:“那怎麼行,你若出了個偏僻題目,那我們不是肯定要輸了!”
文祖峰不懈看了他一眼,略做思索,道:“那咱麼就來斗個簡單的,射物怎麼樣?”說著拾起一支竹筷,甩手扔了出去,臨桌上一個茶碗應聲而碎。
“這未免也太簡單了吧,要怎麼才能分出勝負呢?”岳航道。
“那我們就比一息之內誰射碎的杯子多,多者為勝。怎麼樣?沒有難為你門吧?”文祖峰見岳航捏著下巴猶豫,不時扭頭已眼神詢問身旁得董書蝶,嗤聲笑道:“怎地,沒膽的砸碎,連接個賭斗都要看女人臉色麼?我看你還是回家吃奶去吧!”
岳航被他說得臉熱,微感急躁,可董書蝶一直皺著眉頭,顯然並無把握取勝,他本事不濟,怎敢豁然答應。
正低頭苦思,忽地靈光一閃,背著眾人探手入懷,待觸到一物,立時狂喜“要比一息之內誰射碎杯子多嘛!那此物可正好派上用場呢!”
心里雖樂開了花,表面卻不動聲色,假意赤目怒視:“比就比,難道少爺會怕你麼!”表情猙獰,倒真似被激得失了理智。
董書蝶見他答應了,暗罵他魯莽,扯起他衣袖低聲提醒道:“師弟,咱們可不擅長投擲呢,千萬別意氣用事,免得待會後悔莫及…。”
岳航此刻胸有成竹,那兒還聽得下去勸,甩開她拉袖之手,大模大樣道:“女人家懂得什麼,少來管這些事!”
見他盡來無理取鬧,董書蝶也不知是該氣還是該笑,嘟嘴扭頭,不在理他。
後園武場之內,媚魔宗一眾侍從已布置妥當,在一顆碩巨的大樹上,用絳线稀疏懸了百十來個茶杯,陽光一映,磷光點點,甚為壯觀。
距大樹百步開外,用白漆在地上標了道白线,兩隊人馬分峙线後。
文祖峰扎袖斂襟,神采飛揚,仿佛已見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給自己磕頭認錯的糗樣,不覺笑出聲來。
驚覺失態,略整顏色,對正偏頭生們悶氣的董書蝶道:“董小姐,你為主我為客,所以待會兒比斗時由我方先下場,貴方應該沒什麼異議吧?”
董書蝶呼扇著一對大眼,扭頭瞪視岳航,冷哼一聲:“我一個女人家哪兒做得了主啊!文公子還是去問我師弟吧!”
岳航聽她用言語擠兌自己,尷尬萬分,可此時怎好向她低頭,只好置之不理任她說去。
對文祖峰道:“你先也好,若我先出手,定一下把茶杯通通打碎,到時可就沒有機會看你出丑了!”
文祖峰早認定他是個草包,哪兒會聽他胡吹大氣,不屑地搖搖頭,抬手做了個手勢,身後一位玄衣老者行至身側躬身行禮。
文祖峰略微點頭“許老初至我內司,如今給你個立功的好機會,你可要好好把握啊!”
他語氣頤指氣使,沒有一絲尊老之意,旁人看了都覺別扭,那老者反而展顏一笑,恭恭敬敬應了,卻無半分諂媚之意。
先前看文柤峰做盡姿態,岳航本以為他要親自下場,不想竟著實被他誆了一把,可如今阻止也晚了,先前也並未說明不許別人代替出場,只能暗罵對手狡猾。
許姓老者面貌平凡,身佝體僂,除了那雙熠熠生輝的陰戾小眼外再無一絲出奇之處。
只見他大張十指,雙掌貼在地面上一掃,已夾起一把大小不一的沙石。
沿著漆线踱步游走,目光定定瞄著前方磷光,似乎在尋找最佳的投擲角度。
終於選定位置,老者錯步站直,倏地伸直雙臂,指掌連彈,手里的沙石電射而出,大樹方向立時脆響連連。
一息過後,老者負手回身,笑容滿面來到文祖峰面前:“小老兒技巧微薄,只碎了三十六只杯子,慚愧慚愧!”
文祖峰拊掌大笑:“許老厲害啊!待我回京定要在父親面前好好說說你的好處!”自覺勝局已定,得意洋洋瞧了眼岳航道:“怎麼樣?這位少宗主還要比嘛?”
“一息射碎三十六個杯子,這怎麼可能呢!”岳航猶自不信,只以為著老頭在吹牛皮,剛要出言嘲諷,卻聽樹邊負責點數的侍者高聲喊道:“杯碎三十六整!”
霎時目瞪口呆。
董書蝶看他樣子,搖搖他身子幸災樂禍道:“怎地?剛才不聽人家勸,這下要吃虧了吧!從他投擲手法來看,他必與荊楚郡許家有所關聯,許家暗器天下無雙,看你要怎麼勝他!”
岳航只是被那老者射物神技震懾住了,其實並未考慮到輸贏,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不會輸的,故作輕松回道:“輸就輸嘍,有什麼大不了的。”說罷起身離座,准備下場。
董書蝶緊皺眉頭,咬著嘴唇盯了岳航一會兒,終是不忍看他受挫,伸手抓了他後襟:“師弟,要不師姐來替你吧,師姐雖不精擅暗器,但借著勁力上的技巧或許還有一线取勝的機會!”
岳航心里一暖,再不忍與她斗氣,貼著她臉面私語道:“師姐莫要擔心,岳航可不是莽夫,敢與他賭斗自然有所依仗!”
“平時可不見他有何絕技,怎地今時卻如此自信?”董書蝶將信將疑,不過看他神態不似作偽,不禁想起昨晚打兩位師姐處聽來得稀奇事,嫣然一笑:“哦?那師姐可就擦亮眼睛看你表演了!”
文祖峰見姐弟二人交頭接耳,也不知在商量什麼,怕他們想些取巧法子作弊,猛咳一聲:“你們到底要不要比了,若不敢比就剛快給我磕頭認錯!”
“催什麼催!小爺這不是來了麼!”岳航沒好氣應了一聲,一步三顫地來到漆线前,踮腳看了看那些遠處星星點點的白光,眉頭死死皺了起來。
百步距離說遠不遠,可以岳航目力,堪勘能分得清杯子輪廓,若要規規矩矩投擲,恐怕一只也未必射碎,這時越來越覺得剛才那許姓老者厲害。
岳航弓步而立,雙目凝神,臉上勉強擠出一絲憂色,再配上他全身小幅度的顫抖,旁人看來還真似明明心里沒底愣要衝作勢在必得的樣子。
文祖峰見他作勢半晌沒有動靜,心下暗笑,出言嘲諷道:“你到底射是不射,別在這兒浪費本公子時間!”
岳航懦懦放下架勢:“自然是要射的,不過…就這般分出勝負太過無趣,不若我們加些賭注,那才更有樂趣嘛!”似是太過緊張,連說話也顫起音來,勉勉強強說完這句,額角已隱顯汗跡。
“哦?那你說說要怎麼加大賭注啊?”文祖峰道。
“那咱們就掛一萬兩白銀…。額………不,十萬兩白銀的彩頭!另外如果以後相見,輸的要給贏的鞠躬行禮”岳航胸膛急速起伏,目光始終不敢與文祖峰對視。
十萬兩並非小數,即便有敵國之富,恐怕一時也難以籌措,這賭注可說高得離譜。
文祖峰微微皺眉,思索道:“我當剛才他算計些什麼,原來是想弄個令人難以接受的賭注來詐我,這種拙劣手段也想糊弄住我麼!”冷笑一聲:“既然你想孝敬銀錢,少爺也樂得成全你,就怕你輸了死不認賬,可要擊掌立誓才行!”
見他已上鈎,岳航心里大樂,兩步竄上前去,快速與他擊了一掌:“若誰敢輸了賴賬,那就讓他後代男為奴女做娼!”不等文祖峰反應,已大模大樣回到漆线前,伸臂踢腿,哪兒還有半點心虛之色。
文祖峰被他弄得一怔:“難道他有什麼取巧之道嘛?”心里越發不安,只是誓言已立,想反悔也晚了,只希望他只是裝腔作勢而已。
岳航此時也不必隱藏,笑嘻嘻地舞動雙臂,趁著無人注意,把懷中那對象抓在手里,嘴里念念有詞:“各位看好了啊!今日岳某人就表演一下我最拿手的凌空碎物之術”
“呔,乾坤碎杯手!”岳航一聲脆喝,單掌推出,一顆黑色彈丸拋射而出,無氣無力地落在大樹下,只聽“轟隆”一聲巨響,地面彪起一團黑煙,緊接著枝丫橫飛,砂石亂濺,待到煙塵散去,整棵樹也給碎去大半,更別說掛在其上的杯子,恐怕連粉末都找不到了。
時下火器軍陣中用得最多,江湖中倒很少出現,文祖峰出身貴胄,哪兒認得這等殺伐之器,一時驚的目瞪口呆,再說不出半句話來。
董書碟早認得火器,一下恍然大悟,喜喜走上前去拍了拍岳航肩膀:“死家伙,怎地不早知會師姐一聲,害我還要擔心你!”
岳航揚起下巴,美滋滋回道:“對付那等蠢人還要師姐操心麼?”
董書碟強忍笑意,抬手在那腰眼狠狠掐了下:“瞧你那樣兒,只不過是取巧罷了,值得你這般高興?”
岳航也不躲閃,此刻心情愉悅,樂得跟她嬉鬧“取巧怎地了,不是也給你賺了十萬兩白花花的銀子呢!”說到銀子,二人不約而同看向苦主,不禁掩嘴偷笑起來。
那許姓老者一嗅磺臭,眉頭一皺,凝視一臉得色的岳航,終忍不住上前問道:“這位岳公子哪兒得來我許家的霹靂雷火!”
岳航被問得一愣,這才想起這老者就是許家人,想要否認恐怕行不通,回道:“我這火器是花大價錢從店鋪里買來,原也不知是何名頭,不想竟是許家的霹靂雷火。”
老者佝僂著身子,一對小眼翹視岳航雙目,僵糙面皮微一扯動,露出一個怪異無比的笑容:“岳……。宗主有所不知,我許家的火器按其用途分成很多種,而剛才您用這枚無論藥量還是配比、封包、威力均是巔峰之作,只有我許家家主之尊才配使用,絕不會外賣的………。”
“額…。”本想胡謅幾句敷衍了事,卻自己扇了自己嘴巴,一時倍覺尷尬,紅臉半晌說不出話來。
“哈哈哈哈……”那老者忽然大笑起來,陰戾小眼精光暴漲:“幾日前我許家少主被人偷襲負了重傷,據說那時失了兩枚霹靂雷火,不想……。”
“原來也是個仇家!”岳航冷哼一聲“幾日前曾與你許家衝突不假,但那時可是許子衡無端想要我等性命,相斗時有所傷亡在所難免那,可不要說得好像我們是攔路搶劫的土匪啊!”
董書蝶見這老者有責仇之意思,撫掌一笑:“這位老人家,那自以為是的許小子只丟了兩根手指已經很幸運了,若不是他生了一對鳥畜的事物逃起來神速,說不定小姐我還能剁下他一雙腳來呢!”她可以對文祖峰恭敬忍讓,可並不懼怕許家之人,言語頗有尋釁之意。
老者臉色陰沉,默然良久,長嘆一聲:“好!好!好一個媚魔宗!”轉身回到文祖峰身後,環抱閉目,不再言語。
文祖峰早從震驚中恢復過來,聽得三人對話才明白原來岳航是用火器取巧勝了自己,一時大恨,扯著嗓子罵道:“該死的砸碎,有種便光明正大斗一斗,盡用些無賴法子算什麼男兒漢!”
岳航無奈搖搖頭:“唉!文公子你可說錯了呢!岳航哪兒有半點欺騙之意啊!
咱們又沒規定要用什麼東西射杯子,怎地就不許我用火器了。
“你…。”文祖峰臉色發綠,氣都喘不均勻了,若非估計顏面,早撲上前去咬死這該死的家伙。
岳航走上前去,拍拍他肩膀嬉笑道:“嘿嘿!文公子,咱們可立了誓言呢!
那以前的仇怨就一筆勾消,那十萬兩白銀不知你要何時兌現呢?
文祖峰憤憤扭開肩去,冷哼一聲,轉身闊步向外走去,賓客隨侍見主子走了,也都快步趕上。
“喂!文公子,你不會要賴賬吧!小心誓言會實現的!”岳航心里樂開了花,雙手捧在嘴邊高聲喊道:“還有還有,記得下次見了我可要鞠躬行禮啊!哈哈……”
旁邊的董書蝶笑得小嘴合不攏,勉強騰出揉著肚子的手來揪猶在惡語嘲諷的岳航:“好……好了師弟,氣走他就好了,別在多惹是非了!”
岳航也知追著宰相的公子要債不太可行,畢竟自己現在還沒這實力,也只好出出氣就罷了。
剛要離去,卻聽外面傳來一陰柔聲线:“文公子來傅某家中做客,怎地不先通知我一聲,也好讓我略盡地主之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