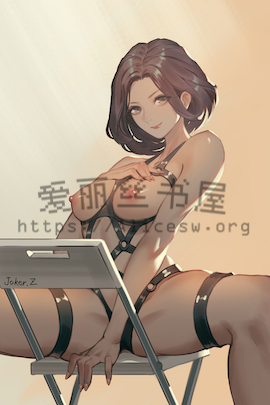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五嫂,五嫂,”每天早晨,剛剛爬出被窩,奶奶家的房客,那個姓范的小腳老太太都要捂著浮腫的面龐,憂心忡忡地走進屋來:“五嫂,五嫂,你看看,我的臉是不是又胖了!”
小腳老太太年近五旬了,如果不是嚴重浮腫,從她那適中的身材、細白的皮膚,可以想見年輕時,肯定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小美人。小腳老太太薄薄的小嘴巴像只老母雞似地一天到晚咯咯咯地沒完沒了地念叨著:“五嫂,五嫂,你看看,我的臉是不是又胖了!”
“喲——”這似乎成了慣例,我趴在被窩里,模仿著小腳老太太的樣子,頑皮地捂著自己的小臉,衝著奶奶喲喲著:“奶奶,奶奶,你看看,我的臉是不是又胖了!”
“這孩子,”小腳老太太見狀,衝我苦笑道:“這孩子,好調皮!”
“嗯,”正忙碌著的奶奶,認真地審視一番小腳老太太的面龐:“是有些胖了,老范啊,抓點藥吃吧!”
“唉,”小腳老太太苦澀地咧了咧嘴:“五嫂啊,還抓藥呐,連飯都吃不上溜,哪來的錢,抓藥啊!”說著,小腳老太太順手從鐵鍋里,抓起一塊熱氣滾滾的玉米餅,老姑見狀,氣鼓鼓地嘀咕道:“這個褶子,真不要臉,總吃咱們家的飯,咱們家的飯是白來的啊,咱們還吃不飽呐!”
“老閨女,”爺爺輕輕地推了推老姑:“老閨女,小點聲,讓她聽到,多不好啊,唉,吃就吃點吧,她,真夠可憐的!”
被老姑嘲諷為褶子的小腳老太太,一邊咀嚼著玉米餅,一邊繼續與奶奶絮叨著她那日益惡化的病情,我與老姑穿上衣服,一前一後,溜出屋門,我一轉身,悄悄地溜進褶子的屋子里,老姑也隨後跟了進來。
褶子租住的這套奶奶家的房間,冷冷清清、空空蕩蕩。她的行裝極其簡單,僅有兩床棉被,一條褥子,以及寥寥可數的幾件換洗衣服。
在光禿禿的土炕盡頭,放置著兩個裝禎精美的小皮箱,這引起我強烈的興趣。我躡手躡腳地爬上土炕,輕輕地打開小皮箱,老姑也偷偷地湊攏過來,我們兩人同時往皮箱里張望起來:豁豁豁,皮箱里面沒有他物,全部都是各種各樣工藝精湛、小巧伶瓏的酒盅、酒杯、盤子、湯匙等等瓷器。
我順手拿走一只小酒盅、一個小盤子和兩把小湯匙。然後,咕咚一聲,跳到地下,老姑衝我使了一個眼色:“快走!”
我與老姑跑到奶奶家的後院,在一處小倉房前,有一塊廢磨盤,我將偷來的瓷器,一一擺放到磨盤上,然後,仿效著大人們的樣子,衝著老姑舉起了酒盅:“啊,干杯,干杯!”
“嘻嘻,”老姑拿起湯匙,學著喝湯的樣子:“喝啊,喝點熱湯吧!”老姑將湯匙伸進嘴里,又掏了出來,她仔細地欣賞起來:“嘿,真漂亮啊,好精細的湯匙啊,呶,這還鑲著金邊呐!”
“哦,”我也瞅了瞅,憑目視,我感覺這些瓷器一定很貴重,於是,我放下小酒盅,站起身來:“老姑,如果你喜歡,我再拿幾個來。”說完,我再次跑向褶子的屋子。
我正欲邁過高高的門檻,突然看見褶子盤腿端坐在炕頭,見我站在門口,一臉不悅地嚷嚷道:“好哇,你這個小家伙,敢偷我的東西等我告訴你奶奶去。”
褶子果然毫不客氣地在奶奶面前,奏我一本,奶奶立即把那個酒盅、小盤子和小湯匙送還給她,褶子小心翼翼地接過來:“五嫂啊,不是我這個人特,其實這些盤盤碟碟的,根本不值幾個錢,可是,可是,我就是舍不得它們啊,這些東西可都是,都是……”說著說著,褶子突然哽噎起來,傷心的淚水噼哩叭啦地滴落到地板上。
嗨——這個老太婆啊,我就拿了你一個酒盅、一個小盤子和一只湯匙唄,你就哭起鼻子來啦,真是沒出息啊,太小氣了。
哼!我和老姑站在褶子的身後,不約而同地衝她哼哼一聲,吐了吐舌頭,然後,溜出屋外,在窗戶底下玩耍起來,一邊玩耍著,我一邊隱隱約約地傾聽著褶子沒完沒了的嘮叨聲。
“你怎麼啦?”奶奶關切地問道。
“唉,五嫂啊,那些箱子我從來都不願打開,一看見這些東西,我就……我就……我就,想起我的老二哥。”
“哦,別哭了,來,上炕坐坐!”奶奶將褶子讓上炕頭。褶子抹了抹眼睛,繼續說道:“五嫂啊,我是個苦命的人啊……”
“哎,這個年景,誰的命好哇!”奶奶打斷褶子的話:“就說我吧,奔奔波波的一輩子啦,什麼髒活、重活、累活沒干過啊,可是,到頭來還能怎麼樣呢,還是吃不飽,穿不暖啊!”
“五嫂啊,你命苦也就是多挨些累,比我多吃點糠、多咽點咸菜,可是,誰的命也沒有我的命苦哇!”褶子繼續講述道:“五嫂哇,我的老家在關里,七歲那年,我的父母再也養不起我們這些孩子,便將女孩子一個接一個地賣掉,只留下兩個兒子。
買我的人是個三十多歲、皮膚較黑的女人,叼著長煙袋,她把我帶上火車,一直坐到關外的奉天,到了她家我一看,就明白她家是干什麼的啦,原來是開窯子的。她和他老爺們養了五六個姑娘,為他們接客賺錢,我一個才七歲多一點的女孩子,要給他們全家,還有那些姑娘們洗衣服,燒火做飯,一天到晚,累得都上不去炕,有時干著、干著就睡著啦,黑女人惡狠狠地把我打醒,不許我睡覺。
十三歲那年,黑女人突然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送到一個軍官家里。晚上,軍官回來後讓我跟他睡覺,說是什麼給我開苞,我給了你媽媽五十塊現大洋啊,這個騷屄娘們可真夠黑的啦。今天晚上我要好好地嘗嘗鮮,過來!
我才十三歲,那個軍官已經快六十啦,他把我折騰得一宿也沒消停,又粗又長的大雞巴拿過來就往我的小穴里面插,疼得我爹啊、媽啊,又哭又喊,這還不算,還用好幾根手指使勁摳我的小穴,弄得滿床都是血啊!接著還讓我啯他的大雞巴,那上面淨是我小穴里的玩意,還有我流出來的血,惡心死人啦,不啯是絕對不行的,他叭叭地扇我的嘴巴。“
褶子頓了頓,喝下一口奶奶遞過來的熱水:“唉,從那天以後,我便不分白天晚上,只要有客人來,管你是正在吃著飯,或者睡得正香,馬上就得陪著客人睡覺,也就是跟他們操屄!那個日子真沒法過啊。
不管多大歲數的、埋汰不埋汰的、瞎眼的、缺胳膊少腿的、半傻不尖的,你都得接,都得讓他們操,一天到晚沒完沒了的也就是這麼點屄事。
有時累得連腿都抬不起來啦,睡覺時兩條腿又酸又疼,就是來例假了,黑女人也不讓我閒著,屄里面全是經血,不能操屄,她就讓我給客人啯,如果好半天啯不出來,客人就扇我的耳光,啯疼了也不行,也得挨耳光。
嫖客什麼花花道都有哇,壓根就沒把咱當人看,有時,一來好幾個,專挑我一個操,你上去,他下來,一操就是好幾個小時啊。唉,我前世做過什麼孽啦,遭老天爺這份報應啊!
有時,我實在不願意干啦,黑女人就跟她老爺們往死里打我,用爐鈎子插我的小穴,把我綁在椅子上,找來十多個賣苦力的,老板不收他們一分錢,讓他們輪班操我,能操到什麼時候,就操到什麼時候,直到我告饒為止。
那些個苦力總也沾不到女人邊,有的人可能一輩子也沒玩過女人,今天,他們可算開了洋葷,解了大饞,剛剛射出來不到一刻鍾又硬起來啦,又排著隊等著再操一次。五嫂啊,哪個女人能經受起這群惡狼沒完沒了的折騰啊,沒有辦法,我只能告饒啦!“
“唉,苦哇!”奶奶同情地嘆息道:“這我知道,早頭我們租的那間房子,離窯子就隔一條街,就是現在鎮上的招待所,剛來的姑娘都不願意干那個事,老板真的是往死里打她們啊,哭喊聲我都聽到了,真慘呀!你老板壞事都做絕啦,不能得好死,下輩子再也托不上人!”
“五嫂啊,你算是說對嘍,太對啦,解放後,她家老爺們被八路給斃啦,而她則被送到煤窯配給了煤黑子。一提起煤窯,我就打冷戰,黑女人每個月都約估摸著下窯的煤黑子,差不多要開餉啦,便領著我們幾個姑娘去煤窯接客,由於價錢相當便宜,許多挖煤的人都願意干。
這可苦了我們幾個姑娘,一天到晚都不用下炕,兩腿一掰,一個接一個上來操,操到最後,小穴都麻啦,什麼感覺也沒有啦,褥子上白花花的一片,全是煤黑子射出來的玩意。這就叫報應,為了多掙幾個錢,黑女人拿我們當牲口使,到頭來,她被配給煤黑子,成天讓煤黑子操,活該。“
“唉,女人那,到這個世上就是受苦來的!”奶奶感嘆道。
“光復那年,”褶子繼續說道:“光復那年,老毛子殺進了奉天城,奉天的臨時政府出錢組織窯姐,說是慰勞幫咱們中國人趕走小鬼子的老毛子,黑女人見錢眼開,便把我們幾個姑娘全都送了過去。
我的媽啊,五嫂啊,我這輩子可是什麼都見識過啦,老毛子的大雞巴長得嚇人,簡直快趕上驢雞巴長啦。渾身上下全是黑毛,還有紅毛,長黃毛的也不少。
老毛子好象特別愛玩女人,他們身高馬大,拎起我來,就像拎起一只小雞似的,大雞巴操得我死去活來,他們的身上有一股嗆人的臭味。“
“老毛子更不是物,”奶奶憤憤地說道:“不管是小鬼子,還是老毛子,沒有一個是他媽的好餅,老毛子就愛女人,他們一來,到處找女人,嚇得女人都不敢出屋,好人家的閨女沒少讓他們糟踏。”
“是啊,政府的官員跟我們說啦,讓我們為蘇聯紅軍服務,免得奉天城里的良家婦女受騷擾。後來,老毛子撒走啦,國軍和八路打了起來,黑女人帶著我們幾個姑娘准備去遼陽她的老家避災,半路上遇到一股胡子,啊,命該如此,我的救星終於降臨啦。
胡子頭頭叫老二哥,騎著棕色的高頭大馬,他攔住我們,向黑女人要錢,你說這個黑女人有多麼狠毒吧,她一輩子都是鐵公雞,從她身上你一根毛也休想拔下來。她哭天喊地說自己沒錢。
老二哥不管那個,沒錢……沒錢你們就全都跟我走,黑女人在別人面前敢耍橫,遇到胡子可就成了霜打的茄子——蔫啦!她跟老二哥說,錢我是沒有哇,如果你願意要我的姑娘,相中哪個你就領走哪個。謝天謝地,老二哥相中了我,因為我是最年輕的一個。“
“是啊,跟上一個固定的主更好!”奶奶說。
“五嫂,誰說不是呢,說句實在話,我與老二哥過了幾年好日子,這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那些碟碟碗碗就是我跟老二哥過日那咱用過的,你孫子玩的那個酒盅是老二哥喝酒時用過的,我一看見那個酒盅,就,就……就想起我的老二哥!”
“那你們怎麼不在一起過啦?”奶奶問道。
“唉,別提啦,我就是這個命啦,老二哥有好幾個姨太太,可是,他對我最好,我給老二哥生了一個兒子,解放以後,老二哥因為當過胡子,被政府給槍斃啦。唉……”
“那你們的兒子呢!”
“兒子,兒子,我的那個兒子長大後,聽說我是干那個的,說什麼也不跟我在一起過,說是丟人,寒磣!唉,我啊!……沒辦法,只有四處流浪,一個人到處租房子住。我還有點錢,都是老二哥臨死前留給我的,老二哥是我一輩子也忘不了的人啊!”
“……”
“五嫂,五嫂,你看看,我的臉是不是又胖了!”
每天早晨,褶子都要履行她的慣例,捂著臉,跑到奶奶的屋里來:“五嫂,五嫂,你看看,我的臉是不是又胖了!”
“喲,”我還是如此這般,趴在被窩里,學著她那可笑的樣子,雙手捂著臉:“奶奶,奶奶,你看看,我的臉是不是又胖了!”
褶子的浮腫病越來越嚴重,最後,終於癱倒在土炕上,再也爬不起來,目睹她那痛苦不堪的境況,奶奶真誠地安慰她,並主動給她換洗衣服。
“五嫂啊,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啊,唉,我這輩子呀!”
“別傷心,想開些,人不都是一樣,我比你強不到哪去,不也得活著。你遭的罪多,我受的累多,我那個累法你是沒有看著哇。混吧,人,就這麼回事吧,什麼好啊、賴啊的,湊和活著吧!”奶奶一邊給褶子脫下粘著糞便的髒衣服,一邊解勸著她:“你別上火,想吃點什麼?我給你下碗面條吧,雞窩里好象還有兩個雞蛋,我給你打到面條里!”
大表哥隊長獲知此事後,立即將情況報告給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派人設法將褶子的兒子尋找到,她的兒子租來一輛馬車,很不情願的將褶子接回家去。
“小子,你可就是你的不對啦,”奶奶提著褶子的皮箱,放到馬車上,毫不留情地教訓著褶子的兒子:“管怎麼的,她也是你媽啊,是她生了你,沒有她,能有你嗎?她願意干那個嘛?不都是逼的嗎?”
褶子的兒子低垂著腦袋,一句話也不說。
病入膏肓的褶子,氣息奄奄地躺在馬車上,走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