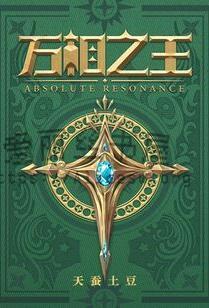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用力、用力!讓年輕力壯的大龜頭按摩子宮頸,啊~不行了,好舒服,快射進來,讓我幫你寶寶,生很寶寶,不行了,被干得腦袋都要變糨煳了,好舒服,啊~尿出來了~”
邵琪用奇怪的語調說著毫無條理的囈語,仿佛醉酒了般。
“哼,才剛開始呢,“大嫂”,還記得前年在洛杉磯那次嗎?現在妳又生了個,穴又松了,我要肏到爽可能要比那次肏久才行,肏!被干到爛的穴還敢夾我!看我肏爛妳這個比公廁還髒的!爛屄!看你今晚會昏過去幾次!”
“用力!用力!把我的屄再撐松點,這樣生孩子舒服,啊~啊~來了!
來了!好舒服!好舒服!”
邵琪最後重復那兩聲“好舒服”根本不怕被人聽到,聲音之大簡直傳遍了整棟透天別墅,但在這之後就沒聲音了。
“又昏過去了,真他媽不中用。”
我聽到自己的弟弟打了他大嫂,也就是邵琪幾下耳光,啪啪的響聲極大,但邵琪似乎仍然昏死著,沒有回應。
“賤貨就是賤貨,次等的基因再怎麼會生,不過就是條母豬罷了,還想幫我生孩子?”
弟弟清了清喉嚨,發出好大聲哈痰的聲音,“呸”的聲吐了出來。
過了會兒,弟弟房間內的浴室的門板關上“框”的聲後,出現了淋浴的水聲,以及弟弟如往常邊洗澡邊哼著歌的聲音;我沒想太,把心橫,小心翼翼地轉開弟弟房間門的門把,探頭確認弟弟確實在洗澡後,進入他房間查看。
不意外地(雖然看到這種情景,我根本應該被嚇個半死) ,邵琪呈現個大字躺在木頭地板上,身上還穿著剛喂完奶,胸口的布料被乳汁給濡濕的連身裙;地上濕濕的灘有股騷味,想必是她失禁尿了地;我蹲下看,邵琪本來就已經被使用過度、外翻松弛的陰道口,竟然完全無法闔上,還隨著她的呼吸開闔著,邵琪的前額瀏海上有口痰,想必是剛剛弟弟吐上去的。
驚人的是,邵琪整個人是保持著翻白眼的狀態昏過去的,嘴巴也沒闔上,而且眼淚鼻涕直流,簡直像整個人被肏到高潮之後,保持性興奮到極點的抽搐狀態下昏過去似的。
仔細看,她整個人都還在以相當高的頻率微微發抖。
照理來說,剛剛頂經過半個小時,再怎麼威勐的男性,也不可能光半小時就把女人給肏昏過去吧?
我想到有可能邵琪被打了什麼藥,但是看了看她的手腕、手肘,都沒有針頭的痕跡,桌上、地上都沒有什麼可疑的針筒或是藥罐,只有包弟弟因為打球運動傷害,長期在吃的止痛藥而已。
我拿在手上端詳了番,懷疑有可能這罐止痛藥可能根本不像封面所寫那樣單純,卻不小心把罐子弄掉了,塑膠罐“砰”的聲落地後,竟然就滾進了床底下去了。
我只好趕緊趴在地上,要把罐子從床底下的空間給搆出來,卻怎樣都弄不出來。
這時候浴室的水聲停了,眼看著弟弟就要從浴室出來了,我只好放棄,起身馬上離開房間,躲回廁所里繼續傾聽房間的動靜。
但這次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房間里靜悄悄的沒有半點聲音,倒是我岳母-邵琪的母親到房間外敲了敲門叫著邵琪,我弟就開門讓她進去。
邵琪的母親進房間里,似乎又給了邵琪幾個響亮的巴掌要叫醒她,她有沒有醒過來從我這邊沒有辦法知道,但沒過久邵琪的母親就離開房間,匆匆忙忙地小跑著下樓去了。
她咚咚咚的腳步聲還在樓梯間里回蕩著的時候,我的手機響起來了。
“兒子!你在哪?找都找不到你?”
電話的那頭是老媽的聲音,聽起來非常著急。
“我在樓上洗手間哩,怎麼了嗎?”
我壓低聲音說,生怕在廁所里被弟弟聽到。
“弈熹在你房間床上躺著,翻了身悶著了臉色發紫,現在你爸在急救,救護車待會就來,快點下來!”
我腦袋片空白,掛掉電話後狂奔衝下樓,看見六十好幾的老父滿頭大汗的在幫弈熹人工呼吸;過沒幾分鍾,救護車就到了門口,急救人員接手後要我跟著坐上車,我只能著急地跟著跳上車後,進了醫院直在急診室外的椅凳上枯等著。
十幾分鍾後,我爸載著媽跟邵琪的母親來了,陪著我起等,邵琪的媽媽-也就是我岳母直不停安慰著哭個不停的老媽,老爸則是眉頭深鎖著,始終言不發。
個小時後,醫生終於出來了,當醫生說弈熹狀況穩定沒有大礙的時候,老媽深深吸了口氣後用很緊繃的聲音喊了聲“太好了”
之後,整個人放松了下來,差點暈倒過去,我趕緊扶著,讓老媽回到椅子上坐好。
但醫生說現在狀況雖然穩定下來了,但仍要住院觀察腦部的狀況幾個禮拜,而且弈熹的腦功能有可能因此受損,要我們必須有心理准備。
聽到醫生這麼說時,邵琪的媽媽臉色陣慘白、十分難看,隨即離開往洗手間去了。
好不容易松了口氣,放下心來後,我這才想到:邵琪人呢?
難道她還昏死在弟弟的房間哩,剛剛邵琪她媽進去也沒能叫醒她嗎?
想起來這件事情,邵琪的本性是個淫蕩、人盡可夫的破鞋已經夠讓我火大了,我們的兒子會沒有人照顧,差點丟了小命,也是因為她這個賤貨就顧著去找自己丈夫的親弟弟通奸,被自己的小叔操得高潮昏死過去的關系啊!
我越想臉色越難看,氣得差點在急診室外狠狠地往牆上掄;好不容易壓抑住心中的怒火後,深深吸了口氣,發現自己氣得拳頭握緊,緊到不由自主地發抖,便跟爸媽說我要到外面透透氣後,走出醫院急診中心大門。
當我走出大門時,迎面來了台計程車開進急診中心大門外的回車道,車子停下後不久,有個穿著連身裙、沒穿內衣的女人走下了計程車;她胸前因為懷孕溢奶濕了片,被奶水濡濕的布料吸附在她的乳房上,如蠶豆般大的奶頭硬挺挺地,讓人無法忽視;脂粉未施的臉上滿布著淚痕,鼻水流個不停、哭得鼻頭泛紅;嘴角掛著像是鼻涕般白白稠稠的黏液,但是只要靠近就能聞到她滿嘴都是男性精液的腥臭味;她靠近急診中心大門口,在大門口那兩盞亮得令人眼睛發疼的白光led燈照亮下,就可以看到兩股體液從她大腿之間潺潺流下,甚至讓她穿著皮制涼鞋的腳,都因為踩著黏煳煳的體液而嘎吱嘎吱地作響。
下半身汨流而出的體液甚至濡濕了她連身裙的裙擺,濕透的裙擺緊貼著她的臀部,讓人看就知道她渾圓豐腴的大屁股光熘熘地沒穿底褲。
這人是我的妻子,我從小到大的鄰居大姐姐,師長親友口中的模范生、好女孩,不但有著留學國外的高學歷、體面的教職,還是樂於助人,教友們的好人好事代表;她是我的妻子邵琪,我冷冷地看著她拖著不穩的腳步朝著我小碎步跑了過來、抱著我哭了起來;我聞道了她嘴里傳出來的精液臭味、甚至可能是陳年龜頭包皮垢的臭味;我摸了摸她濕濕滑滑的裙擺,那種洗不干淨的觸感,我想,她大概在趕過來之前,被剛剛的計程車司機-在這種三半夜,可能被不只個計程車司機,個又個輪流上,整整操了她個小時,全都在她的爛穴里灌完精,才把她送過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