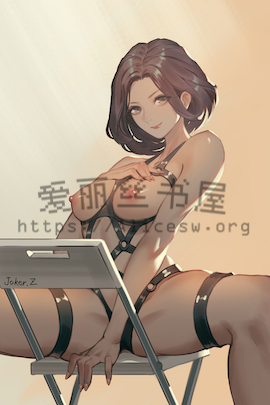廖群玉醒來,只覺喉嚨又乾又痛,腦中昏昏沉沉,費盡力氣才想起昨晚跟高衙內一幫人喝酒,最後喝得大醉。
“老廖!廖叔!”高智商道:“起來了吧?我帶了幾壇酒……”
聽到“酒”字,廖群玉差點兒吐出來,乾啞著嗓子道:“免了免了!”
“別啊。”高智商掀開帳篷,進來道:“我們一會兒上路去長安,老廖,你要不要一起走?”
廖群玉趕緊道:“我回臨安。”
“那正好。”高智商一擺手,劉詔和富安抱著幾壇酒進來,“這些酒是給我爹的。廖叔幫我帶回去。”
“這個……”廖群玉有些為難,他來唐國是給主公辦事的,哪兒能帶著幾壇酒到處跑?
“我讓劉詔跟你一路,”高智商大咧咧道:“出力的事,都交給他!”
身邊多個耳目那還了得?
廖群玉忙道:“不用不用,這點酒我帶上便是。”
“那就勞煩廖叔了。等回臨安,我請你喝酒!”
“嘔……”廖群玉酒意上涌,喉嚨一陣翻滾。
天色剛亮,眾人便整理好行裝。
石越親自帶著人陪同,一行人離開留仙坪,迤邐西行。
那位少主仍未露面,石越不敢多問,只加倍留意,車前馬後地小心照應。
他不知道,程氏商會的少主並不在車隊中,他天亮前就已經啟程,前往北面的山中。
領路的是小廝羅令,他騎了一頭小毛驢走在前面,後面是袁天罡。
袁老人沒有再打那面算命的旗幡,這會兒換了一件遮風的大氅,騎著一匹健馬,頂著風埋頭趕路。
羅令並不知道幾人的身份,只是天不亮幾名客人便叫來掌櫃,說是聽了白員外的故事,好奇心起,想去山里看看,掌櫃對鄉間道路不熟,便打發他來領路。
羅令騎在驢上,不時偷偷望向後面。
最後面一匹高頭大馬,通體赤紅,神駿非凡。
馬背上卻不止一人,而是一男一女共乘一騎。
馬上的男子身形矯健,雖然不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相貌,但氣宇不凡,尤其是那對眼睛,平常倒也罷了,一旦凝神注目,目光如有實質,盯在身上讓人大氣都不敢出。
不過羅令偷看的不是那位男客,而是與他同乘的女子。
那女子整個人都依偎在男客懷中,被他用大氅裹著,露出的面孔也戴著面紗。
但在上馬時,羅令驚鴻一瞥看到她的面容,那種媚艷的風情韻致,讓他回想起來,心頭還狂跳不已。
“那小廝又在偷看我了……”孫壽伏在主子懷里,嬌喘細細地說道。
程宗揚沒好氣地說道:“你要是再故意搔首弄姿,賣弄風情,我就把你扔給蛇奴。讓她好好教訓教訓你。”
孫壽顰眉道:“奴婢不是有意的,往後再也不敢了,求主子恕罪。”
說實話,與其帶著孫壽出行,程宗揚寧肯帶上合德。
趙小美人兒嬌柔軟嫩,讓人怎麼都抱不夠。
只不過白員外的傳說中總有狐仙,這一趟才專門帶上壽奴。
山路多年來少有人行,到處枯草叢生,有些路段因為山洪和落石,變得難以通行,連領路的小廝都走得小心翼翼,程宗揚胯下的赤兔馬卻如履平地,走得輕鬆之極。
程宗揚從鞍側的皮囊中取出一隻苹果,喂到赤兔馬嘴邊。
這苹果是在路上買的,又青又小,味道也極酸,但赤兔馬吃得開心,還高興得打了幾個響鼻。
程宗揚拍了拍馬頸,心下有些得意,要不是有這些苹果賄賂,這赤兔馬還真不一定願意讓自己騎。
別說,赤兔馬果然是名駒,即便在山間,仍然又快又穩,感覺比乘車還舒適。
白員外的故居並不太遠,小半個時辰便即趕到。
遠遠看去,院門已經塌了半邊,上面掛著一方掉漆的舊匾,寫的卻是“蘭若寺”。
程宗揚與袁天罡對視一眼,嘀咕道:“倩女幽魂?”
“不會是狐仙改女鬼了吧?”
“進去看看。”
羅令拴好驢子,過來道:“客官,這邊走。”
程宗揚放開懷里的艷婢,跳下馬四處張望了一番。
白員外的故居建在一處山梁上,位置算不得好,尤其是眼下的時節,北風呼嘯不絕,將院中幾棵槐樹都吹歪了,看上去就像一排伏地爬行的影子。
院內更是殘破不堪,屋上瓦片掉落,露出半朽的椽子,如同一排排裸露的肋骨。
透過破損的牆壁,能看到內牆上繪著佛門畫像,大都剝落得不成樣子,殘存下來的幾處,依稀能看出怒目金剛的痕跡。
羅令道:“這些房子以前都是仆人的住所,後來改成僧舍。兩邊是筒子廊,再往里就是觀音殿。”
“筒子廊?”袁天罡皺起眉頭,覺得有些耳熟。
走廊上原本裝著柵欄般的木架,但如今同樣殘破無余,有的倒在院內,一碰就化為木渣,早已朽爛多年。
院內鋪地的青磚大都已經碎裂,縫隙間長滿齊膝深的茅草。
中間三間正房改成佛殿,由於背對著寒風,比起兩側的廂房,相對還要完整一些,至少殿門還保存下來。
羅令推開虛掩的殿門,“這是觀音殿,供的觀音菩薩。”
半朽的殿門發出“吱吱啞啞”的聲音,昏暗的光线下,一尊佛像出現在眾人眼前。
那佛像盤膝而坐,雙手交迭在胸前,雖然落滿灰塵,仍能看出頭上戴著一頂垂滿瓔珞的寶冠,雙目低垂,寶相莊嚴。
比起常見的觀音像,這尊佛像多了許多裝飾性的細節,尤為奇怪的是,佛像裸露的臉頰和手臂都被塗成綠色。
孫壽打了個寒噤,臉色變得雪白。
袁天罡自從踏入院內,眉頭就沒有鬆開,擰著眉頭道:“好奇怪……”
程宗揚盯著那尊佛像,“這不是觀音。”
羅令正趴在地上給佛像磕頭,聞言愕然抬起頭。
程宗揚眯起眼睛道:“是度母。”
袁天罡道:“番僧?”
程宗揚點了點頭,“到後面看看。”
內院同樣殘破,室內器具更是一概皆無。
院側一角還挖了一口井,井側種著兩棵槐樹。
不知為何,只看著井口,就讓人覺得陰風四起,說不出的壓抑。
程宗揚沒有靠近,只遠遠看了兩眼,然後低頭看著孫壽。
孫壽此時已經渾身戰慄,若不是被主人摟著,連站都站不住。
她拼命縮在主人懷里,發出恐懼之極的嗚咽聲。
羅令也不敢進院,解釋道:“這地方鬼氣森森的,鎮上人平常也不敢來。”
眼看孫壽就要癱倒,程宗揚道:“走!”
四人再無心探察,一窩蜂出了院子,牽了馬匹,匆忙離開。
一直走出里許,程宗揚才呼了口氣,“傳言恐怕有些是真的,這地方死過不少人……”他看著懷中的狐女,“是你的族人吧?”
孫壽渾身劇顫,喉中發出狐泣般的悲鳴。
袁天罡道:“那口井蹊蹺得緊。在山梁上打井,挖到山底也未必出水。”
殿里供的度母……
兩邊的筒子廊,多半是轉經廊,只不過經筒被破壞,只剩下架子……
白員外、狐族、番僧……
“留仙坪,留仙坪……怪不得不是遇仙坪,叫留仙坪。”程宗揚喃喃說著,心里有種不祥的預感。
那些“狐仙”與白員外相遇,便被永遠留在了此地。
而那位白員外,會不會真被番僧切片了?
他心下暗忖,是不是索性耽誤幾日,把人調回來,將整個院子都挖了,看看里面究竟埋藏著什麼秘密。
只是這麼大的院落全部挖開,三五個月都未必能夠干完,只怕誤了正事。
正猶豫間,遠處山路上忽然出現了一群人,領頭的正是那個大主灶。
程宗揚不動聲色地扯下兜帽,遮住面孔。
雙方越行越近,周族眾人的目光幾乎都落在程宗揚身下的坐騎上,對赤兔馬的神駿艷羨不已。
唯獨周飛直勾勾盯著自己懷里的艷婢,眼睛眨都不眨。
干!程宗揚心頭火起,一把握住刀柄。
忽然一聲慘叫,卻是那位大主灶馬失前蹄,不小心跌進一條雨水衝出的橫溝內。
周族眾人慌忙去救,周飛如夢初醒,匆忙上前,雙方就此錯過。
-----------------
來回耽誤了一個時辰,等程宗揚追上車隊,已經是下午時分。
憑借赤兔馬的腳力,原本用不了這麼久,但為了照顧袁天罡,程宗揚只得收斂速度,沒敢縱馬狂奔。
天寒地凍,騎馬也不是個輕鬆活。
將袁天罡送到賈文和車上,又給他喂了些熱水,袁老頭才緩過勁來。
這邊程宗揚講了自己探訪荒宅的經歷,商量要不要派兩名兄弟返回留仙坪,好盯住廖群玉和周飛等人,看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勾當。
賈文和只回了一句:“不用。”卻沒有解釋的意思。
程宗揚也是無奈,秦會之、班超這些謀士不在,身邊擅長陰謀詭計的唯有一個賈文和。
可秦賈兩人的風格全然不同,秦會之策劃計謀,處處用心周密,解釋唯恐不夠周詳,總讓自己聽明白為止。
賈文和卻是不問不說,即使問了,也只說怎麼做,絲毫沒有傳道解惑的心思。
這事兒鬧得……自己不問吧,心里堵得慌;問吧,又顯得自己沒智商。
“行!你說不用就不用。”程宗揚只好安慰自己: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把賈文和當作謀士,就給老賈足夠的信任。
傍晚,車隊抵達商州。
石越已經安排好客棧,眾人歇息一晚,第二天一早繼續上路。
為了盡快趕到長安,眾人出發極早,城門還未開啟,就驅車在城門內等候。
誰知一直等了半個時辰,直到天色將亮,城門依然緊閉。
城內晨鍾響起,本該開門的士卒卻不見蹤影。
正當眾人等得心急,城頭傳來一陣號角聲,接著成群的士卒蜂擁而下。
那些士卒絲毫沒有開啟城門的意思,反而簇擁著一名身著明光鎧的將領,大聲鼓噪著往城中奔去。
程宗揚正在納悶,敖潤面色鐵青地狂奔過來,“不好了,程頭兒!那些軍士嘩變了!”
“什麼!”程宗揚大吃一驚,自己剛在漢國經歷過洛都之亂,怎麼到唐國又撞上軍士嘩變?
難道自己一路開掛,走到哪兒亂到哪兒?
石越氣喘吁吁地跑過來,“莫慌莫慌!這些軍士只是索餉的——小的方才問過,朝廷新派來的金商都防御使昨晚剛到任,這幫士卒商量好了,要給他一個下馬威,約定今日一早三軍齊出,前去討餉——咱們正好趕巧了。”
敖潤急眼道:“兵變啊!還能不慌?程頭兒,我們兄弟這便破開城門,你們先走!我來斷後!”
石越死命拉住他,“敖兄敖兄,你有所不知,這金商士卒嘩變非止一次,自從兩年前許都防御使病逝,朝廷每派來一名防御使,這些軍士都要鬧上一回。不過鬧歸鬧,有許家人在背後約束,這些軍士倒不搶掠百姓,只把朝廷官員毆打一番,趕走了事。”
程宗揚聽著都覺得稀奇,在車內問道:“你是說這里兩年都沒有主官?”
石越不知道貴客的心思,沒敢稱呼,小心回道:“正是。”
“朝廷派來的官員都被打跑了?”
“兩年打跑了三個。”
“背後還有許家的人維持秩序?”
“就是方才那個金甲將軍,許家大公子許重山。”
“他們圖什麼呢?”
石越解釋道:“金商是唐國四十八藩鎮之一,前任許都防御使去世,許家想父死子繼,由許家長子許重山繼任,朝廷不肯,兩邊就僵上了。侯爺放心,這許重山小的也打過交道,是個知書達理之人,從不騷擾百姓,對過往客商也多加照應。眼下無非耽誤一二,斷不會有事。”
知書達理還敢和朝廷對著干,一連打跑三任朝廷派來的主官?
要是不知情達理呢?
難道要把三名主官碎屍萬段,挫骨揚灰?
漢國即使洛都大亂,宗室外戚殺得人頭滾滾,朝廷諭旨一下,各地州郡照樣凜然從命,哪里會像唐國一樣,一個防御使的家人就敢視朝令如無物——這樣的藩鎮,在唐國還有足足四十八個!
袁天罡也過來道:“這是常有的事。打一頓趕走就完。不會牽連旁人。”
好吧,是自己少見多怪了。
半個時辰之後,喧嘩聲平息下來。
一名被打掉冠冕,撕掉官服,揍得鼻青臉腫的官員被軍士們推搡著押過來。
為首的將領一聲令下,軍士們推開城門,將那名倒霉的官員連同幾名隨從都踢了出去。
軍士們發出一陣哄笑,有人甚至拉開褲子,對著那群狼狽離開的家伙撒尿。
程宗揚這回算是開了眼界。
一起藩鎮驅逐朝廷命官的惡劣事件,不見刀光劍影,倒是熱鬧得跟過節一樣。
漢國要是出了這種事,等不到第二天,老霍就得火急火燎地領著羽林天軍殺來平叛。
可聽剛才的話頭,人家這都是第三回了。
石越說得沒錯,耽擱片刻之後,軍士們讓開大路,依次放行。
那名將領還頻頻向眾人拱手,連聲道罪,果然是知書達理。
眾人一頭霧水地離開商州,由於誤了時辰,當晚只能在野外住宿。
再次啟程後,眾人加快速度,終於在第三天夜里,趕到藍田。
這里已經屬於唐國京兆府的轄地,離長安城只有六十余里。
“前面就是藍田,今晚在城中歇息一夜,明日就能趕到灞橋。家主就在灞橋迎候,見到衙內不知道該多高興呢。”
程宗揚在車內聽著石越與高智商的笑談聲,不由莞爾。
這位石家在唐國的大管事是個細致人,知道自己不想露面,特意拉著高智商在車外說話,解釋行程。
石越是石家的世仆,也是石胖子最得力的手下,要不然以石超那性子,根本撐不起這份家業。
程宗揚雖然不想露面,但看在他一路辛勞的面上,在車內開口說道:“做得不錯。這一路辛苦石管事了。”
石越一怔,連忙拜倒,口稱不敢。
說話間車簾揭開,一名美婢拿著一隻精巧的木盒下來,笑道:“一點薄禮,還請笑納。”
盒內放著一迭印刷精致的紙張,石越認得這是程氏商會發行的紙鈔。
每張面值一枚金銖,相當於兩貫銅銖,這一迭起碼有一百張,合二十萬錢。
另外還有一份文書,寫的是舞都開發區田地若干,下面用了“舞陽侯程”和“舞都太守”的大印,卻是一張地契。
“這……”石越慌忙道:“侯爺賞賜太重,小的不敢受!”
“拿著吧。”程宗揚道:“這些地本來是給建康的朋友留的,送你一處。”
高智商也道:“都是自家人,客氣什麼呢?哎呦,這地方不錯啊。師傅,也給我留一塊吧,正好跟石二哥做鄰居。”
“讓你爹挑。”
“他還不是聽我的?不行,我得多要幾處,免得他還沒死呢,就把我的錢都給花完了。”
這位高衙內口無遮攔,說起自家父親也殊無敬意,石越這幾日領教得多了,聞言啼笑皆非,最後拜謝道:“多謝侯爺!”
-----------------
藍田位於長安城東南,自古以盛產美玉知名。
尤其是水蒼玉,出自藍田玉山的溪水中,其色青碧,如冰似水,新采出的原石放置在日光下,甚至能看到水氣裊裊,宛如輕煙彌散。
六朝之中,以漢國最強,而唐國最盛。
只是經歷過數十年前的黃巢之亂,藩鎮蜂起,國勢不復以往,但繁華之處仍遠超諸朝。
不僅境中名州大郡人口稠密,連藍田這樣的小邑同樣規模宏偉。
藍田東西各有一市,西市以絲帛、糧米、酒食生意為主,東市則店鋪林立,做的都是玉器生意。
冬日夜長晝短,酉末時分,天色已暗,隨著夕陽西下,淨街的鼓聲響起,市坊內店鋪關門,行人匆忙返家,喧鬧的街面逐漸安靜下來。
三百通鼓一過,坊門緊閉,街上行人斷絕。
東市西北角,一家不起眼的玉器行早早上了門板,杜門謝客。
此時二樓的軒窗內微微一亮,有人燃起燈火。
一名面帶傷疤的凶漢惡狠狠盯著點燈的掌櫃,缽盂大的拳頭用力握緊,他指背、拳鋒上遍布著厚厚的拳繭,猶如鐵鑄。
“啪”的一聲,掌心一隻玉盞被捏得粉碎,接著一點一點捻成玉屑,從他指縫間灑落下來。
那人低沉著聲音道:“姓譚的!你什麼意思?”
掌櫃吹滅火摺,笑眯眯道:“瞧你說的,樊兄豪勇過人,普天之下,誰人不知,誰人不曉?”
“行了,譚仲!樊某這回虎落平陽,借你的地方避避風頭,你要不方便,樊某這就走!”
“別急啊。”譚仲重新取出一隻玉盞,擺在樊雄面前,然後斟上酒,做出長談的架式。
“自從樊兄去往漢國,咱們可有日子沒見了。這回樊兄攜家帶口來藍田,總得多住幾日,好讓小弟一盡地主之誼。”
樊雄氣消了一些,拿起玉盞一口喝乾,沉著臉沒有作聲。
譚仲又斟上一杯,“來來來!我們兄弟共飲一杯!”
樊雄舉杯欲飲,臉上忽然變色,他一把摔掉杯子,掙扎著想坐起來,晃了幾下,又跌坐回去。
譚仲笑容不改,自顧自飲了半盞,笑道:“樊兄這趟發了不少財啊。光是珠寶就裝了三大箱,嘖嘖嘖嘖,還拐了個花枝般的美婦人……”
樊雄咬牙切齒地說道:“譚仲!你個小人!”
“話可不能這麼說。咱們都是做道上生意的。我總得摸摸底吧?老樊,大伙兒兄弟一場,你也別瞞了,怎麼發的財?跟兄弟說道說道。”
樊雄瞋目不語。
譚仲拿起被他捏碎的玉盞看了看,“可惜了。”說著往地上一丟。
房門“咣”的一聲被人踹開,一名滿身是血的獨眼漢子持刀而入,一手擰著一名女子的髮髻,扯了進來。
那女子衣衫不整,手足都被衣帶捆住。
她豐姿穠艷,容顏頗具姿色,只是此時雪白的面孔沒有半點血色,眼中滿是驚恐。
樊雄瞳孔收緊,低吼道:“杜惡虎!”
獨眼漢子獰然一笑,沙啞著喉嚨道:“樊鷂子,有日子沒見了。”
樊雄狠狠瞪著那廝。
杜惡虎是長安城有名的惡徒,幾年前犯了人命官司,亡命江湖,沒想到會躲在這里。
譚仲道:“都是自家兄弟,不妨把話說開。老樊這回撈了一筆,但錢不到手也是白搭。這幾日我也瞧出來了,你是給人看家護院去了吧?這位小娘子想必是你的東家了。老樊是個厚道人,我猜你是不好下手。這不,杜兄弟出手,幫你把活兒都干了。”
樊雄眼角突突直跳,“人呢?”
杜惡虎獨眼凶光畢露,“除了這小娘子,其他人全都殺了!”
樊雄呆了一下,“都殺了……”
“四個隨從,兩個下人,全都割了脖子。”譚仲比了個手勢,然後輕描淡寫地說道:“放心,後半夜咱們三個一起動手,挖坑一埋——神不知鬼不覺。”
“你們兩個蠢貨!”樊雄恨聲罵道:“壞了老子大事!”
“幾條人命,算得什麼大事?”杜惡虎不屑地說道:“樊鷂子,你可是越活越回去了。”
樊雄梗著脖子吼道:“有種你們把我也殺了!”
“老樊啊,你這說的可是氣話。”譚仲道:“大伙兒都是道上兄弟,義字當頭,說到底還是一家人,對不對?”
樊雄怒視著兩人,最後狠狠啐了一口,“義你娘的頭!扶老子起來!”
譚仲在酒中下的麻藥,是專門用來陰人的,能讓人半身麻痹,手腳無力,不過藥效並不強。
他取來一壺涼水,樊雄一口氣喝了半壺,把剩下的潑在頭上,精神漸復。
譚仲道:“老樊,說說吧,這小娘子是誰?”
旁邊的杜惡虎扯住那女子的髪髻,一手抬起長刀,抵在她頸下,將她下巴挑起來。
那女子唇瓣顫抖著,一個字都吐不出來。
杜惡虎獰笑著伸出血紅的舌頭,舔上那女子雪白的粉頸,沿著她的下巴、紅唇、鼻梁……一直舔到眼角,然後猛一用力,像野獸一樣吸吮著,仿佛要把她眼珠吸出來。
那女子嚇得魂飛魄散,掙扎著哭叫起來。
“哭個屁!”樊雄反手給了她一個耳光。
那女子被打得眼冒金星,更沒想到自己的護衛會突然翻臉,一時間連哭叫都忘了。
樊雄從她衣衫上撕下一塊,塞住她的嘴巴。
然後傾過身,小聲說了幾句。
三人圍著圓桌,腦袋越湊越近,最後同時發出一陣狂笑。
譚仲豎起大拇指,“老樊,有你的!弄到肥羊不說,難得的是沒有手尾。白撿!”
杜惡虎獨目放出淫光,舔著嘴唇道:“老子還沒干過這等體面的貴人,這回可要嘗個鮮。”
樊雄罵道:“老子一路都沒下手,憑什麼讓你拔頭籌?”
譚仲勸道:“人是老樊誆來的,要上也是老樊第一個上。又不是沒開過苞的鮮物,大伙兒輪著來。”
樊雄提起已經癱軟的女子,按在桌上,手掌伸進她衣內,一把扯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