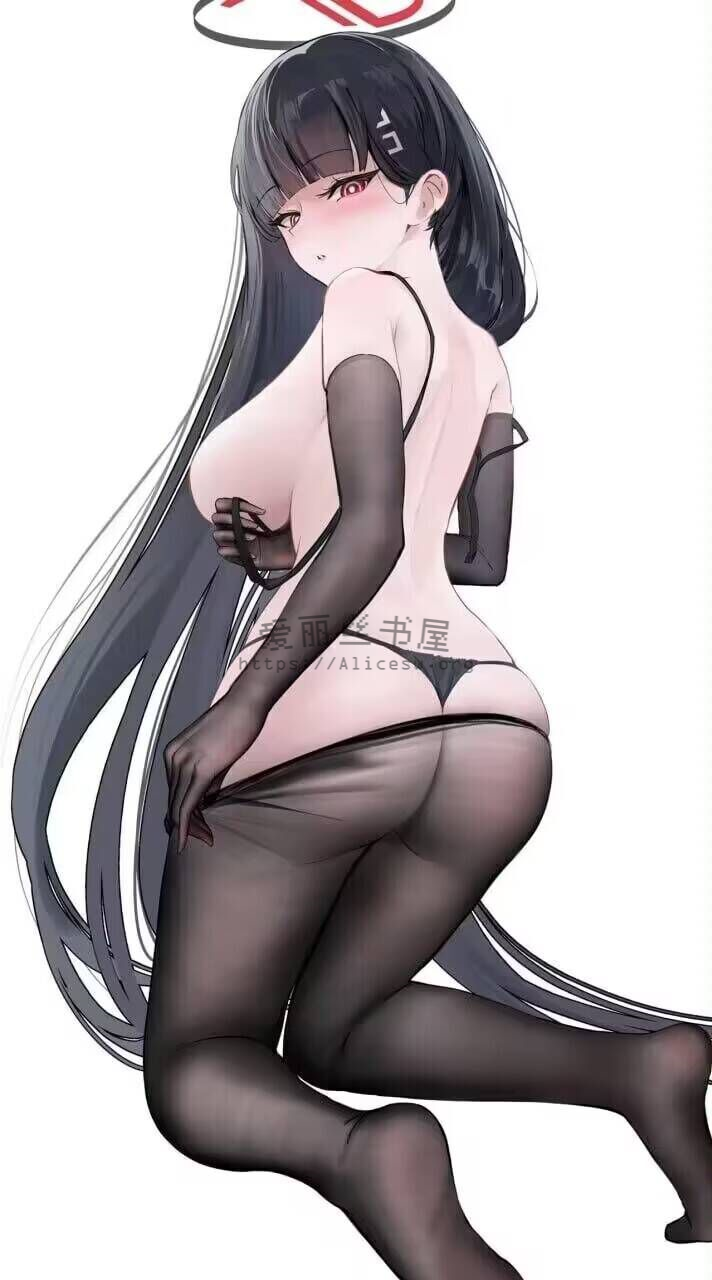張楚離開辦公室時已經七點多鍾了。
他出了機關大門改打的去鼓樓紅唇酒吧。
此時,距下班高峰期已過了一會兒時間,但馬路上的車子依然很亂很擠,行人自行車公交車出租車互相擠著空檔往前趕。
快到了雲南路十字路口時,紅燈亮了。
張楚坐在車子里不免有些著急,他要抓緊時間去見小許,還要抓緊時間趕回去跟詩茗在一起。
今天是詩茗回來的第一天,讓詩茗等久了,他心里過意不去。
他愛著詩茗。
這時候,他已經完全把陳女仕丟到一邊去了,心里只有詩茗小許。
他每次離開陳女仕幾乎都是這樣,他不知道為什麼。
陳女仕對他的態度幾乎挑不出一點不是,他覺得他的心態有問題。
或許陳女仕結婚了,是有了主的人,他只是她生活中的一支小插曲,而不是他生活中的小插曲。
詩茗是他的人,他是她的主人,他念著她是必然的。
那小許呢?
他想到這個時,有些茫然。
綠燈亮起來的時候,他剩的的士剛開到十字路口邊,紅燈又亮起來了,的士不得不停下來,等放行。
這時候,張楚注意到從左側衝過來一輛小跑車,騎車的小伙子一路飛奔。
當他衝到十字路口中央的時候,他與迎面交叉而過的一輛自行車撞在了一起。
騎自行車的是個女孩,當即倒在了地上,那個小伙子倒在她身上。
緊接著,有許多輛自行車在他們後面倒了下來,十字路口中央即時亂成了一團。
眼看綠燈又要亮了,倒下來的人匆忙爬起來推著車子趕路,但那個小伙子壓在那個女孩身上似乎爬不起來了。
女孩子躺在地上,裙子被掀開來了,大腿露在外面,叉著兩腿被那個小伙子壓在地上。
或許那個小伙子身上哪兒摔疼了,或許他有意不想起來,趁機在女孩子身上沾點便宜什麼的。
張楚突然想起有一年春天,麥子成熟的時候,他和幾個小伙伴到田野里去玩。
他們在麥地中間竄,突然,他們聽到前面有一串很重的喘息聲,時而還夾著“啊啊”的叫喚聲。
他們幾個人很小心地收住腳步聲往前面找。
很快,他們吃驚地看到前面麥地里,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全身赤裸著抱在一起,象老鼠挖地洞似的在動作著,四周的麥桔杆也跟著他們的動作在嘩嘩作響。
他們伏在那里看,一點都不敢出聲。
一會兒,那個男的從那個女的身上起來了,但女的還赤身裸體躺在地上沒有動,象是在享受某種酣暢。
突然,那個男的回過頭來對著他們大吼了一聲,看什麼!
他們幾個人嚇得趕緊逃走了。
他逃回來後,一夜都沒能睡得著。
因為他認識那個女的,也認識那個男的。
女的是他的五奶奶,男的是他的二叔。
他有很長時間遇到他二叔都不敢抬頭看他,他想,他二叔一定看到他了。
有時,他在心里想,他二叔跟他二娘在一起時一定也是這個樣子。
他甚至想,哪天去偷看他二叔跟他二娘在一起的樣子。
張楚還在這樣胡思亂想的時候,車子已經停在了紅唇酒吧門前。
他付錢下車後,就往酒吧里走。
酒吧里光线很暗,看不清里面坐的人。
他在場子里轉了兩圈,也沒有發現小許,正在猶豫時,忽然聽到小許在身後喊他。
他循聲望過去,在一個角落里看到了小許。
張楚走過去在小許身邊坐下來,剛想對小許說點什麼,突然發現,對面還坐著一個男的,此時,正瞪著一雙吃驚的眼神看著他。
張楚象是詢問似的看了看小許。
小許裝著有點醉了,眯著眼對張楚說,我給你介紹一下吧,這位是大作家林某某,他是來體驗生活的,為他的新小說《奶子奶子你飛吧》找素材。
小許說到這里,那男的立即微笑著對張楚點了一下頭,然後,把注意力又集中到小許的胸脯上,用眼光挖掘小許的胸部。
張楚看在眼里很不舒服,他抓過小許的手,對那位作家說,她是我老婆,你可以換個地方嗎?
那位作家聽張楚這麼說,就訕笑著站起來走了。
小許卻有些不滿意起來,對張楚說,你討厭,偏這個時候來,我正想看他怎麼在我身上得手。
瞧他色迷迷的樣子,還作家?
八成是才在錄像廳里看了一部肉暴的片子,到這里來把我當野雞套了。
張楚摟摟小許,說,他若真是作家,我倒同情他了。
你要理解,作家是被鎖縛在性飢餓與性壓抑柱子上的受難者。
一個作家,他的激情許多是由女人肉堆起來的。
越是好的作家,越是要在肉蒲團上打滾,象海明威、菲茨傑拉德、拜倫、歌德、雨果等等數不勝數的大作家,哪個身邊不是美女如雲。
這些女人,是支持作家寫作的動力。
作家的筆,其實是握在手上的陽具。
沒有激情的陽具,也就沒有了激情的文字。
很多作家最富抒情最富感人的文章,多是寫於年青的時候,因為那時陽具衝動力大,帶到文字上就有了力量。
性,是作家文字的靈魂,它能讓一個作家的筆硬挺住,否則,作家的筆在手上軟了,也就寫不出好文字了。
你怎麼這麼嘔心,全是陽具什麼的。
小許笑著打斷張楚的話,然後問張楚,你也來得太遲了,做什麼的?
下班後,在辦公室里給我愛人打了一個電話。
掛了愛人電話後,突然想起同學的事,立即給同學打去電話。
先是同學接的電話,然後同學的老婆接過電話,同學的老婆接過電話後,同學又接過電話,同學接過電話後,同學的老婆又接過電話……就這樣,來遲了。
你得了吧,沒人想知道你的隱私,是不是想把你同學的老婆也騙上床?
小許說完這話,招呼酒吧小姐過來,送兩杯紅酒上來。
張楚伸手捏了一下小許的大腿,說,你講這話,好象我上過什麼人似的。
小許說,不是好象,而是事實是。
酒吧小姐把酒送上來後,小許叫張楚坐到對面去。
張楚過去後,她把兩腿擱在張楚的大腿上,抵住張楚的下面,然後舉起杯子,跟張楚碰一下杯,抿一口酒。
小許放下杯子時,故意用勁蹬了一下張楚的陽具,說,你剛才胡說作家的筆是什麼陽具的,那女作家呢?
你這回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吧。
你想聽得明白?
張楚想逗小許,就趁機發揮說,作家寫作時,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性幻想。
這時候,他們手上的筆是陽具,稿紙是陰具。
但男作家與女作家在寫作時還有些區別。
男作家握的是自己的陽具,在別人的陰具上寫字;女作家握的是別人的陽具,在自己的陰具上寫字。
男作家們說,我日夜都伏在稿紙上寫字。
女作家們說,我不寫作就沒法生存。
實際上,他們在潛意識里都在間接地說一個“操”字,操別人和被別人操。
如果一個作家在寫著時,沒有投入這種性幻想寫著,他反而寫不出好小說。
一個作家性欲減退了或者性無能了,他們多半會沉浸在過去的一些回憶里或者對現實捕風捉影一下,寫些散文或者雜文,假如連散文和雜文都寫不出的話,他們只好讀點書寫點學問文章了。
你胡說起來真是有頭。
小許笑著說,然後用腳又蹬了一下張楚的陽具,叫張楚說點別的。
張楚想了一下,說,說什麼呢?
要不就說點與陽具有關的故事吧。
小許說,你別挑逗我就行,否則,你把我帶走。
張楚伸過手拍拍小許的臉,說,就說我上小學的故事吧。
我小時候,班上有個同學,他在課堂上沒事干,常抓住自己的小吊吊當玩具在課桌底下玩。
有一天,他不知道從哪里找來了一根火柴棒,把小吊子上的尿道口扒開來,把火柴棍往里揣。
小許聽到這里,伏在桌上笑得眼淚直滾,一邊叫張楚別說了,一邊用腳蹬張楚的陽具。
張楚等小許不笑了,繼續說,那同學把火柴棍往里面揣,還真把一根火柴棒給揣進去了,但小吊吊收縮後,火柴棍卻跑到里面去了,拿不出來了,疼得那個同學坐在凳子上直喊疼。
老師問他哪兒疼,他不敢說,後來越來越疼,疼得他眼淚都往下掉。
老師就追問他哪兒疼,讓他說出來,並且說疼狠了送他上醫院。
他被逼迫得沒辦法,只好說吊子疼。
老師當場就傻眼了。
因為老師是個女的,還沒結婚,是個大姑娘。
沒辦法,紅著臉硬著頭皮問他,怎麼疼的?
他說,我把火柴棒搞進去了。
結果班上學生全笑瘋了。
張楚說到這里,小許已笑得喊不能聽了。
張楚卻繼續說,後來那個女老師喊來一個男老師,費了好大的勁才幫那個學生把火柴棍從吊子里弄出來。
我晚上回到家,挺蹊蹺那個同學是怎麼把火柴棍弄進去的,自已躲進房間里,也拿來一根火柴棍往里面揣,卻怎麼也揣不進去,因為揣進一點點就疼。
我當時想,那學生挺勇敢的。
第二天上學一問,幾乎所有的男生回家都試過,根本揣不進去。
大家圍住那個男生,問他怎麼揣進去的,他就給大家示范,結果,火柴棒又掉進去了。
小許聽到這里,笑得滾到張楚這邊來,伏在張楚懷里大笑。
張楚攔腰摟住小許,手按在小許的胸前,捏小許的奶子。
小許很快就不動了,伏在張楚的懷里讓張楚捏她。
過了很長時間,小許抬頭問張楚,你哪天去我的宿舍?
張楚聽到小許問這話,心里一下子就有些緊張的感覺。
他想要了小許,可詩茗在他身邊,他抽不出身。
有時候,他還要陪陳女仕。
如果他現在再與小許在性上有交往,他一個人怎麼能對付得了她們三個人?
又怎麼能隱瞞得了她們而不讓她們知道?
這一刻,他突然想到,如果詩芸在身邊就好了,他就有堂堂正正的理由拒絕一個人而去見另一個人。
但現在,她們都認為他身邊沒有牽涉,他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守在她們任何一個人身邊。
他想到這里時,把小許更加緊緊的擁抱住,然後小著聲說,我哪天去再告訴你,現在先讓你多些日子睡不著覺,想想我。
說完了,吻了吻小許。
小許卻把兩只手伸在張楚的懷里,不按地在到處找一樣東西……
張楚回來時,已經近十二點鍾了,詩茗還賴在床上看電視等他。
她見張楚這麼晚才回來,心里有些生氣看也不看張楚一看,只顧自己看電視。
張楚走過去,坐到她身邊,想摟住她,詩茗卻抬手把張楚往旁邊推,不理他。
張楚再想抱住她時,她突然說,你陪人吃飯要吃得這麼晚?
我現在真後悔,上次你在青島打電話,給我抓住了,我就聽信了你,上了你的當。
你給我聽著,你以後別想在晚上出去,要不,你去買個拷機掛在身上,讓我隨時能拷你。
否則,我讓姐姐回來跟你吵。
張楚聽了,笑笑,上去摟住詩茗,說,你怎麼總是往壞處想我,我都是結了婚的人了,哪還有女孩子跟我泡,想泡的人也早泡到手了,就剩下工夫哄住她不讓她離開我。
詩茗聽了,上去揪住張楚的嘴,說,我可不跟你說著玩的,我若知道你在外面不好,我明天就嫁人,決不戀你。
我愛著你心里已經夠受的了,看著你跟姐姐的一切,晚上翻來覆去睡不著。
你自已說說,我今天才回來,你也不早點回來摟住人家看電視,讓我一個人在家里,心里想著都難受,你一點都不愛我。
張楚聽詩茗說這些話,心里不免有些慚愧,同時還有一絲隱隱疼痛的感覺。
他摟住詩茗,用手在詩茗的臉上摸摸,小聲問詩茗,你真的會離開我嗎?
詩茗聽了,很驚訝地抬起眼看著張楚,問張楚,你在外面真有女人了?
張楚說,不是,我真擔心那一天來到,我有時躺在床上想想就難過,你若離開我,我真的沒法接受。
我在很小的時候,就曾幻想過,我要築一個很高的房子,象一個城堡似的房子,里面住著我愛的女人,她生我的氣,想離開我都走不掉,我們就在城堡里曬太陽,在太陽下面做愛。
沒有煩惱,不會害怕失去什麼,甚至自己。
詩茗聽了,把張楚緊緊摟住,說,我真的不想離開你,我也常常想,姐姐知道了我們怎麼辦?
她總有一天會知道的,我就想,那一天越遲越好,等我們都老了,她知道了,她一定能夠原諒我們,說不定我們還能夠住在一起。
晚上,我們就能夠一起坐在床上看電視,或說些童年的話,或聽你講些故事,或聽你讀一本書,我們也可以一起去聽一場音樂會,一起看一場電影,那該多好。
我在家里的時候,每次看著小楚,心里就想要是我們也能夠生個自己的小孩就好了。
我這樣想的時候,就有些後悔,我應該在離婚之前懷上你的孩子,這樣誰都不會知道。
我愛你,如果這一天來得很快,姐姐不能原諒我,我們就不能再在一起了。
你要知道,我心里只有你,也擔心你。
在家里,姐姐說你表面上看上去挺開朗其實心里是挺脆弱的一個人,這一點我都不知道。
若姐姐知道了我們的事,我希望你不要對姐姐說謊,把一切對姐姐說了,把責任推給我,姐姐會原諒你的,她愛你。
等事情過去一段日子之後,她還會一如既往地愛你。
你心里要明白,切不要做出什麼,否則,你傷害了姐姐,也傷害了我,我們都愛你。
我想到這些時最擔心,不擔心別的,就擔心你。
詩茗的一席話,說得張楚臉上流滿了淚。
詩茗用手給張楚擦擦,說,你永遠象個長不大的小孩了,瞧你,我都快要流淚了。
張楚用勁摟了摟詩茗,說,《紅樓夢》我讀過幾遍,每次讀完了,好象就記得這麼一句,“渺渺茫茫兮,彼歸大荒”,人生一世,無論名譽金錢地位如何,終歸於虛無,什麼也沒有。
唯一真真切切的,是醒著的時候,懷里能摟著自己心愛的女人,就夠了。
我常對人說,若是把所有的男人都關在一間黑暗的屋子里,你問他們要什麼?
他們肯定都會說,要女人。
金錢,地位,事業,會統統地拋到一邊去。
因為在黑暗里,金錢,地位,事業都不會生光,而女人會生光。
詩茗聽到這里,用手抓住張楚的陽具,揉揉,說,就因為你心里想的跟別人不一樣,人家才擔心你在外面花心。
你心里女人第一,就象你生來只是個陽具必須要放到女人身體里才是自己似的。
第二天上班,處長一早就找張楚談話。
他先跟張楚聊了一些日常工作,然後對張楚說要張楚在思想上嚴格要求自己。
張楚有些詫異,不知道處長為什麼跟他談這些?
處長說了一大堆話後,才跟張楚說,最近局里要挑幾個人去參加省委組織的一個政治學習班,考慮到張楚還不是黨員,要張楚拿點表現出來,回去好好總結一下自己,三天後,送一份入黨申請書上來。
張楚出了處長辦公室門,心里想,局領導可能要提拔自己了,張楚一肚子正才歪才局里人事處是知道的,以前就有人傳出過這些話。
他出來後,先去陳女仕的辦公室,小許正好也在。
張楚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後,說,唉,真要了我的命,處長我要三天後,交一份入黨申請書上去。
小許聽了,立即說,這下糟了,黨的隊伍里又多了一名腐化墮落分子。
張楚立即說,應該說,腐化墮落隊伍里又少了一名骨干成員。
小許笑著說,誰跟你是一個隊伍的?
就你自己。
張楚也笑著說,我就不揭發了,反正誰誰的心里最清楚。
陳女仕接過話,說,寫入黨申請書就要了你的命?
處長還給你三天時間?
寫革命情書啊!
張楚說,我對黨了解還不夠透徹,怎麼寫?
小許說,寫保證書會吧,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首先要牢記,第一,一切行動聽妻指揮,乖乖聽話回家就會有糖吃。
陳女仕聽了,笑著打岔小許,說,你跟小張說話怎麼這麼流。
張楚接著小許的話往下說,第二,不許調戲良家婦女小許,勾搭上後立即帶她回家。
陳女仕聽了大笑起來,小許卻拿起桌子一本雜志走過去,在張楚的頭上狠拍了一下。
張楚說,我是真心向你討教,你卻拿話耍我,這叫活該。
張楚和小許鬧完了,就回自己的辦公室寫入黨申請書。
小許卻跟過來跟他繼續鬧,陳女仕也跟過來幫小許鬧張楚。
張楚說,你們讓我安靜一會兒,我馬上就能寫好,寫好了讓你們審查,看能不能通過?
一人入黨,全家光榮,你們都有份。
小許陳女仕聽了,都笑著上去揪捏張楚,然後到一邊跟小王聊,讓張楚寫。
張楚伏在桌上,三筆兩劃,就將一份入黨申請書寫好了。
寫好後,他交給小許看看。
小許拿到手上念道:
尊敬的黨支部:
我一直把參加中國共產黨當作自己的最高人生理想來追求,從小立下志願,要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黨的事業,為解放全人類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人民大眾奮斗一生,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事業奮斗一生。
請黨接受對我的考驗,並希望吸收我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申請人張楚
小許念完了,陳女仕說不通。
小許說,挺好的,讓人看了覺得這孩子從小就有黨性覺悟。
張楚不理會小許的話,問陳女仕哪兒不通。
陳女仕說,最起碼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寫上去吧。
張楚說,這倒是,哪象小許,比我還胡說,中午打牌讓她鑽桌子。
說著,從小許手上要過入黨申請書,說,還是要嚴肅認真一點,至少死了,撈個追悼會或者黨旗蓋一下什麼的,死得都比百姓光輝形象許多。
張楚說完這話,小許陳女仕立即大笑起來,一起笑罵張楚。
下午,他打電話約她同學的老婆來,由陳女仕帶著去見社會處的處長。
他同學的老婆去了一會兒就回來了,回來後跟張楚說,成了。
張楚讓她去謝陳女仕,陳女仕卻跑過來,對張楚說,你讓小揚謝我算哪門子,我是幫你的,你應該請我客,人家小揚是你同學的愛人,初次來,你也應該請一次客,心誠一點,今晚就請客。
小許也吵著過來,說張楚應該請客,只是張楚請客別拉下她。
張楚說,要請客還不是一句話,過兩天吧,我今晚還有事,跟記者約了,去同學家里打牌。
小許說,鬼才相信你。
下班後,張楚陪詩茗去新街口百貨商店買衣服。
這是他們昨天晚上約好的。
不巧的是,陳女仕這天下班後也去新街口百貨商店閒逛。
當她在新街口百貨商店門前看到張楚後,本想立即上去招呼一下,卻突然發現張楚身邊還有一位漂亮的女孩,她就悄悄地跟在後面,一路觀察張楚跟那個女孩的關系。
張楚和詩茗走在一起,手常常搭在詩茗的腰上,偶爾,還故意伸到詩茗的胸前,在詩茗的乳房上壓一下。
當陳女仕看清詩茗後,她想起詩茗是誰了。
詩芸生小孩住在醫院期間,她去醫院看望過詩芸,那天詩茗正好也在醫院,她見過詩茗。
她認出詩茗後,竟嫉恨起來。
她站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默默地望著張楚和詩茗兩個人的身影,一直在人流里消失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