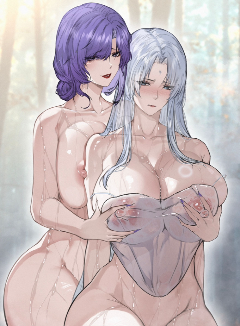青玉和媽剛吃完早餐,我沉悶地放下東西。
青玉向我使了一個眼色,我心領神會,煞有介事地說:“媽,綠玉姐家里來人接她回去了,所以,我也回來了。”
“哎喲,可憐啦,多好的一個孩子,萌根啊!還沒吃早飯吧,快先吃點東西,走了這麼遠的路了。”
我便和青玉來到了廚房,青玉瞪著我看了半晌,似乎要覺察我有什麼異樣。
我渾身發毛。
“是你叫我去的,別這樣看我,我長痱子呢。”
“沒良心的,還真陪她過夜呢。”
“你檢查,貨還在這里。”我摟著她,企圖又想讓她故伎重演。
“我沒轍了。你看怎麼辦?”
“我想咱們的事想了一整宿,想出了一個眉目。但民以食為先,草民得先吃早餐。”
她給我煎了一個蛋,盛了飯,我大口大口吃著。
“我得在咱寶寶出生之前,接你離開這里。媽跟我們一起走,一定。除此之外,別無良策。我現在必須先外出活動活動,哪怕外出打工也有一條生路。”
她看著我,嘴角一翹,大顆大顆地掉淚了。
我趕緊摸了她的手帕為她挹干,沒想到,那淚不由分說,像滴滴泉水,挹了又濕。
我便親她,她伏在我耳畔說:“你說好了。到時你不回來,你到太和井給我撈屍吧。”
我發下毒誓:“五個月不回家接你,死無葬身之地。”
青玉含著淚說:“你放心,我照看著俺們的親娘呢。”
“我們的親娘?”我一把摟緊了青玉,怎麼也不肯松手。
“你走才是正理。窩在家里,好好的一個人,消磨得不成樣子了。”青玉掙開了去,自己抹了淚,“專心讀你的書。家里有我呢。那人今早就去接滿翠了。”
“接她?”我吃驚不少。
“誰知我唱的是哪一曲?滿翠這昵子心高著呢,她不一定來;要是真個來了,這也好,索性和她道個別。”
我的心“咚”的一聲,好像裝了滿滿的一桶水斷了拉繩掉進了黑古隆冬的古井里。
“不,不必多此一舉了吧。我......我早走一晌,早一刻上學。”
青玉抿嘴聳著身子吃吃地笑:“不是躲,而是要向她攤牌。”
我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
挨到晌午,青玉抽身回了家,她家里一攤子事等著她料理。
我本想過去,但想著人言可畏。
算不定我提前回家,那事就鬧大了。
我一直僥幸著:只要還沒撕破臉皮,大家面子上還好過。
吃過午飯,我收拾齊整了;想著青玉過來了,是執手相看淚眼,還是強顏歡笑揮手告別?
眼看約定的時間到了,也沒見個人影。
我想跑過去看個究竟,但想到在她家,很容易顯山露水。
我陪著媽說話,媽沒有睡午覺的習慣,絮絮叨叨地說:“兒啊,這回回學堂,一心要撲在學習上,家里的事放上一放。媽好著呢,有你國慶哥、國慶嫂,還有我那好閨女滿翠,媽活得快樂哩。萌根啊,婚姻家庭百年修,往後你長了進,上了大學,做了大事業,一定不要忘了本。這生不報,來生報。萌根啊,能報答我們的恩情,這生決然要報答個明白。”
我心緒不寧:“媽,孩兒記著呢。”我想著,終是親人照看才放心。
滿翠來了,如何讓一個不相干的人照看媽!
青玉那麼聰明,但願她讓滿翠幫她操持家務事,她騰出身來一門心思照看娘。
我又看了看表,都兩點了,還不見青玉的影子,我有一種莫明其妙的不祥之感,似乎有什麼揪著我的心。
這個時候,我去她家行嗎?
心中有鬼能裝著坦蕩地問訊嗎?
她怎麼忘記了我要走的事了呢?
難道青玉出什麼事了?
媽看出了我的心思:“萌根,要不你過去道個別?”
“媽,不瞞你說,這正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要是我們臨時變卦。現在,我在你身邊,還無所謂。要是——”
“我看你這孩子,心眼怎麼變得針眼那麼細了呢?沒有的事。你到院里看看,總比悶在屋子里瞎琢磨強。”
“媽這話都是你教導孩兒的:遇事要多長個心眼。媽沒忘吧?”
“你這孩子,媽說的是正話,你卻用歪了。”
“媽我說的是正話。咱娘倆相依為命,這不是正話?咱娘倆的事,現在就是我的頭等大事。”
“好孩子,人要看長遠,俗語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你讀書才是長久之計,不讀好書,像你四叔,長得打虎的身子骨,找個媳婦都難。”
“四叔說山上的女人是老虎,他天生怕女人,所以才不找老婆的。我興許也是怕老婆管的。”
“聽他胡謅。嘴里沒幾句正經話。”
我和媽總有說不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