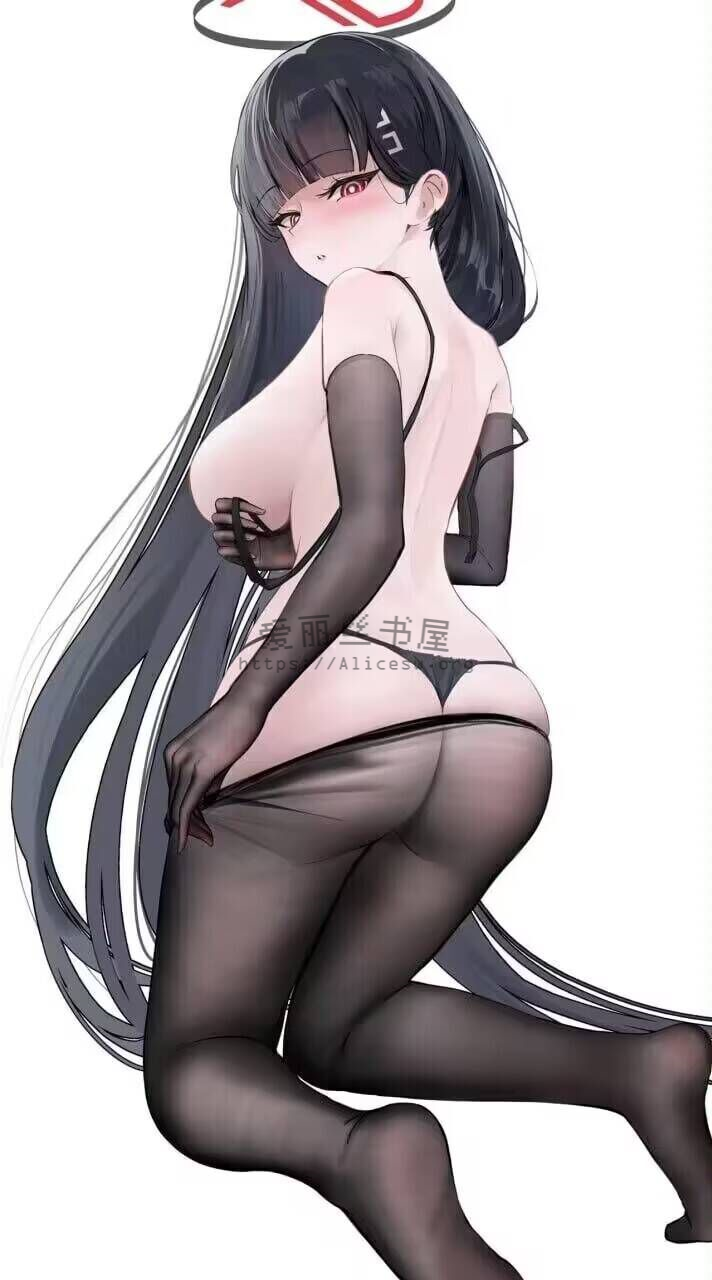我們兩個人盡管背地里對艷艷咬牙切齒,表面上卻服侍的很順從,很恭敬。
要在這個肮髒的地方立足,必須如此。
那次陪艷艷出差去殤市,因為說錯一句話,在街上就被她打的遍體鱗傷,要不是有好心人答應我留宿一夜,真不知道會成什麼樣。
可即使是這樣,次日我還得帶著傷回去找艷艷賠罪。
過了幾天,又遇到了一個很惡心的事。
那天我和沫沫每人只披了一件薄紗,跪在兩邊給艷艷揉腳,剛好有兩個丑男來訪,艷艷笑道:“你們兩位終於來了。准備好談判了麼?”
“不想談判了,我們只付兩千萬,一分不能多。”艷艷說道:“不用著急,你們遠來疲憊,先休息一下。小黃,沫沫,去套間服侍他們。”
這種事早已司空見慣,我滿不在乎的站起來,跟隨他們去套間,而沫沫卻驚愕的呆了好久,才勉強跟著走進來。
我完全不在意被那些丑男玩弄,但是沫沫那樣純潔軟弱,又那麼小,被他們騎在下面欺負就太可憐了,看到沫沫痛苦的哭泣,我心里砰砰直跳。
是我連累了這個女孩受了這些不該受的苦,內疚,慚愧。
三五分鍾後,兩個丑男的發泄結束了,又戀戀不舍的摸了我們半天才走。
沫沫一身汙物,撲在我懷里,放聲痛哭。
就這樣,我們一邊做女奴,一邊做客人的發泄工具。
每逢過節,還會帶一點禮物去拜訪“媽媽”賈青蓮,當然,我和沫沫在那里幾乎是身份最低下的客人,到了屋里就只有跪著,真是人見人欺。
有一次,沫沫給一位女委員叩頭時忘了親吻一下腳背,就被她在襠里狠狠的踢了幾十下,陰部受了很大的傷害。
不僅如此,賈青蓮還讓我們脫光衣服給人們跳舞助興。
我含著眼淚,忍辱做出種種丑態,沫沫實在無法承受這種羞恥和傷痛,沒跳完就昏了過去。
捱過了兩個月後,我們成為艷艷的親信婢女,金錢如同江河一樣流了進來。
而後,艷艷安排我們結交了易市最大的富豪之一,統轄兩個公司的布翼。
憑我的手段,很快就讓布翼著了迷,不久,我和沫沫以侍女的身份嫁入布家。
並且,我只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把關系已經很不好的布翼夫妻弄得徹底分裂,正式離婚。
我也成為正式的妻子。
…………
不願再回憶那段時光。
布翼不但欲望旺盛,還極端喜歡SM,比如針扎乳頭,比如鞭打陰部,一番虐待之後才行房。
我身體素質很好,一點都不怕受虐,我和他瘋狂的尋歡作樂,經常徹夜不眠,只是苦了沫沫,要做很多不想做的事,受很多難以承受的苦。
如我所料,天天過度交歡的布翼迅速瘦了下去,以至於虛弱的走路都打晃。
沫沫私下也會問我:“小姐,我們做的事是不是太過分了呢?再這樣下去,這個男人會死的。”我冷笑道:“就是要他死。”沫沫弱弱的說道:“小姐,我很害怕。”
“你忘了我們受過多少欺侮嗎?只有這樣才可以得到權勢,然後報仇。”沫沫默然無語,只是跪在我腳前,低頭在我腳尖上吻了一口,表示聽從。
布翼在病中仍然痴迷於和我追歡取樂,病情迅速惡化,最後終於無可救藥。
他死以後,我作為妻子拿到了足夠的遺產。
而後如法炮制,一年的時間又折騰死了一個年紀大的富豪,使得資產再次膨脹。
完成了金錢的積累,我雄心勃勃,收斂住放蕩的作風,開始大肆用錢開路,重新回到政界。
我明顯的感覺到,自己的心靈越來越黑暗,所幸有善良的沫沫不離左右,宛如明月一樣照亮著我,如同最後一片淨土。
我的權勢如同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終於橫霸易市。
不過讓我有點著急的是,沫沫病了,雖不嚴重,卻總好不了,醫藥費上萬都沒有治愈。
很大程度上,她的病是因為遭到太多的虐打,嬌小的身體難以承受。
這天,我推掉繁忙的事務,親自捧著藥在床前服侍沫沫,弄得沫沫很不好意思:“奴婢一點小病,怎麼能讓主人這樣費心呢。”
我微笑著吹吹湯藥,剛要安慰幾句,有人來通報:“黃主任,您要見的那對教授夫妻,我們已經找來了。”聽到這話,我頓時眼里冒火,暴戾的心情掩蓋了一切。
在冷清清的密室里,教授夫婦自覺的跪下見我。
我坐在中間的椅子上,說道:“你們兩位還認識我麼?”
教授抖成一團,伏地無語,夫人斗膽說道:“紫凰,對不起,那次都是我不好,我有眼無珠,求求你饒了我們吧。”
“住口!那天晚上我被你打的滿身都是傷,差點死在街上,那一幕,我至今還歷歷在目,像昨天才發生一樣。”夫人嚇得低下頭,自己抽自己嘴巴。
我冷笑一聲,抬起腿說道:“給我脫鞋。”
“是是是。”我今天特意穿了白色高跟鞋和白色絲襪,與那天她穿的一模一樣。
也許她也明白這個意思,嚇得哆哆嗦嗦,脫下的鞋子一不小心還掉在地上。
我狠狠踢了她幾腳:“脫襪子!”
“是……”脫下這雙髒絲襪,我抓過來揉成一團,塞進她的嘴里:“好了,你也嘗嘗這個滋味吧。去喝水。”她可憐巴巴的磕了個頭,從旁邊捧起一杯水,硬著頭皮喝了下去。
水滲透的很慢,好久才流下去。
我凶惡的把她踢倒在地,剝光衣服用繩子捆了,第一次復仇正式開始。
教授夫人被我用鞭子打的滿地亂滾,青紫色的鞭痕逐漸布滿全身,哀嚎聲被絲襪堵住,悶聲悶氣。
直打了一個多小時,我手臂都酸麻無力了才停下來。
看著她痛楚難當,扭來扭去的樣子,我感到很開心。
隨後,又回頭對教授陰冷的笑道:“先不說你是怎麼玩弄我的。我挨打時你為什麼一句話都不敢說?眼看我半死不活,你很開心麼?”
教授驚恐的磕頭不止:“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我穿好鞋子,一腳把他踢到一邊,步出密室。
手下人快步走來說道:“覃市長嫌送的錢少,不給辦事。另外,無常市夢輝集團被查抄的消息已經證實。”
“知道了。再加二十萬給那個老豬狗送過去。還有,給剛才那兩個人羅織個罪名,讓那個男的去坐牢,女的去做奴隸。”
“是。”我離開這里,帶著一層層心事,緩步回到臥室。
沒想到沫沫已經下了床,穿著粉色拖鞋走過來,捧著一杯茶說道:“小姐,終於回來了,請喝一杯茶吧。”
我忙接過來說道:“你病著呢,不要下地,我自己來就行。”說著,坐在床邊,抿了一口茶,試圖整理一下混亂的心緒。
沫沫坐在我旁邊,說道:“小姐臉色不好看啊,一定是又遇到不順心的事了吧?可惜奴婢什麼也做不了,都不知道怎麼解勸。只有好好服侍你,多多端茶送水了。小姐,想開一點,我們受了這麼多苦難,還能被什麼難倒呢?大不了扔下功名,買個小房子清清靜靜生活去,沫沫悉心伺候,一起度過青春吧。”不知道為什麼,我聽完後忽然覺得一陣酸痛,止不住眼淚嘩嘩的流了出來,沫沫剛要拿手絹給我拭淚,就被我一把抱住,哭道:“沫沫,我只有你,我只有你……”
此後,凡是曾經欺凌我的人,從市里的豪商,到省里的顯官,一個接一個被我踩在腳下。
我為了報復,特意開了一個周末派對,每周日的下午把那些上層人物召來,任意羞辱。
漸漸的,以易市為中心輻射出去,千里之內的達官貴人都被籠罩在內。
周末的聚會越來越盛大。
次年夏天,我利用好幾股勢力的衝突,終於使商務部的賈青蓮完全失勢。
就在周末,她和自己剛滿十九歲的女兒被帶到虐待派對,當著幾十個人的面,兩個人跪在門口,頓首參拜,一直爬進來。
我扶著帶病的沫沫一起坐在正中,笑道:“好久不見了,媽媽。”嚇得她慌忙撲到我腳下,帶著哭腔說道:“千萬不要這麼說,求求您原諒我吧……”
我伸腳踩了踩她長長的頭發,說道:“原諒你?還記得那時我是怎麼受你欺負的嗎?”
賈青蓮拼命親吻我的鞋子:“奴婢錯了奴婢錯了,求主人恕罪。”
“說你是老賤人。”
“我是老賤人。”我滿意的點點頭,又抬腿說道:“來,我的腳熱了,給我揉揉吧。”
“是。”賈青蓮迫不及待的抱起我的腿。
我的腿不但白皙、修長,而且非常健美,這是我最引以為傲的身體部分。
她恭敬的把一條腿架在自己肩上,另一條腿捧到眼前,用舌頭給我揉腳。
面對我的淫威,她是百般順從,一點反抗都沒有,半透明的白色短絲襪很快就濕透了,揉腳結束後,她還乖乖的伏在我腳下說道:“奴婢再也不敢冒犯您了,請您原諒奴婢。”
我用腳尖擦擦她的臉,說道:“好啊,要讓我原諒你,就不能做你的女兒了吧?”
賈青蓮急忙把頭埋在我兩腳之間,悔恨的說道:“當然,當然。您是我的姐姐,不,是我媽媽,好嗎?讓我給主人做女兒吧。”
“這還差不多。”
“謝謝媽媽……”
“好,乖女兒,帶著你女兒脫光衣服,給我們跳舞助興啊。”
“是。”她倆早已拋棄羞恥,毫不猶豫的跳起了舞。
臉色蒼白的沫沫靠在我懷里,哭著說道:“小姐,我們報仇了……”
就在我的事業蒸蒸日上的時候,沫沫的病卻越來越重。
我不惜動用所有的錢給她治病,但始終不見起色,眼睜睜的看著病情一天比一天嚴重,到這年秋天,她已經很難動彈了。
我坐在床邊,沉痛的說道:“沫沫,如果沒有那大半年的受虐,你的身體一定不會變成這樣。是我害了你……”
沫沫笑道:“能陪小姐這麼久,我不後悔。”
“我很後悔。早知如此,還不如早點退出這個黑暗的圈子,我們安靜的過日子。”
沫沫睜大眼睛,高興的說道:“我知道活著的日子不多了,小姐,能安靜陪奴婢呆幾天嗎?”
我含著眼淚點點頭:“好,好的。”
在這幾天,我推掉一切重要事務,專心在鄉間別墅陪著沫沫,以送她走完最後一段路程。
在這里,我給沫沫唱歌,跳舞,講故事,盡一切努力哄她開心。
而且我不停的給她拍照,或者合影,積累了很多相片。
那天晚上,本來氣息孱弱的沫沫忽然精神煥發,神采奕奕,對我說道:“小姐,我死了以後,你會想我嗎?”
“會啊,不,你不會死的……”沫沫一笑,又問道:“人死了以後,也許真的還會有靈魂吧?”我使勁點點頭:“恩恩,我也這麼想。”
“真好,我的靈魂還會呆在小姐身旁的。”
“沫沫……”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沫沫伸手脫下我的襪子,吻了一口,說道:“小姐,我聽你說,你家里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妹妹,好多年沒見了。離開家的這些年,都是我在陪你,就讓我高攀一下,做你的妹妹吧。”
“好,好啊,我求之不得呢。”沫沫嫣然一笑,又摘下脖子上掛的水晶吊墜,說道:“這是媽媽留下的,我一生唯獨這件東西從不離身。送給姐姐吧。將來,我會永遠守護在這個吊墜上。”
那天晚上,沫沫永遠的閉上了眼睛。
我控制不住自己,傷心欲絕的哭了好幾天。
數日後的周末,我在派對上一反常態,露出前所未有的猙獰面孔,把好幾個欺侮過我們的,特別是欺侮過沫沫的男人打成傷殘,亡夫布翼的妹妹也被我弄到家來,作為紅襪侍女,經常受虐。
這年冬天當我名下公司成立時,我毫不猶豫的命名為“憶沫”。
很荒唐,很混亂,也許這只是一個夢,也許沫沫只是夢中的過客,但她已經隨著吊墜一起附在我身上,永遠不會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