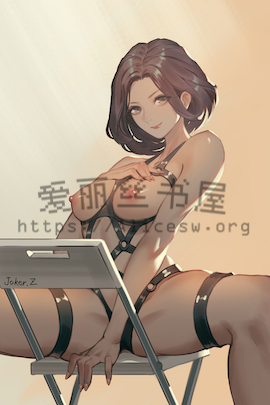人一旦有了固定的行程安排,日子似乎便會過得快起來。
整個十月,顧雙習都按照課表,輾轉於藝術學院的各個教室之間。除去不住在學校宿舍外,她的生活與普通大學生並無差異。
安琳琅和法蓮並不總是陪在她身邊,往往只會有一人跟著她來學校,這人通常是法蓮。
安琳琅早就大學畢業,重讀本科於她而言沒什麼意義。何況她更多負責照顧小姐的飲食起居,就算每天陪顧雙習去上學,放學回來後也多得是待做的家務活兒。
盡管大學課表時間安排靈活寬松,但琳琅每天學校府邸兩頭忙,文闌亦認為她辛苦,因此有意多留她在府邸中,只打一份工。
至於法蓮。文闌也不全信任她,只是看出顧雙習器重她,而法蓮表現也一貫不錯,言行舉止挑不出刺,文管家也就隨小姐心意,讓法蓮陪她去學校。
況且大學里人多眼雜,門禁管理嚴格,邊察也不欲暴露顧雙習的真實身份,如此文管家便不好安排保鏢跟著小姐;法蓮正好身手不錯,能夠保護好顧雙習,文闌越想越覺得滿意,這樣一來似乎所有人都皆大歡喜。
陸春熙也只在最初的一周,勤勤懇懇地當著顧雙習的小跟班。她帶著顧雙習將課表全部過了一遍,告訴她如何找教室、如何占座位,又領她去圖書館,告訴她如何預約座位、如何落座簽到:謝天謝地,顧雙習的手機可以打開圖書館在线預約小程序!
總之,在這一周里,陸春熙教會了顧雙習,身為一名大學生,應當知道的某些小技巧。等到第二周,她試探顧雙習是否還需要她的陪伴,得來小姐爽快的應承:“不用啦,我先自己試試看吧。”
顧雙習眨眨眼:“實在遇到困難,我發信息問你嘛。”
事實上,顧雙習從未給陸春熙發過提問信息。但陸春熙仍不敢放心,又緊密關注了她一周,確認她和法蓮確實已同普通大學生無甚差異,便悄悄放下心來。
她邀請顧雙習去參加社團活動,也邀請她去聽專家講座、看露天電影,當真把“大學生”這一身份體驗得面面俱到,連學生會團建都想辦法拉上顧雙習一起。當然不敢勸她喝酒,飯後的KTV環節也略過了顧雙習,陸春熙先打電話給文管家,請他派輛車來飯店門口接顧雙習回家。
陸春熙先陪著顧雙習在飯店一樓大堂里坐著,等到司機路叔的電話打進陸春熙手機、告知他已經抵達飯店門口,她們方才走出大門。
十月中下旬,天氣轉涼,樹葉開始自枝頭剝落,被風卷裹著掃倒在地。顧雙習席間喝了點兒熱飲,面上泛起溫暖的酡紅,腦袋像一顆漂亮的苹果。她微笑著和陸春熙道別,便和法蓮一起坐進了車里。
法蓮坐副駕,顧雙習坐後座。她背靠靠背,正在閉目養神,裝在側邊口袋里的手機忽而發出一陣震動,提醒著她來電。
顧雙習不想接,沉默地任由它動作,手機震了一分鍾,便也停了。隨後車廂里響起了路叔的手機鈴聲。路叔接通了電話,免提設置使得叁人都聽見,音響里傳出邊察的聲音:“雙習。”
“……”她覺得頭疼,以及疲憊,“您先把電話掛了吧,我用自己的手機給您打視訊。”
她摸出手機,看了眼消息提醒。剛才聚餐時席間太熱鬧,她又給手機設置了免打擾,因此完全沒注意到,邊察給她打了幾十個電話。
換了以前,邊察電話肯定早就打到陸春熙手機上,進而逼迫顧雙習接他電話。如今他能忍到她結束聚餐再來發難,似乎也算有所進步。
……但還是太惡心、太壓抑了。明明沒什麼要緊的事,有必要一連打幾十個電話嗎?
顧雙習把視訊撥過去,對面很快接起。
車輛正行駛在一條城外環路上,道路兩側路燈光线昏暗,一寸一寸地飛快地從車窗上掠過,只短暫照亮顧雙習一瞬,隨後她的臉龐又湮滅在昏暗當中。邊察說:“讓路叔打開車內燈。”
“沒必要,快到家了。”她說,“我們先這樣說說話吧?就像以前我們躺在床上時,就著床頭燈的光线,抱在一起說說話。”
盡管心情頗為煩躁,但嘴上哄起邊察時,顧雙習還是相當得心應手。她總能精准掐中邊察的命脈,把他的反骨與逆鱗一點點地安撫平整。
他明顯生氣,但下意識跟著她的話走,沒再提開燈的事,轉而陰陽怪氣:“看來雙習和同學們相處得很好,都能一起出去聚餐了。他們沒有勸你喝酒吧?”
顧雙習扶額,指尖緩慢地按摩著太陽穴:“沒有。陸春熙攔著呢。”口吻猛地一沉,期期艾艾地問道,“您……是不是不喜歡我和他們出去聚餐?那我以後……”
她把這招“以退為進”使得爐火純青,叁言兩語便勾起邊察的愧疚心,譴責自己逼她太過,連忙表態:“你能和同學們和諧相處,我很開心。……只是你總是不接電話,讓我很擔心。”
“對不起,不知道怎麼回事,手機被調成了靜音模式,聽不到電話提醒鈴聲。”顧雙習說,“我太笨了,玩不明白手機,老是弄出問題。”
她有意貶低自己,因為她知道邊察最聽不得她自輕自賤,會立刻做出回應:“說什麼呢,這不算什麼大事,回家讓安琳琅給你看看,教教你怎麼設置。下次不要再調成靜音了,我很怕找不到你。”
……這實在是,很無聊、很無趣。
車廂里光线不好,她不必粉飾表情,嘴上隨意敷衍著邊察,眼神卻游移向窗外。
一道護欄以外,便是向天際线蔓延而去的海。夜色之下,大海靜謐而又沉寂,只有月亮緊貼近海平线,散發出盈盈一圈輝光。他們正沿著海岸公路飛馳,這條道路的盡頭即為南海灣。
即便邊察同意送她去上學,那也只是把她的活動范圍擴大到了帝國大學。
就像是一款城建玩具,其中那個名為“顧雙習”的小人,每天只能在創世神(邊察)的安排下,沿著既定軌道,往返於南海灣的皇帝府邸與東城區的帝國大學之間,絕無偏離路线、甚至逾越鐵軌的可能。
或許人的天性便是欲壑難填,得隴又望蜀。此前被圈禁在府邸中時,顧雙習雖也覺得壓抑,但每天看看書、寫寫字,生活似乎也照樣過;可現如今能出門上學後,她又遠遠不滿足於僅僅只是“上學”。
她渴望和同齡人交朋友,一起逛街、看電影,一起散步、打游戲,同住在一間宿舍,結伴穿行於校園中。她們可以盡情談論感興趣的話題,從娛樂八卦到心動對象;她們可以相約一起去圖書館、去食堂,抱怨搶座的困難,笑罵食堂的擁擠……這些尋常人眼中再瑣碎不過的日常,於顧雙習而言,卻是一個又一個的幻想泡泡。
只要有邊察在、只要她仍置於邊察的控制之下,她便永遠都不可能過上普通人的生活。
顧雙習深呼吸,不經意間發出細微一聲“嘶”。
邊察似想追問她“怎麼了”,她先一步打斷他:“到家了,我下車。”
顧雙習下了車,一面舉著手機,一面往府邸門廊走去。
門廊處點著一盞暖黃色的燈,邊察在屏幕里看到她的臉龐被溫柔地照亮,黑發柔順地垂落在肩頭,雙眸稍稍下撇,睫毛在臥蠶處暈出淡淡一弧陰影,顯得分外可親。
他們在一起時,他總愛親吻她的眼睫,因為覺得她的五官之中,眼睛生得最美。
半個月不見她,身體與大腦一樣思念她。一想到顧雙習,緊跟著便會喚起與她有關的綺念和臆想,以及他們曾共度過的無數個夜晚。
她皮膚既薄且白,他只需輕輕一捏,就能在她身上留下深深淺淺的印記;她唇瓣既嫩又軟,總被他親得紅腫破皮,他再用舌尖輕舔,她就會瑟縮著避開他。
更遑論床笫間意亂情迷,她被他扣在身下重重深入,龜頭撞上宮口的那一瞬間,她仰起下巴、伸直脖頸,就這樣將她最脆弱的頸部暴露在他面前。像不知道他低頭一咬,牙齒便能割破她的皮膚與動脈血管,令她血濺當場。
他因此總喜歡騰空出一只手,捧在她的頸側,以指腹、以掌心,親昵感觸她的脈搏、她的體溫。然後邊察俯首吻她,另一只手壓向她的大腿,迫使她將腿張得更開、方便他把陽具全擠進她的身體里,一分一厘都不願浪費。
邊察不自覺地發出一聲喘息,下身已因這些回憶而起了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