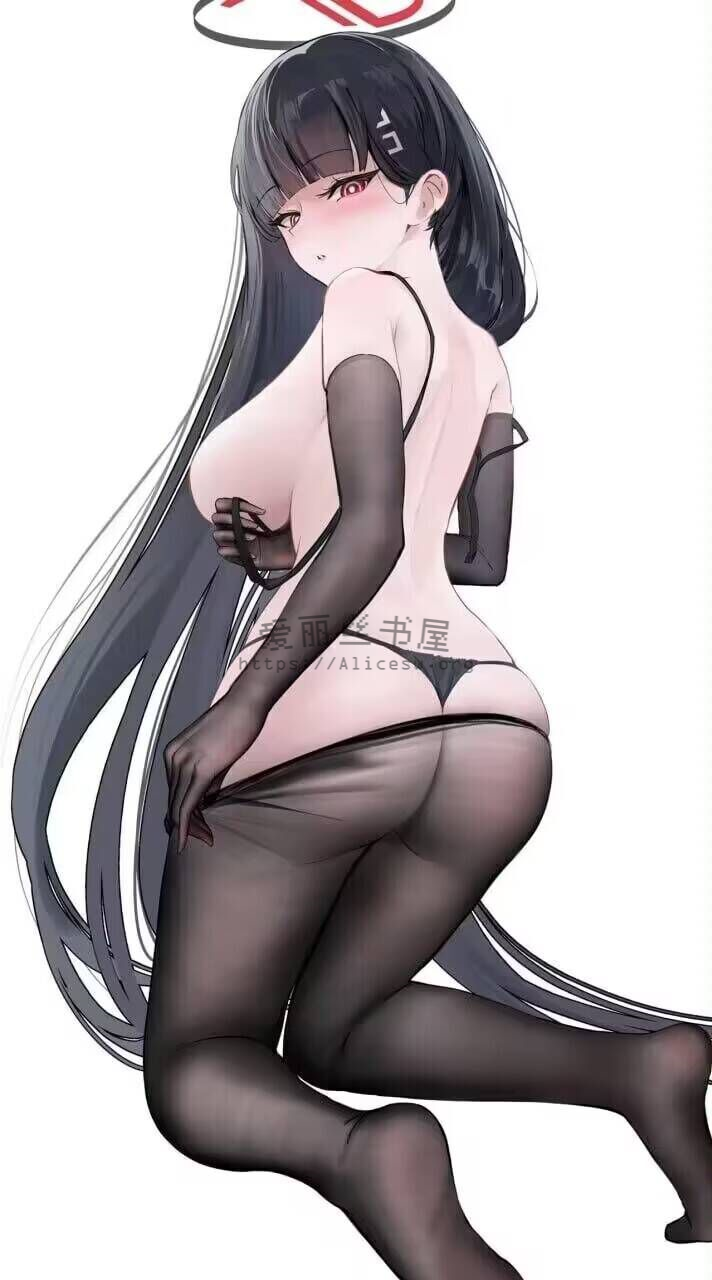第7章 【R-18】KAN-SEN的一千零一夜(?):光輝篇
[chapter:光輝篇]
鏡州市,歐洲大酒店。
貝X銘督造的主體建築與附屬的三個花園,使得東江省播放天氣預報,都會拿這里風景如畫的景觀做開幕背景圖。
…當小光輝此刻剛剛結束嘴巴的活塞運動,最後吐出張國昌那根久經風霜的雞巴;
她的母親,光輝,不情不願地走進了這家酒店的一間總統套房。
“哦,是你啊,我一直都想看看你了。”
南方來的客商高英祥,在光輝工作單位舉辦的一次洽談會上,見到了現在他急於搞到手的女人。他知道,她已婚,她有孩子;不用花錢(別人家老公養),不用教性愛(已婚),爽。
鑒於不太可能直接去找她——那樣有損高英祥這樣堂堂體面的成功人士的面子——他借著一次談生意的機會,設法見到了光輝丈夫的領導。
“高老板,請您…能不能給我一個機會,讓我離開這里?”
光輝完全是不情願來的。然而,有錢能使鬼推磨,高英祥拿著一個“過橋協議”跟光輝丈夫的單位漫天要價,後者隱隱有點吃不消。
實際上,這是一次典型的掏空“戰役”:高英祥貸款給光輝丈夫單位最近投資的一個項目,如果項目不能經營好,虧損了,那麼…
實際上,這是他與那邊一位高管私下君子協議的產物:這個項目壓根沒有可行性。
如果虧損了,很好,建設的全部固定資產與項目殘存的流動資金都要以零(無償)的形式轉給高英祥,並且以債轉股的形式,讓高入股這家非上市的准國營企業;
與省城高官有點交情的他拿到錢,自然會設法幫那位高管一個很重要的忙,因為他的大哥正在省城運動關系,想要從縣長提干成常務副市長,接手一個到年齡退休的崗位。
怎麼說呢,如果那位高管親自上陣去操作,明顯是授人以柄。
高英祥呢,正好這會要把這個項目名下的土地盤下來搞房地產開發。兩者經過熟悉的中間人環節,一來二去,搭上了线。
——當然,這麼多天花亂墜的玩意,不僅光輝,連她的丈夫都未必曉得怎麼回事。
不過不要緊。因為她,高英祥通過那個合作的高管(互贈小把柄,增強大互信),軟硬兼施,借著這個“協議”墨跡未干之際,逼著光輝丈夫的領導派那個可憐的男人出差,“進泥坑”。
光輝是知道這些的。這是高英祥刻意以暗示的形式,通過那個光輝高中的學長(光輝丈夫的領導),傳話給光輝的:
只要你上我的床,把我伺候舒服了,你老公隨時都能回來。不然,你自己掂量吧。
高英祥是做政治投機生意起家的。他的房地產業務與工廠生產業務,幾乎無一不是建立在觀測政治風向、預測政策脈絡、打入決策層內部等常用手段起來的。
要個區區人妻,又有何難?曹操想上了杜氏,她老公秦宜祿不就被姓曹的干死了?
別這麼緊張,光輝,你呢,我是知道的。你有一個女兒,你有一個妹妹,對,兩個妹妹,還有一個妹妹失蹤了。你放心,我會幫你找的…”
才怪。先把這個緊張的人妻搞到床上,抽插射精再說。好像還有個小的?好啊。
高英祥特意在“女兒”與“妹妹”上重讀。光輝害怕了。她,停住了往大門後退的腳步。
“這就對了。你得知道,這個歐洲大酒店不是我的。不過,這家酒店的老板,我沒少關照。你敢從這兒往外跑,豎著進來,橫著出去…對不起,一點玩笑話。”
她肯定不知道,前些年發生的“省議員兩人滅門案”,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省議會“作死”,嚴重地“阻礙東江省經濟進一步快速增長”。
老婆孩子被粗鐵絲捆綁,活活燒死,化為焦炭;幾個嬰兒從屁眼到天靈蓋,一根根拇指粗的鋼筋貫穿他們。
至於兩個當事人,一個身上被打地遍地淤青,脖子割喉放血死的;一個心口捅了估計不下十六刀,再被一刀劈斷正臉死的。
她要是知道這些,從一開始,就不該往門口挪。
“求求你…放過我老公吧!還有我的孩子,我的妹妹,他們都是無辜的!”
光輝作為一介女流,面對權力帶來的威壓束手無策,只好以頭搶地,跪地求饒。
不待她把女人天生的武器(眼淚)用完,知道這個人妻肯定聽話的高英祥,趕忙把她從鋪著克什米爾紫色羔羊皮毯的地上拉起來。
“聽說,你挺喜歡光明的?以前上學,記得還寫過什麼《光明的力量》?”
連那個時候出在校報的消息都知道了…光輝心下,頓時六神無主。
來俊臣在《羅織經》里面早就說過:對不通文化的匹夫,講話也是愣頭青,不如用嚴刑拷打;對通文化而有很多顧慮的文人,要用利誘威逼,勸他們自己招認。
“來,我給你還帶了一套當時的衣服…當然,按你現在的身材做的。”
她終於哭了出來。“求求您,別這樣。我不想背叛我老公。讓我做別的好不好?”
這個答案,不是高英祥想要的。他站起身來,一個巴掌,打得光輝花容破碎,整個人摔在地上,咕咚一聲。
“你都送上門來了,還跟我講價錢?反了你了。”
她無法,只好當著他的面,把衣服換上。看著光輝換衣服時羞澀的神態、一對渾然天成的大乳房、雪白的肌膚,他有了一點征服者的快感。
煲湯要的是耐心。該放的調料早就放了。不給一點時間,讓調料充分入味,把肉煮爛,充分作用,那麼,想要的香味是出不來的。他有耐心。
他已經可以確信,從光輝躲躲閃閃的眼神中,她是依舊不願意這樣委身於人的。
召之即來,呼之即去,那是滿大街到處都有的洗頭妹與女大學生——援交與包養的那部分。
終於,在高英祥熱烈的視奸下,光輝滿頭大汗穿上了這身行頭:
雪白的大遮陽帽,雪白的連衣裙,雪白的女鞋,被菱形發飾分開的兩簇馬尾。
還有,藏在帽子,已經悟出汗的發髻。
出於光輝的意料,高英祥沒有馬上要操她的意思。他指了指酒店桌上的吃食。
“你看看。我為你准備的這頓晚飯,不錯吧?XO燒菲力牛排,香檳烤牛舌…對了,這是我特意吩咐人燒的,一對烤牛鞭,你聞聞,孜然、八角這些佐料是徹底入了味了。”
他不顧光輝的驚訝,風卷殘雲,吃掉了那兩根牛鞭。
“別的我都可以放一邊,現在,我的任務是操你。操完一會,再吃,補精,接著操。怎麼樣,我這可夠給你面子了。”
光輝丈夫出差的那個項目是個盡人皆知的呆賬。誰去都沒有用。
如果真的就在他在的時候出了事,他難辭其咎。誰管事,誰負責。
“…請您過來吧。”
光輝不知道,她為了挽救要被清算的丈夫,躺到床上,掰開大腿的動作,是高的“釣魚”。
他這種地位的男人,下海以前也是堂堂的財務科科長,哪會拉下臉求個女人?
他是熟悉的,錢嘛,當有實權的官都是主動送到他們手里、不用他們催要的。女人,也一樣。
光輝不是大路貨,不是人見人操的婊子。這不代表他滿意之余,會有讓步。
“你自己說說,你現在想要做什麼啊?提示一下,給你十秒鍾。“
高英祥煞有其事地數秒。光輝不甘心,自己只有老公能碰的身軀,就這樣染上他人暴力的精子…
當他數到“九“,天人交戰的光輝終於”顧全大局“,悄悄地說”我求求你,上了我“…
可惜,高沒有玩夠。他借口“聲音太小,聽不到“,斷然數到了”十“。
“唉,可惜啊,明明覺得你是個明事理的女人,沒想到,長得漂亮,腦子還是不靈光。好吧,我也不勉強你,這幾道菜我讓人給你打包回家,這身行頭算我送你的了。“
高英祥作趕人走的姿態。正當他拿起酒店座機准備撥號,光輝不再猶豫,跪倒他的腳邊,發瘋一樣搖著他的腿。
“求求你…隨便怎麼樣都行。操我也行,把我怎麼樣都行。不要傷害我的家人,我求求你…“
他故作難色。現在,還是沒有玩夠。
權力尋租帶來的好處,是現在的狐假虎威。僅僅假借的虎威,他可以不用明說,“自己體會“,讓這個平素溫順大方的賢妻良母,變成自己胯下跪求強奸的女性奴。
要不怎麼那麼多人擠破頭都要報考公務員考試?不發財,不蹂躪別人,這官,當著不如去死。
“這樣吧,你自己得讓我明白,你想干什麼。我呢,不強求。啊,說好了,不強求。”
他別過頭去,放下電話,望著高層窗外如血管車水馬龍的大街。杯中,重新倒了一杯干邑。
光輝絕望了。她為了要保護家人,只好自己脫掉內褲,屁股朝天,兩條腿分別被兩只手套住。
這是平時,她只給丈夫操的體位…
“求求你,快點操我吧。”
游絲如蚊呐。聽者已有心。他突然想到了一個好主意。
“來,寶貝,把嘴張開。”只見他脫下褲子,趕快騎到光輝的頭上,把雞巴套弄進她的嘴里。
一股熱流涌出,騷臭味打掉了光輝此時殘存的理智。她沒敢多想,等尿完,吞盡。
“很好,看來寶貝,接下來的菜你我有機會一起共享了。”
他沒有廢話,調整身姿,對著光輝的下體,一次,貫穿。
光輝仿佛是突然想到了什麼,驚慌失措地叫喊著。
“不行了…要來月經了…高老板,求求你,等一會…”
好容易到了這一步,高英祥怎會善罷甘休。他依舊打樁。光輝雪白的臀肉,打出了一陣陣清脆的波浪。
與服裝肌膚的雪白相對應的,是接下來,光輝下體涌出的血流。
她疼的已經支撐不住不屬於自己的下體,雙手如難產抓著枕頭。高英祥不管不顧,雞巴頂著暖暖的血流,瘋狂突刺著。
“你瞧,吃哪兒補哪兒。我剛吃了一對牛鞭。好嘛,干你的時候,可有勁了。”
光輝不顧他的嘲諷。她現在滿腦子,只剩下疼痛。氣抽抽,抽抽氣。她說不出任何哪怕是錯別字的話語來。汗珠與經血,還有愛液與他的汗水,一起打濕著波瀾萬丈的床單。
她的裙擺,早已成了滿江紅。星星點點的枸杞雪梅,哪里能形容此刻紅潮的洶涌。
“我會死的…求求你,讓我休息一下…我真的會死的…”
高英祥不管這些。他的雞巴,呼喚著與卵子的交合;他的血液,渴望著與子宮的相逢。
真的操死了,不算什麼,一筆封口費,外加一點威脅,足以讓她那個沒什麼背景的家庭永遠閉嘴。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高英祥是個成功的政治商人,不是黑非洲見人就砍的土匪頭子。
“光輝,你雖然這麼說,可是,你下面越來越緊了。怎麼,痛經收緊陰道了?還是你發騷,等著我來操啊?哈哈,要是給你填個兒子或者女兒,我也算大德,做了一次功德哩。“
順便一提,高英祥是個明面上虔誠的佛教徒。一有時間,他沒少給寺廟捐錢蓋樓,修大佛,修佛學院。隔三岔五,他還要當個“科普佛學“的商界”文化人“,參加幾個佛學講學會。
東江省內,方丈們看見他高英祥,絕對比看見親媽要熱情。
“你要是就這麼死了,放心,你的孩子我肯定會照顧好的。“
“不…求求你…啊啊啊…疼死我了…求求你,放過她吧,她才是個小學生,與我們這些大人毫無關系…呀!“
他狠狠地掐了一下光輝的屁眼。銳利的指甲,像是剃刀,要把那軟嫩的菊花碎剁細割。
“老子沒射精,你個娘們插什麼嘴?給我閉上。“
他從腳上脫下襪子,怒視著光輝。光輝的嘴里,很快又洋溢著腳臭的奇異熏香。
光輝本來還有那麼一點微不足道的抵抗。這下好了,徹底蔫了。
高英祥不過損失了一點強奸的快感。他有點生氣。過了夜的剩菜總不如剛燒的香。於是,他撕開光輝的上衣,惡狠狠地咬在乳肉上。
“疼啊…求求…啊…放過…啊…血,不行了。我不行了。啊!“
無論是身上,還是身下,光輝的身上,血液橫流。下體成了長江,雙乳成了淮河。
血液的鐵鏽,混著乳香的酸味,汗臭的酸味,充盈著兩個瘋狂的頭腦。
睾丸對菊花那點可以說溫柔的反復撞擊,龜頭不斷對子宮口那個細孔的衝刺,這二者相較而言,完全可謂名副其實的溫柔體貼。
一個瘋到想死。一個瘋到想殺。一個害怕死亡,一個擔憂家人。
差不多光輝下面的月經,連一點殘渣都不剩,高英祥終於恢復一點理智。
望著昏死過去的光輝,他很滿意。這樣的女人,只會對那個倒霉催的老公張開雙腿。
他實現了零的突破。如果她繼續這樣,他能接著這麼玩她,直到玩膩;
如果她被玩壞,他會找個認識的黑幫,給他們最後爽爽,然後滅口。
“我要好好操你了。放心,我這邊備著一台小的空氣呼吸機,給你備的。你,死不了。”
——光輝今天,要小光輝違約了。
本來,今天,如果沒有這件事,明天,禮拜六,她要早起,帶小光輝去水上樂園玩一天。
“對不起…老公…對不起…”
身上那個渾身大汗的男人,忙著做活塞運動。干涸在床單的紅牡丹,氧化,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