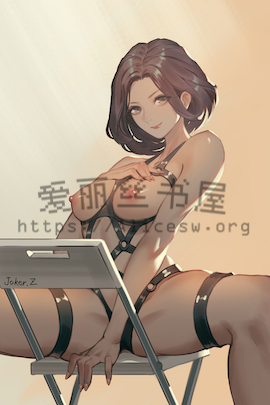雨時落時停,風若有若無,空氣里氤氳著的一種壓抑,變成春末夏初的躁動,似乎成為這個時節,這個地區的一個標致。
馬車在林間行進,一路留下一排蹄印還有車轍的條紋狀花紋來。只不過無論是金屬馬蹄的精致花紋還是車轍,都是印在了泥淖的地上,顯得有些髒亂。
而此時,在馬車後處,跟隨著三個黑衣黑面打扮的人,其中一人蹲坐看著這馬蹄印露出一絲詭譎的笑來。
所謂觸景生情,眼前所看之物於此人心中激起波瀾,不,更深層次來說,應該是相交融在一起,或喜或憂,或是對未來抱有向往,對過去不堪回首,這一切都溶解在空氣里面,鋪展於畫卷的一角。靈兒透過左右兩側的紙紗窗張望著,都是清一色的綠竹,總覺得心里空寂得難受,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啃噬著自己的心。
此時,有一絲淡雅的甜香透過來,讓靈兒倍感舒心。都說人的嗅覺記憶頗為敏感,一種獨特的味道或許幾年幾十年都無法忘記,何況是具有特殊意義的味道。
“張師傅,在這里停一下吧,我想下車,看看這花來。”清甜的聲音透過帷幔,變得更加柔軟。
“啊,在這里嗎?只是這‘鷹林’,不是久留之地呀!,還是早點……”車夫顫顫的聲音或是因恐慌,明顯有些嘶啞。
帷幕一頭傳來“嗤嗤”的笑聲。“就一會功夫,不耽擱的。”
“是,夫人。”張四德也不敢和這個大小姐貴婦人爭辯了,可內心還是有些不情願地讓白馬慢下來。
隨著溫順的白馬漸漸收住了腳步,馬車漸漸在林間放慢速度停歇了下來。後座的簾子被緩緩拉開,先是一只白色水仙軟緞鞋顯露了出來,腳踝處隱隱約約可以看到柔軟的白襪包著。剛讓人想,這該是孱弱的千金女子時,突然玉腿一點,一個俏麗的身子從車內閃現,可見其功力深厚。
不過一旁的張四德完全不懂武功,只是低垂著臉,有些不好意思地再次打量看靈兒。
帶著兩寸高披跟的緞鞋托著女子的身體,方才動如脫兔的身法,此時如同一個工匠做出的瓷人一樣輕輕觸在了碎石路上。邊上一棵碩大的桐花樹不合時宜似的點亮了竹林中一片綠意。方才在馬車里嗅到的香甜,就是這白色花朵間傳來的。
林間時有的微風帶起裙裾,她的光鮮衣著,似乎和這野外林間無法糅合到一起,從某種意味上來說,卻又兼具了自然和人類文明的美。
圓圓的臉蛋顯得有些稚嫩,靈兒身穿一件胭脂紅繡橘色海棠紋的對襟衣,妝緞素雪細葉薄輕紗裙,裙角剛好遮蓋住精致的金絲线繡水仙花雙色軟緞鞋,從背後延伸手腕處的是素白色披帛。烏亮的秀發,頭綰風流別致飛雲髻,輕攏慢拈的雲鬢里插著祥雲花玉簪,紅翡翠滴水耳墜則讓靈巧的雙耳顯得愈發可愛,膚如凝脂的手上戴著一個羊脂玉手鐲,腰系撒花緞面絛,上面掛著一個小香袋,整個人顯得妍姿俏麗貌似天仙。或許是又回憶起什麼傷心之事,眉心處輕輕皺起,反倒讓人更覺憐愛了。
詩曰:
輕蹙寒黛眉,佳人從畫出。
繾綣暮春雨,山水自墨生。
美人配如畫的江山,不禁讓人深思這究竟是從畫中走出來的人,還是說周圍的山山水水都是畫中物呢?
“莫怪小的多嘴,還是想和夫人說說這‘鷹林’的來頭。”
“你說便是了。”
張四德舔了舔嘴唇,東一句西一句的將他知道的拼湊起來。
卻說這鷹林,原本是南州城外一普通的大片竹林,連名字都未有。後乃北宋統一前各國動亂,免不了一些殺人越貨之事,這與主干道偏離的小路也是其中之一。盡管如此,總有地方的富豪或是,乃至運鏢隊為了抄近路,往這里走,遭到毒手。南唐被滅以後,北宋地方官府將這塊區域管轄起來,但是不免還是會成為一些人的目標。捕快時有發現在這竹林間有遺棄的空馬車,或是有血跡的衣物,甚至在深處還有女子艷麗的屍首。官府在初期嚴查嚴打,似乎是抓住了一群采花大盜,竹林也似乎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但是不知從哪一年開始,又陸續接到人或是貨物失蹤的報案。可這次,官府派出的人多是有去無回,好不容易有僥幸逃回的捕快也是被剜去眼睛或是截斷肢體,場面十分慘烈,仿佛是被老鷹啄食一般不忍直視。於是竹林又被稱作“鷹林”,當地人可謂談鷹林色變。
也就是這年四月,從京城專門來了一名女神捕,花羽。據說她查案無數,身手矯健,不僅擁有一手不錯的身法,還有貼身鎖甲護身,刀槍不入,甚是厲害。南州城衙門和花神捕為了展開追捕行動,引蛇出洞,不僅開放鷹林的通行,還暗中讓神捕帶著三名內力高深的捕快,沿途追蹤調查。只是一周下來並無所獲,或許是賊人銷聲匿跡,或許是當地居民也不敢再於“鷹林”成為被捕食的兔子罷。
“哎呀!”囉里囉唆地講到一半車夫一叫,倒是讓沉思中的靈兒一驚,回過神來側身看去。
“那個……,小的內急,能不能……”瑟縮地伸出敦實的食指來,往林子深處指了指。這四十多歲的中年男子在小自己二十多歲的女子面前羞得臉龐通紅。
“啊?嗯……”靈兒聽了是一愣,但又不知道說什麼,拂袖而笑。
老張連忙擺起雙手跑往林子深處。並未有覺察到自己正被數丈開外的三雙眼睛盯上。
此時的靈兒獨自一人,輕輕走向那棵桐花樹去,‘鷹林’也好,惡霸強盜也好,都不是她所關心的。不由分說,失去丈夫的靈兒,現在心中所有的期盼就是那一對雙子女孩兒的健康成長了。但為人母的另一個身份,也是妻子呀,此時,讓她魂牽夢縈的是這散發著幽香的桐花樹。
美目一閉,想起兩年前和夫君趙鯉在趙家後園的事。
“孩……孩子?”
“對,就在今天,不,就現在吧!”
“我,可是,你突然這麼說,我也……”
這時,趙鯉右手用手指按住靈兒纖薄的朱唇,左手伸向發髻下靈巧可愛的耳朵,輕輕觸碰起來。
“我算了卦,說是今日行事,會有雙鳳吉祥之象。”
趙鯉深情地望著愛妻,眼前這位挽著雙丸子頭發髻的女子似乎還未有妻子的老道賢惠模樣,倒不如說是自己的小妹妹一樣令人憐愛。
女子輕輕搖了搖頭,耳環的流蘇發出清脆的搖曳聲。
“鯉,讓我再准備一段時間,好嗎?”靈兒眉間輕蹙,眼光也開始閃躲起來。
“哎,看來我趙家要斷後了啊……”趙鯉坐在太師椅上向後倒去。
“不,不是這樣的……”,“我修煉的清月心法,還未到第八重,如果現在失了……如果現在做那種事情的話,往後怕就只能停止在第七層的修為了。”
“哦?那清月功重要還是你的夫君重要呢?”趙鯉也開始佯裝耍起性子來。
“這……”靈兒小嘴一扁,泛起難意。
“放心,就算娘子你武功全失,我也會拼盡全力保護你的。雖然現在我的功力還在你之下,但是我作為朝廷命官,幾千鐵騎也會成為你的護衛。”又用手指戳戳靈兒柔軟白皙的臉。
靈兒雖出身名門千金,卻自幼拜清月閣門下習武,為的是在五代十國戰亂時習得一技之長,除暴安民,資質優越的她,豆蔻之年便達到了成年師姐門的水平,在門派中可謂頗具期望,換句話說,將來晉升掌門的備選中最具潛力的就是她了。而後北宋朝逐漸統一全國,又機緣巧合邂逅趙鯉,墜入愛河,似乎對於武功的執著也開始漸漸放下。
“好吧,我竟是自討沒趣,……嗯,我先回去了。”趙鯉欲起身離去,其實卻有計策在身。靈兒美目一抬,想著像之前一樣撒嬌,從薄荷綠色的長衫袖口伸出纖纖玉手,去拉趙鯉。
趙鯉一個壞笑,突然側身掀起她下身的裙擺來,一雙穿著淺口繡鞋的玉足顯現開來。還未即靈兒反應過來,捏住腳踝處的柔軟羅襪,一使勁拖拉,讓在池邊石凳坐著的靈兒一個趔趄跌倒下來。頭上雙丸子頭發髻倒是安然無恙,倒是齊眉劉海有些松散開的跡象。
這還沒有完,趁著坐起的須臾,趙鯉揪准一個間隙,將保護玉足的繡鞋剝去,露出完整的蠶絲襪保護的玉足,足尖隱隱約約還能見到被染成淡粉色如同桃花般的指甲來。趙鯉雖然之前早有目睹,但是這次還是看得他心潮澎湃,又旋即往足心涌泉穴一點,就讓要催動功力的靈兒全身酥軟開來。
如果兩人真的比試武藝,的確靈兒技藝至少高做夫君的一成有余,但是此時趙鯉出其不意加上接二連三的“陰招”,讓靈兒落了下風。真氣再度凝聚所需要花費的幾秒鍾,對於趙鯉來說,就成為了關鍵,一切都按照他計劃的來行事著。
他一氣呵成,竟然按住美妻的腳踝,托起靈兒往花池跳去。“撲通”一陣巨響,先是趙鯉渾身透濕,剛想計成大半,等待自己的愛妻也漫入水中濕身的聲音,卻發現靈兒“懸浮”於水上。說是懸浮,實則靈兒在這時間及時調動真氣,一雙素手用起清月門的“輕舞飛揚”,掌法綿軟有力,雙掌觸及水面,竟然將身體拖起,這讓在水中透濕的趙鯉又氣又惱。
“哈哈,夫君,我說你還是別……”
靈兒剛覺給對方一個下馬威,可突然覺得自己雙腳的過膝蠶絲羅襪襪帶慢慢變松動,緊縛帶好像被一點點抽離。不過平時倍加愛護雙足的靈兒,特地讓襪帶的綁法做了特殊加工,不僅形狀可愛,宛如一對翩翩起舞的蝴蝶,若是外人的話,解開也需要費好大功夫。
不好,自己足底若是被愛撫,真氣必然錯亂……當務之急是趕緊掙脫束縛。其實最為簡單的方法是雙足貫穿“輕舞飛揚”,但是這樣趙鯉勢必會被打傷,靈兒怎會下得了手?怎樣才能讓夫君放手,不傷到他……腦海突然想到一念頭。
靈兒右掌突然一收,朝著兩丈開外的桐花樹拍去,銜來一朵桐花後向趙鯉飛去。
這是所謂的假借花瓣之力,將真氣的力量降到最低作為投擲武器來使用。趙鯉“啊”的一聲叫嚷,突然,松開了雙手。也正是借著這股力氣,右腳過膝蠶絲襪襪口的蝴蝶緊縛帶已經被抽離,襪口松松垮垮地滑到膝蓋處。
本想使出輕功躍起的靈兒突然發現夫君沒了蹤影?難道自己還是打暈了他,沉入水底了嗎?
卻說這蓮花池雖為人造池塘,但是趙家闊綽勝過寒家,僅一池塘便有普通人家宅院的正方一般:深數丈有余,內有游魚。此外除去雕欄精致的石橋二座,還有小巧的玉石假山,四周都栽有庭院花木,甚至在水中也有奇石珍寶,讓人夸贊巧奪天工的同時,也不得不感嘆富甲一方里滲出來的奢靡之風。就是這樣一個後園,竟讓靈兒一時半會尋不出夫君的蹤跡來。
“鯉,……鯉你在哪兒?”靈兒調整姿態,將真氣轉移到雙足足底,這樣就可以踏水而行了。蠶絲襪足底碰到水,還是有一股清清涼涼的快感。於是一邊走,一邊呼喚著丈夫。
而此時趙鯉潛在水下,乘著間隙將自己的長袍長靴褪下,赤身裸體。正准備第三波“攻勢”。他在水下睜眼,見一雙玉足在水上行走,透過被打濕的蠶絲襪,可以清晰可見粉白色的足底。所過之處,周圍泛起漣漪。仿佛靈兒的一雙美足踏著的是冰,而不是水一樣。
回到水面來,靈兒見數分鍾過去,還未尋到丈夫不由得擔心起來,叫喚的話語里也帶著一些哭腔。趙鯉自小愛好戲水,水下功夫十分了得,後雖然在朝中做文官,卻也不忘自己的武術絕學。若是催動內力,在水下可以屏氣一個時辰。
“鯉,……是我不好,你在那兒……鯉,……我答應你,做……今天就做……”
突然,右腳的蠶絲襪尖端似乎被什麼夾住,抬不起腳來。靈兒還來不及反應,那個力量陡然增大,一拉,從膝處迅速下滑落到腳踝;一提,從腳踝聚集的襪筒仿佛是剝開果皮一般,一只及膝羅襪被完全剝離下來。
“哦,到手啦!”趙鯉拿著羅襪,突然浮出水面。當作手帕似的擦了擦自己的臉,一股甜香沁人心脾。
“你,你!”靈兒氣得急得抬腳受力,卻忘了自己還在調用真氣保持平衡在水上站著呢!這下可好,一只裸足和另一只羅襪美腿開始濺起水花,一寸一寸地往下沉。靈兒發現不對,此時,水面已經沒過腳踝,沾濕了繪有蓮花圖樣的的襦裙下擺。
正當要運起氣來,准備躍出蓮花池時,突然覺得自己裸露白皙的右腳酥麻奇癢無比,低頭一看,趙鯉正用自己的手,不是,剛在射出去的那枚桐花,按著自己的足底。或許是花瓣遇到水的緣故,又或是水浸泡著常年保養的玉足,帶著純甜的味道,洇染在空氣里。
“別急著跑嘛,剛剛是誰說著答應的?又不是小孩子了,怎麼能說話不算話?”趙鯉在水上浮出半個身子,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的確,這次勝利的天平無疑傾向了他那一邊了。
“不,不要這樣,靈兒還沒有……”說著這話的時候,靈兒雙足的真氣正因為一點點的“按摩”而迅速消散,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靈兒在趙鯉的拖拽下一寸寸,幾寸幾寸地迅速下沉,無論是上身的對襟長衣,還是高過胸部的襦裙,都是用以輕盈光滑著稱的絲綢織成的,雖然美觀,但是一經水泡,就變得透明起來,將里面那件白色連體褻衣襯托得楚楚可憐。
沒等把話說完,趙鯉就用左手輕輕按住青絲盤繞的後腦勺,用自己的舌頭舔舐起靈兒的朱唇,右手溫柔的愛撫起靈兒的曼妙身體來。透濕的對襟長衫和高腰襦裙不再如蝶一般輕盈,反倒成為了累贅,在水里一個動身都顯得極為不便,這樣正是計劃的一部分。在水下,赤身裸體倒是成為了一種絕對優勢。
趙鯉開始完成自己計劃的第四步了。
他潛入水底,先是用剛在抽出的羅襪絲帶,在美妻的腳踝處打了一個牢固的結來,後來不放心,又抽出另一只襪子上的絲帶,綁到膝蓋的位置,這樣除非靈兒全身運起真氣,用清月門的“脫兔式”,否則無法馬上掙開;但是他也料到,自己所愛的靈兒也是不會為了脫身甘願傷到自己的。
趁著靈兒雙手撲騰之際,用手解開襦裙上的緞帶來。失去緞帶的束縛,高胸襦裙頓時變得松松垮垮的,靈兒只覺得腰部被一雙大手一樓,裙子便如同花瓣一樣被輕易地摘掉。現在靈兒除了胸部之上還浮在水面,下身只剩一條推到腳踝處的蠶絲羅襪,還有純白色的連體褻衣遮身,而上身的薄荷綠對襟長衫雖然長度上可以到小腹之下,但是被水浸泡後變得透明,完全不能阻擋住主人香嫩的肉體來。
趙鯉覺得時機差不多了,便開始計劃的最後階段。他催動掌力,讓桐花形成氣旋,包裹在二人周身,桐花的味道頓時讓周圍的空氣變得迷人起來。
於是緊緊抱住靈兒,撲通一下沉入池塘底。而這周遭的花瓣就如同護送二人的屏障一樣,一齊向下沉入。
這時,趙鯉感到,靈兒的雙手也不再是操控真氣的抵抗,反是用指肚輕撫自己光滑厚實的脊背。二人在水中互相注視了一會對方:靈兒看到的是一個血氣方剛,面容英俊又帶著一些風流的青年,健碩的身體渾身裸露,健碩的肌肉重點交匯之處——陰處的體毛濃密而粗大,倒有些像水中的藻類。而趙鯉眼中的靈兒則同人魚一般嬌艷。雖方才的嬉鬧後,華麗的衣著大半被剝去,留下的只有最後幾個屏障,面部精致的淡桃色眼影和鮭紅色朱紅的精致妝容,在水的浸泡下也消去大半。趙鯉摟住靈兒的玉肩開始輕輕舔舐胸口露出的一一小塊梯形的肌膚,逐漸將方向往下的同時,將對襟長衫順著雙臂往下褪去,這長衫的手臂處一對仙鶴的圖案漸漸蜷曲,拉至手腕的地方。
趙鯉腳底慢慢使力,兩人頭碰頭上浮,靈兒借力躍出水面,以頭部為支點,雙足在空中回旋華麗地切割出一個圓,換完氣後又開始下沉。而此時,綠色衫衣也在這外力下,從雙臂間飛出,飄在水面之上。
趙鯉這時又盯上靈兒的發髻來了。雖然被水完全浸濕,可漂浮在水里的劉海反倒是變得更加惹人可愛,少女風韻十足的雙丸子頭,被藏在發間的兩枚銀發針固定住,外面還用淡綠色的絲帶左右各包著一朵胸針般大小的白蓮花。
他用手捏了捏,松松軟軟的。輕輕抽掉兩條裝飾用的絲帶;又看到靈兒輕輕搖了搖頭,似乎在示意請求著什麼。但真是這個讓人愛憐的舉動,反倒是激起了他夫君心中的獸欲來,似乎把靈兒身上的那些高貴優雅,格律工整的美都一一破壞,返璞歸真,才能夠達成自己的欲望。
他繼續用手拉了拉,推了推,發現兩個可愛的丸子並沒有因此而脫落,甚至變型,想必是有什麼固定用的首飾在內。於是從後腦勺開始用他粗大的手指在靈兒青絲間胡亂地摸索,先是將後髻的一對玉蝶首飾拆落下來,隨意一扔,靈兒剛想伸手去奪,趙鯉對著香頸的一問吻,又讓直直的藕臂酥軟垂下來。那玉蝶便直直沉入池塘的泥淖了。可就這看似普通的一枚首飾,也是價值連城,無論是中空鏤刻的工藝,還是蝴蝶眼睛出鑲嵌的兩枚藍寶石,都不是隨隨便便能夠完成的。
趙鯉還是漫無目的地捏拿,像是在靈兒發間尋找什麼機關一樣,手指在發間罅隙穿插,一無所獲。可是在靈巧的耳朵上放,他還是感到了細長的兩根發簪——同針頭一樣的粗細發針在兩端稍稍有圓潤突起,一頭還做出了鳥羽的精致造型來。可此時,這“鳥羽”像是被牢牢地抓住,等待著的似乎只有拔出這一選擇。
為了讓可愛的丸子頭精致而不易松開,每次做這樣的發型總是不讓手下的婢女丫鬟插手,自己親自挽的發髻。也是如此,被拔掉固定用的發簪,也並沒有馬上散開作雙馬尾狀。靈兒盼目一彎,抿嘴一笑。或許是紅了臉頰吧,但是在水下卻也看不出端倪。她輕輕晃動頭部,兩條黢黑的馬尾長辮同靈蛇一樣,在水中上下游動。
趙鯉輕輕抓住發根處的綁帶,只是一提,那其中一條“靈蛇”便撲騰了幾下,消失成為一團柔順的青絲。另一條也是用同樣的方法,烏黑長發霎時披散開來,宛若煙雨。他痴痴地望著那如水青絲,竟有些看呆了。用的半個時辰才編成的精致發髻,就在短短的幾分鍾被“糟蹋”成一團,似乎也在昭示者一名少女正在准備完成她的蛻變。
池塘中的紅白交映的鯉魚群圍繞著二人游動,似乎在准備什麼儀式一般。
長發披身的二人緊密相擁,躍出水面換氣,又再次沉入池中,沒有濺出什麼水花,仿佛只是兩枚相簇而生的花瓣落在水面,僅僅泛起幾絲漣漪。
在靈兒已被池水幾乎洗淨鉛華的臉上趙鯉又是一吻。原本水靈的臉更加柔嫩,仿佛孩童的皮膚一樣光滑具有彈性。雙手輕捏乳尖,緩緩在轉動,後又換作掌狀,索性拿捏起來。一會兒時間,靈兒已閉上雙眸,似乎熟睡過去一樣,在水中舒展開身體。於是趙鯉游走到靈兒的後庭,按住那柳腰,目光窺向那蜜穴處。
他深吸一口氣,緩緩發力,粗大的龜頭在狹窄緊密的穴道內一路向前,頂開稚嫩的肉褶,最後撞在柔韌的處女膜上。
在處女膜溫暖柔和的包裹下,他深吸一口氣,狠狠向前一頂,雖然痛得靈兒仿佛全身觸電,吐出許多泡泡,並扭動起身體來,但是處女膜並沒有被捅穿。盡管女孩已經做好了准備,可一身的神功似乎是在忠實地保護肉體——真氣未完全消退之時,即使精神層面的情欲也無法簡單地讓清月神功被破。於是趙鯉用他粗壯的雙臂握緊愛妻的玉足開始發力,柔軟的玉足凹陷了下去,十枚腳趾張開,像是兩朵微張的花瓣。趙鯉用自己的純陽之力攻入其中,兩股真氣似乎在爭斗一般。不一會十分,靈兒全身開始顫動,雙腳開始往內夾緊。人的足底穴道眾多,又與各個器官緊密相連,此時靈兒體內的真氣已經有些紊亂,無法再全力庇護那蜜穴處的屏障了。
趙鯉胯下發力猛地向前一挺,將粗長堅硬如石的肉棍齊根再次沒入花穴,一插到底,那捅破珍貴的處女薄膜,這還沒有結束,借助慣性,重重撞在了穴道盡頭的子宮口上,將靈兒守了十七年的處子奪去。
落日西斜,落霞映著池塘上漂浮著靈兒的衣衫,褻衣還有蜷縮成一團的蠶襪,無不令人生憐。偶有游魚聞香上浮,魚嘴一頂,發現並非餌食,才懨懨下沉離去。
“啊……嗯……夫君……”
一聲浪叫驚起身旁幾尺外的一對飛燕來,後者撲打著翅膀急急飛去。也不知道這動物能否覺察到這柔軟綿長的音线里,是有什麼樣的意味在。
只覺得自己的呼吸變得急促,香汗從後背,足底開始緩緩滲出,乳房處酥麻的感覺慢慢變得有些脹痛,方才意淫之時,乳孔處又滲出一絲奶水來。
忽有勁風吹過,幾枚桐花花瓣飄零,無力地墜落在地上。
靈兒輕輕蹲下身來,也不顧襦裙被地面的雨水沾濕,伸出雙手,像是舀起一勺清水般,捧起桐花花瓣。於是朱唇一動,聲音還是那麼悅耳,只是添了一份清冷:
桐花爛漫香易逝,清明疏雨人多淚。
芳景如屏年年有,昨年落花誰人記?
珠翠碧玉飛鳥去,荷塘歡情一枕夢。
萬家新聲不覺耳,何為長久為何生?
吟畢,須臾間,撲簌撲簌幾滴清淚打在這一捧桐花中。
料峭春深鎖佳人,愁腸幽夢多弄花。
奈何誤入林間來,今年新草鷹撲兔!
林間環繞著的雄渾聲音里,帶著惡意。
靈兒用還含著淚的俏目往四周看看並未見人影。
“兔子休跑,鷹在這里呢!”在一棵竹子尖處單腳站立一黑衣裝扮的人來。
話音未落,一陣勁風吹來,不同於自然的空氣流動,只覺得流動間分布著殺氣毒意。
靈兒一驚,抬起纖手,輕輕一揚,這些花隨著腕間傳來的真氣,如盤旋的蝴蝶,縈繞在周身。
“撲”一陣悶響,桐花被擊碎成花瓣,後又慢慢分散,頹然落下。原是方才黑衣人擲出的一枚金錢飛鏢,此時竟被彈開,深深插如土中,只露出鏢尾處紅色的緞帶來。
“你是唐門弟子?”靈兒淡粉色眼线點綴下的美目,此時圓睜,雖有尚未被風吹干的淚,但帶著一絲孤傲冷艷來。
“唐鷹是也。”只是說這話時,那男子面無表情,冷峻得讓人發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