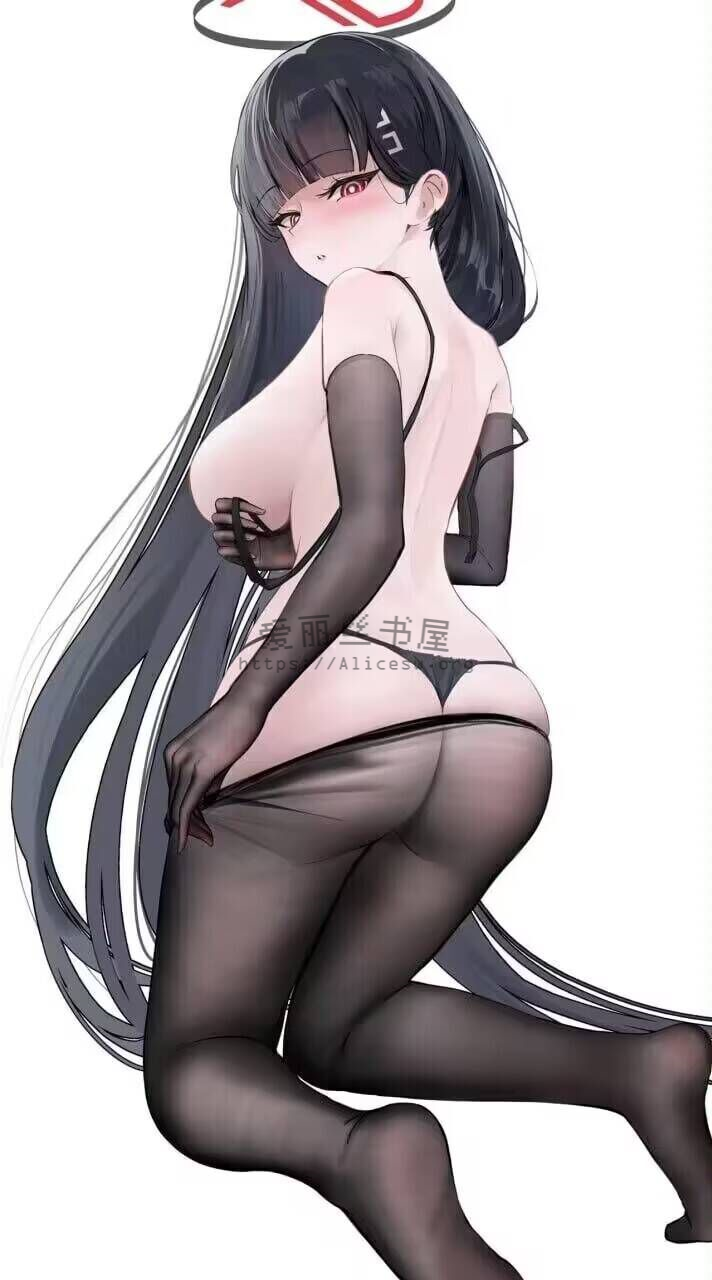龍門市區有多麼光鮮,其背後就有多麼的陰暗。林此時就在這麼一個連地圖都沒有顯示的小巷里。四周彌漫著潮濕的氣息,連流浪動物都不屑於光顧的,百分之一千的貧瘠區域,此時就是林與陳最安全的躲避地。
“生命在於運動……想要活下去就得像是老鼠一樣四處流竄……麼?”
林一邊吃著手里的壓縮餅干,一邊看著在箱子里安睡的陳。舒緩的呼吸與緊閉的雙眼讓她看上去絲毫沒有蘇醒的跡象,也讓林暫時性的可以繼續享受這段獨處時光,
“雖然說老爺子給的那管藥是正規的麻醉劑,但是這個警察睡的也太久了吧……這和正常的丫頭有什麼區別呢?”
看著陳干淨的臉蛋,與舒緩的眉頭,林的心境也從緊張的逃亡中暫時抽離,與這個像是小貓一樣安睡的女孩開始享受起短暫的寧靜。
“雖然我還想看看她剛睡醒的樣子,或者是掙扎的樣子……但是這種女人一定會很吵鬧的吧……我估計還打不過她……而且……”
林把干癟的壓縮餅干一口吞下,又灌了幾口涼水,
“她不醒還能給我省點口糧……怕什麼來什麼……”
“唔……”
是由於有些陰濕的空氣嗎?還是因為林身上無法褪去的汗臭味呢?總不能是藥效已經過了吧?無論是什麼原因,陳輕輕的皺了皺眉,並且從自己除了鼾聲之外沒有再發出過任何聲音的小嘴里擠出了一句悶叫。萬幸的是,修長的雙腿並沒有活動的跡象。黑色的馬丁靴輕微的翻著不遠處的燈光,被白襪包裹的腳踝依然在膠帶的幫助下平穩的並在一起。
“得虧我早有准備……”
林從挎包里拿出一個礦泉水瓶,黃澄澄的茶水里還飄浮著幾片花瓣和枸杞,如果陳能夠以自己的意識睜開眼看看的話,一定能認出這些早些時候讓自己陷入沉睡的特制花茶吧。隨後,林又從挎包里翻出一個油紙包,並且把里面的白色粉末全部倒進了這瓶茶水中。那是專門按照正常女人的抗藥性進行分裝的安眠藥,一次一包,平均一次4小時,再混上這半杯茶水,足夠自己找到一個有屋頂的房子了。
“聽說老爺子的茶水你只喝了半杯就睡了三個小時,這下你可有的睡了”
林一邊嘟囔著,一邊把一只連著pp軟管的針筒伸進了瓶子里,並且吸滿了液體。
“乖,乖乖喝水”
林輕輕的把陳扶了起來,讓她跪在箱子里,同時上半身靠在自己的身體上。他輕輕推了推陳的下巴,讓她的小腦瓜無力的歪在自己的肩膀上,微微的向上仰著。
呲啦
林小心翼翼的撕開了一部分陳嘴上的膠布,並且把pp軟管伸進了陳的小口里。
“咕唔……咕……唔……”
盡管可能在睡夢中有一萬個不願意,但此時任人魚肉的陳還是安順的喝起了茶。通過注射器推進她嘴里的茶水永遠都不會超過她的吞咽能力,也就讓她不會嗆到。綿綿不斷的茶水像是一條細水長流的小溪一樣,和平而安穩的被陳盡數接受。看著陳的喉頭上下蠕動著,林也變得口干舌燥,他痴迷於陳白皙的肌膚,但又始終覺得有什麼缺憾,但他又無法想到缺了什麼,也無法停止自己在給藥之余的這種思考。這種對於未知的追求可能正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動力吧,但此時被這份追求推動的只有陳在昏迷程度上的大步前進。
“乖,好好睡”
林一邊舔舐著從陳嘴里抽出來的pp管,一邊把陳嘴角的膠布封好。花茶的芳香混雜著陳的體香,衝擊著林的思維。
“不行,現在還不是休息的時候,得趕緊找出路”
恍然大悟的林把注射器和礦泉水瓶放回了挎包中,隨後又扶著陳的腦袋讓她躺回了箱子中。
“哼……呼……哼……呼……”
不多時,悠悠的鼾聲再次從箱子中傳出,也打消了林立即動身的念頭。
“稍微歇歇吧……”
林也點起了一支煙,聽著陳的鼾聲開始了自己短暫的休憩。
“哼……呼……哼……呼……”
…………
“哼……呼……”
……
…
被褥上的汗臭味與男女體液的特有腥味在晨光的照耀下漸漸升騰起來。原本潔白的被褥也已經被汗漬變成了有些惡心的乳黃色。床頭櫃上和周圍擺放著男女之間的各種玩具,在這張床的正上方還懸掛著幾根鎖鏈與圓環,方便有特殊愛好的雙方進行危險的游戲。而被眾多稍顯重口的玩具包圍在中間的,卻是衣冠整齊的陳。這身黑色衝鋒衣搭配黑色緊身褲和馬丁靴的配置與周邊環境太不搭調了,但凡林有一點點閒錢肯定都會給陳換上另一套新衣服吧。不管是蕾絲內衣搭配吊帶襪還是三角式胸罩搭配一只黑色的choker,哪怕是全裸都要比現在的這一套衣服要和周遭環境更搭一些。但特殊的內衣不是林能買得起的,而肮髒的被褥也讓林不想讓陳的肌膚與這張可能已經布滿蟎蟲的床墊有過多的接觸。哪怕是陳的睡臉都被林用自己的大衣墊了起來,讓她遠離這方汙穢。
現在的陳也只能穿著她已經穿了很久的那套衣服,單調乏味的睡在這張透露著貧窮的睡床上了。打理得當的衣物使她看上去依舊干淨利落,黑色的緊身褲勾勒出她完美的腿部曲线。完全松弛的肌肉被緊身褲充分包裹、塑形,並最終變成了現在這幅纖細而富有肉感的景象。處於身體末端的兩只馬丁靴微微反射著金色的陽光。與全身色彩相統一的這雙皮靴被兩條打著完美活扣的鞋帶綁在陳的雙腳上,幾只小巧的金屬環閃著金色,它們一方面為鞋帶留足了通過的空間,另一方面也為陳這一身偏暗的搭配帶來了些許亮色。中規中矩的白色棉襪依舊藏在黑色的靴子里,只能從鞋舌頭的縫隙中瞥見一點潔白的顏色。不知會有多少男人在看到這一幕之後會幻想著將陳被白棉襪包裹著的玉足捧在手心精心呵護呢?至少在這個房間里就有一個,只不過他想在一個干淨一點的地方開始這個“儀式”。
當然了,如果陳的意識能夠上线的話,她要對這上述搭配提出的第一個質疑一定是“為什麼一定要讓我去搭配這個環境啊!”,只可惜現在的她一方面沒有機會說出這個質疑,另一方面她也暫時沒得選擇。
似乎仍處在安眠藥的壓制之下的陳將這股略顯肮髒的空氣照單全收。也許是被褥上的氣味過於難聞了吧,安睡著的陳輕輕皺起了眉頭,這也是她為數不多的得以反抗安眠的方式了。
“也差不多該讓她醒來了,我得稍微看看藥物的後效”
毫無蘇醒跡象的陳讓林做出了決定。在確認了陳身上的綁束仍然有效之後,林將幾根草葉撕碎,並將其汁水塗抹在已經被陳的口水浸濕了一部分的自己的大衣上。
“咕唔……咳咳……”
很快,被封住的嘴能發出的最具有標志性的悶咳聲打破了房間中的安寧祥和。陳的眉頭漸漸變得緊皺,兩道眉毛不自覺的跳著,一同抖動的還有陳的身體。
“唔……?唔嗯……”
終於,陳睜開了惺忪的睡眼。三生有幸的林注意到了陳睜開雙眼的那一瞬間,他看到了陳的眼白與赤瞳從上眼瞼向下滑落的一幕,也讓他再次回想起了這次短暫的旅途之中幾次三番的偷嘗陳的睡眼的禁果時的景象。雖然他僅僅是翻開陳的雙眼看看而已,但均勻分布的眼白、赤瞳與血絲還是讓他看的面紅耳赤。陳的無奈與安詳被那對完全散瞳的眸子體現的淋漓盡致,而此時,慢慢恢復對焦能力的雙眼再一次讓林的心跳加速。
“唔嗯!唔嗯!”
盡管模糊的視野還不能讓陳分辨出站在自己面前的是誰,但從身體的各個關節傳來的束縛感已經讓她意識到來者不善了。她一邊扭動著自己的關節,一邊用力抬起頭盯著眼前的人。視野漸漸的變得清晰,一襲黑衣的輪廓也被細化得更加容易辨認。很快,陳就辨認出了這個男人手背上的紋身,與上面那一道刀口。
“醒來啦陳警官?身體還舒服嘛?如果醒來了的話,能不能把你臉下面的大衣還給我?哎哎對,高抬貴臉,謝謝謝謝”
說是為了拿回大衣,實際上林是在觀察陳的身體狀態。如果陳能夠很自然的抬起頭,那就說明她已經能夠較為自由的控制身體了,那麼自己的處境就已經很危險了,很可能要立刻對她進行壓制了。
“唔?唔……嗚嗚!”
在聽到林的話語之後,陳的眼睛在不遠處的林和自己臉下的黑布之間游蕩了一下。突然爆發出的悶叫聲大概是對於這塊被稱為大衣的黑布的發自內心的鄙視和惡心吧,但陳的小腦瓜並沒能從大衣上抬起多少距離。
“唔……唔……唔嗯!”
劇烈的頭痛與肌肉酸痛讓陳皺起的眉頭中多添了一絲有別於憤怒的情感。眉頭緊鎖、用力瞪向林的陳可以說是一只困獸,但這也是林想看到的。
“非常好,你果然對這些藥劑毫無抗性”
滿意的微笑掛在了林的臉上,他自此也算是明白了為什麼娼館的人能夠做到那麼高的捕獲成功率。就那麼一小包的藥就可以維持這麼久的高質量睡眠與長時間的副作用時間,就算是陳這樣的精英警察都不能從中掙脫出來,更何況那些披著吹彈可破的肌膚的女孩呢?
“稍等下,我喂你吃一些早餐”
林的身影消失在了門框的另一端,悠悠的小曲從對應的方向傳來,看樣子林的心情真不錯。
“唔嗯!!”
盡管嘴上沒認輸,或者說早就輸的連底褲都沒了,陳的大腦依然在冷靜的飛速運轉著,
“早餐,再加上這個光线,現在可能真的是早上,也就是說我從昨天下午一直睡到了早上……也不能這麼樂觀嗎……”
幾次和塔露拉的不期而遇讓她體會到了長時間昏迷對時間觀念的影響,她只希望自己真的只是從昨天下午昏睡到了現在,而不是從“前幾天”一直睡到現在了,
“這里大概是妓院,難道他叛逃到了娼館?或者說這里就是娼館的領地?不管如何,我現在得找機會扯開這堆東西……”
嘎吱嘎吱的聲音輕輕的響起,那是陳在嘗試掙脫身體上的膠帶時發出的噪聲。
“話說回來,那家伙看樣子是背叛了洛安會了呢……動機、後果未知,但我得注意避開他的雷區呢……這種時候就開始希望能讓星熊來幫我潤色一下啊……見鬼……為什麼膠帶擰在一起就會這麼難弄……”
陳的掙脫過程並不順利,被撕扯了幾下的膠帶開開始相互粘連,並且漸漸的擰成了一股遍及陳全身的束縛力。被橫向或是縱向拉伸過的膠帶並不像影視劇里的那樣直接應聲斷裂,反而發生了形變,變成了像是黏在鞋底的口香糖一樣的甩不掉的煩人精。
噗 噗
那是利刃貫穿肉體的聲音
噗呲 噗呲
那是被撕裂的肉體與血管向外噴灑液體的聲音。根據聲音判斷,被切開的大概是一條動脈。
“唔嗯?!”
陳的眼睛因為眼前發生的一幕而驚得瞪圓。
一大團血液飛散在空中,隨後一邊發出了啪嘰啪嘰的聲音一邊灑在了前面的地板上,就像是住家潑在地上的髒水一樣。
“咳啊——”
伴隨著幾大簇煙花一樣的血液的林在下一秒也映入了陳的眼簾。黑色的長衫不再能遮掩血色的汙漬,敵人的攻擊卻仍未停歇。
“短刀!”
盡管林已經在渾身的刀傷中進入了走馬燈的狀態,但陳依然能從他身邊看出襲擊者的真容,而下一秒,那個襲擊者也已經衝到了她的眼前。
“早上好啊,龍門近衛局的陳警官,我們也算很久不見了啊~”
魯珀族的紅發女性從漆黑的面罩下打著招呼,
“上次還是在一年多以前吧?你那時候還穿著人字拖追我呢,怎麼現在被人捆成這樣放在妓院了呢?”
“嗚嗚!”
陳的怒氣繼續上升著。眼前的人毫無疑問就是自己追查了很久的弑君者,空氣中彌漫著的血腥味就是她的危險系數的最佳評判指標,而她右手的短刀也配合著把還帶有些許體溫溫度的林的血液丟棄到地面上,並發出了危險的滴答聲。
“咕唔!嗚嗚!”
陳劇烈的掙扎著,自己這幅任人魚肉的狀態自然是無法應對弑君者的,特別是當她看到了弑君者從懷里掏出的一支吸滿了乳白色液體的針筒之後。雖然不確定是不是同一種內容物,但短時間內第二次見到這種顏色的藥劑的陳自然會聯想到上一支讓自己陷入昏迷的麻醉劑,
“咕嗚嗚嗚!”
“省省吧陳警官,你就不覺得你掙扎的樣子和一個人畜無害的小女孩沒有任何區別嗎?而且啊,整合運動的幾個干部都一致同意,你這樣的人,越掙扎越讓人想迫害你。一動不動的裝死可能還能好點”
弑君者一邊稍顯笨拙的用單手把針筒握住,一邊輕輕的推出了針筒里的氣泡,習慣直接抹殺目標的她肯定不熟悉也不理解這種軟弱但浪漫的方式吧,
“好了陳警官,老老實實睡一覺吧,別讓我不好做哦~”
弑君者手中的針管漸漸的逼近,又漸漸的消失在陳的視野上端。雙手被捆在後腰附近的陳也的確沒有能讓弑君者下針的地方。在咂了咂嘴之後,弑君者決定把這管藥液打進陳的頸部靜脈。
“嗚嗚嗚!唔!”
另一方面,陳的掙扎也從做開始的毫無阻攔而變得有所顧忌。畢竟一根針已經抵在了自己的脖子附近,就算再怎麼想要掙扎,陳也本能性的為了提防被這根針有意或是無意間刺穿氣管而收斂起掙扎的幅度,更何況她的身體狀況也並沒有比幾分鍾前好多少。冰涼的鋼針頂在了陳的頸部,盡管陳並不想認命,但現在似乎除了接受自己的命運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方法了。
………………
“這也是我的命運嗎……”
看著弑君者因為興奮而挑起的眉毛,陳憤恨的閉上了眼睛,就算自己很快就要昏迷,她也不願意讓弑君者看到自己上翻的眼睛。她用力的閉緊眼睛一方面是為了自我欺騙、讓自己暫時性的忘記自己這個屈辱而無助的境地,另一方面也是期望自己的雙眼能夠在昏迷時老老實實的閉緊,不要擅自開窗。
…………
……
啪!
玻璃破碎的聲音打破了兩人之間的詭異寧靜,也讓陳睜開了雙眼。視野中,一抹熟悉的綠色搭配著大塊的黑色快速的橫跨了她的整片視野,而近在咫尺的弑君者則在最後一刻抽出了自己的手,以一個匪夷所思的後跳完成了規避。
“咕唔!”
自己的視野再次被黑色遮住,但這次並不是因為層層疊疊的睡意,而是由於那位破窗而入的隊友。
咣
名為般若的三角形大盾被插在了地面上,它的主人則像是一堵牆一般立在了陳的前面,用自己的身體護住了陳的身軀。
“沒事吧陳?抱歉我來晚了~增援馬上就到”
“咕唔!嗚嗚嗚!”
陳的悶叫聲中也不再帶有憤怒與絕望,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如釋重負的欣喜。
“少在那嘮家常了!別小看人啊!”
弑君者的身體附近漸漸放出濃煙,那是她從自己的口腔分泌出的遮蔽視野用的煙霧。如果是一般的干員的話,陳想必已經開始悶叫著提醒他注意安全了吧。但,眼前的是星熊。也許她無法跟上弑君者的腳步並將她制服,但她也不會被弑君者打倒。最差最差的情況,這也是一場沒有輸家的比賽,下一步只要等增援到位就可以了。
“陳,你沒被注射,放心,剩下的交給我吧”
簡短的對話讓陳明白了自己的處境。為了防止自己的身體認定了【被打藥了】的虛假事實而變得無法動彈,星熊在第一時間就和陳進行了狀況溝通,讓陳不會因為心理作用而喪失行動能力。很快,星熊的身形也被籠罩進了白色的煙霧中,只剩下朦朧的身形、偶爾迸出的火星和兩人的嘶吼還能從煙霧的那頭傳來。
“唔……唔……”
被晾在一邊的陳十分信任星熊的能力,而現在她又獲得了針頭這個足以切開膠帶的利器。在蠕動了幾次之後,陳已經將針筒握在了手里。不遠處的戰斗仍在繼續,這也說明了陳的大致安全。她也不用再擔心給突然出現的弑君者做嫁衣、讓對方直接把自己抓在手里的針筒扎進手腕的靜脈並直接注射的情景了。她一點點的用針頭在自己手腕附近的膠布上扎洞,並期望在隨後的撕扯中讓這段膠帶應聲斷開。
“咕唔!嗚嗚嗚嗚——————”
身下的床板突然展開,形成了一個秘密的通路的入口,而還沒能掙脫綁束的陳就隨著床板的向下傾斜而被倒進了地道中。或許是打斗中的兩人誤觸了機關,也或許是有人在遠程進行控制,但不管是哪一種,陳都已經從這間睡房里消失了,而正在為了陳的“所有權”而爭斗的兩人甚至沒有意識到漁翁得利的事實。
“嗚嗚————”
陳一邊哀鳴著,一邊在流淌著潤滑液的滑梯上滑行著。無論這個滑梯通向何方,陳都會驚訝於這個讓自己時而向下、時而向前的設計與能夠滿足這個設計的高低差。毫無光照條件的封閉式滑梯,或者說隧道內漆黑一片,長時間的漆黑滑行也讓陳失去了時間觀念和方向感。
“都這麼久了竟然還能繼續下降,我到底是從多高的地方開始滑行的啊……這是什麼!”
“咕唔!”
清涼的液體從隧道上端的噴水器向下噴灑著,而陳也從這股清涼中感受到了有些熟悉的氣息,陳確信自己不是第一次聞到這股味道。
“這股熟悉的氣味是……糟了……!是那次的!”
陳回想起了多年前的事情。那時的自己和同事在接到舉報後愣頭青一樣的衝進了一家可疑的店鋪,隨後便在與現在相仿的甜膩氣味中失去了意識。多年以後,相關的記憶已經被塵封,但自己的身體仍然會對這熟悉的氣味做出反應。
“不能吸入……可惡……雙手還被綁在身後……”
“咳唔!嗚嗚!”
陳本能性的想要伸出雙手捂住口鼻,但卻又再一次的意識到它們仍然被綁在身後。處在快速滑行與時不時的下落中的陳根本做不到憋氣抵擋,身體對於失去重心時的本能性驚慌是她無法抑制的,而驚慌的後果就是身體需要更多的空氣來應對可能到來的危險,殊不知已經到來的危險本身就是會隨著空氣逼近的……
“這藥效……還真快……該死……連這一步都能算到嗎……”
盡管不想承認,但陳已經從各處關節傳來的酥麻感預料到了自己的結局。這些被噴灑下來的藥水打濕了自己的衣物,並且會在接下來的很長時間里都呆在自己身邊,直到自己把這些揮發性的液體全部吸干,或者在吸干的過程中昏睡過去為止。上方的噴頭早已停止了工作,或者說也許自己已經通過了安裝了噴頭的區塊,而對方已經認定自己不會有任何翻身的余地了吧……視野始終是一片漆黑,而陳也漸漸的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是睜著還是閉著了。無窮無盡的隧道麻痹了陳的意識,讓她敏銳的辨析能力在這漫長的滑行中被消磨殆盡。潺潺的水流聲與自己的滑行聲在最初還因為有些新奇而可以引起陳的注意,而現在已經習慣了這些聲音了的身體已經把它們分類成無法屏蔽的背景音並加以忽略了。簡而言之,陳的身體與意識在漫長的隧道與從天而降的藥物的作用下已經變得麻木怠惰了起來,盡管不情願,但陳也已經對這種感覺十分熟悉了。
在滑行中飛濺起來的潤滑液偶爾會拍打在陳的臉上,讓陳的意識從昏迷的泥沼中上浮一些。
別撐了,撐不過的。
環繞在自己身邊的香氣依然沒有散去的跡象,而已經基本放棄抵抗,或者說失去抵抗能力的陳已經開始猜想這個香氣究竟是從哪幾種花香中提取出來的了。在這種對於無所謂之事的求索之中,陳的意識也被拖入了彌留的狀態。漸漸陷入半昏迷狀態的她已經失去了控制思考的能力,花香、香氣這樣的單詞在陳的腦海里像是幾顆流星一樣出現而消失,既沒有開頭也沒有結尾,就像是自顧自的蹦進陳的意識之後又自顧自的消失了的精靈一樣。
大量的液體再次被噴灑在陳的身體上,溫度之低、體積之大讓哪怕是漸漸劃入昏睡的深淵的陳都要清醒起來,用自己幾近停滯的腦袋思考一下這些液體的來意。
“大概……是……補藥的吧……真是的……”
昏昏欲睡的陳有些不滿的歪了歪臉,讓上面的液體流下自己的臉頰,
“我睡……我睡還不行麼……我又躲不掉的……”
意志完全被睡意征服的陳一邊嘟囔著自己的敗北宣言,一邊像是求饒一般的大口呼吸了幾口,而這也耗盡了她的全部力氣。
“咕唔!”
撲面而來的熱風再次驚醒了陳。視野內的紅光預示著高溫電阻絲的存在,也讓這一段通道得名為“干燥區段”。
“咕唔……唔?”
算是被熱風吹得有些回光返照的陳意識到了自己身體上的新伙伴。乳白色的纖維甲殼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爬上了自己的身體,哪怕是自己視野內的頭發或是領口都沒能幸免的被乳白色的纖維糊在了一起。
“什麼……鬼………”
對於目前的陳來說,高溫帶來的影響就是掛在塔身上的藥水被瞬間蒸發,並且被風干機的熱風拍在自己的臉上,並最終被自己盡數吸入。自己被打濕的衣物也在熱風的幫助下變得溫暖而干燥,讓陳感覺就像是在被陽光曬過的被窩里一樣溫暖愜意。在麻醉藥物與精神放松的雙重衝擊下,陳的意識還沒能掙扎幾次就沉入了漆黑的泥沼之中……
燥熱的風繼續吹拂在陳的身體上,越來越多的液體在高溫下完成了化學反應,在陳的身體表面形成了一層乳白色的膜。這些被大量噴灑在陳的身體上的液體所形成的白膜會盡量覆蓋住陳的身體,讓白膜下的正體不會被暴露給其他人。另一方面,從陳身下流出的液體與加熱裝置則會照顧好沒被噴灑到的另一半身體,使得陳完完全全的被包裹在了一只白繭里。這樣的處理方式一方面可以消除掉被正常人發現這種罪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可以依靠這些白膜束縛住那些還沒有失去意識的頑固的獵物,當然,陳警官自然不在此列,倒不如說如果滑道的設計者能夠看到陳酣睡的模樣與這只近乎完美的白繭的話,一定會露出欣慰的微笑吧。
“呀呵?想不到那座荒山上的機關還能捉到人啊?”
守在隱秘的隧道口的工人盯著這個新鮮產出的貨物評價道,
“好家伙,這還是個龍族?”
工人一邊用半干燥狀態的乳膠一樣的白色膠體幫助沒能完全覆蓋住陳的龍角的白膜完成他們的工作,一邊又把這些乳膠纏繞在這對龍角之上。在用小型吹風機進行干燥處理後,陳的龍角也變得無法辨認,看上去就僅僅是一塊長方形的凸起而已。一切能證明陳的身份的特征大概都已經被遮蓋在白膜之下,不管是她那對微睜著的白紅相見的眼睛還是那頭柔順的藍發都已經變得無法辨認。被完全麻醉了的身體自然是無法動彈,哪怕是那條尾巴也不例外。安分的躺在兩腿之間的尾巴自然也在白膜之下隱去了身形。到現在為止,陳還露在外面的部分就只剩下這雙穿著馬丁靴的腳了。
“誒呦我操,這怎麼還有個針筒扎老子一下?我日你媽……”
工人的粗口在他看到了針筒上 的字跡之後戛然而止,
“【麻醉劑,一針管夠】……現在的貨都自帶干糧了嗎?”
男人氣哼哼的踢了踢陳的雙腿,自然除了充滿彈性的觸感之外毫無反饋,
“我管你是死是活,敢扎老子,我日你媽”
男人一邊扒開陳的褲腳,一邊把鋼針扎進了腳踝處的青筋上,
“干完這批好收工,走著”
急著回家的男人飛速的推著針筒的活塞,乳白色的藥液不一會兒就被全部推進了陳的身體中。曾經被不常用藥的弑君者寫在針筒上的提醒用的文字成為了提醒工人把這只麻醉劑注入的體內的罪魁禍首,而已經陷入昏睡的陳到最後也沒能躲過這一支麻醉劑,更壞的情況是,被兩種藥效疊加的她的昏迷時間將會遠超過這兩種藥效本身的時間,無論前途是福是禍,陳也被迫決定先睡一覺再說。
“好家伙,這家伙還真不輕……”
在用乳膠包裹住陳的身子後,工人將這只完整的白繭碼到船艙里,與其他好幾只白繭並排放著。
“哼……呼……”
安靜的貨倉很快就被新朋友的鼾聲所打破,與陳有著相似處境的女孩們也在各自的白繭中昏睡著,只是遠不及陳的程度之深而已。
“可能藥打多了……算了,關老子鳥事”
急著回家的工人可沒有什麼睡眠癖好,他只關心這一船運到目的地能給自己幾個錢。在扣上暗門之後,工人在這層偽造的貨倉上堆滿了活蹦亂跳的鮮魚,完全抹消了女孩們的氣味與暗門的存在。工人撐起船,唱著漁歌,加入了其他同行的船隊。偽裝成打漁歸來的船隊延綿不絕,消失在了龍門的山水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