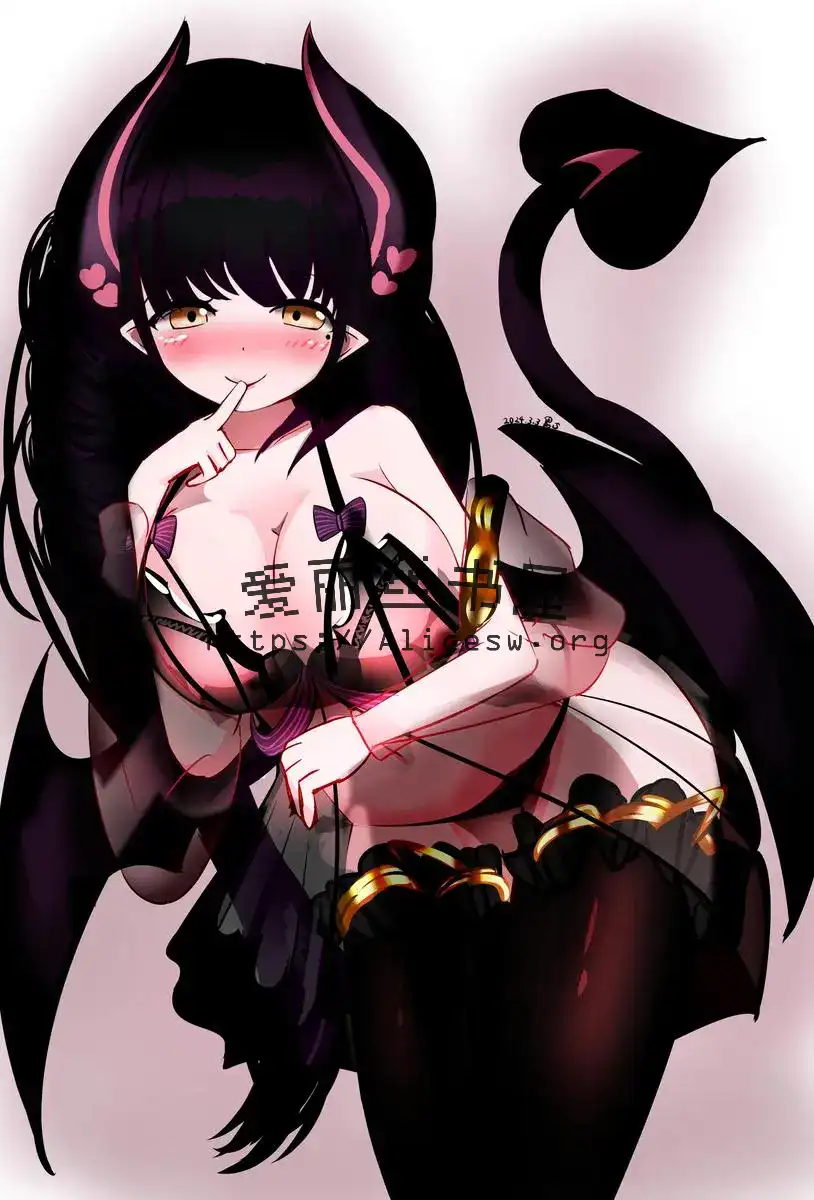瑞諾伊從昏迷中醒來,滿臉是汗。不久前,她剛剛誕下一名女嬰,但在長時間緊繃的神經終於得到放松後,她幾乎立刻陷入昏迷,沒有親眼看見自己孩子的機會。再次蘇醒時,她早已被推出產房,和另外幾名在此暫留的產婦一同稍作休息,等待下一個“生育周期”。
“水……水……”瑞諾伊用嘶啞的嗓子護換,一名護士立刻走到她身邊,遞上一杯溫水;溫水帶著些許咸味,她知道這是為了補充她在分娩過程中流失的電解質。
“感覺好些了嗎?”護士拿著一塊手寫板,記錄著什麼東西。瑞諾伊有些出神:她還是沒法適應孩子一出生就被奪走的事實。這感覺就好像什麼東西被偷走,不,是某個極其重要東西被活生生挖去,留下的傷口不斷流淌著鮮血,那是世界上最慘烈的痛,能致人於死地。
分娩是很痛的。市面上雖有抑制藥物,但為避免對嬰兒造成影響,醫院從來都不曾使用;更別提諸多後遺症,如情緒低落、身材走形。比生理痛楚更加殘忍的是心理折磨,她雖是孩子的生母,卻無法擁抱它:嬰兒出生後短短幾秒鍾便剪斷臍帶、用布包裹起來放進恒溫箱,在此期間她只能看到一團模糊的肉團,聽著它發出的哭聲。若像這次這樣昏過去,就連一面之緣都沒有了。她只能想象著嬰兒皺巴巴的小臉,幻想自己在它的陪伴下度過幸福的余生。
是啊……余生。她的余生本來不該是這樣的。
“敞開衣領”護士命令道。在瑞諾伊恍惚恍惚之時,護士已然等不及:她伸手解開瑞諾伊身前的扣子,露出雪白的胸脯;兩顆乳房飽脹著,蘊含著 豐富的乳汁;幾個月來的催乳術卓有成效,只輕輕一碰,乳汁便從乳頭噴涌而出,濺射在被子上。護士用一管儀器在她的乳頭邊沾了些乳汁,幾秒後儀器上的綠燈亮起,伴隨發出輕微的滴答聲。
“奶水質量……合格,允許使用……”護士又在手寫板上記錄下什麼東西,然後將一個吸奶器交給瑞諾伊:
“從今晚開始吸奶,別餓著了孩子——我是說,客戶的孩子”
交代完,護士便離開瑞諾伊去照顧其他產婦。瑞諾伊拿起吸奶器,罩在乳汁流個不停的乳頭上,啟動。伴隨著單調的嗡嗡聲,久違的吮吸感再次攀上身體。乳汁被一股腦兒地從乳頭中吸出,流入奶瓶;吸奶器像是個貪婪的黑洞,幾乎要將她的乳頭扯掉;不止一次,她在自己的乳暈上發現血痕,也許還有少量血液混入乳汁,但醫院從來都不曾在意,照樣將乳汁交給嬰兒們食用;在他們離開保育房之前的三個月里,這是他們唯一的食品。
另一名護士推動瑞諾伊的病床離開休息室。休息室外是一段開著天窗的走廊,自然光從頭頂照下,刺得她微微眯起眼睛;但她很享受這微弱的溫暖,相比於病房里慘白的燈泡,還是日光更令人安心。
為了保護孕婦脆弱的免疫系統不受病原體襲擾,整座醫院幾乎是全封閉的,只有日光平台和少數幾段走廊能看到外面的景色,且視角極其有限。這段走廊外是醫院附屬的小花園;不知為何,瑞諾伊突然對那一方天地起了興趣。
“能慢些嗎?我想看看那些花朵”瑞諾伊開口打破平靜。
於是護士的腳步慢了許多;瑞諾伊得以看清花園里的景色:藤蔓攀上醫院外牆,其間點綴著各色花朵;幾座支架橫亘在花園中間,上面結著些果實,也不知道能不能吃。幾名園丁在其中忙碌著,她們披著雨衣,噴灌的水花不時掃過她們的身體,但她們都彎著腰不為所動,專心地處理著手中的活計,也許是除草,也許是播種……
不等她將一切盡收眼底,護士的腳步恢復往日的頻率;依舊安靜、平穩,但花園里的一切都變得模糊,並且很快就被迎面撲來的牆壁所遮擋。在曲折的走廊里徘徊許久,瑞諾伊終於回到自己的病房;房間里還有另外三個女人,她們的預產期都和瑞諾伊差不了幾天,因此也都處於產後虛弱階段,正安靜地睡著。護士將瑞諾伊的床推到預定位置,鎖住輪子,然後靜悄悄地離開;期間兩人沒再有一句交談。在這個機構運行的一千多天里,大部分時間都這樣寂靜無聲。
她們之間也沒什麼好聊的。瑞諾伊是這里的老“員工”,所有人都對她了如指掌;她不是一個喜歡麻煩別人的人,總是會在自己能力范圍內把一切安排妥當,除非因疼痛或疲憊而動彈不得。至於她的身份,大家更是倒背如流:作為曾經的高材生,她的名字和頭像高掛在醫院廣告頁的正中間,以此宣揚代孕機構的“生產資料”有堅實的品質保障。
不少戰爭結束後涌現的新富對此趨之若鶩,他們無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沾一沾高智商人才的聰明氣,好擠進貴族圈子。
但醫院不可能保證每個孕婦都是狀元,因此大多數時候只能以次充好。這並不意味著其他孕婦都是大字不識的文盲,相反,能進入這里的女人最低也要有大學學位,只不過醫院所貪圖的並非她們頭腦中的知識,而是她們腹中的子宮;聰明的頭腦只是附屬品——唯一用途是提升商品的價值,豐滿的體態和美麗的相貌同樣如此。對於一些沒什麼文化、滿腦子想著性與暴力的客戶來說,也許後兩者還更重要一些……但無論如何,智慧與美貌並存的瑞諾伊都能穩坐“客戶喜愛榜”榜首,這麼多年下來,她竟然連一個完整的產假都沒休過。
一個月,這是醫院留給產婦的休息時間。但是作為搶手貨的瑞諾伊不敢奢求能夠休滿整個假期;事實上,只要不是分娩當晚被拖出去人工授精她就心滿意足了。這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醫院自有辦法:多種藥物通過口服、注射、皮膚或黏膜滲透的方式灌進身體,只需短短十幾個小時就能讓生殖器官恢復到產前水平,足夠容納新的胚胎。但這些藥物無一例外都只為生殖系統服務,至於對身體造成何等損害則完全忽視。
濫用藥物、連續懷孕對身體造成的極大損耗根本無法用吃和睡彌補,更何況時有時無的排異反應,讓她根本無法安眠。她的感官似乎已經紊亂:她需要捂緊被子、渾身發抖對抗寒冷,盡管房間里的溫度已經調到最高。同房的女人們都很照顧她,依著她的指示將溫度調高;但結果卻是四個人都不好受:三個熱得汗流浹背,剩下一個依舊冷的發抖。
吸奶器的嗡嗡聲仿佛能夠催眠,困倦交加的瑞諾伊昏昏欲睡。生孩子不會因為次數增加而變得熟練,每場生育都是在鬼門關邊上游走。她真的很怕哪次生育過程中出現差錯而死掉,沒了媽媽的孩子該多麼孤獨!雖然之前幾胎也沒有在她身邊久留,但是生與死是不一樣的;她要堅強地活下去,哪怕只是為了遠在天邊的孩子。
是啊,孩子們。他們現在都在哪兒呢?瑞諾伊知道她的客戶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富豪,但也僅僅是聽說——醫院包辦一切對外聯絡,她自己根本沒可能聯系上孩子的父母。就算聯系上又能怎樣?乞求他們把自己從醫院里贖身嗎?且不說那對父母是否願意為一個陌生女人出這筆錢,單看她自己的條件:臃腫、松垮,幾乎沒個女人樣,出了醫院又有誰能看上她呢?
說起來……自己的人生應該是什麼樣子?戰爭以前她曾對此有清晰的規劃:進入頭部企業工作,賺大錢,和自己愛的男人結婚,生幾個娃兒,看著他們健康成長。又或者,獨自一人工作到中年,攢夠養老錢後躲到某個地圖上都找不到名字的村莊里,蓋個大別墅安享晚年。但無論哪種,都絕不是在全封閉的大樓里當一個生育機器、產奶機器,這樣活著連作為人的尊嚴都失去了。
退休?瑞諾伊沒有想過自己退休的圖景。代孕母親真的有退休一說嗎?等她老去,到沒法安全生育的年齡,醫院會不會如同處理死胎和醫療廢品一般把她隨意處理掉?一想到自己的結局可能是被溶解、切碎、倒進下水道,她就感覺渾身戰栗——多麼殘忍的死法。
恍惚之中,瑞諾伊聽到門外傳來叫罵和呼喊,伴隨著物體被打碎的聲音。同房的一個女人被吵醒,疑惑地看向瑞諾伊;得到她“我也不知道發生何事”的回應後,女人從床上爬起,穿好拖鞋,准備出門察看。
門被猛地撞開。“都給我從床上滾下來!”推門的人說。她身穿短襯衫、百褶裙和皮鞋,裝束簡直和瑞諾伊的學生時代一模一樣;唯一的不同之處是她手中的長棍,半晌瑞諾伊才意識到那是一杆槍。
難道這就是女人們之間討論的“內戰”?她只從只言片語中了解到這場戰爭極其慘烈,但兒童兵的存在還是遠遠超出她的想象。
另外兩名產婦也被吵醒,皺著眉看向門口;看到門口站著的是個小孩時,她們的眉頭又都舒展開來:
“喲呵,這是誰家的小屁孩,怎麼闖到這種地方來鬧惡作劇了……”
話音未落,站在門口的少女快步走到她身邊,扇了她一巴掌:“快點從床上滾下去!現在這張床是老娘的了!”
瑞諾伊扭頭看向門口,果然,正如她聽到的那樣,另外幾名穿著學生服的少女正膽怯地看向房內;她們身邊也各有一杆槍。
女人終於被揪著耳朵扔到地上。少女翻身上床,向門口的伙伴招呼,叫她們也進來。
“可是……這樣不好吧”門外的少女提出異議。
“你們看誰不同意就開槍打死她”少女用手中的槍對准瑞諾伊,隨後口中發出啪啪聲,像是要對她開槍一般。瑞諾伊害怕極了,她強撐著從床上爬下,然後扶起摔倒在地的女人一同向後退,直到抵住牆角。
“還有你們兩個!”少女蠻橫地說,用槍指著仍留在床上的女人;她的槍好像有魔力,能把女人從床上卷走。不一會兒,四張床上躺著的就不再是產婦而是少女士兵;她們在溫暖柔軟的床上打滾、休息,而體質虛弱的產婦們只能靠著牆、互相攙扶才能勉強不摔倒。她們眼睜睜看著這群小鬼奪去本應屬於她們的位置,咬牙切齒卻無可奈何。
“看什麼看?滾出去!”少女大聲呵斥,不等她舉起槍,女人們便驚慌逃竄,推搡著離開房間,連門都忘記關上。她們身後繼續傳來少女的叫罵;誰都不曾預料她一個孩子怎麼能說出那麼肮髒的話語。
可是門外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走廊里人滿為患,每個病房的女人都被趕出房間,騰出地方供蠻橫的少女休息。其中一些女人挺著大肚子,懷孕使她們虛弱不堪,不得不坐在長椅或地上喘著粗氣。地上依稀可見血跡,瑞諾伊在心中默默祈禱,希望不要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脫離人群聚集之處,瑞諾伊發現一張無人問津的空病床;同房四人屁股貼著屁股地坐上去,床腿發出不詳的吱嘎聲,但好在最終撐住女人們的重量;雖然擠在一起很不舒服,但總比站著好。走廊里冷氣很足,坐下後不免感到寒冷;她蜷縮成一團,瑟瑟發抖,牙齒也不住地打顫。
怎麼越來越冷了……瑞諾伊感覺自己好像回到多年前的那個冬天。那時的她一貧如洗,對未來的期望完全幻滅。飢饉脅迫下,她不得已走進醫院,出賣身體換取活下去的機會。如今想來,自己和妓女又有什麼區別呢?無非是進入妓女身體的是男人的生殖器,而進入她身體的是注射器罷了。
“披上這件”一張毯子蒙在瑞諾伊身上,她抬頭看去,是一名男青年。他穿著筆挺的軍綠色制服,胸前的綬帶繁瑣而浮夸,從胸口一路排開到腰間的銀色徽章閃閃發亮,簡直像是一件甲胄。
“你是誰……”瑞諾伊的聲音低到幾乎聽不見。
“我是薩治北境國軍官,負責指揮這支連隊;請您諒解孩子們的淘氣;事後我會批評她們的”
“你是……薩米萊人?”瑞諾伊繼續問。
“正是,親愛的女士,您可真細致。我學習聖凱妮亞語已經有十年之久,自認為和本地人發音沒什麼區別,請問您是如何分辨出的?”
“你的語調中有不可磨滅的特征”瑞諾伊虛弱地笑笑,“我也學習過薩米萊語,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發音習慣一聽便知”
“原來是這樣”男青年沉思少許,“如此聰明的女士,怎麼會在這樣一家機構‘任職’呢?難道自由市提供的工作崗位不符合您的胃口嗎?”
“好意思說!”另一個女人打斷他倆的對話:“要不是你們國家侵略咱,我也不至於來這種鬼地方!”
“就是,再說可別忘了當年是誰把聖凱妮亞人趕出自由市的!”
“抱歉我對那段歷史不太熟悉,而且我也沒有參與驅逐聖凱妮亞人”男青年收起笑容,“這樣汙蔑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恐怕不太禮貌吧?”
“有什麼差別呢,你不一樣在享受在聖凱妮亞的特權?”第四個女人也參與進來,“我老公可是被埋在萬人坑里了!你作為一個男人不被殺掉,不就因為你那薩米萊人身份麼……”
面對三個怒氣滿滿的女人,男青年有些尷尬;但他很快便恢復了笑容,向最近的房間招手:
“去把你們隊長叫來”
於是那個搶占瑞諾伊房間、穿著水手服的少女來到男青年面前。瑞諾伊等人這才知道少女為何表現得那麼囂張:她竟然是管著這麼多人的士官,在連隊中的地位只在男青年之下。
“這三個女人想要破壞薩米萊和北境國之間的關系,立刻帶上幾個隊員,把她們送去槍斃!”
女人們哭喊著、掙扎著,但無一例外都被捆得結結實實,押到醫院的花園里。曾在此勞作的園丁被驅離,眼睜睜看著自己的成果被搗毀、重新平整成刑場。女人們跪在地上,身後站著身穿學生服的少女士兵。
“從今天開始”男青年大聲說,“這所醫院,以及整片地區,歸屬薩治北境國管轄!
“我的隊伍會時刻留意你們的言行,若發現有任何人有損害薩治北境國利益的行為,她們的下場可以作為參考”
說罷,他揮下手,爆響從女人身後傳來,九顆子彈整齊地射入三個女人的身體,她們慢慢向前趴下,其中一個還打了個滾;在女人的抽搐中,血泊在她們的胸前慢慢擴散,染紅了病號服。
第一次目睹死亡的瑞諾伊被嚇得目瞪口呆,定在原地一動不動。在少女士兵推搡著其他女人回到醫院里時,她還呆站在原地。最後,一名少女士兵拉著她的胳膊,想把她送回醫院;瑞諾伊卻不知從何處有了勇氣,竟掙脫她的手,向被槍決的女人走去。少女剛想喝住她,便被男青年抬手阻止;瑞諾伊猶入無人之境,緩慢但順利地走到女人身邊。
她蹲下,用身上的毯子蓋住死去女人的面部;其中一個還半睜著眼睛,眼中滿是驚恐;瑞諾伊便幫她闔上雙眼。淚水不住地流下臉頰,滴落進泥土里。她們住在同一屋檐下已經有五年,對彼此的了解深入骨子里,就像家人一樣;在這個破碎的世界中,能有這樣親密而互相照顧的家庭是多麼幸福……可是,這一切都被打破,僅僅是因為薩米萊人占領了這里,而她們說了些不該說的話。
“緬懷完就走吧”身邊傳來男青年冷峻而毫無感情的聲音。瑞諾伊還想陪她們一會兒,但少女士兵已經開始拉她;這次,瑞諾伊沒能抵過少女們的力氣:六個少女一齊把她舉起來,無論她如何掙扎都不放松,直到把她送進醫院大樓里。磨砂玻璃門關閉後,她就再也看不到躺在地上的女人了。
一切照舊,只是多了日常操練和聒噪的少女。她們擠占著孕婦的床位,和孕婦爭搶食堂餐食,動輒對孕婦破口大罵,但好歹收斂了些,沒有動手打人。在院長的懇求下,醫院爭取回來一些床位,但遠不夠容納所有孕婦;院長表示這已經是她所能爭取到的最大福利,但多達三成缺乏床位的孕婦顯然不這麼認為;於是床位只能分給那些臨產的孕婦使用,畢竟她們最為脆弱。
意料之中,瑞諾伊被安排打地鋪,因為她暫時沒有懷孕;至於她還在產後恢復期這件事則無人關心。在醫院里根本就沒有什麼產後恢復期概念,否則也不會強迫孕母們時隔不到一個月就再次懷胎了。
醫院的生意自然受到戰爭影響:瑞諾伊奇跡般地度過產後的第一個星期,沒有被送去受孕。雖然還沒有度過產後最虛弱的時期,但能休息這麼多天,對她連軸轉了幾年的身體來說可謂福音。唯一需要擔心的是:若過了一個月還沒人找她代孕,她的下場會是怎樣……
表面收斂的假象之下,是少女們蠢蠢欲動的破壞欲。她們已經在戰場上見過太多死亡,甚至很多人曾親手殺死敵人,自然提不起什麼對生命的敬畏。一連幾天,被槍殺的女人都是她們的話題中心,那幾個親手執行槍決的少女更是成為眾人的焦點,獲得英雄般的禮遇。
對此,男青年沒有加以阻攔;他聲稱少女想說些什麼是她們的自由。這一番狡辯讓瑞諾伊憤恨至極:一邊說著少女們可以不受管束地大放厥詞,另一方面卻把她的舍友殺死?
“你沒說錯,薩米萊人就是要比聖凱妮亞人更高貴”那青年斜著眼睛瞧著她,“你有什麼要反駁的嗎?我希望你更惜命一點,你的那幾位朋友還曝屍院子里呢……”
瑞諾伊忍著憤怒的淚水被少女士兵們推開;在她身後,男青年放聲大笑:
“你很聰明,不會因為這點小事把命丟掉”
……
如果只是言語上的羞辱,瑞諾伊倒還能忍受;她無法接受的是少女們犯下的罪惡:在這一片無約束的小天地,少女們仿佛被放出籠子的瘋狗,瘋狂地啃咬周遭的一切,醫護、孕婦乃至嬰兒都沒能逃脫魔掌。隨著反對她們侵占床鋪的醫生、護士和孕婦被槍殺,所有人都沉默寡言;少女們厭倦了這種沉默,便將目光轉向保育房:哭泣的嬰兒是她們唯一能聽到的聲響。每時每刻都有幾名少女在保育房外轉悠,想趁護士的疏忽溜進去肆意破壞。
瑞諾伊的神經幾乎緊繃到極限:在她內心深處仍無法說服自己所生下的孩子和自己沒有任何關系。每次送走吸出的乳汁,她都會站在保育房附近,緊張地與少女們對峙,同時悄悄觀察自己的乳汁被送到哪個嬰兒手中;遺憾的是,她的乳汁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目的地:或許是為了增強嬰兒的免疫力,醫院會把孕婦們的乳汁混合起來給她們食用。
她也曾試過向護士請求進入保育房見自己的孩子一面,但被拒絕;護士的理由是若允許她進入勢必會造成大規模的恐慌。
在反復懇求無果後,瑞諾伊只得返回自己地鋪邊默默流淚。夜里,她從噩夢中哭著醒來,在夢中,她的孩子被人搶去,她在奪走自己孩子的身影後面追著,雙腿卻如同深陷雪地,每邁出一步都要付出極大力氣。最終,身影消失在風雪之中,她再也沒能追回自己的孩子。
轉機發生在薩治北境國軍隊占領這里後的第八天。少女們終於按耐不住性子,策劃衝擊保育房;她們囂張到扯著嗓子爭吵如何規劃進攻方案,但瑞諾伊再明白不過,面對手無寸鐵的醫護,所謂進攻將會是一場一邊倒的血腥屠殺。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這場混亂中受到傷害,毅然推開院長辦公室的大門,向院長請求從保育房中帶出自己的孩子。
院長也很為難:繼續拖延肯定不是辦法,延遲交貨不過幾天,醫院便已蒙受可觀的違約金,若這種狀態持續,必然會造成資金鏈斷裂,到時候連食物供應都會成問題。再說,保育房門外的少女蠢蠢欲動,引爆衝突只是時間問題;面對少女們手中的槍支,醫護沒有任何勝利的可能。若嬰兒被成規模殺害——那可真是最惡劣的情況——醫院被迫解散也非不可能之事。無奈之下,院長只得同意瑞諾伊的請求:允許她把孩子接出來藏好。
“請務必保護好她,有您的女兒在,我們就能宣傳稱我們有能力保護最珍貴的資產……”
“您准備放棄其他的孩子嗎?!”
“我們不可能大規模轉移嬰兒!”院長極力壓低聲音,避免被附近游蕩的少女聽見,“只缺少一個或許不會引起她們的警覺,但是大規模分散開的話……”
“這也太冷血了……”
“你以為我不想保住醫院的資產嗎?這可是我的全部身家!面對這種橫禍,你又有什麼奇思妙想?”
於是瑞諾伊接受了院長的方案:至少保住一個嬰兒。一名護士帶領著她,穿過不安的人群,走進保育房;為了掩人耳目,院長還特地安排了一群護士帶著孕婦擋在保育房和少女之間;但毫無疑問,一旦衝突爆發,她們將是最先受傷的。
“她們知道她們可能會被打死嗎?”
護士沒有回答。她腳步匆忙,瑞諾伊氣喘吁吁,幾乎跟不上。
“停下……停下!”瑞諾伊抓住護士的手,但還沒等護士轉過身,她便聽到刺耳的電流聲——
“聽到廣播的各位,請停下手中的一切工作”
是個清脆的男聲,毫無疑問,是男青年的聲音——他可是這里唯一的男人了。
“我對貴院的工作表示理解和尊重,但是本人依然需要行使作為薩治北境國軍人的職責,也就是清除敵人、維護國家利益。
“我從未參觀過貴院的保育房,那是個很機密的地方嗎?抱歉,我不這麼認為。嬰兒固然需要悉心呵護,但貴院的做法是否有些偏激?貴院只是一個代孕機構,不應存在任何不能對我軍開放的地方,不是嗎?
“我命令連隊……組成戰斗隊形,向保育房方向進攻……記住,我們的目的是保育房,不想死的就給我讓路,否則,別怪子彈不長眼,完畢”
瑞諾伊渾身發抖地聽完男聲廣播,她沒想到,男青年竟會下達這樣的命令。沒有時間思考,護士拽住她的手,帶她小跑起來。瑞諾伊雙腿無力,幾次要摔倒在地,都被護士撐住;最後,護士幾乎是背著她一路跑進保育房。
瑞諾伊終於看見她心心念念多年保育房的內部:成排的恒溫箱整齊擺放,多數中都躺著一個嬰兒;儀器的滴滴聲平穩地傳來,仿佛暴風來臨的前奏。唯一與她想象不同的是保育房里沒有繁忙工作的護士,大概是都被調去堵門了吧。
“這扇門擋不住她們多久”護士手忙腳亂地鎖上門,拿起名冊尋找瑞諾伊的嬰兒。嬰兒們正在酣睡,卻被護士的動靜吵醒,開始咿呀。趕在嘈雜演變成哭鬧大聯歡以前,護士將一個襁褓中的嬰兒交給瑞諾伊。
“這就是你的……”
瑞諾伊終於抱上一會兒自己的孩子,淚水不住地向下流淌。嬰兒身形圓滾滾,兩只小手蜷縮在身側,眼睛緊閉,平靜地呼吸著。瑞諾伊對嬰兒實在太過專注,連護士叮囑她的話都沒聽進去多少。
“是一名女孩子,多可愛啊……”
是啊,自己有了一個女兒。瑞諾伊抱著她,輕微顫抖、搖擺,口中唱著不成調的兒歌,眼淚止不住地流淌。
“……這里還有些母乳儲備,她一醒來就用這個喂她……你知道如何防止哭鬧嗎?是的,就像這樣……”
瑞諾伊回過神來時,護士已經將放進冷藏箱的母乳交給她:“快拿上!去隔壁的衣櫥里躲一躲,我去拖住她們!你要記住:千萬不要發出聲音!”
瑞諾伊被推搡著,擠進又黑又狹窄的衣櫥。嬰兒依舊安靜,希望她能永遠安靜下去——至少在危機解除之前;瑞諾伊艱難地把箱子放在地上,然後緊靠著衣櫥隔壁,以極其難受的姿勢稍作休息。
不遠處傳來零散的槍聲,瑞諾伊一驚:沒想到衝突這麼快就爆發。她在心里默默祈禱不要有更多傷亡,但她也知道這是徒勞:她什麼都改變不了。
保育房的大門被暴力撞開,警鈴大作。熟睡的嬰兒被驚醒,哭喊著,伴隨刀劍揮舞的金屬砰擊。殺戮開始,哭喊如同瘟疫般在嬰兒中擴散開,讓少女們無比煩躁;她們大吼著將嬰兒一個個殺死:用刺刀、用子彈,甚至直接把嬰兒扔在地上……
瑞諾伊的心在滴血。仿佛被殺死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孩子;她用力捂住自己的嘴巴,想要抑制哭泣,但眼淚還是不爭氣地流淌下來,滴落在嬰兒的被褥上。長時間抱著嬰兒是很累的,衣櫥里空間又十分狹小,她感覺自己就象是被裝進棺材里一般難受。究竟要躲藏到什麼時候?那個護士會不會已經死掉,如此便沒有人知道她的藏身之處,她就要被餓死在這里了……越是細想,瑞諾伊就越感到絕望和寒冷。她咬緊牙關,用手臂撐住衣櫥隔板,避免自己發抖。
但寒冷不會因此停止侵襲,更何況她正處於幾乎絕對黑暗的環境里。瑞諾伊驚恐地發現自己竟有幽閉空間恐懼症,四周的一切都好像正在向她壓下來,將她擠成齏粉。恐懼之中,她根本無法控制自己的呼吸頻率,急促而粗重的喘息驚醒了嬰兒,她開始無法控制地哭泣,慌亂之中,瑞諾伊把大半瓶奶倒在她的臉上更加劇了這種聲響。
衣櫥里的響動被少女們捕捉到,她們舉起槍對准整排衣櫥:
“那里有誰,快出來!”
男青年撥下少女手中的槍,自己走上前,挨個衣櫥查看。瑞諾伊聽著衣櫥門被打開的吱嘎聲,絕望地屏住呼吸,但最終還是逃不過被男青年發現、從衣櫥里拽出來扔到地上的命運。
少女們圍著瑞諾伊瘋狂地吼叫,她們在喊什麼?讓自己放下手中的嬰兒?瑞諾伊卻無意識地將嬰兒抱的更緊,在她的潛意識里,懷中的嬰兒是極其重要的東西,絕不能松手。
男青年撥開正在對瑞諾伊拳打腳踢的少女們,扶起她的身體;瑞諾伊的一只眼睛腫脹著,無法睜開,鼻血流淌的到處都是,嘴角也被弄破,滲出殷紅的鮮血。懷中嬰兒倒安靜了不少,是她的母親用身體護住了來自外界的擊打。
“放開手”男青年平靜地說。
瑞諾伊恐懼到忘記說話,一個勁兒地搖頭。淚水順著臉頰流淌,但她不敢用手擦拭。
在多次命令沒有得到回應後,男青年放棄說服她,轉而指揮少女們把瑞諾伊拉向保育房外。少女們粗暴地拉扯著瑞諾伊的衣服,直到將她的病號服扯破;瑞諾伊徒勞地掙扎著,但並沒有松手去抓周圍的東西;她似乎已經與懷中的小生命融為一體,無法再被分開。
一路上她看見的殘忍景象已經無法用語言形容:保育房滿地是鮮血,刺刀扎穿嬰兒的身體、子彈打碎他們的頭顱,又或者干脆被切成幾段,殘肢和內髒隨意灑在地上;護士倒在門邊,臉淹沒在自己的血泊里;她身上中了多少槍?瑞諾伊無法知曉,反正整套護士服都被鮮血染成可怖的深紅色……門外的殺戮雖然少很多,但並非不存在:臨近生產的孕婦被推倒在地,粉紅色的羊水流淌出來,但孕婦已經不再嚎叫,她大張著眼睛和嘴巴,還保持著臨死前的驚恐;醫護在她身邊徒勞地搶救著,但誰都知道,即使把嬰兒搶救下來也只可能是死胎……還有幾名醫護被槍殺,她們的屍體被推到一邊,留下駭人的血跡。踩在血跡上很容易打滑,瑞諾伊好幾次差點摔倒。
就這樣,瑞諾伊被一路拖著來到花園里。被槍殺的女人們還躺在花園中間,她們的屍體已然腐爛,蒼蠅在其上飛舞,蛆蟲在肌肉間蠕動,只看上一眼都會令人干嘔。
少女們把瑞諾伊丟在女人屍體旁邊,任由她在恐懼中顫抖。接下來就是槍決了吧……瑞諾伊恐懼地想著,用自己的身體包裹住嬰兒,好像這樣就能為她擋住子彈似的。可是,少女們卻紛紛後退,並沒有對她舉起槍。
男青年上前一步,抽出腰間的佩刀。刀刃閃著寒光,令人本能地感到恐懼。
“最後一次警告:放下嬰兒”
一如既往,瑞諾伊搖著頭拒絕;她已經恐懼到沒有沒有辦法說話,牙齒緊咬著舌頭,幾乎把舌頭咬破。她緊抱嬰兒的力氣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嬰兒都因呼吸困難而再度哭泣。慌亂之中,瑞諾伊不知怎麼著,竟然開始解開扣子;男青年停下手中的動作,饒有興趣地看著將死的女人在慌亂之中的行為。
她竟然開始喂奶。她慌張地把嬰兒湊到自己的乳房邊,想讓嬰兒含住正在流淌乳汁的乳頭;但是她顯然對此沒什麼經驗,嘗試了好幾次,除了把乳汁噴灑到嬰兒臉上以外沒有任何成果。不遠處傳來少女們的嗤笑,令瑞諾伊更加緊張。她想要證明自己是個好母親,到頭來卻一場空:既沒有育兒經驗,也沒法保護孩子……
男子看夠了這荒唐的表演,叫來一名少女抓住瑞諾伊的頭發,迫使她低著頭露出脖頸。但盡管如此,瑞諾伊依然沒有放棄嘗試,她用顫抖的胳膊抱著嬰兒到胸部,希望她能在自己死掉以前喝一口真正的母乳。
男青年高舉佩刀,刀刃的寒光在地上投下閃亮的光影,但瑞諾伊卻從未感受過如此平靜。刀落下的瞬間,時間好像凝固。她的眼睛緊盯著地面,余光里,是襁褓中的嬰兒、圍觀的少女、孕婦和醫護,以及男青年軍綠色的長褲。自己終究是一個失敗的母親啊……她想要長嘆一口氣,卻感受到後頸的疼痛;她猛地收縮脖頸,卻感覺身體一輕,下巴落進土里。半秒鍾後她才意識到發生了什麼:自己已經身首異處。在她看不見的地方,無頭屍體正在掙扎、抽搐、踢蹬,飽滿的乳頭繼續分泌出乳汁,少許流淌到嬰兒身上,但是更多的則融進泥土中。
一個少女抓著她的頭發,拎起女人的頭顱。女人的眼球不停地轉動,想弄明白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看到自己噴涌著鮮血的斷頸時,她露出難以置信的神情,大張著嘴巴,眼淚幾乎要從眼眶里溢出。但是隨著血液流干,她的表情最終歸於平靜,眼睛半閉著,露在外的一縫瞳孔已經不再有光澤。
嬰兒被保護的很安全:母親被斬首的瞬間,她的腦袋完全被母親的軀干擋住,這一刀僅僅要了母親的命而已。母親的屍體倒地後依然呈現抱緊她的姿勢,連鮮血都沒濺到她身上多少。
女人的無頭屍體尿液失禁、乳汁四溢,顯得肮髒又淫靡。自始至終,她的雙臂都沒有挪動分毫,似乎已經固定在抱著嬰兒的姿勢上;倒是雙腿踢了好一會兒,除了踢掉鞋子、弄髒雙腳以外,還把褲子褪到腰肢以下,以至於站在她身後的男青年能清晰地看見她的股溝。
男青年踢著瑞諾伊的身體,讓她仰面朝上。女人的乳房攤開,變得扁平了不少,勃大的乳頭依然流淌著溫熱的乳汁。嬰兒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危險,眨巴著大眼睛,一動不動地看向母親的乳房,伸著小手,好想要將乳頭握在手中……
佩刀再次劈下,將嬰兒一刀兩斷;這一刀力道之大甚至貫穿了女人的肋骨,幾乎將她也切成兩截。已經不會再疼痛的女人自然沒有什麼掙扎,但是嬰兒的上半身從襁褓里脫落,揮舞著雙臂,在土壤里翻滾了幾圈後才死去。她死掉的位置距離母親不遠,清澈的大眼睛依然望著母親的方向;不知她小小的腦袋中會否疑惑:面前的女人、自己的母親,為何一動不動……
後記
男青年找來一根木棍,將瑞諾伊的頭顱插在上面,擺在她的裸屍旁邊。在薩治北境國軍隊統治醫院所在地域的幾個月內,她的頭顱會慢慢腐爛,直到化為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