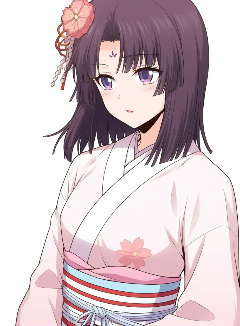第3章 第二章 乳環
難得我會被俾斯麥親自叫過去,這不禁令我驚訝,過去俾斯麥對我一直是極為性冷淡的態度,但是當我提出記錄酷刑的想法後,她似乎熱心了很多,除了上一次帶我去刑房和主動幫我聯系德意志外,也總會搜找一些資料給我。不過她也確實很忙,想要讓她給我講述一些實例也找不到時間。
今天似乎是她要到白鷹辦什麼事,大早上突然打電話希望我陪她。自從來到鐵血以來我就和無業游民一樣無所事事,難得能夠和她一起辦事,我倒也樂得自在。只是她說要給我提供素材,倒是令我十分好奇,就她而言大部分刑具之類都被銷毀或者封存了,一時之間拿不出手,也就是說這個刑具是她自己收藏的了,到底是什麼讓她得以收藏下來,還願意提供給我呢。聯想到她足控的癖好,怕不是什麼腳刑器具吧。
(實錄)
俾斯麥轉過身去,鞭打聲明顯比一開始小了不少,她用手勢阻止了量產艦們的輪流鞭笞,再看那個被大字型用鎖鏈捆綁的黑色短發的艦娘,後者很是和煦地衝她笑了笑,沒事人一般。俾斯麥不禁皺起了眉頭,因為對方的身上雖然被打得鞕痕交錯,但是很不明顯,倒像是用針尖劃過留下的白印,腫起來的都沒多少。也難怪打了半天連慘叫聲都沒有。
巴爾的摩,俾斯麥不得不親手抓來又親自審問的白鷹艦娘,說實話以巴爾的摩的特殊性確實必須要俾斯麥審問,不光是因為她在白鷹中的地位,最主要的是那明顯久經鍛煉鍛煉的身體,雖然沒有肌肉夸張的程度,但是身體的韌性是可以從那勻稱的身材中看出來的。事實上這一頓鞭打也足以看出,一般的酷刑恐怕對她效果不好。
俾斯麥用手勢讓量產艦們站到一邊,自己則走到巴爾的摩面前,冷冷地看著她。
“你好啊,”巴爾的摩笑了笑,甩了甩因為被抓捕而有些雜亂的利落短發,“一覺醒來居然就被一頓鞭子招待,這感覺還有點新奇。不過對我來說用處也就是勉強提神吧。俾斯麥,你要好好想辦法招待我啊,不然我都提不起興趣。”
俾斯麥扯動了一下嘴角,突然揮出了拳頭,巴爾的摩還沒有反應過來,兩側臉頰和腹部就已經各挨了一拳。不得不說俾斯麥畢竟是鐵血的首領,拳頭的力道非比尋常,直打得她頭暈眼花,胃液混著鮮血從口中噴出,在嘴角染出一片血紅。
“這樣可以嗎?”俾斯麥收回拳頭,靜靜地等待著巴爾的摩的回復。
巴爾的摩被打得弓著腰,連晃了好幾下腦袋才勉強從暈眩中回過神來,又清楚地感覺到臉頰的劇痛,不禁倒吸一口冷氣:“嘶……真不愧是鐵血的領袖,我還以為靠偷襲抓到我的人沒什麼本事呢。再來啊,我還是挺能扛的。”
“一般敢在我面前說這種話的最後都會後悔的求饒。巴爾的摩,我倒是挺佩服你,艦娘的身體很難像人類那樣通過後天鍛煉重塑,但是你卻做到了,看起來是很勤奮的類型。”俾斯麥這麼說著,卻是上下掃著她的全身,尤其是在腳上多停留了幾眼。正如巴爾的摩所說,俾斯麥她們是通過偷襲抓獲的她,那個時候巴爾的摩還在運動場上玩樂,現在也穿著一身相當暴露的運動裝,在抹胸和熱褲間腹部和大腿大片的裸露在外,腳上也只是運動鞋和黑色短襪。這樣子倒是完全把巴爾的摩那勻稱的身材和白皙的肌膚展露出來,並且更加讓俾斯麥好奇她的雙腳如何……雖然現在還不是時候。
“那真是可惜了,我大概會成為例外呢,求饒什麼的,總得讓我看看你有多大能耐吧。”巴爾的摩下意識地挑釁著俾斯麥,大概這種挑釁是家常便飯。只是她確實不夠了解俾斯麥,如果她能夠有所了解的話,至少之後能夠少受點罪。
俾斯麥淡淡地看著這個口出狂言的艦娘,一眼便注意到巴爾的摩肩膀上的傷疤,一個圓形的疤痕,還沒有完全長好。
“這是穿甲彈的傷痕嗎?我抓你的時候打的嗎?”俾斯麥歪著頭,用手觸摸著那道傷痕,然後抬起頭注視著巴爾的摩的雙眼,“傷還沒好呢。我看你是不疼了。”
俾斯麥的手向著量產艦伸出,後者心領神會地將鞭子遞給她。而就在俾斯麥握住鞭子的那一瞬間,巴爾的摩只覺得胸口一陣劇痛,差點沒讓她痛叫出聲,只見她的胸口處立刻鼓起一道腫脹的鞕痕,鮮紅而粗長,在一堆交錯的細小的鞕痕里顯得那麼突出。
巴爾的摩自己都不記得挨這麼毒的鞭子是什麼時候的事,只是現在她深刻地體會到了鞭笞的痛,哪怕是強忍著不慘叫出聲,冷汗也止不住地從額頭往外冒,巴爾的摩實在沒想到近期自己挨的最狠的打來自同一個人之手,還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她不禁苦笑出聲,看來自己有的受了。
“我這一下頂她們十下。”俾斯麥用鞭子把敲了敲巴爾的摩垂下的腦袋,然後把鞭子遞了回去,“好好受著,然後思考一下你該如何扛住我的拷打。以前沒人能收拾你不代表我不行,我有的是手段,能夠讓你久違地體會一下什麼叫做生不如死。”
“真是……難得我會感覺有點害怕。正義可不應該向邪惡低頭啊。”巴爾的摩苦笑著搖搖頭,然後挺直身子,“來吧,反正已經落到這步田地了,能不能拷打地動我就看你的本事了。”
“看起來你對自己還是很有信心,但是我明確地告訴你,你身上的弱點可比你想得要多,腋下,雙乳,外陰,雙腳,這些都是無論怎麼鍛煉都十分脆弱的地方,而且恰好也是我比較喜歡拷問的地方。怎麼樣,要來驗證一下嗎?”
俾斯麥當然沒有給巴爾的摩回答的機會,而是徑直走向刑房的炭火堆里,拿出一個燒的通紅的烙鐵,略微在水桶里過了一下,使得紅色變成了暗紅色,然後才走到巴爾的摩面前,也不等她說什麼,一下便把烙鐵按在了巴爾的摩的右腋下。
“嗚……啊——!”
饒是巴爾的摩意志堅強如鐵,也扛不住烙鐵烙在脆弱的腋下,沒忍多久便慘叫出聲,右臂瘋狂的抽搐顫抖。但是俾斯麥卻絲毫沒有放過巴爾的摩的意思,烙鐵用力地在巴爾的摩的腋下碾著,簡直要把巴爾的摩的腋下烙穿一般,當然過水的烙鐵終究沒毒到那種程度,雖然仍舊是完全燒焦了巴爾的摩的一塊皮膚。俾斯麥一直到烙鐵失去了溫度才肯把它拿下來,可巴爾的摩卻是吃盡了苦頭,手臂還是因為劇痛不斷顫抖,烙鐵不似其他酷刑,一瞬間的痛苦真的如同地獄里走了一遭,真就是死去活來。巴爾的摩全身如同水洗了一般直冒冷汗,很難想象剛剛還游刃有余的她這麼快就在拷問的淫威下變得粗喘連連、雙目失焦。但是俾斯麥卻還是沒打算饒過她,又是一塊烙鐵過水,直逼著巴爾的摩的左腋而來,但是並沒有直接按下去:
“怎麼樣,巴爾的摩,你的信心還剩多少。要不要再來一塊,我這里還有很多,把你全身烙一遍都沒問題,就怕你撐不住提前求饒。”
“我說過……我可能會讓你失望……在求饒這方面啊啊啊——!”
俾斯麥可不太想聽巴爾的摩說廢話,烙鐵不由分說地按在了巴爾的摩嬌嫩的腋下皮肉上,直燙得巴爾的摩尖叫不止,死命地拉扯著鎖鏈下意識要夾緊腋下,可惜她不是神仙,鎖鏈紋絲不動,只能任由俾斯麥碾轉著烙鐵,讓熱量充分地作用在巴爾的摩身上。皮肉發出呲呲地烤焦的聲音,一縷縷青焰不斷升騰,巴爾的摩眼前黑一陣紅一陣,劇痛幾近要剝奪她的意識,但是憑借著她的意志力,直到烙鐵冷卻,她也沒有暈厥過去。
“居然連捱兩塊烙鐵還不昏死,果然沒有讓我失望啊巴爾的摩。”俾斯麥將兩塊烙鐵收攏著扔回火堆,然後掐著巴爾的摩的下巴強迫她抬著頭,“這只是個開胃菜,我的手段還很多,想要多試幾個嗎?”
“求……求之不得,反正我也……沒什麼好說的對吧。”這當然是嘴硬,說實話在俾斯麥往火堆里放烙鐵時她都害怕俾斯麥再拿起一塊接著燙她……幸好這道刑應該是熬過去了,巴爾的摩可沒有想過第一道都這麼難熬。
“哼,開胃菜結束了,那麼,”俾斯麥俯下身去,抓著巴爾的摩的腳踝,“正式用刑之前,我的慣例,先把你的鞋子脫了比較好。”
巴爾的摩還在喘息著恢復氣力,想辦法提起精神應付接下來的拷問,所以冷不丁聽俾斯麥這麼一說還有點奇怪,但是俾斯麥已經動手解開巴爾的摩的鞋帶,將一雙運動鞋迅速脫下。藏在運動鞋里的一雙腳倒是不怎麼符合巴爾的摩體型的嬌小,到底還是女孩子,俾斯麥輕輕點了點頭,雙手在巴爾的摩被汗水浸得濕漉漉的黑色短襪上短暫地撫摸了幾下,而後又迅速扒掉它們,包裹在短襪中的腳在俾斯麥看來質量很不錯,雖然因為鍛煉生了一些繭子,但總體而言手感很是舒服,擁有著只屬於艦娘天然細膩和符合巴爾的摩元氣性格的火熱,雙腳呈現著健康的顏色,不很粗壯也不很纖瘦,同她的身材一樣勻稱而有力。俾斯麥思忖著,這樣一雙腳確實適合用刑,想來巴爾的摩也沒有應對足刑的經驗,從剛剛被烙鐵燙的反應可以看出,她意志力確實很強,但是該是弱點處依然沒那麼容易扛刑。
光腳踩著石磚地板,巴爾的摩只覺得一絲寒意從腳底往上滲。是為了增加精神壓力,還是要對雙腳用刑?巴爾的摩猜不透,當然也不可能猜透,從短期看俾斯麥只不過是想看看巴爾的摩的腳而已,她的癖好可並沒有多少艦娘知道。
“應該很涼吧,巴爾的摩。過不了多久就習慣了,我們這里的囚犯都是這種待遇,有些連衣服都沒得穿,因為身上都是傷口,需要時不時的清理。不過你還好,因為我不打算對你的身體直接用刑,那樣子太沒有效率了。”俾斯麥拿出一對環狀物,在巴爾的摩面前晃了晃,“知道這是什麼嗎?”
“乳環嗎,聽說是用來侮辱女犯的東西。”
“倒是知道的清楚,但是這個大小充其量只是陰環,套在你陰唇的兩邊,這才是乳環。”俾斯麥又拿出一對更大更重的環狀物,巴爾的摩連乳環都只是道聽途說,根本想不來乳環還能這麼大,再加上陰環,簡直聞所未聞。
“你不知道很正常,正常人誰會去了解這些。”俾斯麥從刑具中取出一把長針和一瓶消毒水,“不過那只是情趣用品,用作刑具就完全不一樣了,不然也不會有這種體積的乳環,純粹是為了好好折騰你的乳頭。”
撩開巴爾的摩的抹胸,扯下乳罩,巴爾的摩不大不小的一對酥胸暴露在俾斯麥面前,胸前的兩點此時不自然地立起,巴爾的摩羞恥地偏開頭,倒是俾斯麥毫不在意,想來也是剛剛的烙鐵產生劇痛讓身體來了反應,不過這樣也方便。在鋼針上塗上消毒水,俾斯麥捏起巴爾的摩的乳頭,針尖緩緩刺入。
“嘶——”再怎麼堅強,巴爾的摩的痛覺感官還是正常的,敏感處的刺穿不能說不疼,只是勉強可以忍受。俾斯麥的手法正是將這種前戲也變成折磨人的酷刑,一個洞都要穿一分多鍾,還不時攪動兩下,攪得巴爾的摩渾身打顫。長針留在了乳頭上,俾斯麥捏住針的一端,又開始慢條斯理地穿另一個乳頭,不多時兩個乳頭被穿到了一起,巴爾的摩不時地吸著冷氣,顯然並不好受。
當然這的確只是個開始。
俾斯麥取出一個打火機,開始在長針的一端緩緩加熱。
“喂,這是要做什麼?”巴爾的摩顯然慌了神,烤乳頭這種事未免也太過恐怖,巴爾的摩怎麼想都是不可逆的後果。烙鐵的滋味她已經吃過,要是在乳頭上……何況還是慢慢的烤。
“不把傷口燙焦,怎麼給乳頭塑形。”俾斯麥不帶感情地解釋著,“我要讓你的乳頭即使取下乳環也要留兩個孔在上面,一輩子都記著這恥辱。”
“……哈?”巴爾的摩的眼神都變了,變得憤怒,變得歇斯底里,她哪里聽說過這種懲罰,一輩子都要帶著的恥辱什麼的,她開始胡思亂想,想到自己每次換衣服都會看到乳頭上兩個難看的孔洞……她想要說些什麼,但卻又說不出口,說到底自己明明已經做好了被各種折磨侮辱甚至殘廢的准備,現在怎麼反而害怕起來了。巴爾的摩連咽幾口口水,突然覺得舒心了很多,眼神一瞬間變得決絕和毅然,反正遲早還有更嚴酷的懲罰,別說穿個洞,就算乳頭被整個剪掉都有可能,沒必要這麼在意……她如此安慰自己。
“居然比我想的要淡定嘛……”俾斯麥說著,關掉打火機,“我還以為你也會和其他艦娘一樣劈頭蓋臉地無能狂怒。”
“不打算烤了嗎?我覺得排開恥辱,應該會很疼吧。”巴爾的摩有些訝異,但很快表情恢復了輕松的樣子。
“如果你真的開始歇斯底里,我就真的把你的乳頭烤熟,但是現在沒意思了,不過和我推測的也差不多,要是真的烤壞了,之後的刑就上不了了。”俾斯麥猛地抽出針,在巴爾的摩疼痛的悶哼聲中,幾滴血濺在了俾斯麥手上。
“你就好好地,”俾斯麥拿起乳環,套在了剛穿好的血孔中,“享受著這乳環的滋味吧。”
不過中指長直徑的圓環,卻如同吊了塊磚頭一樣猛地壓在巴爾的摩胸口上,巴爾的摩身體一沉,乳房被拉扯著下垂,乳頭撕裂般地疼痛,巴爾的摩齜牙咧嘴地忍著乳頭的劇痛,緩緩直起身子,然而畢竟是敏感處受罰,劇痛還是讓她嘩嘩地淌著汗,看上去殘忍而悲慘。
當然,俾斯麥可是不會心疼她的,乳環的折磨還沒緩過勁來,巴爾的摩的熱褲又被解開,似乎是因為雙腿分開拘束著讓褲子不太好脫,俾斯麥干脆撕碎了她的熱褲,系帶的內褲出現在了她面前,俾斯麥顯得有些驚訝,饒有興致地在內褲附近撫摸著,有些潮濕,不知道是因為疼痛流的汗濡濕的,還是過度刺激來了反應而浸濕的,但是黑色的系帶內褲,某種程度上反而很適合巴爾的摩。
“很可愛啊,巴爾的摩,沒想到你還會穿這麼風流的內褲。”
“也許我就是這麼讓人出乎意料吧。”巴爾的摩倒是回答得很輕松,當然從表情上來看是輕松不到哪里去,她還沒有適應雙乳的增重。
俾斯麥跟著陪笑著,卻是毫不留情地扯下巴爾的摩的內褲,整個下身完全暴露給了俾斯麥。被濃密的恥毛保護的小穴若隱若現,縱使是巴爾的摩此時臉上也不是完全能掛的住,畢竟連下體都完全暴露給了敵人,羞恥之下還有些隱隱地擔心,不知道有什麼折磨在等著她。
俾斯麥有些不太滿意得搖頭,顯然是覺得巴爾的摩的恥毛過於濃密而礙事了,但是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的,她拿起鋼針,撥開巴爾的摩的恥毛,對著巴爾的摩的一瓣陰唇狠狠地刺了下去。
“唔......”巴爾的摩一個吃痛,整個身子都向後彎曲,俾斯麥眼疾手快地按住巴爾的摩的腰部,逼迫她不得不強忍著接受陰唇被穿孔。鋼針拔出,俾斯麥掰開巴爾的摩有些流血的陰唇,將陰環掛了上去,未經人事的巴爾的摩還是第一次被其他人碰自己私處,而這個第一次就要以被穿陰環作為開始,下體哪里受到過這般折磨,劇痛讓她忍不住雙腿打顫。俾斯麥正在毫不耽擱地給巴爾的摩穿另一半陰唇,看到了她在打顫,不由得得意一笑:“這才是准備工作,就害怕成這樣了?如果你真的那麼脆弱的話倒不如將你知道的都跟我說一說,不然後果我可無法保證......我這里的一些乳環上血跡都沒有干透呢。”
“害怕可不代表就一定要招供,更何況只是這死沉玩意兒拉得我有點疼......用刑就不要婆婆媽媽了,有什麼手段就快一點用出來,這麼點疼痛還不如我給自己一炮。”巴爾的摩連珠炮般耍著貧嘴,一方面是給自己打氣,另一方面則是想要轉移自己的痛苦,她現在感覺下體一陣疼一陣刺激,這可是她從未體會過的,天知道之後會怎麼樣,但就現在來說下體和乳房的劇痛讓她全身不快。
俾斯麥當然不是婆婆媽媽的人,剛穿完陰環,她就一把拉住巴爾的摩的乳環,強行拖拽著她來到刑房的一側,傷口還未愈合,巴爾的摩的乳房被拉得生疼,但是陰部的疼痛讓她很難跟上俾斯麥的腳步,只能是半拖半就地被俾斯麥拉著,一把推到一個刑台上。刑台形似一個安檢機,巴爾的摩只能判斷自己大概坐在一個履帶上,兩側半人高的立柱上拉出兩道鈎鎖,俾斯麥一腳踢在巴爾的摩渾圓緊致的屁股上,逼她跪倒在地,然後將兩邊的鈎索連在巴爾的摩的乳環和陰環上,俾斯麥來到巴爾的摩面前的立柱前,轉動把手,巴爾的摩只覺得兩邊的鈎索越拉越緊,逼迫得她不斷地跪伏著拉伸身體,胸部用力向前挺出,屁股後張,直到身體拉伸到極限,俾斯麥才總算是停了下來,而巴爾的摩已經是全身肌肉酸痛,稍微動彈一點乳頭和陰唇就撕裂般的疼痛。
“怎麼停下來了,接著拉我大概能爆發一下極限。”
“就這麼把你放著你最多能撐一個小時,不要太自信了,白鷹的正義戰士。”俾斯麥不是那麼容易受挑釁的人,她知道要是把巴爾的摩的乳頭拉斷或者陰部拉壞,之後的刑罰就不好實施了。
“是嗎?但我不覺得你就打算把我這麼放著,還有什麼惡毒的後招吧。”
俾斯麥沒有搭理她而是啟動了刑台,履帶開始緩緩轉動。
“咦?”巴爾的摩察覺到這一點時,乳頭已經被狠狠地拉扯了一下,一時間劇痛讓她下意識地開始移動身體跟上履帶,避免鈎索被扯動,但是因為保持著跪姿,她只能手腳並用地往前爬,隨著履帶速度加快,巴爾的摩只能盡全力爬動,才能保持身體與刑台的相對靜止,避免鈎索拉扯對乳頭和陰部的傷害,這番拷問極其消耗體力,巴爾的摩很快便全身發汗,微微地喘著粗氣。
“你還挺熟練地嘛,是不是經常爬給你的指揮官玩,來滿足她什麼奇怪的癖好啊?”俾斯麥適時地出口羞辱巴爾的摩。
“那我現在應該謝謝我的指揮官,雖然帶著項圈像小狗一樣爬很奇怪,但這不是派上用場了嗎?”巴爾的摩雖然累得氣喘吁吁,但是嘴還是一如既往地貧。
“......”俾斯麥突然意識到羞辱這種拷問方式對她起不了作用,畢竟這家伙太能貧還不要臉。那麼該做的事只有一個了,讓她知道什麼叫痛苦就好了。
俾斯麥揮了揮手:“那就給我爬半個小時再說,不夠享受了再加刑,我看看你的膝蓋是不是真的不會軟。”
看到俾斯麥轉過身背對她,巴爾的摩終於是繃不住了,輕輕嘖了一聲,然後死死咬住了嘴唇。
“哈呼......哈呼......”巴爾的摩的喘息聲已經可以在偌大的刑房里產生回聲。雖然這是必然的,她再強,體力也終究會有限度,但是機器不會累,那折磨就只有持續。俾斯麥淡然地看著全身汗如雨下的巴爾的摩,後者的膝蓋和手腕都已經磨得青紫,每爬一步都是劇痛的折磨,更不用說持續刺激著的乳頭和陰唇,隨著時間的推移,讓她越發的痛苦和疲憊。俾斯麥在觀察,她當然不可能讓巴爾的摩的乳頭真的被撕爛,所以要抓住巴爾的摩脫力的時機把機器停下來,當然到那個時候積累的痛苦估計夠巴爾的摩喝好幾壺了。
“......哈呼......喂,一直盯著我......哈呼......不累嗎......”都到這份上了,巴爾的摩還是想貧嘴。
“管好你自己吧,再不爬快點乳頭可要沒了。”
“哈呼......這可有點不妙啊......哈呼......”巴爾的摩只覺得手臂和大腿抽筋了一般酸痛,即使是跑這麼久也會累,更何況是手腳並用的爬,全身赤裸又沒有什麼防護措施,受傷加疲勞,她感覺自己已經在脫力邊緣了。
“唔!”巴爾的摩手臂一軟,整個人側滑過去,胸部瞬間被拉長了兩倍,劇痛讓巴爾的摩慘叫一聲,乳頭差點被真的撕裂,俾斯麥眼疾手快地衝上前,拉著巴爾的摩的頭發把她扔回刑台,順便關上了電源。
“唔,嘶——!”巴爾的摩雙手捂著胸部,鮮血不斷地涌出,雖然沒有拉扯斷,但是這一下可真的讓巴爾的摩疼得差點背過氣去,這會兒還在渾身打顫,拼命忍著差點疼出來的眼淚。她也不是超人,真疼到一定程度還是會想哭。
“還想要繼續嗎?巴爾的摩。”俾斯麥拉著巴爾的摩的頭發,逼迫她抬著頭,“你也累到極限了吧,現在招供還來得及,我還有幾道酷刑沒給你上完呢。”
“嘶——,來唄,我倒還好奇你還有什麼奇怪的招呢,像這跑步機之類的,我還沒在拷問訓練中見過呢。”
俾斯麥眯縫著雙眼看著巴爾的摩,突然一腳踢在她的陰部,巴爾的摩一時沒有防備,哀嚎一聲想要躬下腰去,卻被俾斯麥再次強行拖著扔到了刑房中央。麻繩迅速地套在了巴爾的摩身上,一圈一圈地捆緊。很快,巴爾的摩被捆成了m字開腿的樣式,雙腿折疊著吊在身體兩邊,下體大敞四開,要命的是俾斯麥將巴爾的摩腿上和手臂上延伸的繩索連在了天花板掉下來的鎖鏈上,把她一點點吊起,繩索在重力的作用下收緊,勒得她生疼,氣都喘不勻。
“這用的可都是活結,一會兒你可千萬別因為疼就隨便掙扎,否則會越勒越緊把你勒死。”俾斯麥“好心”地提醒著,但是巴爾的摩已經被勒地夠嗆了,在捆綁之前她上身最後的抹胸也被扯了下來,麻繩完全勒在了她的肉上,似乎是浸過油的麻繩,還沒開始用刑就在她的身上勒出道道青紫,加上開腿的束縛術,身體被捆綁地很不舒服,可以說這一吊就讓巴爾的摩有些吃不消了。而當她看到俾斯麥拖來的東西,那一瞬真的想掙扎著逃出去,可惜能做到的只有蕩秋千一樣在鎖鏈上晃蕩。
那是一個金字塔形的刑具,不過整體上比金字塔要瘦一點,尖端鋒利地發著寒光,而側面還有些干涸的黑色血跡,整個刑具說大不大,但是正對著巴爾的摩的菊穴,就不得不說這刑具的體積有些大了。
“這個是猶大的座椅,本來是想拷問你的下體,但是剛才穿環的時候我發現你居然是個雛。”俾斯麥嘲諷似地輕笑一聲,“只好對你的屁股用刑了,放心,我會把握力道,至少你的後庭以後還能用。”
還能用究竟是一個什麼程度的概念,巴爾的摩不知道,她只知道這會兒幾乎緊張地想吐,那鋒利的尖角此刻正對著她的後庭,這東西扎進去是什麼感覺,有什麼效果,巴爾的摩一概不知,她只能隱約猜到,這東西絕對不會仁慈,至少不會像之前穿乳環那樣輕松。
俾斯麥摸到鎖鏈的絞盤,略微瞥了巴爾的摩一眼,然後突然松動絞盤,巴爾的摩只感覺到自己在自由落體,不由得尖叫出聲。
“啊!!!”
尖端離菊穴不過兩寸,繩子猛地收緊,巴爾的摩緊閉著雙眼大口呼吸著,額際大滴大滴地淌著汗。看起來是被嚇得不輕。
“不要緊張,巴爾的摩,剛剛那個距離要是真的落下,你恐怕就要內髒破裂而死了。你對我的價值有多大,你應該對我不會殺你而有些自信才對。”俾斯麥拉著鎖鏈,戲謔地說道。
“呵......我要是就這麼死了,就輕松了對吧。”巴爾的摩長出一口氣,笑道。
“大概吧,我也不清楚那樣要多久才會死,但是這個距離一定不會死。”
巴爾的摩一個心驚,這一次俾斯麥可沒有停下,巴爾的摩尚未開發的嬌嫩後庭直直地撞向了座椅。她很難形容那種疼痛,只知道自己一秒鍾都沒忍下來,直接慘叫出聲,菊穴一瞬間被擴張開裂,鮮血在座椅側面緩緩流淌,異物入侵進了穴內,攪動著細嫩的穴壁,更加的痛不欲生。有一瞬間巴爾的摩懷疑自己會不會真的就這麼死了,但是後庭的劇痛又讓她無比清醒,知道自己是在受刑,泯滅人性的酷刑。
“啊啊啊啊啊——!!!!”
“唔、啊!疼......啊啊啊——”
“疼......混蛋.....啊啊啊......”
“嘶......”
巴爾的摩想要通過晃動身體讓自己摔下來,可惜這時她才發現俾斯麥仍舊拉著鎖鏈,放出的長度讓她幾乎全身重量壓在菊穴上,又沒法掉下去,而且俾斯麥剛才的提醒也並不是說著玩,越是掙扎,繩子勒地越緊。巴爾的摩倒是想著讓繩子把自己勒死算了,自己也不用再熬受這地獄般的痛苦,但是很明顯這只是在給自己徒增壓力,因為繩子並沒有勒到她的任何死穴上,單純會勒地她更疼而已。
“該死,唔......疼......”
“啊!......放我下來......”
“嘶.....疼死了.....嗚啊——”
巴爾的摩那含混地痛叫俾斯麥當然是聽得一清二楚,不如說俾斯麥現在還有些驚訝,換其他的艦娘這會兒已經又哭又號著失去理智一般尖叫著讓俾斯麥把她放下來,何況巴爾的摩完全就是個雛,後庭還很緊,一下子被刀子一樣的東西擴張侵入,那疼痛可想而知。但是現在結果卻是巴爾的摩一邊苦苦強撐一邊發泄式的喊疼,給俾斯麥的感覺是......疼地很沒實感一樣。
但是俾斯麥已經拿不出什麼其他手段了......大概吊重物在巴爾的摩腳上還可以,但是剛剛那個自由落體帶來的侵入深度和擴張的力道已經有很多重物加身的程度了,可惜巴爾的摩只有第一聲喊得最撕心裂肺,後面反而適應了一樣......這時候重物的效果也有限。
但是,也不能說巴爾的摩此刻就不難熬了,相反她不停嘗試著保持身體平衡,以期緩解疼痛——當然是沒那麼容易,反而有時候微小的摩擦和碰撞都會讓她齜牙咧嘴慘呼出聲,菊穴的鮮血和身上的汗水一起大滴大滴地流淌著,在地板上形成淡紅色的一灘。十幾分鍾就在這掙扎和慘叫中過去了,巴爾的摩也感到自己力不從心,安安靜靜地端坐在座椅上,一邊熬刑一邊輕聲呻吟著,等待著俾斯麥的釋放。
然而俾斯麥臉都黑成一片了,她還沒見過這麼難對付的,這已經是大刑的級別了,結果巴爾的摩的反應卻很有限。俾斯麥固定住鎖鏈,走到巴爾的摩面前,環抱雙手。
“嘶——可以了吧......這個真是吃不消......唔呃......”
“話這麼多,我可看出來你吃不消。”
“什麼......啊啊啊啊啊!”
俾斯麥抬腳用力踢在座椅下方,巨大的力道反饋給了椅尖和巴爾的摩的菊穴,一時間踢得巴爾的摩七葷八素,菊穴似乎又開裂了一點,劇痛差點沒給巴爾的摩頂暈過去,疼得她連連慘叫,身體不住地掙扎。
“啊啊啊......混蛋.....啊啊啊....!”
“你說不說!”
又是一腳,巴爾的摩疼地汗如雨下,慘叫地如同殺豬宰羊,她能感覺到座椅在一點一點地侵入後庭,每一分的擴張,都如同刀割斧劈,痛不欲生。
“你說不說!”
“唔呃呃呃呃呃.....大不了....你殺了我啊!!!鐵血的渣滓!!”
巴爾的摩從被拷問以來第一次這麼明顯地將憤怒的感情向俾斯麥爆發,劇痛讓她有些不計後果,只想要通過發泄的方式緩解被折磨的積郁。可惜俾斯麥早就習慣了這不痛不癢的怒罵,何況巴爾的摩不會說髒話一樣。但是俾斯麥這下算是找到了教訓巴爾的摩的渠道,抄起皮鞭狠狠向她抽去,巴爾的摩一時間有些失去忍痛的能力,每一鞭都是一聲不成人樣的慘叫,打了還不足十鞭,她的身體一傾,第一次昏厥過去。
“......真是麻煩,還沒見過哪個艦娘受得了這道刑的,腳都踢疼了。”俾斯麥也算是冷靜了下來,不由得嘆了口氣,命令獄卒把巴爾的摩放了下來。
再次醒來時,巴爾的摩已經是完全自由地狀態被丟在地板上,地面有些潮濕,在她印象里大部分刑房似乎都是這樣,傷口受潮會加速潰爛,很多犯人會因此感染而死,死前還會痛苦好一陣子。
這麼一想,巴爾的摩的痛覺神經像是突然回來了,後庭的劇痛再一次清晰,鑽心剜肚地疼,讓巴爾的摩想再一次睡過去,當然是不可能的,俾斯麥就在她的面前看著她。她被拖到了一張椅子上,面對著寫字台對面的俾斯麥,身上沒有束縛,但是巴爾的摩此時也不太能動,就這樣面對著俾斯麥大張著腿,緩解著後庭的疼痛。俾斯麥倒也不在意,安靜地盯著她,冷漠的眼神,像是要從巴爾的摩身上看出什麼。
“需不需要上點藥。”俾斯麥還是發話了,畢竟巴爾的摩現在的狀態估計也不想多說話。
“......你又有什麼折磨人的新點子了?”
“不,作為重要人物,我不可能讓你感染而死。”
“我還真不知該感謝你還是該罵你。”
“你那軟弱無力的罵人法就算了。”俾斯麥說著,命令獄卒將巴爾的摩背對著她按在椅子上,巴爾的摩自然是有點緊張,不過很快她就發現俾斯麥真的在給她噴藥,後庭有種清涼舒爽的感覺。
“你這藥還真不錯。”
“給犯人用的速效藥當然不錯,因為通常在兩道刑中間的休息時間用,很快就能止痛。”
“止痛不是和拷問的初衷相反吧。”
“多種疼痛交加,會相抵,也會麻木,最重要的是犯人有可能會疼死。所以要在幾道刑的間隔中安排休息時間,並且用止疼藥。”俾斯麥退回寫字台後重新審視著巴爾的摩,“所以你現在感覺如何,休息好了嗎?”
“我倒寧可沒有休息好,雖然我現在感覺精神地能一拳打暈你。”
“這麼能貧,看樣子是休息好了。”俾斯麥居然也不由得會心一笑,“既然上了藥,那你應該明白,下一道刑更難熬,而且這個刑不是意志堅強就能扛住的,身體會不由自主地扭曲掙扎和痛苦。”
“你說的我反而感興趣了,今天我吃的苦頭比我這輩子加起來的都多,所以我不介意再多來點。”巴爾的摩保持著一向的從容,仿佛那個在猶大座椅上又是哀嚎又是歇斯底里的不是她一樣。
“你其實一直很聰明,巴爾的摩,你的挑釁更多的是針對站在我這個立場上的人的心理吧。”俾斯麥指了指自己,“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會被你挑釁到,我可以保持著鎮定讓你一點點崩潰,你也可以保持鎮定讓我失去耐心,這種對等條件下,我們總有一個會輸。我相信那個人只能是你。”
巴爾的摩感覺到手心在出汗,俾斯麥說的一點沒錯,因為她個人的特殊性,在敵人手里要麼被拷問折服,要麼被持續性的關押和拷打,所以要想不招供,就只能求速死……但是俾斯麥確實不愧是鐵血最強大的拷問師,到現在為止即使是發怒,拷問力道也達不到能把巴爾的摩折磨死的程度,而實際上到現在沒有一個刑是巴爾的摩能夠輕松扛過去的,都是針對性的用刑,又毒又精准。巴爾的摩很難判斷自己能否一直不變節。
這麼想著,巴爾的摩突然發現俾斯麥拿著一把剃刀走過來。要用刑嗎?這麼想著的巴爾的摩閉緊了雙眼,繃緊全身的肌肉,但很快她就發現,俾斯麥再自己的下體上鼓搗什麼,嚓嚓聲響起,當她意識到不對勁而睜眼時,自己的恥毛已經被刮得差不多了。
“你,你這是……”
“刮你的恥毛,顯而易見。”俾斯麥甩了甩剃刀,“不然不好用刑。”
不容得巴爾的摩有半點的質疑,俾斯麥將巴爾的摩再次拖到一個類似躺椅的刑椅上,整個身體呈四十五度後仰,雙手被銬在了銬環里,握在扶手上,雙腳則自由放開,因為全身赤裸,巴爾的摩的腳趾因為緊張而扇動被俾斯麥看得一清二楚。看來巴爾的摩也並沒有她想得那麼強大,和一般的受拷問的艦娘一樣,一旦吃到了苦頭,總會產生對未知刑罰的焦慮和緊張感,這種緊張感倒是能好好利用。俾斯麥拿出一根金屬棒,在巴爾的摩眼前晃一晃:“你覺得這個東西能不能塞到你的小穴里。”
“什麼,你要做什麼?”巴爾的摩顯然不理解,但是一聽到要塞到小穴里,語氣都變得急切了。
“我之前說過為了不讓你破處,就不打算都小穴用刑,但是你一直不怎麼聽話,我就只好剝奪你的處女了,你沒有意見吧。”
“……我敢有意見嗎?你想怎麼做隨你,我只是個囚犯,難道還要被你憐惜人權嗎?”
俾斯麥看出巴爾的摩鐵了心要硬撐,反而真的沒什麼憐惜之心了。掰開巴爾的摩的雙腿,俾斯麥用金屬棒對准巴爾的摩的小穴,猛一用力。
“嗚——”巴爾的摩不由得皺緊了眉頭,被破處的感覺比她想的還要疼,然而破處之後,俾斯麥沒有急著深入,而是拿出金屬棒給巴爾的摩展示那上面的精血:“看好了,你的第一次是交給它的,等用完刑我就把它送給你做紀念吧。”
“……”巴爾的摩偏過頭去,不再搭理她,但是從她眼中蘊藏的淚水來看,她的心里並不好受。
俾斯麥也不在意,將金屬棒再一次塞進巴爾的摩的下體,這一次巴爾的摩看清楚了,那金屬棒的末端連接著一根线,一直通到一個機器上,俾斯麥拿出那台機器後,巴爾的摩終於知道俾斯麥要做什麼了。
她要用電刑。
巴爾的摩忍不住打了個寒噤,她終於知道為什麼俾斯麥之前要那樣說了,她是了解電刑的,明白那東西的恐怖,就算拷問訓練里提到了,她也沒有親身體會過,說到底這種刑罰太恐怖太危險了,一不小心很容易被電死,或者落下什麼永久性的損傷。而現在巴爾的摩終究是逃不過這酷刑。
說話間俾斯麥已經將電極接到了乳環上,電流從胸部進去,從陰部流出,真是好手段,巴爾的摩苦笑著,現在也唯有苦笑,等到時候是什麼感覺只有自己知道,俾斯麥很是貼心地又盤問了她兩句,她打著哈哈搪塞過去,事到如今她只想趕快受刑,趕快結束,大概也能樂得自在。
俾斯麥看出來巴爾的摩已經開始焦躁了,此時正是用刑的好時機,用持續的劇痛,使巴爾的摩內心的焦躁轉化為不安和絕望,這都是很老但是很耐用的精神拷問法了。俾斯麥扳動電閘,電流一瞬間產生。
“嗚咦咦咦咦咦咦噫噫噫啊啊啊啊啊啊啊……!”
巴爾的摩的身體幾乎是突然地挺起,肚子連帶著腰腹高高的挺著,用力挺起,肌肉的緊張使得身體的力度繃到最大,甚至隨著巴爾的摩的慘叫聲快速地顫動,顫動的幅度大得夸張,豆大的汗珠再次在巴爾的摩身體表面產生,那是使得每一寸肌肉,每一個細胞的刺痛,身體幾乎是在不由自主地掙扎,很快腰部不再挺出,卻是身體開始縮成一團,兩條腿向著胸口用力收縮,同時左右擺動著大幅掙扎。巴爾的摩的身體整個兒用扭曲形容再合適不過,收縮是不由自主的,但是肌肉卻完全不聽使喚,連腳趾都在一縮一縮地掙扎,雙手更加不用說,抻直僵硬如一塊鋼板,不停地拍打著扶手,發出有節奏的啪啪聲,另一個有節奏的聲音來自巴爾的摩的後背,不停地、用力的匡匡砸著椅背,從沉悶的撞擊聲中就可以判斷巴爾的摩砸地有多用力,膝蓋已經頂到了下巴,雙腿卻還是要用力收縮,收縮,瘋狂地顫抖,一雙玉腿被汗珠覆蓋地亮晶晶一片,扭曲中有著別樣的性感。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噫噫噫噫噫噫噫噫……”
奇怪的慘叫,奇怪的扭曲,奇怪的反應,這足以概括巴爾的摩的現狀,其實她的身體到目前為止就一種感覺:疼,無論是內髒的灼痛還是皮膚的刺痛,說到底就是疼,尤其是電極接入的乳頭和下體更是瘋狂地疼,這疼痛中還有著異樣的快感,實際上她自己不知道,俾斯麥可看得一清二楚,巴爾的摩的下身早就濕漉漉的一片,不說那泛濫的一塌糊塗的愛液,她早就被電得失禁,現在還一陣一陣地滋著尿水。巴爾的摩又開始用手肘砸著椅背了,身體的狀態已不能用打顫來形容,那是抽搐,微小的抽搐中偶爾夾著幾下劇烈的抽動,砸地刑椅匡匡巨響。她開始口吐白沫,從嘴角流出,淌到乳房上,還在不停地流,眼白用力地翻著,雙眼全是血絲,兩行清淚從眼角流出,終於是被折磨地受不了了。
俾斯麥斷電時,巴爾的摩的身體正持續挺著,一下子砸在了椅子上,還接連抽搐了兩下,俾斯麥發現巴爾的摩已經不動了,用手在眼前掃了掃,果然表情呆滯。俾斯麥對著獄卒招了招手,一桶涼水從頭澆到腳,巴爾的摩才勉強恢復了些意識,開始大口大口的喘氣,仿佛這輩子沒有呼吸過空氣一樣,簡直要把肺都喘出來。
“還能說話嗎?巴爾的摩。”俾斯麥簡直明知故問。
停止了喘息,巴爾的摩只有雙眼死死地盯著天花板,充著血的眼珠簡直要瞪出眼眶,過了許久,才算是恢復了些神采,但依舊不說話。俾斯麥知道那是用了電刑後的正常反應,但是她還有手段沒有用出來。
取下金屬棒,出現在俾斯麥手中的,是一把電擊槍,改良過的至少不會一下把巴爾的摩打暈。
俾斯麥將槍頭對准巴爾的摩的陰蒂,快速開關。巴爾的摩悶哼一聲,身體又是猛地一挺一砸,神志也終於是恢復了一些:“疼……你這混蛋……”
俾斯麥沒有停手,又是一電。
“唔唔……喀……”
這瞬間的電流實際上比電刑的強度要高不少,兩下過後,巴爾的摩又開始渾身抽搐。
俾斯麥將電擊放輕,用槍頭對著巴爾的摩的陰蒂一點一點,巴爾的摩照例是挺著身子,在電流的刺激中雙腿不停打顫,但是俾斯麥注意到,巴爾的摩的臉色已經泛起一片潮紅了,而陰蒂果然開始分泌出愛液。巴爾的摩就這樣在電流的刺激下來了感覺。
俾斯麥刻意地在巴爾的摩被電的挺起時抬高電擊槍,在此之前她持續電擊著巴爾的摩的陰蒂,隨著電擊的放緩,巴爾的摩的身體抬得越來越高,倒像是迎合著電擊的刺激。她本來就未經人事,這種情況下基本也只能按照自己身體的舒適本能走了。
但是俾斯麥可不會如她所願,電流瞬間增強,巴爾的摩痛叫一聲,身體重重地砸了回去。
“嗚……饒了我吧……”巴爾的摩終究是難以忍受俾斯麥對下身的調教和折磨,出聲屈服。
“疼就招供啊,不要說這些沒用的廢話。”
“招……不,我不會說的……你這惡毒的家伙……”
“……”結果倒還是這樣,俾斯麥心里反而有些竊喜,這只是第一次巴爾的摩的屈服,日後注定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直到巴爾的摩肯說為止。
現在巴爾的摩被固定在一張矮桌上,手腳被固定在四條桌腿上,胸部和下體高高挺起,陰部因為充血而腫大,整個人還沒有從電刑的遺留症狀中清醒過來,目光還是有些呆滯。
這是俾斯麥的個人喜好釋放的環節,她脫掉了左腳的鞋襪,露出來自己的裸足——一個足控的裸足,因為這個癖好她向來將自己的腳保養得十分之好,雖然喜歡女孩子的腳,但是很少有其他艦娘的腳能比得上她的白皙而細膩——這只腳此時正踩在巴爾的摩腫大的下體上,愛液沾滿了腳趾,但是俾斯麥毫不在意,她腳下緩緩加力,本來就腫痛的下體更加的疼痛,巴爾的摩輕聲呻吟著,目前她已經很難再熬痛了。
“這是今天最後一次問你,如果你還是那個回答,我只能說恭喜你熬過了今天的拷打。”俾斯麥用大腳趾一下一下點著巴爾的摩的陰蒂,疼得她苦不堪言。
“我……不會招的……”
俾斯麥用力地一踩,巴爾的摩慘呼一聲,下意識地挺著身子,但是又被束縛拉了回去。俾斯麥將陰環套在自己的大腳趾上,猛地一拉,兩瓣陰唇大大地綻開,露出血紅的陰部肉壁。她迎上肉壁,將大腳趾塞進巴爾的摩的下體,慢慢攪動著,令巴爾的摩不斷地呻吟痛叫。
“你很不錯,巴爾的摩,意志力堅定是一方面,能夠從容應對又是另一方面,如果換作其他人,還真不一定對付得了你。”
白皙的裸足從巴爾的摩的下體抽出,腳趾踮起,在巴爾的摩的腹部一道道染著愛液。又滑到巴爾的摩的下體處,腳踝向著下體的軟肉按壓,壓得巴爾的摩差點又失禁。
“可惜了,你的拷問人是我……今天也只能如此了,好好地享受在牢房里的第一晚吧,環境大概會很差,但是至少拷問後你還能睡得香甜些。”
(記錄)
我倒不是有多討厭俾斯麥所講述的拷問故事,但是聽完之後,我不大敢看她給我展示的乳環。無疑,它代表著一類對女孩子非常、非常嚴苛而殘忍的刑罰,幾度令我渾身發寒,差點不敢聽下去。
也就俾斯麥能夠一路上淡然地講完這些。
我掂量了一下那個乳環,如她所說,很沉,這是最重的一組乳環了,持續地折磨著女犯,讓她一刻不停地忍受著折磨。對於敏感帶的拷問,真是泯滅人性而又百試不爽。
“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俾斯麥,你是否有那麼一刻感受到自己的殘忍。”
我這樣嘗試地問道,對於俾斯麥來說這是很新奇的問題,正如她所說她是鐵血最強大的拷問師,一直以來是否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呢。
“我可以放低自己的人性也可以嘗試著反思,卡倫,如果你只把我當做一個惡魔,那我必定就是,但是能夠活得心安理得,正是因為我對自我的反思。如果不是為了去找巴爾的摩,我也不會想起給你看這個乳環。”俾斯麥理所當然的表情,讓人很難判斷她的態度。
“你要去給她道歉嗎?”我有點不敢相信。
“我道歉就是這麼稀罕的事情嗎?我有必要再多提醒你一句。”
“嗯?”
“我也是會做噩夢的。”
俾斯麥的雙眼平靜如鏡,但我總算能看清楚一些藏匿其中的疲憊,許久以來,或許未有一天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