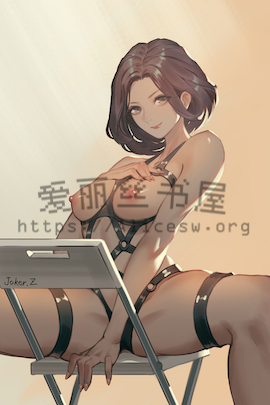卻說弘晝只命顧恩殿之使喚丫鬟秀鳳,喚寶釵並妙玉進來。
眾人一時皆靜默無語,冷眼偷瞧弘晝,卻見他神色只是淡然,亦難辨喜怒。
可卿乍了膽子,上前才道一聲:“主子……”
弘晝擺擺手,示意可卿勿需多言。
不一時,秀鳳撥起珍珠垂簾,卻見寶釵款款搖搖進了屋來,身上兩肩繡棉錦緞衣裳,已經沾滿了雨珠,想是才自風雨里急急趕來回話,不曾掌傘掌得妥帖。
寶釵亦不敢抬眼,只是深深蹲身一福,卻也不起身,只順眉柔聲回話道:“回主子……寶釵奉命去瀟湘館見林妹妹,瞧著林妹妹卻是著實病得不輕,紫鵑說已是身上滾燙了兩日,怕是掙扎不動,寶釵去床頭探望,臉色蒼白身子卻是滾燙,呼吸喘咳不止。如此形狀不奉命也實在不當來見主子伺候的。一邊卻湊巧遇著櫳翠庵里的小姐妙玉……妙玉姑娘也在探病看望林妹妹,妙玉說是她前幾日夜里頭邀林妹妹去櫳翠庵賞月聽琴,林妹妹身子弱,才染了風寒,想來終究是她的不是,若主子有見責之意罪,是她的首尾……故此必定要來向主子請罪……這會子妙玉妹妹跪在後頭院外雨地里不肯起來,求主子發落。恩……寶釵也勸不周全,也不敢胡亂揣測主子心意,只得隨她。只是院子里雨大,她弱體女兒家怕經不起,我卻讓秀鸞打了傘……”她偷偷抬眼微微瞧弘晝一眼,亦難辨弘晝臉上陰晴喜怒,隨即低了眉接著道:“……寶釵並不敢胡亂揣摩主子心意……亦不知辦得妥帖不妥帖,只求主子發落就是了……林妹妹亦罷,妙玉妹妹亦罷,若有不是,主子要乏,也請主子一並懲罰寶釵些個……也能稍安我伺候不到惶恐之心……”
弘晝衝寶釵淡淡一笑,卻起身緩緩下了炕,就在地上劃拉幾下,找著棉底靸鞋穿上,起身走向書齋門口。
走過寶釵身邊時,只隨手伸出,手指頭向上略勾幾下,示意寶釵起身,然後也不看眾人,就似笑非笑得舉步走出書齋門去,秀鳳忙打起簾子。
屋內眾人面面相覷,不知這主子是何等差遣,還是鳳姐和可卿交換一下眼色,都起身迤邐,要跟著弘晝出屋子。
弘晝卻回頭道:“你們跟來做甚麼……”眾人只得停了腳步,弘晝搖搖頭,一個人踱步出了屋子,自回廊處轉身向後院去了。
原來那顧恩殿本是大觀園正殿,前殿有鳳鸞朝月殿,本可排班接受朝賀,只是弘晝嫌棄朝堂氣濃,封存了難得開啟。
此時自書齋走出,卻是後半進得院子,穿過紅棕綠蕉廊,邁過雕著麒麟祥瑞之白玉影壁牆,出得月牙門,才到了顧恩殿之後院,這一方青石小院,內有六六三十六方古木花壇,滿栽金桂梧桐,取意“梧桐棲鳳”之意,若是夏日,滿院梧桐遮天蔽日,倒也自涼爽。
只是此時秋深風冷、愁雨綿綿,那梧桐、金桂俱是枝葉枯萎,小院滿地亦鋪滿了敗落之黃花殘片。
弘晝說這亦是風雅,並不許打掃。
此時秋雨滲骨攝魂,正是淋淋落落敲打得一地滂沱,一派悲冷蕭瑟之意。
小院靠近院門處,但見淒風苦雨之下有兩個人影,一個站著,一個跪著。
站著得掌著一頂黃紙厚楠油傘,一身宮裝,身形修長玲瓏,卻是顧恩殿頭一個曾被弘晝奸汙臨幸之丫鬟秀鸞,正所謂二八少女,豆蔻年華,顏色身量總是秀美難當,論起來也是雲鬢玉顏,柳眉星目,腰柔腿修,胸起兩墳,難得的上等美色。
只是與地上跪著之人一較,卻再也襯不起來。
地上跪著一團窈窕白影,遠看似冰山雪蓮,近賞如觀音降世。
頭挽展額歸月發髻,一總歸到頂心,用一方蓮花嫩蕊冠扎束而定,後擺只垂一方白紗為蓋;這千根青絲,絲毫不用釵玉珠翠妝點,本是素雅之色,卻偏偏愈發顯得綿長柔美,根根點點醉人心脾。
眉不畫,淡淡掃兩道新月;唇不點,微微抿一葉軟紅;雙目微垂,深瞳遮人間秀色,玉鼻挺拔,兩腮削世上嬌羞;秀美端莊的臉龐上,除了眉心用一點朱砂戒念琺琅紅,再不用絲毫凡世間之妝容顏色,偏偏愈發顯得冰潔無方。
本來是不沾染人間煙火氣之冰雪般臉龐,卻偏因為那柔美櫻唇處幾多誘人溫軟,白玉雪腮旁一片淡粉曲婉,凝容長睫處靈動俏麗,以及因為長發歸頂,而裸露出來的一對有著小玉肉耳垂的耳朵,竟然是一片肅穆端莊里,用幾處少女仙姿般五官里難得的小小肉感,摻雜了多少人間風流嫵媚之動人顏色。
身上穿一領月色一體寬袖大袍、繡著蓮花淡銀色“卍”字紋之佛尼長衫,說是袈裟卻也精致玲瓏,柔絲細絞,外罩著一件素色田字坎肩棉褂,胸前用兩條雪絨花條綴勾邊,腰間用荷色絲絛扎定,素雅清純,寧靜安然。
只是長衫之袖口裙角,卻隱隱用了蓮花之色,棉褂的領口肩邊,亦用了小風毛的棉絨,真是一片素女修行、佛心安靜、不染凡塵半點之衣著里,偏偏透著許多嬌顏美意。
若再看身量體格,更是讓人不由得攝魂奪魄,難以自持,那兩肩柔媚下垂,如玉藕般之長臂雖在佛衣大袖遮掩之下,亦能見得骨骼清麗,胸前驕傲動人得起伏著兩座柔美的少女乳峰,在衣衫並雪絨花條綴遮掩之下,偏偏要奪得世上造化之功,人間風流之最,那絲絛扎定之柔媚腰肢,細若柳枝仿佛半臂就能環箍,倒愈發襯托得下擺里有著萬種風情,一片深幽春色秘境。
正是櫳翠庵里的絕色女尼:妙玉。
只是此時,秋雨摧魂,那妙玉跪在院門之邊,雖有秀鸞用黃油紙傘遮雨,奈何下身裙擺已經沾濕汙染。
她如此一個妙人兒,有著佛前仙子之儀態,亦有世外天香之嬌容,卻如此由風雨催逼著,憑是鐵石心腸之人,亦要動憐香惜玉之容。
弘晝便有千般不快,到底是來自後世之人,心中一點不忍便起,上前幾步,便道:“跪著做什麼……且起來……”。
只這弘晝身邊未跟著下人,他上前幾步,便自有著遮雨之頂的回廊處,步入了院中秋雨之內,那秀鸞見狀,忙不迭只能棄了妙玉,口中只道:“主人小心淋了雨……”,快步走過來,替弘晝用雨傘遮雨。
不想那妙玉卻是不動顏色,只是靜靜以目視地,憑雨打風吹,亦不遵命起身,片刻寂然方柔聲回道:“……回主子……貧尼有罪,跪著便如懺悔罪過,何必起來……”此時她無有雨傘遮擋,風中雨點兒頓時密密灑灑,敲打在她秀發、臉龐、身體之上。
她嬌嫩體格如何能受得,頓時只能美目迷離起來,才片刻,頭發之上已經是沾濕了雨花,臉龐上點點滴滴掛滿了雨珠,身上的棉褂也漸漸潤濕了起來。
只是這一等風雨摧玉人,越發惹人心動愛憐,弘晝上前幾步,走到她的跟前,心下雖不忍,卻不知怎得,見淒風苦雨打得這嬌美玉人齒冷骨凍,竟然別有一份摧殘之美感,而見那雨水慢慢潤澤妙玉的佛衣,一時想著若是只管憑著雨水浸透,這佛衣裹身,該有多少玲瓏體態可以觀賞,竟然有了褻玩這雨潤嬌軀的興致。
便也不接著命她躲雨,只淡淡道:“罪與非罪,不由你等自說,卻只在本王一念之間,你倒說說,你有何等罪過當罰?”
妙玉低眉似乎無聲頌禱了一句佛號,片刻後似乎鼓足了勇氣,微微一抬頭,以目視弘晝一眼,這美玉臉龐如此嬌美淒婉得一抬,風雨摧打之下,秀目睫毛上似乎沾濕了淚珠雨花,臉龐香腮滿是水痕,朱唇上亦沾濕的仿佛要誘惑人立即去舔弄吸吮一般,饒是弘晝已經多品過人間極品女子,亦是神魂幾乎顛倒。
卻聽妙玉口中寧靜肅穆道:“貧尼本畸零之人,寄身於佛祖,既蒙榮國公府上相容,又有主子收養,算來亦是這一世糾葛孽緣,本當安分守己,只於佛前為主子頌禱,求主子身體康健,福澤萬年;卻一入紅塵,五色皆迷,難以割舍這風花雪月,奇淫巧技,前日擾了瀟湘館里的林姑娘,只說賞月對詩,聽琴說譜,也忘了夜露寒沉,貧尼……本為菩薩座下檻外之人,林姑娘……卻是主子庇佑之奴,整這難以名狀之勞什子詩詞,林姑娘才因此得病,淑小主今日來探視,我才知耽誤了林姑娘伺候侍奉主子……這豈非是貧尼之罪過……”
弘晝聽她鶯語柔婉,瞧她身子更是越來越濕,一件月色佛衣更是漸漸沾濕了黏著在她柔和嬌媚的身子之上,香肩渾圓,兩臂修美,與那衣衫若即若離,粘黏處如渾然水乳,分離處似空谷藏香;逐次得,那被佛衣連著田字背心遮蓋嚴實的胸前乳型也已經漸漸被雨水澆打得,緊貼清晰半透秀色起來,這一對香筍玉峰被濕潤的衣衫包裹,上半球點點滴滴雨水滋潤,漸漸見其峰巒起伏,貼緊處仿佛能清晰可見兩顆蓮花乳豆慢慢凸起頂得衣衫張揚,這乳型雖不巨,但是“卍”字佛衣遮蓋之下,淒風苦雨摧殘之中,這一片人間最是香膩的媚肉,兩顆凡俗里最是淫羞之紅珠,卻偏偏最是耀眼奪目,形成的鮮明反差,更是添得幾分攝魂奪魄之淫意。
弘晝一時雨中賞此人間尤物沾濕之色,幾乎就要難以忍耐,就想不顧一切,亦不念甚麼雨地露天風冷,雨地濕滑,青石泥濘,黃花殘敗,就這在院子里,將這如此魅惑之小女尼兒,就一把按到在地,哪管她喜怒哀怨,哪理會她羞恥屈辱,更不論佛音戒律,只管扯去這一身早已沾濕之羅衫,剝落這已是挑逗淫心之佛衣,就口兒品嘗品嘗其一身必然是難得的香羞美肉,直挺挺將自己的龍根巨陽,插入這少女的最私密羞恥處,偏偏要采得她這童貞初紅,特特要奸得她這佛前侍女。
只是想著這等色淫浪蕩之事也就罷了,弘晝早已深知風月,如今更愛慢慢品香弄玉,並不急色胡為,他又到底是聰明之人,聽她答話,卻似乎話里有話,雖稱自己為“主子”,卻仍然是自稱為“貧尼”,想著今日之事左右有些異樣,更想著憑這女孩子是不是修行之人,總是自己案上羊羔,胯下臠臣,倒不急著行那等事,只笑笑接著話茬道:“……聽你說來,倒是為了擾了我的興致……那倒也不假……林丫頭也罷……你也罷……本來就是伺候本王之奴,若是本王興致來了,自然是要奸你們的身子取樂……若是病了不能來承歡伺候,難免掃興……自然不便……”
妙玉本來矜持身份,雖然言辭恭謹,卻冷冷自若昆侖雪蓮一般,聽弘晝如此說,一時倒不知該怎麼答話,她也知此時風雨之中,自己觀瞻不雅,此時自己身形曼妙皆現,必然是羞恥萬分,只是今日她來這顧恩殿里“請罪”,實則已經做好了不能全身而退之心理准備,就想透了難免遭主人奸玩身子玷汙貞潔,辱沒自己這一世清白,越是如此,舉止偏偏要守禮,言語自然要冷峻,亦是下意識要維護得自己幾分孤傲自尊之心念。
只這弘晝如此大咧咧的說出這等霸道淫色之“你也罷”、“自然要奸你們的身子取樂”之道理來,她雖孤傲乖僻,其實畢竟是不涉紅塵之少女,頓時不由得羞惱得滿臉通紅,蒼白玉顏上倒泛起一片紅潮來,身子也開始氣惱得戰抖起來,勉強才能收拾神色儀態,口中只咬碎玉牙,切齒答了個“是”。
卻聽弘晝哈哈一笑道:“這便是你的罪?”
接著慢慢低頭彎腰側身下去,湊近妙玉,身後的秀鸞忙將紙傘移位遮擋。
弘晝伸出左手,用兩根指尖微微前探,觸及到妙玉那尖俏冰涼的下巴,指尖一片滑稽柔軟,竟然仿佛有奇香撲鼻而來,不由心下一蕩,再慢慢既挑逗又霸道得將妙玉的玉頦抬起。
這妙玉孤潔自詡,此時無奈只得忍羞順從仰面視主,將秀美嬌媚的五官對著弘晝。
才逼視得片刻,到底還是覺著羞了,將目光躲閃,再不敢直視弘晝,只能將眼簾微微下垂,許是為了遮掩羞辱之意,口中搜尋著話來胡亂答對道:“是,林姑娘並非有意回避主子,實在是病得沉了……這卻都是貧尼的不是……若是掃了主子的興致……自然是罪過。只是若主子責怨了林姑娘,豈非是貧尼唐突所致,但求主子不要嗔怒於她……只管……懲戒貧尼就是了……”她本來是鼓足勇氣才來此地,奈何到底世事經驗不足,被弘晝微微言語一逗,已經是慌亂,說到末一句,已然是細若蚊聲難以聽聞。
弘晝卻搖搖頭,似乎是只管在繼續欣賞妙玉的身姿顏色,半晌才湊上前去,仿佛要湊近妙玉的耳邊,那男子氣息撲面而來,妙玉驚惶得幾乎閃躲,到底忍耐了,卻聽弘晝在自己耳邊仿佛是挑逗一般問道:“那你說……掃了我的興……該怎麼懲罰你呢?”
妙玉心下一苦,緊咬玉齒,悲聲道:“貧尼無狀……憑主子發落,便是死罪也只得認了……”
弘晝幾乎要笑出身來,抬眼更瞧妙玉的身子,此時秀鸞之傘已經遮著二人,只是適才風雨連綿,妙玉的身子早已經濕透了,身上那朵朵蓮紋圖案已經都貼著肌膚,胸前那一對妙乳兒顫巍巍柔漾漾直挺挺在那里,用拱起的曲线和那頭上兩顆微軟顫抖的小肉豆而,哪里還有半分佛清禪冷,只是悠悠訴說著少女軀體的誘人犯罪和美艷無方。
他笑著,左手仍然托著妙玉的下巴,右手已經忍耐不住,伸過去,輕輕在那胸前濕濡濡凸起的那一點上微微一觸。
妙玉頓時如同被電著一般,但覺自己那少女妙胸上,傳來一陣從未感覺過之奇酸異麻,雖然隔著衣衫輕輕一觸,卻到底是自己人生第一次被男子辱及乳房,一時羞憤得幾乎欲要死去,想到若是等會子,不知有多少凌辱奸玩、褻瀆汙弄等著自己這純潔無暇、珍貴貞潔的胸前妙乳,幾乎就要落荒而逃。
只是她到底靈台尚有一絲清明,自己今日又所為何來,究竟世界雖大,並無自己可逃之方,可躲之處。
死命得咬著嘴唇,將陣陣恥辱羞澀,咬牙切齒得忍耐住,還要死命忍耐著自己將身子後縮的衝動。
生生將身子把持住,任憑弘晝輕薄。
卻見弘晝也未曾繼續動作,只是似笑非笑道:“死?你也罷、林丫頭也罷,都是性奴身份,本王泄欲玩弄之禁臠,既為奴,論禮論情論法,都只有用女子身體來讓本王玩弄狎褻,換些許本王的快感來盡本分贖罪孽,人世間才有立足之地,豈有動不動就要死要活的?難道要罰罪,只有一個死字?……你既然說是你惹得林丫頭病了,掃了本王的興致,此時又來請罪,自然是要乖乖用這身子讓本王淫樂上一番才是了?……”
妙玉雖然怪癖,奈何到底本來只是二九女嬌,憑佛經青燈洗沐心緒,到底是少女情懷,今日雖然早已有了失身喪貞,遭辱被奸的想頭,之此時被弘晝半是挑逗半是恫嚇,到底心下淒苦羞恥,五內一酸,眼淚頓時止不住了,自美瞳明目中就堪堪流淌了下來,臉上頓時分不清雨水淚水,漫漫皆是波痕,身子更是驚慌得陣陣戰抖,玉唇勉強動了動,忍耐不住慌亂之心,抗拒哀求道:“主子……貧尼是佛前修行之人,蒲柳之質,卑賤之軀,命犯華蓋,才寄托菩薩蓮座之下……”
弘晝聽她說得楚楚可憐,奈何此時說甚麼“佛前修行”、“菩薩蓮座”盡是推托,卻更增禁忌快感,他自持主人逗弄調戲女奴之身份,亦不顧前因後果,打斷了她的話頭,只管沒口子胡亂戲謔道:“什麼佛前修行?難道本王就奸不得?本王只記得園子里收過性奴女眷,聊以慰藉本王罷了,不記得請過位菩薩啊?便是真請過尊菩薩,既然進了園子……難道……本王就玩不得你這菩薩?”
他口中胡扯只管說著,心癢難耐,又伸過手去,這會卻是隔著衣衫直接撫摸上了妙玉濕濡濡的胸乳,這手上一觸美肉,頓時覺得一片軟滑溫柔,便是他已經品過幾多國色天香,此時隔著濕淋淋的佛衣,能夠撫摸玩弄這修行之女最是羞澀嬌嫩之處,感受著指尖的一片濕濡濡里兜著的肌里肉感,但覺那妙玉的乳兒之形態便如初春小筍一般,圓潤尖俏,雖然不是滿懷脂膩,一手便能把玩,卻向上倔強得尖尖翹起甚是挺拔,其乳形果然是少女情懷,軟妙無方,此時佛衣已經濕透,那嬌嫩乳肉已經貼緊了衣衫,每一觸摸捏弄,便是軟軟得在指尖滑動,竟是說不盡的風流意濃。
那乳豆隔著濕透的衣衫,此時已經隱隱泛出紅色,嬌滴滴挺立起來仿佛就要破衣而出。
弘晝一時情動,更直接開始用三根手指轉圈捏弄妙玉的乳頭,隔著衣衫那一捏一揉,頓時一種說硬不硬,說軟不軟的觸感如同纏綿一般自指尖傳遞到心窩里舒服。
妙玉遭辱,但覺心下苦楚哀戚,胸前恥辱酸澀,那矜持了半日的儀態終於把持下來,待到弘晝隔著衣衫捏弄自己的乳頭,也不知是疼痛是羞辱,實在忍耐不住,身子猛得一縮一躲,將乳房從弘晝的指掌中掙脫出來。
她這一縮身,才想起自己如此躲避主人猥褻玩弄,乃是不敬之罪。
偷偷抬眼瞧弘晝一眼。
卻見弘晝只是淡淡得盯著自己,一對眼中神色如有雷鳴電閃一般,雖不怒而自威,手卻停留在適才玩弄自己乳房的半空之中。
不知怎得,竟然唬得心慌意亂,適才勉強支撐的安靜鎮定已是蕩然無存,慌亂中有些無所適從,心中一片空蕩蕩怯生生,仿佛是群魔亂舞在擾亂自己心神方寸,但覺四下左右無處依靠,八荒六合皆是絕境,也不知是思緒所致,還是下意識,竟然慌了手腳,只是將身子又向前一挺,竟然將自己的一對濕衫裹遮下的胸乳,又乖乖送回到了弘晝尚停留在空中的手環之中。
這一躲一送,透著多少幼稚可憐,淒楚凌辱之快感,倒讓弘晝不由得嘲諷一笑,妙玉仿佛恢復了幾份意識,頓時臉色慘白,如此情形,真恨不得自己立刻死去,方能了卻此間之辱,自己來到此處,本已存了獻身之念,不想遭弘晝言語一逗,便亂了方寸要躲閃,身子遭弘晝小小試探狎玩,躲閃之際,自然是少女矜持吃恥,奈何卻不合禮法身份,只是既然躲都躲了,居然受不得弘晝小小眼神逼迫,就又乖乖得如此主動淫賤得將自己那從未讓男子摸玩過的乳房,又“送”回弘晝手中,這何等可笑,何等悲涼,何等恥辱,何等羞澀使人愈傷愈絕。
弘晝也是受用這小美人的驚惶之後的順從,繼續施展魔爪,只管享用衣衫之下濕濡濡的乳肉觸感,口中直道:“這便是了……便是菩薩的身子……也是本王玩得,什麼修行不修行……恩……摸著倒是軟和受用……,便是那林丫頭一般道理……什麼病了不病了,既然是性奴身份,病了……就可以不來承歡,讓本王享玩?……”
弘晝本是狎玩少女時口中亂言語,不想那妙玉卻驚得睜開了適才因為羞恥而緊閉的雙目,忙不迭愈發將乳房蹭送上弘晝掌心,口中道:“主子……不要!林姑娘……確實有病,她是喘咳病氣,先天來帶來的不足體弱……禁不起的……不……主子……主子若此時定要林姑娘伺候,萬一過了病氣給主子,豈非真是彌天大罪。”
弘晝本來只管受用,只等下一步繼續奸辱玩弄這妙玉,聽她如此緊張訴說,不由心里一動,笑道:“你倒真有金蘭義氣,一心想著護持那林丫頭……既如此,這會子自然是用你的處子身子來伺候取樂……”妙玉此時被弘晝已經是摸玩的渾身酸軟,幾乎就要癱倒在地,幾番忍耐到底是無法阻止五內里傳來的少女初次遭男子近身玩弄時的羞意,口鼻中已經開始嬌喘低吟,腦海中更是開始混沌起來……
話說原來這妙玉,本是蘇州人氏,祖上也是讀書仕宦之家。
她自幼卻是多病體弱,叫有道行之人瞧了,卻說命不許紅塵富貴,買了許多替身皆不中用,到底自受戒入了空門,方才好了。
不想沒幾年,父母雙亡,家族破敗,便更是隔斷紅塵,了卻富貴,只隨著師父同在京郊牟尼院住著,只是帶發修行。
這妙玉雖年幼,卻是經書禪機,詩詞文章,樣樣通達。
之後其師圓寂,臨終遺言“衣食起居不宜回鄉。在此靜居,後來自然有你的結果”。
十七歲上,榮國府為迎元妃省親,要幾個清淨修佛之人裝點櫳翠庵,才接她入府伺候,只是賈府知她向來驕傲,便還下了個帖子道個“請”字。
這等達官顯宦眷族之中所謂府內修行,說是修佛,其實便是賣身給了人家充點門面,寄人籬下,三餐一宿罷了,不過是借著佛祖自我安慰,又仗著賈府詩書禮儀寬厚人家,自己同自己說一聲身份自清淨高貴,絕非人家女婢,用人富貴給養不過是佛家用度罷了,其實也不過是青燈古佛了此花樣年華。
不想才一年不到,賈府事變,內務宗人兩府如狼似虎抄檢寧榮二府,這等族內豢養之女尼,哪里論得佛法人倫,只視為鸚鵡八哥一般,此時也不論佛俗,不論尊卑,只瞧是既是年紀合適之女孩子,自然是一並圈入,為王府性奴,只供弘晝有興之時奸玩享用罷了。
可憐這侯門千金小姐,連遭劫數,連青燈古佛下作個修行了緣斷俗之人也不得已,居然又淪為王府之性奴。
小小年紀,花朵般人品,神仙般作養,冰雪般純美,如菩薩降世玄女臨凡一般之肅穆潔淨之人,居然一邊身著袈裟,口誦梵音,獨對佛祖,輕掀經卷,朝參觀音,夜點蓮燈,居然一邊要隨時等候著以這少女之身,行那羞恥之事,去取悅伺候王爺,真正是人間荒唐事,倒分外令這修佛女尼百轉千回,凌辱難堪。
這妙玉自胎里帶來孤傲自矜,世上凡俗之人本自不放在眼里,習得幾分禪宗密意,又每多知詩書學問,常自言“男女之痴怨孽緣汙穢不堪,歡喜機鋒是六根不淨之魔障”,卻也每每有“世生那汙濁男子為六垢俱全等類,只有女兒家清淨聖潔,更親近佛心,只是紅塵迷亂,三惑難解,若是和男子廝混,情愛嗜欲,自然要入了魔道,唯有得菩薩咒解,方可除此汙濁,了卻苦難。”
這類混解經文之念頭。
她雖自小厭惡男女之事,即被兩府圈入大觀園為奴,卻也不尋短見,偏偏生出來古怪想頭來,自以“浮世蒼生乃是婆娑世界,人間色事亦幻亦空,我這等品格,世尊當不棄我,若是劫數亦是前緣注定,不過是佛祖點化”聊以自慰,雖然長夜深沉之時,也常畏懼時刻可能到來的弘晝奸辱性事,卻也知命數使然難以回避,不過是輾轉反側,禪定誦經度日罷了。
其實妙玉雖知幾分佛理,其實並不曾真正深參禪道,她一心以為自己得知先天之機,其實不過是少女家憑著聰慧冷眼瞧著世人罷了。
其實自己如今這等“性奴”身份,她心下一般是又羞又恥,即覺得褻瀆了菩薩,卻又究竟不敢冒犯弘晝之威,只是一味躲著便罷了,有時無奈時也常幻想迷思,琢磨那弘晝來奸玩自己之時男女之事,即是羞恥恐惶難當,也未免隱隱有一分好奇,不知那是何等滋味,緣何世人皆好此道。
時常也自我欺瞞安慰一番:“以我之容貌,那色王必是早晚要來奸汙我的,想是菩薩許我以孽,煉我心智,我只管閉門不見,日夜頌禱,或虔誠所致,能許我清白。若一日那色王若真來時,想來也是我修為不夠,命數使然。不過是經文上所說佛女孽障,滅法劫數,憑他辱我汙我,我雖不得不從他,卻必不假以顏色,汙我身子不得汙我佛心,此生雖遭人侮,來世必有功果。”
也不過是胡亂自慰罷了。
只這妙玉卻自持才貌過人,凡俗等人雖不放在眼里。
只是她在園子里憑內務府供奉,雖有個小姐的名位,卻不與眾人往來,連鳳姐、可卿處也不去應酬,見了眾人,只是言語冰冷神態倨傲待之以禮就罷了。
眾人也知她性情古怪,並不與她計較。
她自無可無不可,只冷眼看去,但覺園子里只有寶釵、黛玉二人與眾不同,均是世外仙姝、瑤池神妃般人物。
但凡琴棋書畫,詩詞曲賦均高過眾人,見識才具,樣貌氣質更非凡品,便是偶爾談論禪宗佛法,亦能知音一二,寂寞之余,便生了親近之意。
只是又每每厭棄寶釵為人寬和豁達,總以為“她這等人物,怎麼與那等俗人自來往”,就更喜黛玉孤芳自傲、清潔不塵,與自己是一路的性子。
又見那黛玉病軀柔弱纏綿,體態婀娜自怯,自有一等風流之意,若每見其自哀自怨,嗟嘆命數,傷懷悲泣,也不免動了憐憫之意,常與黛玉作詩品茶,聽琴對譜,聊以安慰黛玉,時時也自以為“禪師”,欲用佛法禪機點化於黛玉。
卻日升月落,心下一日較一日覺著異樣,每見黛玉,便自歡心,即喜黛玉之展顏,又喜黛玉之凝眉,即喜黛玉之窈窕,又喜黛玉之怯弱,即喜黛玉之仙才,又喜黛玉之姿容,竟然一路便如走火入魔一般,只日夜痴痴念著黛玉安好作息。
那日寶釵托紫鵑來書請托,她心下雖不甘,卻也有幾分異樣心動,更甘冒瀆神之險,不惜壞了自己清譽佛性,用自昔年寺內帶來的《潮生曲》譜,以誘惑情欲之簫聲在瀟湘館外催動黛玉欲念,讓黛玉與紫鵑女女歡好,泄欲慰懷,免得傷了黛玉身子。
只那一夜之後,她亦自知不妥,卻越發少見黛玉等人,自是誦經斷欲,只望能挽回功果修為。
只今日聽聞黛玉病重,便耿心去瀟湘館里探望,見黛玉雖非大病,卻又是愁思過度,邪魔侵體,才安慰得幾句,卻知黛玉愁思,一半是因為時日長久,越來越難以回避弘晝,只怕弘晝便是排著隊一個個園中女子享用來,也該輪到黛玉了,妙玉也無從安慰,只得寬慰她“這不還有我這方外之人麼……”
兩人才在病榻前說話,寶釵便來奉命探病,寶釵雖不明言,兩人都是聰慧人,如何不知是弘晝有了責難之意。
妙玉見黛玉身子不好,心一橫,便求寶釵帶自己來請罪。
她初來時也想得透:這色王不過是要尋女孩子家玩弄清潔身子來逞他淫欲。
以我容貌身材,雖是佛衣素朴,到底是處子初春,艷蓋群芳的品格兒……
左右將來難逃他的奸汙,便是今日主動迎上去,就引他來辱,便是我受辱遭汙,破了身子……
至少也能讓林妹妹先逃過這病中之劫。
豈非正和了我佛割肉喂鷹,舍身飼虎之意?
便強自來到顧恩殿前跪了,憑雪打雪蓮,要以色相自承劫數。
不想她其實說到底只是一個二九少女,這羞意恥心,春懷軟綿,終究是天性,被弘晝一威一嚇,更是禪心一片凌亂,才有了適才之事之情。
她被弘晝幾句言語折辱,更有:“既如此,這會子自然是用你的處子身子來伺候取樂……”,手上更是輕薄摸玩不止,直刺激折辱得已經是一片混沌慌亂,難以清明答對。
欲知後事如何,請侯下文書分解:
這真是:
禪心似月迥無塵
綸音如滌淸常冷
奈何奴生滅法世
霜雨摧殘女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