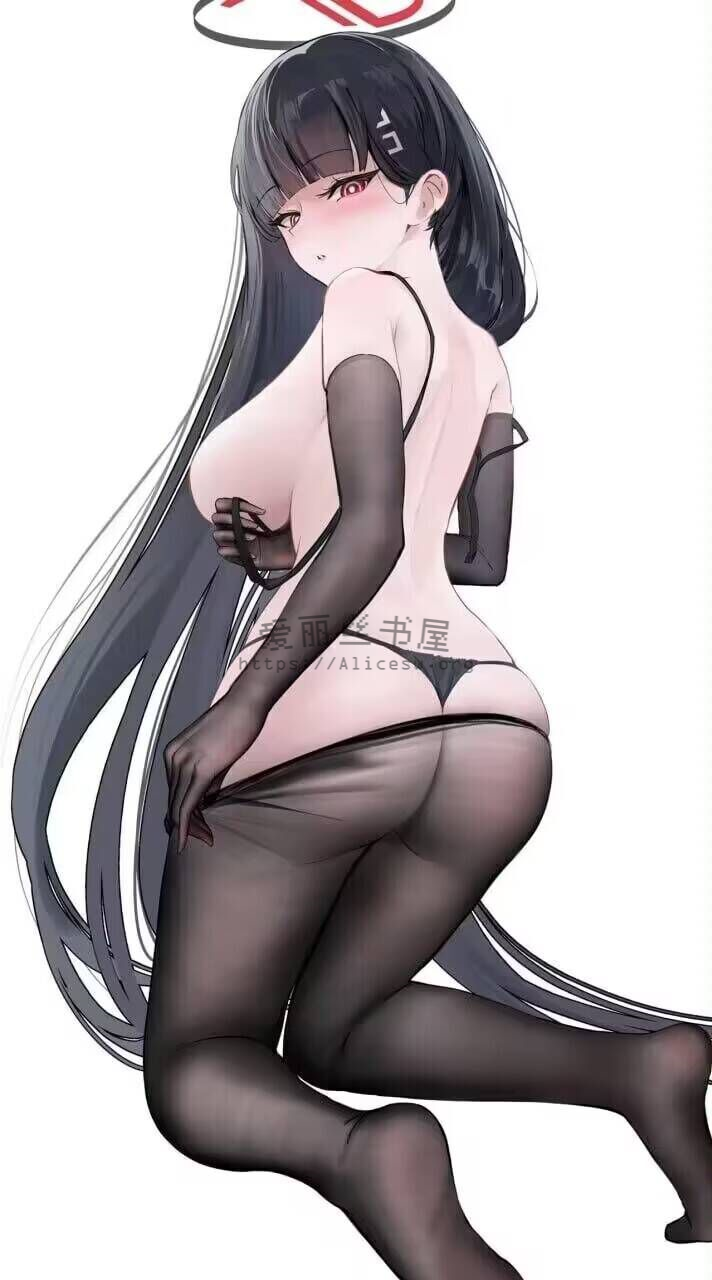每個月份到了十五的這一天里,月亮總是在太陽落下去的同一個時候升起來的。
滿月剛升起來的樣子其實就已經很大很圓了,只是在晴朗傍晚的閃爍天光中不太招人在意。
從一開始就在意看著東邊的女人,一直等到滿天上紅紅火火的晚雲全都收成了昏沉的暮色,這才平平淡淡的說了一聲:月亮真圓啊。
她說,殺我的時候就該到了吧。
每個月份十五的這一天是安西采玉人的祭日。
祭玉在安西是一件有歷史,有傳承的事。
出安西城溯河而上兩百里的水路,沿途可以看盡幾十座蓄奴踏玉的工場。
每回十五滿月正達天頂的時候,每一座工場都要獻祭遴選出來的采玉女人,舉辦儀典,殺生祈福,希望未來的玉事可以更加豐盛。
祭玉要殺女人。
我們似乎傾向於相信殺戮可以贏得世界的回報,我們遇到的各種問題總是可以通過殺掉一個人,一些人,或者更多的人得到解決。
也許我們從過往經驗中得到的教訓就是如此吧。
我們的確知道岫玉隱藏和顯現的規律神秘而且詭譎,並不能被理性的智慧所認識,但是我們仍然確信一定存在有規律。
孕育是因為媾和,萌發是因為雨露,太陽升起是因為有金烏負載,心口疼痛是因為有人做了布偶並且用針扎它。
在這個萬有相愛相殺,生與死對立而統一的天地中間,事物具有普遍的聯系,天行健,而我們自強不息。
我們極盡所能調理互相聯系的元素,嘗試去構建符合我們願景的運勢,日之反的月,山之反的水,石之反的玉,還有陽之反的陰和男之反的女,以及,生之反的死。
踏足而玉現,或者不現,一定是因為月下水中所積蓄的寒涼屬性既會有充盈也會有虧虛的時候,那麼合理的祈玉方法應該就是以陰器滋益其陰。
依照如此推測的天演之道,如果我們祭獻出女人的生命,用女身為河月的血食,也許可以使陰更陰,使玉可玉。
通過直觀就可以判斷,滿月的那一天陰氣最盛。
在滿月祭陰看起來是一個理所當然的選擇。
按照民間口口相傳的說法,那些被挑選出來在這一天殺死的女人都會是一些非常漂亮的年輕姑娘,我們送給鬼神的禮物當然應該是些最好的事。
不過那些傳說的真實性存在有疑問。
其實我們彼此之間用以聯絡感情的贈品從來就不是最好的,它們只是合理的,說得過去的。
一家維持正常運作的采玉工場也會采用一種合理而且說得過去的方式處理玄之又玄的陰陽數術和現實的腳疙瘩肉摸玉之間的關系。
安西的采玉業界經過長期實踐,已經針對祭玉典禮發展出一整套完整,細致,具有充分時間長度的執行程序,被用作犧牲的女人也會遭遇到足夠痛苦而且緩慢的死亡。
非常認真嚴謹的行為模式可以使我們看起來非常在意某事,那就是說,如果我們在意的是另外的事。
正在凝視月亮的女人想到的可能是她的死。
每一個將要成為犧牲的女人肯定已經知道她會遭受到的殺死方法。
並不需要聽人談論,她們已經在很多的月份里看到過了很多次。
她們中的有些人也許從某一個總是不太走運的時候開始就已經猜測過了,在即將到來的下一次的殺祭當中,被所有其他人看到的那個祭品恐怕就會是她自己。
女人們在經歷過持續一整個通宵的涉水勞作之後,總是在早晨返回到河岸上,她們總是覺得累和餓,還有冷。
雖然冰封的季節沒法下河,但是高山融雪匯聚出來的踏玉河即使在夏天也不會是溫暖的,早春和晚秋的河水更是冷得讓人發抖,有時候讓人覺得從自己小腿肚子的地方蕩漾起來的,根本就是一堆尖銳鋒利的琉璃碎片。
晚秋早晨的河灘上有一些荒草和滿地的白霜,她和全隊女人一起哆哆嗦嗦的解開系在腰上的盛玉小筐擺放在身前,哆哆嗦嗦的跪在地下,等待玉場里的監工點算匯總她們一晚上揀起來的收成。
這一天早上她的籃子里沒有籽玉。
也許是因為身體越來越不行了,腿腳和腰都硬,更不行的是心,不過也許就只是因為不夠走運。
滿腳板底下堵著的一直都是跌跌撞撞的石頭,滿心里混混沌沌的也像是堵著石頭,根本就沒有一塊像玉的地方。
從上一個月中的十五開始數落下來,這一個月里她的筐子經常是空的,當然她會挨打,會被餓飯,也許還要被捆住手腳跪到河邊的荒草叢里去讓蚊子咬。
這一個月里她背上的鞭傷一直就沒有愈合過,總是血淋淋的,屁股都被大棍子打的不敢往地下坐了。
踩玉女人每天清早一字排開跪在河灘的時候,還會聽到收完了玉的工場管事們按照記賬清冊,大聲念出每一個女人自從上月十五以後揀到的所有籽玉數量,累計最少的那一個排在最後。
每一個女人一直都知道自己相比其他女人的排行變化,落在後邊的次數多了就很難追趕。
反正等到十五滿月的當天早晨事情就不會再變化了,她在那時就可以確定地知道,今天晚上要被貢獻出去的,的確就會是她自己。
采玉工場在祭日上殺死的女人總是在前一個周期里揀到最少籽玉的女人,這是一件從來沒有人會明說的事,他們只不過一直是那樣的做。
用倒數的辦法挑選供奉用品聽起來也許有些輕慢褻瀆,但是只要不說出聲來,不要讓住在天上,或者河水底下的那些奇怪東西聽到,它們多半就不會在意了。
實際上對於一個使用奴女采玉,希望能夠確保奴隸們努力工作的玉場經營者而言,一場鄭重其事,公開張揚的虐殺犧牲很容易變成一種可以激勵先進,汰換落後的程序設計。
月圓和月圓的間隔可以被當作考核周期,在評定出一個公平的結果之後,使用非常痛苦的方法殺掉那個排在最後的人。
依照著對於人性的一般判斷,在親眼目睹了低劣的勞動效率將會導致的可怕疼痛之後,犧牲者的同伴應該會出於畏懼而將極致的用心投入到尋寶的努力中去。
在被狗熊追趕的時候,你必須比至少一個同伴跑得更快。
末位淘汰制度應該會產生很有意義的結果。
寶石采集行業所關注的另一個要點在於資源供給,如果你是那個吃掉同樣的糧食卻提供最少產出的人,換掉你肯定是一個有益的嘗試。
天演規則的優勝劣汰。
印度王子想。
這事在本質上也許是一種嘗試著擬合天道的社會實踐。
或者所有的神聖信仰都是。
當然了,這是個非常哲學的問題,太哲學了。
王子當時乘坐的那條翹首尖尾的白羊皮船正在緩緩地漂離碎石岸邊,旋轉著船頭進入河道的中流,王子想,他不會在這樣的時間與場合,對他的同船旅伴們討論那種關於天道的問題。
在滿月初升的黃昏之下,劃向西方遠處的采玉奴場的白船上乘坐著兩個男人和三個女人。
男人們背向航线坐在船頭,在他們所面臨著的船體中央,兩個並肩跪立在艙板上的赤身少女正在挺身打槳。
同樣謹守住跪姿的第三個女孩留駐在最遠端的船尾,她的膝頭以前放置一盞沒有點亮的紅紙燈籠,一口空的瓦甕,和一些瓶罐、鐵器、紙片的零碎。
女孩的手臂輕曼下垂,她在交合的兩手中握持一具陶塤。
三個年輕女人都是全身赤裸,手腳系戴鎖鏈的玉事奴隸。
岫兒雖然在以前的幾天里被安排當做王子的向導,但是她在滿月之夜仍然需要承擔被賦予的責任。
岫兒和另一個女孩正在劃槳。
她們纖巧柔韌的赤裸身體在王子面前三尺之外的船板上俯仰頓挫的樣子,如同在風中搖曳的小白楊樹。
乳房下動蕩的銅鈴,和船舷外邊被打破的水。
王子現在已經發現游歷安西的旅客可以從官定的玉奴制度中獲益的一條隱秘路徑。
每當男人獲得機會直面一些年輕的,好看的,赤裸裸的女人胸脯的時候,安西既有的社會共識更為他提供真誠,開朗,無需顧忌公眾負面評價的觀察位置。
坦蕩暴露的天然身體既然已經在法律以及事實的兩個層面成為安西婦女生活的一個有機組成,一個精英階級的衣冠男人當然擁有細致周全地審視社會普遍現實的道德權力,你不會自責或者羞愧。
姑且不去討論更多的深入考察實踐,安西提供的視覺福利並不僅僅是那些沿街或者溯河時候繽紛環繞的光身子女人。
安西使你凝視。
印度王子凝視了岫兒運作自己纖細的腳踝提高鐐鏈的負重,跨越過舷側擋板的整個過程。
不過等到她面向著船頭跪正,那一雙稚朴於輕肌,卻又守拙於沉銅的赤腳便被她自己的窄腰軟臀悄然遮掩到了身後,女孩附身撿起又一面銘牌,低頭鈎掛到洞穿過自己右邊乳頭的環圈底下。
王子事先已經看到這一件循例仍是銅質的標識比較原先懸系的安西府奴牌照更加闊大,做工也更精細,牌面周邊環繞有龍和鳳的紋飾,中心凸顯出來的古色古香的篆體文書應該就是讀如一個祭字。
當時女孩的右乳以下有一小銅方曰府奴,一大銅方曰祭,兩副金屬的器物琳琅堆疊,沉沉欲墜,已經將女孩這一邊的酥軟胸脯拉扯成了凋謝的百合花朵一般,等到她操起木槳前後發力起來,還不知道會招搖出一個什麼樣的動靜。
岫兒在發力操槳之前最後所做的事,便是將自己脖頸上的系鏈鎖定到船邊的一處鐵制掛環上去,她也將抽出的鎖匙放置在自己攏合的膝頭前邊。
實際上登船的奴隸姑娘們都是同樣的長跪,攏膝,給自己的乳頭底下掛好出祭的銘牌,並且為自己上鎖。
她們的行止工整流利,她們的神色馴順安穩。
已經坐定在王子身後,更加靠近船頭的第二個男人說,還有一陣子水路要走呢,讓丫頭們費勁倒飭去吧。
那人一巴掌拍在王子的右邊肩膀上,兄弟,來上兩口?
第二個男人是一個身形十分壯大,長有許多胡須的漢子,他把手中提起的一具盛酒皮囊朝向轉臉的王子懷中直塞進來。
王子知道這一位胡須兄弟是安西駐軍派出的軍官,他在今夜需要負擔的責任可能是一些應該被稱作監祭的事。
軍官上下披掛一套全般的皮革甲胄,腰間佩帶彎刀,但是卻在頭上戴起一頂現方現棱,十分峭立聳直的高帽子,黑色的方形高帽上繡有銀色的雲紋,實際上那東西使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出發去唱戲的人。
幾乎像是為了能夠中和掉那種會被所有人意識到的不協調感,魁梧並且虬髯的漢子在臉上顯露出來多少有些討好意味的憨厚笑容。
其實吧。
這種事看多了就沒什麼大意思了。看到等閒了,就跟平日里殺個雞一樣。有誰一門心思盯著殺雞去看的?
看少了也沒意思。剛看過一回兩回的時候,他就得老那麼想著,想過來想過去的,一閉眼睛哎呀滿腦袋都是……漿糊一樣。
所以倒飭這種事都要喝點酒。喝好了以後不溫不火,看什麼都透著快活勁頭,快活完了兜頭便睡。喝酒有意思。
軍官說,這位公子兄弟,早年待在你們自家印度的時候,見過活剖姑娘沒?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統治安西的韓將軍很早就已經認識到了管控民間淫祀的重要意義。
公權力的施行天然地憎恨一切私相授受,他當然不能任由著自己治下的山野草民一不高興就活剖個大姑娘把她送去見鬼。
如果一定要送,那也得是官家來送。
韓將軍領導的安西鎮守從祭玉的時間,地望和資質等等幾個方面著手,塑造並且規范了玉信仰的意識形態。
祭玉的時間順應民俗,確定就在月之滿盈,祭壇設立雖然可由各個奴場選點自建,但是必須上報府中批准,待等到得了當此時,當此地,尊天,循理,祈玉安民的那一場殺祭重典,經手操辦的巫祝男女更是必須經由鎮守府中授權派出。
如此一來,韓將軍便將安西地方連接天和地,玉和人之間的溝通管道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安西鎮守府中原先已有掌管玉業的弄玉閣,這些給玉神玉鬼磕頭送肉的事也就交給他們去統籌管理,當時遇到的一點麻煩,是閣里平常只管玉石交易,還有礦奴的贖買之類,並不專攻殺人。
弄玉閣里除了一些擺攤守店,展覽當地河玉文化的奴隸女孩之外,管事的都是精於算賬簿記的文官。
每到十五的祭玉當口上,安西城里可是要一連氣的派出幾十條舟船,奔赴所有礦場去殺姑娘的。
將軍說,就是要去殺個人啊。
殺人怎麼就成了件難事兒了?
對於一個把打仗當作畢生職業的武人來說,這是個合情合理的關於世界的看法。
將軍的麾下當然另有許多低階一些的副將偏將,還有兵士,他們的看法也都和將軍一樣。
從那以後弄玉閣領銜的祭祀典禮都會邀請軍隊派員協助,專門負責那幾下子真刀真槍的實際操作。
雖然再後來的程序安排又發生過一些調整變化,不過這個軍官監祭的法統一直保留了下來。
武人出祭著甲佩刀,氣質陽剛,可以震懾月夜水西,歃女血,盟碧玉的極致寒涼,其實也是與逢盈防虧,遇滿思溢的陰陽命理暗合。
不過這事或許還可以有一個更加直白的說法,那就是老子派兵盯著你們呢,別他媽給我整出什麼妖蛾子來!
無論如何,將軍還是從善如流地接受了幕僚的建議,命令那些監禮的軍官在履行責任時戴上特別設計的,可以彰顯出神聖和威儀的一種所謂祭冠,官員們都覺得那是個能夠將殺伐與頂禮統合成為一體的好辦法。
實際上,祭玉也是一個能讓殺人和娛樂結合到一起的好辦法。
很多人,主要是男人,會在祭祀的這一天從很多里地之外的安西城中前去采玉工場觀看典禮,他們會在城外租乘那些使用玉事女奴駕馭的白羊皮船溯河而上。
在暮色和月亮底下的原野平整而且廣大,積雪的山脈一直是在非常遠的南方,它們的起伏,褶皺,還有無窮無盡地綿延的樣子在晴朗的白天顯出沉默,凝聚的自然力量,但是它們在月夜變得迷茫。
女人從她所在的沙土漫坡上極目展望所見到的似乎只是踏玉河水宛轉的波光,踏玉河的深處有時是會凜凜的散漫出清光的,而後她會從雲水之間分辨出正在遠方飄搖行進的,星星點點的航船燈火。
在女人逐漸地抬起眉眼之前,她看到的沙土坡地從她自己曲張的足趾和筋腱收束的跟踵底下繼續延伸出去,在二十余步之外變成了河岸。
祭玉所用的木作平台還在河岸之外。
那一座連接著沙沿,但是前伸入河的棧台是使用了厚木寬板鋪面,倚靠著釘下河床的樁腳橫平在水线以上,長大方正的台面上另外樹立有兩支高峭的木柱,它們相隔著三尺的距離並排設置的樣子,在臨河的空曠之中劃定了形狀和界限,它們像是一座連接沙陸和水域的空門。
那是奴場中每一個女人熟稔於心的祭玉的門。
它也是女人們平日入水采玉的門。
並列的立柱可以約束犧牲女人的肢體,確定她在祭禮的延續中應該保持的位置和姿態,而平整的棧台在沙坡和流水之間提供了一處穩定的立足場所。
每一天出發勞作的女人們排成整齊的隊列,鐐鏈啷當地走上木台,她們循序穿越門柱,沿著台邊遠側的步梯拾級而下。
在那以後女人們的赤足將遭遇到十數里的亂石,散玉,還有奔流在石玉之上的十數里寒涼的水。
安西境下的采玉工場應該都是遵循著相同的運作方法,它們也總是會被建造成彼此相像的樣子。
每處玉場都只是一片暫時地居住人群的空泛荒涼的河灘,河灘上會有一間孤單的木板房子,那里邊住著工場的管事和守衛,會有一長排葦草鋪頂的棚屋,當然,還要有一群住在棚屋里的,被相關律令禁止了穿著一切衣裙襪履的奴隸女人。
實際上采玉工場會沿著河流遷徙自己的位置,它們在使用女人的腿腳仔細搜尋過當前河段積底的每一寸沙石,揀走混淆其中的玉塊之後,就會出發前往另外的收獲水域。
每到一處新的河岸,他們都會重新搭起木房和草棚,也一定會在岸邊建造一座新的棧台用以登臨入水,當然,還有殺生祭玉。
每一天赤身裸體的采玉女人們都在這片河邊的沙土坡地上看到日落。
她們知道還會有很多人在這里看到自己的死。
很疼的死。
但是在疼和死確定地到來之前,她們仍然需要振作起精神,努力去渡過更多彼此相似的,周而復始的日子。
每一天她們都要在這個時候開始排列隊伍,准備著隨後將要持續一整個晚上的水中跋涉。
在那以前女人們已經離開居住的棚屋等待在河邊了,現在她們零零散散地,倦怠地從沙土中站立起來身體,而她們身體上佩戴的鐵質刑器互相觸碰,發出此起彼伏的金屬聲音。
有人輕聲嘀咕了一句,這棚子外邊的風吹上來……
像是比昨天更冷了啊。
當然了,下水以後還會更冷,女人們總是希望會有更多一些暖和的天氣。
但是沒有人接上她的話頭。
大家都在檢查整理著自己手腳腕子上拖帶的鐐鏈鐵環,把環圈和環圈之間扭轉打結的地方調換通順。
女人一開始要收拾的還是緊連在腳跟後邊的那一副重鐐。
整個白天工場里的所有女人都只能單靠自己的腿腳硬生著拖帶鐐鏈行動,這些沉重的刑具本來就是為了禁制女人們日常的舉手投足,方便管束。
不過下到水中以後一副拖延在身後的鏈子很容易被河底的亂石勾住卡住,那樣就會影響到正常的工作進程。
所以走河以前女人們都要使用一根草編的繩子系住腳鐐中段,好把那些生鐵的累贅提高一點拴掛到腰上。
女人坐在沙土地上的時候總是往身體前邊寬緩地伸張開去兩條腿,她現在已經在手里扯住粗草繩索的一頭,下邊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要把那些大包大攬,總是繞成了麻花卷兒一樣的腿腳和鐵,一齊收攏到自己的屁股跟前來。
抽動了一下兩下都沒怎麼管用,還得再攢上第三回力氣。
自從住進了奴場以後,女人總是覺得她那些腿腳都不像長在自己身上的物件,連鎖在她左右兩根腳脖子中間的腳鐐鐵鏈太沉了,可能要有快三尺的長,那些使用手指頭粗細的鐵條盤繞出來,一個一個穿綴在里邊的大的長的黑鐵環圈,她撐開手掌的虎口都量不住兩頭。
要讓一對淺轉輕回的細巧女人踝骨去承負那樣一條豪橫壯闊的東西當然已經很能吃住腳力了,不過從女人右邊的腳踝往後數到的第二個大環里邊,還被另用長杆鐵鎖掛進了兩個打鐵大錘的錘頭。
這就是說的,有時候嫌尋常鐐銬磨折不夠還要故意再拴兩塊生鐵,直是要教你好生的見識著,領教著,甚麼一種樣子可以叫做個烈火烹油,還有錦上添花。
做奴隸的女人總是要被人教出來各種各樣的見識。
要是你的奶頭底下或者腿股夾縫中間被鈎掛上了一個帶刺的小鈴,你就是個做人肉包子出道的強盜婆娘也會學成一副溫良恭儉,戰戰兢兢的樣子。
不管是為了調教,還是為了振發金聲引動人玉之間莫須有的神秘關系,戴鈴踩玉在安西也要算是一件做玉相關的傳承風土,尋常都能在工場見到。
那些圓面上遍生尖刺,內腔里包藏有活動響芯的鏤空鐵球本來都是與刑禁用具一樣的黑鐵質地,當然也是一樣的粗野生愣,偏偏還要使用機巧縝密的環圈系鏈把它們和人身上特別軟嫩的地方糾結去到一處。
人身一有動換你自己是知道的,生鐵和扎刺可不知道,它們的動靜你也不知道。
互相都不知道的時候欲拒還迎,鐵的尖角可能就扎進了你的肉。
女人從松軟的沙土堆里慢慢抽回來她的腿腳的時候,她一邊是用一只手把貓在腿胯里的那個刺兒球遮擋在掌心里的,反正自從這個又活潑,又鬧騰的小兔崽子占住這麼個地方之後,她就很少再能合攏過腿縫了。
她每回需要立身站直的時候,其實都得往身體兩邊斜著撐持出去兩條腿,分叉都得分到比左右肩膀更遠的外邊,走步子的時候腳板也不能回中,她一直都覺得那種步子就是一個往前平行著挪移的大方框格。
就算現在坐到沙土窩里歇息的時候也是一樣。
反正一直得給中間留出來一個雙開門的鋪面,而且一直都不能有一把遮擋。
一種那麼多年下來什麼都沒穿著的女人生活已經很奇怪了,更奇怪的大概就是那麼多年里什麼都不穿,還得一直叉分開腿胯過日子的女人生活。
好像是,每回她往那底下留一點神的時候,就會發現里邊的肉皮褶子總是被鈴鐺拉扯著垂墮在外邊的,而且相比早先總像是又被拉長了幾分,一回比一回更長,褶子收夾包裹著的芽苞也長,而且還大,血氣旺盛,興致勃勃的大。
掛鐵鈴的環圈有一根筷子那樣粗細,橫梗在她圓潤珠子的稚嫩心蕊中間,一年一年刺刺啦啦的磨琢,當然它還要連帶著鈴鐺的重量往下拉扯。
拉扯磨琢刺激出來的寬皮贅肉一層一層滋生,把她那一丁點女人的如意骨朵撐張成一大顆墮墜到了葉片遮掩之外的西域馬奶葡萄。
女人的手指頭按在上面輕輕摸摸,輕輕的哆嗦一下。
就那個又剔透又招搖的樣子,任誰都要往這家早晚總是開著門,擺明了貨色的檔口里多看上一眼兩眼吧。
女人從河灘上站起來身體的時候胸脯前的奶房總是撲簌簌的搖,奶房頂頭上拴住的鈴鐺飄搖起來的動靜更大。
一副胸脯上邊,兩個頭都在響,女人抬手起來收住一個,別讓它們飄大了繞到了一氣。
女人的手上也是戴著銬的,雖然系鏈不長不能怎麼樣的開合,好處就是還算輕巧,當然那是因為采玉工場里原本就指望她們下手撿采的時候動作輕巧。
兩邊的奶房都是一樣的有鈴,有環,各自也都長著一個越是拉扯越是粗長茁壯的烏黑奶頭。
誰把這樣一個長著勃勃的陰蒂和茁壯大黑奶頭的婦人看到第三眼上,一准就會覺得她興許還真賣過人肉包子。
從河灘里站起身子的女人們眼睛往下,再抻一抻腰間盛玉用的草編小筐,看看這個能給自己掙飯食的家什是不是真的拴結實了,就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什麼時候,在家里出門趕集以前打量一回挎肩的藍布印花包包。
也不知道多久的以後還有沒有點指望,能夠提一個更精整點的小竹籃子,自由自在的上山采蘑菇呢。
采玉女人周身遍體都不能有寸絲牽掛,當然也不能系上一條用布的,用麻的腰帶,玉奴從手足到頸項一身用鐵,腰也用鐵,玉場里的所有奴隸女人都是使用這一圈鐵打的連環圍腰,再加前後的系鏈全部拴鎖到一起的。
草籃子都是寄掛在鐵上,鐵都是寄掛在光溜的胯骨和肚子上,即使是在女人們踩過了一整夜的河,回到工場,睡進了棚子以後,她們仍然會被腰鏈拴鎖在一起。
除了先要大聲報告才能得到的幾次解手方便,或者是有一天病倒了再也爬不起來,她們已經這樣地度過了住進玉場以後的每一天,住過三年的就被拴過了三年,住過五年就被拴過五年,她們已經不像是一個,和另一個單身的活物,她們活得就像是一整條長的大的爬蟲為了踽踽蠕行而挪動起來的,那許許多多條腿。
在每一個河面上開始逐漸變得迷茫的傍晚,排在踩玉隊伍最打頭的幾個女人開始走動起來,她們會逐漸地帶動起身後邊跟隨的每一個人。
實際上玉場里的女人們白天住在棚屋里的時候可以使用火盆取暖,她們也在那里邊吃掉了好幾大塊烤羊肉。
玉場里專門用人砍沙柳梢子生火,找周邊的牧民買羊,采玉工場在吃和住的事上並不吝嗇,當然了,只要你是那個能揀到玉的女人。
你得是一個每夜出走到西北邊地的霜天秋水中去,一直都能揀到玉的人。
還有就是鐵鏈仍然是鐵鏈。
那樣一條前後相接著延伸出去幾十丈的金屬長物,單靠赤身永遠捂不出一點點的熱活。
天地間凡是金鐵之類都是極能夠吸納熱力又源源的傳散出去周邊的屬性,人從外邊看到你身上的鐵打刑器都會知道那是個收束負累,他們不知道的是你從里邊緊貼住的鐵器除了負累,它還是你緊握在手心里放不開的冰。
薄的體溫沒有底的去填寒世的深淵。
一副腰環在冷夜里就是一塊壓鎮在女人溫暖矯揉的肚臍上的冰。
一個帶著粗鐵腳鐐的女孩子在冷夜里永遠緩不過來她的冰涼的腳趾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