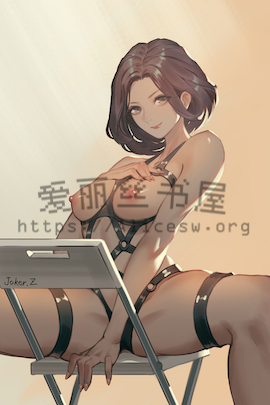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公主。”
見薛品玉醒來,劉子今急切道:“身體可有不適?”
小肚子墜漲,想要如廁。
薛品玉不方便同劉子今講,虛聲問道:“桃夭呢?太醫呢?”
“他們都不在,公主想做什麼,你告訴我。”
“恭桶。”薛品玉轉過臉,摸到自己額頭上搭了一塊熱帕子,渾身不舒坦,將熱帕子扯下來。
劉子今立馬吩咐候在一旁的奴才去准備恭桶,把薛品玉扯下來的熱帕子拿到手里,擦起了她的臉。
“公主發燒了,額頭滾燙,那些蠢奴才們備上的帕子浸過冷水,要為公主降溫,可公主如今這個身體,受不得寒,碰不得冷,我將他們罵了一通,讓他們換來了熱帕敷上。”
熱帕在薛品玉臉上走了一圈後,被劉子今放在了薛品玉的額頭上搭著。
此時,門外兩個太監抬著恭桶走進,放在了屏風後。
薛品玉再次扯下搭在額頭上的熱帕子,撐著身子從床上坐起來,要下床如廁,劉子今去扶她,她抽回手,說道:“你該知道的事,不該知道的事,你都知道了,為何還留在本宮身邊?本宮不缺伺候服侍的人,你找個清淨的地兒去呆著。”
“找個清淨的地兒,一個人躲著哭嗎?我無事,我比公主你認為的要頑固,我雖雙腿殘廢不能走路,坐在素輿上,但我能為公主出力,我定當竭盡全力。”
薛品玉看向坐在素輿上的這個男人,衣服已從昏迷前看見他身穿的紅色喜服,換成了一身素白黑紋。
他整個人,似與成親前見到的不一樣了,感覺上,就是不一樣了,有什麼東西,在悄無聲息間發生了改變。
薛品玉小腹陰疼,需要劉子今在一旁扶著,才可以在恭桶上坐穩,她花了三炷香的時間,才把體內的死胎、血塊、穢物一一排出。
那孩子已成了形,像只沒毛的小老鼠,薛品玉依稀看了一眼,就不願看第二眼,讓奴才們抬下去倒進糞池里。
這出乎劉子今的意料,以為她會大哭大叫,再不濟也會叫人把孩子屍體裝好,找個地方埋了。
她的冷血與淡薄,讓劉子今匪夷所思,懷疑她究竟是不是薛品玉。
桃夭從外走來,端著一碗太醫開的藥,要服侍薛品玉喝下,劉子今坐在床邊,自然地伸手去接桃夭端在手里的藥。
“我來。”
桃夭看了看薛品玉,薛品玉沒有拒絕,她就把藥給了他。
劉子今舀起一勺藥汁,在嘴邊吹了吹,送去了薛品玉的嘴邊。
那藥苦到薛品玉皺緊眉頭,艱難下咽,在抿下那難喝的藥後,她就當劉子今不存在似的,對桃夭說道:“太醫可打點好了?”
“回公主,打點好了。”
薛品玉嘴里泛著一股藥味的苦,可這遠不及心中的苦,她道:“你去尋個與本宮差不多月齡的窮苦產婦,提前與婦人說好,花錢買了她孩子,待她孩子降生時,本宮也要進行生產,將她孩子抱來,蒙混騙過皇兄。”
假若此時失了孩子,讓皇兄知道,今後自己還怎麼立足,母憑子貴,任憑生下是女還是男,都是皇兄的第一胎,便都能憑此胎穩固地位。
桃夭:“是,公主。”
這是最好的處理方法了。
與其到薛滿面前哭訴賣慘說孩子因俞飛雁流產了,還不如就這樣靜悄悄地處理了。
薛滿對抗不了俞飛雁,向他訴苦也白搭,不如快些把失去的傍身之物,迅速想辦法找回來。
薛品玉深知這在肚里夭折的孩子,就是她今後的依傍,她要假孕,要‘生下’這個沒有血緣但至關重要的孩子。
被視作隱形人的劉子今一聲不吭,直到把那碗藥全喂給了薛品玉,他放下碗後,掖緊了薛品玉蓋在身上的被角,說道:“公主冷嗎?”
寢殿內點滿了蠟燭,看上去很溫暖。
春天不遠了,一想到冬雪消融,花朵競相開放的場景,薛品玉覺得自己這忽冷忽熱的身體再糟糕,都能熬過去。
“不冷。”
饒是回答了不冷,劉子今也還是往前俯身,輕輕抱住了薛品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