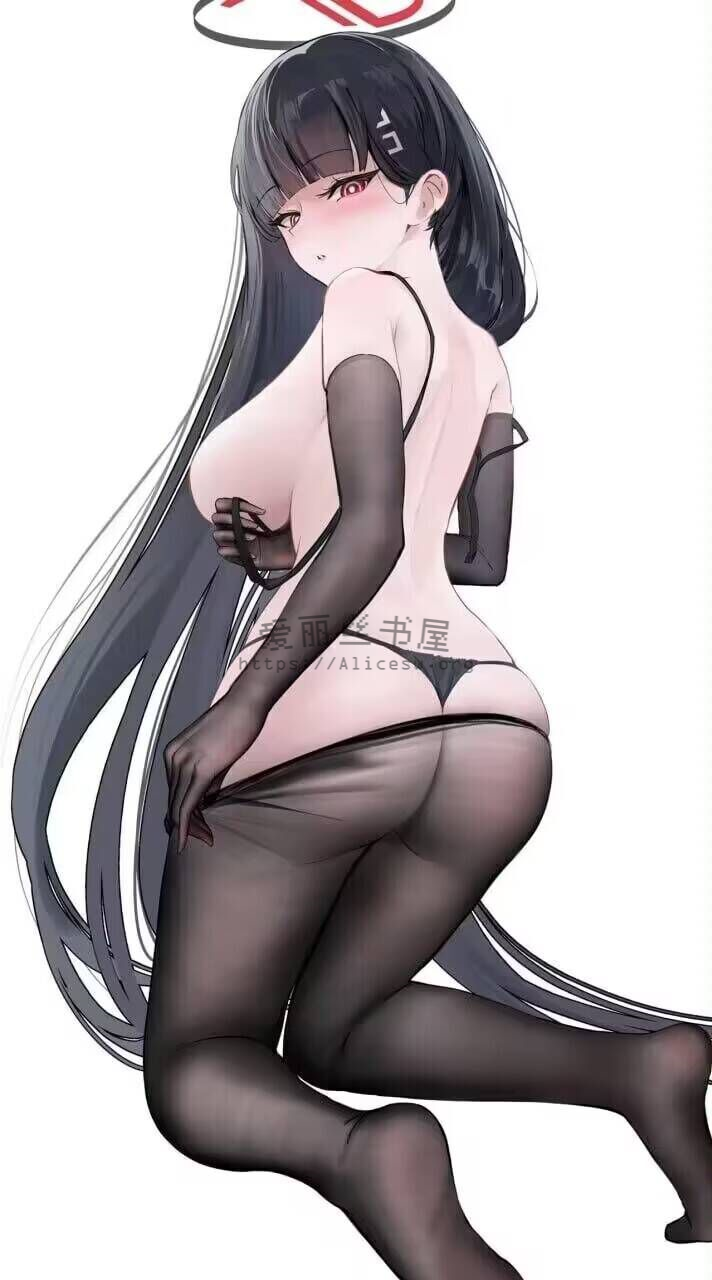第9章
再過幾天就是五一黃金周,這次府辦排的領導帶班值班表,江凇月是最後兩天,呂單舟就有了回家鄉探親的念頭,畢竟春節沒回去。
與女領導說了這個意思,江凇月當即就表示同意,而且還加碼,她要跟著去。
江凇月與方家決裂,與娘家似乎也是冷冷淡淡,七天假期還真沒什麼地方可去,只是呂單舟家里的條件實在不怎麼樣,怕是會委屈這位想著去玩兒的女副縣長。
三家村距羅林有兩百多公里,先是火車到縣,再是鄉村客車到鎮,最後是一人一輛三蹦子,回到村口。
這地方種的大概是早稻,五月正是插秧的季節,走在機耕道上,不斷的有人發現這衣著光鮮的兩人。
“是呂三伢子回來啦,你媽昨天還念叨著呢!”
“三叔公,過兩天去你家插秧!”
“三蛋,帶女朋友回來認門啊。”
“你看三蛋對象,城里人她就不一樣,你看那手背多白……”
農村人大概都看不懂城里人的真實年齡,這女人很清新脫俗的樣子,那就是三蛋女朋友無疑。
江凇月臉有點紅,捅捅呂單舟道:“哎,你的名字真多,他們怎麼還叫你“三蛋”?還當人家叔公!”
幸好是農忙時分,要不經過村頭那大榕樹下,得從左右兩排大媽大嬸的如刀目光中穿行。
“輩分大嘛,我是老呂家的第三顆蛋,就“三蛋”。”
呂單舟忙於應付村民的熱情招呼,他是三家村能飛出去為數不多的金鳳凰,就成了大人教育小孩的榜樣,是稀罕人物。
這時還能聽到婆娘們大大咧咧的聲音:“三蛋相的小媳婦兒可了不得,你看那屁股,比荔香的都大,一胎兩個都是少的,嘖嘖……”
“我跟人家比啥子,人家是吃營養品吃出來的,肉多,我是砍柴火砍出來的,骨架大——”大概是那位荔香不樂意了。
“你說那城里人怎麼過日子的,手白腳白,哎穿那麼高的鞋子,走起路來比扭秧歌都好看!”冷不丁冒出一個男人的聲音。
“看哪呢!看秧!要看一會你看她走石子路怎麼走!”
一片哄笑聲……
江凇月臉特別熱,感覺在大會主席台上做報告都沒那麼熱,看到呂單舟笑嘻嘻地看著她,趕緊道:“我箱子里帶有運動鞋……”在羅林,她下鄉要麼是平底鞋要麼是運動鞋,也不是沒經驗。
只是這次跟這小秘書回家,按說下鄉游玩嘛,就該穿運動鞋,可她神使鬼差就一根筋地想著,第一次和他回家,就得穿正式的,哪怕多帶一雙鞋。
回家前的一天,在她的好奇心驅使下,呂單舟簡單說了下自己家里的過去現在將來,他家所在的小村是戴帽子的貧困村,家里在村中本也算中上生活水准,可年幼時父親一次開山炸石弄了個拐瘸腿,生計就有所拖累,一度成了貧困村中的貧困戶,父親在村里沒少被小童們嘲笑,跟在後面學走路姿勢什麼的。
呂家兄弟三人還算爭氣,長大成人後各有各的小成就,才漸漸扭轉了呂家在村中的地位,要是說幼時經歷,呂單舟的童年怕是比女人的來得更艱苦,但並未給這陽光大男孩帶來絲毫陰霾。
江凇月暗自佩服著小秘書的樂觀向上精神之余,卻也給自己種了顆小心思,不知怎麼想的,這天出門前她就很是費心思地收拾一番自己,還偷偷出去做一次頭發,選一套特別顯年輕的小西裝,將一對精致的高跟鞋擦得鏜亮,很有要為曾經遭受白眼和譏諷的呂家爭點臉面的意思。
呂單舟還是習慣性地落後女領導半步,拉著她的的行李箱,笑道:“領導別理會那幫子悍婦,她們還是小媳婦的時候去哪都是被點評的對象,生過孩子奶過娃,成婆娘了,才敢對別個的小媳婦評頭品足,這是把以前當小媳婦時受的擠兌給發泄出來呢,她們就愛看你臉紅——”
說著也是忍不住,不斷瞄向女人的圓臀,這臀部他看過無數次,但像現在這樣明火執仗地“欣賞”,那還是首次。
“姐,要說她們心里還是有一把尺子的,荔香嫂是真比不過我小媳婦兒……”
女人在腦子里繞幾圈才知道他說的什麼,想發作又發作不得,眾目睽睽之下,辯又辯不過這些流氓話,一把搶回拉杆箱,怒道:“前面帶路!”
偷偷摸一下自己屁股最翹那部分,圓,還彈,不知道該是羞臊還是驕傲。
這是她為數不多的跟在呂單舟後面走路的情形,紅著臉低著頭亦步亦趨,遠遠看去還真像剛過門的受氣小媳婦兒。
呂家坐落在一個小山包的山頂,周圍還有三幾戶人家,三伢子的歸來成了小山包的頭等歡樂大事,幾家人將飯菜都端出來,宰兩只雞再加幾盤煙熏肉,湊在幾戶房屋圍起的曬谷坪上,挑燈夜飲。
乍回到時呂母也以為兒子帶了個驚喜回來,搞清楚狀況之後失落一陣,很快又回過神來,拉著江凇月坐身邊嘮家常,老人年紀大了嘴碎,江凇月慣常下鄉下基層,有自己和鄉親們打交道的一套本領,三言兩語和老人家打成一片。
“原來三伢子問的野芝麻——就是你們說的益母草——是給閨女你用的吧?他還要配上指定的什麼花的蜂蜜!又說城市里的蜂蜜都是西貝貨,說給女人調養身子的東西馬虎不得,讓我去找村里的人買。我說既是這樣,三家村里的也不指定是最好的,他二哥翻了幾個山頭找養蜂人家兌的陳年老蜜,閨女你放心的用!”
呂母拍拍江凇月手背:“咱們女人哪,自打生下來就比那些殺千刀的男人虧一大截,我看閨女你也是操勞出來的,有事情你得讓三伢子去做,你坐著指揮他就行!他要敢蹦半個“不”字,你跟我說!”
呂母末了得意地小聲道:“三伢子他誰都敢犟,就不敢逆他老娘。”
呂單舟宿舍里擺放的那一排有桂圓蜜、黨參蜜、枸杞蜜、益母草花蜜,到現在她才知道原來都是那二愣子秘書有目的性收集的,無一不是針對婦女理氣益血的蜜中佳品。
那人,干嘛要把這些藏在心里都不說,被她委屈了也不說……
江凇月雙手放在老人家粗糙的手掌中,任由她摩挲著,陣陣感動涌上心頭,這種被人無聲地真誠地關愛著的情形,已經很多年未曾享受過了。
她看一眼地坪中間還在與一圈男人豪放碰杯的小年輕,連聲道:“小舟平時很能干的,也都是我動嘴他動腿,都累著他了。”
回來之前江凇月說過,不准透露她的職位,只能說是同一辦公室的同事,所以呂家老母還真以為兩人之間是簡單的平等同事關系。
第二天清晨,江凇月起個大早,昨晚就聽男人們商量今天要給一家耙田,另一家的田可以插秧,呂單舟回來得正是時候,她就想跟著去。
這小山頂的四戶人家從來都是結伴做農忙,做完一家輪下一家,像個小小的互助社,讓她感覺十分新鮮。
這里才是真正的山村,放眼望去小村莊被群山環繞著,白色的公路從天際线蜿蜒而來,臨近了忽地消失在群山之間,而後又從山間忽地冒出,筆直插進村莊之中。
此時能看到山下農舍垂直的炊煙,一層薄薄的晨霧籠罩在村莊上空,晨風拂面,雞犬相聞。
正沉浸在山村的清新空氣中,突然廂房呯地竄出一人,正是她的秘書,羅林縣人民政府辦公室呂單舟副主任,然後是呂母罵罵咧咧地拿著掃帚在後面追。
江凇月大驚,“哎哎哎”地想阻止事態發生,又不知該攔哪個。
“大妹子別管他娘倆,三伢子沒准就故意去找打來著,走咱們吃早飯去。”二嫂不知什麼時候捧個飯碗經過身邊,見慣不怪地道。
“這是什麼道理?”江凇月奇道。
“三伢子說的,讓老母親保持戰斗精神。”二嫂笑道,“這不剛就學人家城里人,去叫老母親的小名兒——不管他們,揍幾下兩人都高興。”
什麼叫“揍幾下兩人都高興”,挨揍的能有揍人的開心?江凇月有點不明所以,但能想象得到二杆子秘書以前在家沒少弄得雞飛狗跳。
說話間呂單舟已經跑到她們身後,隔著兩個女人怪叫道:“大哥二哥都能抽,我怎麼就不能抽了。”看來又扯到抽煙的事。
呂母見到江凇月就有點訕訕,昨晚還吹噓能治這孫猴子,今早就被他打臉了:“讓大閨女看笑話了——這小兔崽子,你看給他倆哥帶的什麼回來——幾百塊錢一條的煙!十幾條!”
指著呂單舟喝道:“你那兩毛錢工資,夠買卷煙嗎,就抽這麼高檔的。都跟你說了城里人不興抽煙,你一身的煙泡味道,哪個女孩願意跟你!”
江凇月連忙道:“大嬸消消氣兒,三伢子那是工作需要,抽煙也是應酬領導聯系工作什麼的,我們那里的風氣,男人見面都遞上一根,連我這女人,他們都照遞不誤,臉色都不帶改的,遞順手了。”
再瞪呂單舟一眼,不知是瞪他一身的煙泡氣味兒,還是瞪他惹老母親急眼。
“真的?可那三伢子工資光買卷煙都不夠哇,忒貴的煙,他嫂子說那煙都幾十塊一盒,村頭張家鋪子都沒得賣的……”呂母狐疑一會,旋即又心疼起幺兒的錢包來。
江凇月拉呂母到一旁小聲道:“大嬸放心,三伢子現在大小是個干部呢,好多人求他辦事都送的禮,他不用自己掏錢買卷煙。”
這話有點騙人了,呂單舟抽的牌子她暗中了解過,也就十塊錢,絕對是自己掏錢買的煙,如今哪還有人送十塊錢香煙,帶回家的煙估計是平時別人送禮他攢下來的。
至於是否送的禮,有心人自然是不會讓她見得到,但現在辦事都是事前酒開路,事後煙感謝,官場常態,只要是無傷大雅的禮物,也是呂單舟應該享受到的小小福利,她無意追究。
“他那綠豆大的干部,能幫人辦什麼事——”呂母有點眉開眼笑,隨即想到江凇月還是幺兒的同事,可別把人家也埋汰上了,連忙道:“大閨女,收禮這事可是違反國家法律的,你是三伢子同事,還得是他姐!得管他!嬸在這里說了,在單位,你就替嬸看著他,不准他犯錯誤!”
這話有點大聲,就是說給幺兒聽的。
“是,聽大嬸的,您放心,我管著他可嚴實呢……”江凇月看一眼小秘書,心里樂開了花,仿佛有呂家老母的這道旨意,往後就更名正言順了一般。
幾戶人家的水田並不在一處,大家就由近及遠的去做,江凇月終究是沒能如她想象中一樣的能下田喚牛使耙,那是大老爺們的事兒。
於是在她強烈要求下,就和大嫂二嫂等婦女們一起,在家做飯,然後送到田頭。
她專門給呂單舟盛飯,藏好多塊肉在飯菜下,偷眼看他與男人們坐一排在田埂的大口吃得暢快,心里竟有甜絲絲的感覺……
看他才半天功夫就曬得通紅,又有點心痛,真想給他擦擦汗……
看他夾著煙卷在人群中小聲說大聲笑,拍打身上的泥塊,就覺得世間上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也就他這樣兒了……
農家下田干活,一般都做到日頭下山,今天不知是否有美女在田頭看著的緣故,連幾頭老牛都格外賣力,四五點就干完計劃中一天的活,於是眾人紛紛洗腳上田。
見天色早,江凇月就要呂單舟帶著去摘覆盆子野草莓那些野漿果,落在後頭,待往家走的時候,晚霞已經燒紅了半壁天空,遠處炊煙直上,隱約傳來婦人呼兒喚女歸家恰飯的聲音。
田間小道上只有暮歸的這兩人,一側是耙平如鏡的水田,倒映絢麗晚霞,一側傍山,松濤陣陣入耳,一天的勞累隨風而去,心曠神怡。
江凇月四處張望許久,躊躇片刻道:“……小舟你等等,站這別動。”說著閃身走進路邊的松樹林。
呂單舟心下啞然,女領導一路東張西望好幾回了,原來是找作案地點,再往前走就是機耕道,兩邊都會是大片水田,剛耙完光禿禿的,那才是藏無可藏。
江凇月似乎沒走多遠,隱約能聽到女人小解特有的噓噓聲。
不一會女領導就低頭走出來,呂單舟玩心忽起,隨即道:“姐您也等等我。”
沿著她走出來的路也鑽進林子,留下江凇月在那“哎哎”的叫喚。
天色只是昏黃,呂單舟目標挺明確,稍加環視就找到了一棵樹旁的白色紙巾,泥地上一道水漬。
看樣子女領導憋了好長時間,這小解解得挺急,泥地上都衝涮出一個小坑,水漬的形狀象一只大蝌蚪,蝌蚪的腦袋圍著一小圈泡沫。
呂單舟掏出作案工具,對著小坑也來了一發,不知道那是不是螞蟻窩?
如果是就好玩了,小時候就愛找螞蟻窩干這事。
似乎江凇月猜到他在樹林里會看到什麼,有點尷尬的樣子,呂單舟出來之後兩人就默默地走著。
野外解手這種情況,很奇怪,不刻意去想,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一分鍾就過去了,要是放不下,別人尷不尷尬不知道,自己先尷尬了。
呂單舟到底還是忍不住,仰天哈哈大笑起來。江凇月就使勁瞪他一眼,臉紅紅的樣子,嗔道:“嚇人一跳,笑那麼大聲。”
“姐剛才您在樹林里有沒有找到螞蟻窩?”
“我找那東西干什麼。”
“不是,我剛才進去,看到地上有紙巾,然後我的和您的混在一起了。”呂單舟忍不住得意道,好像戳破了大人做壞事的小孩。
“什麼混……呂單舟你這惡心人,你髒不髒啊!”江凇月話到一半明白了,頓時臉上一片燥熱。
呂單舟兀自在一旁得意洋洋:“什麼髒啊,又沒下手去摸——我在想那會不會有個螞蟻窩,然後那螞蟻會說,這地兒今天邪門了,才下一場酸雨,正咋呼著要搬家,怎麼又來一場鹼雨。”
江凇月想半天才弄明白他酸雨鹼雨的意思,越發臊得不行:“什麼亂七八糟的,你的才酸,惡心不惡心你!”
揚手就要往他屁股呼去,半道拐個彎,拍在小秘書的後腰上。
夜色將起,田畔蛙鳴漸濃,白色機耕道上兩道人影時快時慢地或追逐或閃避,嘻笑著,不時還停下看看田壟,翻找可能出現的野漿果。
雖然已經見慣鄉下地方,但工作狀態下與閒暇狀態下走在這環境,就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情,當然與身邊人是誰或許有更大的關系。
這下雨還真說不得,酸鹼雨的笑話猶在耳邊,天空就變了臉,稀稀拉拉下起雨來。
“春雨貴如油啊!”江凇月高興地張開雙臂,仰臉承接這甘露:“再下大一點,這雨值五十萬農耕資金!”
呂單舟遠遠看著自己的女領導,本就高挑的身材,在她盡情的舒展下猶如芭蕾舞者,修長脖子,柔腕,蔥指。
難得她如此開心忘形,幾乎不忍心去打擾她,度假期間下個雨都聯系到自己的工作,這領導當得太累了。
但是雨下得還是有點大,呂單舟只好從自己手提包里翻出一把折疊傘,撐在江凇月上方。
只要領導在旁邊,手提包是他無論去哪都得帶上的裝備。
“你還備有傘呢,小舟你這八寶袋還能變出什麼來?”
江凇月有些驚奇,而且折疊傘很小巧,淺綠色的還帶有蕾絲花邊,非常女性化的款式,顏色也是她所喜愛的顏色。
“姐您別再走出去,不然這雨值不值五十萬我不知道,它得值兩盒康泰克。”
江凇月頓時想起男人的包包里還有很多為她准備的藥品和女性用品,心下為這大暖男的細心體貼所感動,靜默一會,輕聲道:“小舟,跟著我,你包包里都是為女人准備的小零碎,搞得你都女性化了吧?”
“為領導服務麼,這都是小問題,服務好了領導,領導才能更好地為羅林人民服務。”呂單舟舔舔唇邊的雨水。
“你總有這種繞口令一樣兒的話,說慢點行不行。”江凇月又嗔一句,雨傘下的她安靜許多,回歸那個嫻雅的女人。
不知不覺,前面出現燈光,是一事一議建起來的太陽能路燈,在斜斜的雨絲中點亮歸途。
這路真短,這雨也不夠大……
呂單舟側頭看看迎著燈光的江凇月,白皙的臉頰沾有幾點雨水,端莊素雅的熟女,竟也有那麼點嬌艷欲滴的感覺了。
江凇月向他微側著臉,突然道:“小舟,我……生理期是每月的月初這樣子……”
“呃——”呂單舟一下子還沒反應過來女領導突然說這個的意思。
恍惚間手臂又挨著了女領導,趕緊的挪開,雨傘比較小巧,兩人有點擠,難免碰來碰去。
“我意思是說,其他時間你可以不備著那些——衛生巾。”
江凇月手臂也無意中碰到了男人,“我現在挺准的,一般都是四五天完事……其實你也不用准備這些,我一個女人哪能問個大男生要衛生巾,男人不是嫌棄這個晦氣嘛。”
確實,他雖然准備有,但江凇月從沒問他要過這東西。
女領導的體香又出現了,飄飄渺渺地鑽進鼻子,比田野花香更讓人陶醉。
呂單舟真誠地道:“我倒是願意您問我要呢,您不也說了嘛,私下里,一個是姐姐,一個是弟弟,您越使喚弟弟,就越不把弟弟當外人,不是麼姐?”
“嗯。”江凇月很認真地回應道。
“姐,我知道,您是眼里容不進沙子的人,可我在您那,做了那麼多亂七八糟的事,您重話都沒說過我一句,我都心里有數的……所以,姐您總得讓我為您做點什麼。”
呂單舟說的是用江凇月內褲絲襪自慰的事,她不僅沒責備呂單舟的胡搞,甚至采取的是縱容態度,裸睡了她的床,也不說要換床單就接著繼續用,那對裝滿精液的淺灰色絲襪,她也是默默地洗干淨後繼續穿。
這些對於一直以來有潔癖傳聞的女副縣長來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江凇月微微笑一下,又去揉他的刺頭,溫柔地道:“我弟弟已經是個男子漢了啊,男人要做點自己喜歡做的事兒,只要不出格,這沒什麼錯啊,干嘛要拿來說。”
呂單舟的痞子氣又上來了,無恥地打蛇隨棍上道:“那我還喜歡替您把衛生巾貼到內褲上呢,您得用弟弟親手貼好的比較好——”
“懶得理你!”
兩人的手臂又碰一起,江凇月往旁邊閃一下,這次呂單舟沒客氣,手臂追過去再貼,江凇月沒再退讓,走得幾步,她手臂也往中間使上點勁,兩人肩膀終於緊緊貼在一起。
“姐。”
“嗯。”
兩人都希望這段路能無盡地走下去。
“不對!姐,那今天就是您生理期啊,您還咋呼著要下田!”呂單舟突然反應過來,幸虧那時阻止了這虎娘們兒。
“這不沒下嘛——而且……這種到小腿肚的水應該沒事兒。”江凇月滿不在乎道。
但是呂單舟是真的有點生氣了:“什麼叫應該沒事?身體的事能心存僥幸嗎?枉費別人照顧你,你自己卻都不愛自己!”
還頂開女領導靠過來的胳膊。
江凇月意識到這小阿弟是來真的,連忙道:“我現在都很好了的,基本不痛,所以也沒怎麼在意,那時還真忘了有這回事……”聲音放得軟軟的:“姐下次不這樣兒了……”
男人並不回應她的軟話,將一顆石子踢得老遠,驚停一片蛙鳴,周圍只有寂靜的雨點打在傘上的噼啪聲,江凇月一把拽停男人的腳步,雙手摟著他一支胳膊,就靜靜地看他,眼神是祈求,是歉意。
通常情況下,呂單舟對這雙會說話的大眼睛是沒有防御能力的,對視數秒只好投降地看向別處,悶悶地道:“那……暖宮貼,還有在用嗎,您得堅持用著。”
“在用在用,有在用啊。”
“真在用?姐不能糊弄我。”江凇月這個人,有時候自己的事情就嫌麻煩,經常那些益母草茶,也是催著趕著她才多喝一點。
“真在用,不信你——”江凇月說一截呆住了,呂單舟幫她選的這種暖宮貼貼的是肚臍的位置,其實就是自發熱的一種東西,可以提供持續的微微的熱量,發熱材料里再加點中藥成分進去,可以利用熱力逼進腹腔內,達到調理子宮的目的,冬春這種季節尤其有效果。
貼在這個位置,難道能給呂單舟看,還是摸?
呂單舟抓到女人語句中的破綻,趕緊扭頭回來對視,還特意看一眼女領導的小腹,這回一點都不避嫌了。
江凇月輕挪半步向前,剛想說什麼,就被呂單舟猛地擁進懷里。
她輕叫一聲“小舟!”
,隨即雙手環在男人的後腰上,沒半點抗拒,甚至可以說是迎合。
男女擁抱,手放的位置有點講究,虛環在後背,握掌成拳,那是禮節性的擁抱,譬如上次動車中那回。
手放在後腰,手掌還攤開全捂在對方身體上,就有點親密的意思了,而且手的位置越低,親密度越高。
現在江凇月的手就在男人的褲腰上一點點,要不是男人的皮帶礙事,她可能願意再低。
呂單舟的手一開始是有點高,甚至按到了女領導胸罩的邊帶和背扣,然後被女人的手勢感染,也是逐漸降低,堪堪來到女人圓翹的臀部上方,才將手擱在女人後腰上,說“擱”不為過,那臀部凸出一大塊,手擱得很舒服。
女人的小腹有一點點凸出,淺淺的圓弧,頂在呂單舟下腹位置:“沒騙你吧,貼有。”
暖烘烘的溫度傳了過來。呂單舟眼珠子轉轉,裝糊塗耍賴:“沒有啊,是這里嗎?”他也是色膽包天了,居然伸手就往女人的肚臍部位探去。
江凇月伸手按住呂單舟手腕,將他的手拉回放在後腰上,她並沒生氣,平常慣於緊抿或者唇角朝下的的情形並沒出現,甚至有微微向上的角度,下巴美人溝也沒加深,這是她心情愉悅的表現,很罕見。
就是這微翹的唇角給了呂單舟信心,他箍緊女人雙臂防止她反抗,然後慢慢吻過去。
這雙唇非常非常的柔軟,與女人冷峻的外表絲毫搭不上线。
容素的嘴唇豐滿,富有彈性,這江凇月的唇從不施抹口紅,唇线輪廓清晰,想不到是這麼的玉軟花柔,與她強硬冷峭的形象有極大反差。
江凇月沒打算要躲開,只是象征地矜持了一下,動個手臂什麼的,然後在呂單舟雙臂強力緊箍下很快安靜下來,象征性的都不行,動一下,男人的力道就緊一分,動一下再緊一分,夾得女人雙臂生疼,於是她只好老老實實地,認真地與秘書做這個甜蜜的口舌互動。
其實與這種女人親吻很致命,口舌香軟,然後女人的體香還非常馨郁,身軀的女性特征部位又豐滿多肉,呂單舟想認真親吻那是不行,下體陽具以光速狀態抬頭,他悄悄將卡在褲襠里的小弟弟撥正,已經鑽出內褲的龜頭,隔一層薄薄的長褲頂在女人軟軟的腹部上。
她的嘴唇柔軟,胸部柔軟,小腹柔軟……
一切一切都是柔軟柔軟的,可怎麼會有一副強硬的外表?
她得做多少事才能撐起這副堅硬的鎧甲?
得怎樣磨煉自己才有堅強的意志?
呂單舟很心疼這個冷傲又孤獨的女強人。
呂單舟確實將她抱得很緊,除了頭部,幾乎動彈不得,害得她身體的姿勢很別扭,感覺硬邦邦的。
但是江凇月不在乎,她在乎的是男人的嘴唇特別特別軟,軟到她心里去了,她閉上眼睛,沉迷其中,無法自拔。
其實她並不懂如何真正地接吻,但不妨礙她學,男人咬她嘴唇她就咬回去,男人推舌頭進來她也要舌頭頂進他嘴里,男人吸她口水她也吸回來,男人舔她牙齒,她也一定要舔上他的牙齒才算數……
原來,接吻可以是這麼陶醉的。
那把小雨傘始終被男人牢牢地握在手中,遮擋在兩人上方,雨點擊打傘面的聲音浪漫綿綿,江凇月不知是吻得還是被吻得全身無力,輕輕靠在男人肩膀上,嘴唇盡是兩人的津液,感覺就是甜甜的,舍不得拭去。
短短的一個多公里路程,走了三個小時還沒到家,直到家人不放心拿了手電出來尋找,才驚醒二人。
呂母無意間得知江凇月來例假還想著下田,更是大發雷霆,把呂單舟攆得上屋竄下屋,趕著他去找老生姜燒水。
女人忙活了一天,又被淋濕了頭發,老人家就想給她洗個頭,再泡個腳,很能給身體驅寒氣,女人的痛經就是宮寒所致。
老生姜剁碎了丟鍋里燒開,加上茶麩浸泡後慮渣倒進盆中,黃澄澄的散發著老姜和茶籽果的混合香味。
江凇月解開一頭濃密的黑發,就想泡進生姜水里,呂母就道:“大閨女你坐著別動,嬸來給你洗。”
江凇月想阻止,呂母已經不由分說將她按在椅子坐下,洗頭盆就擱小凳子上,動手撩水濕潤她的長發,於是就老老實實地低頭。
老姜本就辣,加上熱水,燙得江凇月齜牙咧嘴的挺舒服。
呂母一邊洗一邊嘆道:“閨女這頭發是真的柔順……自打呀,生了老大之後,一心想著要個女娃兒,結果接連兩個還是混世魔王——”
說道這里又是轉頭斷喝,似乎要把沒生女兒的氣撒到幺兒身上:“三蛋你還要再燒一鍋——偷個懶試試!”
“現在呀,終於能給閨女洗洗頭發了……”呂母的雙手滿是老繭,但按摩江凇月的腦袋殼很柔和,就這樣一邊叨叨絮絮,一邊不停手地給她澆水清洗。
這種場景,千萬次地出現過在江凇月的夢境中……她低著頭小聲道:“大嬸……要不您就給閨女個機會,讓閨女也叫您一聲“媽”唄……”
“哎哎哎,好好好,好閨女——”呂母登時喜笑顏開,連聲應著,扭頭又是一聲喝:“三伢子!給你姐端水出來,還要泡腳!你來給你姐洗腳!”
把“你姐”
倆字咬得特別響,聽得呂單舟拿著根燒火棍一愣。
晚上臨睡前,江凇月敲門進來呂單舟房間,趿拖鞋提拎個小袋子。
“明天你陪我到鎮上,買兩身衣服。”女人進來就坐床沿,脫鞋上床盤腿。
“沒帶夠衣服嗎?”
“有,可帶來的衣服都不適合做農活的,穿出去不合群,被人當猴看。”
她要換成那種寬寬大大的,挽個褲腳也方便,還有就是能掩蓋一下自己的大屁股,否則去到哪都被人的目光追隨著。
“您都還來著大姨媽,還干什麼農活,嫌我媽沒揍我快活的是不是。”
江凇月得意地白他一眼:“是“咱媽”,咱媽揍你是活該,誰讓你不保護姐姐。”
雪白的小腳丫子動來動去,顯然是心情不錯,“媽說了,回來帶我去挖野芝麻——就是益母草,媽說這活也不累人。”
她一口一個“媽”,似乎就沒喊夠。
那腳板腳丫子剛才泡腳的時候呂單舟玩了很久,三寸金蓮柔若無骨,就連腳後跟也是一點硬皮都沒有的,如果套上絲襪……
呂單舟知道女領導的絲襪看著款式簡單,顏色單一,但質地卻都是上乘的,套在腳板上,手感絲滑不說,即使是灰色甚至黑色,都會讓人有似乎沒穿絲襪的錯覺。
呂單舟伸手去拽女人褲腳,江凇月下意識把腳躲起來:“干嘛?”
“被咱媽攆著洗您這小腳,得親一口補償!”
“呂單舟你變態!腳是能親的地方麼?”
江凇月大驚失色,慌亂中左推右擋著,又不夠二愣子秘書的力氣大,眼看抵擋不住了,連忙道:“這個!這個!”
那是她拿來的小塑料袋,現在被她用來擋秘書的拱豬嘴。
呂家房間不多,江凇月跟著來,呂單舟就將自己房間讓給她,他來和大侄子拼床,這是大侄子的房間,說不定別的人隨時會闖進來,江凇月完全沒有安全感。
“這是什麼?”
兩條女裝內褲,一條淺綠一條淺紫,不是女領導的常備顏色。
“你說幫姐貼衛生巾,那你貼。”江凇月已經開始習慣秘書的流氓行徑,說這些也不怎麼臉紅了。
呂單舟想拿出來看,女人又是瞪眼:“好了不准拿出來!”當著她的面翻看她內褲,這還是接受不了的。
“那我怎麼貼,瞎鼓搗啊?”呂單舟就怪叫一聲。
“我管你怎麼貼,明早給我就行。”
那流氓秘書就耍賴道:“我個大男人不知道怎麼貼呢,要不姐姐您示范一次唄?”
江凇月很認真地想了想男人的請求,好一會才發現上當了,衛生巾的包裝袋上就有使用的說明圖,且這個流氓弟弟也知道用“貼”這個字,分明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就板著臉道:“那你自個兒研究明白再做這事兒。”
作勢要拿回袋子。
煮熟的鴨子豈能還讓它飛了,呂單舟一把將袋子塞屁股底下,歡迎來搶。
江凇月做賊似的返回房間,坐到床上抱著一團毛毯發呆,這毛毯肯定是呂單舟自用的,即使洗曬過,還是帶有她熟悉的流氓弟弟的味道,他說,她的味道能讓他安神靜心,對這個解釋她有點存疑,因為,他的味道,她聞著就有點……
躁動。
兩條內褲是年初被秘書笑話她款式老土之後就上網買了來,但一直不敢穿,因為穿過就得洗晾出來,那王八蛋是經常關注她晾的衣服的,害得她有一段時間,內衣褲都得藏著掖著的晾。
這兩條新買的,打算帶來之前更是偷偷的洗做賊似的晾,只是這種款式,不知算不算年輕化的,要是被他發現了,不知還會不會嘲笑她的眼光……
你到底喜歡怎樣的內衣褲,直接說好了嘛,又不跟我說……她扯開褲頭悄悄看一眼正穿著的……好吧,被你說過,我也覺得老土了。
他居然還想親腳!
整天包裹在鞋子里的部位怎麼能下得去嘴!
江凇月搖動幾下腳指頭,那象幾朵鑲嵌在腳板上的含苞玉蘭花,捧起腳遞到鼻子下聞聞,其實也沒什麼味道,想伸舌頭試試味道,終究是不敢。
對,回去還是得買一瓶指甲油,把腳指甲塗上,紅色能讓腳看起來更白皙,還顯得年輕……
她又死死盯著腳丫邊的手機,那東西直到現在都還是黑屏狀態的不聲不響,江凇月一陣懊惱,就不該那麼快就逃離男人的房間,他要親腳怕哪樣,給他親就是了,最多不讓他再親嘴……
嗯,其實也可以親了嘴再親腳的呀……
再其實……
即使親了腳再親嘴也不是不行——這小王八蛋,平時不是挺膽大包天的嗎,怎麼剛才稍微阻攔他一會這人就退縮了呢?
也是個苗而不秀的銀樣鑞槍頭!
江凇月生氣地用腳趾頭將手機扒拉到一邊,仿佛是那流氓秘書的幫凶。
也就才十來分鍾,手機拿起放下不知多少遍,江凇月甚至不敢去刷牙洗臉,生怕漏了小王八蛋的信息和電話,才十分鍾,她就急忙的檢討自己,是不是剛才她做得有點過火了嚇著這個笨弟弟……
怎麼還不來信息,是不是不准他親腳指頭生氣了,才十分鍾,她看了兩次手機信號格,確認手機正常……
才十分鍾,她心中已經有了一千個懊惱。
江凇月窩在床角里再也不想動彈,嘴角含春,回憶今晚歸家時的點點滴滴,甚至有想去松樹林里看看混在一起的“酸鹼雨”是啥樣的衝動,那是她的體液與他的體液混合在一起的呢……
外套沾有他依稀的汗味煙味,她披在身上舍不得拿去,其實煙味也不是那麼的難聞吧,怎麼以前自己就那麼厭惡呢?
此時的羅林縣女副縣長,根本看不到一貫以來的凜若冰霜模樣,就是一個渾身散發著春意的風韻女人。
這時微信的提示音響起。
“姐,就休息了嗎?我想你了。”
這才分開多久啊,就想了?
這笨蛋弟弟一點都不曉得矜持!
有必要說得這麼直白嗎?
就不能詩情畫意一點嗎?
她嫌棄地撇撇嘴,將手機扔到一邊,又趕緊地撿回來,很認真很認真地讀上面的每一個字,然後拿出寫博士論文的勁頭,很認真很認真地編寫想要發出去的內容。
即便這房子里只有她一個人,她依然的脖子滾燙,臉頰暈紅……
江凇月根本沒意識到,這是她人生47年來,第一次談戀愛。
47歲才來到的初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