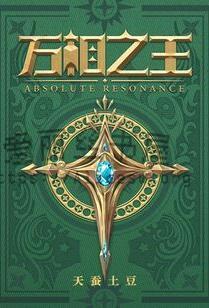水液輕松的就滲入衣料、洇濕一條條的水痕。
這些水痕蜿蜒著、不斷向上生長,堪比一條條虬結泡水的麻繩,勒住他皮下鼓動的血、扼住他的呼吸,纏繞住胸口那團理解不能的郁結,一團亂糟。
斬猙開始感覺喘不上氣。
他不得不伸出手、粗暴地扯開自己高束的領襟,有暗扣經不住他過度暴力的行為,當啷被扯掉在地上,但似乎也無濟於事。他還是憋的難受。
過高的身高差,他得費力的低頭,她得拼命的仰起臉,才能保持視线的平衡。但這好像是他們之間僅剩下唯一的平衡。
她扶著他的胸口,努力在維持身體的平衡,也有可能是某種尊嚴的平衡——
她為什麼要哭?
為什麼哭成這樣?
為什麼說話這樣捏聲捏氣?
為什麼會讓他產生難以理解的反應?
她為什麼會穿成這樣?
為什麼下午對著坎猙做出那樣子的事情?
為什麼要半夜來這里……一切都亂七八糟的。
斬猙全都不懂,也看不懂她的眼淚。
倒唯一能認出來她眼睛里唯一熟悉的情緒:是不甘。
很奇怪,斬猙見過這女人幕考里所有的表現,以他的標准絕對稱不上強。
但是……他並不否認,他會想跟她打一架:她……有著很能打架的氣質。
他躍躍欲試,也很想試試。
可現在,兩個人還沒認真打一架,她就已經毫無疑問的輸了,被鉗制地動彈不得。
但她不斷地哭著。
帖地太近,兩人周遭愈加朦朧晦暗。
不甘被眼淚糊成一團,從她的眼角朝下滾,把昏朦的夜在一張圓肉的臉上、塗出鮮嫩的粉艷,揉作一團。
她輸了,但還是不甘。要是換做其他對手,斬猙只會當做這是繼續的信號。所以同理,他沒放開她。
“別……快點……難受……不舒服……放開……”
她的確難受。男人沒有放開她,反而更近了,抬起小臂抵在她頭頂,懸起膝蓋用力朝上一頂。
“不放。”斬猙吐出兩個字。
“……啊!”赤裸的股間被男人膝蓋用力一頂,哪怕沒有任何裝飾物的褲子也因為力道而直接把她的淫屄給撞扁了。
猛地一下力道,突兀地就砸到了陰蒂上,快感直衝鼻腔,把眼淚立刻衝地更加洶涌了。
“你……!”
斬猙注視著眼淚沿著她的眼眶一路滑下去,滾到她的唇角。
和悠哭地吸氣,把眼淚也吸進去,嘴唇張著,舌頭頂出來輸家的求饒。“……不要這樣頂……受,受不住了……斬,斬猙……”
斬猙聽地倒是挺清楚。叫他名字。叫的干脆,也利落到陌生。
他腦子里不知原因地、蹦出來的卻是下午頭女人在視標里的叫喊,『“猙哥哥”』
胸口中郁堵的團結,更加令人暴躁。
他什麼都不知道,也想不清楚。再回過神來的時候,已經俯身下去,一口咬住了她的嘴唇。
激烈而粗劣的吻。
嘴唇碰上嘴唇。牙先撞上。她嚇壞了,不張嘴。
沒關系。
第一口。他就撕咬開她的嘴唇,吃到了血的味道。她的血,比他想象中的味道還好。
她被咬疼了,驚懵之中,第一反應是抬手就要打他。
拳頭砸在他的胸口——好反應。
但沒什麼用,軟綿綿的。
這般反抗,只像扔進火力的棉花,把戰斗欲肆虐地熊熊:想要看她還能怎樣反抗。
“繼續打。”
斬猙一把掐住和悠的兩頰,像掐一只不會進食的小貓,她不張嘴,他有的是辦法讓她張嘴。
他可太清楚對手身體每一個關節、每一處血肉哪里是弱點,用怎樣最有效的方法強給予對方難以站起來的暴擊。
她上牙槽兩邊的肉窩被人隔著腮肉用力一卡,她就無比酸疼地張開了嘴唇,甚至把舌頭都吐了出來。
斬猙俯身下來,當吮到女人柔軟的小舌尖時,他的腦子里嗡地一下——那團近乎結痂的郁結一下就被撕開了,衝出來洶涌的血潮,燒地他雙目通紅,什麼都看不見了。
他像一頭野獸一樣把女人壓在牆上開始瘋狂的接吻。
可怎麼說呢,他並不會接吻。
他想分化的時候,好像胡亂親了某個女人,但年代過於久遠,他早就記不住了。
沒有人教他怎麼做。
但斬猙卻莫名覺得此刻好像有了與坎猙莫名的共感,以坎猙現在的狀態,距離這樣遠,他也聽不見坎猙說話——但好像坎猙就在旁邊,教他,去親她,去吻她。
然而——
“嗚……啊……滾…開不要……親…啊………嗚嗚……”破碎的字句從她被糾纏的喘不上氣的舌頭里吐出來,仰起臉努力地回避著斬猙。
她的拳頭一下一下砸在斬猙胸口上,對方紋絲不動,還把她壓地更狠了,直到她的奶子都被男人的身體快要壓扁了,喘也喘不上,脖頸都要仰成直线了也躲不開男人胡亂而粗暴的親吻。
“啊……啊……”
不,不是。也不可能與坎猙這個狗比有任何關系。他想親她,就是想親她。
斬猙抬手按住她的額頭,近乎刑訊一樣殘忍地將她的脖子快要掰折過去,以便自己能更加方便的吻她。
他只是想這樣親她,嘴唇對嘴唇的,想要讓她連不甘都功虧一簣,讓她成為自己又一個手下敗將……跪在他腳下,哭地一敗塗地。
女人越來越沒有力氣,毫無招架之力了,四肢都垂了下去,撐不起驅干,像團濕透的棉花被斬猙的身子山一樣籠罩覆蓋,壓扁在牆面上,時不時能看見肥嫩的奶肉和屁股被從男人強壯的身軀外面擠淤變形的軟肉,水流一樣泄出來。
斬猙吻地愈加上癮,盡管他的吻拙劣粗笨,但凶殘。
和悠的唇舌像過甜的酒水,越喝越渴。
他煩躁而不得紓解,隱約聽見她喘息中小口呼疼,只知道不能繼續在這里,要找到自己房間,自己的……床?
他干脆地一把將女人抱起來,拖住她的屁股。
她已經沒有了力氣,雙手軟綿綿地搭在他的肩上,體型差讓他看起來像抱著睡到迷糊的孩子去撒尿。
就算這樣,斬猙也沒有放開她,一手掐著她的後頸子,只要有空隙就要吻著她的嘴唇,但這個姿勢的確不適合走路,他踉蹌地走了沒多遠,余光好像瞥見了自己的房間——也顧不上去拿鑰匙開門了,抬起腿來一腳就把門給踹開了。
“誰?!”
不過,房間里卻傳來了陌生男人的聲音。就看到一人錯愕無比地看著闖入的兩人,驚呆在原地,“斬……”
斬猙皺眉,不認識這人,但應該是天壤的部眾。果然又走錯房間了,媽的。
不過無所謂了。他看向里面的床。冷漠地,“滾出去。”
那天壤部眾一愣,雖仍然沒從震驚中回過神,還是忙俯身下去抓起衣服就打算走。
可和悠……卻慌了。
她趴在斬猙的懷里頭,拼命地搖頭,“不要……不要在這里……嗚嗚嗚……去你房間里……去你的……房間里,求求你了……斬猙……”
也不知道是不是剛才被親地太狠了,這會總算有點空氣了,和悠哭地上氣不接下氣。
她其實已經迷糊著接受了即將會發生的事情,但仍絕對不能在這里……因為她分明聞到了,四周還有別的清人氣息,也就是說,大概就是隔壁,也有清人,也不知道有幾個。
斬猙好像有些無奈,“你可真作。”
但是——
他環顧了四周,確實……這里是普通天壤部眾的宿寢,條件各方面比起他們的宿寢要差上不少,尤其他打眼看了一眼里面的床。
不行,他覺得那床的質量夠嗆。
功夫不負有心人。
折騰了半天,斬猙總算抱著人到了,他抬腿踹開門,看見門里的裝飾……
頓時大喜。
總算找到了……
“操!”斬猙朝後退了半步,抱著和悠轉過身子,避開了一道凶險的刀氣。
然後就看見——
但他們面前的屏風被削掉了半個,轟地一下倒塌在地面上……
內室的床上,靠著一個年輕男人……衣衫不整。他比斬猙還要震驚,臉色還要難看。
“阿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