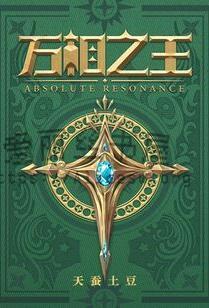和悠的聲音隨著嚴是虔手中的書,一起緩緩低了下去。
嚴是虔坐起了身子看向她,“你什麼意思?”
她一下就被問住了,連擺手說道,“我沒什麼意思,就是隨口一說,你別放在心上啊。”
啪。
“不放在心上……呵。”嚴是虔一聲冷笑被蓋在扔到一邊的書本之下,直直盯著她的眼睛,“和悠,你是在懷疑我騙你是嗎?”
和悠一愣,“什麼騙我?”
但剛說完,她目光掃過他的小腹登時反應過來,“不不不,我沒……”
可是她壓根沒注意到她現在的這種反應,看在嚴是虔眼中是多麼的欲蓋彌彰。
“你懷疑我什麼?”他追問,“懷疑我拿這種事情來騙你、要挾你、威脅你?”
【這種事情】
都到了這個時候了,他還是難說出口,仿佛什麼見不得人的東西。
但只是這句話,這件事麼?
不是。是只要面對她,就越來越難以開口。
是他不可一世的自尊和高傲在作祟?
是輕松把絕大多數人踩在腳下的睥睨吊著他?
是坦蕩到浪蕩的無畏縫上了他的嘴?
他這樣的大妖,刀山火海里打滾都不見得能覺痛,半生都從來不以疼為然,但……事到如今,他陡然覺得,面對和悠的這一切就像生在疏於照顧指甲下生出的倒刺,生出令人煩躁的細小疼痛,置之不理疼,撕開也疼。
掛著“小閻王”的名號令人聞風喪膽,扒皮抽筋都只會笑著啐出一口血而已,但卻難熬與這樣丁點的細小疼痛,說出去,誰會相信。
難以啟齒也無可厚非。
但不管,不看,這毛刺越生越深,越來越多余。
就在這一刻,他不理解聞督領為什麼非要讓他來轉交這法器,他本可以不用帶她來自己房間,隨便找個房間讓她自己等就行,更不用給她買什麼飯菜,也不用對她發火——
這都是多余的。
都是這該死的、多余的種族生理本能,讓他做出這樣多余的事情。
如果不是這個特殊時期的本能,他不會無法自控地想要她來自己剛搭的窩巢,不會無緣無故的發火,不會想要做這些多余的事情——不會克制不住地想要和她近一些、再近一些。
但是。但。
他的目光忍不住穿過和悠,穿過這面牆,好像看到了另外一個房間里躺在床上昏迷著的另外一個男人。
滿腔自以為被種族本能激發出來的火氣,把毛刺撕地皮開肉綻。
“你把我當什麼了?用這種手段要挾男人上位、可憐兮兮的下賤婊子?”嚴是虔冷笑著站起來,走到她面前,眼神冷到令和悠陌生。
“我用這種惡心的招數騙你?我圖什麼?騙你什麼?啊?和悠,你要不要仔細看看自己,你身上有什麼可以讓我騙的?”
這些字句聽到他自己耳中刻薄尖銳的令他心頭一個勁的痙攣,但有些話,如同洪水一樣,不摧毀所見之處的東西是不會停下來的。
和悠最細小的神態在他眼中都一覽無余,錯愕,震驚,直至憤怒。
“我也想問你,你有什麼好騙我的?”她反過來質問著,聲音有些磕巴,但越說氣勢越旺,仰著臉迎著嚴是虔的目光,“對,我又丑又窮,在你眼中又笨又傻,修為也低,沒權沒勢,你能騙我什麼?!”
“…………”
“你不圖我什麼,不騙我什麼,那你為什麼要三番兩次主動惹我?你也像那些男人一樣想挖出我身上所有的秘密?哦對,我忘了,你是圖我容易操,是個人盡可夫的騷貨,對吧?”
“我他媽不是這個意思!”嚴是虔硬生生被逼出一聲吼。
“你不是這個意思?是因為我懷疑你懷孕?”她也不知道自己怎麼了,但這一刻委屈和憤怒全衝了上來。
仿佛這些日子里亂遭的各種事情所帶來的負面情緒,全都一股腦的在這個讓她覺得莫名緊燥的房間里被逼上心頭。
提心吊膽地算計了一天一夜,神經從昨夜緊繃到現在沒有松懈過分毫,腦子根本沒有停下來過哪怕一秒,生怕漏出丁點紕漏,甚至來不及去注意身體也早就是強撐到了極限,被秦修竹和聞望寒折騰過的身子,硬生生扛著一整夜至今沒合過眼。
她今天過了並不算好的一天。
而最可怕的是,這樣的一天,不過是她最近這些日子里其中一天。
她像一根被拉到極限的皮筋,在她自己眼前一點點裂開口子,在嚴是虔的火氣之下快要被燎斷了。
嚴是虔看著她氣到漲紅的臉,思緒遲滯。
他們在做什麼?是在吵架?
可他從來沒有跟人吵過架,對他來說,動手比動嘴簡單的多。一切都亂了套,對話也不像兩個人平時的冷靜和有邏輯,但話說回來——
要是都冷靜講邏輯了,還叫什麼吵架呢。
但不應該。他並不想。
“你還覺得我懷疑你,對啊我就是懷疑你。我怎麼相信你?相信你一個大男人懷孕,你讓我怎麼接受?我怎麼可能接受得了?”
不能吵了。
嚴是虔深深吸了一口氣,剛抬起手……
“而且我憑什麼接受?!”他的沉默好像如同自知認輸一樣鼓勵了她,她冷笑一聲,“就算你現在真的懷孕了,跟我有什麼關系?!”
嚴是虔的手懸停在半空,一瞬間他甚至忘記了自己抬手是要做什麼的。
是想掐捏她的臉,是想捂住她的嘴,還是想干脆拉到懷里讓她閉上嘴——?
都不重要了。
“你說什麼?”
“我之前就說過了。”和悠認真地盯著他,“你那麼多女人,誰把你搞懷孕的,你去找誰。別擺出一副我是孩子親媽的樣子賴上我要我負責的態度。”
他放下了手。
和悠看著他,莫名有些想咬住嘴唇。但是——
這件事本來早就該解決了,擇日不如撞日,她本來就想找他一次說個清楚。
上次就沒來及說,但既然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了,不如就現在就直接攤開說透吧。
“哪怕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你懷了,還真是我的……”和悠的臉色比剛才要沒那麼紅了,這讓她的笑容像從心底透出來的明顯,明顯到刺眼。
“嚴是虔,你怎麼就覺得,我會認它?”
“…………”
她倒是抬起了手,還碰到了他的小腹。
“你認為,我會接受妖物這種髒東西流著我的血,成為我的後代嗎?”
【髒東西】【後代】——【它】
嚴是虔只是看著她,長時間不眨眼的注視讓他的視线開始虛化。虛化的邊緣,諷刺地和甲床上紅白的倒刺沒有分別。
那些毛刺的背後,是緊閉著的內室門,那里面,那里面……他自以為放著他嚴是虔這一生最為難以啟齒。
他今天早晨還疲憊地躺在那,看著自己的小腹……但他發誓,他從來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如果假如,像手里這本人類賣的書里寫的一樣,俗氣的,她碰到自己的小腹時,會露出怎樣的表情呢?
但這會,電光火石之間,這個突然沒有想過的問題,就一下被她給出了答案。
她第一次碰了他們的孩子,動作也像像那本爛書上寫的一樣,很輕。
書上沒寫的,是,輕到輕蔑。
『“如果是聞望寒呢?”』
一根倒刺,從心尖上撕開,撕到眼睛里,卻沒能撕開他緊閉著的唇齒——仍沒問出口。
從來不是他對她難以啟齒。
是他,才是她厭惡的難以啟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