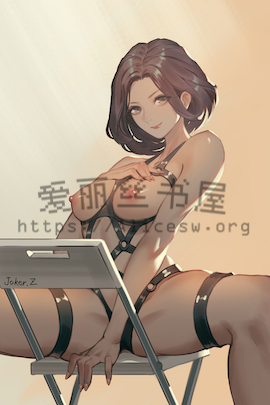親民的家主在視察林木部門後,和屬臣們一起到森林外緣的景區休閒山莊吃晚餐。
餐後的娛樂項目是觀賞他的一名三等奴隸光著屁股只穿件圍裙給他烤肉。
手里還拿著根竹鞭,時不時在奴隸身上這里戳一下,那里抽一下。
有時輕,有時重,沒有定數,只看心情。
“咻——啪!”
竹鞭在幾下輕戳之後突然狠狠在景川屁股上抽下去,他“啊”地驚叫一聲,手里拿的一小瓶調料差點掉下去。
“磨蹭什麼?”風贏朔說,“拿個調料拿半天。”
景川忙往鐵網上的肉刷油。
“啪!”屁股上又挨了一下。
“油刷早了。”
“啪!”
“翻面太慢了。”
“啪!”
“醬多了。”
“啪!”
……
景川心想,您經驗豐富,您來。但手上沒敢懈怠,該干嘛還是在老老實實在干嘛。
只是忍不住說:“主人,我在瀾星上的時候烤肉都是很隨便的,醃好隨便烤一烤,熟了刷點調料就著啤酒就吃了。精細的做法我真的不會。”
“沒指望你會。”身後傳來一聲嗤笑,屁股上新添一道熱辣的痛。
是了,這只是為了娛樂家主罷了,還能真指望他技術趕上專業廚師?
夕陽金色的光线透過樹枝間的縫隙灑在景川光裸的後肩上,薄汗使得肌膚在光下反射溫潤的微光。
順著脊椎往下是交叉著系在後腰上的圍裙帶子。
窄窄的一截腰在這個部位有一小段凹陷的弧度,再往下則是鼓突圓翹的兩瓣屁股。
此時已經完全紅了,布滿一條條清晰的棱子。
青翠的竹枝“唰”一下抽在隆起的圓潤臀尖上,臀肉就會不由自主地顫動。
圍裙系帶多出來的部分被鞭子的風帶得飄起來,然後落下,垂在鞭痕交錯的臀肉上。
風贏朔欣賞著他奴隸的肉體在他鞭子下被留下印記,顯露出斑駁的顏色,彈動,戰栗。
如果某一鞭抽得特別狠,奴隸還會叫出聲來,甚至小幅度地跳一下腳。
但是不敢伸手去摸傷處。
那兩條有力的胳膊,指骨修長的手都懸在操作台上方,老老實實在烤那幾塊肉。
但香氣四溢的烤肉對於風贏朔來說誘惑遠不如圍裙下這副身體。
原本只打算讓他隨便烤一些就算了,但風贏朔抽打得上癮,沒有說停。
景川就只好把烤好的肉夾起放到空盤子里,再夾起幾塊生肉鋪到鐵網上。
“雖然技術不行,動作還是挺熟練的嘛。以前在瀾星經常烤肉吃?”風贏朔聊天似的說著“咻!”又來一鞭。
“嘶——”這一鞭疊在之前的鞭痕上,疼得格外尖銳,景川咬著牙倒抽一口氣,喘了幾下才說:“沒有,不過我們都不太講究,只想著快點烤熟了吃。”
“‘我們’?你和誰?”
又一鞭。
“啊……呼……我,我和我爸,或者其他朋友。”
“你朋友挺多。”
“唰!”又一鞭。
“嘶……大多數……大多是雇傭兵的伙伴。我幾乎沒有別的職業的朋友。大家在這些事情上都很隨便,所以也比較合得來。”
“都跟野人似的?”
“唰!”再一鞭。
“呃嗚……不講究有不講究的舒服,怎麼就是野人了?”景川疼得出了滿頭的汗。
或許是聊天的內容脫離了平常他和風贏朔的身份及陌星的背景,或許是屁股不堪折磨,說著說著語氣就有點衝了。
這為他贏來連續三下狠辣的抽打。
“舒服是吧?”拿鞭子的那個還冷言嘲諷,“還開懷暢飲呢是吧?生活豐富多彩呢是吧?”
“……”景川不想說話了。反正說什麼都是挨打。當然,這人本來就是想打他,跟他說什麼也沒關系。只是這麼聊天太怪了。
然而不管他想不想,風贏朔還是時不時問他點關於在瀾星的事,他也還是回答了。
這讓他回憶起了曾經覺得很平常很普通的過往。
原來哪怕是平凡的生活,在失去之後都會顯得如此珍貴。
揮汗如雨的訓練,任務結束後一起喝酒,把剛買的烤雞喂給路上偶遇的流浪狗,休假的時候到河邊釣魚一整天……沒有刻意記,也沒有刻意去回憶的片段在隨口的問答中被翻出來,又被竹鞭抽打得支離破碎。
他就這麼在鞭子的驅使下胡亂烤出了一些從外表已經不太看得出原材料的東西,分兩個盤裝著。
“主人,您真要吃這玩意?”他自己看著都嫌棄。
“端過去。”風贏朔臉上沒什麼表情,看不出來他有沒有不滿。
景川端起那兩盤東西往亭子走過去,屁股火辣辣的,每邁一步都不舒服。
山莊的工作人員退下之前收拾過桌上的杯碟和食物,現在長木桌上原先屬臣們坐的位置都是空的,只在風贏朔座位前擺了五六樣菜和沒開封的酒及飲料各一瓶。
他座位的右邊側面隔了兩個位置也擺了幾盤菜和同樣包裝的酒及飲料。
景川看到的時候閃過一個念頭,想著這個位置不會是留給他的吧?
別的奴隸或許不會想到主人的桌上會有自己的位置,但他是跟風贏朔同桌喝過酒的。
風贏朔跟在他後面過來,把亭子外的兩個護衛也遣走。而後用竹枝點了點那張長桌,說:“手撐著桌子,屁股撅起來。”
這是還要打。
景川無奈地放下烤肉,兩手撐住桌子,把腰塌下去。
撐著長桌的景川屁股整個暴露出來,比之前站著的姿勢更方便被責打。
風贏朔手里的竹枝只有拇指粗,但每一鞭都比之前凌厲狠辣。
痛從臀肉或腿根彌漫。
烤肉的時候就已經被抽了幾十鞭,現在再這麼一鞭一鞭抽上去,整個屁股已經痛成一片。
每一鞭下去,這新鮮的痛感就像刀割一般突出。
景川忍耐力很強,但那並不能讓痛感減弱。
他只能用雙手死死抓著木桌邊緣,拼命抑制逃開和反擊的衝動。
但他抑制不住喉嚨里低沉的呻吟。
確實太疼了。
鞭痕整齊地在他屁股上重新鋪了一層。雖然看不到,但從痛感和皮膚發緊發脹的感覺,他也知道整個屁股一定全都紅了,也腫了。
鞭打終於結束之後,風贏朔把鞭子隨手立靠在亭子一角,說:“圍裙脫了吧。”他語氣輕松,表情愉快,和之前在辦公樓前的樣子以及跟屬臣們吃飯時的狀態完全不同了。
好像前前後後在景川身上的鞭打令他身心放松了似的。
景川瞥他一眼,被他那種仿佛做了全套按摩後的放松狀態氣到了。
不是不知道三等奴隸的用途,但那不等於能被景川接受和認可。
他永遠也沒有辦法接受和認可。
景川站起來,手在後腰摸索了好一會兒才把帶子解開。將圍裙取下來後,他又完全赤裸了。
“轉過來。”
身後的風贏朔等他轉身之後,捏著他乳頭根部的曲別針直接拽了下來。
微微腫脹的乳頭被強行拉過狹窄的夾縫,疼得景川又叫了起來。
唯一勉強值得高興的是風贏朔在取掉曲別針後允許他把衣服穿上。
“穿好了可以坐下來吃點東西。”風贏朔說,“你自己先試試你烤出來的這些玩意能不能吃。”
——那個位置果然是留給他的。
在景川看來風贏朔這些一時風雨一時晴的舉動並非喜怒無常——他只是在想打人的時候打了,想操人的時候就操了,想讓人真的像個人一樣坐下來吃飯喝酒也就讓了,並非由於情緒失控,也根本就沒有人能看出他真正的喜和怒。
景川心里有一堆混亂的疑團沒辦法弄清楚。曾在生死間游走的他隱隱感到有什麼事情很快會發生,就像追逐的鬼怪已經在迷霧中露出了它的角。
他右手輕輕動了動,一把小刀在袖子里稍微往下滑了點,刀柄觸到了他的手心。
這是操作台上廚師用於在食材上劃下口子方便調料和醬汁入味的。很小,但足夠鋒利。
穿著圍裙時他已經悄悄把它藏在圍裙前兜里,在亭子里穿衣服時又把它轉移到了袖子里。
風贏朔不是個每天只想著怎麼擺弄奴隸的大閒人,項圈的遙控器不會時時刻刻隨身帶著。
當然他的智能微端也可以操控,但調出程序是需要時間的。
三檔致死。
項圈外側是絕緣材料,內側導電。
但人體也是導電的,只要控制住風贏朔使他處於電擊景川時自己也會觸電的境地……
用風贏朔的命交換項圈的解除和他的自由,對風贏朔來說怎麼也算是個劃算的買賣吧?
即使過後會被通緝追捕,這附近的森林也適合逃亡和躲藏。
他不動聲色尋找最佳時機。
景川像曾經坐在風贏朔對面喝酒的時候一樣,腰背挺直,不卑不亢——即使屁股疼得他仿佛坐在刀尖上。
襯衫之前脫下來之後他是疊好放著的,現在穿回來也還是干淨整齊。
風贏朔抬了抬下巴,示意他自己倒酒,說:“這是我最喜歡的酒,叫做‘暮光’。入口綿滑,後勁卻非常猛。”
景川隱約覺得這句話有哪里不對勁,卻一時想不到。
他把右手袖子里的小刀貼著手腕內側推了上去,袖口卡著刀柄。
他小心地扭開酒瓶蓋子,倒了大半杯。
綿甜醇厚的酒香立即彌漫開來。
他抿了一口,果然和之前喝過的兩種又不同,甘潤醇和之中隱著綿綿後勁,如果有機會仔細品味,應該是會有種令人心甘情願慢慢沉醉的快意舒暢。
景川又啜了一小口,放下酒杯,夾了塊烤肉放進嘴里。
烤肉在醃制時就已經切成合適入口的大小,放了一會兒熱度正好合適。
看著有點丑,吃起來味道還是挺足的。
廚師醃制的技術高超,外面烤得焦酥了,里邊還是鮮嫩的。
“這酒真是滋味美妙。我做的烤肉雖然配不上這酒,不過味道其實也還過得去。”景川說,“主人,您嘗嘗?”
兩盤烤肉,一盤在景川面前,一盤在風贏朔面前。風贏朔夾起烏漆麻黑的一塊打量著說:“都成了碳還能吃?”
“只是外面的醬汁焦了而已,要是不喜歡的話,刮掉就可以了。”景川說完就看到風贏朔嫌棄地把那塊肉丟回盤子里。
他站起來道:“要不我來處理一下?補救補救。”他一邊說一邊往風贏朔那邊走過去。
兩手自然垂在身側,步子輕慢,看起來就只是要主動過去伺候他這位主人。
說話沒規沒矩,是他被允許和風贏朔同桌共飲時自然而然的樣子。這種時候的風贏朔也從不計較過這些事,大度得簡直算是縱容。
等等,縱容?
景川心底里不對勁的感覺越來越強烈。他好像走在一條懸空的索道上,索道的另一頭隱在濃重的迷霧里。
以他的經驗,每當覺得不對勁,最終就真的是有問題的。
八年來應對過那麼多的危機,這已經成了直覺——雖然有了直覺未必就能百分之百反應得過來,或能夠在正確時機采取正確的處理方式。
就像他背鍋成為替罪羊那一次,當時也已經覺得有說不上來的奇怪,然而仍然被任務和對手營造出來的氛圍推著往前,最後讓事情成功按照對方的預設劇本發展下去。
可如果放棄今天的機會,什麼時候才能有下一次機會?
等到身體淪陷在那種性虐折磨中?
等到連精神都變得服從?
景川害怕那些偶爾出現的令他深深恐懼的預兆。就算有再大危機,他今天也要試試。
“你腦子里的筋是直的?”養父的聲音似乎在腦海深處又響了起來。嚴厲地,警告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