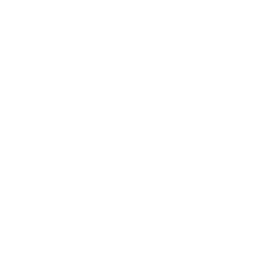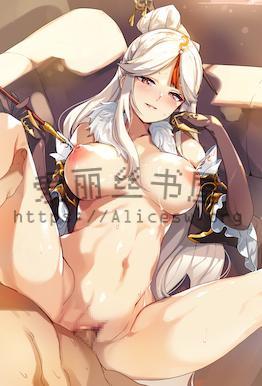第36章 雜談古籍中的“童男童女”(其二)
雜談古籍中的“童男童女”(其二)
(r18g警告)
疑似顓頊大墓
在繼續講古籍之前,我覺得應該“插播”一則我剛剛翻到的考古舊聞。這是一則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證明早在漢字誕生之前或之初,中華文明形成之初,“青龍白虎”和“童男童女”這兩組概念就產生了某種聯系,絕非後世方士或道士的牽強附會:
河南濮陽,傳說是黃帝嫡孫顓頊的出生地、都城、埋葬地,舜帝故里,張姓始祖發源地。1987年5月,因為引黃供水工程,將城牆挖開了一角,於是就在濮陽老縣城西南角發現了西水坡遺址。很快,考古工作人員發現遺址文化層歷史驚人,自上而下,依次是宋、五代、唐、晉、漢、黃河淤積層、東周、商文化層和龍山文化層、仰韶文化層,光是仰韶文化層就有上中下三層——後來又發現下層之下還有一層,命名為“第四層”。當年8月以後,在仰韶文化第四層下陸續清理出四組蚌圖(即用蚌殼擺砌的圖案),被標記為B1~B4。B1屬於M45墓葬,發現於T137探方。該墓主人為一老年男性,頭南足北,身長1.84米,身旁緊挨的東側蚌殼龍圖長1.78米,西側蚌殼虎圖長1.39米,背對背,皆頭北尾南,北側蚌殼圖案難辨(後猜測為鹿圖)。B2在B1南20米處,發現於T176,有龍、虎、鹿、石斧等內容,虎在西,鹿在東,相向而立,頭皆向北。而龍則奇怪地在虎南,龍身迭壓在虎身之下(俯首甘為孺子牛是吧?),張嘴伸舌,露出上下牙齒,龍嘴南則是一近圓形蚌堆(龍珠?),龍頭東又有像蜘蛛的圖案,再向東又置一石斧。(B2存疑,不同的資料有一些互相矛盾的記載,不知道是不是一開始認為是虎西龍東,後來改正為虎西鹿東導致的。)B3在B2南25米處,發現於T215,有一只奔虎,頭西尾東,背南足北,作蹺尾奔跑狀,虎背騎一人。與虎背對背為一龍,頭東尾西,作昂首騰飛狀,龍背騎—人。B4在B3西南,被兩個晚期灰坑打破,已難辨形象。隨後,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采集蚌殼標本作碳十四測定,經樹輪校正,年代為距今6600年前,誤差135年內。於是,該遺址的蚌龍被譽為“中華第一龍”,即目前考古出的最早的龍形象。(此外,國內還有三四處與該遺址大致同期的遺址出土龍、近似龍的形象的文物,但都是玉龍,目前只有這一處蚌龍。)有學者認為M45就是傳說中的顓頊墓,第四層全部都是M45及其附屬建築、物品。
而在M45墓的東、西、北三小龕內則各葬一少年兒童,其西龕人骨長1.15米,似女性,年約十二歲,頭有刃傷,學者們判斷應該是非正常死亡的殉葬者。(其他兩具骸骨資料未載有刃傷,應該是沒有或沒有發現。)
可憐,生前是奴隸,主人死了被殉葬,殉葬死後也被認為不配和主人葬得太近,被用蚌虎代替了自己的位置,葬在了蚌虎外側。不過,又比沒有自己單獨小龕的殉葬者尊貴一些。
這一墓葬啟示我們,某些古籍上的龍、虎、鹿,很有可能就暗示著童男童女(鹿可能是閹童)。
佛經綜論
古代佛教著作中,“童男童女”一詞出現的頻率遠遠超過了道家著作。我思考了一下,大概原因是:道教喜歡用“童子”一詞,逐漸“童男童女”就用的少了;而佛教則喜歡發明和使用“三、四字詞/成語”,所以佛教有時會用“童子”,有時會用“○○童子”,有時又用“童男童女”。大家覺得我分析的有道理嗎?
雖然出現的總數比道教多,但大部分佛教著作中,“童男童女”一詞出現的頻率都是個位數,只有兩個例外:唐·玄奘《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出現了31處,北涼·曇無讖《大方等大集經》中出現了16處——不過,其實都是“套話”,沒有什麼需要額外解讀的地方。
恒傳法師說,童子是指慧根深厚,福德具足的人。後世佛教著作很多將童子/童女定義為四或八歲以上,未滿二十歲,有慧根但尚未剃發得度者。但日本佛教則以幼童供諸種法會、庭儀使喚,稱為童子。則佛教最初的“童子”,可能年齡上限不是二十,而是十二或其他。(不過,懶狗我仍然只看“童男童女”不看“童子”,各位感興趣的話自己研究吧。)
佛經一
佚名翻譯的《別譯雜阿含經》(一九九)中出現了一處“童男童女”:
“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童男童女共相聚會,歡娛燕會,隨意舞戲,是名相應。譬如有人,年過八十,頭白面皺,牙齒墮落,然猶歌舞,作木牛馬,作於琵琶、箜篌、箏、笛,亦作小車及踏鞠戲。如斯老人,作如是事,名不相應。其有見者,當名此人為作智人,為作痴人?」
梵志(即僧侶)對曰:
「如是之人,名為嬰愚,無有智慧。」
佛告之曰:「我佛法中,相應相順,如童子戲。梵志當知,聖賢法中,如童子戲。」”
這里大致就是說,老年人“返老還童”,像童子一般嬉戲,也是符合、順應佛法的,有智慧的。(甚至有說佛法本就“如童子戲”的意思。)和孔子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有點類似。
三國吳·康僧會《六度集經》明度無極章(共九章)第六出現了一處“童男童女”:
“佛言:「吾昔為菩薩,在尼呵遍國,其王聞:『人或為道升天,或為神祠升天者。』王自童孺來,常願升天未知所由。國有梵志四萬餘人,王現之曰:『吾欲升天,將以何方?』耆艾(即長老)對曰:『善哉問也!王將欲以斯身升天耶?以魂靈乎?』王曰:『如斯坐欲升天也。』曰:『當興大祀,可獲之矣。』王喜無量,以金銀二千斤賜之。梵志獲寶歸,快相娛樂。寶盡,議曰:『令王取童男童女光華踰眾者各百人,象馬雜畜事各百頭,先飯吾等,卻殺人畜,以其骨肉,為陛升天。』以事上聞,王曰:『甚善!』王即命外臣疾具如之,悉閉著獄,哭者塞路,國人僉曰:『夫為王者,背佛真化,而興妖蠱,喪國之基也。』梵志又曰:『儻殺斯生,王不獲升天,吾等戮屍於市朝,其必也。』重謀曰:『香山之中,有天王妓女,名似人形神,神聖難獲,令王求之。若其不致,眾事都息,吾等可無尤矣。』又之王所曰:『香山之中,有天樂女,當得其血,合於人畜,以為階陛,爾乃升天。』王重喜曰:『不早陣之,今已四月,始有雲乎?』對曰:『吾術本末。』王令國內黎庶並會,快大賞賜,酒樂備悉,(問:)『今日孰能獲神女乎?』民有知者,曰:『第七山中,有
兩道士,一名闍犁,一曰優奔。知斯神女之所處也。』王曰:『呼來!』使者奉命,數日即將道士還。”後文講述的,大致就是道士施妖術蠱縛天女獻給王,然後王的嫡孫如何如何慈仁賢明,勸阻了王的暴行,和天女談戀愛什麼的。
我們知道,古時候寫書的人,大多都是聰明人中的聰明人。既然後文有道士施妖術的故事情節,那麼康僧會為什麼不直接編是道士給國王出主意殺生祈福,而要說是國中佛教僧侶呢?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這叫“自暴其短,取信於人”。正因為早期佛教里這種僧侶不少見,所以康僧會要“自我批評”,親筆揭露出來,表示自己不會和這種人同流,同時自己並沒有因為信佛教就“護短”不寫,是相對客觀公正的。後來漢傳佛教發展得和藏傳佛教(特指解放前的)大相徑庭的源流,可以說從康僧會這里就初見端倪了。
聲與香
唐代道教著作《洞玄靈寶太上真人問疾經》中,列舉世間的聲和香時,出現了“童男童女聲”和“童男童女香”。即,不能將它們和其他的聲或香區分開來的話,就是耳朵或鼻子有疾病。其實,這兩個概念或許最早見於西晉·竺法護《正〈法華經〉》,後來影響了道家。
魂魄之說
《朱子語類》是宋代朱熹及其弟子、再傳弟子編寫的語錄類理學著作。其卷三談“魂魄之說”:“……耳目之聰明為魄,魄是鬼,魄是耳目之精,魂是口鼻呼吸之氣。眼光落地,所謂體魄則降也。”黃升卿在“鬼”字後面注曰:“某自覺氣盛則魄衰,童男童女死而魄去化。”先不論現代科學,我對黃升卿這句話的理解是:童男童女魄盛,所以耳目聰明、眼中有光;到了青壯年時,就氣盛而魄衰了,所以被人打壓一下氣勢,眼中就會無光。童男童女如果夭折,“魄”會逐漸“去化”。
佛經二
佛經中的羅刹女這種妖精,會奪取童男童女的精氣乃至吃人。南朝梁·僧伽婆羅《孔雀王咒經》:
“阿難復有八大羅刹女,飲血啖肉,惱觸於人,常守護菩薩入胎時、生時及生後時。雲何為八,其名如是:
牟訶阿矢摩等鳩釋棄枳矢尼甘蒲
侍阿蜜多羅虜喜多馱柯羅邏
此鬼飲血啖肉,常取童男童女及初產嫗家。
恒隨逐人,或入空處,或喚人名字。恒噏人精氣。無慈悲心,大可怖畏。此八大羅刹女有光明神通。以此大孔雀明王咒,常守護我願壽百歲。”
如此惡神鬼,卻有“光明神通”,可見早期佛教有多怪。後世漢傳佛教很少說“求羅刹女保祐”,都是想辦法怎麼敬而遠之,可以說是進步了。
此外,還有誘導童男童女說話,進行占卜預言的密法。唐代不空等人筆下是七八歲童男或童女,但宋元時流傳的則是十二歲。
姚秦·佛陀耶舍《四分律》卷五十三:
“如餘沙門、婆羅門食他信施,但作種種斗戲,或弓斗、或刀斗、或杖斗、或雞斗、或狗斗、或斗豬、或斗羖羊、或斗羝羊、或斗鹿、或斗象、或斗馬、或斗駝、或斗牛、或犎牛斗、或水牛斗、或斗女人、或斗男子、或斗童男童女;斷除如是一切嬉戲斗事。”“斗”可以作兩解,一是自己參與“斗”,二是觀看、挑逗另外兩方“斗”。
元·發合思巴《彰所知論》序:
“卻敵各有七樓。一一寶樓各七小樓。一一小樓各七池沼。一一池沼各七蓮華。一一華上各有七數童男童女。奏種種樂歌舞歡娛。”這里的“敵”大概是指“佛敵”。
個人學識有限,不再過多分析佛、道著作和海外著作中的“童男童女”。下一篇還是把關鍵詞換成“童男女”,然後看我心情寫吧。
2022年10月8日、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