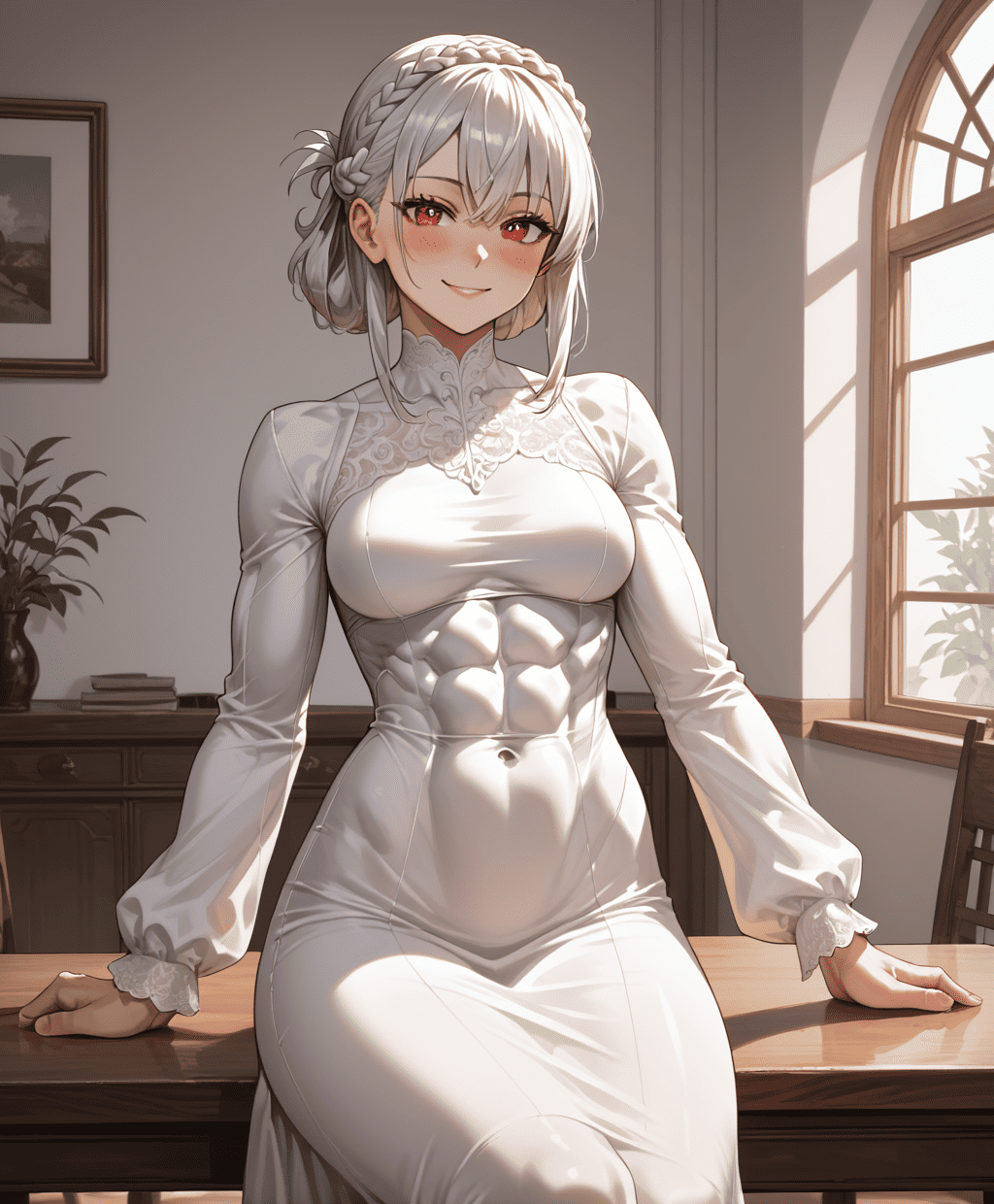今天是上元正節,路上行人反而比昨天少了些。
一來昨晚徹夜歡歌,二來要留著精神對付今晚的熱鬧,三來各處寺廟道觀今日廣賜福緣,街上倒是比昨天好走得多。
車馬駛入丹鳳門,在左金吾仗院停下,眾人步行入宮。
程宗揚回頭看了眼城牆上的燈樓,笑道:“大唐繁盛一至於斯。”
李溶道:“都是各地歷年進獻的貢物,仇士良拿來建了三十間燈樓,不知道有多少流到……”
“程侯可聽聞京師新詩?”段文楚插口道:“他鄉月夜人,相伴看燈輪。光隨九華出,影共百枝新。歌鍾盛北里,車馬沸南鄰……”
“好詩!”李溶撫掌道:“我近日也聽了一首:三五月華新,遨游逐上春。樓上看珠妓,車中見玉人……”
兩人打著哈哈一唱一和,程宗揚心下暗笑,偏不讓你倆得意!
李溶與段文楚口吐珠玉,程宗揚只當沒聽見,一臉好奇地問道:“是不是仇公公昨晚跟人打架了?”
兩人齊齊噤聲,面面相覷。
你們不知道?莫非這事被壓下去了,仇士良反應還挺快?
程宗揚又拱了把火,“聽說仇公公把田樞密使給打死了?”
兩人不敢再裝啞巴,齊聲道:“沒有!”
開什麼玩笑!
仇士良要是敢當街把田令孜打死,唐國干脆改姓仇算了。
“難道傳言有誤?”
“謠琢!”段文楚義正辭嚴地說道:“典型的謠琢!”
“哦,”程宗揚恍然道:“我說呢,幾個宦官怎麼可能這麼囂張?要是在我們漢國,早就打死了。張惲,你說是不是?”
張惲腰躬得蝦米一樣,“侯爺說得再對不過!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閹奴,早該打殺!”
兩人紛紛側目,你丫的可真不要臉啊,你們漢國太監的氣焰,不比我們唐國差多少吧?
不過話說回來,唐國還真缺個像你這樣,真敢把太監拖出去打死的權臣。
羅令閉緊嘴巴,緊跟在張惲身後。
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一個荒村客棧的雜役小廝,竟然有一天能進入皇宮,與朝廷的大臣、親王聲息相聞,甚至可能有機會一睹皇上的天顏,簡直就跟做夢一樣……
說話間,一輛香車自東邊的側門駛入內宮。
“咦?那不是安樂公主的車駕嗎?”程宗揚看著就眼熟。
李溶道:“上元節嘛,公主們來給各位太後敬賀。安樂這會兒才來,八成是起晚了。”
程宗揚好奇地問道:“宮里有幾位太後?”
段文楚道:“今上的祖母太皇太後,敬宗皇帝的生母義安王太後,今上生母積慶蕭太後,一共三位。”
“皇後呢?”
“自玄宗皇帝以來,宮中向不立後,如今主持六宮的是楊賢妃。”
難怪唐國的宦官勢大難制,你這是制度問題啊!
唐國只立太後,不立皇後,外戚難有出頭的機會,宦官少了掣肘,對付起科舉出身的官員,更是得心應手。
因此唐國有世家,有豪門,卻很少有世代勛貴的外戚家族,倒是出了一批仇士良這樣幾代宦官的權宦家族。
宴席設在清思殿,出乎程宗揚的意料,宴上一共只設了四席。
這種小范圍的宴會,分明是家宴的形式,不必像外朝大宴一樣恪守禮節,屬於關系很親近的私宴了。
上首一席是皇帝李昂的位子,主賓是自己,安王李溶與鴻臚寺少卿段文楚作陪,但程宗揚入宮已近午時,足足等了一個時辰,也不見李昂出來。
在席間服侍的是魚弘志,兩人在紫雲樓見過一面,此時舉茶奉酒,十二分的殷勤。
皇上遲遲未至,李溶和段文楚都有些沉不住氣,但還是勉強說笑著,盡到陪客的禮數。
段文楚覷空出來,揪住魚弘志道:“皇上呢?”
魚弘志苦笑道:“本來說好過來的,可前頭議事給絆住了。”
“什麼事能比這邊要緊?”段文楚壓住心底怒火道:“程侯可是身兼兩國正使!豈能輕慢?”
“少卿莫急,小的去前頭問問。”
魚弘志來到前殿,李昂正拿著一本書,心不在焉地看著。
“皇上,”魚弘志低聲道:“程侯已經等了一個多時辰了。”
李昂放下書卷,看著對面的鄭注,微微嘆了口氣。
鄭注道:“命宮中的舞伎去席間獻藝,把屏風設好,吩咐各宮,切不可一涌而入,輪番去看便是。”
魚弘志看著李昂,“皇上?”
李昂擺了擺手,“就這樣吧。”
魚弘志領命退下。
李昂放下書卷,“姑姑將來若是怪我,該如何是好?”
“程侯非是佳偶,況且已有正妃,太真公主以宗室之尊,豈能下嫁?”
“罷罷罷,就依卿所言。”
鄭注伏身拜倒,“臣這便前往鳳翔,李訓、韓約等輩不足恃,請陛下務必待臣入京,再行起事。”
“朕知道了,你去吧。”
鄭注再拜,“陛下保重。”
良久,李昂扭過頭,“窺基大師?”
窺基坐在屏風後,身著紫袍,膝上橫著禪杖,沉聲道:“時候尚早,再拖一個時辰。”
-----------------
堂上歌舞翩躚,李溶與段文楚賣力逗趣,倒也不顯枯燥,但程宗揚一坐快兩個時辰,說不著急那是假的。
李昂這是搞什麼呢?
把人請來,自己卻不露面?
難道是仇士良和田令孜突然斗起來,讓他焦頭爛額?
還是出了什麼大事,讓他分身不得?
程宗揚盤算著,要不要干脆裝醉罷席算了,眼看日影偏西,正主還沒出來,這要等到什麼時候?
曲樂聲中,忽然傳來幾聲低低的輕笑。
程宗揚不動聲色地往堂側瞥去,只見堂側正對著他的方向,擺了幾張白紗屏風,隱隱能看到人影晃動,似乎有人正在往這邊窺視。
再看李溶和段文楚尷尬的臉色,程宗揚突然間恍然大悟,這是相姑爺啊!
不用問,屏風後面肯定是三宮太後,六宮之首,外加湊熱鬧的諸位公主,借著家宴的機會,來看看哪位英雄好漢吃了獅心豹膽,敢娶太真公主?
幸好獨孤謂被留在外邊,不然光看臉,自己只剩給獨孤郎提鞋了。
長得不帥不要緊,只要氣質到位就行!
程宗揚挺起胸,瀟灑地拿起金樽。
在後面侍奉的張惲躬身捧起酒觥,給他斟上。
程宗揚一口飲干,然後肚腹鼓起,重重打了個酒嗝,聲震屋宇。
在李溶和段文楚驚詫的目光下,那位程侯張手抄起席上精心炙烤的乳豬,一口咬下大半。
曲樂聲中隱隱傳來幾聲驚呼。
程宗揚心下得意,自己這算是把楊妞兒的臉面給砸了吧?
讓你們見識見識什麼叫糙漢!
這要是不糙點兒,根本鎮不住楊妞兒那流氓!
霎時間,程宗揚如同趙充國、金兀朮、豹子頭、青面獸、敖潤、王忠嗣組團附體,風卷殘雲般將席上的酒肴一掃而光,吃不完的全都塞給袖子里的小賤狗。
一通猛吃下來,席上的玉箸少了一雙,金盤少了三只,連用來擺放看果的高腳果盤也沒了蹤影。
但這會兒滿席狼藉,根本沒人留意這些細節。
在場的大臣、親王、歌伎、後妃,有一個算一個,就沒人見過誰把御宴吃得這麼干淨徹底的,要不是桌子沒拿油煎過,說不定這位程侯能把桌子都給啃了。
程宗揚瀟灑地抄起巾帕擦了擦手,“再上一份!”
屏風後又是一陣驚呼,聲音明顯多了不少。
李溶和段文楚目瞪口呆,剛從殿外進來的魚弘志也看愣了,趕緊張羅著又送了一份酒肴。
那位程侯大袖一揚,赤手撈起盆中的肥雞,汁水淋漓地往口中一塞,再吐出來時,只剩一小截慘白的腿骨。
接著他抄起一根尺許長的蒸羊腿,“咔”的一聲脆響,像折黃瓜一樣,把羊腿骨一折兩段,仰首將骨髓一口吸盡。
等他舉起沸騰的銅鼎,准備往嘴里倒時,“嘩啦”一聲,屏風翻倒,一群女子推擠著跌倒在地。
最前面一個正是在長生殿見過的小美女安樂公主,看到程宗揚目光掃來,她不禁玉臉飛紅,掙扎著爬起來,轉身就跑。
其中一名年輕美婦倒是頗為從容,起身向程宗揚福了一福,然後掩口出門,到了殿外才放聲大笑。
那些女官、宮眷紛紛退下,接著外面笑聲響成一片。
程宗揚笑吟吟放下銅鼎,和藹地說道:“差不多了吧?再吃下去,天都快黑了。”
魚弘志沒趕上看前頭一段,這會兒人都快傻了,期期艾艾地說道:“程……程侯稍等片刻,聖上這……這便過來。”
“該看的都看見了,再等也沒什麼意思。”程宗揚一抹嘴,起身道:“改天再跟陛下喝酒吧。張惲,我們走!”
“程侯留步啊!”魚弘志道:“今晚聖上在城樓賞燈,與民同樂,邀請程侯同去。”
李溶與段文楚也趕緊上前相勸,但程侯看似步履從容,不緊不慢,可他們怎麼追都差了少許,連他衣角都摸不到。
羅令守在殿外,見主人出來,趕緊上前張開大氅。
程宗揚把大氅推到一邊,雖然小小地戲弄了宮里的貴人們一把,但李昂藏頭露尾的舉動,讓他心里難免窩火。
相姑爺你就好好相,我又不是拿不出手,用得著耗我一下午工夫嗎?
來到金吾仗院,天色已經昏黃,程侯躍上車,沒好氣地說道:“走!”
鄭賓甩了記響鞭,馬車緩緩起步。
剛出大明宮的宮門,他便看到韓玉立在外面,身後一名女子,正是驚理。
程宗揚心頭斗然一沉,顧不得周圍的目光,直接掀開車簾,“上來!”
驚理不言聲地躍入車內,然後屈膝跪倒。
看到她惶恐的神色,程宗揚眼前頓時冒出一片金星,咬牙道:“說。”
“紫媽媽入水之後,一直沒有露面。奴婢等了十個時辰,試著下水去找,可渭水泥沙極多,水面下遍布湍流,奴婢試了幾次,實在難以尋找。後來韓大哥帶人趕來,我們從兩岸一起搜尋,仍然無果。”
“說重點!”
“直到午後,渭水來了幾條船。”驚理道:“奴婢看到,有幾名鮫人從船上下水,潛入水底。”
“咔”的一聲,程宗揚手中玉佩捏得粉碎。
鮫人!
他只想著小紫水下無敵,卻忘了這個世界上還有鮫人!
和小紫一樣,能在水下自由呼吸,生活在海洋中的鮫人!
“你們怎麼會被人盯上?”程宗揚盯著驚理,眼中透出濃濃的殺氣,“是不是你!”
“回主子,紫媽媽出城時根本沒有掩飾,連奴婢都察覺到有人盯著。可紫媽媽說,要試試看能引出來多少盯梢的,免得他們打擾程頭兒。”
程宗揚心頭像被割了一記,痛得抽搐起來。
他掀起簾子,喝道:“去城外!”
鄭賓剛要打馬轉向,南方的天際突然間升起一點火星,然後在半空無聲地爆開,赤紅的光焰猶如流星四濺,在昏暗的天色中分外醒目。
街上響起一片歡呼聲,這是來自臨安的煙花,在長安極其少見。
程宗揚掀開車簾的手指僵住,望著那支煙花,渾身的血液都仿佛凍結。
那是自己家宅的方向,升起的煙花是內宅遇襲的信號,赤紅的光焰意味著敵人很強,警示眾人設法躲避,而不是來援。
張惲臉色煞白,“主子!”
程宗揚閉了下眼睛,然後道:“回去!”
-----------------
宣平坊,升平客棧。
“沒用的東西!”說話的是一名棕發紅髯的胡人,他靠在一張翠竹榻上,望著窗外的焰火,暗棕色的眸子流露出一絲惱怒。
一名白胖的商賈進來道:“是平盧的人露了行藏,被里頭發覺。”
“這些外藩的土狗!”那胡人罵道:“成事不足,敗事有余!龍宸的人呢?進去沒有?”
“總共進去三個。其余被前院的人截住,正在廝殺。”李宏道:“蘇執事,要不要我們的人也進去?”
蘇沙皺起眉頭,“黑魔海的人呢?”
“宮萬古帶著人去了安興坊,說在那邊截殺程賊。”
“混帳東西!”
提起黑魔海,蘇沙氣就不打一處來。
眾人合計誅殺程賊時,黑魔海各種激昂慷慨,姓宮的一副衝鋒在前的嘴臉,表示在洛都與廣源行發生衝突,純屬漢國方面的私自行動,絕不會影響雙方在唐國合作的大局。
並且聲稱已將事情經過稟報給教尊,漢國方面的負責人被勒令召回,接受審劾,一旦證實責任在己,必將嚴懲當事人,一查到底,絕不姑息!
蘇沙壓根兒就不信這幫人渣的鬼話!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有意無意將黑魔海放在外圍。
果然,黑魔海那幫人渣嘴炮打得山響,各方分派完人手,他們一點兒意見沒有,大大方方接了外圍觀風示警的閒差,然後一堆人就跟死了一樣,一點兒動靜都不帶有的。
“這是各方最終確定的購買清單。”李宏拿出一頁紙。
蘇沙不耐煩地擺了擺手。
上面的內容他已經看過無數遍,為此耗費的心血,比布局捕殺程賊還多。
為了分配程宅諸女,各方經過無數次爭吵,最後才勉強達成一致,同意由參與各方共同出資,公平購買。
具體金額根據各方角逐的結果,確定如下:呂雉:由十方叢林出價五萬金銖認購,同時聲明,待窺基大師渡化之後,送回漢國秉政。
此後獲益,由各方按照出資比例分配。
趙飛燕:由廣源行出價三萬金銖購下。
廣源行保證她從此之後不再出現,不會對漢國的政治格局產生任何影響。
趙合德:由魏博出價一萬金銖購買。
收歸樂從訓私房,同時敬獻給十方叢林一筆香油錢,延請密法大師,為其灌頂。
蛇嬈、罌粟女:合計作價三千金銖,由田令孜認購。
驚理:作價一千五百金銖,由龍宸認購。
孫壽:作價四千金銖,由周族認購。
義姁:作價一千金銖,由廣源行認購。
孫暖:由黑魔海出價五百金銖認購。
其余阮香琳、成光、尹馥蘭無人出價,各方商定,誰想要誰拿走,沒人要就殺了,如果拿走,則必須與其余諸女一樣,從今以後,絕不允許在市面上再度出現。
至於程宅可能存在,但不在名單上的女子,由各方競價。
最後也是最麻煩的一個,是程宅目前唯一所知的處女,小紫。
黑魔海在此事上盡顯攪屎棍本色,一會兒聲稱小紫是黑魔海已有物品,絕不同意認購交易;一會兒拿殤振羽那老賊來嚇唬眾人,聲稱那老東西二十年前就瘋了,而且越老越瘋,誰要敢買走小紫,保不定當天就得全家死光光;一會兒又表示黑魔海願意出一百萬金銖!
但必須要現貨,拿到人再出錢。
等眾人好不容易捏著鼻子同意,黑魔海又說太貴了,不如抓到之後大伙競價,底價就按孫暖的標准來。
蘇沙二話不說,當場拍了手印,這才沒給黑魔海那幫人渣再次翻轉橫跳的機會。
目前被各方認購的九名程宅女子,一共作價十萬金銖,收益由各方平分。
其中十方叢林購買的呂雉一人,就占了總額的一半。
其實十方叢林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但各方爭吵之後,一致認定不能超過五萬金銖。
不是各方願意給十方叢林那幫禿驢省錢,而是因為按照各方協定,將來通過呂雉獲取的收益,也按照同樣的比例分配,出資最高的十方叢林拿走一半,而黑魔海只花五百金銖買了個孫暖,拿走二百分之一的收益——數量雖然微乎其微,但意味著這事以後就別想甩開黑魔海,份額再少他們也是參與者,甚至在某些極端情況下,廣源行還真需要他們那百分之零點五的支持。
這事蘇沙想起來就膩味。
十萬金銖在廣源行眼里真不算大生意,要不是黑魔海私下串通惡意壓價,輕松能翻上四五倍。
再說了,對呂雉有需求的只是十方叢林和廣源行兩家,其余各方在漢國能有什麼利益?
難道唐國的宦官還想跑到漢國接著干?
當漢國那幫大臣是假的嗎?
還有魏博、平盧、淮西這幾家藩鎮,他們跟漢國都不挨著!
還能隔著別的藩鎮把手伸到漢國去?
就算他們能夠得著,漢國的世家豪強難道是吃素的?
最可恨的就是黑魔海這根攪屎棍!
一通亂攪,引來各方紛紛插手,最後偏偏他們占的份額最少,損人不利己,真不知他們操的什麼心思!
好在黑魔海只顧著偷懶,卻把命門忘在腦後。
蘇沙拿過購買清單,用指甲在孫暖的名字上劃了一道。
李宏心下會意,收起清單。
-----------------
程宅內,此時已經是血肉橫飛。
偷襲者避開實力強勁的前院,趁著石宅主人不在,護衛被借走的機會,從月洞門潛入。
把守月洞門的是一名星月湖大營的老兵,當袁天罡流著鼻血衝出來時,他已經被人用重手法擊斃。
此時南霽雲守在月洞門前,一柄鳳嘴刀刀刀見血,神擋殺神,佛擋殺佛。
吳三桂守在內庭的垂花門前,他手持雙矛,裸露著上身,雙臂金光燦燦,將偷襲者擋在階下。
敖潤蹲踞在主樓的飛檐上,挽起鐵弓,策應四方。
隨行的星月湖老兵有兩人護送阮香琳返回舞都,還有兩人與韓玉前往渭水,鄭賓負責駕車,此時留在院中的只剩五人,他們分成三組,兩人協助南霽雲,兩人協助吳三桂,另外一人則將袁天罡和賈文和擋在身後。
青面獸把皮甲扒到腰下,露出滿是鬃毛的獸軀,雙手揮舞著巨槌,一下一下轟擊著主樓的正門。
以主樓為界,整個內宅被一道奇異的光幕籠罩著,那道光幕呈半球形,半透明的表面上,隱隱有青綠的光澤流動。
當眾人察覺敵襲時,已經有三人闖入內宅,接著這道光幕便即張開,將眾人全都隔絕在外。
敖潤第一時間便已試過,這道光幕以天井為中心,覆蓋了整個內宅,而且防御力極其強悍,眾人一起動手,恐怕也要一刻鍾才能轟開。
而在這一刻鍾內,除非施法者解開禁制,否則內外隔絕,無論聲音還是光线,都無法穿透禁制。
也就是說,這段時間內,里面的人只能靠自己活下來。
若是以往,有蛇夫人、罌粟女、驚理三名侍奴,再加上中行說和小紫,偷襲者再多上十名八名,也未必能討得了好去。
然而此時,內宅只剩下一個中行說,其余全是女子:飛燕合德姊妹,四名奴婢,孫暖、孫壽、成光、尹馥蘭,以及呂雉和那個不能動彈的波斯胡姬。
三名偷襲者在這個時候闖入內宅,不啻於虎入羊群。
賈文和盯著那層光幕,眼神冷厲駭人。
這道光幕完全在他計劃之外,一舉將主公的姬妾置於絕境。
旁邊的袁天罡鼻血流得滿臉都是,這會兒坐在地上,緊抱著老賈的大腿。
光幕內一片幽暗,宛如深夜提前降臨。
趙飛燕與趙合德握著手坐在床邊,屏住呼吸,不敢發出一絲聲音。
黑暗中忽然傳來一聲尖叫,接著腳步驀然響起,有人緊追著那聲尖叫往天井掠去。
趙飛燕一手與妹妹相握,一手撫著小腹,手心里滿是冷汗。
她剛才與妹妹正說著話,一邊翻看嬰兒衣服上用的花樣,商量著是用小兒撲蝶,還是用龍紋的圖案,好體現夫君大人的威儀。
突然間,前院有人叫道:“刺客!”
緊接著,天色便猛地黑了下來。
那聲尖叫逃到天井,猛然拔高,接著像被利刃斬斷一樣,戛然而止。
腳步聲踏上樓梯,踏入走廊,然後“呼”的一聲,有人吹亮了火褶。
那人站在廊內,開口道:“我念到名字的,乖乖出來,饒你們不死。”
他的聲音又濕又冷,就像毒蛇一樣往人耳內鑽去,令人渾身的血液都仿佛凝固。
“阮香琳。”
樓內一片寂靜。
“成光。”
趙飛燕緊緊咬住嘴唇。
“尹馥蘭……唔,這個就是吧?”
那人拖起尹馥蘭的長發看了一眼,“美人兒,你沒人要,就歸我了吧。”
火光在窗上晃動著,映出一個光頭的輪廓,他伸出長長的舌頭,在尹馥蘭臉上舔了一記,發出夜梟般淒厲的尖笑聲。
尹馥蘭穴道被制,她顫抖著想擠出一個討好的笑容,淚水卻嚇得滾了出來。
那人白布芒鞋,相貌俊美,頭頂光禿禿的,卻是一名僧人。
他用力一摟,將尹馥蘭圈在臂間,然後繼續念道:“孫壽。”
“孫暖。”
那僧人陰冷的聲音從廊內傳出,又在不遠處被擋回,帶來陣陣回響,愈發讓人毛骨悚然。
“都不在嗎?”那僧人陰聲道:“一會兒若是被貧僧逮到,可就沒有這麼好的事了。待貧僧用過你們之後,便將你們的頭顱砍下,掛在程宅的大門外。至於屍身……”
“桀桀……”那僧人發出怪笑,“待貧僧拿來充飢,也不負了你們的冰肌玉骨,雪膚花貌。”
尹馥蘭美目猛然睜大,露出痛楚的表情,卻是被他張口咬住耳垂,生生將她的玉墜從耳垂扯落。
雪白的耳垂當即被豁開一道口子,鮮血滾滾而出。
那僧人咬著沾血的玉墜笑了起來,看著一行血跡順著美婦的雪頰流到腮下,露出欣賞的目光。
“噗!”那僧人將玉墜吐到尹馥蘭痛叫的口中,繼續念道:“趙合德。”
回答他的只有沉默。
“趙飛燕。”
“呂……”
那僧人剛念出一個字,旁邊房內猛然傳來一聲悶響,靠牆的床榻被一只大手翻了過來。
躲在床下的成光喉嚨一緊,被擰著脖頸,提到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