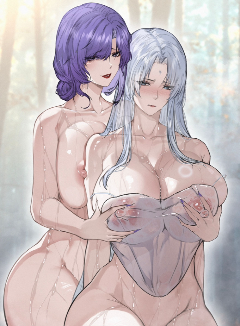第19章 背叛
十公主的侍女被引到了偏殿的側間,只因皇帝不讓人在正殿伺候,數十號人都在屋里候著,等李望的傳喚。
那個引路的小太監本想著溜走,卻被李望攔住了,說是他留在這里等著伺候。
但攔下了他,李望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他就這樣被晾在了一邊兒,也沒活干,搭手他人也被躲開了。
此刻正惴惴不安著立在角落,不住地冒冷汗,裹挾著微微寒意的夜風讓他偶爾打戰,牙齒也在抖擻。
侍女冷眼旁觀著,也不出聲,也沒人與她這個失了勢的公主的婢女搭話。她只靜靜坐在下人用的馬扎上,打量著屋里來來去去的奴仆們忙碌著。
屋里就他們兩個閒人,一個心中有事,一個無聊沒事,竟也搭不上話。
酉時末,外頭傳話說讓人去收拾正殿,小太監忙趁著這個由頭就要往外趕要去找自己的師傅,不想衝進來兩個大力太監,不由分說一把將他架住了就往外走,小太監懵了一下馬上猛力掙扎起來,呼喊道:“放開我!放開我!你們要把我帶到哪里去!我可是御前的人!”
兩個大力太監朝他一笑:“公公這話什麼意思,見著我們您難道還不知往哪去呢?”
小太監目眥欲裂,他當然知道這兩個太監是哪處的,他們可是慎刑司,責罰有罪宮人的司刑太監!
那地方進去一趟不死也要去了半條命,想到自己就要這麼交代了,不由得上下俱泄,哭嚷著要饒命。
侍女見他年紀尚小,今天那一出怕不是被人當了槍使,怎地就要了命去,連忙跟著走到門前替他說話求情:“兩位公公且站一站,這是要去哪里一處?李公公剛才叫人來傳話,要這位小公公候著伺候陛下呢。”
兩個大力太監打量了她一番,見她穿著打扮並不似宮里人,心下知道這是十公主身邊的人,便放了幾分尊重:“姑姑好,原就是李公公叫我們兩個來拿了他去,說他犯了陛下的忌諱,做錯了事,可不是應罰的嗎?”
侍女知道是皇帝的意思,不敢再置喙了,又聽其中一個大力太監道:“陛下與十公主剛用完了膳,小人領完陛下的命時,十公主正用茶,插嘴說要喚姑姑過去交代些事。”
侍女聞言點了點頭,不在理會小太監的事情,叫住了個宮女帶路,往正殿里去。
撥開珠簾卻只見屋內仆從雖多,手上都有著事,在宮門處有一面之緣的李望拿著拂塵,正站在暖閣門前,見侍女進來連忙迎了上去:“姑姑可來了,等您半天了。”
“不敢當,還請公公通報一聲。”侍女福了半身算還了禮,垂手立在門口等著李望出來傳她。
不多時李望引了她進去,侍女低著頭不敢亂看,這位新皇雷霆手段連著處置了自己主子的丈夫與公公,威名赫赫,所以戰戰兢兢,只盯著自己的腳指頭。
見李望回完了話出去了,連忙跪下磕頭行禮:“奴婢給陛下請安。”
“起來吧。”說話的卻是十公主,侍女抬起了頭卻只見暖閣里只有十公主坐在紅桃雕花的搖椅上,姿態十分放松,“這里沒別人,怎麼行這麼大的禮?”
侍女見只有自己主子,那根繃著的筋也放松了下來,小步走到了十公主身側給她揉肩:“嚇死奴婢了,奴婢以為還有陛下在,可不敢失了禮數,丟了咱們公主府的臉面。”
十公主搖了搖頭,讓她不用再揉了,讓她到自己面前,盯著她的眼睛:“今天領路的小太監被拿去了?”
侍女點點頭,十公主又道:“今夜陛下賜恩,讓我在宮里住一夜,你先帶著母親給的東西和人回府去。但是出宮前,我有件事讓你去辦。”
見十公主勾勾手,侍女彎腰湊上前去聽,主仆兩嘀咕了半晌,侍女領命去了,留十公主一個人緩緩躺在搖椅上兀自出神想事。
皇帝更完了衣進門就看到一幅美人和衣春睡的景色,心下稍悅,放輕了腳步挪到了搖椅旁,突然起了頑心,蹲下身子伸手慢慢抽出她頭上的朱釵。
那朱釵本就綰著十公主的發髻,一天奔波下來已是松動了,待皇帝完整抽出時青絲就跟著散落下來。
皇帝將她的朱釵收入囊中,見她睡得如此之沉,竟這樣還未醒,便湊上前去吹動她的發絲。
十公主半夢半醒中只覺得面上癢癢的,拿手擺了擺反倒被人一把抓住了,緊接著就是熟悉的濕軟物舔弄著她的手背。
她知道來著何人,嘆息了一聲該來的還是得來,睜開了眼睛側頭看他:“陛下就這麼喜歡舔啊。”
他輕笑一聲,拉著她的手摩挲著,卻不接她的話:“皇姐累了,洗漱了就與朕歇息吧。”
十公主剛剛醒過來,腦袋有點迷糊,起身就要去時才想起他說的最後一句,轉過身來擰著兩條秀眉道:“陛下這話何意?毓敏只答應了留宿宮中,並未答應與陛下你同眠。”
皇帝愜意地躺在她剛剛坐著的搖椅上,眉眼含笑著看她:“皇姐這話可差,現如今這闔宮上下朕哪里去不得,更何況朕只是想著與皇姐親近親近,又有何不妥呢。”
十公主輕輕啐了他一口這些無賴話,扭頭去洗漱了。
回來時只披了一件薄薄的外袍,內里是貼身的褻衣褻褲,腳上也換了睡鞋,釵環都卸下了,清素一張臉,頰邊飛上被熱氣烘出來的紅霞,比之白日里多了些裊娜的柔軟光彩,直叫人想親近。
皇帝正坐在暖閣的茶案前看奏章,聽到響動抬起頭來看得有些呆了,與之前溫泉歡好時不同,此時的十公主像是一只拔了刺的刺蝟,神態間柔和了不少,她年紀不算大,嫁做人婦已經五年多,與待字閨中的小姐們更多了一分成熟女人的風韻。
浴後宛如一只夏日剝了殼的新荔,從衣物里露出的些許白生生水靈靈的皮肉像是等待著誰來咬一口似的。
十公主才不管他怎麼打量自己,徑直走到暖閣里熟悉的床榻邊,將外袍褪下,就要躺下。
皇帝見狀連忙放下奏折,快步走到她身邊接她的外袍:“朕來吧。”
她掃了他一眼,沒有答話,理所應當地躺下了。
皇帝將她的外袍掛在了床邊的龍頭雙面黃花梨衣架上,轉身見她已經合上了眼,心里有一點點不舒服,將鞋脫了也上了榻去推她:“皇姐不好奇朕晚膳時提到的事嗎?”
十公主不耐煩地睜眼,見他一副快問自己的樣子,覺得好笑,撐起了身子靠在了床櫃上好整以暇地看著他:“陛下能與毓敏談的,不外乎三件事,一是侍衛長,二是駙馬,三是與我的床笫之事,不知陛下要說哪件呢?”
皇帝摸了摸鼻子咳嗽了一聲:“皇姐還真是玲瓏心思,朕想說的就是關於皇姐的侍衛長的事。”
“陛下都將人替毓敏處置了,現在才告知緣由?”她挑眉諷刺道,“陛下做什麼毓敏哪里有機會置喙呢?”
皇帝知道這件事自己操之過急了,她有些惱了,連忙跳下床到外間的書架暗格里拿出一封信和一塊印章,疾步走回床榻前,將手里的東西遞給她:“皇姐看後再怪朕吧,朕那時氣急了才忍不住將人砍了,早知皇姐會生氣,朕就應該留他一條狗命。”
十公主抽出信,展開一看,是侍衛長的筆跡,仔細一看侍衛長竟然細細寫了早年何德與何相的幾樁舊案,附帶上了說她與何家一體同心,對皇帝有不臣之心,何德在府里豢養了眾多逾制的奇珍鳥雀,公主見之不報,而隨信附上的物證則是當年何相私刻的仿傳國玉璽印章,都是大不敬之罪,信尾更是借了曹操的名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來表達自己對新帝的投誠之意。
十公主越看越氣,沒想到自己五年來看重的、寵愛的竟是如此狼心狗肺的貨色,自己只被扣在宮里幾天就這麼迫不及待地另尋新主,氣得雙手微微顫抖,最後一把將信撕碎,連聲冷笑道了幾句好:“好,好得很,毓敏竟不知道侍衛長竟有如此大志向,想來陛下應該好好賞他,這可是有功之臣,為何又將他殺了呢?”
“皇姐怎麼能這麼揣度朕,”他憤憤道,爬上了床榻靠近了直視著她的雙眼,“一個不忠心的玩物,朕只是不高興他竟敢如此對皇姐,朕替皇姐不平。”
十公主氣紅了眼睛推他:“陛下好一張利嘴,三言兩語就成了替毓敏料理不忠心的奴才,可有問過毓敏到底怎麼處置嗎?還是說陛下想要借著侍衛長敲打毓敏什麼?”說著與他扭打著就要下床穿鞋。
皇帝見她要走,慌里慌張地去撈她,摟住了她的腰肢就不放手:“皇姐別動怒,此事是朕做錯了,朕不該饒過皇姐直接插手你府里的事,皇姐原諒朕吧。”
十公主恨恨錘了他手臂兩下,心里暗道:我管侍衛長這白眼狼怎麼死的,但是不借著他好好泄口惡氣,我這公主倒也白當了。
她仍用力想要掰扯開他摟著自己的手,嘴里氣憤道:“陛下真的做錯了,在我府里布下的探子難道還少嗎?”
皇帝將她拉近自己,低頭去吻她氣紅的面頰,討饒道:“朕放探子在皇姐身邊,絕不是想要害皇姐,只是保護皇姐而已。”見她不雅地翻了個白眼,手上的動作卻停了,心里覺得自己的皇姐真是好哄,真是可憐可愛,又得寸進尺地去咬她的耳垂,直咬得人吃痛掙扎起來才罷休,“誰知皇姐與駙馬可真是恩愛,出了宮轉身就將弟弟忘了,與駙馬柔情蜜意,分都分不開。”
十公主轉身雙手抵著他不給他親,偶有抵抗不得被他啄吻到敏感的頸間,忍著癢意道:“陛下說得輕巧,毓敏自有侍衛隊護著,就不勞陛下費心了,陛下還是撤走他們吧。”
皇帝嘴上連聲敷衍著,轉過了話題,吃醋道:“皇姐對何德那樣的廢物還日日事必躬親,侍奉湯藥十分殷勤,聽聞何德一日大鬧不肯吃藥,還是皇姐親自去哄去勸才好的呢。”
十公主聞言哼聲道:“人現在已經被你流放了,西南那地方去了凶多吉少的,我身邊就只你一人了,你還到處亂找由頭撒氣。”
聽得十公主像是氣頭稍降,他又得起意來,心猿意馬間手也攀上了她的蜜處和雙峰,胡亂揉弄著,她被他這一通揉搓身體也起了熱潮,閉上眼勸慰自己只當身後是一根活著的取悅自己的玉勢罷了,不值得生氣。
皇帝的下身也漸漸抬了頭,硬硬地抵著她的肉臀,她低低地呻吟出聲,下身涌出了些許熱流,皇帝卻倏然停手,摟著她躺倒在床上,眼睛亮晶晶的,紅潤的薄唇春光無限:“皇姐,睡吧。”
十公主被他這樣不上不下地吊著,心下不快,身體也難受著,尚存的神志與廉恥卻不允許她主動向自己的親弟弟求歡,只好憤憤躺下,調轉身體用背對著皇帝,就這樣睡去。